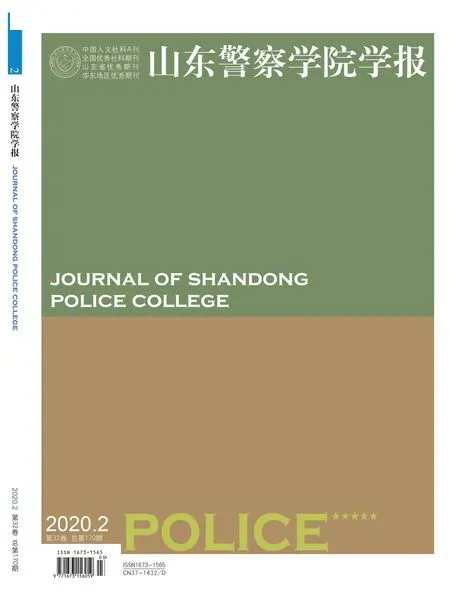论侦查取证质量的提高途径
——基于取证之实体层面的分析
2020-02-23李尧
李 尧
(中国政法大学司法改革研究中心,北京 100088)
证明力是对证据与待证事实之间关系的重要评价,“是一种以经验为基础的说服力”[1],对裁判者认定案件事实至关重要。侦查取证的主要目的之一,是收集具有足够证明力的证据,支持控方在审判中完成证明活动。在以往司法实践中,“存在办案人员对法庭审判重视不够,常常出现一些关键证据没有收集……进入庭审的案件没有达到‘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法定要求,使审判无法顺利进行”[2]的情况。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要求贯彻证据裁判与庭审实质化,在证据裁判规则下,实质化庭审的核心是质证。要改善以往粗糙取证影响实质审判的问题,健全并保障刑事证据的证明力,充分发挥质证活动对案件事实查明的重要作用,使犯罪者受到应有惩罚、(1)在刑事审判愈发注重人权保障的背景下,疑罪从无在司法裁判中的阻碍日益减少,“证据不足作无罪判决”作为一项明规则取代了“证据不足作留有余地判决”的潜规则。参见李玉华.刑事审判人权保障40年:理念、制度与细节[N].人民法院报,2018-09-12(05).而在党的十八大以来的5年中,各级人民法院“落实罪刑法定、证据裁判、疑罪从无等原则,对2943名公诉案件被告人和1931名自诉案件被告人依法宣告无罪”。参见周强.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2018年3月9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N].人民日报,2018-03-26(02).由此不难推知,若因侦查主体取证质量粗糙致使庭审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则势必对准确、有效打击惩治犯罪产生消极影响。无辜者受到法律保护,就必须正本清源,在侦查阶段努力从实体层面(2)之所以强调“实体层面”,是因为取证质量还包括“程序层面”,即以规范合法的取证程序保障证据能力。尽管实践中这两个层面常有交织,但在理论上可以对二者进行概括式区分,而“程序层面”的质量并不在本文研讨范围之内。提高取证质量,从而有效保障庭审证据具备足够的证明力。而且,在检察介入侦查的常态化机制相对缺乏(3)尽管在一些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大要案件和某些地方性审前程序实践中已经出现了检察介入侦查的做法,但其并不普适。对于检察介入侦查的案件范围、尺度深度等,亦未达成理论与实务上的普遍共识。参见刘子阳,等.检察机关频频提前介入热点案事件引关注 专家建议增强检察官有效引导侦查能力[N].法制日报,2018-09-05(03).的现实背景下,侦查主体切实保障取证质量,对于减少刑事程序倒流、(4)对我国刑事程序倒流现象的具体分析,可参见汪海燕.论刑事程序倒流[J].法学研究,2008,(5):129-138;陈瑞华.司法体制改革导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8.307-310.提高诉讼效率具有重要意义。另外,随着境外追逃追赃工作的深入开展,取证随意、证据粗糙等问题已成为制约外逃犯罪嫌疑人成功引渡的重要障碍之一。(5)有关案例可参见黄风.中国境外追逃追赃:经验与反思[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133-142.提高取证质量,使证据体系满足相应证明标准,能够令我方的引渡申请更多地得到境外司法机关认可。鉴于此,本文试图以证据全面性要求与“排除合理怀疑”标准为指引,探赜提高侦查取证质量的具体途径,引导和促进取证者“以全面、细致的取证工作,确保证据体系对全案事实的综合证明力,为控方在庭审中有效举证、证明犯罪奠定扎实基础”[3]。
一、证据全面性要求指引下的取证质量提高途径
(一)证据全面性的基本要求:从刑事案件的结构要素展开
刑事案件的结构要素包括“何事”、“何时”、“何地”、“何物”、“何情”、“何故”、“何人”七项。(6)区别于刑法学意义上的犯罪构成,这里的“结构要素”主要出自对刑事案件侦查实践的总结。参见张鹏莉,陈士渠.刑事案件侦查[M].北京:群众出版社,2010.6.以“七何”结构要素为标签开展取证,有针对性地收集相关证据,可为形塑证据体系、全面证实犯罪奠定充分基础。
“何事”指事件性质。发生严重侵害法益的事件后,须先明确其是否为刑事案件。在看似意外事件,如自杀、单人交通事故的情况下,尤应注意甄别是否存在涉嫌犯罪的线索、证据,避免误将刑事案件定性为意外事件。
“何时”指犯罪时间。在传统刑事案件中,要着重收集现场上能表明时间的证据。在网络犯罪案件中,应联系网络服务提供者,收集含有犯罪信息之数据包的网络收发时间记录。锁定嫌疑人后,还要进一步收集证据,判断其是否有作案时间。
“何地”指与犯罪密切相关的空间。传统犯罪空间中蕴藏着大量证据,勘查犯罪现场、辨认作案现场、搜查可疑处所都是取得实物证据的重要途径。网络犯罪案件存在虚拟空间,其中的电子数据须以专门技术与法定规则提取;网络犯罪案件的物理现场由犯罪嫌疑人设备终端处、受害人设备终端处和网络服务器所在处所构成,要针对3处现场的软硬件及周边予以取证。(7)这仅是一种理论性的表述,在云存储环境下,实际上很难确认涉案数据究竟位于哪些具体处所的服务器之上。
“何物”指与犯罪密切相关的物品,涵盖大部分宏观物证与微量物证。洛卡德交换原理指出:“无论何时,只要两个物体互相接触,总会伴随物质的转移。或许侦查方法的灵敏程度不足以揭示转移过程;抑或转移过程所留证据的衰减速率是如此之快,以至于一定时间后它们都消失了。但是,物质转移确实已经发生。”[4]微量物证通过物质转移留在犯罪现场,虽易于灭失而难于发现,却对揭示犯罪事实具有重要作用。
“何情”指犯罪行为过程及具体情节。犯罪是动态的过程,“在嫌疑人寻找、接近、侵害直至离开目标所遗留的一系列印迹中,载有丰富的犯罪活动状态信息”[5]。收集反映犯罪过程的证据,可回溯性地重建案件现场、复原案件细节。
“何故”指犯罪目的、动机。收集关于犯罪目的的证据,可证实犯罪的主观方面。通过发掘证据细节探寻犯罪动机,可深入揭示案情脉络、明确犯罪目的。
“何人”指犯罪嫌疑人。通过收集现场物证、监控录像、被害人陈述与目击者证言等证据,结合犯罪时间、地点、手法等对犯罪嫌疑人进行特征画像,逐步缩小排查范围。待犯罪嫌疑人到案后,以收集到的人身同一认定证据及人身辨认程序,进一步确定其作案可能。
此外,收集无罪或罪轻证据也是确保证据全面性的基本要求。在某些刑事错案中,“由于侦查人员主观地认为抓到的嫌疑人就是实施该犯罪行为的人,所以就只去收集能够证明该嫌疑人有罪的证据,不去收集能够证明该嫌疑人无罪的证据,甚至对于已经发现或者由嫌疑人及其家属提供的无罪证据也有意无意地忽视了”[6]。当前的刑事政策已经由单纯强调惩罚犯罪逐步转向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为预防错案,取证主体应一视同仁地收集无罪或罪轻证据,切不可忽视无罪线索,更不可在“有罪推定”的惯性思维下有意无意地排斥无罪证据。
(二)现场勘查中的全面取证
有论者指出:“要弱化口供在案件侦查中的作用。在司法实践中,‘有罪推定’、‘口供至上’的陈旧观念仍然没有得到有效克服,一些案件的侦查活动主要还是围绕取得口供来开展的,有的是先‘突破’口供,再根据供述线索去寻找其他证据,有的是‘突破’口供后就万事大吉,疏于收集其他证据,有的则不能正视、排解供证之间的矛盾,甚至将错就错。这既是刑讯逼供屡禁不止的重要诱因,也是造成一些案件被告人翻供后难以处理的重要原因。”[7]淡化口供则更应重视实物证据,犯罪现场是绝大多数案件获取实物证据的起点与主阵地,做好现场勘查是全面收集证据的基本保障。
全面收集实物证据的首要前提是及时到场。有专家曾估计,“3分钟赶到现场,破案率达2/3,10分钟赶到达1/2,半小时赶到要降到1/3”[8]。毋庸置疑,若不能及时到达现场并加以保护,现场蕴含的证据很可能遭受人为或自然因素破坏,从而失去全面取证的良机。现场勘查人员应按照不同的业务分组,各司其职、分工配合,遵照现场勘验检查规范全面、仔细地收集、提取各类证据,对证据和案情进行初步梳理和筛查。随着犯罪嫌疑人反侦查意识的增强和侦查主体取证能力的提高,除了收集传统宏观物证外,现场勘查更要重视收集“状况证据”和微量物证。
1.对状况证据的收集
“状况证据,是指犯罪现场中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物品、痕迹、尸体、伤体等有体物的存在状况、变动情况和相互关系,以及温度、光线、烟火、气味、时间等非静态实体的理化现象”[9]。在某些案件中,状况证据是破案的关键,其证明价值不容忽视。但是,状况证据在现场的存在形式相对隐蔽,且通常需要结合精巧的逻辑推理方能发现其证明案件事实的作用。因此,它们容易被取证者忽略而无法发挥应有的证明价值。状况证据主要有以下两类:
一是有体物的存在状况、变动情况与相互关系。收集此类证据需要取证者具备丰富的勘验经验、推理与想象能力,能集思广益、通过事物的普遍联系获取启发,深入追溯看似孤立、无证明价值的现场状况背后可能存在的因果与联系,并将其复原为状况证据。例如,在对某起入室杀人案的现场初步勘验中,勘验人员未能提取到有价值的人身同一认定证据。之后,勘验人员发现现场房屋后门一盏外观完好的灯不亮了,于是推测可能是犯罪嫌疑人入室前故意将灯泡拧松,以令其无法亮起。勘验人员检查灯泡,果然从上面提取到若干枚指印,并由此缉获犯罪嫌疑人。[10]
二是各类非静态实体的理化现象。此类现象常稍纵即逝,即所谓“暂时性证据”。这类证据是“基于自身的性质而言具有暂时性的特点并且很容易改变或消逝的证据。常见的暂时性证据包括气味、温度、暂时存在的痕迹以及一些生物和物理现象”[11]。若勘查人员未能及时意识到这些现象的证明作用,就有可能彻底失去取证机会。例如,现场发现一只水杯,应观察其中是否盛水,确定水温如何;进入现场后闻到异味,应在气味消散前加以注意并记录。
总之,寻找状况证据要有效利用经验、推理与想象,并充分调动五感;(8)“如经视觉(对犯罪现场、尸体位置、伤口、血迹、指纹、足印等的观察)、听觉(吵闹的投币式音乐自动播放器)、嗅觉(腐烂的食物、未加掩盖之肥料坑穴)、触觉(刀刃的锋利程度)等。”[德]克劳思·罗科信.刑事诉讼法[M].吴丽琪,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268.发现状况证据后应及时将其提取固定为法定证据形式。
2.对微量物证的收集
微量物证,是指“案件中提取的体小量微,能以其自身结构、属性证明其与受审查的人、事、物、时、空等内容存在客观联系,从而证明案情的一切物质性客体”[12]。基于两方面因素,微量物证在取证实践中愈发受到重视:“由于传统的刑事侦查手段已为犯罪嫌疑人所熟悉,在案件现场已经越来越难以提取到指纹、脚印等可对罪犯进行直接认定的痕迹物证,案件侦破工作对微量物证的需求不断增加。另外,随着当代科学技术尤其是仪器分析技术的发展,以仪器分析技术为基础的微量物证检验技术也得到快速发展。”[13]
为有效收集微量物证,第一,依据洛卡德交换原理,须重点检查客体发生接触的位置,确定是否有微量物证残留。例如,在嫌疑射击者袖口处寻找火药颗粒,在嫌疑肇事车辆碰撞位置寻找车漆颗粒或服装纤维。第二,留意宏观痕迹上是否附着微量物证。例如,在一起杀人案中,从现场遗留的足迹上提取到面粉成分,而犯罪嫌疑人最终在现场附近一家面粉厂被缉获。[14]第三,对于在现场提取的可能含有某种具备证据价值的微量物证的物质材料,尚须借助仪器分析确定具备证据价值的微量物证是否存在。例如,在爆炸现场提取的尘土中分析炸药成分,以推断爆炸物种类。
然而,在重视收集微量物证的同时,应对其形成与转移过程作正确分析,“避免出现因为忽视物证的形成经历过多次作用而错误关联物证与待证事实之间的联系的情况”[15]。例如,在美国法庭科学会披露的一起案件中,因在杀人现场提取到一位流浪汉的DNA,他被指控谋杀一名硅谷富豪,可能被判死刑,但其也有“案发当晚因醉酒入院治疗一夜”的不在场证据。经后续查证,流浪汉的DNA系在其醉酒入院时先转移到救护人员身上,然后由救护人员无意带到谋杀现场的。[16]
必须指出的是,证据保管链是收集实物证据不容忽视的重要方面。根据布莱克法律词典,证据保管链是指“从获取证据时起至将证据提交法庭时止,关于实物证据的流转和安置的基本情况,以及保管证据的人员的沿革情况”[17]。国内外许多知名争议案件均是在证据保管链上出现严重问题,导致已收集的关键实物证据来源不清、流转不明,或被污损、篡改甚至遗失,从根本上动摇了证据证明力,最终令被高度怀疑有罪的人无法被定罪或无辜的人被判有罪,(9)有关案例可参见李雅健,郑飞.乱象与规制:中国刑事证据保管制度研究[J].证据科学,2019,(1):35-52.酿成了错案。为从根本上避免此类问题,在发现并收集到实物证据后,每个证据操作和流转环节的经手人都要依法依规妥善记录和保管证据,努力确保到审判时实物证据保持客观原始、可以溯源,进而有效发挥证明力。
二、“排除合理怀疑”标准指引下的取证质量提高途径
证据体系又称证据锁链,“在缺乏直接证据的情形下,据以定案的全部间接证据必须环环相扣,形成完整无缺的证明体系……因各种间接证据如同链条相接、不可脱节,故称‘证据锁链’。如果这种证据锁链中有一环不能吻合,或有疑问,就不能据以定案。否则,就可能造成错案。在运用间接证据定案时,必须对全部证据进行综合审查判断,只有在查证属实形成完整的证据锁链时才能据以定案”[18]。由于直接证据通常表现为言词证据尤其是口供,而口供的证明力受法定限制,故几乎所有案件均须构建证据体系。在侦查终结时,就应初步形成满足一定标准的侦查证据体系。
“无论我们今天如何强调、抬高法律程序的本体性价值,但面对现实世界中大量发生的刑事案件,在高度形式化的程序规则之下,居于整个刑事司法制度起点而具有最基础性意义的,仍然莫过于司法人员在侦查勘验、搜集证据、发现事实、形成判断这一系列活动中的对事实问题的认知过程。”[19]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以往某些司法实践中,“法庭审判不过是在侦查人员调查工作的基础上,沿着侦查人员的思路,对案件事实做出进一步的审查和确认而已”[20]。可见,关注侦查证据体系的构建,就是关注对全案事实整体认知的起点。从起点把关,探赜提升侦查证据体系质量的途径,有助于避免刑事司法在运行中出现“起点错、跟着错、错到底”的错案径迹。
“排除合理怀疑”源于西方刑事司法传统中的证明标准。2012年《刑事诉讼法》将其正式引入我国刑事证明标准规范体系,属于“中体西用”的立法模式。(10)对我国刑事证明标准“中体西用”立法模式的深入思忖,可参见李训虎.刑事证明标准“中体西用”立法模式审思[J].政法论坛,2018,(3):127-141.根据立法者的解释,“‘排除合理怀疑’是指对于认定的事实,已没有符合常理的、有根据的怀疑,实际上达到确信的程度”[21],法官认定事实所依据的证据体系必须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排除合理怀疑”既是目的论又是方法论,亦即,它既是审判中的证明标准,又可参照作为侦查中的取证标准。这是因为,它“不仅指出了证明目的即证明应当达到的状态要求,而且指出了达到这种目的状态的方法”[22]。《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第2条第2款规定:“侦查机关、人民检察院应当按照裁判的要求和标准收集、固定、审查、运用证据,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认定证据,依法作出裁判。”根据与2012年《刑事诉讼法》配套出台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侦查主体应围绕“排除合理怀疑”的取证标准,构建“排除合理怀疑”的侦查证据体系。(11)参见《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66条。质言之,对侦查取证质量而言,全面收集证据是“量的积累”,而构建“排除合理怀疑”的侦查证据体系则是“质的提升”。
(一)“牵强取证”与侦查取证中的“排除合理怀疑”之祛魅
构建侦查证据体系,就是组构以实物证据为主、言词证据为辅的闭环证据锁链。要防止出现侦查证据体系在形式上“排除合理怀疑”,却在实体上错误认定事实的情况,就应当在构建过程中避免“牵强取证”——在全案证据不足、难以排除合理怀疑的情况下,坚持对到案犯罪嫌疑人的有罪假设,再根据“排除合理怀疑”的“需要”强行“设计”证据链条,并依此“设计”牵强收集证据的行为。
传统刑事案件侦查多遵循“由事到人”的模式,侦查主体对犯罪嫌疑人“人选”的确信可谓是在案件事实认知过程中的“惊险一跃”:一旦该环节出现偏差,牵强取证就有可能乘虚而入。例如,侦查人员首先发现犯罪现场,又阴差阳错地锁定了实际无罪的“犯罪嫌疑人”,因已有证据不足以形成“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据体系,就以种种身心强制手段迫使“犯罪嫌疑人”指认现场,取得关键的“指认笔录”,直至酿成错案。“越是冤案,其事实认知的任务往往就越是艰巨。”[23]同样,越是重大、复杂的案件,稍有不慎则更容易出现事实认定错误。所以,在重大、复杂案件的侦查过程中,确定并缉获犯罪嫌疑人之前,必须充分收集证据、研判案情,全面排查可疑对象。犯罪嫌疑人到案后,侦查主体应结合实际情况继续收集证明其有罪或无罪的证据,反复梳理案情。对于涉及非罪或罪轻合理怀疑的线索与证据,应仔细查证核实,不得排斥或隐匿。确实不能排除合理怀疑的,不得为追诉到案犯罪嫌疑人而牵强取证、强行“印证”其有罪。
鉴于此,有必要对侦查取证中的“排除合理怀疑”进行祛魅:它并非机械、形式化的目标,而是动态、不断修正的过程。侦查主体以逻辑和经验法则对案件线索、证据材料进行梳理、拼图,对侦查过程中出现的“合理怀疑”进行排除或查证,不断完善侦查证据体系,最终使全案证据达到排除合理怀疑或确认无法排除合理怀疑的状态。质言之,“排除合理怀疑”在侦查取证实践中的进路,是一种“摸着石头过河”的探赜,而非以其为唯一目标却罔顾具体情况与认知规律的“突击完成任务”。
(二)构建“排除合理怀疑”侦查证据体系途径再探
1.“溯因推理”与构建“排除合理怀疑”侦查证据体系的操作步骤
构建“排除合理怀疑”的侦查证据体系,需要一系列基本的操作步骤。刑事诉讼是对人的追诉,侦查中的合理怀疑是侦查主体在确定犯罪嫌疑人后,结合已有线索和证据进行推断,对犯罪是否系犯罪嫌疑人所为产生的怀疑。侦查假设与合理怀疑是共生关系,二者皆源自“溯因推理”。“这种推论方式(溯因推理)就是逻辑学家们所称的在一定条件下采纳解释性假设的方式……如果一种假设能够解释案件事实或案件事实的某些部分,那么我们就可以采纳此种假设。此种形式的推论如下:一个意想不到的事实C发生了;但是,如果A是真实的,那么C理所当然也是真实的;此时,我们有理由假设A是真实的。”[24]
根据上述阐释,事实C是已有证据支持的案情,侦查主体据此推测(假设)导致C发生的原因A。A往往包含多种可能性,既可能是已知犯罪嫌疑人实施了犯罪(侦查假设),也可能是包括“尚未纳入侦查视线者实施了犯罪”在内的其他原因(合理怀疑)。因此,A可能为若干互斥的原因A1,A2,A3……An中的任何一个。这些原因应当由“不带偏见的人,经过审慎的思考,在一定的根据(证据)基础上所提出”[25]。之后,分别沿A1,A2,A3……An的路径进行查证,慎重斟酌并排除其中与证据不符的侦查假设或合理怀疑,选出可被证据材料支持的假设或怀疑作为下一步重点查证的目标,不断缩小对A的“包围圈”。在排除某些可能的同时,调查过程中还会发现新的可能,而新的查证路径通常更加明晰,数量也逐步减少。
以上“试错—收缩”步骤被侦查主体反复、交错使用,不断缩小犯罪事实的可能性区间,直至以此剥茧抽丝、去伪存真式的调查与认知途径,将“历史遗留的碎片”全面拼合,得到由“排除合理怀疑”之侦查证据体系支撑与建构的全案事实蓝图。
2.构建“排除合理怀疑”侦查证据体系过程中的矛盾应对
“从总体上看,证明过程中有矛盾是正常的,完全没有矛盾反而是不正常的”[26],在组构证据锁链时发现矛盾,亦是合理怀疑浮现之时。“有矛盾就有可疑之处,矛盾解决的过程就是合理怀疑消除的过程。”[27]构建证据体系时可能遇到的矛盾包括证据间的矛盾、证据与事实间的矛盾和证据与普遍经验间的矛盾。
证据间的矛盾,是指对同一待证事实,一项证据指向一种情况,另一项证据却指向另一种情况,二者无法同真,至少一假。出现这种矛盾时,除依据经验法则辨别证据来源是否可靠外,还可借助形式逻辑判断证据的真伪:若两情况为对立事件,则两证据一真一假;若两情况互斥而不对立,则两证据至少一假。在此基础上,针对待证事实进一步收集证据,若有更多证据相互印证、指向一种情况而排斥其他情况,则该情况为案件事实的盖然性更高,相关证据真实的可能性亦更大。但是,取证者不能只重视印证数量而不关注印证质量,更不能因片面追求印证数量而非法取证。
证据与事实间的矛盾,是指侦查主体对案件事实的阶段性认识与取得的证据存在矛盾。遇到这种矛盾,除考虑证据可能不实外,还须考虑对案件事实的阶段性认识存在偏差的可能:之前的认识并不完全符合客观实际,证据与其存在矛盾,正是对这种认识偏差的反映。侦查主体应以矛盾为起点,“兵分两路”:一路审查证据真实性;另一路则考察对案件事实的认识是否存在偏差,能否以新的思路或证据,对之前的认识进行修正或完善。
证据与普遍经验间的矛盾,是指所获证据指向的案件事实不符合社会生活的普遍经验,即所谓“不合常理”。出现此类矛盾,先要考虑是否存在故意伪造证据误导侦查的情况。若证据真实性没有明显疑问,则应考虑案情是否存在特殊性,或调查对象是否具有尚未被侦查主体认识到的属性。然后,从“不合常理”的证据切入,“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运用“溯因推理”等方法探求案件真相。
3.“排除合理怀疑”侦查证据体系超越“印证困境”之可能
司法实践中的“印证困境”,是指尽管围绕犯罪事实收集到较为充分的间接证据并形成证据链条,但犯罪事实的关键部分缺少特定证据加以证明,使证据锁链核心部分出现“印证空洞”,导致证据体系难以被裁判者认可达到法定证明标准的困境。“印证困境”通常出现在犯罪嫌疑人隐秘作案的案件中。例如,在犯罪核心现场没有提取到能够对犯罪嫌疑人进行人身同一认定的证据,主要实行行为也缺少目击者证词或仅有被害人陈述证明,但全案间接证据链条却能将作案嫌疑高度指向犯罪嫌疑人。
诚然,为了在最大程度上预防错案,相当一部分存在“印证困境”的案件应当按照“疑罪从无”的要求处理。但是,有些被认为存在“印证困境”的案件,其证据体系实际上可以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尽管这一标准难以十分精确地量化固定,(12)域外对“排除合理怀疑”的量化概率,通说为“接近确定性,约在95%以上,而不是100%”。参见陈光中.刑事诉讼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180.但“排除合理怀疑”并非“排除一切怀疑”,(13)就“排除一切怀疑”在刑事诉讼中的非必要性,美国的金斯伯格大法官(Justice Ginsburg)曾在一起联邦最高法院判例中援引道:“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多少事情是我们绝对确定了解的,在刑事案件中,法律并不要求证明达到‘排除一切可能的怀疑’之标准。”See Victor v. Nebraska, 511 U. S. 1, 27 (1994) [quoting Federal Judicial Center, Pattern Criminal Jury Instructions, at 17-18 (instruction 21)].对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据体系仍然犹豫不决的“印证困境”,实质上是对证明程度达到“100%的绝对确定性”求而不得的困境。(14)本着慎用死刑的理念,《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已规定可能判处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必须达到“结论唯一”,以下讨论范围限于非死刑类案件。然而亦有论者主张,对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重罪案件来说,当前过于强调客观化及“结论唯一”而排斥合理推断的证明标准,可能会给刑事司法实践带来矫枉过正的风险,有引发包括侦控机关对供述的偏好、虚假证据、事实认定障碍乃至因轻纵而损害实体公正等一系列弊端之虞。参见左卫民.反思过度客观化的重罪案件证据裁判[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9,(1):112-122.
从法律运行实践角度看,由于以往“庭审虚化”(15)有关论述可参见汪海燕.论刑事庭审实质化[J].中国社会科学,2015,(2):103-122.204-205.、“卷宗审理”(16)有关论述可参见霍艳丽,余德厚.论以审判为中心完善刑事案卷移送方式[J].法律适用,2016,(12):107-112.及“审者不判,判者不审”(17)有关论述可参见刘少军.司法改革语境下合议庭独立审判问题研究[J].法学杂志,2017,(10):111-119.130.情况的存在,一则,在较少依赖庭审中直接、言词审理的情况下,为保证判决质量,审判法官必须更多依赖侦查卷宗中形式印证“几乎完美”的证据体系塑造心证;二则,若由并未参加庭审者决定案件审理结果,则证据体系必须具备外部明确性,即证据锁链在形式上的“完美印证”,以使并未直接参与庭审者也能“一目了然”地确信证据体系所证明的案件事实。在这种“印证压力”的层层传导下,为避开“印证困境”对案件审理结果的消极影响,居于刑事诉讼起点的侦查主体势必想方设法获取口供、指认笔录等直接证据,以填补证据锁链核心部分的“印证空洞”。
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要系统性地改善以往存在的“庭审虚化”等实际问题,那么,侦查证据体系就有超越“印证困境”之可能——这并非让侦查主体放松取证标准,亦非让侦查主体在缺少能够证明主要实行行为之“关键证据”的情况下草率认定犯罪嫌疑人;而是让侦查主体在穷尽一切合理资源与合法手段收集证据,并形成足以“排除合理怀疑”的侦查证据体系,但依然面临难以“排除一切怀疑”的“印证困境”时,杜绝使用非法取证手段强行攫取“认罪口供”或“指认笔录”等用以填补“印证空洞”的直接证据,提防出现“印证的功能扩张可能会变相鼓励虚假的印证”[28]之弊端,进而确信地将侦查证据体系推向下一诉讼阶段。
三、结语
取证是认识案件事实的基本前提与主要途径,以怎样的实体标准指导取证,决定了呈现在司法人员面前之案件事实图景的视角宽度与景深深度。拓展案件事实图景的视角宽度,需要从取证的全面性要求入手;而增加案件事实图景的景深深度,需要以“排除合理怀疑”的取证标准指导侦查证据体系建构。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既要求进入实质化庭审的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又要求严防冤假错案、让案件处理结果经得起法律和历史检验,这是对办案质量提出的更高要求,本文述及的提高侦查取证质量的两大途径,不失为落地这种要求的可行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