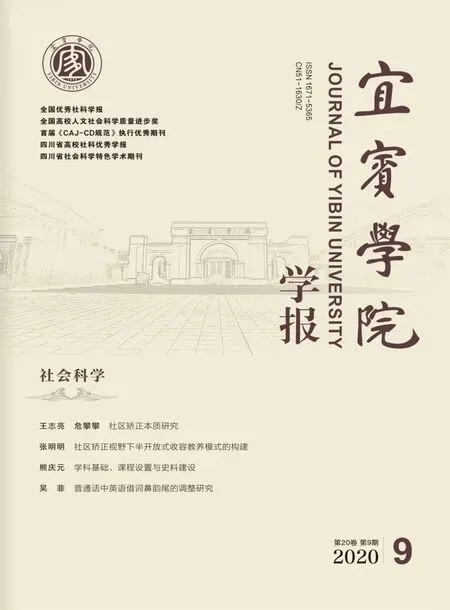中日近代语言变革运动与翻译小说的文体嬗变
2020-02-22王梦如陈多友
王梦如,陈多友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日语语言文化学院,广东 广州 510420)
日本“言文一致运动”和中国清末民初的“白话文运动”是都是在推进近代国民国家建设过程中,顺应社会变革的需要而发生的。有关日本“言文一致运动”和清末民初“白话文运动”的单面度研究较多,就二者之关联性所开展的比较研究也不少。但这些研究多从文学观念转型、近代国民国家建构、语言民族主义等角度进行史实梳理和理论解读。然而,从小说译介的角度,探讨中日两国前述语言变革运动的比较研究尚不多见。①
推动日本“言文一致运动”和我国清末民初“白话文运动”展开的重要载体就是小说。明治维新以降,日本大量地、迅猛地翻译欧美的小说。在我国,晚清翻译的小说中,最多当属英法小说,但“日语小说”(包括日本小说和被翻译成日语的其他国家的作品)也为数不少。据统计,1898-1911年间中国翻译的日语小说共201种,[1]3日本成为我国晚清时期引进世界文学的一个重要枢纽。从翻译小说的文体,可以爬梳中日两国这场语言变革运动的历史痕迹。那么,中日两国的翻译小说究竟有哪些文体;这些文体之间是否存在相似性或类似的文体演变脉络;两国的语言变革运动之间存在哪些内在联系和共性;表象的共性背后,又有隐藏着哪些差异?因此,本文通过梳理两国的翻译小说文体,分析其文体嬗变的规律,探究日本的“言文一致运动”与清末民初“白话文运动”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共性以及差异。
一、日本的“汉文直译体”和中国的“文言体”
日本“言文一致运动”初期出现了“汉文直译体”,即将汉文训读直接改写成汉字与假名混合书写的文体。反观中国晚清时期,译文仍然保留文言文的句式,只是加入少量口语词、外来词,一般称之为“文言体”。两种文体都出现在中日语言变革运动的初期,保留了大量汉文(或文言)的成分,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一)日本的“汉文直译体”
日本启蒙文学思潮的一个重要环节是“文体改良”,目的是改变旧文体“言文分离”的状况。1877年(明治十年)前后,日本文坛掀起一股介绍西方文学作品的“翻译热”,催生大量译作。
以思想启蒙为目的进行文学翻译的先驱是织田纯一郎。他翻译了英国政治家、作家利顿的《阿内斯特》和《爱丽丝》,译名为《欧洲奇事·花柳春话》(1878)。作为翻译作品,它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通常被视为政治小说的镐矢。他采用汉文直译体,而不是过去的“汉文体”或“和文体”。下面选取一段其译文:
マルツラバース曰ク 卿ノ顔色甚ダ悪シ。余ト共ニ庭園ニ歩シテ清気ニ触ルルアレヨ。必ズ健康ヲ助クルアラシ。アニス微笑シテ庭前ニ下リ 師主ト共ニ逍遥ス。マルツラバース 雪落花ヲ摘ミ アリスニ問フテ曰ク 卿草花ヲ愛スルヤ。曰ク妾大ニ之ヲ好ム。[2]
译文中夹杂着“曰ク”“甚ダ”等汉文训读词汇,还多处使用诸如“庭園”“清気”“逍遥”等汉语词汇。此外,“師主”原本是佛教词语,指在学问修行中所拜的老师,在这里是指迈特瓦。主人公对爱丽丝的称呼“卿”以及爱丽丝的自称“妾”都是陈旧的称呼方式,带有浓厚的文言色彩,是一种典型的汉文直译体。
事实上,幕府末至明治初的日本文坛,从文体来看,主要的行文体式就是汉文和汉字假名混合文这两种。精英阶层多用汉文,类似中国的文言文。而汉字假名混合文,实际上也夹带大量的汉语语词、汉文训读词汇或平安时代假名文中所使用的雅语,文章风格或类似直译汉文,或模仿古代假名文的雅文体。
1866年,前岛密向幕府将军德川庆喜提交《汉字御废止之议》,提出废除汉字的方案。前岛密的建议书,终结了汉字作为“真名”②文字的权威性,是为日本近代“言文一致运动”之滥觞。维新之后,明治政府采取改革措施,明令公文采用汉字片假名混合体。明治元年颁布的《五箇条の御誓文》就是用汉字片假名混合文行文,如“広ク会議ヲ興シ万機公論ニ決スベシ”,既包含了“会議”“万機”“公論”这样多用于书面语的汉语词汇,句末也使用了“ベシ”之类的汉文训读表达方式。日本自有文字以来,汉文或汉式和文一直被奉为最具权威的文体,然而,明治政府却彻底改变了公文的文体。这对当时的翻译小说等也产生了巨大影响,出现了大量的汉字片假名混合文体,织田纯一郎的《欧洲奇事·花柳春话》就是其中例证之一。它采用的是一种汉文训读式的、带有浓厚文言色彩的文体。
(二)中国的“文言体”
从第一部翻译小说《听夕闲谈》(1873)至19世纪末,中国的翻译小说都以文言体为主。及至晚清,林纾是文坛最重要的文学翻译家之一,他将180余部外国小说译介到我国,不过,其中仅有一部日本小说。1908年,林纾依照英译本,转译了德富芦花的《不如归》。此书被誉为“晚清翻译的日本小说中唯一的名著”。下面是摘自林纾译《巴黎茶花女遗事》中的一段文字:
余入室取书授之,客展书至第一页,见署名尚存,而眼泪已沾湿书上,曰:“君蓄意爱宝此书乎?”余曰:“何谓?”曰:“求割爱尔。”余曰:“是书固君赠马克乎?”曰:“然。”[3]
文中采用了“曰”“乎”“尔”等文言文的助词,句式简短明快,但又并非中国古典文学语境中的“古文”文体。林纾的译文吸收了大量的史传文章和章回笔法的文言,是他认为“较通俗、较随便、富于弹性”[4]271的文言。
吕叔湘将文言作了二分:“正统文言”与“通俗文言”。前者指“拿周秦文做理想”,且“在表面上也做得很像”的文言;后者则是“虽然沿用文言的架子,却应合当前的需要,容纳许多口语的成分”[5]4。吕叔湘提出了通俗文言的概念和范围,但并未包括和涵盖像林译这样的文言翻译文本。笔者认为,两相比较,林译语言应该属于后者。正如钱钟书所说,林纾的译作虽然保留若干“古文”成分,但比古文自由得多,在词汇和句法上,“规矩不严密,收容量很大”,“古文”里绝不容许的文言“隽语”“梁上君子”“土馒头”等形形色色的名词出现了,口语中的“小宝贝”“爸爸”“天杀之伯林伯”等也经常掺杂进去。流行的外来新名词——林纾自己所谓“一见便觉不韵”的“东人新名词”——像“普通”“程度”“热度”“幸福”“个人”“团体”等应有尽有。[6]13林纾译本不再是纯粹的文言文或“古文”,而是加入些许口语、俚语的“通俗文言”。另外,“东人新名词”指的是从日本回流到我国的新词,尽管译文是文言句式,但日本的词汇已经开始融入晚清的译文之中。
(三)“汉文直译体”和“文言体”的变革力度
日本的“汉文直译体”和中国的“文言体”都是各自语言变革探索阶段的产物,皆保留大量的汉文(或文言)成分。但是,也有了语言形态上的改观。例如,林纾译文的“东人新名词”,对晚清的白话文热产生了重要影响,为后期翻译小说文体的革新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然而,就翻译小说文体变异程度来看,晚清时期我国语言变革的力度与烈度,跟日本相比,还是比较微弱的。日本明治维新之后,政府层面已经开始推动语言变革,彻底改变用汉文书写公文的惯例,采用汉字片假名中混合体,为翻译小说以及其他类型的小说创作提供了文体模板。然而,反观我国同期情状,不仅政府层面没有推进语言革新之举动,文人自身亦倾向于保守。林纾沿袭“桐城体”,并未跳出“文言体”的羁绊,但其译文仍然被奉为翻译文体的典范,影响了鲁迅、周作人、胡适、钱玄同等一大批青年文学家、翻译家。他们惯常采用的“文言体”,多沿用“古文”,或明清时期的通俗白话,即便融入了新词汇,也不过是在文言文框架体系内加了一种点缀,总体观之,我国文坛文体变革的冲击力仍然相当薄弱。
相形之下,同时期的日本文人在问题革新方面用力甚勤,效果显著。例如,《经国美谈》作者矢野龙溪为塑造丰满的人物形象,讲述生动的志士佳人故事,以感动读者,行文中采用了多种文体,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触。后来,他夫子自道,指出最好的文体是集当时并存的“汉文体”“和文体”“欧文直译体”和“俗语俚文体”四种文体之长所创辟的“混用”文体。具言之,当表现“典雅悲壮”之际,用“汉文体”格调;想表现“优柔温和”的时候,就用“和文体”格调;欲表现“致密精确”的场合,则用“欧文直译体”格调;须表现“滑稽曲折”的情景时,便用“俗语俚文体”格调。[7]80然而,林纾在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时,却忽视了这种复调叙事特征,一以贯之地采用古文体迻译之。结果导致译文不仅文体单一,而且大量内容被缺省,变成了典型的“文言体”小说。
二、日本的“雅俗折衷体”和中国的“文白参半体”
随着中日两国的语言变革运动的推进,还出现了两种相似度极高的文体,即日本的“雅俗折衷体”和中国的“文白参半体”。
(一)日本的“雅俗折衷体”
1887年,二叶亭四迷用“言文一致体”创作出写实主义开山之作《浮云》,这象征着日本近代文学的里程碑(后文细述)。但是,当时“言文一致体”并没有形成破竹之势,被大众广泛接受。从1885年至1902年,欧化热潮减退、国粹思潮勃兴,日本的小说文体陡然复出元禄式雅俗折衷体,文坛掀起复古热潮,幸田露伴、樋口一叶等率其始,砚友社作家们随其后,文人们纷纷效仿。鉴于此阶段的“雅俗折衷体”具有向“言文一致体”的过渡性质,故笔者在此先讨论“雅俗折衷体”,再分析“言文一致体”。
据分析,我们发现尾崎红叶的《两个比丘尼的情色忏悔》(1889)和《金色夜叉》(1897-1903)中所采用的文体就是“雅俗折衷体”。人物对话部分使用当时的白话文,而叙述部分则采用文言文,沿袭了江户时代“西鹤调”③的文体特征。这种叙事用文言、对话用口语的叙事手法,与我国古典小说的叙事手法如出一辙。事实上,明治时期,由于小说地位很低下,小说还未完全登上艺术的殿堂。尾崎红叶模仿井原西鹤的写作手法,将雅文体(即文言文)和俗文体(即白话文)巧妙地结合起来,既提高了小说的品位,使小说进入艺术之行列,又没有失去原有的读者层,不仅小市民可以阅读,文人雅士也可以把玩、品鉴,达到雅俗共赏的效果。[8]1101889年,幸田露伴采用井原西鹤雅俗折衷体写成的《风流佛》问世,也获得世人广泛赞誉。第二年,森鸥外的《舞女》(1890)华丽登场,至此,“雅俗折衷体”成为日本文坛的文体典范。
用“雅俗折衷体”翻译外国小说的代表人物亦数森鸥外。他翻译了《于母影》(1889)、《即兴诗人》(1892)、《浮士德》(1913)等名著,致力于西方文学往日本的译介。尤其是他翻译的安徒生的长篇小说《即兴诗人》,历时10年问世,被誉为是“超过原作水准的名译本”。这对日本新文学语言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下面是森鸥外所译《即兴诗人》中的一段:
この夕我と同じ年頃なる人々にて、中には我を知れるもの幾人か雑りたるが、アヌンチヤタが家の窓の下に住きて絃歌を催さむといふ。姫が帰りてより一時間の後なりき。一群はピアツツア、コノンナに至りぬ。出窓の内よりは燈の光さしたり。楽器執りたる人々は窓の前に列びぬ。[9]35
文中保留了大量的古典日语的“たる”“なりき”“たり”“ぬ”等句式,但又同以往的汉文训读法有所不同,是一种将雅文体(文言)和俗文体(口语)巧妙结合的“雅俗折衷体”。其实,“雅俗折衷体”可以细分为“和汉雅俗折衷体”和“和汉洋雅俗折衷体”。前者是基于日本古来的语法框架(比如自动词与他动词的区别、动词的时态以及活用等)建构的文体,因此又可以成为“古文法派”。后者除了保留“和”“汉”传统之外,还掺杂了“洋”的因素,它在文章中纳入了种种欧化句式和新的思想观念,不时打破固有的行文规则。森鸥外的“雅俗折衷体”显然属于后者。但随着“言文一致体”的纵深发展,“雅俗折衷体”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
(二)中国的“文白参半体”
我国晚清的白话文热浪,催生了同日本“雅俗折衷体”相似的“文白参半体”文体。梁启超在主导《时务报》(1896)、《清议报》(1898-1902)和《新民丛报》(1902-1907)等报刊期间,为发挥报纸特有的传播功能,达到助维新志士“新国”“新民”的目的,发表了一系列激情澎湃、令人耳目一新的文章,如《变法通议》《过渡时代论》《新民说》等。内容涉及近代中国种种社会问题,开创了一种“条理清晰,笔锋常带感情”“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和外国语法”的“新文体”,也被称为“报章文体”。[10]195从文章体式上看,虽然“报章文体”打破了桐城派一统天下的沉闷局面,却并没有将它彻底推翻,其自身所用的语言也并未解决“言文合一”的问题,所采用的仍然是骈散结合的文体是一种文白参半的过渡性文体,故笔者称之为“文白参半体”。
1902年,梁启超将森田思轩译《十五少年》转译为《十五小豪杰》。他尝试将森田思轩的叙事和会话部分的汉文体改为白话体,然而因长期浸淫于古文,他在“纯用俗话”翻译之时,反而“甚为困难”,反倒是“参用文言,劳半功倍”,最终梁启超采用“文白参半体”顺利地译出了该小说。兹摘录其第5回部分译文内容如下:
杜番道:這太費事。費事猶可。但我断其労而無功。
武安道:然則低留在此處。等我与興沙往前探察之何如。
葦格道:我们自然也該同行。随喚杜番道:来我們一斉前進呀。[11]
上文中既保留了“費事猶可”“探察之何如”等典型的文言表达,也有“我们自然也該同行”,“来我們一斉前進呀”这种比较自然活泼的白话文。不过,“新文体”不是纯粹的白话文,仅是一种文言和白话混合的改良文体,尚未真正实现“言文合一”的目的。因此,在新文化运动兴起后,其逐渐被“新白话文体”所取代,也属情理之中。
(三)“雅俗折衷体”和“文白参半体”出现的历史必然性
对于浸淫在古文里的传统文人,要实现“言文一致”目标并非易事。日本的“雅俗折衷体”和中国的“文白参半体”,便是在语言变革运动中出现的一种典型的过渡性文体。
受日本武士阶层和中国士大夫阶层固有观念的约束,“雅俗折衷体”和“文白参半体”分别在日中两国思想文化转型期出现有着其历史的必然性。明治中期,日本人的意识还没有彻底地从江户时代的身份制度中解脱出来,身份等级意识仍根深蒂固地留存在人们的头脑中。对于统治阶级来说,唯有统治阶层的精英们才能写出的文章,比任何人都能写的文章更具魅力。接受过汉学教育的精英武士阶层还没有完全摆脱政治上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观念,片面认为,可显示身份差别的文章能够给自身带来优越感。因此,承继如此思想意识的知识精英阶层里推崇“雅俗折中体”的人并不少。
我国晚清时期白话文的倡导者们也存在类似的想法。他们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着“先知”角色,面对下层民众时,心理上存在等级意识。如同周作人所说,当时那些倡导者在态度上是二元对立的,“不是凡文字都用白话写,只是为了一般没有学识的平民和工人才写的白话”,“古文是为老爷用的,而白话是为听差用的”。[12]2这种士大夫阶层的“集体无意识”,使得启蒙者与被启蒙者之间难以真正拉近距离,也使得晚清的白话文思潮没有成为一场彻底的语言变革运动,“文白参半体”的出现就是这种等级意识下的调和物。
三、日本的“言文一致体”和中国的“新白话文体”
为更好地吸收欧美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加快语言形态的现代性转型,从而实现思想文化的转型成为中日知识分子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日本的“言文一致体”和中国的“新白话文体”便是顺应时代发展需要的产物。
(一)日本的“言文一致体”
物集高见的《言文一致》(1886)、林瓮臣的《言文一致歌》(1888)、山田美妙的《言文一致概略》(1888)等重要论著,把“言文一致体”的运用由散文扩大到诗歌和小说。随着坪内逍遥的《小说神髓》(1885)问世,日本文坛开始觉醒。坪内逍遥提出要从日本小说界清除曲亭马琴以来的“劝惩主义”,提倡英国小说中的写实主义。随后,二叶亭四迷《浮云》(1887)上梓,“文体采用日本最早出现的清新的言文一致体”(中村光夫语),被誉为日本近代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开山之作。他接受了坪内逍遥的建议,句尾采用了“だ”体,而没有采用“です”“ます”“でございます”等敬体表达。由于避免了使用敬语,行文不用考虑对象,从而更加收放自如。之后,他又以“言文一致体”翻译了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作品,译名为《猎人手记》(1888)。下面是其中的一段内容:
何ン時ばかり眠ッていたか、ハッキリしないが、兎に角暫くして目を覚ましてみると、林の中は日の光が到らぬ隈もなく、うれしそうに騒ぐ葉を漏れて、はなやかに晴れた蒼空がまるで火花でも散らしたように、鮮やかに見わたされた。[13]
译文出现了“ハッキリ”“兎に角”和“なやかに”等日语口语常用的副词或形容动词,句式层面采用表示转折的“が”和表示假设的“と”的接续词,构成了一个较长的复句,这带有明显的欧文句法特点。行文自然流畅,没有生硬的翻译痕迹,演绎了易于传播新思想的“言文一致体”。
除了二叶亭四迷,山田美妙也采用“言文一致体”创作了《夏木立》等小说。但在山田美妙的名声堕落之后,效仿“言文一致体”创作的人日渐减少。直到砚友社盟主尾崎红叶疏远“雅俗折衷体”,转而青睐“言文一致体”,这种颓势才有所改观。其中,其代表作之一《多情多恨》中“である”文体的出现,初步确立了“言文一致体”在日本文坛的地位。可见,由尾崎红叶、山田美妙等引领的写实派“砚友社”文学,在推进并巩固“言文一致体”的过程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这派作家们在其机关杂志《我乐多文库》上发表了一系列作品、文章,客观上普及了“言文一致体”的影响。
(二)中国的“新白话文体”
晚清时期,翻译事业异常发达,译家辈出。不同于严复、林纾等文言风格,一些有识之士开始自辟蹊径,独树一帜,成为开辟翻译新途径的先锋。周桂笙率先带头使用白话文译书。1903年出版的《新小说》第八号发表了他翻译的侦探小说《毒蛇圈》。该翻译小说是纯粹用白话行文运思的,开头的那一段省略主称的父女间对话,就颇为脍炙人口:
“爹爹,你的领子怎么穿得全是歪的?”
“儿呀,这都是你的不是呢;你知道没有人帮忙,我是从来穿不好的。”[14]201-202
周桂笙用白话文体译书,在当时是一种大胆的尝试,吸引了大批爱好西洋文学的人争相效仿,如包笑天、伍光建、方庆周等人。这种省略主称的方式,没有了中国惯有的“某某曰”来区分不同人物谈话的条件,所以都不得不使用引号。从引进标点符号这一点来看,他的文学翻译手法把我国的语言文字变革往前又推进了一步。
尽管在清末民初,白话文已经开始发端,文学领域也表现出某些革新的气象,但是文坛整体仍是尊崇文言。例如,鲁迅用文言文翻译了日本井上勤译述的《月球旅行》,取名《月界旅行》(1903)。“初拟译以俗语,稍逸读者之思索,然纯用俗语,复嫌冗繁,因参用文言,以省篇页”(《月界旅行·辨言》)。鲁迅的体例、用心和参用文言的做法,都与梁启超的《十五小豪杰》近似。可以看出晚清时期译介小说的一般风尚,“文白参半体”仍然占据上风。
这种状况,直至“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开始才得以彻底改变。1917年胡适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阐释了“八不主义”,对传统文学予以否定。其主要的文学语言观是“言文一致”,即“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继胡适之后,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影响深远的《文学革命论》,提出了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提倡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为改革民众的思想和观念,他们选择了白话文这个“新的工具”,新时期的白话文运动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下拉开帷幕。笔者将清末民初时期出现的纯白话文,称为“新白话文体”。再看鲁迅在新文化运动之后所译芥川龙之介的《鼻子》,从中能明显看出与他之前文言译文的差异:“一说起禅智内供的鼻子,池尾地方是没一个不知道的。长有五六寸,从上唇的上面直拖到下颌的下面去。形状是从顶到底,一样的粗细”[15]225。鲁迅在新文化运动之后,译文也采用了平易的“新白话文体”。可见,随着国语运动的开展,“新白话文体”已成为我国小说创作和翻译的主流。
(三)“言文一致体”和“新白话文体”的语言变革向度
日本的“言文一致体”和中国的“新白话文体”都有回溯本民族语言口语文体的倾向。日本是回溯速记体等民间口语,中国是回溯自古及今的白话文。
日本“言文一致体”的雏形可以追溯到明治十七年若林玵藏用速记体写下的圆朝的《怪谈牡丹灯笼》人情相声剧本。不仅会话部分,连叙述部分也能用口语记述的方式,打破了江户时期西鹤调的“叙事文言、会话口语”的书写模式,最终为“言文一致体”的诞生提供了模板。[16]
当胡适向古文开战,提倡白话文的时候,他是凭借其历史进化论,从历史中寻找理论依据的。他认为:“一千年来,白话的文学,一线相传,始终没有断绝”[17]62,并指出在唐诗、宋词、元曲及明清小说中,始终贯穿着一条白话文的发展路径,是一种“古已有之”的有别于文言的工具形式。胡适的《白话文学史》体现了旧白话资源观,证明了“新白话文体”的合理性。
另外,日本的“言文一致体”和中国的“新白话文体”又都有“欧化”的趋势。西方势力入侵带来的社会结构变迁和奋起直追西方文明的迫切需要,是两国追求“言文一致”的内在动力。中日两国语言的“欧化”,也是为吸纳西方思想观念而在语言层面所推动的改革。
不同的是,中国的新白话文体,受日语词法和句法的影响,还出现了语言的“日化”。众所周知,“经济”“社会”“革命”“思想”“意识”“国家”等词汇,都与日语有着直接且内在的联系。近代以来,大量日语词汇向我国白话文的逆输入极大地推动了后者的转型、发展和现代性重构,而新白话文对日语词汇的接受,则主要是通过日文书籍的翻译来实现的。如周作人在翻译日语小说的过程中,将大量的日文词汇、句法引入新白话文,并介入到“汉语由文言文转化为白话文的现代性语言变革进程中,日语与汉语实现了‘挪移——引用——借鉴——融合’的双向互动”。《现代日本小说集》的译文出现了许多宾语前置的句子,这一点明显是受到了日语的影响。例如,“恐怕家里对不起”“时光的过去也不知道了”,“贞子的华丽的声音听到了”等都是典型的日语“S-O-V语序”的句子。[18]73-94日语的翻译小说为“新白话文体”的生成提供了词汇、句法、文法的资源和参照系。
四、余论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和日本的语言变革运动,都是以“言文一致”为目标,试图通过语言的变革来推动思维模式变革的运动。日本“言文一致”运动时期,尽管多种文体同时并存,但就翻译语言的发展趋势而言,大致经历了一个“汉文直译体→雅俗折衷体→言文一致体”的变化过程。与之相似,中国翻译小说文体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由“雅”趋“俗”的过程,“文言体”→“文白参半体”→“新白话文体”。当然,这种发展变化的过程并非线性展开,而是在并存、悖离、融合的过程中,呈现出总体发展态势。日本的言文一致运动和中国清末民初的白话文运动都经历了漫长的、反复的、曲折的变革之路,才逐步实现“言文一致”的目标。
文体问题,其实并不单纯是文体问题,而是文化取向的选择。王国维就认为,“言语者,思想之代表也,故新思想之输入,即新言语输入之意味也”[19]41。日语的“欧化”、新白话文的“欧化”“日化”,都是我国吸纳西方和日本的思维模式和意识形态行为在语言层面的体现。我国清末民初的白话文运动可以说是在日本言文一致运动的影响之下发生的一场语言变革运动,日语小说的翻译是这场变革的催化剂,是中国白话文运动的“他者”和参照系。因此,中日翻译小说的文体呈现出类似的演变轨迹,正是这种深层文化内因的具体外现。
日本的语言变革,是一个解构固有的汉文成分、建构一个新话语体系的过程。“言文一致”的推行及逐步实现,实际上是“语言模式的转换”,是“对‘汉字式语言模式’的否定,是一种新的‘语言模式’的建立”。[20]从翻译小说文体嬗变的过程,反映出日本的言文一致运动是一个“回头看”和“往西看”的过程,是国粹主义和欧化主义相结合的过程,是语言层面 “脱亚入欧” 的过程,也是汉字或汉文被逐渐边缘化的原因所在。
中国清末民初的白话文运动与日本不同,不存在摆脱汉字符号的问题,也不存在以语音为中心重新创制书面语系统的问题(试图摆脱汉字的罗马字运动和拉丁文运动均失败)。白话文运动是在贵族与平民,“雅”与“俗”的对峙关系中建立起自己的价值取向,通过语言的深层内里的“欧化”“日化”“白话文言化”,形成 “中·西·日”相结合的“三位一体”的语言内核。这正是中国在以西方和日本为参照系的历史语境下所形成的语言变革向度。
注 释:
① 先行研究硕果丰赡,在此仅举部分较有影响力的论文:魏育邻《“言文一致”:日本近代文学的形式起源——从历史主义到“历史化”》,载于《解放军外国语学报》,2003年2期。刘金举《日本“文言一致”运动再认识》,载于《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5期。刘芳亮《近代化视域下的话文体系变革——中国“五四”白话文运动和日本言文一致运动之共性研究》,载于《解放军外国语学报》。齐一民《日本近代言文一致问题初探》,博士论文,北京大学,2013年。
② 汉字传入日本后,日本对汉字一直倍加推崇,认为汉字是“真名”,而根据汉字创造出的日本文字是“假名”。
③ 江户时代,井原西鹤在文章的叙述部分使用文言体,在人物会话部分使用口文体,这也是井原西鹤的文体特色,因而被称为“西鹤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