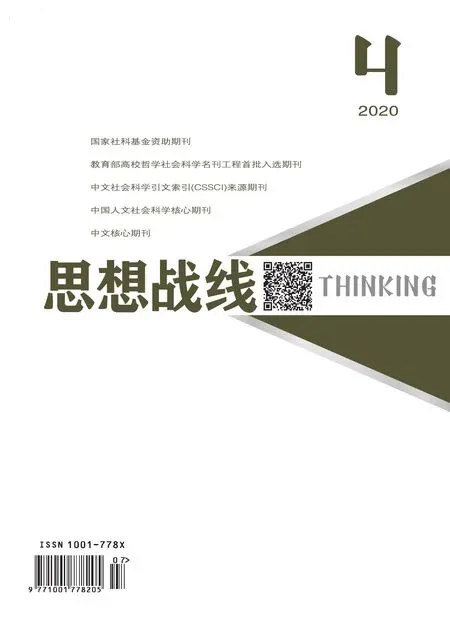文明国家:中华国家范式的一种理论阐释
2020-02-22朱碧波张会龙
朱碧波,张会龙
国家是政治学研究源远流长而历久弥新的经典母题。“国家范式何以阐释”向来是中西政治学者皓首穷经而致力求解的重大议题。我国学界通常借助通用型的王朝国家、主权国家、民族国家和多民族国家等范式来解读中国和理解中国。这些理论范式固然从不同维度揭示了我国不同时段国家形态的特定面相,但是,全球多元国家形态的非线性演进,使得中国国家形态呈现出与西方国家形态迥然相异的精神气象。单纯借助全球通用型国家范式的理论阐释,并不足以揭示中国国家范式的全貌,尤其无法揭示五千年中华历史滋养出来的国家格局与文明神韵。更何况,由于中文“民族”一词本身的多义性,学界在以民族国家(nation state)和多民族国家(multi-ethnic country)范式解读中国国家形态之时,常常必须借助英文的转译,才能实现理论话语的精准表意,这难免导致相关知识生产的难题和知识传播的困境。(1)朱碧波:《中国边疆学:学术争鸣的回顾与学科发展的前瞻》,《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因此,当前我国迫切需要立足中国本土,展开国家范式的自主性阐释和补白性研究。这不仅是以“中国理论”解答“中国问题”的必须,而且是以“中国研究”理解“中国本体”的关键。有鉴于此,本文将直面中国国家形态的复杂面相,并试图透过中国的结构性肉身,洞悉中国的精神内核,并着眼中国“外在肉身”与“内在精髓”的互构,尝试性提出和论证“文明国家”(中华文明国家)的中国范式,并以此就正于方家。
一、国家形态:中华文明国家之“形”
国家是人类创造的最为有效的社会治理形式。国家一旦被人类创造之后,就具有了政治统治、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之类的基本职能,就形成了自我的行动逻辑和政治权能。不过,虽然现代国家的形态差相仿佛,但不同国家各种职能的权重却并不尽然一致,其行动逻辑和政治权能更是各有千秋。究其根本,乃是缘于各个国家都拥有不同的历史,不同的历史又催生了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化又模铸了不同的国家品格。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华文明五千年的未曾断裂,不但塑造了古今中华国家的精神气度,而且滋养了古今中华国家的治理能力,使得中华现代国家彰显出独具一格的中华风范和文明品格。
(一)国家地理疆域:中华文明驱动下的自然凝聚
疆域是国家最为基础的构成要件,是人口繁衍和文化生成的根本前提。中华文明正是中华民族在中华大地上不断建构的产物。诉诸历史可知,各民族在辽阔的中华大地上先后出现,并星罗棋布地遍布四野。由于中华各地的自然禀赋和生态资源具有差异性,各民族的先民为适应不同的自然环境而创造出别具一格的民族文化。中华大地由此形成“泛中原农耕文明板块”“大漠游牧文明板块”“东北渔猎耕牧文明板块”“雪域牧耕文明板块”和“海上文明板块”。(2)于逢春:《构筑中国疆域的文明板块类型及其统合模式序说》,《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3期。随着各民族的迁徙流动和交往交流的加深,这五大文明板块相互撞击和吸纳,最终涵化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板块,奠定了中华文明国家疆域的基石。在这个过程中,“泛中原农耕文明板块”对其他文明板块的凝聚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原地理条件相对优越,民族开发程度相对较早,具有同时代边疆文明板块难以媲美的发展程度和文化优势。这使得中原地区的政治理念和文化精髓对边疆地区产生了强大的感召力。中原地区一些基本的政治理念逐渐成为边疆地区普遍信奉的政治法则和价值准则。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大一统”思想、“民族观”和“正统”理念的传播与认同。“大一统”思想强调“天下一统”乃“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为天子者,当“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大一统”思想形成之后,便逐渐扩散至边疆并得到各民族的普遍认同。边疆各民族入主中原之际往往都怀抱“天下一统”的理想,致力于国家的统一。同时,“泛中原农耕文明板块”还秉持“夷狄进于华夏则华夏之,华夏退于夷狄则夷狄之”的民族观。民族之间的区分不以“族裔身份”而以“文化身份”为标准。这种民族观为少数民族追求华夏正统提供了可能。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之际莫不在文化上以中华自居,追溯自我与华夏先王之间的血脉渊源,并以此自证入主中原的合法性和一统天下的正统性。这就是说,中原地区孕育的文明板块以其强大的内聚力,使之滚雪球一般吸附周围的文明板块,驱动中华各文明板块的涵化交融和自然凝聚,(3)李大龙:《自然凝聚:多民族国家中国形成轨迹的理论解读》,《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最终统合成一个整体的中华文明板块,奠定中华文明国家疆域形成与存续的基础。
(二)国家治理制度:中华文明浸润下的制度创建
国家治理制度是国家治理架构的创建与运转的法则,是国家治理能力生成与提升的基础。当代中国创建的新型国家制度和治理制度并不是决裂历史而向壁虚构的结果,而是传承中华文明和吸纳人类制度文明不断创建发展的结果。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历史积淀和一脉相承,模铸了我国新型国家制度的文明品格,催生了我国国家治理制度的中华风范。这种中华风范大体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和合”基因。“和合”是中华传统文化最重要的价值理念。“和”乃“天下之达道”(《中庸》);“天地和合”乃“生之大经”(《吕氏春秋》)。“和合”成为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基本法则。它型塑了中华人民的价值旨趣,影响了中华民族的心理意象。正是在“和合”主义的浸润之下,当代中国才不断汇聚时代智慧,创造性设计出中国特色的新型国家制度,如合议型的民主制度、合作型的政党制度与和睦型的民族制度。二是“均平”理念。中华传统文化中蕴藏着丰富的“均平”思想,强调通过政治调节(“均”)来达到社会平衡(“平”)。不管是儒家“不患寡而患不均”,还是墨家“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抑或法家“论其税赋以均贫富”,都折射出古代中国对于社会分配之思考。中华文明的“均平”理念,使得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和制度供给都折射出鲜明的底层立场和弱势关怀。当代中国不断创建和完善的共享发展制度,包括针对边缘区域的对口支援制度、扶助边缘产业的乡村振兴制度和救济边缘人口的精准扶贫制度,事实上都带有传承、发扬和创新性实践中华文明“均平”理念的影子。三是“修身”传统。中华传统的人文理想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为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正如《礼记》有云:“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强调自我的道德修炼和人格完善。朱熹《孟子集注·离娄上》又云:“思诚为修身之本,明善为思诚之本”,强调正心、诚意、慎独、明德。中华文明的“修身”传统内化为国家和社会的道德理想和价值旨趣,使得中华国家治理形成重视道德治理的传统。当代中国开展的道德治理制度化实践,如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以及“两学一做”的常态化制度化,事实上都是植根中华文明并经时代淬炼而成的制度供给。
(三)国家治理能力:中华文明润泽下的能力养成
国家治理能力是在国家治理价值体系的指引下,依托国家治理的结构体系,按照国家治理的制度规范,治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国家治理能力体现为国家治理智慧的独特性、治理方式的丰富性和治理手段的多元性。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既需要我国放眼世界、海纳百川,参鉴全球国家治理的经验教训,又需要我国立足当下,回顾历史,吸收中国治理历史的传统智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与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4)习近平:《牢记历史经验历史教训历史警示 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人民日报》2014年10月14日。中华文明五千年的智识结晶,不仅能为当代国家治理提供历史智慧和文化资源,而且为当代国家治理提供基本的文化工具和道德手段。进而言之,首先,中华文明提供了国家治理的历史智慧和历史资源。当代中国是古代中国的扬弃性传承和创造性发展。中国历史演进的一脉相传,决定了当代中国治理并不能够割裂历史而另起炉灶。历史证明,一个国家如果简单粗暴地以国外文明为蓝本进行全盘的制度移植和文明置换,那将可能诱发国家治理的不测之祸。因此,中华现代国家的治理必须植根本土文明,发扬本土文明的优秀传统,尤其是民惟邦本、政得其民、礼法合治、唯才是举、为政以德、居安思危的历史智慧。其次,中华文明构成了国家德性之治的基石。德性之治和法理之治是现代国家治道的双维,如鸟之双翼,缺一不可。德性之治强调政治主体的德性修养,它强调依靠道德这种软约束的制度安排和人格养成,内塑政治主体的道德情怀和行政权力的伦理向度,并激活整个社会的公民美德,实现国家与社会的善治。就中华文明而言,中华文明“德性之治”的话语一直不绝于史。古代内圣外王、修己安人的道德传统和当代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的政治情操,都是中华文明德性之治的历史传承。它构成了中华现代国家治理的道德资源,滋养了中华现代国家治理能力的生成。
二、中华民族:中华文明国家之“体”
中华文明国家是中华文明、中华民族和中华国家“三位一体”的互构。中华文明是中华文明国家的根柢,中华国家是中华文明国家的外观,中华民族则是中华文明国家的肉身。
(一)中华民族是中华文明孕育的文明共同体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而成的族类共同体。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带来民族文化的交相辉映和相互涵化,催生了一体多源的中华文化。中华民族由此表现为民族结构的多元一体和文化结构的一体多源。在中华民族的形成与演进中,中华文明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演变中创造的文化结晶,是中华民族代际传承中智识结晶的符码再现。它为各民族提供共享的文化体系、共通的文化认同和共有的精神家园,建构了中华民族共享的集体记忆和共同的文化身份。
中华文明为中华民族提供的共享的集体记忆,包括中华民族演进的时空节点、中华民族的文化品格、中华民族的远祖想象等。其中,中华民族演进的时空节点揭示了中华民族诞生与发展的生命轨迹,使得中华民族共享历史中华的辉煌与屈辱、荣光与苦难。中华民族的文化品格则是指中华民族在历代中华经典文本的浸润之下形成的一种民族性的集体无意识,它使得当代中华与历史中华在文明的一脉相承中发生着超越时空的对话和情感共鸣。至于中华民族的远祖想象,则是指中华文明以特定的叙事结构和既定的符码体系,代际传递中华民族关于远祖的记忆,驱动中华各民族不断生成血脉相连的袍泽情怀,进而凝聚成休戚相关的命运共同体。
中华文明不仅为中华民族提供厚重的集体记忆,而且为中华民族提供共享的文化身份。如果说中华文明蕴藏的历史记忆回答了中华民族“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的终极拷问,那么中华文明提供的文化身份则回答了“我们何以成为我们”“我们怎样成为我们”的哲思之问。中华文明提供的文化身份,对于中华民族至少具有双重价值。第一重价值体现为,中华文明是解决中华民族个体心理失衡的良方。中华文明孕育的文化身份,为民族成员漂泊的灵魂找到精神的皈依,为孤独的心理寻获根系的传承。第二重价值体现为,中华文明的文化身份构成中华民族形成的重要纽带。中华文明为中华民族提供相同的文化符号、相似的文化理念、相像的思维模式、相通的审美情趣和相近的行为规范。中华文明的浸润,使得中华民族在与他民族交往之时,产生“对他而自觉为我”的“民族自觉”意识和“民族共同体”意识。
更为重要的是,中华文明不仅以其文本书写和文化符号,为中华民族提供共享的历史记忆和共有的文化身份,而且以独特的价值体系和智慧情怀,塑造了中华民族的群体人格和精神气象。正是中华文明的熏陶,中华民族才形成独具一格的基本人格结构,即君子人格。这种君子人格,儒家称之为“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论语·季氏》);道家称之为“以仁为恩,以义为理,以礼为行,以乐为和,熏然慈仁”(《庄子·天下》);墨家称之为“贫则见廉,富则见义,生则见爱,死则见哀”(《墨子·修身》)。君子人格是中华轴心时代各派关于个体理想品质的想象。它在历史演进中不断丰富和成型,并成为中华民族普遍认同和致力追求的理想品格。在君子人格的感召之下,中华民族与其他民族呈现出大异其趣的人格结构和价值取向。
(二)中华民族是中华国家锻造的政治共同体
中华民族是中华现代国家的基础性资源,是中华现代国家崛起的支撑性力量。中华民族对中华现代国家极端重要的价值,使得中华现代国家不断从中华民族的政治定位、法律地位、实体建构和意识引导等方面积极展开中华民族一体化的锻造,推动中华民族成为一个紧密联结的政治共同体。
中华民族是国族意义上的政治共同体。在中华现代国家的建构中,中华民族不仅获得了各派政治力量的承认,而且还获得了现代中国法律的确认。早在1912年,孙中山在《五族国民合进会启》中就赋予中华民族以国族的政治定位,强调“于民族主义上,乃求汉、满、蒙、回、藏人民密切的团结,成一强固有力的国族”。(5)《孙中山全集》第7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华民族的法律地位乃至宪法地位都渐趋明晰。2004年,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将《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写入宪法。国歌乃是词曲的一体。宪法对国歌(包括国歌歌词“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确认,意味着“中华民族”一词的间接入宪。2018年,我国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增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内容。中华民族就此从政治概念走向了宪法概念,从宪法的隐晦表达转向宪法的明示宣昭。这就使得中华民族认同与宪法认同、中华民族建构与依宪治国密切关联起来,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锻造提供了充沛的合法性。
中华民族入宪是中华民族建构的顶层设计。中华民族建构的顶层设计又指引中华民族建构的实践推进。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宪法目标,中华现代国家不断从本体和意识两个维度来推动中华民族一体化煅造。本体层面上,中华现代国家顺应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大势,不断推动各民族的互嵌共生,奠定中华民族一体化的社会基础。中华各民族的共生互嵌是各民族展开社会交往和心灵交流的前提,是缩小民族心理距离和推进族际跨界涵化的关键。因此,中华现代国家不但在政治导向上强调拆除民族流动的樊篱和社会融入的障碍,而且聚焦各民族的居住生活、工作学习、文化娱乐等,创造各民族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社会条件。(6)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学习辅导读本》,北京:民族出版社,2015年,第290~292页。这些社会条件的创造包括:全面强化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筑就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语言桥梁;(7)王春辉:《中华人民共和国语言扶贫事业七十年》,《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积极推进边疆与内地的双向交流,稳步促进边疆民族群体到内地接受教育、就业和安居,增进各族群众在共同生产生活和工作学习中的了解;逐步推进边疆教育领域的“民汉混校和民汉混班”,强化青少年群体的跨界交流,促进各民族群体的社会互动和人际吸引;顺应时代潮流,借助全媒体时代的多元媒介,建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网络平台,创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载体与形式。
至于意识层面上,中华现代国家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引导各民族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各民族对中华民族身份的认同归依,是各民族对中华民族“情感的自发”“理性的自知”和“身份的自觉”。中华现代国家延承和超越中华民族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话语,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概念,其内在政治诉求乃是推动各民族个体超越自我利益的局囿,引导各民族群体超越差异政治的追求,将“自我”和“我群”的利益诉求和政治忠诚,导向更为宏阔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寻求中华民族共同体公共利益和至善生活的实现。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现代国家树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集体愿景,提振中华民族内在凝聚的动力;推进中华民族与中华国家的互构,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政治基础;引导中华民族一体化发展,强化中华国民的整体性。同时,中华现代国家还特别强调再造中华文化(中华文明)的自信,推进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传承和创新性发展,并通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和中华传统节日振兴工程,让各民族在沉浸式的文化体验中生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
三、中华文明:中华文明国家之“神”
中华文明国家是中华文明孕育的政治共同体。中华文明定义了中华现代国家的伦理底蕴、精神气韵、国家气度和天下想象,使得中华现代国家呈现出与西方资本国家大相径庭的政治风范和国家气象。
(一)中华文明国家的伦理底蕴:人民立场
伦理底蕴是中华文明国家最深层的价值考量。在中华文明国家的价值体系中,“以民为本”可以说是一以贯之的伦理底蕴。纵览中华文明的话语体系,以民为本的思想充盈其中,上承天道而下启王道。如《尚书·五子之歌》有云:“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孟子·尽心下》有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管子·霸言》有云:“夫霸王之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这些以民为本的话语深远地影响了中华文明国家的伦理取向,并成为中华文明国家治理的价值基石。及至当今,以民为本的价值理念更是得到一脉相承的发扬,并推动现代中国形成“人民立场”的治国道统。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现代中国的人民立场,既是对古代中国以民为本的传承,更是对古代中国以民为本的创新。现代中国的人民立场不但摆脱了传统民本与君本的纠缠,而且发扬传统民本思想的“民生”与“民心”,创造性提出“民权”和“民治”,使得中华文明国家“人民立场”的伦理底蕴更具时代气象。进而言之,现代中国传承传统文化之精髓,吸纳时代文明之菁华,使得中华文明国家的人民立场呈现出民生、民权、民治、民心的交相辉映。这种人民立场注重以民生为基础,以民权为核心,以民治为关键,以民心为目的。其中,民生强调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确保人民群众全面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民权强调坚持和完善中华现代国家的各种新型制度,确保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民治强调完善人民群众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为中华现代国家的崛起汇聚磅礴力量。至于民心则强调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只有最大限度地凝聚民心,中华民族复兴的事业才能无往而不胜。
(二)中华文明国家的精神品格:“刚健有为”
在中华文明演进史中,中华文明奋发蹈厉的基因与中华国家的品格融为一体,孕育了中华文明国家的“刚健有为”。“刚健有为”之“刚”,强调的是独立不惧和立不易方。在个体而言,“刚”乃是“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厚德载物,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在国体而言,“刚”乃是“天下之大,非体乾刚健,其能治乎”,(8)程 颢,程 頣:《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51页。强调国家治理要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至于“刚健有为”之“健”,按照《彖传》所说乃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体运行,永无止歇,故称“健”。君子法天,故应自强不息。因此,个体与国家都要奋发图强,永不懈怠。个体当以自强为贵,乾乾进德,至诚不息。国家则要取法天道,顺天应人,以期天下化成,国泰民强。古代中国正是缘于“刚健有为”的品格,才铸就了秦汉雄风、盛唐气象、康乾盛世。及至近代,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中华国家“刚健有为”的气象更是得到前所未有的高扬。中华民族众志成城,百折不挠,完成中华现代国家的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创建之后,这种“刚健有为”的品格又驱动现代中国择取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之路,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改革开放之后,现代中国又传承中华文明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革故鼎新之志,以刀刃向内的勇气,持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国家制度,推动中华现代国家续写中华文明古国的传奇,重返世界政治舞台的中心。
(三)中华文明国家的生存理念:“天人合一”
中华文明国家最为基本的生存理念乃是“天人合一”,即尊重自然,道法自然,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先秦时期,这种天人合一的理念就已雏形初现。《易经·文言》有云:“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又云:“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这些表述就已经流露出中华先民“敬天法地”的意识。汉代时期,董仲舒和王符进一步深化“天人协调”的理解。董仲舒指出:“以类合之,天人一也。”(9)董仲舒:《春秋繁露》,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94页。王符指出:“天本诸阳,地本诸阴,人本中和。三才异务,相待而成,各循其道,和气乃臻,机衡乃平。”(10)王 符:《潜夫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431页。及至北宋时期,张载明确地提出“天人合一”的理念。他指出:“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遗人。”(11)张 载:《张子正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39页。“天人合一”的生存智慧,其精义在于强调“人亦天地间之一物”,强调人与自然的优态共生,将自我视为天地的一部分。为了实现“天人合一”,中华先民强调人类首先要“敬天”,道法自然,“与自然无为”。其次要“齐天”,“人在天地间,与万物同流”,(12)程 颢,程 颐:《二程遗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56页。人并没有凌驾于万物的权利。再次是“爱天”,即“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仁民爱物”,“恩及禽兽”(《孟子·梁惠王上》)。最后是“用天”,即“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尊重天道,“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论篇》)。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不仅是中华民族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切体悟,而且还是中华民族对自我生存理念的深刻反省。(13)相较于中华文明国家的“天人合一”,西方国家始终存在一种挥之不去的“人类中心主义”。这种“人类中心主义”强调的是“人为自然立法”(康德),“人是万物的尺度”(普罗泰戈拉)。虽然这种“人类中心主义”对于西方社会“人性的彰显”和“人权压倒神权”具有比较积极的意义,但它始终潜藏着“自然状态与人为状态的对抗”(赫胥黎)和“自我”与“非我”的对立(费希特),难免导致“自然对人类的报复”(恩格斯)。近年来西方“人类中心主义”频频遭遇“生态中心主义”的批判,但其彻底矫正依然举步维艰。它内化为中华文明国家的生存态度,使得中华现代国家即便经由“人与天交相胜”的曲折,依然能够回归天人合一的传统。及至当代,随着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化,“天人合一”的文明传统更是由中华民族自发的生态取向转向中华现代国家的政治自觉,从中华民族的生存理念转向现代国家的理性建构。
(四)中华文明国家的天下想象:协和万邦
中华文明是一个由人与自我的和解、人与社会的和合、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天下的和睦交织而成的价值体系。它影响甚至宰制中华文明国家的思维模式,使得中华文明国家形成协和万邦的天下想象。协和万邦的思想,按照《尚书·尧典》的表述是“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按照《周易·乾》的表述则是“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万国咸宁”。不过,不管是《尚书》的协和万邦,还是《周易》的万国咸宁,都不强求各国的千人一面和千篇一律,而是强调各国的和而不同和五色交辉。中华文明“和而不同”与“五色交辉”的理念,不仅成就了古代中国的天下想象,而且孕育了现代中国的外交理念,使得中华现代国家与西方资本国家呈现出迥然不同的政治逻辑。纵览历史,西方资本国家始终潜藏着难以祛除的“对抗”思维和“霸道”逻辑。及至近代,“对抗”思维和“霸道”逻辑更是成为西方资本国家处理国际关系的内隐法则。在国际关系上,一些西方国家强调修昔底德陷阱和国家安全困境。在国际和平上,一些西方国家强调“霸权稳定论”,认为超级霸权国的存在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中坚。在意识形态上,一些西方国家则带有极其浓烈的“西方中心论”,认为西式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14)[美]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黄胜强,许铭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页。为了实现其政治理想,西方国家不断鼓吹(西方)自由世界对(非西方)极权世界的“不战而胜”。(15)[美]尼克松:《1999年:不战而胜》,王观胜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第15页。在全球一体化日益深入的当下,西方资本国家“文明优越”和“文明冲突”的理念显然无益国际社会的和平稳定。与其大异其趣的是,中华现代国家始终坚守中华文明的亲仁善邻和协和万邦,并创造性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强调各国的文明交流和文明互鉴,主张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
四、结 论
我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华文明始终与中华国家的建构与发展相生相随。中华国家形成演化的独特历史,决定中华国家范式的认知要超越主权国家、民族国家和多民族国家等普适性国家范式的解释,而从“中华文明”的角度阐释中华国家的范式,即以“中华文明国家”定义古今中国的国家范式。中华文明国家是贯通古今中国的一种范式表达,它强调中华国家、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三位一体的同构。国家形态是中华文明国家的政治外壳,中华民族是中华文明国家的肉身实体,中华文明是中华文明国家的精神气韵。正是中华文明的浸润和中华民族的践行,中华文明国家才形成人民立场的伦理底蕴、刚健有为的精神品格、天人合一的生存理念和协和万邦的天下情怀,才呈现与西方资本国家迥然相异的政治逻辑与文明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