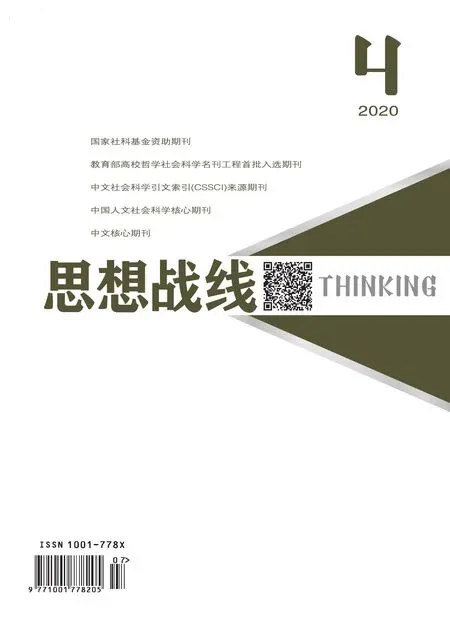语言学视野下中西医原创思维模式对比研究
2020-02-22刘志成
刘志成
中医作为中华文明的瑰宝,守护了中华各族儿女数千年的健康,但是随着西医的进入,中医的地位不仅被动摇了,而且各种反中医、视中医为伪科学的声音时有发生。与此同时,对西医盲目崇拜,“重西轻中”的现象时有发生,包括一些文化名人的言论,如傅斯年、吴汝纶、汤尔和等。但中医常在危机中显示出其作用,并因此受到国家重视。2003年“非典”期间,中西医结合治疗就取得了显著效果。(1)陈 欣,林江涛等:《中药治疗对SARS恢复期患者肺功能、生存质量的影响》,《中国康复医学杂志》2006年第2期。2009年国务院出台的《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了要“中西医并重”的方针。(2)《国务院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厅网,http://www.gov.cn/xxgk/pub/govpublic/mrlm/200905/t20090507_33358.html,2020年1月12日。但是如何促进和实现“中西医并重”却是亟待研究的问题。2020年初新冠肺炎的肆虐,使用中医和中西医结合治疗的显著疗效,让中医再次成为人们和广大医务工作者关注的焦点。如张伯礼院士科研团队的《中西医结合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34例临床研究》,(3)夏文广,安长青:《中西医结合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34例临床研究》,《中医杂志》2020年第2期。李杰、李靖等的《基于中医瘟疫理论浅析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证特点及防治》,(4)李 杰,李 靖等:《基于中医瘟疫理论浅析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证特点及防治》,《世界中医药》2020年第2期。蔡圆梦、吴澎泞等的《“肺脾同治”法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中的应用》(5)蔡圆梦,吴澎泞等:《“肺脾同治”法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中的应用》,《中药药理与临床》2020年第2期。等文章表明,中医药在治疗新冠肺炎当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大大降低了死亡率。而著名西医医生特鲁多墓志铭上的名言“有时治愈,常常帮助,总是安慰”亦提醒我们,需要认真考察一下西医的治愈率了。正如“西医实践中一般误诊率不下于1/3”。(6)钱学森:《钱学森书信选》下卷,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8年,第1086页。近些年来,虽有众多的专家学者对中西医思维进行了介绍,如中医的象思维、形神一体思维、辨证施治思维,西医的还原分析、身心二元、逻辑思维等思维模式,(7)相关研究可参见张延丞,张其成《浅谈象数与中医学的关系》,《中华中医药杂志》2018年第11期;程雅君《阴阳辩证法与中医哲学刍议》,《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张宇鹏《从范式的不可通约性看中西医学关系》,《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16年第3期。但是这些文章并没有深入到中西医思维方式的核心,更没有指出中西医为何会有这样的思维模式。本研究试图从语言与思维关系的角度,探索中西医原创思维及其治疗理念的特点,因为“一个人思维的形式受制于他没有意识到的固定的模式规律。这些模式就是他自己语言的复杂的系统”。(8)[美]沃尔夫:《论语言、思维和现实——沃尔夫文集》,高一虹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272页。
一、语言与思维的关系
要研究英汉语言是如何影响中西医的思维模式,首先就要探索语言与思维的关系。语言与思维不仅相辅相成,而且相互影响,二者是同生同灭的关系。
(一)语言与思维
语言作为思维的外化形式,二者同质而异名。正如“我们的思维就是我们的语言”。(9)辜正坤:《中西文化比较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8页。
由于“不论人的头脑中会产生什么样的思想,以及这些思想什么时候产生,它们只有在语言材料的基础上、在语言的词和句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和存在”。(10)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论语言学的几个问题》(1950年6月29日),载《斯大林选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525页。以及“在内在或外在的言语中,语言也起着组织思想的作用,并由此决定着观念的联结方式,而这种联结方式又在所有的方面对人产生着反作用”。(11)[德]洪堡特:《洪堡特语言哲学文集》,姚小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267页。基于此,通过分析一种语言的词法和句法,则能了解使用该语言认知主体的思维特点。
(二)语言的体验性
语言是体验的还是先验的?由于“语言是通过人的感官和知觉形成的!语言并非先验之物,而是感性活动的产物,所以,语言起源问题只能用经验的、归纳的方法来解答。一切观念都只能通过感觉形成,就不可能存在任何独立并先存于感觉的观念”。(12)[德]赫尔德:《论语言的起源》,姚小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65页。可见,语言的本质属性就是其体验性,语言不同的词法和句法特点,正是基于认知主体不同的心灵经验。而不同的心灵经验,则来源于认知主体对客观世界不同的心理体验。正如“我们的全部知识是以我们的感官所给予我们的报告为基础的”。(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57页。而外部世界正是我们的体验之源。因为“思维永远不能从自身中,而只能从外部世界中汲取和引出存在的形式”。(14)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全集》第1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4页。承认语言的体验性和物质世界的第一性,亦与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因为外部世界往往会先在认知主体的心灵留下一种印象,然后才能形成相应的心理结构,而相应心理结构的固化,则是通过相应的词法和句法结构表现出来的。正如“语法比语言的任何其他部分都更隐蔽地存在于说话者的思维方式当中”。(15)[德]洪堡特:《洪堡特语言哲学文集》,姚小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121页。可见,分析一种语言的语法,同时与另外一种语言的语法进行对比研究,无疑是了解两种语言思维方式最切实可行的方法之一。
(三)英汉语言不同的体验来源
由于“人类语言的起源,是我们了解自己最重要的谜团”。(16)[美]戴蒙德:《第三种黑猩猩》,王道还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第143页。同时,语言是体验的,物质是第一性的,不同的物质世界会带给认知主体不同的心灵经验,从而形成不同的心理印象和概念结构,这种心理印象及概念结构被逐渐演化为相应的词法和句法结构。因为“人的整个内在世界始终受到外部感性的刺激和限定”。(17)[德]洪堡特:《洪堡特语言哲学文集》,姚小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269页。而在遥远的古代,带给原始初民最直接心灵经验的,则是自然因素。因此,“语言学必须首先考虑地理因素,我们决不能把语言与人、把人与大地隔绝开来。大地、人和语言,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18)[德]洪堡特:《洪堡特语言哲学文集》,姚小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346页。
1.西方文明起源于天人二分的海洋文明
西方文明起源于地中海沿岸,地中海地区的自然条件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从地理环境来看,地中海地区陆海交错,岛岛相望,为外出航海提供了天然的良好条件。希腊文化尤以雅典为代表,雅典三面环山,一面傍海,由于其地理位置,迫使雅典很早就从事海上贸易;其次,从气候来看,地中海地区夏季干燥炎热,冬季潮湿,不适合农作物的生长;第三,从土质来看,地中海周边土地贫瘠,主要为沙地和盐碱地为主,不适合农作物的生长;第四,从地貌来看,地中海地区被天然的障碍分割成众多孤立的小区域,正如“(希腊)没有一个伟大的整块。相反地,希腊到处都是错综分裂的性质”。(19)[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第211页。
内因和外因导致西方人必须扬帆远航、外出谋生,而大海的凶猛与狂暴带给西方原始初民最直接、最深刻的心理体验,就是天人相争、天人二分,大海的野性激发起人类战天斗地的豪情去战胜自然。古希腊神话中的波塞冬、福耳库斯、刻托、欧律比亚等神话人物,以及后世的《老人与海》等小说,无不是人与大海之间争斗的具体写照。
2.中华文明起源于天人合一的江河文明
中华文明则起源于江河文明之中,不论是河姆渡文化、红山文化、三星堆文化,还是仰韶文化等,均与大江大河、冲积平原紧密相关。可以说,中华文明是一种典型的农耕文明。
首先,从地理环境看,江河和冲积平原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天然有利的条件。如土地肥沃、水源充沛,满足了农作物的灌溉等基本需要;其次,从气候来看,中华文明位于欧亚大陆的东部,太平洋西岸,跨越了热带和温带两个气候带,非常适合农作物的生长;第三,从外部环境来看,东海西漠,北雪南莽的封闭式的环境,很难让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原始初民超越这些自然环境。
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下,农耕文明诞生了,农耕文明具有靠天吃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秋收冬藏、不违农时等特点,这些特点带给原始初民的心理体验,就是天人合一、顺应自然、乐天知命、尚同不争等。
综上可知,中西文明起源于两种完全不同的自然环境,我们虽不是环境决定论者,但不同的自然环境带给中西原始初民不同的心灵体验,不同的心灵体验对中西原始初民的思维方式、语言系统、民族性格起了巨大的模塑作用。正如“地方的自然类型和生长在这土地上的人民的类型和性格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个性格正就是各民族在世界历史上出现和发生的方式和形式以及采取的地位”。(20)[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第74页。
二、英汉语言与英汉思维模式对比
由于语言与思维密不可分、相辅相成,且是同质而异名的关系,因此,对英汉语言的词法和句法特点进行对比,则可以为进一步揭示英汉思维特点及中西医思维特点打下坚实的基础。正如“语言的语法构造及其基本词汇是语言的基础,是语言特点的本质”。(21)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论语言学中的马克思主义》(1950年6月20日),载《斯大林选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517页。而“语言乃精神的自我显启,语言结构的差异也即精神显示的不同形式”。(22)[德]洪堡特:《洪堡特语言哲学文集》,姚小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序言,第4页。可见,一种语言中的词法和句法,则是一个民族最基本思维模式的反映。因此,将英汉语的词法和句法进行对比研究,对揭示相应的思维模式就显得尤其的重要。
(一)主客合一思维与主客二分思维
汉英语言系统分别诱导了主客合一与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而这些思维模式在各自的词法和句法结构中均有相应的体现,而相应的词法和句法结构又进一步强化了相应的思维模式。
1.汉语词法和句法体现主客合一思维
第一,从汉语词法来看,汉字主要是象形文字,象形文字的造字方法即为“画成其物,随体诘诎”,(23)许 慎:《说文解字》,徐 铉等校定,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316页。即通过对事物本体形象性的描绘,然后对事物本体再进行抽象概括,形成具有图画性的文字符号,而形声、会意等构词方式,均是以象形为基础的。可见,汉字造字的基本意象图式就是观物取象,以天人合一为基础的。因为从文字本身,可以直接看到事物本体的诸多特点,而这些特点正是对事物本体形象性的模拟,体现了主客合一的特点。因此“中国人只要用汉语言文字来思考写作,就注定会有天人合一的思想产生”。(24)辜正坤:《中西文化比较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33页。
第二,汉语句子里的词和句子,必须通过宏观的语境才能理解。正如“在汉语里,上下文的含义是理解的基础”。(25)[德]洪堡特:《洪堡特语言哲学文集》,姚小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169页。汉语的词义和句意,只有放入一定的语境中才能被明确,这正是汉语句法“天人合一”整体观的语言学依据。
第三,汉语句子的主语往往是人,谓语动词也往往是有灵动词。正如“汉语的‘有灵动词’一般只能与人称搭配,因为根据汉人的思维习惯,人或社会团体才有这类有意识、有意志的行为”。(26)连淑能:《英汉对比研究》,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08页。汉语的人称倾向,正是中国人主体意识的反映。汉人的思维是以人为中心的思维。正如孟子所言“万物皆备于我”,(27)《孟子》,万丽华,蓝 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290页。以及“人与天地相参”(28)《黄帝内经》,姚春鹏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1446页。的主客合一思维方式。
第四,汉语句式中的主语可以变换、可以隐藏。受“主客合一”思维的影响,汉语主谓结构中的主语,往往可以变换甚至隐藏,不像英语中的主语必须显性化、明确化。正如“西洋的语法通则是需求每一个句子有一个主语的,没有主语就是例外,是省略。中国的语法通则是,凡主语显然可知时,以不用为常,故没有主语却是常例,是隐去,不是省略”。(29)王 力:《中国语法理论》,载《王力文集》第1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4年,第52页。
2.英语词法和句法体现主客二分思维
第一,英语单词和字母均是抽象符号,斩断了人与自然之间的联系。正如“印欧语系的文字,是完全符号化的,缺乏象形味,你看到这种拼音文字以后,不可能立刻把这种文字跟外部自然界联系起来,因为它已经失掉了人这个主体和外部自然界这个客体之间息息贯通的诱导因素”。(30)辜正坤:《中西文化比较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19页。
第二,英语往往以物称为主语,体现了西方人主客二分的对象性思维。物称主语表明西方人主客分明、区分了自我意识与认识对象,从而把认识对象客体化,把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对立起来。正如“思维的本质在于把自身的进程分为若干片段,并将自身活动的某些部分构成一个整体;如此构造起来的东西既相互有别,又都作为客体对立于思维主体”。(31)[德]洪堡特:《洪堡特语言哲学文集》,姚小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1页。
第三,英语句法的主谓结构,亦是“主客二分”思维的具体体现。考察英语的几种基本句式,每一种句式都必须含有主语和谓语,这是整个英语句法的核心和基础。
综上可知,英汉语法与英汉思维是相互照应的,英汉语言的词法和句法分别诱导了“主客二分”与“主客合一”的思维模式。“主客二分”的思维在西方人的思维中有诸多体现,如黑格尔的“精神与实体”、宗教中的“此岸与彼岸”、哲学中的“现象与本质”、西医中的“药食二分”等;“主客合一”的思维模式在汉人思维中亦有诸多体现,如“文史不分”“书画同源”“家国一体”“药食同源”“兵民一家”等。
(二)整体性思维与分析性思维
汉语以及以英语为代表的印欧语系语言,分别诱导及反映了整体性思维与分析性思维,这些思维特点,在相应的词法和句法结构中均有相应体现。
1.汉字词法和句法体现整体性思维特点
汉语是一种典型的分析语。所谓分析语,指的是不用形态变化,而用语序及虚词来表达语法关系,高度依赖于语境才能理解语义的语言。正如“(汉语)由于有语境的提示和补充,有说—听双方在交际意图上的相互配合”。(32)徐通锵:《“字”和汉语的句法结构》,载李瑞华《英汉语言文化对比研究》,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448页。
首先,从汉字词法来看。正如“汉字构形体现了汉民族的文化心理”。(33)申小龙:《汉字思维》,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1页。由于汉字往往是单音节字,汉字没有性、数、格的变化,汉语的基本单位就是字,汉字恰如活字印刷一样,在中文表达中扮演着核心作用。《文心雕龙·章句》指出:“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34)刘 勰:《文心雕龙》,王志彬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393页。正因如此,汉字的词法对汉人的思维具有重要的模塑作用。
许慎通过六书对汉字的构词法进行了解释,即“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形声,四曰会意,五曰转注,六曰假借”。(35)许 慎:《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316页。六书第一次较为系统地阐述了汉字的构词方式。指事中的“事”,虽然指代的是抽象概念的字,如上、下,但是却有“视而可识,察而可见”的效果,具有模拟事物本体的元素。此外,形声字亦是在象形的基础上演化发展而来的,正如“形声字是复体字,都是一声一形”。(36)高 明:《中国古文字学通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4页。会意字亦是以象形为基础的,因为“会意字是在象形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新的字体结构”。(37)申小龙:《汉字思维》,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57页。此外,假借字的出现,是由于许多抽象的事物难以造像,许多具体的事物亦难以描绘。同时,假如一事一字,而字有不可胜造之数,此必穷之数也。假借字可救造字之穷而通其变,假借字便应运而生。但假借字并不造新字,假借字使汉字的表词功能大大增强。实际上,转注和假借,是汉字在使用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表词现象。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讲,二者均不应该被理解为造字法。
汉字的演变大致经历了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隶书、草书、楷书和行书这样一个过程。可以说,甲骨文属于最早的较为成型的汉字。根据申小龙对甲骨文意指方式的统计,“甲骨文以象形、象意为主要意指方式,两者加起来占三分之二强,形声也有大量的使用,约占四分之一,指事字很少,约占百分之二”。(38)申小龙:《汉字思维》,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90页。可见,汉字是一种表意文字,而象形、象意为其主要的构词方式和意指方式。汉字所诱导和表现的即是“主客合一”的心理结构,这种结构亦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合一思维方式的体现。
汉字的词法主要是以象形为基础的,这种以象形为基础的汉字思维,即是象思维。汉字的象思维正是基于对事物本体形象性的整体把握,而形象思维正是整体思维的具体体现。正如“形象思维是从整体上对对象认知,所以不必再把‘整体’加上”。(39)钱学森:《钱学森书信选》,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8年,第797页。中医中的取象比类的思维模式,正是来源于《易经》中的象思维。所谓取象比类,就是运用感性、形象以及直观的概念和符号,表达对象世界的抽象含义,这就是所谓的“引易入医”。正如“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40)《周易》,杨天才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373页。象思维成为群经之首《易经》最重要的思维模式。正如《易传》所言:“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相之。”(41)《周易》,杨天才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358页。可见,卦象实际上既有象的形式,又是对世界变化之象的模仿。这种功能动态模型,正是人类基于象形文字的象思维的最原始运作。此外,《易经》中的卦象虽然数量上有限,但是它们在功能上却可以“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42)《周易》,杨天才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367页。以及“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则天下之能事毕矣”,(43)《周易》,杨天才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349页。可以把天下万事万物全部概括起来,形成整体性和统一性的认识,这正是整体性思维的体现。由于“汉字都是四方四正的,它的偏旁部首伸向上下左右、四面八方,它强有力地暗示这种文字的使用者看问题须全面、综合,各个方面都要考虑到”。(44)辜正坤:《中西文化比较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1页。
其次,从汉语的句法来看,汉语句法是以整体语境为核心的句法结构。认知汉语语境的整体性,正是汉语句法整体观的表现。汉语没有曲折变化,一个词很难靠自己本身确定其含义,必须依赖于语境甚至语感才能确定其意义,“汉语的这一特点与汉人注重整体关联性的思维方法(relational thinking)有关”。(45)连淑能:《英汉对比研究》,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29页。
第三,从汉语句法来看,汉语地名由大到小的排列、汉语姓名先姓后名的排列,反映了由整体到个体、由家族到个体的思维方式,这正是整体观思维模式的反映,而这种整体思维模式又进一步强化了汉语相应的句法结构。
2.英语词法和句法体现分析性思维特点
英语是一种典型的综合语。所谓综合语指的是,运用形态变化,即通过性、数、格等的变化来表现语法关系的语言。由于词的本身已有很强的语法标识,很容易诱导出注重微观、分门别类的思维。正如“印欧语系的语法系统容易诱导形成分门别类的思维模式”。(46)辜正坤:《中西文化比较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1页。
首先,英语的字母和单词均是抽象的符号,完全摆脱了模拟事物本体象形的痕迹。属于典型的“睹字识音,据音断义”拼音文字。英语单词本身形象思维的欠缺,恰好被善于抽象思维的优势所弥补。毫无疑问,英语这种纯粹化的符号系统,善于进行高度抽象的逻辑分析,善于步步为营式的逻辑推理。
其次,从英语的句法来看。英语必须有主谓结构,这也正是印欧语系中主客二分思维方式的体现。正如“英语句子必须有主语和谓语。这种结构导致了同一律的概念,这是亚里士多德逻辑的基础”。(47)Meskill,John.(ed.),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Civilizatio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3,p.599.哲学上同一律指的是,每一个“个体”都是“一”,具有独特性,即完全与自己等同,与别的所有事物均有不同的特性。同一律正是强调个体、注重微观的思维方式。
第三,英语单词本身有性、数、格、词尾变化,其词义、词类、语气、语态等本身就能靠自己确定,对语境的依赖性极小,英语的句法形成了以单个词为基础的句法特点。
第四,英语句法特点是时间、地点从小到大的排列,姓名中把表示个人的名放于代表家族姓前,亦是注重个体的分析型思维模式。
综上可知,汉语的词法和句法诱导了整体性思维特点,正因为是整体性思维,故在中医思维中往往采用联系的、辩证的观点治疗;印欧语系的句法强调每个单词的独立身份,诱导了典型的分析性思维模式,注重个体本位。在西医的思维方式上则强调靶向用药、局部用药,往往用静止、孤立的观点治疗。
(三)辩证性思维与逻辑性思维
由于“人类思维中从概念的形成到推理的展开,都需要有语言的形式的‘模铸’而形成和巩固,同时又向前推进了人的认识。因此,语言形式和思维形式、思维方式有着密切的联系。各民族不同的思维方式,必然深刻影响与之相应的语言形式,反之亦然”。(48)申小龙:《汉字思维》,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102页。汉语和英语的词法和句法,不仅分别诱导了辩证性思维和逻辑性思维,而且亦分别是这两种思维模式的反映。
1.汉语词法和句法诱导辩证统一思维
首先,从汉语的词法来看,汉语的词法完全体现了汉人的辩证思维,具体表现在:
第一,汉字的象形与象意造字法体现了二元辩证统一思维。古汉字是以象形为基础的,但象形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采用形声相益的办法造字,而形声相益正是汉字辩证思维最直接的体现。由于语言的经济性和省力性原则,大部分象形字都是以偏概全、画部分以代整体。如“目”,因为左右对称,所以以一目代二目;“看”的上面是“手”的变形,下面为“目”,意为用手遮目以望远;“伐”的古文本意是“以戈击颈”等。正如“作为文字构形的一种手段,这种以部分代全体的造字方式,使用了一种经济实用的手法,又为造字者和识字者所共同认可,体现了象形与象意的辩证关系”。(49)申小龙:《汉字思维》,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105页。此外,由于“(汉字)基本上是以二合为基础的。也就是说,象形汉字的孳乳,是一个由‘一’到‘二’的过程,由单体到合体的过程,由简单象形到会意象形的过程。言此而意彼,据义构形,最终实现两象融合的符号化过程。而会意,正是汉民族辩证思维的一种原始运作”。(50)申小龙:《汉字思维》,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106页。汉字的词法,基本是二元、二合结构为基础的。如“男”以“一田一力”会意、“竞”字古字以二人竞争会意、“从”以两人相随会意等。此外,汉字还有一种解释性的二合结构,如不正为“歪”、少力为“劣”等。
第二,汉字的音义关系亦是辩证的。汉字最初往往是单义的,随着社会发展,在隐喻和转喻的认知思维作用下,往往会发展成为一词多义。但是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一词多义还是无法满足生产和生活需求。正如“古代汉民族在造字时认识到,仅仅通过意义结构上的辩证二合,并不能满足汉字表达的功能;只有在音义关系上贯彻辩证二合的观点,才能从根本上完善汉字结构的表达功能。具体来说,就是需要为一形表多词的字加注形符以义别之,或加注音符以声别之”。(51)申小龙:《汉字思维》,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109页。汉字的音义辩证关系主要体现在,如上形下声:霖、茅;左形右声:肝、惊;内形外声:闻、阙等,通过内外、左右、上下等对立统一的关系来体现音义辩证二合的关系。可见,形声二合结构是一种较为成熟的表词方式,体现了二元辩证思维。
第三,汉字字形体现了二元辩证的平衡结构。内外、左右、上下是汉字典型的二元对立统一的平衡结构。上下结构,如贷、赏;左右结构,如材、炒;内外结构,如围、困等。此外,即使对于三个相同字符组合而成的字,为了平衡,也是采用极为稳定和平衡的“品”字结构,如众、淼、犇等。值得注意的是,为了保持汉字的这种平衡结构,二合结构总采用大小相见、阴阳协调的基本布局,并不是二元相等,而是有大有小的基本布局。如左小右大的捧、搁、溯等;左大右小如创、影、乳等;上小下大的如室、家、它等;上大下小的如点、品、众等。
第四,汉字的音节体现了二元辩证结构。汉字的音节有声母和韵母,声母和韵母正体现了对立统一的二合结构,声母与韵母有区别,但二者只有协调才能发出声音。正如“韵母内部韵头有开合、洪细的对立,韵尾有阴声韵、阳声韵的对立。汉语的声调既有高低的对立,又有平仄的对立,还有舒促的对立。因而汉语的音律具有整体的平衡美”。(52)申小龙:《汉字思维》,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116页。
第五,汉字有四个声调,分为阴平、阳平、上声、去声。一句话只有按照阴阳、上去的声调排列,才能形成抑扬顿挫、高低起伏之感,尤其是律诗等还讲究声调平仄的对立统一,只有这样才能形成汉语特有的音律美。此外,汉字中有众多的一字多音现象,如“发”“强”“正”等,这种现象的出现,其根本原因在于调和句子的阴阳平衡,更好地体现汉语的音律之美。
第六,有些汉字的字形从不同角度看均表示同样的字,亦是一种辩证思维的体现。如米、回字等。
第七,从汉语语法范畴来看,汉语语法范畴会随着表达的需要而不断变换。汉语中,尤其是古汉语中虚词和实词相互转化的例子比比皆是。正如“汉语虚实词内部及两大词类之间的相互转化极为普遍”。(53)林汝昌,李曼珏:《中西哲学观对汉英语言之影响》,载左 飚《冲突·互补·共存》,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251页。而词义的虚实转化正是辩证思维的具体体现。
其次,从汉语的句法来看,汉语句法亦体现了典型的辩证思维。汉语句法的辩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汉字由于没有曲折变化,由此汉语句法可以左右通读而逻辑通顺。左右通读既可以意思完全一样,如: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南江客运站运客江南;亦可以意思不一样,如:我怕太太,亦可以理解为太太怕我。汉语的句法体现了“正反相成、对立统一”的特点。正如“一阴一阳谓之道”,(54)《周易》,杨天才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340页。由阴阳又可以进一步演化为缓急、君臣、正反等辩证统一的关系,中医讲求正治与反治,正是基于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第二,从书写及诵读方式来看,汉语句子既可以从左至右书写诵读,亦可以从右至左书写诵读。体现了双向二元的辩证思维模式。
第三,从汉语的语音特点来看,汉语语音特点亦是二元对立统一辩证思维的典型体现。正如“汉语的双音词往往用双声叠韵的关系构成,一个双音词构成一个音步。汉语中四字格成语的大量运用就是因为它由两个音步构成,适于表现汉语独特的‘一分为二’的音乐性。汉语成语的声率也是平仄相对。而西方语言以多音词较为普遍,且词中以辅音占优势,因而无法达到如汉语这样的二元对立统一的局面”。(55)林汝昌,李曼珏:《中西哲学观对汉英语言之影响》,载左 飚《冲突·互补·共存》,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250页。
2.英语词法和句法诱导逻辑思维
第一,英语字母及单词均是抽象化的符号,这些符号虽然与所指没有任何形式上的相似性,但这恰好构成了进行逻辑推理的前提。正如“(印欧语系的文字)尽管把文字的自然性特点抹掉了,但是它的书写形式造成一种回环勾连。如溪水长流斩而不断的流线效果,容易诱导人们去注重事物的联系性。这种状态和其语法形式共同起作用,极大地强化了印欧语系民族对事物的表面逻辑联系的感知能力”。(56)辜正坤:《中西文化比较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19页。
第二,英语句法的显性逻辑,大大促进了逻辑推理的明确性。英语对句子之间的逻辑性有非常明确的限定。如句子之间的逻辑必须明确化、显性化。此外,由于逗号不能体现句子的逻辑关系,只能体现停顿,因此逗号不能连接两个独立完整的句子,可以通过句号、分号、加连词、使用非谓语动词、独立主格、主从复合句等众多表达逻辑关系的手段来明确化,这也是导致英语句子句意明确、很少含混的重要手段,同时亦强化了英语的逻辑思维。
综上可知,英汉语言特点与其各自的思维模式是互为关照的。汉语的词法和句法体现了二元辩证统一的思维,辩证思维是双向的,与逻辑思维相对,这种思维在中医的治疗理念上则体现为正治与反治、标本兼治等多种治疗方法;而以英语为代表的印欧语系,则诱导了逻辑思维,西医的逻辑思维则体现了典型的步步推导、有理有据,常采用单向治疗法。
(四)悟性思维与理性思维
汉语句法是宽式句法,所谓宽式句法,就是没有性、数、格等曲折变化。而以英语为代表的印欧语系语言是严式句法,即单词的性、数、格、语气、语态等,都要通过单词的曲折变化表现出来,故“印欧语言是严式语言,汉语是宽式语言”。(57)陈保亚:《语言影响文化精神的两种方式》,《哲学研究》1996年第2期。前者诱导了悟性思维,而后者则诱导了理性思维。
1.汉语词法和句法诱导悟性思维
第一,从汉语语音来看,汉语是单音节,同音词较多,很容易造成仿拟现象。如“有痔之士”“咳不容缓”“努力战痘”等。
第二,从汉语句法来看,古汉语由于没有标点,一个句子可以在不同的地方停顿,逻辑亦通顺,但含义却不同。如“这个苹果不大,好吃”与“这个苹果不大好吃”表达的含义迥异;此外,汉语中大量的谚语、歇后语,正是汉语悟性思维的具体表现。如:白骨精说人话——妖言惑众、长颈鹿进马群——高出了头、半山崖的观音——老实(石)人等,汉语歇后语的后半句必须要靠悟性思维才能理解。此外,由于汉字没有屈折变化,即没有性、数、格的变化。因此,汉字往往像活字印刷一样,一句话中的各个汉字甚至可以打乱重新排列,从而赋予句子新意。如于右任的“不可随处小便”,重新排列可以“小处不可随便”,所体现的句意则完全不同。
第三,汉语句法的隐形逻辑。汉语句法之间的逻辑往往是隐性的,由听者或读者自己去理解,无须像形式逻辑那样步步推导。正如“汉语看重的是概念意义的一致性,并不关心形式上的一致性”。(58)[德]洪堡特:《洪堡特语言哲学文集》,姚小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130页。汉语句法的隐形逻辑不仅是悟性思维的体现,同时亦强化了汉语的悟性思维。
第四,汉语主谓结构的模糊性,亦是汉语悟性思维的重要语言学依据。汉语的主语往往可以隐藏,甚至一组句子之间的主语实现了转移和变化也都是在隐藏的情况下实现的,这些都需要听者自己去把握。比如“今天很冷,(有人)已经打过电话了,(暖气公司)明天就来装暖气,(暖气片)最多三天就能装好”。正如“中国言语的构造上主语与谓语的分别极不分明,换言之,即可以说好像就没有这个分别。这是中国言语构造上的最特别处,而其影响则甚大”。(59)张东荪:《从中国言语构造上看中国哲学》,载《张东荪文选》,张汝能编选,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第334页。也就说,在汉语中“句子中‘谁’在说话不重要,只要有‘话’就行了——也就是说主语与谓语身份模糊,难以明察”。(60)尚 杰:《中西:语言与思想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84页。张东荪曾以汉语表达式“走得快”为例进行说明,由于汉语缺乏曲折变化,名词与动词在形式上是完全一样的,当“走”被理解为名词时,固然可以理解为所谓的主语;但“走”亦可以理解为动词,其就变成了谓语。可见,主语与谓语没有严格的界限,可以随意切换,以及主语的隐藏与变换都需要听者自己去把握,汉语的表意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其句法和意义的飘忽不定都需要听者在其心灵上打上相应的符号。
2.以英语为代表印欧语系诱导理性思维
第一,英语的词法需要性、数、格。英语单词有单复数、有主宾格等形式,要根据在句中所做的成分,而选择相应的不同形式。
第二,英语句法需要显性逻辑。有标点、非谓语动词、独立主格、主从复合句等众多表达逻辑关系的手段。
第三,英语句法要求语法一致、意义一致和就近原则,这是英语句法的三大基本原则。所谓语法一致主要指的是主谓的单复数一致;意义一致主要指的是主语形式上为复数,但意义上为单数,则谓语也需要使用单数;就近原则指的是,谓语动词的数必须与其最靠近的主语的数保持一致。
第四,主谓结构是英语句法的刚性要求。英语所有的基本句式都必须有主语和谓语。正如“英语句子有严谨的主谓结构。主语不可或缺,谓语动词是句子的中心”。(61)连淑能:《英汉对比研究》,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51页。英语句中的主语不能隐藏、亦不能变化,如需变化,必须明确说明。
综上可知,汉语的句法往往省略了中间的、内部的逻辑,实现了思维的跳跃性,有的时候甚至使用违反逻辑的表达。如“养病”,表面上看是违反逻辑的表达,其实是省略了形式逻辑的“因果关系”,表示“因为生病所以需要休养”。要理解“养病”的真实含义,必须需要悟性思维才能做到,而这种隐含的、省略式的逻辑无疑是“意合”句法的一种体现,而这种“意合式”的句法,无疑能够诱导出悟性思维。按照印欧语系显性逻辑的理性思维来认知汉语的这种特点,无疑汉语省略了很多中间的部分。正如“汉语让听者自己去添补一系列中介概念,而这等于要求精神付出更多的劳动:精神必须弥补语法所缺的部分”。(62)[德]洪堡特:《洪堡特语言哲学文集》,姚小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133页。英语正是靠这些刚性的语法形态,保证了句子的一致性、完整性,从而让句子在人称、意义、性、数、格等方面保持一致,从而也保证了英语句法的刚性和思维的理性。
(五)主体思维与客体思维
由于“文字构形要解决的不是事实问题,而是意义问题,即客体与人的关系问题;在一般情况下,甚至不是真假问题,而是价值选择问题,即客体与人的情感需求的问题”。(63)申小龙:《汉字思维》,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122页。汉英语言亦体现了主体性思维和客体性思维的特点。
1.汉语词法和句法诱导主体性思维
第一,从汉字最初的造字方式来看,皆体现了人的主体性。正如“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64)《周易》,杨天才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367页。这说明汉字造字的基本方法就是“俯仰之间”,而“俯仰之间”只能靠人去完成。因此,万物之象皆有造字者主体思维的印记。
第二,从汉语词法来看,汉字的构形体现了造字者本身的主体视角。汉字是以象形为基础的,但是汉字却取“人象”而不是“物象”来表意,充分体现了人的主体地位。如“首”,物皆有首,但取人首之象;又如“身”,动物皆有身,但从“有大肚子的人”来取象等。正如“汉字的构形及其发展凝聚着汉民族观察探索外在世界及其自身主观世界的思维和心智的轨迹,有清晰的造字者和使用者的主体视角”。(65)申小龙:《汉字思维》,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119页。此外,汉字构形的主体思维还体现在以人体而不是以物体的偏旁构字,如常见的有“眼、口、头、手、足等”,相应的汉字有“睡、甘、颜、友、逐等”。
第三,从汉语句法来看,汉语往往是以人为主语。汉语句子主张“事在人为”“万物皆备于我”,注重人的主体意识,句子往往以人称为主语,因此“汉语的人称倾向反映了中国人的主体意识”。(66)连淑能:《英汉对比研究》,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16页。
2.英语句法诱导了客体性思维
第一,从英语的词法来看,英文单词都是由字母组成。从英语单词本身看不见其与自然万物的任何痕迹,已经完全被抽象化、对象化、客体化了,抽象的字母和单词里面看不到任何造字者的主体元素。
第二,从英语句法来看,英语往往是物称主语。正如“英语的非人称倾向反映了西方人的客体意识”。(67)连淑能:《英汉对比研究》,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16页。英语中往往使用物称主语,而谓语往往用有灵动词,体现了英语的客体思维。
第三,从英语句法来看,英语往往亦通过被动语态来体现客体思维。尽管很多表示被动的过去分词已经形容词化了,但其表示被动的含义还在。被动语态体现客体思维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直接以物称为主语且省略动作的发出者,如“书籍已还”;其二,以人称为主语且保留动作的发出者,而动词的过去分词往往形容词化,构成系表结构。如汉语“她喜欢电影”,如果通过分词翻译的话,则翻译成英语的时候必须译作“She is interested in films”(她被电影感兴趣了),强调的是“电影”这个客体的作用。
综上可知,英汉语言的词法和句法分别体现了客体思维与主体思维的特点,由于语言与思维“同质而异名”的关系,相应的思维特点又会进一步强化相应的词法和句法特点。
三、英汉语言与中西医思维模式
由于语言与思维相辅相成,不可分割,二者是同质而异名的关系。因此,语言特点与思维特点是相互照应的,西医体现了典型的印欧语系的思维模式,而中医则体现了典型的汉语语言系统所诱导的思维模式。
(一)西医与中医的对抗性治疗和调和性治疗
1.西医的对抗性治疗
西医受到“天人相争”和“天人二分”思维的影响,对待疾病主要采取对抗性治疗、支持性治疗,具体体现在:
第一,西医讲究杀菌、灭菌、消炎,注重症状的消失。比如,西医对待肾病的治疗,往往使用抗生素采取抑制炎症的办法来延缓病情,但是消炎的同时往往也会杀死大量的免疫细胞,引起较为严重的副作用,甚至影响了肾脏的正常功能。在严重情况下,西医甚至干脆使用肾脏透析来代替肾功能,甚至直接移植新的肾脏。
第二,西医认为,人生病的根源在于病菌感染和侵扰了肌体,通过消除病菌,则疾病自愈。西医往往以对症支持治疗为主,主张对症下药。正如“西医药物主要为抗病毒药物、抗感染药物及辅助支持药物”。(68)夏文广,安长青:《中西医结合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34例临床研究》,《中医杂志》2020年第2期。西医对抗性治疗理念,反映在语言中就是西医术语中含有大量的表示“抗”“杀”“斗”的词汇。正如“西医术语中常见‘anti-(抗)’、‘kill(杀)’、‘fight(斗)’等字,如antigen(抗原)、antibody(抗体)、antibiotics(抗生素)、anticoagulation(抗凝剂)、bactericide(杀菌剂、杀虫剂)、parasiticide(杀寄生虫药)、fight against pandemics(对抗传染病)等。”(69)刘 峥,梅德明:《中西医语言认知差异及其战争隐喻分析》,《外语电化教学》2015年第4期。
2.中医的调和性治疗
中医受到“天人合一”思维的影响,主张调和性思维治疗,具体体现在:
第一,中医的象思维。所谓象思维就是取象运数的方法。正如“中医所谓的‘象’指直观可察的形象,即客观事物的外在表现。‘取象’是为了归类或类比,它的理论基础是视世界万物为有机的整体。中医以‘象’构建了天人相合相应、人的各部分之间相合相应的理论体系”。(70)张其成:《“象”模型:易医会通的交点——兼论中医学的本质及其未来发展》,《周易研究》2002年第2期。
第二,中医取象与四时相应,认为人体“证象”与天地运行、宇宙万物的消长是紧密相关的。正如《素问·阴阳别论》:“人有四经十二顺,四经应四时,十二顺应十二月,十二月应十二脉。”(71)《黄帝内经》,姚春鹏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76页。此外,中医针灸的“子午流注”的思维理念,亦正是这种“人与天地相应”思维的反映。
第三,中医认为,人生病的根源在于阴阳失调,治病的根本在于调和阴阳。正如《黄帝内经》指出:“实则泻之,虚则补之。必先去其血脉,而后调之,无问其病,以平为期。”(72)《黄帝内经》,姚春鹏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196页。中医中的阴阳失调又可以进一步引申为症状的寒热、升降等。故《黄帝内经》亦指出:“独热者病,独寒者病。”(73)《黄帝内经》,姚春鹏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197页。中医注重“热者寒之”“寒者热之”等,强调阴阳调和。同样对于肾病,中医认为是由于血瘀不畅、清浊不分引起的,通过行气活血、平衡阴阳即可。
第四,中医的调和性思维在中医术语中亦得到充分的体现,如调和身心、心态平和、调中理气、调和营卫等。正如“据统计《中医方剂大辞典》中以‘和’字为首的方名就有298个,诸如‘和中、和气、和血、和胃、和胎、和解’等等不胜枚举”。(74)刘 炜,林文娟:《中医、西医术语文化渊源比较》,《医学争鸣》2014年第3期。
(二)中西医的整体性思维与分析性思维
汉语语言系统诱导了“天人合一”的思维,这种思维亦正是整体性思维的体现,此外,整体性思维亦包含了辨证论治的思维模式;以英语为代表的印欧语言系统,诱导了“天人二分”的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方式往往把主体与客体、物质与精神、此岸与彼岸等对立分割开来,分析性思维的显著特点是,注重对物质世界的无限分割、注重微观世界,这也是西医思维的典型表现。
中医是整体性形象思维。正如“中医里的‘证’(辨证论治)即人体的整体状态。形象(直感)思维是系统整体思维”。(75)钱学森:《钱学森书信选》,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8年,第774页。而西医恰好是局部性的,很多时候甚至强调靶向用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缺乏整体性思维。正如“近年来我们这些人一直讲人体是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就是这个意思。所谓现代医学科学,即西医的弱点即在于此”。(76)钱学森:《钱学森书信选》,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8年,第771页。
1.西医的分析性思维
以英语为代表的印欧语系,诱导了西方的分析性思维。分析性思维指的是,一次前进一步为特征,包括归纳推理、演绎证明等逻辑思维。其基本特点,是将个体从整体中剥离,将其分离成分别的个体,探索各个个体的本质属性,然后总结规律形成对事物的判断。正如“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比较显著的特点就是注重分析,西方分析思维比较流行,比较占势力”。(77)张岱年:《中西哲学比较的几个问题》,载左 飚《冲突·互补·共存》,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339页。西医的分析性思维主要体现在:
第一,西医是局部、靶向用药,往往孤立地看问题。西医正是基于分析性思维的分类方法,往往“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但是从人体科学的整体观来看,割裂开了的手并不是整体意义上的手。
第二,西医分析性思维往往注重定量分析,注重仪器、相信数据,把人体当做一个机械的系统,容易陷入机械唯物主义的怪圈。而人体科学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人体科学亦是生命科学,不能仅仅靠仪器数据作为判断的标准。正如“一要注意不搞机械唯物论,盲目相信仪器;二要注意不搞简单化,把人体当做简单系统。仪器读数是表象,深层实质是复杂的,决不能‘一对一’”。(78)钱学森:《钱学森书信选》,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8年,第520页。
第三,西医没有把人的情绪和意识考虑到治疗过程中。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决定意识,但意识对物质具有反作用,西医的理性分析性思维把人的情绪排斥在外,这是西医的一大缺陷。而中医《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指出:“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79)《黄帝内经》,姚春鹏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60页。正如“中医讲究意识、情绪的重要性,这又是西医论者的大忌!他们以为讲科学就不能讲意识,不能讲精神,这也是个误解”。(80)钱学森:《钱学森书信选》,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8年,第52页。
2.中医的整体性思维
中医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人体器官的功能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人生活在一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当中,必定会受到二者的影响。中医的整体性思维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人体本身是一个完整整体。其整体性主要体现在:其一,结构上的整体性。即人体各个器官是相互联系的;其二,功能上的整体性。即人体各个器官的功能之间是相互联系的;其三,病理上的整体性。如肝属目,五脏之中,一脏有病,可以影响到其他脏腑,而且体内有病,亦可以显现于体外,“有诸内,必行诸外”;(81)《孟子》,万丽华,蓝 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273页。其四,治疗上的整体性。局部病变是整体病理变化的反映,故“从阴引阳,从阳引阴”“病在下者高取之,病在上者下取之”。(82)《黄帝内经》,姚春鹏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950页。
可见,中医强调要从整体着眼,从宏观入手,化繁为简的思维方式,从宏观上研究中药对人体产生什么影响。如生姜暖胃、麻黄出汗,而不会从微观的分子结构上考虑药物对人体的影响。中医讲“肚腹三里留”,即肠胃消化不良按摩足三里穴位即可。中医认为,人体的经络是一个整体,尤其是通过穴位和经络的按摩等,让整个身体好起来,免疫系统得以扶正。
第二,人与自然环境是有机统一的。这种有机统一性主要体现在:其一,人体的生理变化以及生活方式会受到环境和气候的影响,故“春三月,此谓发陈。天地俱生,万物以荣。夜卧早起,广步于庭。披发缓形,以使志生”。(83)《黄帝内经》,姚春鹏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26页。其二,不同的自然环境往往会导致不同的疾病,即有些疾病是季节性的。如“长夏善病洞泄寒中,秋善病风疟”。(84)《黄帝内经》,姚春鹏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46页。其三,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与自然环境紧密相关。由于人体会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因此养生保健亦应该顺应自然规律,即“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
第三,人与社会环境是统一的。人不仅是自然的产物,亦是社会的产物,亦会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因而社会地位的剧烈变化亦会导致人生病。如《素问·疏五过论》指出:“故贵脱势,虽不中邪,精神内伤,身必败亡;始富后贫,虽不伤邪,皮焦筋屈,痿躄为挛。”(85)《黄帝内经》,姚春鹏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773页。
第四,人与自身是统一的,即平人当形神兼备。所谓平人,即阴阳调和之人,中医把人的情绪及精神因素亦考虑在内,不仅把人当作一个活着的生命体,而且相信人的精神和情绪对疾病的康复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认为精神与形体乃生命的两大基本要素,缺一不可,二者相辅相成,构成一个完整的整体。故中医认为人有三宝:精、气、神。
(三)西医与中医的逻辑性思维和辩证性思维
西医的思维模式往往基于逻辑推理,步步推导,有理有据,注重定量分析,以逻辑思维为主,正如“西医考核脏腑血脉有理有据,推论病形,绝无影响之谈”;(86)吴汝纶撰,施培毅,徐寿凯点校:《吴汝纶全集》,安徽:黄山书社,2002年,第141页。而中医思维注重整体出发,以辩证思维为主,可以实行对疾病的“正治和反治”;此外,中医亦坚持“‘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的原则。”(87)张其成:《“象”模型:易医会通的交点——兼论中医学的本质及其未来发展》,《周易研究》,2002年第2期。可以说,辨证施治,正是中医最基本的特点之一。
1.西医的逻辑性思维主要体现在
第一,西医的诊断往往具有明确性和绝对性。逻辑思维讲究步步推导、有理有据,得出结论,因此西医的诊断是明确的,以便明确病原体,找出疾病的原因,对症下药。
第二,西医的逻辑性思维往往是单因单果,包含了非此即彼的精确性,往往是从微观具体的角度来考察疾病。
第三,西医的逻辑性思维是单向的,前后一贯的,而不可能自相矛盾的,不可能出现对疾病反治的情况,因为那是违反逻辑的。
2.中医的辩证性思维
第一,严格区别了“证”与“症”的关系。正如“‘证’,即证候,是疾病过程中某一阶段或某一类型的病理概括;而‘症’,即症状和体征的总称,是疾病过程中表现出的个别、孤立的现象”。(88)孙广仁主编:《中医基础理论》,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7年,第19页。因此,中医往往使用“证状”而不是“症状”来描述疾病。
第二,同病异治与异病同治。由于证候与病症的对立统一性,故中医亦可采用辨证治疗,同病异治指的是同一种疾病处在不同阶段,表现为不同类型,则采用不同的治疗方法;异病同治指的是,不同的疾病,如果表现出来的症候相同,则可以采用相同的治疗方法。如子宫下垂、胃下垂、脱肛等不同的病变,大都是由于中气不足引起的,故均可使用补中益气的方法来治疗。可见中医主张证同则治同,证异则治异,这就是辨证论治的实质。
第三,正治与反治。由于在错综复杂的治疗过程中,有疾病与证候一致者,亦有疾病与证候不一致者,故有正治与反治之说。正如《素问·至真要大论》指出:“逆者正治,从者反治。”(89)《黄帝内经》,姚春鹏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753页。
综上可知,西医逻辑思维往往是单因单果论,往往是从微观的角度,而且逻辑思维在推导过程中很难得出互为因果的结论,没有从宏观的角度看待疾病;而中医辨证论治往往是整体思维影响的结果。
(四)西医的理性思维与中医的悟性思维
英语的刚性句法如性、数、格的一致,以及时态语态等曲折变化等特点,诱导了英语的理性思维,汉语的柔性句法,诱导了汉语的悟性思维,二者分别影响了西医和中医的思维方式。
1.西医的理性思维
第一,西医注重定量分析。西医疗法有理有据主要来源于西医思维采用形式逻辑,注重因果逻辑,层层推进,通过数据分析,显得严谨理性。西医诊断往往借助仪器对疾病的指标进行量化,如听诊器、显微镜、叩诊锤、血压计、体温表等,对疾病的诊断和认知以数据为准。
第二,西医注重微观分子结构,以还原论为基础。西医是建立在近代自然科学基础上的医学,是基于观察、假设、求证的逻辑推理的基础上的,生命特征往往依靠器官组织的功能和结构来说明,疾病都是基于器官机能以及生物机制的紊乱来解释,对疾病的诊治都是基于生物指标的量化来进行。通过定量分析,逻辑推理,从而找出病因。正如“正是应用这样的方法,西医学对人体正常或异常的结构和功能、对影响人体健康和疾病的各种因素,从宏观到微观再到超微,认识越来越深入、深刻”。(90)赵春妮,吕志平:《中西医结合导论》,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0年,第166页。
第三,西医思维往往以解剖生理学、组织胚胎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作为基础。西医认为,疾病是由于人体器官发生病理变化引起的,因此治疗多以恢复这些脏器实体的正常功能即可。对于人体器官,如心脏,西医往往只是理性的对器官实体本身的考察,西医是典型的形而下的具象性的思维。如“人之所思在脑不在心”,是典型的西医思维方法,而中医的思维层次却是形而上的,如“心为君主之官”。
第四,西医的理性思维还体现在对事物的分类。西医分为众多的专科,如外科、内科、五官科等,体现了对事物范畴化的科学精神。
第五,西医的理性思维,还体现在往往排斥了人的主观情绪和意识的作用。对于研究人体科学以及生命科学而言,西医没有意识到意识、情绪能对物质产生巨大的反作用。
2.中医的悟性思维
第一,“医者,意也”是中医悟性思维中最核心的要素。正如孙思邈指出:“医道之为言,实惟意也。故以神存心手之际,意析毫芒之理。当其情之所得,口不能言;数之所在,言不能谕。”(91)孙思邈著,李景荣等校释,《千金翼方校释》,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8年,第397页。
第二,中医悟性思维不仅是“主客不分”“天人合一”思维的体现,也是汉语柔性模糊句法结构的反映。《黄帝内经》中《素问·八正神明论》指出:“神乎神,耳不闻,目明心开而志先,慧然独悟。口弗能言,俱视独见,视若昏,昭然独明,若风吹云,故曰神。”(92)《黄帝内经》,姚春鹏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243页。“医者意也”正是基于“万物一体”的认识,从而以自然之物来比喻人体之证象。正如《灵枢·岁露》指出:“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故月满则海水西盛,人血气积”(93)《黄帝内经》,姚春鹏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1446页。。
第三,中医的思维是形而上的,不是形而下的。正如“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94)《周易》,杨天才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362页。因此,中医的思维是意象性的、悟性的,不是具象性的。正如“西医说血就是循环的血罢了,说气就是呼吸的气罢了,说痰就是器官分枝里分泌的痰罢了。老老实实的指那一件东西,不疑不惑。而中医说的血不是血,说的气不是气,说的痰不是痰。他都别有所指”。(95)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42页。
综上可知,以英语为代表的印欧语系的刚性句法诱导了理性思维,西医的理性思维强调了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具有知识容易传承、诊断有理有据等优点;而汉语的柔性句法诱导了悟性思维,但中医悟性思维往往更难以把握和传承。
(五)西医与中医的主体思维与客体思维
印欧语系的思维模式往往是对象性的、客体性的思维,把世界当做认知的对象,而且把认知主体与认知客体对立起来。正如“思维的本质在于反思,即区分思维者和思维内容”。(96)[德]洪堡特:《洪堡特语言哲学文集》,姚小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1页。而汉语的思维是主体思维,且是把认知主体与认知客体合二为一的思维。
1.西医的客体思维
第一,西医治病是针对性极强的。西医的客体思维体现在找出具体的病原体、病毒,然后杀死病毒,消灭病原体,疾病自然就好了,可见,西医是见病不见人。
第二,西医的客体思维还体现在往往取代人体器官本身的功能。比如肾病,西医往往用仪器透析的方式替代肾脏的功能,甚至直接切除肾脏换成新的。
第三,西医治疗疾病是病越重、下药越猛。西医的客体思维认为,病情越重,则越需要下猛药,但下药越猛副作用可能越大,对身体的伤害可能越大。
第四,西医的客体思维还体现在治疗疾病最终必须依赖药物,由此导致西医的支持性治疗的理念。西医使用抗生素正是典型的杀戮的方法,通过药物杀死病原体,但杀死病原体的同时亦可能会导致人体自身免疫力的大幅受损,导致副作用大。
第五,西医注重治病。西医思维注重可以感知、量化的东西,追求的是存在,西医思维亦是一种典型的显性思维,显性思维决定了西医只有首先发现病原体,然后才能消灭病原体。
2.中医的主体思维
中医的主体思维体现在中医治病的根本理念是“扶正”,也即是说中医不是治病,而是治人。中医认为,人生病的根本原因在于正邪失调,即人体免疫系统遭到了伤害。中医关注的是人体自身的免疫功能,使用药物或者养生的方法,使人体功能恢复正常,达到“扶正祛邪”的目的。
第一,中医的主体思维主要是先分虚实,从病人身体状况本身出发。所谓分虚实就是指病人如果身体好,治病的原则就是祛病;如果身体虚弱,治病的原则就是扶正。所谓“正气存内,邪不可干”(97)《黄帝内经》,姚春鹏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814页。就是这个意思。
第二,中医的主体思维还体现在,认为战胜疾病的关键在于病人自己的免疫能力,即中医治疗往往以治本为原则。中医认为,人体战胜疾病最终还是要靠病人本身的免疫力,只有调理好身体本身,免疫力提高以后才能战胜疾病;中医同时认为,治病的最终目的就是让病人成为“平人”。所谓“平人”,即阴阳调和之人。正如“阴阳者,天地之道也,治病必求于本”。(98)《黄帝内经》,姚春鹏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50页。此处的“本”,就是阴阳,因此,要尽可能地带来小的副作用。可见,中医考虑治病的起点和终点都是以人为本,这也正是主体思维的体现。
第三,中医的主体思维还考虑到疾病所处病者主体的位置。如病在表,如体表;病在里,如肠胃;病在表里之间,如脏腑等,然后按照病人体质与疾病位置分为太阳病、少阴病、阳明病、太阴病、少阳病、厥阴病等,真正做到对症下药、对人下药。
第四,中医注重上医治未病。汉语思维是一种典型的隐形逻辑思维,“无”是汉人思维的最高境界。老子所讲“大道无形”“圣者无名”,世间的一切“存在”和“有”均来自于“无”,故“无中生有”。中医思维中,注重上医治未病,就是提高人体免疫力,依靠人体自身免疫力,让人体不生病,这就是中医所谓的“最好的医生就是自己”,这正是主体思维的具体体现。
综上可知,中西医思维方式的差异,导致了治疗理念的不同,中医的主体思维,导致了中医的治疗理念是提升人体自身的免疫力,治疗的同时亦注重调养,由此,中医的医患关系也较为和谐。而西医的客体思维,往往导致西医的对抗性及支持性治疗的理念,这种理念或许正是西医医患关系较为紧张的根源。
四、结 语
本研究从语言学的视角探索了以下一些问题:
其一,语言与思维不仅相辅相成,不可分割,而且语言特点与相应的思维特点是相互照应的。本次对比研究亦为“一方面,语言的全部词汇展现了其所在世界的广度,另一方面,语言的语法结构体现了语言对思维有机体的关照”(99)[德]洪堡特:《洪堡特语言哲学文集》,姚小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64页。的观点并为这一观点提供了重要的对比语言学方面的依据。
其二,本研究对于探索语言与思维的关系亦具有重要的意义,汉语二元对立统一的语言特点本身就决定了汉人会认为“我们的思维就是我们的语言”,(100)辜正坤:《中西文化比较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8页。而西人则一定会用二元对立的观点考察两者的关系,并且会考察谁是第一性的问题。就如同阴阳关系,按照汉语的概念系统,老子一定会提出“万物负阴而抱阳”,(101)《老子》,汤漳平,王朝华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165页。即阴与阳是统一于一体的。也就是说,英汉语言系统在探索“语言与思维”关系的时候,本身就预设了“二元对立”与“二元合一”的结果。正是由于汉语与英语语言特点的差异性,导致在探索“语言与思维”关系时存在着不可调和性。因为“同样的物质现象并不能使所有的观察者对世界产生同样的认识,除非他们的语言背景相似,或是可以通过某种方式得到校准”。(102)[美]沃尔夫:《论语言、思维和现实》,高一虹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226页。
其三,汉语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103)《论语 大学 中庸》,陈晓芬,徐儒宗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352页。的“和”“合”文化,以及“求同存异”“和平共处”的大国方略提供了重要的语言学依据。
其四,通过英汉语言及中西医思维方式的对比可知由于汉语的“意合”等语言特点诱导了中医“医者,意也”的悟性思维,与西医的理性思维相比,二者各有所长,故“我认为汉语作为思维工具无疑远远比不上拥有完善的语法形式的语言”(104)[德]洪堡特:《洪堡特语言哲学文集》,姚小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185页。的观点亦有值得商榷之处。汉语思维重在感受或者体悟,而西方思维重在逻辑上的因果关系或反思关系。但“思想与语言之间,有极其复杂的关系:言不尽意,是说真正的思想难以被语言把握”,(105)尚 杰:《中西:语言与思想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95页。在表达观点或描述客观世界的时候,亦有“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106)《庄子》,方 勇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221页。的情形。正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107)《老子》,汤漳平,王朝华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2页。
其五,一个民族的语言特点及思维模式与该文明所处的地理环境是紧密相关的,语言学必须首先考虑地理因素,这亦符合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物质第一性的观点。
其六,本研究亦探索了中西医思维模式、治疗理念的来源。中医思维及治疗理念具有很多优越性,如辨证施治、整体施治,但也具有模糊性、意会性,造成中医的精髓较难把握,亦较难传承等缺点。西医注重逻辑思维,有理有据,但亦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用孤立的观点看问题的缺陷。
其七,西医讲究所谓的理性的科学思维,往往把人的精神、主观情绪排斥在治疗之外,往往容易陷入机械唯物论的怪圈。
其八,对疾病的治疗可以中西医结合。如西医可以学习中医的宏观思维,确定方向后再进入微观领域,让疾病的复杂性和不可预测性大大降低。同时,西医亦可以学习中医以人为本的思想,尤其是对重症患者,要首先匡扶正气,正气足则邪不可干,同时注重中医的“三分治七分养”的思维,学习中医辨证统一的“药食同源”等思维;中医亦可以学习西医严密的逻辑思维以及西医的表述方式等,中医的语言比较生僻难懂,中医的表述急需使用现代语言以便更好地推广。因此,中西医的结合势在必行。正如“从人体科学的观点,中医有许多比西方医学高明的地方,但将来的医学一定是集中医、西医、各民族医学于一炉的新医学”。(108)钱学森:《钱学森书信选》,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8年,第5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