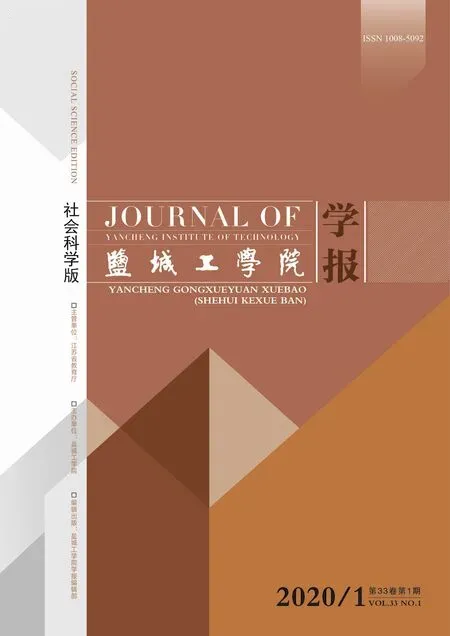艾丽丝·门罗短篇小说《逃离》的叙事策略
2020-02-22陈丽秋
陈丽秋
(集美大学 诚毅学院,福建 厦门 361021)
加拿大女作家艾丽丝·门罗是当代杰出的短篇小说大师,著有短篇小说集十余部。她于2013年荣膺诺贝尔文学奖,成为该奖设立百余年来首位凭借短篇小说获此殊荣的作家。除此之外,她还曾获得2009年曼氏布克国际文学奖,多次被授予加拿大总督文学奖、加拿大吉勒文学奖、英联邦作家奖等重要奖项。英国作家A.S.拜厄特把门罗称为“作家中的作家”,认为“作为一名短篇小说家,门罗的创造性与启发性足以与契诃夫、莫泊桑、福楼拜并肩”。[1]426乔伊斯·欧茨、赛克·罗伯特等人也盛赞门罗的短篇小说,认为它们具有“其他作家的长篇小说的深度”,能在有限的篇幅中展现出复杂的生命体验。
门罗创作始于20世纪60年代,但直到80年代她的短篇小说才逐渐在欧美国家流行开来并引起了评论界的注意。随着门罗相关研究的进展,涌现了一系列研究其作品的论文、书评和专著。其中,露易丝·马肯德力克于1983年编撰了《小说也能这么写:艾丽丝·门罗的叙事手法》(Probable Fictions: Alice Munro’s Narrative Acting),针对性地探讨了门罗的叙事风格。[2]1984年朱蒂思·米勒编写了论文集《艾丽丝·门罗的艺术:无法言说的情感的表达》(Munro: Saying the Unsayable)。[3]该专著深入剖析了门罗作品的表达方式,为门罗研究奠定了基础,也为以后的研究指明了方向。门罗在叙事手法上独辟蹊径,她摒弃了传统小说线性叙事的结构,灵活使用倒叙、插叙等叙事手法,改变叙述节奏,使小说叙事充满无限张力。也正因如此,其作品的叙事艺术成了近年来一些学者关注的焦点。撒克曾对门罗早期习作和后来发表的作品进行研究,总结了回顾视角叙事手法的作用。他认为它“不仅符合门罗风格而且为此奠定了基础,它有助于作者建立起一种过去和现在的辩证关系,亦是经验与理解的辩证关系……最终使读者获得了错综复杂的阅读感受”[1]428。Coral Anne Howells在其论著《艾丽丝·门罗》(Alice Munro)一书通过回顾门罗的创作生涯发现门罗小说的主题虽然没有太大变化但其叙事手法却在不断创新和发展。[4]
我国学者对于门罗作品的研究起步较晚,主要原因是其作品以短篇小说为主,难以吸引国内学者的兴趣,译介研究相对匮乏。2000年以前我国对门罗的研究几乎空白。直到2000年以后,才陆续出现了一些研究其作品的学术论文。
短篇小说集《逃离》是门罗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该书一经问世就广受喜爱和推崇,荣获了2004年吉勒文学奖。它收录了八个不同的短篇故事。它们共同围绕“逃离”主题生动展现了逆境中的女性在追求精神独立和自由之路上所遭遇的坎坷及内心感悟。门罗塑造人物心理的技巧多种多样,但由于篇幅有限,本文仅以其中的同名小说《逃离》为例分析弱化情节和全知视角两大叙事策略在塑造人物心理方面的作用。
一、弱化情节
关于门罗弱化情节的技巧,凯瑟林·罗斯说过,“门罗作品不提供情节,而是提供排列布置的材料,这种方法改变了读者对寻常事件的体验,迫使我们用一种不同以往的方式看待平常事。”[5]的确,弱化情节在一定程度上变革了传统叙事模式,突破了其因过于强调政治学及传统观念中的人和事而无法立体展示人物的生存状态的局限,因而能更加充分地揭示人物心理的变化和发展。[6]当情节退居到人物情绪之后,人物的外部危机也将相应被内心危机所取代,这使得人物内心情感在最大限度上得以扩张。
《逃离》中门罗不再采用完整而紧凑的故事情节,而且截取了生活中的几个横切面揭示主人公的生存状态和内心感触,增强了小说的情感冲击力。小说开篇并未从人物和故事背景入手,而是讲述了卡拉躲在自家的马厩房门后面等待西尔维娅度假归来的极度紧张和惧怕的神态,呈现其巨大的心理压力。小说由此回叙了压力的来源。原来卡拉的丈夫对她极其冷漠,态度粗暴。更让她难以忍受的是当克拉克得知刚刚去世的贾米尔先生生前曾调戏过她时,他非但不愤怒、也不怜悯她,反而把这视作一个敲诈贾米尔夫人西尔维娅的绝佳机会。在这之后小说讲述了卡拉在西尔维娅家与之见面的场景。此处情节颇为简单,不过是卡拉帮忙打扫房间,两人对话也显得随意,然而在这表层之下却如波涛般涌动着两人频繁而复杂的心理活动。通过碎片化的回忆可以看出西尔维娅对卡拉的喜爱和与她再见面的愉悦心情,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卡拉内心饱受煎熬、苦闷至极的状态。小说紧接下来讲述的是卡拉在西尔维娅的帮助下出逃却在中途放弃的经过。至此小说突然笔锋一转,叙述了克拉克深夜来到西尔维娅家并与之发生冲突的场景。最后小说以西尔维娅搬离小镇和卡拉陷入迷思收尾。从以上各环节的安排上看,作者似乎有意让人物心理取代情节推动故事的发展。关于卡拉为嫁给克拉克离家出走、婚后与克拉克之间的龃龉、西尔维娅家中烦人的琐事等碎片化的情节也是断断续续地、以一种触景生情般的回忆和感触穿插在小说里。
《逃离》关于情节的弱化还体现在它对情节的省略。文中有一个明显的省略是克拉克把逃离未遂的卡拉接回家。关于这个情节,仅在第三章末尾三言两语简单带过:“来接我一下吧。求求你了。来接我吧。”“我这就来。”[7]36虽然省略了说话人,但从前文可以看出这是卡拉在迷途知返后求助丈夫带她回去,而即将发生的场景必然是她被丈夫接回家。然而,作品并没有讲述这个过程,而是转而叙述那天晚上西尔维娅忘记锁门和克拉克不期而至。克拉克把卡拉接回家的情节就此被省略。从上文可以看出克拉克是一个脾气火爆、容易冲动的人,面对妻子的逃离他极有可能表现出强烈的反应。这对传统的叙事模式来说将是一个十分戏剧化的环节,而门罗却把它省去,原因在于下一环节中西尔维娅在与克拉克冲突中的“顿悟”似乎比这更具陈述的价值。那次“顿悟”不仅改变了西尔维娅此后的生活,冲击了卡拉的内心,也深深震撼了读者。
门罗通过弱化情节的方式凸显了人物内心的变化。这篇小说的情节看似随意、分散,却启迪读者调动已有的知识经验对此进行整合、拼凑,建立其中的联系,观察并思考人性之谜,找到使他们产生共鸣的要素。
二、灵活的全知视角
如果是弱化情节为塑造人物心理做了有益的铺垫和陪衬的话,那么全知视角的灵活运用则是人物传情达意的重要手段。
根据申丹关于叙事视角的理论,全知叙述者不仅是观察者也是叙述者。它能从任何角度观察事件,透视到任何人物的心理活动,偶尔也能借用人物内视角或者佯装旁观者。[8]短篇小说《逃离》大部分采用的是全知视角。作者用它叙述人物的情况,尤其把他们的生活经历和所思所想展现给读者。小说中卡拉带着对家人的厌倦和“过一种更为真实的生活”[7]33的愿望,从家中逃离,执意嫁给了出身寒微的克拉克。婚后两人共同经营着一家小牧场,可生意并不好,日子过得并不舒心。克拉克脾气暴躁,不仅为一点琐事与周围人发生冲突,连对自己的妻子也是一副蛮横的态度。他无视妻子为婚姻所做的牺牲,经常冲她发火,对她的辛勤劳动也总是挑三拣四、不断抱怨,这让卡拉觉得克拉克好像很恨她,这种日子“真要把她逼疯了”[7]22。有一只山羊叫弗洛拉,它是卡拉生活的唯一的慰藉,只可惜它已经丢失了。通过全知视角读者可以清楚地看到卡拉的思想活动。在卡拉心中,丢失弗洛拉的痛苦远远不及她和西尔维娅的烦心事给她带来的痛苦,也没法与她跟克拉克之间的龃龉给她带来的伤痛相比。确实克拉克给卡拉内心带来了巨大的伤害和沉重的负担。为了金钱他甚至丝毫不顾及卡拉的感受和名誉叫她去敲诈他们的邻居西尔维娅。后来,在西尔维娅家里,卡拉再也承受不了这种痛苦和压力,她让西尔维娅帮助她逃离丈夫,希望从此“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手里”[7]34。在乘坐大巴前往多伦多的途中,她发觉自己重拾了自信,正要把一切抛掷脑后,可往日生活却不断浮现在她的眼前。而当她开始构想未来的生活时,她突然变得害怕起来,担心自己不能独自融入陌生的世界。此时此刻,她越发感觉克拉克仍然在她的生活里占据着一个无可替代的位置。终于,在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她给克拉克打电话,请求他来接她。卡拉的逃离以失败告终。通过全知视角,作者成功塑造了一个逃离苦难、渴望自由的女子的形象。她内心苦闷、渴望改变现状,然而对于未知世界的恐惧以及长期以来对男性的依赖使她中途放弃了逃离,重新回到她所习惯的生活中。
值得一提的是,小说中全知视角的运用也非一成不变。它可以灵活地与人物的内视角相结合并通过二者之间的重叠以强化某一事件对于人物心理的影响。文中克拉克为卡拉逃离一事深夜来到西尔维娅的家。正当两人发生冲突的时候,山羊弗洛拉神秘出现了。对此作者用了全知视角交代了弗洛拉出现的背景和情况。事情发生在距离屋子不远的一片浅洼地,由于气候和地理原因,每年这个时候都会弥漫着夜雾。可是就在这个夜晚雾变得特别浓,而且凝结成了“单独的形体,变得有尖角,还闪闪发光”[7]39,显得十分奇怪而诡异。它最初看上去像一个向前滚动的“蒲公英球体”,却又不断变化,后来竟然“演变成一个非人间般的动物……朝他们这边冲过来”。[7]40原来不过是弗洛拉从远处而来,但它刚刚在浓雾中的怪异的形态还是给克拉克带来了莫大的恐惧。根据叙述者所讲,克拉克早已被惊吓的喊了一声,还紧紧抓着身旁的西尔维娅的肩膀以使自己保持镇定。因为弗洛拉的神秘出现,正发生矛盾的两个人几乎都忘记了他们刚才的争吵,不约而同地低下头看着那只山羊,最后还相互友好地告别。然而,同样的场景在西尔维娅写给卡拉的信中再次被提及,只是这次是以人物内视角进行陈述的。她回忆那天晚上他们两人正站在平台上说话,而她的脸朝外,因而她比克拉克先看到了一种“白色的东西”[7]46朝他们移动。她说她明白那是地面上雾气产生的效果,但还是觉得有点恐怖。两个成年人都被这情景吓呆了,而更让他们感到惊奇的是浓雾中走出来的竟是那只丢失的山羊。关于她与克拉克的冲突的瞬间化解,西尔维娅说那是“人性的共同基础”让“两个因敌意而分成两个阵营的人”“联结到了一起”。[7]46如果说上文的全知视角使读者观察到主人公的心理变化,那么此处人物内视角则进一步拉近了读者与主人公之间的距离,聆听其对这一事件的感受和顿悟。全知视角和人物内视角的交叉产生了多声部的效果,它们不仅将事件的背景清晰展示给读者,而且加深了事件对人物心理的影响。
小说中全知视角也并非总是“全知”的。有时为了烘托主题的需要,全知叙述者悄然撤退,似乎有意把叙述任务交给小说中的人物,从而制造出一种叙述者受制于常人局限的现象。这尤其体现在小说对山羊弗洛拉的去向的处理上。山羊弗罗拉,是卡拉的生活陪伴和情感依靠,可它最终还是丢失了。既然小说采用的是全知视角,叙述者不可能不清楚弗洛拉的下落。然而全知的叙述者竟然退出了,取而代之的是克拉克和乔依之间的对话。
“丽姬看上去状态不错嘛,”她说,“可是她的小朋友呢?叫什么名来着——是弗洛拉吧?”
“丢了,”克拉克说,“说不定进了落基山脉了。”
“那边野山羊可真不少。犄角什么模样的都有。”
“我也听说过。”[7]45
全知叙述者对这一事件的留白非但没有减轻反而增强了弗洛拉事件给卡拉内心带来的影响。尽管克拉克从西尔维娅那里返回后对他曾看到弗洛拉的事情只字未提,但西尔维娅寄来的一封信还是让她陷入了惊慌和痛苦之中。它如同“一根致命的针”扎在了她的肺里,使她每次深深吸气的时候都能感到疼痛。[7]47尽管如此,卡拉并没去找丈夫验证事实,也许因为缺乏与丈夫抗争的勇气,也许因为害怕知道事实的真相。她只能暂时把自己麻木起来,让自己慢慢习惯“心里的那个刺痛”[7]47。对弗洛拉去向的猜想使她陷入了迷思。虽然她在草丛中发现“所有的了解,都捏在了一只手里”[7]48,但她又抗拒着这样的猜想,想象着其他情形,为克拉克开脱,也为了安慰自己:“他说不定会把弗洛拉轰走。或是将它拴在货车后面,把车开出去一段路后将它放掉。把它带回到他们最初找到它的地方,将它放走。不让它在近处出现来提醒他们。”[7]48
山羊弗洛拉具有明显的女性特征。克拉克考虑到养只山羊在畜棚里可以起到抚慰和安定马匹的作用,所以把它买了回来,而后一段时间把它当成了身边的小宠物对待。和卡拉一样,它活在男性划定的区域中,沦为了被物化的他者。门罗用隐喻的方法将依存于男性的女性的命运和被圈养起来、任人摆布的山羊的命运巧妙地联系在了一起。 出于潜在的认同感,逐渐长大的山羊弗洛拉与卡拉越发依恋彼此。小说中作者先是通过全知视角先后陈述了山羊弗洛拉的消失和卡拉离家出走两个事件,淋漓尽致地刻画了男性压制下的女权主义意识的涌动和暗藏着的反抗,而后全知叙事者的隐退带来的山羊弗洛拉命运的不解之谜则引发了卡拉对于自我命运的探寻和思索。弗洛拉的结局不确定,卡拉寻找自我的事件就没有完结。弗洛拉是被克拉克杀死或丢弃的吗?从丈夫身边逃离失败后又回到家中的卡拉将如何展望自己的未来,她最终能找到自己所希望的真实的生活吗?小说结尾具有经典的门罗式叙事的开放性和不确定性。同门罗撰写的其他小说一样,不论结局是分离还是重逢,伤痕是依旧还是愈合,缺陷似乎成了人类社会中普遍的现象。然而,平静的生活之下隐藏着不断滋长的破坏性力量。这种力量伴随着焦灼和不满日益累积,等待着破土而出的爆发,之后转为沉寂,带着些苦涩、心酸和感悟回到原来的状态。通过灵活的叙事方式,门罗给读者带来了一种超越单一时间维度的如同顿悟般的体验,使读者进入了更为深远的哲学层面。
三、结语
总之,《逃离》中门罗灵活运用了弱化情节和全知视角生动展示了主人公复杂而微妙的内心世界。弱化情节巧妙地转移了读者对故事情节的注意力,邀读者步入人物内心;“全知”视角时进时退,在逼真刻画人物和事件的同时发人深思。如此高超的写作手法使人物内心塑造的过程不再平稳单调,而是富于变化。它也紧紧抓住了读者的思绪,给他们带来了别样的阅读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