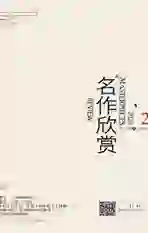论全媒体背景下非国有博物馆的传播策略
2020-02-21倪湘玲
摘 要:随着全媒体的不断发展,非国有博物馆的文化传播功能越来越得到重视,然而大部分非国有博物馆在馆藏内容建设、媒体技术和平台的利用,以及传播队伍壮大等还不是非常完善,使其文化传播效能受到影响。非国有博物馆只有顺应全媒体时代发展的趋势,建设精良的传播队伍,制作精彩的传播内容,结合数字技术,搭建良好的传播平台,从而形成各自的传播特色,真正发挥博物馆的文化传播作用。
关键词:全媒体 非国有博物馆 传播 困境 策略
与国有博物馆一样,非国有博物馆也具有一定的教育、研究和欣赏功能,通过收藏、保护并向公众展示那些人类活动和自然环境的见证物,实现文化传播、教育的基本任务。但是,不少非国有博物馆存在着传播力度小、传播功效差的问题。在传播技术和信息技术不断发展、媒介类型不断变化、媒介形态不断融合的多样化的媒体背景下,非国有博物馆传播的深度和广度的问题更是凸显,如优质的传播内容与专业化运营传播团队的缺乏,传播平台与传播技术的低端,受众与博物馆传播之间的联系单一,等等。因此,在全媒体社会背景下,为了更好地发挥非国有博物馆教育、欣赏和研究等作用,必须顺应全媒体时代发展的趋势,建设精良的传播队伍,制作精彩的传播内容,结合数字技术,搭建良好的传播平台,加强与受众之间的沟通,利用文字、图形、图像、声音、视频等媒体表现手段,运用具有战略规划性的传播策略,满足大众对非国有博物馆的文化需求,从而实现非国有博物馆的传播功能。
一、全媒体背景对非国有博物馆传播的必然要求
“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国家强”,博物馆是一个城市乃至一个国家文化的象征,非国有博物馆作为博物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地方特色化文物的收藏聚集地,见证了一定社会历史时期的人类活动和自然环境,充当着历史叙述者与文化传播者的角色,是与社会公众进行沟通交流的一个重要纽带,对社会文化事业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而,要弘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让非国有博物馆文化实现自身价值,就必须重视非国有博物馆的传播。
在全媒体背景下,现代信息化媒体的出现和渗透,人们的生产生活愈加便捷,愈加丰富了,人们获取信息资源的渠道和媒介大大增加。新兴媒体借助现代人们常用的微信、微博、抖音、客户端等实现了信息的多渠道传播。因此,全媒体社会背景对非国有博物馆的传播提出了新要求。如果非国有博物馆能够整合信息资源,积极引进数字网络技术,开拓信息传播平台,打破传统博物馆在传播过程中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就能够有效且便捷地向人们展示非国有博物馆特色的文化资源,更好地传播中国文化。以宁波金银彩绣艺术馆为例,如果能引进全息技术或者3D打印技术,制造出金银彩绣衣物的3D立体模型,让人置身其中,感受传统衣物穿在身上的感觉,在视觉、触觉等方面吸引受众,激发受众的兴趣,让受众自发地进行传播,从而扩大传播的范围,既迎合了大众不断增长的文化需求,也能帮助非国有博物馆实现更大的自身价值。
二、非国有博物馆传播的困境
随着全媒体的深入发展,非国有博物馆的文化传播显得尤为重要,做好非国有博物馆的传播工作,为大众提供良好的体验,对于促进博物馆的良性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因此,大部分非国有博物馆也在不断地推陈出新,通过各种方式渠道進行文化传播,将更多的文博知识带给大众。但总体上,这些非国有博物馆对全媒体的利用还处于初级探索阶段,在内容生产、传播技术与平台渠道,传播队伍建设等方面还存在着一定的困境。
(一) 优质内容缺失 信息呈现模式化
全媒体社会环境中,传播渠道是极重要的,但是,优质的传播内容更是影响传播的重中之重,即“内容为王”。然而大部分的非国有博物馆缺少有吸引力的内容,内容零散,缺乏系统化的整合,发布形式也趋于模式化,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博物馆的文化传播。
一般来说,媒介传播内容可分为线下线上两个部分,线下主要是馆藏展陈,文创产品的展示以及供游客取阅的图集或文集,线上主要通过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的方式进行整合编辑,发布到不同的平台上。如2019年大火的《国家宝藏》,就是寓教于乐,运用时代性的传播方式,表现文物的“前世”“今生”,对博物馆传统文化内涵进行广泛传播,引起人们对博物馆文化的广泛关注。但不少非国有博物馆还没有构建完善的内容生产系统,虽然博物馆本身具有丰富而有特色的内容,其中不乏文字、照片、视频、音频等大量的信息,但是未能对这些素材进行系统的整理,需要一定的挖掘才能生产出一些有价值内容。就目前来说,宁波非国有博物馆与地方特色文化关联不是很强,导致传播内容也不够丰富。线下传播时,也都是通过最基础的展陈来表现,一般是实物与图片文字相结合的模式;线上传播时,其信息表现形式也是过于模式化,同样是图片与文字结合的静态展示,可读性较差,导致受众失去对非国有博物馆的兴趣,从而影响传播效用。
(二) 传播技术受限 传播平台单一
全媒体的传播具有多样化、多形式、多渠道的特点,人们乐于接受形式多样的新鲜事物,但非国有博物馆在传播技术方面没能及时跟进,对多样化的传播平台利用率也较低,因此对文化的传播效果较差。
一方面,许多博物馆的传播得到了飞跃式发展,一些博物馆采用三维技术,将场景再现,通过3D技术打造出一个近似真实的场景,通过对场景的还原,使许多原本“平面化”的信息传播、文物展示变得更加“立体化”,带领受众仿佛“穿越”到真实的情景中,通过自身的体验,吸收这些博物馆想要传播的知识。在这种情况下,数字技术竞争力就是影响传播效果的重要因素。但在日常的传播过程中,大部分非国有博物馆传播很少运用数字技术,仅仅是线下展陈来实现博物馆“物”的传播,如紫林坊艺术馆,就是通过简单的陈列与简短的文字说明来进行展示,缺乏一定的数字化、娱乐化传播手段,缺少新意,难以实现博物馆传统性与时代性的共存。
另一方面,许多非国有博物馆的展陈基本以静态的文物展示、图片展示、文字解说为主,以“你展示,我浏览”的模式来传播,这样的传播只能对文物进行简单的展示,对文物的了解也仅仅停留在文物表面而缺乏深入的了解,展示生硬,传达出的信息量也受到一定的限制。就目前的情况来说,宁波市非国有博物馆在传播过程中只是借助传统纸质媒体来进行简单的信息传播,极少通过独立的网站来传播,很多非国有博物馆连当下极为普遍的微信公众号也未申请运作,这便导致了非国有博物馆的传播力度和范围大打折扣,更别提近年来流行的H5、抖音等不同平台的新型传播了。可以说不论是新媒体还是以报刊为代表的传统传媒,非国有博物馆都未能充分利用好这些渠道做好相应的传播工作。
(三) 忽视传播主客体联动 传播效能受限
专业化人才是博物馆传播的主要发起者,学校、企业、公众是博物馆传播的主要对象,并接受博物馆传播出来的信息,在博物馆文化传播事业发展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对博物馆来说都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非国有博物馆在传播过程中往往忽略传播的主体和客体联动,使得传播效能受到各种限制。
就传播主体而言,非国有博物馆没有形成专业化的传播运营团队,虽然部分非国有博物馆工作人员具有了一定的传播意识,在工作中试图通过多种渠道开展博物馆的传播的工作,如宁波金银彩绣艺术馆,开通建设了微信公众号,积极进行文创产品的开发,从而扩大博物馆的传播面。但由于缺少相关传播方面专业人才的培养,信息传播滞后,传播内容简单,缺乏创意,未能呈现博物馆已有的特色。宁波金银彩绣艺术馆自2014年创建微信公众号以来,仅有两篇原创文章,2018年一整年,仅发布五篇文章,可见非国有博物馆工作人员虽然有这个意识,但是关于非国有博物馆的信息传播少之又少,原创文章少,发布频率低,说明非国有博物馆传播人才的缺失。
而不论博物馆在传播上做多大的努力,若是受众的参与度程度不高,那么博物馆的传播功能显然也是不足的。事实上,宁波不少非国有博物馆偏重手工类制作,具有较强的动态性,更容易进行公众与博物馆之间的互动,提高受众参与度。如宁波“中国插花艺术馆”,这所被称为首家“国”字号民间艺术馆,安装了声控讲解的电子设备,对特定部分的历史背景及与展品有关的信息进行了深入讲解,博物馆门口还有触控式屏幕,观众很容易了解中国插花艺术馆的基本信息,甚至还可以用来了解其他非国有博物馆的相关信息,当然,在具体运用中,博物馆还可以增加一些基本功能,改变左右滑动的浏览方式,丰富相应的信息量。但还是有不少非国有博物馆很少能意识到这一点,如宁波金银彩绣艺术馆,它继承了浙江省非物质遗产金银彩绣工艺,其深刻的内涵就不能通过简单的绣品展示来实现,绣品的陈列只能让受众感慨绣品的精美,而具体的绣法、用线等方面的工序则鲜为人知,人们来馆只是参观,没有讲解,没有工艺展示,没有互动,仅在一个不大的房间里走一圈就完成了参观,受众来馆参与度较低。因此一些能与受众进行互动的博物馆,互动的程度还有待加强。
三、优化非国有博物馆全媒体传播的策略
为了扩大非国有博物馆的教育、欣赏等功能,非国有博物馆必须紧握全媒体社会发展的脉络,充分运用新媒体、多媒体等手段,利用不同的传播渠道,从各个方面优化非国有博物馆的传播策略,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的发展。
(一) 重视传播队伍建设和受众体验
目前,非国有博物馆表现出传播途径单一、内容缺失等问题,要改变这些问题,让非国有博物馆得以长期发展,最主要的就是重视传播主客体的综合素质。
首先要加强非国有博物馆的队伍建设。博物馆应积极引进相关人才,建立一支专业化传播团队,设立专门的媒体部门,策划有特色、有内涵、有深度、有创新的传播活动,为非国有博物馆的传播开辟新的传播思路。如可以借鉴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发展,将非国有博物馆馆长打造成“媒体发言人”。如宁波紫林坊艺术馆的馆长陈明伟,他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和“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博物馆可以利用全媒体社会的“名人效应”,将这双重身份转变为紫林坊艺术馆的一个标志,进而再转化为骨木镶嵌技术的一个标志,相信一定能起到很好的传播效果。
此外,全媒体具有交互联动的特点,受众是博物馆信息传播的主要体验者,非国有博物馆的传播要了解受众的心理变化特点,创新传播方式,增强受众与非国有博物馆之间的联系,使受众更加积极地参与到信息传播活动中,实现博物馆的社会价值。现如今,不少博物馆积极利用各种全媒体手段,推动传播的升级转型,如利用动画、H5、AD、3D、VR、全息影像、视频、文本、图片等形式,激发人们的好奇心和关注度,以强大的互动性加深与受众的联系,让受众更有效地参与传播的过程 ,因此,非国有博物馆也应完善用户体驗设计,重视受众体验感,如定期开展面向市民大众的培训班,不仅兼顾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还能帮助受众获得良好的体验,从而推动非国有博物馆传播的深度和广度。
(二)制作精彩的内容,传播特色文化
藏品是博物馆展览展示的重要内容,是博物馆进行教育与社会传播的信息与价值导向的重要载体。一个博物馆要想发展得好,“让文物活起来”,不仅要找准自身的办馆定位,聚焦馆内特色展品,还需要制作精美的内容进行传播。因此,博物馆可以依托当地的特色文化,形成各自的办馆特色,还可以结合时代特点,创新传播内容。
地域特有的历史文化基础就是非国有博物馆传播的最大优势。大多数非国有博物馆展品不多,但都经过了长期的积累逐渐形成,具有鲜明的特色。如宁波十里红妆博物馆就以古代女子生活为专题,还原了当时人们的生产生活,呈现了具有浓郁江南特色的婚俗习惯,传播了浙东独特的历史文化。
除此之外,博物馆也应积极制作与时俱进的传播内容。博物馆可以寓教于乐,塑造受众喜欢的博物馆品牌形象,最大限度地传播非国有博物馆的个性文化。如中国插花艺术馆可以将传统的花神形象与插花的内蕴相结合,一幅插花对应一个独特的故事,以一种独特的讲故事方式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博物馆还可以根据自身藏品的特点和文化元素,突破文化跨界合作壁垒,积极开发有市场、有价值、有文化内涵的文创产品,延续情感的共鸣,将自己博物馆的文化特色传播出去。如宁波熨斗银锡蜡就积极开发了锡器首饰盒、水墨艺术馆推出了鲍贤伦书法抱枕,生活随处可见的小物件与非国有博物馆传统技艺的结合,让非国有博物馆的文化得到广泛的传播,真正的“热”起来。
(三) 利用数字技术,搭建传播平台
全媒体不断深入发展,使得信息的传达方式变得多样化,传播范围变得更广阔,传播速度变得更快,传播有了不同的媒介形态和丰富的传播平台。当下,博物馆与媒介的优势互补、与平台之间的资源共享是大势所趋,博物馆要想吸引更多的人、发挥更大的价值作用,就应该与时俱进,利用数字技术,进行多平台传播。
数字技术的丰富发展可以加强非国有博物馆的文化传播;全媒体的多元传播则拓展了非国有博物馆的传播渠道。在条件允许下非国有博物馆要加快馆内数字化建设,搭建传播平台,如可针对受众的不同需求,选择最适合的媒体形式,建设AR技术体验馆,增强现实技术。通过这种新奇的方式,提高非国有博物馆的展陈特色,丰富游客在参观过程中的体验感,提升博物馆的传播效果,增加博物馆的热度,带动博物馆的发展建设。
在平台建设方面,非国有博物馆最重要的任务是加快建设“两微一端”的脚步,并且运营出本馆的特色。可参考故宫博物院开设微博,并将雍正皇帝“活化”,制成gif动图、表情包,在微博微信等平台大量传播的方式,因势利导,结合视频,文本、图片、直播等形式,借助微博微信甚至是近年来大火的抖音平台,将非国有博物馆特色文化在多平台传播,构成全方位的沉浸式体验,激发受众的好奇心,提升受众的关注度,实现博物馆文化在受众之间最大限度的传播。
打铁还需自身硬,非国有博物馆要解决传播中遇到的种种问题,需要靠自身的优化发展,不断顺应全媒体发展的潮流,加强团队建设,充分发挥新媒体技术,搭建各種媒体传播平台,密切与受众的联动,提高传播质量,从而给市民带来更加丰富多彩的文化享受。
(指导老师:浙江万里学院郑健儿副教授)
参考文献:
[1] 王琪.全媒体背景下国内数字博物馆的问题分析与改善策略研究[J].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1(2).
[2] 徐紫笛,樊传果.地方博物馆品牌新媒体传播策略研究[J].戏剧之家,2018 (30).
[3] 李保平.融媒体环境下博物馆宣传的改革与创新策略[J].新闻战线,2019 (4).
[4] 黄逸鲸.博物馆文化传播中人与环境的互动性研究[J].汉字文化,2019 (3).
[5] 吴珊珊.融媒体时代的博物馆传播——以故宫博物院为例[J].新闻研究导刊,2019,10 (3).
[6] 曾一果,陈爽.博物馆文物的数字化展示和传播研究——以台北故宫博物院为例[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8 (1).
[7] 王亚军,李瑜.基于博物馆教育、传播功能的文化创意产品开发思路——以山西地质博物馆为例[J].自然科学博物馆研究,2018,3 (4).
[8] 毛逸源.本土视域下的浙江民间博物馆建设与发展研究——以宁波为例[J].大众文艺,2018 (22).
[9] 徐敏.“互联网+”模式下小众博物馆的发展研究——以甘熙宅第为例[J].中国商论,2018 (30).
[10] 刘欣.论当代博物馆知识传播模式的转变[J].文博学刊,2018 (3).
[11] 赵君香.博物馆地域文化特展的媒介传播[J].遗产与保护研究,2018,3 (9).
[12] 吴英琦. 数字技术背景下遗址博物馆品牌传播策略研究[D].电子科技大学,2018.
[13] 李晨. 三星堆博物馆社交媒体传播策略优化研究[D].电子科技大学,2018.
[14] 贺传凯. 中国博物馆营销体系研究[D].河南大学,2016.
[15] 张品方,相丽均.鄞州:打造“博物馆之乡”[J].浙江人大,2009 (6).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19 年浙江省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计划暨新苗人才计划“宁波市非国有博物馆发展现状调研及分析”( 2019R420010)成果
作 者: 倪湘玲,浙江万里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生。
编 辑:赵红玉 E-mail: zhaohongyu69@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