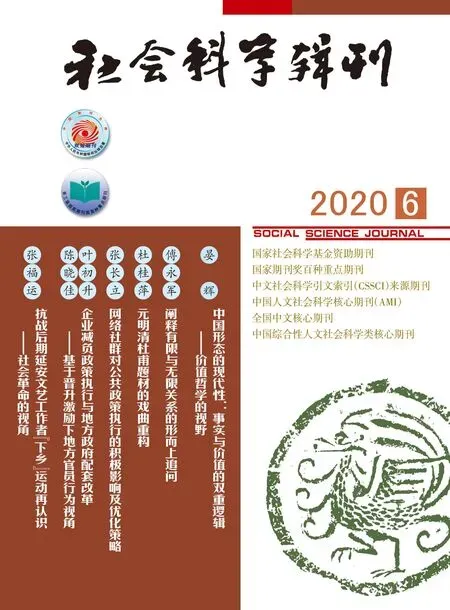阐释有限与无限关系的形而上追问
2020-02-21傅永军
傅永军
近来年,汉语学界阐释学①为使本文的论述在概念使用上融贯一致,笔者在本文中使用“阐释学”,而不使用习惯使用的“诠释学”。研究最为引人瞩目的现象之一是张江先生对中国阐释学的探索性建构。从强制阐释到公共阐释再到阐释逻辑,张江先生所致力建构的“中国阐释学”,在理论建构的系统性以及理论的自我证成能力等方面确有独到之处。最近,他在《探索与争鸣》发表《论阐释的有限与无限——从π到正态分布的说明》(以下简称《论阐释》)一文,讨论阐释的边界约束,提出“阐释π”概念,思考“诠”的有限与无限关系及其标准正态分布等问题,对涉及中国阐释学建构具有重要基础性意义的理论议题进行了系统探究。毋庸置疑,张江先生的学术新见已经引发众多学者关注,阐释的边界约束(阐释的约束与开放、有限与无限、确定性与非确定性)这个古老的阐释学难题再度成为学术热点。来自不同领域的学者与张江先生对话,从不同角度拓展这个议题的内涵,以求进一步辨理明义,寻幽探胜,以便补苴罅漏。虽然前此的对话已经在多个层面多维度地展开,但在笔者看来,要对阐释学的这个基本问题形成更为清晰、确定和具体的理解,清除观念上的模棱两可,有必要深入到这个基本问题的哲学形而上学奠基处去剖辨。因为,这种辨析不再纠缠阐释活动本身及阐释活动所涉及的诸种阐释行为、要素之间的实际性关系,而是去追问阐释所以可能的根据、基础、条件以及合法性要求。唯有这种形而上的追问才能为一门学问划定基本的逻辑区域,提供合法使用的原则,奠定其存在的哲学根据。有鉴于此,笔者主张,应当返回理解活动的根基处进行批判考辨,从讨论阐释基本问题的认知视域返回它的源发的本体视域,延展张江先生对阐释学基本问题思考的哲学形而上学维度。
一、阐释有限与无限关系的新解说及其内在张力
张江先生明确表示,他在《论阐释》一文中的任务是,“借鉴自然科学方法,由圆周率π而上手,达及概率的正态分布”,对阐释的开放与收敛、有限与无限、确定性与非确定性这些事关阐释实践及理论发展的重大问题,给出分析与说明。〔1〕为此,他首先对几组基本概念进行了澄清与解释。显然,张江先生对这几组概念的分析与解释,除了要依据自己的阐释观定义这些概念外,更重要的是要确立解说它们的基本原则,给出理解它们必然要先行隶属的哲学立场,追溯它们的“元”(meta)根基。有鉴于此,如若我们要对《论阐释》一文中所提出的新见作出更为深入的理解,就必须越过对这几组概念所进行的内涵解释与意蕴分析,展开“元”追问,揭示它们背后直接承受的哲学观念,钩沉它们的形而上学根基。当然,这种“元”追问并不是一种纯然的思辨游戏,它必须建立在对阐释有限与无限所涉及到的那些基本观念的内涵及相互关系澄清之上。只有明了问题讨论的共同语境,清除概念使用上的混乱,讨论才能避免偷换概念、背离逻辑以至陷入“鸡同鸭讲”之窘境,取得成效。
张江先生讨论了“文本开放与阐释开放”“阐释的边界与阐释的有效边界”“意蕴、可能意蕴、意蕴可能”“诠与阐”四组概念。这四组概念分别关联于文本(阐释的对象)、阐释者(阐释活动的主体)和意义(阐释的知识论表现)。
第一组概念中的“文本开放”指的是文本的意义外向敞开,阐释者可以对文本的意义展开无约束的理解与阐释。也就是说,在阐释者的阐释活动中文本绝不会封闭自身,而是有着朝向阐释无限开放自身的诸种可能性,这也就同时揭示出“阐释开放”的意涵,即阐释开放指称着阐释者的主体性活动的自由,阐释自身是开放的,阐释者的阐释行动是不受约束的自由行动。但是,这种阐释的自由是一种主观行为,而不属于作为阐释对象之文本的属性。张江先生强调这组概念之于阐释行动的基础性,为正确理解阐释有限与无限关系的基本前提,同时也强调要在这两个概念之间划清界限,指出:“以阐释的开放代替文本的开放,将阐释意义的无限代替为文本意义的无限,违反阐释逻辑。”〔2〕
第二组概念“阐释的边界与阐释的有效边界”相关于文本。先行于阐释而存在的文本的意涵(由作者意图形成的文本的自在意义)具有存在论上的优先性,它构成阐释有效性的客观判据。基于此,无关于文本的阐释者的自由阐释是无限且开放的,阐释没有任何边界约束,但这种源自阐释者自由意志的阐释只具有主观的必然性,且由于未经公共理性的批判检视而属于一种无效阐释。有效的阐释是有边界约束的。“作者赋予的意图,文本的确当意义,文本的历史语境,民族的阐释传统,当下的主题倾向,如此等等,决定了阐释是否有效及有效程度的边界。”〔3〕在存在论意义上先行于阐释者意识活动的这些因素约束着阐释者的自由意志。这决定了出自阐释主体自由意志的阐释活动,其揭示文本意义的知识行动,虽然形式上表现为一种在公共理性架构下主体意识反映客体实际的“符合”行动,但由于这种“符合”行动从属于历史,接受当下使阐释成为可能之种种条件的节制,它就不能仅仅是一种机械复制行为,而是一种受制于阐释者主体能动性作用的行为,阐释者的“前见”对文本意义的生成并非不重要,阐释造就的是“效果历史意识”。
第三组概念讨论“意蕴”问题。《论阐释》一文提出三个概念:意蕴、可能意蕴、意蕴可能,从文本角度对阐释的有限与无限作出进一步解释。“意蕴”指的是包含着作者意图于其内的文本的原意。由于文本的原意遮蔽在文本的符号系统之中,需要解释才将自身呈现出来,为阐释者所把握。故而,从文本与阐释关系看,与阐释直接相关联的文本“意蕴”是一种“可能意蕴”,即在阐释中呈现出来且不为作者所知的、处在可能状态的文本意义。这是一种由文本自在意义所规定的意义,但却是一种因应不同的阐释处境而历史地呈现出来的意义。从阐释与文本关系看,与阐释直接关联的文本“意蕴”是一种“意蕴可能”。当阐释者更多关注自身的主体自由时,阐释者就会基于阐释意愿而自由阐发文本的意义,由此带来两种结果:或对文本意义进行强制阐释,阐释因而无限、开放和自由,但却与公共理性的有效使用无关,阐释因此成为一种无效的阐释;或阐释者自由发挥对文本意义的解释,揭示出作者无意识赋予文本的意图,在无意识中实现文本的能指与阐释的所指之间的一致性,阐释遂成为一种为公共理性所接受的有效的阐释,“意蕴可能”与“可能意蕴”合二为一。通过对“意蕴”不同意涵的分毫析厘,可以抽绎出判定阐释有效性的判据,为阐释的自由划定明确边界。
最后讨论的第四组概念是“诠”和“阐”。这两个概念主要是从阐释主体角度规范文本解释活动的不同层面。“诠”确定、追索、言说文本的本义,总体上属于一种“我注六经”式注释活动。“阐”则侧重阐发文本大旨,推衍生成义理式诠释,总体上可归入“六经注我”式阐释范畴。“诠”指向典籍文本,必然受文本的自在意义约束,以解说出文本的“可能意蕴”为目标追求,且由于解释锚定“可能意蕴”而在一定意义上开放基于文本意义之历史解释的无限可能,体现“诠在有限中无限”这样一种辩证面相。与“诠”不同,“阐”因为隶属于阐释者,可纳入阐释者的主体自由范畴,因而本性上是开放的、无限的和自由的,解释锚定文本的“意蕴可能”而将阐释的所指要求充分发挥出来,体现“阐在无限中有限”这样一种辩证面相。
根据以上分析,张江先生给出了对阐释有限与无限关系的基本判断:“阐释是开放的,同时也是收敛的。阐释因开放而无限,因有限而收敛。作为一对相互依存的共轭变量,两者之间是相互包含、相互决定的积极关系,而非相互否定、相互排斥的消极关系。开放与收敛平衡,无限与有限相融,无限在有限中展开,有限约束界定无限。”〔4〕阐释的有效性就在这种有限与无限之间的张力平衡及和平相处中实现。在这个基本判断中,“阐释的无限”指的是“对确定的对象文本,阐释可创造无限意义”;“阐释的有限”指的是“阐释为多种条件所约束,其总体结果是收敛于有限论域之内的”;“阐释的收敛”,意味着“公共理性的承认与接受,约束阐释向有限收敛”;“阐释的有效性”,揭示了“阐释的开放为无限,但是,无限生成的阐释绝非无限有效。阐释的有效性由公共理性的承认和接受所决定”〔5〕。
这个基本判断对文本、阐释者、阐释之间的关系以及由之体现出来的阐释学原则给出了一种新解说,进而凝练提出“阐释的正态分布”概念,用以表达阐释的开放与约束、有限与无限的关系,展开对诠释现象的定量研究。放下这个基本判断对阐释现象及其关系的实际性描述不论,对这个基本判断所立基的“元”哲学立场进行剖辨,笔者发现,这个基本判断所作出的关于阐释有限与无限关系的新解说,在认知层面和形而上学层面存在着一种内在张力。
从阐释、文本与意义三者关系看,阐释的有限性指示出文本对阐释的边界约束,它的核心要求是,阐释必定是“对一确定文本的阐释,确定于该文本之所能蕴含的意义,而非游离于该文本之外的其他意义,亦即阐释主体的对象是此文本而非他文本”〔6〕。可见,相对于阐释来说,文本具有存在论上的优先性。阐释的责任就是要找到先于自身而存在的作者及其意图。作者意图作为文本直接承受的自在意义是各种阐释集中的“有效点位”,它将无限可能的阐释约束于文本自在意义所允可的区间之内,“此约束说明,无论何种文本,只能生产有限意义,对文本的无限阐释约束于文本的有限之中”〔7〕。显然,对阐释有限性的说明实际上是一种形而上学分析,它强调文本意义的客观性,强调阐释与文本意义之间的存在论差异。文本先于阐释而独立存在,文本的自在意义是阐释收敛的聚集点。在意义本质问题上,新解说倾向于接受实在论观点。
按照意义本质的这种实在论观点,阐释应是一种反映行为,意义阐释应取“符合论”方式。但如此一来,文本的意义就是一种固定不变的意义实体,阐释就是一种机械的克隆行为,旨在阐释中还原出文本之独一无二的原意。由于固化了的文本意义并不能在不同阐释中自由转换,阐释无限就是一个伪命题。这当然悖谬于张江先生新解说的本意。在新解说中,阐释者的主体性以及文本意义的开放性,是一个在实际性意义上被论断为真的命题。相应地,阐释的无限性就不是一个有无的问题,而是一个如何可能的问题。虽然阐释无限的核心要义是承认多元解释的合法性,但阐释毕竟是对文本的阐释,文本意义若封闭,阐释则不可能多元开放。文本开放是阐释无限的认识论前提。文本开放意味着意义开放,意味着文本的意义可以在阐释中被创造性地解释。在阐释之前,文本的自在意义并不能被实体化,先于阐释而成为被描述和反映的真理。意义生成于阐释,阐释的真理与阐释者对文本的解释密切相关。这就是说,文本意义与阐释活动之间有着一种本质性共属关系。阐释在认知层面抵抗着有关意义本质的实在论要求。
这样,关于阐释有限与无限关系的分析,新解说在存在论层面和认识论层面就出现了裂痕,内部存有一种张力关系。新解说应正视这个问题。
二、“弱的阐释实在论”与内在张力的消解
在上面的论述中,笔者发现了存在于张江先生关于阐释之有限与无限关系新解说中的内部张力。为什么这种张力关系会在新解说中出现?笔者首先要寻求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只有对这个问题有所理解,对话才能开始,并逐渐走向对“隐藏于这类问题背后并对这类问题予以规定的更深层的东西,亦即作为众源的那个何所为”〔8〕的揭示,在发现他人思想中合理的可接受内容的同时,也通过对其思想中有争议内容的辨析讨论,敞开理解的新视野。“凡在人们寻求理解之处,就有善良意志。”〔9〕这是阐释学“善意原则”(principle of charity)的基本要求。
众所周知,从古到今,抵御相对主义对阐释学的侵蚀,又同时为阐释的自主性、开放性和创造性留足合法空间,始终是阐释学者致力解决的一个严肃的阐释学难题。阐释学中实在论与非实在论之争,与这个难题的解决有着密切的关系。它们分别提供了回应这个难题的不同思路。
按照阐释实在论,文本的意义来自作者,作者有绝对权威决定文本的意义。因此,文本有独立且先于阐释而存在的“原意”,这是一种由作者意图客观化而形成的独立自存的意义实体。阐释即重述文本的“原意”,重述的确定性和有效性端赖于与文本“原意”的符合程度。由于阐释实在论把阐释解释为对实体化的意义载体(文本)的反映与把握,阐释不过是发现文本意义的知识宣告。在这种知识宣告中,阐释者找到的不是自己意识的创造物,而是被阐释对象在自身意识中的投射物。阐释者需要“自觉地脱离自己的意识(Gesinnung)而进入作者意识”〔10〕。可见,阐释实在论的重心是文本意义的客观解释,它只允许依据符合论要求对文本意义作出复原式描述,并且是剔除了一切语境因素的客观性描述。由于阐释实在论将文本意蕴理解为一种意义实体,阐释对应这个不变的对象,因此,阐释实在论是阐释相对主义的“克星”。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阐释实在论的困境也源自于自身的这种意义实体主义立场。阐释实在论在认识论上必然会遭遇到符合论难题,无法回应现代阐释学在文本和意义阐释问题上对其提出的挑战:实体的绝对性不过是一种形而上学神话,阐释的真理性取决于阐释的历史性与阐释的主体间性,阐释学的任务不是对文本进行客观解释,而是给出一种合理解释。在近现代哲学对实体主义所展开的无情攻击下,阐释实在论逐渐式微。
阐释的非实在论不仅否认文本的意义源自作者的意图,而且否认文本负载着经由语言符号可以传递出来的特定意涵,它不承认文本未经阐释就先行于阐释者及阐释行动而存在。依照阐释的非实在论,阐释不是相关于作者意图的特殊解码行为,而是建构文本和阐发意义的创造行动。在阐释之前,并没有文本和意义存在,阐释的真理依赖于阐释者的理解行动,它在阐释的历史处境中生成。换言之,文本是时间意识里的事件,意义在其中发生。相关于合理解释的阐释学行动,基于自身的形而上学立场,为文本阐释的开放性和创造性开辟出广阔的空间。阐释不再以客观还原文本自在意义为圭臬,而是以追求更好的意义阐释、不断地给出新阐释为目标。阐释的非实在论能够满足阐释的开放性和无限性要求,让阐释从机械复制的反映传统中脱身而出,成为一种创造性的自主意识行动,与现代阐释学的旨趣完全切合。但另一方面,阐释的非实在论也遭受到广泛的批评,批评者指责其为阐释相对主义敞开了大门。“相对主义在过去两百年里是哲学的一条支脉,它开始是涓涓细流,近来已经成长为一股奔腾咆哮的洪流。”〔11〕阐释学者对此感受深刻,思考并探寻走出困境的道路,是他们必须承担的义不容辞的学术使命。
可以说,张江先生对阐释有限与无限关系的新探索就是在践履这种学术使命。毋庸置疑,张江先生的阐释理论是一种现代阐释学理论,其阐释理论的重心不是意义和阐释的客观性,而是合理解释的本质及其可能性,其任务主要不是为描述和重构文本的自在意义而去发现正确理解的方法,而是探究创造性阐释的可能性,考察意义阐释真理性的主体间性基础,演证阐释的公共性,证成公共理性作为有效阐释判据的合法性。所以,按照张江先生的阐释学主张,一个完整的阐释学事件包含文本(阐释的对象)、阐释者(阐释的主体)和阐释(在阐释对象和阐释主体之间建立联系的理解行动)三个基本要素。一个完整的阐释活动完成于理解活动发起者(阐释者)对阐释对象(文本)的意义揭示。阐释者在自己的传统脉络中对文本展开理解,文本的意义在阐释者的视域与文本的视域相遇中历史地生成,“这经常表现为,不同时代和语境下,同一文本的不同意义被发现,呈现文本自身所可能的丰富意蕴”〔12〕。这就是说,阐释主要不是一种反映论行为,而是一种创造性阐发文本意义的理解行动。张江先生在阐释的两种方式——“诠”与“阐”之间所作的区别,很好地呈现出阐释行动中“反映”与“创造”的差别。“诠”追溯文本之本义,“核心追求是寻找与求证文本的可能意蕴,排除文本以外的任何可能”〔13〕;“阐”推论文本大旨,衍生义理,“核心追求是附加与求证文本的意蕴可能,将无限可能赋予文本”〔14〕。阐释学之阐释主要是一种“阐”,它在完成文本处境化的同时,生成处境化的意义阐释,是一种朝向“意蕴可能”的无限性展开的解释行动,它使得文本意义处于不断生成中并展示出面向未来之价值。
不可否认的是,阐释行动注重“阐”而不是“诠”,就不能回避阐释相对主义问题。或许正是出于对阐释相对主义的抵御,张江先生在关于阐释有限与无限的新解说中,一再强调文本对“阐”的存在论优先性。文本不仅是“诠”之有效性的聚集点,也是“阐”之有效性的聚集点。文本收敛着阐释者的视域,限制阐释者的视域于文本“意蕴”所实然指向的方向展开理解行动。换言之,“阐”依附文本展开无限的创造性解释,而不允许阐释者主观任意地解说文本,对文本的无限阐释约束于文本自身的有限意义空间之中。如伽达默尔所说:“阅读和理解就意味着,把消息回溯到它原初的真实性。往往在被记述的东西的意义内容是有争议的,从而需要获得对‘消息’的正确理解时,阐释的任务就会被提出来。”〔15〕由此可知,新解说一再强调文本在存在论上优于阐释,主张阐释和意义基于文本而发生,意图十分明显,即不给阐释相对主义以存在的空间。
然而,为了给创造性阐释留足发挥的场域,新解说又不得不拒绝将自在存在的文本直接认作阐释的对象。新解说不把文本当作一种固化的僵死物,文本与阐释之间有着一种共生关系。文本实际上是一种可能的阐释对象,它是在自身所遭遇的阐释学语境下进入理解视域,成为阐释对象的。与之相应,文本的“意蕴”作为必然要通过阐释者的理解活动显现出来的意义,不过是一种“可能意蕴”,并且,只有作为“可能意蕴”,它在存在论意义上才具有先于阐释者的理解行动而存在的品格。但在认识论意义上,文本的“可能意蕴”既在阐释中成为阐释的对象,又在阐释中生成意义,而阐释生成的意义在解释语境中将衍生溢出文本自在意义的新内容。由此可见,尽管新解说承认文本的客观自在性,主张对确定文本的阐释只能指向该文本可能蕴含的意义,反对阐释者游离文本进行自我阐释。但是,文本的这种独立自在的品格,只是在约束文本无节制开放意义上有其存在论上的优先性,而在实际展开的阐释活动中,阐释的创造性总是将文本放在一种不断生成状态中,将文本及其意义阐释解释为处境化的生成物。由此可见,新解说虽然在意义本质问题上无法完全摆脱实在论立场的纠缠,但在意义生成问题上却走向了一种建构论立场。如果我们将阐释的素朴实在论称之为“强的阐释实在论”的话,那么张江先生所坚持的阐释实在论,就可以被称为“弱的阐释实在论”。
“弱的阐释实在论”承认文本对阐释有着边界约束效用,但给予阐释者以较大的自由,允许阐释者对文本意义进行“效果历史”式解读,鼓励阐释者以负责的态度去追求对文本意义更好的阐释,并将其奉为阐释的美德。新解说主张阐释是有限的,阐释者自由意志绝不可能无约束地自由发挥,凌驾在文本之上,将阐释行动演绎成在文本身上展开的一种无止境的主体建构游戏,尽情地去享受文本意义自我解释的思维乐趣。但另一方面,阐释有限也不排斥阐释无限,阐释者接受文本的约束,但约束不代表着绝对限制,阐释者在阐释的历史原则指导下,完全可以将文本带入新语境,在阐释中与“他者”相遇,通过主动性的阐释行动将文本意义从遮蔽状态中解放出来,显现一切可显示的东西。
职是之故,笔者一再强调,张江先生对阐释有限与无限问题的讨论采用了复合视角分殊进行。阐释的有限主要从存在论角度加以论证。阐释收敛于文本的有限意义,文本的“可能意蕴”构成阐释的边界,其先于阐释的存在论优先性构筑起防范阐释相对主义的大堤。阐释的无限主要从认识论角度加以论证。阐释以处境化显现的文本为对象,在确定的语境和公共理性规约下展开自由诠释,通过不断地实现文本与阐释者的“视域融合”,成就不同的理解事件,衍生不同的意义解释。在此种分层言说格局下,有限性指引出阐释的边界约束,无限性毕现了理解的自主性,前者是实存着的限制条件,后者是意义阐发的认知根据。
“弱的阐释实在论”就这样消解了新解说内部的逻辑自反现象。但是,这种消解的有效性取决于“弱的阐释实在论”是否可能,又如何可能。这个问题并不是一个自明性的问题,它需要解释,需要一个更本源性的说明。
三、“弱的阐释实在论”如何可能
新解说通过分层言说阐释的存在论要求和认识论要求,解决自身可能遭遇到的逻辑自反现象,严格说来,这只是一种策略性选择。这种策略性选择并没有从根基处解决存在于新解说中的内在张力。对新解说内存张力的根本性解决依赖于对它的实在论立场的重新解释。通过解释,促动其完成一种哲学范式的转换。
新解说以“弱的阐释实在论”对抗阐释的相对主义,在阐释现象的本体层面,文本相对于阐释具有存在论上的优先性,文本所承受的、由作者意图所构成的自在意义,相对于文本源自“可能意蕴”的有限意义具有存在论上的优先性。“弱的阐释实在论”将作者意图视作文本意义的源发根源,“找到作者及其意图,是显现文本自身的重要方向,是阐释必须承担的责任,这是无法摆脱的确定性之一”〔16〕。但是,为了摆脱“符合论”纠缠,在认识层面与现代阐释追求合理阐释的阐释学立场保持一致,新解说又不反对阐释者放弃文本的自在意义,认可“文本的自在意义也可以由读者在文本的呈现中自由理解”〔17〕,认为在确定的条件、确定的语境和确定的公共理性标准下,阐释可以按照意义生成的历史原则,让文本的能指(可能意蕴)和阐释的所指(意蕴可能)之间达成平衡关系,以“视域融合”方式开放文本不同的意义或者符合时代要求的意义。
然而,阐释的对象究竟是文本的自在意义,还是“在文本呈现中自由理解的意义”?“诠”与“阐”的区分在认知层面对它们进行了分层处理。“诠”追索文本之本义,它以文本的自在意义为阐释对象。“阐”对文本进行创造性解释以衍生文本的新意义,它以“在文本呈现中自由理解的意义”为阐释对象。但是,文本的自在意义与“在文本呈现中自由理解的意义”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显然是一个需要在本体层面讨论的存在论问题。在《论阐释》中,张江先生的重点不是处理这个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问题不重要,更不意味着不需要对这个问题进行更本源性的分析。在笔者看来,从存在论角度探究这个问题,恰恰是证成“弱的阐释实在论”如何可能的关键。
在传统存在论视域中,文本的自在意义是独立于阐释者而存在的客观意义,“在文本呈现中自由理解的意义”生成于阐释者的理解活动中,是阐释出来的意义,是文本自在意义在阐释者理解中的创造性呈现。是故,文本的自在意义与“在文本呈现中自由理解的意义”之间的关系就被解释成显现之物(是其所是)与显现(是其所现)的关系,即本体(本质)与现象(表象)的关系。相应地,阐释选择意识哲学范式。阐释活动在主客二元结构中展开,表现为意识反映对象的符合论行动。阐释在实在论立场上必然是“强”的。应当承认,“强的阐释实在论”从文本意义客观性立场出发,基于符合论认知立场解释阐释现象,其自身的形而上学立场与认识论立场并无扞格。问题在于,阐释的意识哲学范式以及实在论上“强”的立场,在近现代哲学攻击之下,漏洞百出,已经难以自圆其说。
康德率先指出事物的“是其所是”(文本的原意)区别于它的表象(“是其所现”),而我们的认识只能把握事物向我们表象出来的东西。事物的表象不过是事物表现在人们心中为人们所把握的主观表象。显然,事物的“是其所现”与事物的“是其所是”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它们之间有着存在论差异。也就是说,在原初意义上,“是其所现”存在于心灵(意识)中,它是内在的,而“是其所是”是外在于心灵的。当我们的意识有了对事物的表象,只不过意味着我们把握住了内心的表象,意识有了自己的内容,并不意味着我们把握了外在的事物。人们无法通过事物的“是其所现”实现对事物“是其所是”的把握,更不能将自身的主观感觉等同于事物本身。外在而独立存在的东西与在我们心中存在的东西之间的存在论差异,是无法通过认知活动消除的。
海德格尔则直接解构了事物先行存在的实体性。存在只是一种可能性,并且是一种在世界中存在的可能性,它不是先行上手的实体存在物,而是由在世存在根据其世界性而开显出来的。符合论所依存的存在论哲学并不理解实存概念的存在论意义,所以在意义阐释问题上要求阐释符合文本的原意。虽然海德格尔不同意康德在“是其所现”和“是其所是”之间划定的存在论差异,但他也不否认这种差异的存在,不过在现象学意义上重新对其作出解释而已。按照海德格尔的观点,人是在世的存在,他不是前往到内心的表象中,而是前往到达世界中的物那里去。世界中的物在人的理解中呈现自身。因此断言一个命题是真的,不过意味着命题所指称的事实正好以它所指示的那个样子呈现自身。也就是说,从存在论次序上说,一个断言为真的命题,奠基在人的发现上,让人看见。它在人的看见中将自身揭示为真,展示自身。海德格尔由此断定:“命题的‘真在’(真理)必须被理解为揭示着的存在。所以,如果符合的意义是一个存在者(主体)对另一个存在者(客体)的肖似,那么,真理就根本没有认识和对象之间相符合那样一种结构。”〔18〕
意识哲学范式在英美现代哲学那里也遭遇到激烈批判,普特南认为,寻求一种与人无关且对应着外部现实世界的客观真理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思想(从而心灵)便具有与物理对象根本不同的本质。思想具有意向性的特征——它们能指称别物,物理的东西都没有‘意向性’,尽管那种意向性要通过心灵对于那种物理东西的运用而得到”〔19〕。这就是说,思想或者心灵只有借助某种神秘的力量——即诉诸“上帝视角”——才能完成对物理东西的运用。但问题恰恰在于,并不存在这样一种“上帝视角”。设想一种形而上学实在论,设定一种心灵的神秘力量,不过是思想无能与懒惰的一种表现。人只有人类视角,只能带着人类的立场和偏见去理解自身经验。人必须承认自身的局限性,容忍认识产生错误,将对真理的追求转换为追求一种合理的可接受性。
阐释理论抛弃意识哲学范式,意味着抛弃主客二元结构。实体与属性、本体与表现、本质与现象等一系列对立的关系范畴,被当作形而上学虚构的未经证实的观念被放弃。阐释重心也将从自在意义与客观解释转移至合理解释。文本作为被阐释的对象并非在阐释之前就先行于阐释者和阐释行动而存在,阐释活动不仅建构作为阐释对象的文本,也同时建构意义。如此一来,现代阐释学的任务就不是去理解文本的自在意义,而是去理解文本的合理的可接受性内容。在现代阐释学视域中,文本的这种合理的可接受性内容就是文本的“事情本身”,也就是文本的真理性内容。作为阐释的对象,文本的真理性内容存在于理解中,在历史地展开的理解活动中开显自身。“也就是说,意义不栖身在呆滞的客观实体(文本)中,而是存在于充满活力的阅读经验中。”〔20〕就此而言,“在文本呈现中自由理解的意义”比文本自在的意义在阐释学上更具有存在论上的本真性。换言之,从文本意义的真理性呈现来说,阐释比文本更重要,阐释出来的意义比作者意图更重要。
需要注意的是,这种阐释观并不否认作者意图的存在,也承认作者意图先行于阐释而进入文本,并构成文本的自在意义。这种阐释观只是指出,无论是作者意图,还是文本的自在意义,都不能直接成为阐释对象。阐释以作者意图和文本自在意义所包含着的合理的可接受性内容为对象,文本中所包含着的这些真理性内容才是文本的“事情本身”,是阐释所直接面对的东西。这样,阐释的意识哲学范式就被阐释的现象学范式所取代,阐释的实在论立场也就相应地转向现象学存在论。
以现象学存在论观点解释阐释对象(文本及其意义),就不会将其作亚里士多德式实体主义理解,归属为必须进入心灵或认识的机能作用范围而被把握的现成之物。文本的“事情本身”,不是文本的自在意义,而是存在于时间中,在时间中延续、变化,将自己的本真性“如其所是”地展露出来的文本的“事情本身”。阐释必须承认这种在“去存在”过程中将自身现实化的“事情本身”的先行具有,否则阐释就是从无中生成有。但这种“事情本身”又不能是现成之物,因为如果将作为阐释对象的“事情本身”当作现成物,阐释就是复原,就是机械克隆,意义就是实体化的意识构成物,一种形而上学怪兽。只有将文本的自在意义解释为现象学的“事情本身”,才能够保证阐释一方面接受文本的限制——阐释不是阐释主体的意志纯粹的、无边界约束的自由发挥,另一方面又能够使得文本的“事情本身”在阐释中“存在”,并生成与阐释所对应的“真理”,让自身的“所现”成为“所是”,在理解中达成“是其所现”与“是其所是”的统一,实现意义诠释与真理解释之间合法的理性关联,从而使得“旧的东西与新的东西在这里总是不断地结合成某种更富有生气的有效的东西”〔21〕。就此而言,对文本的阐释,既不完全受外在于阐释者且自在存在的文本意义(作者意图)的支配,也完全不受阐释者的前理解结构的控制,它必然是理解视域与被理解者视域的视域融合过程以及经由这种融合造就的“效果历史意识”。如同文本只能在阐释中才能成为阐释的对象那样,阐释只有相关于文本的可理解的合理性内容,才能生成真理性的意义诠释。这意味着,只有承认文本的“事情本身”先行于阐释者及阐释行动存在,具有存在论上的优先性,阐释直接面对的是文本的可接受的合理内容,阐释作为一种有界而无限的活动,作为一种不断发生着的历史事件和祛除遮蔽、开显真理的行动才是可能的。职是之故,张江先生关于阐释有限与无限的新解说须立基于现象学存在论之上,方能在逻辑上达致融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