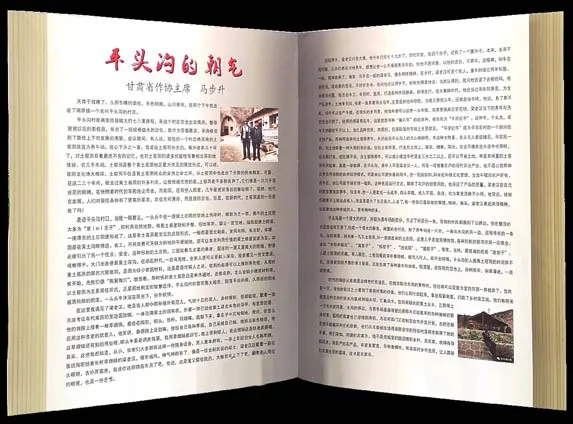平头沟的朝气
2020-02-21马步升
马步升
天终于放晴了。久雨乍晴的崇信,天色明媚,山川秀丽,在那个下午我走进了锦屏镇一个名叫平头沟的村庄。
平头沟村距离崇信县城大约七八里路程,来这个村庄完全出自偶然。整体脱贫以后的崇信县,举办了一场规模盛大的论坛,我作为受邀嘉宾,亲身感受到了崇信上下对发展的渴望。会议期间,有人说,崇信的一个村庄将原来的土窑洞改造为养牛场。我心下为之一喜。我是在土窑洞长大的,离开老家几十年了,对土窑洞有着磨洗不去的记忆,也对土窑洞的诸多优越性有着相当深刻地体验。在几千年间,土窑洞是整个黄土高原地区最为常见的居住形式,可以说,窑洞文化博大精深,土窑洞不仅是黄土高原民众的安身立命之所,从土窑洞中也走出了无数的民族精英。可是,在这二三十年间,我去过黄土高原的许多村庄,让我倍感无奈的是,土窑洞差不多都废弃了,它们像是一只只干涩迷茫的眼睛,在怅惘着时代的车轮绝尘而去,而窑洞,在有些人眼里,几乎是贫穷落后的象征物了。固然,时代在发展,人们对居住条件有了更高的要求,非但无可厚非,而且理所应当。但是,在新时代,土窑洞真的一无是处了吗?

走进平头沟村口,当我一眼看见,一头头牛在一座座土庄院的空地上徜徉时,眼前为之一亮。养牛的土庄院大多为“崖(ai)庄子”,即利用自然地势,将黄土悬崖斩削齐整,挖出窑洞,留出一定空地,版筑起黄土院墙,一座漂亮的土庄院便形成了。这是黄土高原最常见的庄院形式,一般都是面北朝南,背风向阳,采光好,保暖,因是在黄土沟畔修造,省工,不用浪费可开辟为耕地的平缓坡地,还可让本无利用价值的黄土悬崖变废为宝。如此便引出了另一个优点:安全。这种形制的土庄院,三面贴着几丈高的悬崖,留出的一面又是高大的院墙,野兽很难得手。大门出去便是黄土深沟,在动乱时代,一旦有危险,全家人便可从容躲入深沟。我曾看见一些文章说,黄土高原的居民穴居窑洞,是因为缺少建筑材料,这真是强作解人之语。窑洞的起源可以上推到周先祖,从那时候开始,先民们便“陶复陶穴”,想想看,那时候的黄土高原还是林木遍地,走兽成群,怎么会缺少建筑材料呢。以土窑洞为主要居住形式,正是因地制宜的智慧选择。平头沟村的窑洞高大敞亮,院落平坦开阔,久雨后的阳光遍洒向阳的院落,一头头牛沐浴在阳光下,分外欢快。
在这里我遇见了梁老汉。他是在人群中那种格外有范儿,气场十足的男人。身材瘦削,但却挺拔,戴着一顶无法考证年代来历的宽边圆顶帽,一身沾满黄土的粗布衣,外罩一件已经被黄土遮去本色的马甲。有意思的是,他的肩膀上搭着一根旱烟锅,垂挂在胸前,铜头,铁杆,玛瑙嘴。我解下来,拿在手中沉甸甸地。我说,你怎么还用这种古老的玩意儿,他笑说,香烟抽上没劲嘛。他给自己栽种旱烟,自己采摘自己抽。他相当自负地说,我这旱烟锅还有别的用处哩,哪头牛要是调皮捣蛋,我用旱烟锅教训它,碰上恶狗咬人,我这烟锅还是防身武器哩。其实,这些我都知道,从小,长辈们大多都有这样一件随身设备,男人基本都有,一些上年纪的女人也抽旱烟。我说胸前挂着长杆旱烟锅的梁老汉,格外威风,精气神都有了,像是一位全副武装的战士。梁老汉还戴着一副石头眼镜,古朴而高贵,我说你这眼镜有年月了吧,他说,这是家父留给我的,大概百年上下了吧,戴着老人用过的眼镜,也是一份念想。
说起养牛,梁老汉兴致大增。他今年已经七十九岁了,四代同堂,有四个孙子,还有了一个重孙子。本来,生活不成问题,儿孙们都反对他养牛,都想让他一心不操颐养天年的。但他不愿闲着,以他的话说,不养牛,没精神,和牛在一起,精神就来了。确实,与牛在一起的梁老汉,像牛那样精神。在乡村,梁老汉可是个能人,童年时读过两年私塾,他笑说,娃娃家的贪玩,不好好念书。我问他还认得字不,他有些得意地说:当然认得的。我问他能读下去报纸吗,他说那没问题。他还会木工,年轻时,盖房,打造各种木质器具,都很在行。在大集体时代,他还当过两年饲养员,为生产队养牛。土地承包后,他家一直养着两头母牛,主要是耕地和积肥。为啥只养两头牛,还都是母牛呢,他说,多了养不起,母牛可以生产牛犊。在很长的岁月里,他每年都可以出售一头牛犊,给家里换来日常花销。
梁老汉当下的养牛与先前完全不同了,他养的都是商品牛。这是优质牛种“秦川牛”的改良种,被命名为“平凉红牛”。这种牛,个头大,成牛大约都在千斤以上,加之品种优良,肉质好,在国际国内市场上大受欢迎。“平凉红牛”成为平凉农村的一个新兴的支柱产业。而利用废弃的土窑洞养牛,大约出自平头沟人的无心插柳吧。牛这种大牲畜,自从与人类结缘后,和农民一样,对土地有着一种天然的亲近感。住在土窑洞里,行走在土地上,踏实,健康,阳光,完全不像关进水泥牛栏那样,或无精打采,或狂躁不安。在土窑洞养牛,可以减少建造牛栏资金三分之二以上,还可以节省土地,将废弃闲置的土窑洞利用起来,真是一举数得。在平头沟,养牛人不是梁老汉一人,而是一项普惠农户的现代农业产业,也不是以前那种自养自用自销的自然经济模式,而是由公司提供基础母牛,统一配给饲料,科学化和模式化管理,生出牛犊归农户所有,成牛后,由公司按市场价统一收购。这种兜底运行方式,解除了农户的经营风险,也保证了产品的质量。梁老汉在自己的院落里独自养牛,仅去年,他一人便卖出一头成牛,四头牛犊,收入不菲。我说,你为家里贡献不小啊,他笑说,娃娃们都看不上我这点收入,我主要是为了自己高兴,人老了,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精神。
确实,梁老汉看起来很精神,比起像他这种年纪的人,要有精神的多。
平头沟是一个很大的村庄,开辟为养牛场的部分,只占了村庄的一角。原有的村民都搬到了公路边,住在整洁的水泥房或砖瓦房了,形成一个很大的聚落。闲置的老村庄,除了养牛场这一片外,一条洪水沟的另一边,还有很长的一条沟,沟的两面,排列着一孔孔土窑洞,和一座座废弃的土庄院。这里几乎是窑洞博物馆,各种形制的窑洞庄院一应俱全,诸如“半明半暗庄”“高窑子”“拐窑子”“地坑院”“箍窑子”等等,当然,最普遍的还是“崖窑子”。人是土窑洞的灵魂,有人居住,土窑洞看起来朴素粗糙,使用几代人,都不会坍塌。平头沟的人搬离土窑洞的时间并不长,原来被刮削齐整的黄土崖面,已经生满了各种灌木和杂草,院落里,庄院前的空地上,杂树疯长,杂草凄迷,一派破败感。
时代的脚步从来都是这样匆忙而凌乱,在抛弃陈旧无用的事物时,往往将可以变废为宝的东西一并抛弃了。忽然有一天,当地的有识之士看到了窑洞村落的价值。他们立即行动起来,拿出规章制度,打响了乡村保卫战。他们将原来横亘在村庄间的洪水沟筑成梯级水坝,汇集洪水,在向来缺水的黄土山乡,已算得上一方有水的风景。水沟的那边,与养牛场遥遥相望的是那片已经废弃的杂树掩映的窑洞村落。聪明的商家也已经嗅到商机,与政府部门正在制定合作开发计划,总的思路是绝不能破坏村庄的原貌,他们从无数被改造得面目全非的传统村落那里获得了新的灵感,他们深知,所谓的农家乐,绝不是把城里的饭店搬到乡村。是农家,就得有田园风光,有自产的农产品,有家畜家禽,有牧童横吹,有真实的乡村生活,让人体验到农家生活的真谛,这才是农家乐。
现在到处都在说乡愁,留住乡愁的愿望无比强烈,但是,究竟什么是乡愁,却很少有人给出一个清晰的回答。其实,乡愁的本义,不是对乡村的留守者而言的,而是给离乡者留存一些乡村记忆,中华文明之光是从大地深处迸发出来的,不懂得中国农村,很难真正理解中华文化精髓。再者,让那些生长于城市的新一代人,在课余,在作业之余,在繁忙而烦乱的工作之余,有一个亲近土地的场所,借以换一换心境,补充继续前行的能量。说的再远一点,随着老龄社会的到来,老人们在清风明月的乡村养老,花费少,接地气,在一个闲适宽松的活动场所里,做一些简单快乐的农活儿,比如种菜种花,比如像梁老汉那样与牛为友,似乎会更有利于身心健康,而介入平头沟开发的商家,正是以这样的理念勾画未来的。
离开平头沟时,正是夕阳西下时分,阳光仍然明亮,梁老汉弯腰与他的牛在说着什么话,离老远,都能看到他志得意满的神情,另一些老人也在养牛场不紧不慢忙活着,个个兴致勃勃的样子。在如今普遍缺少年轻人的村庄里,弥漫着挥之不去的暮气,而同样缺少年轻人的平头沟村,散发的却是朝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