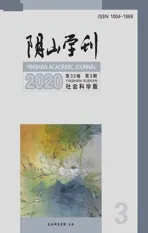舒婷、芒克、多多诗歌导读
2020-02-20吴投文
吴 投 文
(湖南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湖南 湘潭 411201)
趋向爱情之美的深挚情怀
——舒婷《致橡树》导读
我如果爱你——
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
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
我如果爱你——
绝不学痴情的鸟儿,
为绿荫重复单调的歌曲;
也不只像泉源,
常年送来清凉的慰藉;
也不止像险峰,
增加你的高度,衬托你的威仪。
甚至日光。
甚至春雨。
不,这些都还不够!
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
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
根,紧握在地下,
叶,相触在云里。
每一阵风过,
我们都互相致意,
但没有人
听懂我们的言语。
你有你的铜枝铁干
像刀,像剑,
也像戟;
我有我红硕的花朵,
像沉重的叹息,
又像英勇的火炬。
我们分担寒潮、风雷、霹雳;
我们共享雾蔼、流岚、虹霓,
仿佛永远分离,
却又终身相依。
这才是伟大的爱情,
坚贞就在这里:
爱——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977年3月27日
(选自舒婷诗集《舒婷的诗》,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
舒婷(1952-)在中国当代诗坛具有特殊的影响力,是少数几位最为大众熟悉的当代诗人之一,在某种意义上,说她是大众心目中的新诗形象大使,似乎并不过分。实际上,舒婷诗歌创作的时间并不长,前后不过十年,诗歌数量也不是很多,从1985年基本停止诗歌创作,一直到现在,少有诗歌新作问世。舒婷一直是读者关注的一个焦点,只要有她出场的文学活动,读者的反应依旧那样热烈,而舒婷总是以她特有的矜持把自己疏离在读者的文化怀旧之外。舒婷是一位安静的写作者,坚持“三不”原则:不接受采访,不朗诵诗歌,不参加会议,偶有参加也不发言。文学圈里的热闹她很少侧身其中,她安静地写着自己的散文,出版的散文集很是不少,散文集《真水无香》获得过“第六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08年),但读者对她的印象基本上还是停留在朦胧诗时期。现在看来,在朦胧诗谱系中,舒婷的创作实际上并不具有典型性,这其中包含着特定历史时期读者的误读,也包含着文学史辨认的某种误差。
舒婷诗中新异的浪漫气息和特有的温婉迥异于朦胧诗向历史真实的纵深切入和重在挖掘心理深度的现代主义艺术实验,她的创作风格在整体上还是趋向一种古典式的中和之美,她的诗歌尽管也显示出热切拥抱现实的诚恳,但主要还是倾向于自我性情的真实流露。舒婷诗中的真诚特别打动人,她的语调和词语的内在温度协调在一双眸子闪烁着憧憬的光彩里。从舒婷的整体创作来看,她的温婉和温婉里微带的忧伤都是自我性情的流露,显得毫不做作,而在诗的形式上,她似乎沉浸得更深,自我的性情与词语毫无间隔的敌意,而是相互融汇在恰当的回旋里,恍如诗人的情绪是透明的,又是柔软的,没有急躁和过深的压抑,似乎是从词语中自在地生长出来的,趋向形式上的圆满与和谐。这使舒婷的诗具有中国古典诗词的美质,也就有现代主义诗歌的某种气韵。与传统的隔与不隔,与现代主义的疏与不疏,都在舒婷恰到好处的掌握里。舒婷的艺术尺度倾向平衡与内敛,然而拒绝晦涩,可能在诗的深度上有所欠缺,却有雍容和华茂的气质,把读者引向对生活和生命富有激情的静思和凝眸。
在舒婷的诗歌中,《致橡树》在读者中的影响最大,流传最广,另一首《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也是她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不过,两首诗比较起来,前者更多地表现为一种个人话语,显得真诚得多;后者也萦怀着个人的情愫,到底像是一个把宏大抒情自我化的装置,我总觉得诗中的意象组合远没有达到《致橡树》的流转自如,诗中表达的情感还是没有压住主题的飘浮,尚不能与艾青《我爱这土地》的沉雄壮美形成对称。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其中可能包含着个人的偏见。不过,阅读中的偏见有时作为一种直觉,未必完全没有可靠性,也未免不是一种读诗的方式。阅读的公正性对诗歌只是一种理想状态,实际上很难转化为可靠的阅读实践。尊重阅读中的直觉与个体感受,对诗歌阅读恐怕特别重要。在很多时候,喜欢或厌恶一首诗几乎没有什么道理可言,诗歌阐释中的相互抵牾也是一个常见的现象。
《致橡树》在结构上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从开头到“甚至春雨”一句为止,诗中纷繁的意象皆缠绵在爱情的复杂选择上,而诗人有自己爱的确信。“我如果爱你——”,“我”将如何选择自己在爱情中的位置?这是爱情的难题和痴情男女的普遍困惑。凌霄花、鸟儿、泉源也好,险峰、日光、春雨也好,这些意象都是某种爱情观的体现,却都不是诗人理想中的爱情选择。凌霄花的依附、鸟儿的痴情、泉源的奉献、险峰的衬托、乃至日光的温煦、春雨的滋润,在诗人看来,这些都是女性在爱情中的自我迷失,不符合现代爱情观所要求的人格平等。诗人站在女性自觉的位置上提出“如何爱”的问题,爱情是女性人格尊严的确证,哪怕成为日光,成为春雨,也不是女性在爱情中的确切位置。在诗人深情的倾诉中,对爱情的渴求是对爱情本身的皈依,而不是中国传统婚姻中的依附。在中国的传统婚姻中,两性关系总是投射着物质的暗影,诗中被一种明亮的情绪底色所取代,显示出女性的爱情自觉和自信。爱情作为女性人格尊严的体现,既是对传统婚姻观的质疑,也包含着对女性追求自身幸福的肯定,彰显出爱情关系中两性平等的正当性。
诗的第二个层次从“不,这些都还不够”到“却又终身相依”为止,是在第一个层次上的深度递转,诗的境界在此变得异常开阔,凸显出两性爱情关系的健全与丰富。“不,这些都还不够”一句承上启下,从诗人果决的语气里,可以发现一位新时代女性追求爱情的坚定和执着。诗人告诉我们:“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这就是诗人向往的爱情,也是一种理想形态的爱情。诗人用木棉代表女性,用橡树代表男性,这两个意象用得非常贴近,符合理想爱情中男女双方的人格形态。橡树挺拔高大、木质坚硬,对环境的适应性很强,符合男性雄强的身形特征,具有阳刚之美;木棉树又叫英雄树,生命力顽强,是花树中最高大的一种,花朵鲜艳饱满,符合女性秀美的外形特征,具有阴柔之美。在诗人的笔下,橡树和木棉对称于爱情中和谐的两性关系,但这种两性关系却又不是互补的,而是对称于双方平等的人格和健全的意志,“我们分担寒潮、风雷、霹雳;/我们共享雾蔼、流岚、虹霓,/仿佛永远分离,/却又终身相依”。在此,诗中的情感变得异常热烈而又内敛于清醒的人格意志,如一曲音乐中最高亢的部分,突然又有趋向静止之美的微妙的过渡,却终于没有停止,而是转向两性体验最深刻的共鸣。这就是爱情的实质。木棉所彰显的独立女性之美在此呼之欲出,诗中回荡着激越的爱情的誓约,在极富想象力的画面和婉转起伏的旋律中,流露出趋向爱情之美的最深挚的情怀。
诗的第三个层次从“这才是伟大的爱情”到全诗的最后一句,水到渠成,由抒情转入带有总结性的议论,也是全诗主题的升华部分。我注意到有一种说法,认为诗歌结尾的这几句显得多余,可以删除,就在诗的第二个层次戛然而止,可以起到此处无声胜有声的效果,让读者自己去回想。若如此,在诗的整体结构上无疑是一个败笔。诗的最后这几句相当于全诗的缓冲地带,把诗中的余音引向读者心中更丰富的涟漪,在诗境上显得更为开阔,也似乎具有一种陡峭的效应,诗中所有的对立、冲突、希冀与和谐都纠缠在这里,变得深幽、绵渺,也有斩钉截铁的果决,诗人把全部身心倾向于生命与爱的远景。“爱——/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还有什么比诗人心迹的这种流露更为动人呢?犹如我们走向生命的一个隘口,一个爱的眼神在前方召唤着我们。
舒婷的诗并不“朦胧”,《致橡树》也是如此,近乎透明却耐人咀嚼。舒婷多次表示,《致橡树》的创作起因是呼唤和展现当代女性的觉醒意识,她是在用自己的声音说出对世界的感受,因此,这并非一首爱情诗。《致橡树》主题明朗,却也不是一览无余,舒婷的说法自有其道理。这是理解此诗的另一个角度,与读者往往把此诗解读为一首爱情诗实际上并不相悖。1977年3月在鼓浪屿,舒婷与诗人蔡其矫因为女人的外表和独立性问题产生争议。舒婷认为,每一个女人都有自己的观点和理性的思考,女人应该独立自强。那天晚上,舒婷一气呵成写出此诗,原题《橡树》,第二天被蔡其矫带到北京交给诗人艾青。艾青看后非常赞赏,并建议把诗的标题《橡树》改成《致橡树》。[1]艾青对标题的修改是恰当的,符合诗中抒情主人公的倾诉口吻,橡树的位置产生某种微妙的偏移,成为抒情主人公倾诉的对象,而木棉凸显为诗中的抒情主体。木棉与橡树的并肩而立对称于“我”与“你”之间爱情的浪漫抒写,这是此诗在构思上的新奇之处。
《致橡树》之所以得到读者的喜爱,在主题的新颖之外,还在艺术形式的别致上。此诗气韵流动,情采盎然,结构浑然一体,全无滞涩和梗结,所有的词句几乎都是通体透明的,闪烁着诗人情绪的光泽,有一种高度圆融的秩序感。诗中的意象纷至沓来,每一个都恰如其当,对应诗人内心的微妙波动。在意象的疏朗处,可以看出诗人的犹豫;在意象的绵密处,于层峦叠嶂之中,可以看出诗人的急切与激烈。由此,诗的意境是斑斓而清澈的,在单纯中有一种玉石般圆润浑然的美感,毫无雕琢的痕迹。诗的语言大体是敞亮的,用词洁净而有鲜活的光彩,句式的变化保持自如的柔韧度,词句层层渐进,情感的复杂与丰富通过精心处理的假设、让步等特殊句式表现得曲折尽致。诗中丰富的象征意蕴既是修辞产生的综合性效果,也是诗人爱情观的体现。爱情诗还是要写得美一些,写得丰饶而跌宕一些,舒婷深得其中的奥秘。这也是《致橡树》的魅力所在。
抗争是通向自由的坦途
——芒克《阳光中的向日葵》导读
你看到了吗
你看到阳光中的那棵向日葵了吗
你看它,它没有低下头
而是把头转向身后
它把头转了过去
就好像是为了一口咬断
那套在它脖子上的
那牵在太阳手中的绳索
你看到它了吗
你看到那棵昂着头
怒视着太阳的向日葵了吗
它的头几乎已把太阳遮住
它的头即使是在没有太阳的时候
也依然在闪耀着光芒
你看到那棵向日葵了吗
你应该走近它
你走近它便会发现
它脚下的那片泥土
每抓起一把
都一定会攥出血来
1983年
(选自芒克诗集《芒克的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
向日葵似乎是诗人的偏爱之物,在古往今来的诗中多有表现。因为向日葵具有向光性,诗人的吟咏也往往由此生发开去,不太容易摆脱“葵花朵朵向太阳”的构思模式和主题意向。古诗中有“葵藿倾太阳,物性固莫夺”(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更无柳絮因风起,惟有葵花向日倾”(司马光《客中初夏》),“可曾沾雨露,不改向阳心”(刘克庄《向日葵葵》),“花开能向日,花落委苍苔”(戴叔伦《叹葵花》)等等,皆是如此。新诗中更不少见,如“一颗慷慨的心脏/并成满地的向日葵满天的太阳”(余光中《向日葵》),“向日葵低头微笑着,望不尽太阳起处的红色天涯”(郭小川《团泊洼的秋天》),“百姓们谁个不知道向日葵?/我们是向着太阳,也向着农家”(郭沫若《向日葵》),等等。我在网络上粗略查找,以向日葵为题的诗实在是一个泛滥,多到几乎读得腻味的程度。这些诗大同小异,都借用向日葵的向光性作为想象或构思的起点,表达一种忠顺或皈依的情感。从诗的构思方式来看,这都是象征惹的祸,从更深一层来看,还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心理的流露。从这个角度对照来读芒克(1951-)的《阳光中的向日葵》,就会发现此诗的独异之处。
从诗的标题来看,阳光中的向日葵该是一个多么和谐的画面,该是在风光旖旎中呈现出一棵向日葵向着阳光开放的生动图景,然而,诗中出现的向日葵却是太阳的一个怀疑者和反叛者。它有不屈的意志,有勃发的生命元气,象征一种人格性的力量,是一种健全的人格力量的化身。向日葵本是一种极普通的植物,但因它的向光性而被诗人反复吟咏,已经形成一种高度模式化的写作规制。人们把向日葵称作“太阳花”,乃至有“向日葵的花语是太阳”一说,这也是诗人很难摆脱的思维陷阱。此诗不落窠臼,呈现出向日葵不同流俗的傲岸形象,从深层的创作心理来看,还是诗人自我形象的漫溢,是诗人生命体验的真切流露。当然,诗中也隐含着某种时代症候,个体的反叛对于整体秩序的冲击,在此诗写作的1980年代初期,是一种相当普遍的时代情绪。
此诗有非常清晰的层次感,三节之间的转换流畅自如,而又让人停顿在沉思的间隙中。诗的第一节写向日葵的抗争,“你看它,它没有低下头/而是把头转向身后/它把头转了过去/就好象是为了一口咬断/那套在它脖子上的/那牵在太阳手中的绳索”,这是两种力量的对比,两种力量的抗衡。看哪,阳光中的那棵向日葵如此桀骜不顺,以令人震悚的方式要挣脱太阳的控制!诗中的几个动词用得非常精准,向日葵的“转”与“咬”,太阳的“套”与“牵”,呈现出控制与反控制,奴役与反奴役的激烈状态,向日葵要咬断太阳套在它脖子上的那根看不见的绳索,竭力摆脱太阳对它的奴役,争取获得自由生长的空间。
诗的第二节写向日葵获得自由之后生命状态的舒放,它不再被太阳的绳索所牵引,而是昂着头,怒视着太阳,“它的头几乎已把太阳遮住/它的头即使是在没有太阳的时候/也依然在闪耀着光芒”。这是一种肆意生长的生命状态,阳光中的向日葵享受着精神的自由与超迈!从向日葵的生物特性来看,它的花朵明亮大方,给人以喜庆、热烈、愉悦的感觉,诗中对向日葵的描绘并没有偏离这一特性,但其象征意义却是颠覆性的,显然不同于一般的模式化写作。向日葵的头可以把太阳遮住,它的光芒完全是属于它自身的,在此,向日葵的向光性被忽略和移除,而被置换为一种富有尊严的生存方式。
第三节写向日葵为争取自由所付出的代价,“它脚下的那片泥土/每抓起一把/都一定会攥出血来”,原来向日葵脚下的泥土浸润着鲜血,可见它的抗争是多么的酷烈。在此,诗人的想象何其大胆而峻险,尽管前面有所铺垫,仍有出其不意之处。这符合诗的想象的逻辑,尤其一个“攥”可谓笔力千钧,让人警醒。作为一种人格精神的化身,在向日葵伟岸的形象中包含着一种健全的诗性力量。这就是向日葵作为一个生命个体带给读者的启示。
芒克是“白洋淀诗群”的核心人物,和多多、根子一起被称为“白洋淀三剑客”,是朦胧诗的代表诗人之一。《阳光中的向日葵》创作于1983年,是芒克流传最广的代表性作品,似乎和朦胧诗的主导性风格有较大的差异,带有非常突出的个性化色彩。其中的原因,一是创作年代相对偏晚。朦胧诗到1983年已是强弩之末,朦胧诗群体的内部分化已相当明显,“朦胧诗”作为一个诗人群体在“第三代”诗人的冲击下实际上已经溃散;二是来源于诗人对大自然的亲近。芒克是一个天性纯真的诗人,对做作有一种近乎本能的厌恶,正如诗人多多所说,“芒克正是这个大自然之子,打球、打架、流浪,他诗中的‘我’是从不穿衣服的、肉感的、野性的,他所要表达的不是结论而是迷失。迷惘的效应是最经久的,立论只在艺术之外进行支配。芒克的生命力是最令人欣慰的。”[2]诗人的气质投射到他的创作中,大概就是这种旷野般裸露的宽厚和芜杂,另一方面又有掩饰不住的锋芒和锐气,把旷野的生机融合到天真之中,因此,才有芒克充满肉感和野性的写作。
从《阳光中的向日葵》所表达的主题来看,向日葵是一个粗犷的人格形象,有一种饱满的力量感,而这正是诗中隐隐燃烧的火焰,给人一种似乎将要炸裂的感觉。朴实的口语化形态也是此诗的一个重要特色,在亲切中埋伏着催促和期待,使“你”忍不住一步步靠近向日葵。诗人自己在诗中并未出现,却是“你”的另一个化身。诗中用第二人称叙述,既是一种隐藏,也是一种袒露,在隐藏和袒露之间,实际上是一种生存真相的揭示,抗争是通向自由的坦途。“我”包含在“你”之中,又诞生在向日葵的启示之中。当“你”弓下腰,攥起一把向日葵脚下带血的泥土,那是“我”的心在战栗。此时,“你”还能说什么呢?而“我”也在无言之中。阳光中的向日葵,显得通透明亮,它的内心怀着峻急的渴望和热烈的趋赴自由的向往。读者可以想象,向日葵即使站在黑暗中,仍然在静静地生长内部的力量,积蓄对太阳的新一轮的抵抗。
看得见乡愁绵密而细小的触须
——多多《阿姆斯特丹的河流》导读
十一月入夜的城市
惟有阿姆斯特丹的河流
突然
我家树上的桔子
在秋风中晃动
我关上窗户,也没有用
河流倒流,也没有用
那镶满珍珠的太阳,升起来了
也没有用
鸽群像铁屑散落
没有男孩子的街道突然显得空阔
秋雨过后
那爬满蜗牛的屋顶
——我的祖国
从阿姆斯特丹的河上,缓缓驶过……
1989
(选自王家新编选《中国当代诗歌经典》,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1989年,诗人多多出国,“先后辗转漂泊于荷兰、英国、加拿大,后定居荷兰”,[3]期间曾任伦敦大学汉语教师,加拿大纽克大学、荷兰莱顿大学住校作家,直到2004年归国,担任海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在旅居国外十五年的时间里,多多的家国之思在他的诗中时有流露。对一位诗人来说,这几乎是一种写作的本能冲动。皈依故乡是一种普遍的人类情结,敏感的诗人更不例外。从《阿姆斯特丹的河流》注明的写作时间“1989”来看,写于诗人去国不久,当时他居住在荷兰首府阿姆斯特丹,还处在初到国外的适应时期,可能情绪心理上有一些波动,有一种特别的思乡情结。因此,把此诗看作一首以思乡为主题的诗歌,亦无不可,不过,诗中似乎别有一层更幽深的意味,值得细细咀嚼回味。
诗中铺展的情景在现实与回忆中交错闪回,此情此景与故国故家牵连在诗人的思绪中,诗中时空的转换带动一幅充满想象力的图景,似乎看得见里面有一个身处异国而孤独的人在凭窗凝望。诗中的语气极其冷静而节制,“十一月入夜的城市/惟有阿姆斯特丹的河流”,“惟有”二字意在强调,诗人在孤单中凝望一条河流的波动,此处,河流暗示思乡情绪的绵绵不绝。入夜大概是一个好时辰,此时喧嚣在慢慢沉寂,正是一天中放松的时候,适合于把内心倾倒在华灯初上的迷彩里。此时,诗人临窗而望,他所看见的只有穿越阿姆斯特丹的河流,一种静的气氛荡漾开来,然而又是诗人内心的紧张在扩散,似乎隐隐地要发生什么,或者诗人在期待着什么。
“突然”正是诗中的一个逆转,独立成为一节,这个处理非常巧妙,带有强化的意味,突出一种瞬间的触动。这两个字是多么孤立,仿如诗人置身于悬崖上,惊心于毫无依傍的处境,给人突兀险峻的感觉。这也是诗人面临的真实处境,独在异乡为异客,他似乎被突然击中,心神摇晃于一个过去的时刻,于是才有“我家树上的桔子/在秋风中晃动”的幻觉。桔子这个意象在诗中极其重要,中国人喜爱在房前屋后和庭院里栽种桔树,既可以美化环境,亦含有对品行高洁的向往;桔子也是含有美好祝愿的食品,象征大吉大利。因此,诗人选择桔子这个意象,具有文化心理上的依据。试想一下,诗人沉浸在回忆中,似乎他在窗前触手可及故家树上的桔子,秋风中的桔子已经熟透,欲落未落,晃动在秋天默片般的寂寥中。中国古人的秋思都带有这种特殊的气息,这与诗人远在异国他乡的心境是很契合的。此时,时空距离不复存在,诗人恍然置身于故国故家的实景中,但诗人又是清醒的,竭力抑制内心情绪的起伏,而又无法镇定于自我的克制。这是一种非常微妙的心理情绪,身在异国而又心怀故土,诗人见景生情,由眼前的景物不自觉地想到故家最熟悉的事物,却又不忍回首,心中有一种突然而起的无法言说的刺痛感,似乎是隐隐的却又是如此的强烈。一个海外游子的形象跃然纸上,还有什么可以抵挡他内心的刺痛?
于是,才有第四节这样的妙句,由回忆转换到现实中来,“我关上窗户,也没有用/河流倒流,也没有用/那镶满珍珠的太阳,升起来了”,这几句看起来显得很平静,却是无声胜有声,有极强的张力感,似乎波澜不惊,平静之中却有情绪的暗流奔涌。诗人关上窗户也没有用,心中的刺痛依旧,哪怕是河流倒流,也没有用。为什么“河流倒流”?此处并非写实,而是诗人的想象,也可能与阿姆斯特丹独特的地形地貌有关。阿姆斯特丹是一个沿海城市,河流向西流入大海,这与中国因地势西高东低而河流东流入海不同。中国人对东方有一种隐秘的崇拜心理,阿姆斯特丹的河流倒流意味着河流东流入海,投射在诗人的心理上,大概暗示诗人的家国皈依情结。说到底,这是文化心理使然,诗人骨子里是东方人的文化基因。诗人就这样处于彻夜的无眠之中,直到太阳升起来也没有用。黎明到来时,诗人静立窗边,一夜无眠,此时他还沉浸在对故国故家充满伤感的眷顾里。“镶满珍珠的太阳”是指黎明时太阳投射在河流里,水天一色,景致优美而宁静,反衬出诗人内心的孤寂和怅惘。
在第四节和第五节之间有一个跨行,把本该属于第四节最后一行的“也没有用”移到第五节第一行的显著位置,意在强调诗人彻夜无眠的孤悬状态。诗中接连出现三个“也没有用”,丝毫也不显得累赘,反倒是恰到好处的强化,把诗人身在异国的处境倾倒在一片乡愁的粘稠里。三个“也没有用”在位置的间隔和语气的关联上,既有情境上的延宕,也有情绪上的延展。读者可以想象这样的图景,诗人孤灯独坐,长夜漫漫,无论如何都无法抚平内心的刺痛。当黎明到来,诗人看到“鸽群像铁屑散落/没有男孩子的街道突然显得空阔”,眼前之景也是诗人此时心境的体现。把鸽群比作铁屑,一是形容鸽子之多,一是反衬出街道的空阔和宁静。“没有男孩子的街道”看起来有点突兀,实际上包含着时间的流逝所带来的伤感。在此,男孩子是童年的象征,大概也是诗人自我童年的投射。诗人曾经熟悉的那个男孩子在哪里呢?童年已经变得如故国故家一样渺远,这何尝不是一种彻骨的思乡之痛!
第六节又从现实切换到回忆之中,“秋雨过后/那爬满蜗牛的屋顶/——我的祖国”,这是我们多么熟悉的情景,既与上一节中的“鸽群像铁屑散落/没有男孩子的街道突然显得空阔”形成对照,也是对前面的“我家树上的桔子/在秋风中晃动”的呼应。在此,空间与情景转换在诗人的思绪中,现实与回忆交错闪回,诗人的乡愁在这种对照和呼应中显得更加真实感人。一场秋雨过后,屋顶上满是蜗牛,如此寻常的情景却是珍藏诗人心中的一个剪影,既具体入微,历历在目,又小中见大,别有深意,把祖国这一意象化虚为实,深情毕现。在此,蜗牛之小与祖国之大看起来完全不成对称,其中却包含着奇妙的张力,祖国的抽象性呈现为鲜活的意象性,蜗牛之小几乎包含着祖国之大的全部生动性,似乎看得见乡愁绵密而细小的触须。这是一位诗人深湛功力的体现,也是一个意象的精微之处。诗人把自己的情感凝练为一个恰当的意象,非得要有独到的发现才行。只有透过内在的灵视,诗人才能发现内心的隐秘契合于一个意象的鲜活性和有效性。诗中的蜗牛这个意象用得极好,不仅切合诗人此时此地的心境,而且具有动感。那是乡愁的蠕动,大概诗人的心中有一种温润的潮湿,又透着一丝凉沁。
诗的结尾“从阿姆斯特丹的河上,缓缓驶过……”,一个并不完整的句子独成一节,需要与上一节联系起来,才能得到完整的理解。在此,可以把“秋雨过后/那爬满蜗牛的屋顶”理解成“我的祖国”,也可以理解为“我的祖国”“从阿姆斯特丹的河上,缓缓驶过……”。这里,“我的祖国”同时起着粘连上、下句的作用,既是上一节的结束,也是下一节的开始。这是一种特殊的跨行排列,起着特殊的修辞作用。只有这样理解,才能排除阅读上的障碍。同时,这也是一种由粘连所形成的特殊的意象叠加,表达诗人瞬间情绪上的恍惚,“我的祖国”似乎从眼前的阿姆斯特丹河上,像一条船一样缓缓驶过。这里面包含着情绪上的含混、视觉上的迷蒙,既是幻觉性的,似乎又是诗人视野中的实景在情绪上所引起的波动,带给读者心灵上的颤栗。清晰中有迷蒙,含混中有确信,在确定与不确定之间,落在诗人心中的一切都在缓缓远去,全诗收束于诗人内心的远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