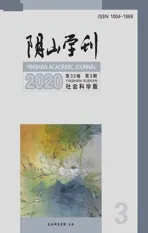革命语境下“晚年茅盾”文学创作中的现实主义追求
2020-02-20李燕英
李 燕 英
(中山大学 博雅学院,广东 珠海 510275)
茅盾的文学道路与现实主义紧密相关。纵观茅盾研究整体现状,对于现实主义主张的研究大多集中于1949年以前,而对于1949年以后的也多从理论层面入手,至于创作层面则有所忽略。商昌宝的《茅盾先生晚年》以1949年为临界点对茅盾晚年的思想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梳理,笔者沿用这一时间界定,以“晚年茅盾”代指1949年以后至茅盾去世这段时期,对年龄的考虑是一方面,更多的是为了论述的方便和行文的需要,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界定。与1949年以前相比,1949年以后茅盾的理论与创作的数量和质量都明显逊色不少,且将更多精力放在了理论研究上,创作方面只留下了100多首旧体诗和五万余字的《霜叶红似二月花》续写片段。《霜叶红似二月花》续稿在茅盾生前并未发表,死后很久才被家人发现,而且旧体诗创作中的很大部分也不是为了发表。与理论相比,“晚年茅盾”创作的绝大部分处于沉潜地下的状态,因而以此为出发点更能较为真实地透视出他这一时期的现实主义主张。鉴于“晚年茅盾”所处的革命时代语境和个人的革命经历,本文选择在革命语境中对“晚年茅盾”创作中体现出的现实主义主张进行研究。因“新时期”以后,茅盾精力和时间大不如前,理论和创作的数量都比较少,所以本文论述主要集中于1949年之后,“新时期”以前。
一、旧体诗词创作:从“新台阁体”回归现实主义
“晚年茅盾”的旧体诗词创作主要集中在1958—1964年和1971—1981年这两个时段。在建国以后的革命语境中,茅盾创作的旧体诗词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类:受时代影响的“新台阁体”、抒写个人情感和生命体验以及反思政治和历史。后两者较为明显反映出茅盾对现实主义的隐性呼唤,而那些受时代影响的“新台阁体”诗作则主要与革命规范下的现实主义主张存在契合之处。
(一)受时代影响的“新台阁体”诗词
1957年,茅盾曾在文章中表露过对于明代永乐至成化间盛行的台阁体的批判之意,他认为它其实是“一种平正典雅、不痛不痒、虚伪地歌功颂德、不敢触及现实的文风。”[1]这种文体(主要是诗体)具有“宫廷文学作风”,是一种反现实主义的诗潮或文学潮流。但1958年大跃进浪潮中,当茅盾建国后重提诗笔之时,他也有意无意地落入了台阁体的窠臼。茅盾的新台阁体诗词,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它们或歌颂或批判,或雅正平和,或义正词严,这是由诗人的政治身份所决定的,是诗人强烈的政治人格的艺术投射。[2]
身为文化部部长,茅盾必定会经常参与国内外的各种活动,题赠唱和自然也是在所难免。写于1958年的《观北昆剧院初演〈红霞〉》(二首)主要介绍《红霞》一剧的情节和人物,从“古为今用”等角度高度肯定了它的意义和价值,结尾两句的“哀丝豪竹颂英烈,此是北昆跃进花”[3]394更是染有鲜明的跃进气息,受到时代风潮的很大影响,其中透露的观点也契合了当时的官方主流。1959年,茅盾又先后写下了《一九五九年春节》《春节摸彩》等诗,跃进色调同样浓厚。他于1962年所作的《在海口观海南歌舞团演出》结尾两句这样写道:“庆丰收,于何有?归功于人民公社。”[3]417人民公社是时代的产物,为当时的官方正统所提倡,对当时的经济发展确实起到了一些作用,但其弊端却是显而易见的。茅盾站在官方立场,对其以歌颂为主,这其中既有社会原因,又有个人局限。
在与国外进行文化交流的过程进行的诗歌创作,也能较为明显地体现出茅盾“新台阁体”诗词中的“颂歌”意味,1960年2月创作的一首组诗《祝日本前进座建立三十周年(二首)》便是较为鲜明的反映。一首称赞剧团成立以来所取得的成绩,“继承发展翻新艺,卅载斗争步步前”;一首表达自己的良好祝愿,“曼舞浩歌张我道,曙光欲透海东隅。”[3]405这首组诗流露出作者内心的愉悦和对反帝斗争取得最终胜利的高度自信。茅盾在1960年9月左右出访波兰时写下的《参观凯纳尔工艺美术中学》《访玛佐夫舍歌舞团》等风格与此类似,大多都是抒发对所写对象的赞美之情,语言通俗易懂,以叙述为主,带有典型的“颂诗”风格。
除了歌颂以外,茅盾的这部分旧体诗词还有对当时国际上的“修正主义”思潮的讽刺和批判。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关系严重恶化,茅盾先后写下《壬寅仲冬感事》《感事为凤子作》《感事为赵寻作》《阅报偶赋二律》等诗篇表达对苏联所作所为的愤懑和不满。与上述诗篇直接表露不同,茅盾在《为徐平羽之新出土秦汉瓦当拓本作》则“借古鉴今”,通过新出土的秦汉瓦当发表个人看法,认为国际上的反华逆流不过“爝火”,根本无法掩盖马列主义的光辉。不管是直接讽刺,还是间接写之,茅盾都对现实保持了强烈的关注,目光始终不离国内外的政治形势,在抒发自己豪情的过程中较为明显地契合了官方的主流价值观念。
(二)抒写个人情感和生命体验的诗词
“晚年茅盾”在旧体诗词中安放了不少真我情感,总体来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深沉热烈的爱国情、魂牵梦绕的故乡情、真挚感人的亲友情……它们安放了茅盾真实和自由的灵魂,为人们展现了他官员和学者以外平凡化、生活化的一面。
一直心系国家命运的茅盾,写下了不少表达爱国情怀的诗篇。在国庆三十周年之际,茅盾喜不自胜,写下了《国庆三十周年献词》,对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尤其是粉碎“四人帮”以来所取得的成就进行热情洋溢的歌颂和赞美。而在《沁园春·为〈西湖揽胜〉作》中,茅盾以“千秋业,党英明领导,赢得大同”[3]523为诗词作结,并在其中寄寓了自己对党的深情。
长期离家在外不能常回归故里的茅盾,始终怀着对于故乡的深深牵挂。《西江月·故乡新貌》《一剪梅》《沁园春·为〈西湖揽胜〉作》《桂枝香·咏时事》等十余首诗作都很好地体现了茅盾对于故乡的深深眷恋。以应故乡来人要求而作的《西江月·故乡新貌》为例。听说故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茅盾难掩欣喜之情,“祖国红花开遍,故乡喜沾余妍”。[3]519希望故乡在遭遇“霜冻百卉”之后能够“天青雨过”,又见“千红万紫”,茅盾对故乡的深深眷恋,在旧体诗词当中得到了很好的表达。
经历风风雨雨和众多知名人士都有着深情厚谊的茅盾,在旧体诗词中同样留下了不少感人篇章。对于同辈和战友,他真诚以待,对于后辈,则以劝勉激励为主。《寿瑜清表弟》《菩萨蛮·奉答圣陶尊兄》《赠赵明》《赠曹禺》《丹江行——为碧野兄六十寿作》《奉和雪垠兄》《赠丁聪》……这些朴实无华的诗词传递出的是茅盾对于友人的真挚情怀。但是茅盾的这些诗作中的部分不仅仅是论述个人情感,而是将之与政治和社会相关联。像《寿瑜清表弟》《赠赵明》《丹江行——为碧野兄六十寿作》《清谷行》这些诗作,虽说是出于个人情谊而作,但却能把个人经历放在宏大历史叙事中予以观照,做到了个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
儿时丧父的茅盾对母亲怀有别样的情愫,这在他的《七律》体现得尤为明显。《七律》是茅盾在“文革”期间写下的第一首旧体诗词,在此之前,他卸任了文化部部长,成为了“靠边站”群体中的一员,创作之笔也沉默了六七年,又经历了丧妻等一系列变故。诗的全文如下:“乡党群称女丈夫,含辛茹苦抚双雏。力排众议遵遗嘱,敢犯家规走险途。午夜短檠忧国是,秋风落叶哭黄垆。平生意气多自许,不教儿曹作陋儒。”[3]437诗中流露的尽是茅盾对母亲的赞美和思念,颔联两句更是情深意挚,催人泪下。母亲“大节贵不亏,小德许出入”的生活准则始终在无形中影响着茅盾,他在《八十自述》这首诗中描摹了儿时与母亲有关的生活细节,再次表达了对母亲教诲的感谢之情。虽只有区区两首纪念母亲的词作,但读来却勾人魂魄,句句戳心,令人深思。
(三)反思政治和历史的诗篇
作为对社会现实有着较为深刻体认的文艺工作者,茅盾的创作不可能离开当时的政治和历史。除了在旧体诗词当中安放个人情感,“晚年茅盾”还在此寄寓他对当时政治和历史的反思。将这些反思政治和历史的诗篇放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进行考察,人们便会更加容易发现它的难能可贵。
1959年前后,历史剧成为文学界讨论的热门话题,置身其中的茅盾不仅洋洋洒洒写下十万余字关于历史剧的评论文章,还在旧体诗中表达了自己的观点。1959年,茅盾写下《观剧偶成》,对改编的《赤壁之战》发表意见。“千秋功罪正难论,乱世奸雄治世臣。我喜曹瞒能本色,差胜沽名钓誉人。”[3]403茅盾建议还原曹操真实面目,不主张站在现代人的立场上对其进行改编。曹操的本色性格和艺术魅力才是人们应予以重视的,这体现出茅盾对于艺术规律的尊重。田汉改编的《西厢记》上演之后,茅盾同样以诗的形式对其进行点评,“崔娘遗恨留千古,翻案文章未易工。”[3]413茅盾不主张更改元稹剧作中崔莺莺和张生的悲剧结尾,这也就在侧面否定了田汉“光明的尾巴”所体现出的新公式主义。在否定“田西厢”后,茅盾又对石鹤龄改编的《西厢记》加以肯定,认为它虽然以喜剧结尾,但却具有鲜明的“五四启蒙特色”。从这三篇“诗的评论”的文章中,人们就会发现茅盾的不随流俗和对于艺术规律的尊重。
大跃进带来的种种问题,茅盾可能有所察觉,由于种种原因并未直言,人们只能在他的某些诗词中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在《题动画片〈小蝌蚪找妈妈〉》中,茅盾在对动画片进行高度评价的同时,还由物及人,发表见解,认为现实生活中像小蝌蚪这样好心办坏事的人大有人在,我们不要抱着一味取笑的态度。联系当时国民经济困难的社会现实,这样的表述明显带有对现实的反思和感悟。
沉默长达六年的茅盾在“文革”后期同样写下了不少反思政治和历史的诗篇,虽然很多在当时并未发表,但它们同样折射出茅盾的思想和观念。周总理批判林彪极左思潮,江青一伙却横加阻挠,听闻此事的茅盾写下《偶成》,表达了对于“四人帮”所作所为的厌恶之情。像这样对“四人帮”之流进行揶揄讽刺的诗篇还有不少,比如《读〈稼轩集〉》《无题》《读〈临川集〉》……《读〈稼轩集〉》是其中写得非常好的一篇。“浮沉湖海词千首,老去牢骚岂偶然。漫忆纵横穿敌垒,剧怜容与过江船。美芹荩谋空传世,京口壮猷仅匝年。扰扰鱼虾豪杰尽,放翁同甫共婵娟。”[3]424面对南宋末年的黑暗现实,曾纵横驰骋疆场的辛弃疾心思郁结,满腹牢骚,但好在有陆游和陈亮这样的同道中人能为其提供心灵的慰藉。“醉翁之意不在酒”,茅盾所作的这首诗明显夹杂着他对于“文革”现实的不满之情,也鼓舞和激励了当时文化界的各位战友。黎丁在《读茅公遗墨》中就表达了这首诗对于当时爱国文化工作者的鼓舞之情。在《读〈临川集〉》中,茅盾表面上借“呜呼真龙未窥相公庭,伪凤翱翔逞诡谲”[3]448写王安石遭受保守派攻击、“左右无良弼”的艰难处境,其实是借此讽喻现实,表达己意。“批林批孔”运动的矛头直指周恩来总理,当时的中国局面岌岌可危,茅盾在写王安石艰难处境的同时也流露出了对于时局的忧虑之情。
二、小说创作:疏离时代的现实反思
以《子夜》等小说闻名于世的茅盾在1949年之后鲜有小说问世,只为后世留下了五万余字的《霜叶红似二月花》续写片段。续稿的出版对于人们了解“晚年茅盾”的文学思想,尤其是其现实主义主张,有着较为重要的意义。
(一)续写《霜叶红似二月花》的心理动因
《霜叶红似二月花》写于抗战时期的1943年,由于各种原因,茅盾只能将未完成之作先行出版。这部小说在出版之后广受好评,让人不可思议的是,1949年之后却很少有人提及,但茅盾却对此念念不忘。新中国建立之初,茅盾不愿担任很多人都“虎视眈眈”的文化部部长一职,只想和妻子孔德沚一起定居西湖,完成未竟的小说创作,这些未竟之作中就有《霜叶红似二月花》。尽管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接受了文化部部长的任命,茅盾却总是在忙碌的夹缝中寻找各种机会进行小说创作。应公安部之邀而写的一个电影剧本也被认为是过于像小说,就连他晚年创作的旧体诗也保留着浓厚的小说痕迹。茅盾为报刊而写的诗词以及那些题赠友人的作品带有小说创作方面的鲜明印痕,或用叙事笔法进行宏观评价,或不自觉地突出人物的生平事迹。
虽然旧体诗词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茅盾无法进行小说创作的遗憾,能为其提供心灵的慰藉,可在他心中,也许小说才是“正途”。小说这种在古代被称之为“稗官野史”、不被重视的叙事文类,在现当代具有了正史的意味,并逐渐被官方化、政治化。旧体诗词在当时不被接受,而小说却被广泛认可,茅盾对小说的留恋在某种程度上显示其向官方靠拢的一面。
1974年,姚雪垠恢复和茅盾的通信往来,并将他写作的《李自成》寄给茅盾,茅盾不仅耐心提出意见,甚至于有时还不由自主地替其写作一些片段,这都透露出此时的茅盾对于小说创作的渴望。大约也就是在此时,听从儿子韦韬的建议,茅盾开始重新考虑心念已久的小说创作问题。当时的茅盾已经78岁高龄,加上长期疾病缠身,精力和时间都极为有限,重新开始新的小说创作显然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经过一番思量,茅盾将目标定位在了未完成的小说创作上。考虑到其它未完成的小说结尾勉强能“圆场”,《霜叶红似二月花》在当时很受欢迎的情况,茅盾决定续写《霜叶红似二月花》。
另外,续写这部小说还与当时的时代语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九一三”事件之后,政治形势渐趋好转,可“四人帮”发动“批林批孔”运动,他们的作威作福又使得全国局势一片紧张,茅盾在《读〈临川集〉》中就表达过对时局的忧虑之情。在此情况下,续写不与时代过分牵连的《霜叶红似二月花》是一个相对保险和比较明智的选择。
有研究者指出,茅盾续写《霜叶红似二月花》有对母亲陈爱珠的思念在其中,这样的看法应该与茅盾在续稿中凸显婉卿这个人物形象有关。虽没有材料加以佐证,但也不妨将其作为创作动因之一。茅盾母亲陈爱珠像婉卿一样聪明能干,对他的人生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茅盾虽没有多次撰文纪念母亲,可在面临政治困境、意志消沉到极点的情况下写作的《七律》和《八十自述》流露出的深情读来让人无比动容。文学创作本就是人们寄托情感的一种方式,茅盾借续写《霜叶红似二月花》寄托对于亲人的深深眷恋,这也完全可以理解。
在各种创作动因的驱使之下,“晚年茅盾”重拿创作之笔,开始进行《霜叶红似二月花》的续写工作。令人惋惜的是,由于搬家的影响,茅盾无法投入专门的精力进行小说创作,加上想要进行回忆录的撰写工作,续写工作被迫中断。虽然只留下了五万余字的大纲片段,但人们还是能为一睹茅盾晚年的创作风采而深感荣幸。
(二)人物形象改变中折射的政治与文化反思
按照之前的写作意图,茅盾应该会在续稿中塑造一些在大革命失败之前和之后假左派的人物形象。可在续稿片段中,人们却发现他在之前小说人物形象的基础上,或突出,或淡化,或改变,表现出对于当时政治和文化的反思。
之前的钱良材不仅可以牺牲自己的利益而为农民着想,带领乡党筑堤防水,还能担负起养育女儿继芳的责任和义务。在续写片段中,钱良材的形象得到进一步深化,他不仅帮助农民参与实际的革命斗争,还和女国民党张今觉一起刺杀谋害她丈夫的仇人。在1949年以后的革命语境中,地主经常作为农民的欺压者而存在。但茅盾却塑造这样一个肯为农民着想、乐善好施的正面青年地主形象。虽没有延续之前的写作意图写其在风云激荡的革命斗争中的表现,可从日常行为出发描摹革命的做法仍旧让人印象深刻。
婉卿是续写中最为着力突出的人物形象。之前,茅盾也借助他人之口和婉卿本人的言行举止交代了她的聪慧能干,但这仅限于对内一面。续写中,茅盾将之塑造成为了一个“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女强人形象。对内,帮助丈夫戒烟,和丈夫柔情蜜意,在变卖房产一事上处理果决,把家庭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对外,为北伐军入城出谋划策,巧妙布局帮助苦命女子琴仙脱离苦海,在张今觉复仇遇到困难的时候为其四处奔走。对内,对外,婉卿都做得极为得体,足不出户却尽知外界一切事情,她的能干为人称颂,以致于在当地形成了一个“拥婉派”。为了弥补婉卿无子的缺憾,茅盾甚至安排了和光“性无能”的痊愈,使得他们的夫妻生活能够像他人一样正常,并成就了他们儿女双全的幸福生活。
除此之外,茅盾在续稿中塑造出了张今觉这个敢爱敢恨的女国民党形象。张今觉聪慧美丽,知书达理,协助丈夫处理一些事务,在丈夫严主任被刺杀之后,更是和钱良材一起为夫报仇。在此之前,茅盾主要塑造了两类女性人物形象,一类是像慧女士、孙舞阳、章秋柳这样的“时代女性”,另一类是像静女士、方太太这样的“传统女性”。婉卿和张今觉是“晚年茅盾”在女性人物方面的新创造。
张今觉的丈夫严主任同样是“晚年茅盾”对人物形象塑造的一大贡献。由于只是大纲片段,茅盾的着墨并不多,然而却塑造出了一个正义无畏的国民党军官形象。茅盾对于张今觉和严主任这对夫妇形象的塑造充分地体现了他摒弃党派之争的可贵见识。当时的时代语境要保证的是革命的合理性,对于敌对力量国民党的形象大都是以丑化为主,甚至于站在阶级对立的立场上对其进行夸张的描摹。可茅盾却能出离其中,塑造了一位正面的国民党军官形象,并对其加以肯定,光是这份见识就足以令人们心生敬佩。
当然,除了以上提到的在续稿中改变较大的人物形象外,与之前相比,茅盾还着力强调了王民治和冯秋芳这对夫妇,对其婚礼情形也着墨不少,但却对之前塑造的王伯申和赵守义两个反面人物形象着墨很少,这应该与其淡化阶级斗争有关。
(三)立足私人家史展开日常生活叙事
按照之前的写作意图,茅盾将描摹从“五四”到大革命这段风云历史。小说中的前十四章只涉及了“五四”这一段,尽管如此,人们还是能看到阶级斗争的身影和宏大叙事的可能。赵守义是封建地主的代表,王伯申是资产阶级地主的代表,这两人之间的争斗是那个时代两个阶级不同思想倾向的缩影和见证。然而续写片段却更多聚焦于日常生活琐事,并对其中的细节用尽笔墨。
续稿一开始,茅盾就叙述黄和光的戒烟,对于中药的描写特别详尽。“朱懂中医,为配合‘枪上戒’药膏,中有附子、当归、党参、沙参、甘草等,与鸦片烟膏有一定比例,十日递减。又:食谱为燕窝、鱼翅、海参、鸡、鸭、鱼等,早上参汤。”[4]如此详尽的描写,我们还能寻得好几处,这倒是让人们想起了茅盾的家世。据茅盾回忆录记载,他的外祖父是一个闻名乡里的中医,茅盾的父亲也随之学医,有此环境,耳濡目染,茅盾描摹的详尽便自在情理之中。儿女情长的场景在续写中也出现不少,婉卿夫妇和钱良材灯下共酌,吟诗作对,类似的描写在小说中处处可见。和光打趣婉卿和亲自为其宽衣解带的场景所显露出的柔情蜜意羡煞旁人,这在之前也曾出现,只不过次数较少,没有像续写中那么频繁。重阳前夕,良材来张府拜节,看到婉卿和巧儿的光彩照人的打扮,不由得一时失神。小说中对两人尤其是婉卿的服饰的描写极为讲究,叙述得也特别到位,细致描摹、不厌其烦,扎实的细节描摹功夫让人们看到了茅盾创作旺盛时的风采。
日常生活与小说的生活并不存在对应关系,人们也不能拿两者进行对比,但小说中的描写是作者日常生活的部分折射却是被众多文学研究者所承认的。茅盾出生于一个庞大的家族,生活也还算富裕,儿时地主小姐的生活场景应该会经常出现在他的生活当中,这样的细节展现似乎是对私人家史的某种回应。建国以后的革命语境强调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尤为重视宏大题材和阶级斗争,而对于日常生活叙事则持一种不太赞成的态度,茹志鹃的《百合花》面世后的遭遇就很能说明问题。立足私人家史展开日常生活叙事,这体现出茅盾对于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的尊重。
三、“晚年茅盾”创作中的现实主义追求
“晚年茅盾”生活的年代被继续革命的氛围所笼罩,它一方面确保政权的巩固与统一,另一方面则为当时的人们提供了幸福的承诺和关于未来的美好设想,从而保证他们能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参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必然在其中发挥巨大作用。建国以后的革命文化语境依靠强大的政权力量和革命话语权威,使得以意识形态为诉求旨归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对文坛施加着强而有力的影响,在“文革”期间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对阶级性、倾向性给予了更多的关注,特别强调阶级立场以及世界观对现实主义这一创作方法的主导作用。以胡风、秦兆阳等为代表的学者通过不同的途径对被过分扭曲的现实主义主张进行反抗,更愿意强调文学本身,较为关注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不主张过分强调文学的政治功用。建国以后的茅盾虽也受到革命话语的影响,没有直接反抗,但也以自己的努力呼唤心目中的现实主义。
“晚年茅盾”曾为阶级斗争和人民立场高唱赞歌,对社会、经济等客观世界给以了足够的强调,而这也都在他的旧体诗创作和小说续写中得到了较为鲜明的反映。“晚年茅盾”创作了不少受时代影响的“新台阁体”诗词,有的是应他人之邀而写,有的离不开他以官员身份出访的各种活动,而有的则和当时的文艺论争有关。这些诗词与当时的社会现实有着较大的关联。“大跃进”“人民公社”“文革”“反修”……这些带有鲜明时代痕迹的词语在茅盾的旧体诗词中经常出现,就较为直接地反映出他对于社会实际的重视。这些“新台阁体”诗词以歌颂为主,还有部分诗词侧重讽刺或者批判,不仅契合了当时的官方主流,也是茅盾政治人格的投射。总而言之,这部分诗作渗透着浓烈的革命理想情结,与革命规范下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主张存在某种程度的契合。由此可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提倡影响的不仅仅是主流层面的新文学,作为传统文学样式的旧体诗词同样会受其影响。
在反思政治和历史的诗篇中,茅盾企图借助对古人古事的评论发表对现实的见解和看法。所有的反思都没有离开当时的社会现实,出发点也都是想有利于当时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小说续稿在疏离时代中反思现实,同样与当时的社会实际有较为密切的联系,也表现出茅盾对于革命传统的维护。茅盾这一时期的创作体现出他从未舍弃过革命,与当时的官方主流存在某种程度的契合。对革命的认同随之而来的是他对于革命规范下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主张的某种认同或迎合,以上提到的对于社会客观实际的强调都与此有关。
“晚年茅盾”身处的革命语境和官员身份对他这一时期的现实主张产生较大的影响。因为“党外布尔什维克”的政治声誉和之前的文坛威望,晚年的茅盾被政府委以重任,成为了共和国的第一位文化部部长,这样的身份使得他成为“一体化”体制的一部分,并尽职尽责地服务于当时的官方文艺政策,由此出发进行的创作表明了他的观点与革命规范下的现实主义主张的契合之处。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历史的产物,它的推行决不仅仅是官方提倡的结果,也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了当时人们的思想观念和心理期待。身处其中的茅盾创作当中体现出的与官方提倡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主张的契合,与他的革命经历密不可分。作为较早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之一,青年时期的茅盾参与了不少革命活动,后来虽因为种种原因脱离党组织,但他的理论和创作却从未与革命有所脱离,众所周知的《子夜》在当时产生的轰动效应就与当时的革命现实有着极大的关联。为革命事业奋斗一生的茅盾自然希望人们以高度的热情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这符合当时全国人民的心理期待,也折射出一个文艺老兵的炽热情怀。“晚年茅盾”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某种程度的接纳不仅仅是对官方正统的迎合,更与其革命经历有着莫大的关联。
从对“晚年茅盾”创作的分析中还可看出他对于自身情感和艺术规律的尊重。在抒发个人情感和生命体验的诗篇中,官方主张的工农兵人物形象没有太多出现,反而出现了不少被作为打压对象的知识分子以及平凡普通的“小人物”,比如瑜清表弟、赵明、碧野、赵清阁……这些人物的一言一行浓缩在了简短的旧体诗作当中,他们的革命经历和平凡人生同样成为了被赞美的对象。爱国情、故乡情、亲友情,这些私人化的情感在茅盾的这部分旧体诗词中得到了很好的展现。这些情感因为与日常生活和个人经历紧密关联而显得愈加真实。除了真情实感的流露之外,茅盾还在这些诗作中不刻意回避重大题材,善于将个人经历放置于宏观社会予以审视,这似乎是对于革命规范下的现实主义的某种背离。旧体诗词因为它的不引人注意而囊括了官方社会意识形态所不能容纳的东西,从这个角度来看,旧体诗词于新文学的建设还是有一定功劳的。
由于当时社会环境的限制,茅盾不能随心所欲,可他思考的脚步从未停止,他在以自己的方式反思现实和政治。那些反思当时社会现实和历史的诗作因为掺杂着茅盾的切身体验而显得更为真实可信。因为真情实感的流露,茅盾的这部分诗词更加贴近人性的真实,审美意义自然而然地显露了出来。
小说续写动因中虽然有其它成分在其中,但更多的是为自身情感体验所驱使。在人物形象的改变中,茅盾除了着力突出婉卿和钱良材这两个人物形象以外,还借张今觉和其丈夫严主任两个人物形象表明其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某种思考。除了延续宏观叙事的风格之外,还着意强调日常生活叙事,这和人物形象改变一样表明了茅盾对于艺术创作规律的尊重。
小说续稿对于日常生活叙事的强调,旧体诗词流露出的真实而又平凡的生活细节,尊重文学特性和艺术规律,这都反映出茅盾对现实主义的隐性呼唤。他呼唤的现实主义带有19世纪欧洲现实主义的鲜明印痕,继承了“五四”现实主义传统,考虑到文学自身的特性,重视个人生命体验,与胡风等人主张的现实主义有相似之处。
由此可见,“晚年茅盾”的创作中不仅有与革命规范下的现实主义相一致的地方,还有与它不一致之处,这种矛盾和冲突和当时的革命语境有着很大的关联,也与茅盾的生平经历和个人选择密不可分。“晚年茅盾”不仅仅有官员的身份,还是一个文艺工作者和独立的个体,有着自己对于文艺的见解和看法以及较为私人化的情感,以上提到的对于文学和艺术规律的尊重便是很好的体现。“晚年茅盾”通过旧体诗词创作,尤其是对历史剧的评论来表达文学见解以及在隐性层面进行创作的做法,是一种审时度势较为明智的选择。从个人情感体验出发进行的创作表明了茅盾对于文学和艺术规律的尊重,显示出他对现实主义的隐性呼唤,这在当时的革命语境中显得难能可贵,也与如今提倡的文学观念存在契合之处,同样能为今天的文学发展提供某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但同时,人们也不能忘记,时过境迁,不能仅仅停留在历史语境中的分析,更应着眼现在,理性分析晚年茅盾的现实主义主张。不过分关注,也不过分忽视,理智看待、冷静分析,是较为正确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