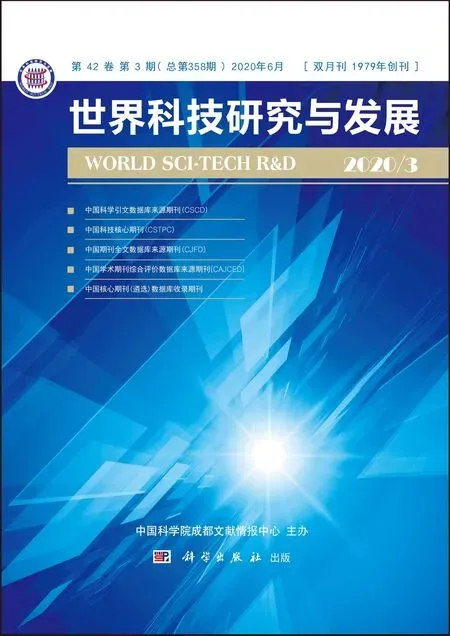日本生物安全战略规划与法律法规体系简析*
2020-02-17张志强
陈 方 张志强
(中国科学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成都610041)
生物安全问题关系到国家稳定、公共健康和社会福祉。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国际经济贸易形成了高度全球化的发展局面。伴随着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和生物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人类社会在生物安全领域面临的挑战逐渐凸显。新发突发传染病、高致病性病原体管理、生物技术安全管理以及生物武器防御等问题成为跨越科技、经济、安保、公共卫生和社会治理等多个领域的全球性挑战。
日本作为亚洲太平洋地区的重要发达国家,拥有较强的科技实力和工业基础,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三位,近年仅次于美国和中国。日本在微生物学、细菌学和预防医学等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早,20世纪初,生物学家野口英世就在蛇毒、梅毒等病原学研究方面获得重大发现;二战时期,日本侵略者将“细菌方法作战”作为新式武器,在中国领土上犯下惨无人道的罪行,违背医学伦理开展了大量关于鼠疫、霍乱、伤寒等病菌的人体实验;进入21世纪,日本将生物技术视为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影响重大的战略新兴技术,在生理学或医学领域取得了多项诺贝尔奖级别的研究成果;近年来,日本在人工智能、机器人和数字技术等方面逐渐形成领先优势,推动生物技术在医药、材料、能源和制造等应用领域迅速发展。
日本对广义生物安全领域课题的关注由来已久,较早与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和美国等发达国家接轨互动,逐渐发展形成了战略规划与法律法规体系。本文对日本生物安全战略规划体系和法律法规体系的要点进行了梳理分析,重点介绍了日本在传染病防控、病原体等安全管理、生物技术安全管理和生物武器防御方面的法律、规章和指导政策等,并提出了启示与建议。
1 日本生物安全战略规划体系特点
1.1 多灾害现实条件造就特有的忧患和灾害防备意识
日本位于亚欧大陆东部、太平洋西北部,领土由北海道、本州、四国、九州四大岛及7200多个小岛组成,是一个自然灾害频繁的国家。日本四面环海,太平洋上的热带气旋经常经过日本,导致台风灾害。日本群岛地处位于亚欧板块和太平洋板块的消亡边界,即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火山、地震、海啸活动频繁。多灾多难的客观环境与条件,使得日本从政府到民间都锻炼出较强的忧患意识和防灾能力,并逐渐发展出世界先进的灾害预警、信息发布、应急响应和灾后复兴系统。同时,日本高度重视全民防灾演习,除了针对台风、地震等自然灾害之外,还对火灾、航空船舶意外、剧毒等事故做出了应对措施安排。
日本在传染病预防方面起步较早,在1890年制定了《传染病预防法》,其后在20世纪50年代颁布了《传染病法》和《检疫法》。然而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生物安全的概念在日本研究界仍未普及,也没有建立专门开展生物安全实验的现代化设施。日本对于生物安全问题的关注起始于70年代拉萨热病毒在西非地区的流行以及重组DNA研究的兴起和迅速发展。1976年,国立预防卫生研究所(国立传染病研究所的前身)开始研究病原体等的安全管理体系,于1981年制定和执行《国立预防卫生研究所病原体等安全管理条例》;日本生物危害委员会则于1984年总结并公布了《日本生物危害防止指南》。
其后,以埃博拉和艾滋病病毒等致命性病毒引起的急性和难治性传染病、肠道出血性大肠杆菌O-157引起的集体腹泻症、超级致病菌MRSA(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引起的院内感染、被认为与幽门螺杆菌有关的胃溃疡和胃癌等多种细菌性疾病的出现,以及疯牛病病毒引起的动物疫病和潜在生物恐怖主义威胁等,促使日本多个政府部门、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逐渐加强重视生物安全问题,将生物安全风险视为应慎重防备的灾害。
1.2 生物技术产业立国政策推动生物科技的长足发展
日本拥有相对较为丰富的森林资源和渔业资源,但工业原料资源十分缺乏。除煤炭、天然气、硫磺等极少量矿产资源外,其他工业生产所需的主要原料、燃料等都依赖海外进口。20世纪80年代,日本确立了“技术立国”战略,提出将生物产业培育成与信息产业并列的21世纪的国家战略产业。1999年,日本科学技术厅、文部科学省、厚生劳动省、农林水产省、通商产业省等5个部门提出了“开创生物技术产业的基本方针”。其后,日本于2002年发布《生物技术战略大纲》[1],提出生物技术产业立国的战略部署,2008年推出《促进生物技术创新根本性强化措施》,不断强化政府预算,联合产业振兴中心、基金会、协会、联盟等团体,振兴生物技术研发和产业化活动,逐渐在精细化学品、发酵技术、生物制造、育种技术、机器人、再生医疗与免疫等生命科学领域形成了国际竞争力。2019年 6月,日本发布《生物战略2019》[2],展望“到 2030年建成世界最先进的生物经济社会”,提出加强国际战略,并重视相关的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
为了保障生物技术安全,日本颁布了《重组DNA实验指南》《转基因生物工业化指南》。为提高国民对新技术的理解和对新产品市场的接受度,日本政府重视加强合作,注重生物技术领域特别是食品生物技术领域的安全性评估和审查,颁布了《农林渔业及食品工业应用重组DNA指南》和《转基因食品管理指南》,在科学技术会议上通过了“关于人类基因组研究的基本原则”等。
在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管理方面,日本早期建设了200多家生物安全3级(Biological Safety Levels3,BSL-3)实验室设施[3],目前全国共有 17个支持危险病原体封闭实验的3级实验室设施[4]。正在运转的4级实验室(BSL-4)设施有2处,其一位于东京都武藏村山市的国立传染病研究所村山厅舍,该实验室于1981年建成,但直到2014年埃博拉病毒在西非地区传染扩散后,才于2015年8月宣布正式启用;其二位于茨城县筑波市的理化学研究所筑波研究所,于1984年建立。此外,正在建设的长崎大学4级生物安全实验室设在长崎县坂本第一大道,将作为东京大学、长崎大学、大阪大学、庆应义塾大学、北海道大学等9所大学的传染病共同研究中心,并可作为政府指定传染病的全国性研究开放设施。
1.3 新世代难题挑战促使全面思考生物安全战略布局
日本国土面积狭小、人口分布地区差异大,加之老龄化程度高、城市人口集中化等实际情况,给日本的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带来较大压力。同时,日本所处的地缘政治环境历来脆弱,再加上近年来与周边邻国在岛屿问题上关系紧张,使得日本不得不重新审视各类外来威胁的风险。
面对新的生物安全形势带来的挑战,日本意识到自身尚未建立完善的生物安全危机应对系统,各个相关机构和部分仍处于单独应对的状态,还存在生物安全的应对策略不足、管理体制不成熟、技术研究落后和国际化水平不高等问题[5]。为此,日本建立了以内阁官房为中心的协调机制,文部科学省、厚生劳动省、经济产业省、环境省以及外务省、防卫省等中央政府部门分工、联合发挥关键作用,海关、警察厅等事务部门与公共卫生机构等配合开展具体工作,通过《国民保护法》《传染病法》《新型流感等对策特别措施法》等,调动多机构合作应对。2001年,日本建立了生物安全学会 (Japanese Biological Safety Association,JBSA),作为日本在生物安全领域具有带头作用的学术组织,推进生物安全相关的学术研究和知识普及,为生物安全的提高和发展作出贡献。
自2015年起,日本文部科学省拨付特别领域研究补助金资助开展“全球传染病等生物威胁的新冲突领域研究”项目,由国立保健医疗科学院健康危机管理研究部高级主任斋藤智也担任负责人,参与单位包括防卫医科大学、东京工业大学、国立传染病研究所、防卫研究所等,致力于形成一体化的政策建议,针对全球生物威胁提出国际共享与外交纷争的解决方案。项目研究认为生物安全的概念包括传染病、公共卫生和安全保障三个重要方面,重点关注生物安全发展现状与全球治理、生物安全与病原体管理、合成生物学与基因工程的生物安全,以及两用生物技术的生物安全研究与教育等。2016年至2019年期间,该项目组织了6次生物安全研讨会,每次研讨会均会邀请20~30位来自行政部门、公共卫生部门、民间研究机构的管理人员,以及企业和大学的研究人员参与研讨。此外,项目还在2018年9月协调组织了公共卫生、市政危机管理、消防、警察等部门开展了应对突发生物恐怖袭击的桌面推演。
2 日本生物安全法律法规体系框架
2.1 传染病防控
做好传染病防控是日本生物安全法律框架体系的首要考虑。在传染病防控方面,日本制定有《传染病法》《检疫法》《新型流感等对策特别措施法》等法律。在动植物检疫及疫病防控方面,日本制定有《植物防疫法》《家畜传染病预防法》等法律。
2.1.1 《传染病法》
在《传染病预防法》的基础上,为了应对传染病发展情况的剧烈变化,日本从1999年4月1日起实施《传染病法》[6],采取了预防传染病的各种措施,以及协调对患者人权关怀的传染病对策。为了应对2002年11月至次年7月初以东亚为中心向世界各国蔓延的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SARS)等海外传染病的暴发和扩散形势的发展,以及适应人力与物资的迅速灵活转移、保健医疗环境的变化,2003年10月对《传染病法》做出了首次修订;其后再与《结核预防法》等整合修订,于2007年6月1日起正式施行。
为防备高致病性禽流感(H5N1)的感染扩大状况和新型流感发生时的蔓延,日本在2008年5月对《传染病法》做出了修订。《传染病法》根据症状的严重程度和病原体的传染性等将传染病分为5类传染病和指定传染病、7类新传染病,根据传染病的种类不同,医疗机构的处理方法也不同。2012年开始的中东呼吸道综合征(MERS)以及2013年以后确认为人感染的H7N9型禽流感疫情发生后,《传染病法》再次修订,将它们指定为与H5N1流感同等的乙类传染病。
2.1.2 《检疫法》
1951年6月,为执行《国际卫生条例》,日本制定了《检疫法》[7],目的是为了防止在日本以外地方流行的传染病病原体通过船只或飞机进入该国,并采取有关船只或飞机的其他必要措施以预防传染病。随着国际传染病形势的变化和现代交通的快速发展,《检疫法》经历了数次修订,上一次修订于2008年完成。
2019年底暴发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COVID-19,以下简称新冠肺炎)疫情在日本蔓延后,日本内阁于2020年1月28日通过了政令,根据日本《传染病法》和《检疫法》,将新冠肺炎列为“指定传染病”和“检疫传染病”。被列为指定传染病后,日本各都道府县的知事有权劝导新冠肺炎患者其前往符合条件的医院接受住院治疗,如果患者不听从劝阻可强制其住院,医疗费用由国家负担。被列为检疫传染病后,检疫部门可以在机场或码头等检疫关口要求新冠肺炎疑似患者依据法律接受检查以及诊治。
2.1.3 《新型流感等对策特别措施法》
鉴于2009年新型甲型H1N1流感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的流行,日本于2012年4月制定了《新型流感等对策特别措施法》[8],规定了防止病毒入境、储备疫苗、禁止使用人员集中场所等措施。该法旨在通过法律手段强化对新型流行性感冒等传染病的对策,保护国民的生命健康并将对生活及经济的影响减至最小。
2020年3月13日,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表决通过《新型流感等对策特别措施法》修正案,在2013年实施的法案基础上增加了新冠肺炎相关内容。此修正案通过后,日本首相可根据疫情随时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各都道府县知事可要求民众避免外出、学校停课、限制使用娱乐设施等。随着疫情变化,4月7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对7个都道府县发布了日本史上首个紧急事态宣言,积极采取措施开展疫情防控,5月16日扩大至所有都道府县,直至5月25日完全解除紧急状态,进入全面经济恢复和第二波疫情防备阶段。
2.1.4 动植物防疫法
日本农林水产省的消费安全局负责家畜防疫、动物检疫、植物检疫等相关工作。1950年5月,日本制定颁布了《植物防疫法》,旨在对进出口植物及国内植物进行检疫、驱除植物上附着的有害动植物、防止有害动植物蔓延,促进与保证农业生产的安全,该法律最近一次更新是在2015年。1951年,日本制定颁布了《家畜传染病预防法》,其目的是通过预防发生和防止蔓延家畜传染性疾病来振兴畜产,该法律刚刚在2020年完成了第8次修订。
2.2 病原体等安全管理
日本的生物安全管理法规体系中,将“病原体等”定义为病毒、细菌、真菌、寄生虫、朊病毒以及微生物产生的毒素,将其视为危害人体健康的主要因素之一。国立传染病研究所制定了基于生物安全理念的病原体安全管理条例,努力防止病原体和毒素的非故意暴露或泄漏事故。日本公共机构制定的关于病原体等安全管理的法规包括1981年启动制定的《国立传染病研究所病原体安全管理条例》、1993年制定的《家畜卫生试验场微生物等处理规程》、1998年制定的《大学等研究用微生物安全管理手册》,以及2000年制定实施的《生物制剂等制造厂的生物安全相关问题指南》等。
在学术团体方面,日本细菌学会在1984年《日本生物危害防止指南》基础上制定发布了《日本细菌学会生物安全指南》,1990年发布了《关于病原菌株分配中的生物安全指南》,1993年发布了《病毒研究中的生物安全指南》。
2.2.1 《国立传染病研究所病原体等安全管理条例》
《国立传染病研究所病原体等安全管理条例》[9]的最早版本于1981年制定发布,条例参考了日本国内实验室感染的调查情况和欧洲及美国的管理体系,其后,该条例经过了几次修订,基本符合世界卫生组织和发达国家卫生和疾控部门的通用标准。由于病原体的安全管理体系不受法律规章制度的约束,只是研究机构等自行制定和运营的原则,因此本条例也被用作日本研究设施等相关规定的制定规范。
鉴于海外传染病的发生情况和医疗条件的变化,日本意识到应积极采取措施,防止由生物恐怖主义引起的传染病的发生和传播。针对日本面临的生物安全国际新形势,根据《传染病法》在2006年的修订以及世界卫生组织相关文件,国立传染病研究所召集所内的生物风险管理委员会等多个委员会,对《国立传染病研究所病原体等安全管理条例》做出了第3次全面修订,于2007年6月开始实行。新修订版本旨在建立一个新的框架,以防止病原体和毒素的遗失、盗窃、非法使用和蓄意释放。
2.2.2 日本细菌学会《病原体等安全处理管理指南》
2001年,美国发生了“911”恐怖袭击事件,接着又发生了炭疽生物恐怖事件,使得全球对病原体安全管理的关注高涨,日本政府也认识到对病原体等严加限制的必要性,因此在2006年修订《传染病法》时,把有可能被用于生物恐怖事件的病原体的处理首次纳入法律限制框架内。但对于有些病原体则尚没有及时做出法律规定,日本细菌学会认为有必要向会员提供作为法律法规对象的病原体的相关信息,以及与其他病原体生物安全相关的充分信息。
在此背景下,日本细菌学会在《日本细菌学会生物安全指南》《关于病原菌株分配中的生物安全指南》等基础上,重新总结发布了《病原体等安全处理管理指南》[10]。指南提出,如果对病原体的处理不当,就会引起实验者自身、同室者甚至第三者的生物危机。如果管理不当,病原体就可能被滥用为生物恐怖主义的材料。指南在病原体处理设施的运营、实验室的日常安全管理、紧急事件的应对策略以及健康管理等方面提出了明确指导意见。
2.3 生物技术安全管理
日本重视对转基因等生物技术的安全监管,文部科学省于1979年8月颁布了《重组DNA实验指南》[11],规定无论是进行物理控制还是生物控制的重组DNA实验都必须确保其安全性,并在其后多次修订相关管理办法。此后,日本通产省、厚生劳动省和农林水产省分别颁布了各自的转基因生物安全指南,包括《转基因生物工业化指南》《农林渔业及食品工业应用重组DNA指南》和《转基因食品管理指南》等。2003年日本加入生物多样性公约《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之后,废除了《重组DNA实验指南》,代之以执行《关于控制使用转基因生物以确保生物多样性的法律》,于2004年2月18日起正式实施,将对转基因生物的监管上升到法律层面。近年,日本还在生物安全研讨会上专门介绍合成生物学和基因工程的最新进展,分析近年来发展迅速的基因组编辑技术的两用性,围绕前沿生物技术安全的研究和教育等问题开展研讨。
与早年间支持发展转基因工业产品与食品时的态度相类似,日本对于新技术的应用抱持审慎积极的态度。2016年4月,日本政府的生物伦理机构批准了利用受精后的人类卵细胞进行基因修饰的基础研究[12],但鉴于该技术可能对人类的未知危害,暂未批准相关的临床研究。2018年9月,日本卫生和科学部门领导的专家小组公布了允许在人类胚胎中使用基因编辑工具的指导方针草案,最终于2019年4月1日正式发布实施。
2.3.1 《关于控制使用转基因生物以确保生物多样性的法律》
2003年,为了与国际组织和其他国家合作保障生物多样性,日本制定了《关于控制使用转基因生物以确保生物多样性的法律》[13],要求采取措施规范转基因生物的使用等,以确保生物多样性公约《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以及《关于赔偿责任和补救的名古屋-吉隆坡补充议定书》适当和顺利地执行,同时为现在和将来的日本国民健康和文化生活保障做出贡献。
该法律中所用的“生物”一词是指单个细胞(不包括组成细胞群的细胞)或由主管部门相关条例规定的具有转移或复制核酸能力的细胞群和类病毒。“转基因生物等”也即“改性活生物体”是指具有通过使用遗传生物技术或其副本获得的核酸的生物。该法律对转基因生物的使用、扩散、进出口检验与监管等基本事项做出了限制和规定。
2.3.2 《关于在人受精胚胎中使用遗传信息改变技术等研究的伦理指南》
2019年4月1日,日本文部科学省和厚生劳动省正式公布了《关于在人受精胚胎中使用遗传信息改变技术等研究的伦理指南》[14],该指南是针对人受精胚使用遗传信息改变技术等的基础性研究,从尊重受精胚胎、对遗传信息的影响及其他伦理观点出发,对参与研究的人员开展适当工作的规范提出了若干规定事项。其中涉及的“遗传信息改变技术”主要包括基因组编辑技术和其他操作核酸的技术,“遗传信息”是指通过研究过程得到的、或已经伴随着人受精胚胎的后代传承的那些能够表现出遗传特征和体质的信息。
伦理指南对人受精胚胎的处理、废弃以及个人相关信息的保护、个人权益和其他知识产权保护等做出了限制和规定,对参与研究的机构和个人的行为规范提出了指导意见。指南规定,此类研究工作仅限于有助于提高辅助生殖医疗的基础性研究,人类受精胚胎只能在原始线条出现之前的14天内处理,且不得将进行了基因组编辑等操作的人受精胚胎移植到人或动物体内。指南同时指出,从事此类研究的机构应当设立伦理审查委员会,对研究计划的科学妥当性和伦理妥当性进行综合审查,就其适用与否、注意事项、改进事项等向研究机构的主管提供意见,必要时可对研究进展情况和结果的报告进行调查。
2.4 生物武器防御
近年来,暴力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势力在一些国家和地区逐渐抬头,两用生物技术在全球的快速发展也加大了公众对于蓄意的生物威胁的担忧。采取预防措施防止恐怖主义集团非法获取危险生物制剂十分重要。1995年,日本的邪教组织奥姆真理教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在对此案的审查过程中发现,其此前还曾多次企图用肉毒杆菌和炭疽杆菌进行恐怖袭击,但由于当时所使用的菌株和传播设备不够强大而失败。日本是《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全称《禁止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的发展、生产及储存以及销毁这类武器的公约》)缔约国,在1982年制定法律,禁止生物武器的生产、拥有和转让以及生物制剂的扩散,并确保对违反行为予以惩罚。日本在2018年12月发布的新版《防卫计划大纲》[15]中指出,国际社会在安全保障方面的课题正在广泛化和多样化发展,来自核武器、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的威胁等继续成为重大课题。2019年1月19日,日本生物安全学会在东京举办了主题为“新世代的生物安全”的研讨会[16],会议研讨认为公共卫生和安全部门在自然发生的传染病和人为传染病(生物武器)威胁的风险控制方面面临着巨大挑战,在外交和发展援助方面更多的是应对自发性传染病威胁,而从公共安全和国家防御的角度来看,更多的重点是应对人为传染病的威胁。会议专门探讨了在《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框架下促进不同研究领域的互动,以及与包括科学家社区在内的不同行为主体的互动和逐渐推动全球合作治理的做法。
2004年6月,日本内阁官房通过了《国民保护法》,提出了《国民保护基本指南》,根据《国民保护法》把可能遭受的武装袭击的各种形式、避难与应对措施等进一步具体化。根据《国民保护法》和《国民保护基本指南》,指定的行政机构和地方政府、指定的公共机构和地方机构将有序组织疏散居民、营救人员,应对武装袭击和灾难。为此,日本针对每个机构采取的措施制定了《国民保护计划》《国民保护业务计划》等具体计划。
2.4.1 《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国内实施法
1972年4月,日本加入了《禁止生物武器公约》,该公约于1975年生效。1982年6月,日本发布了该公约约束下的国内实施法,全称《关于〈禁止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的发展、生产及储存以及销毁这类武器的公约〉等实施的法律》[17],并在其后根据《制止恐怖主义爆炸的国际公约》内容进行了修订,最后一次修订是在2007年5月。该法律明确禁止生物武器和毒素武器的制造、拥有、转让和受让,并要求采取措施管制散发生物制剂和毒素的行为。
该法律对所涉及的生物制剂、毒素、生物武器、毒素武器等进行了明确定义,对几种将受到处罚的行为进行了规定,包括生物武器等使用罪、生物制剂等散发罪、生物武器等制造罪、生物武器等持有罪、生物武器处理事务虚假报告罪等。该法律还规定了在必要的限度内例外允许开发、生产、储存、获取或拥有生物制剂或毒素的情形,仅限于防疫目的、人体防护目的或其他和平目的。
2.4.2 《国民保护法》和《国民保护基本指南》
《国民保护法》[18]的全称是《关于在武装袭击情况下保护国民的措施的法律》,于2004年9月17日正式实施。为了在武装袭击事态等中保护国民的生命、身体、财产,制定了国家和地方公共团体等的责任、居民避难的措施、避难居民等的救援措施、武装袭击灾害的应对措施以及其他国民保护措施等必要事项。该法对国家层面和都道府县、市町村和特别区的职责任务和具体措施都作出了规定。《国民保护法》要求在发生武装袭击事件或其他危险迫在眉睫的情况下加强对生物制剂和毒素处理设施管理人员的警卫和其他安全保障措施,同时要求都道府县警察和消防机构提供加强安全的支援,以及当认为有紧急需要时停止使用相关办事机构,等等。
《国民保护基本指南》[19]针对各种武力侵犯和化学、生物和核武器袭击紧急事态下的避难方法、应对措施提供了指导意见。指南专门提出了生物武器袭击紧急事态的应对方法。生物武器袭击具有扩散不易察觉的特点,特别是在受到以人为传播媒介的生物制剂的袭击的情况下,二次感染造成的损害将进一步扩大。为此,指南提出加强以厚生劳动省为中心的一手信息收集和数据分析监测,及时确定感染源及污染地区,根据可能成为感染源的病原体的特性,及时部署医疗活动,防止扩散蔓延。
根据《国民保护基本指南》的规定,经济产业省每年定期对其管理的行业和研究机构开展病原微生物或毒素的持有及管理情况调查,并制定了《关于确保生活相关等设施安全的注意事项》,以确保其严格保管和管理病原微生物等物质。
3 启示与建议
着眼于强化灾难性生物事件防范与应急响应、发展生物科技创新和能力手段、持续完善生物安全战略研究布局,日本从传染病防控、病原体等安全管理、生物技术安全管理和生物武器防御等方面,逐步建立了国家生物安全法律法规体系,并形定了一系列指导政策,尽管还有不尽完备之处,但其一些理念和做法具有一定启示和借鉴意义。
首先,日本强调,在生物安全相关风险识别、管理和应对方面,加强各级政府、各行政部门的合作至关重要。在立法和监管层面,由日本内阁官房作为指挥中心,各中央政府职能部门、事务部门与公共卫生机构等分工协作;在实践操作层面,由中央政府发挥管理协调作用,各地方自治体做出响应并根据实际情况采取措施。例如,在这样的组织架构下,日本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方面取得了一定效果,但在此过程中也暴露一些体制官僚、机制刻板和沟通执行不畅等问题,特别是在处理领海内“钻石公主号”国际游轮上的新冠肺炎疫情传播时,因为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依据、未能严格执行相关指导政策而出现了明显延误和失误。
其次,日本在法律法规体系完善方面,注重科学规划,充分发挥国立科研机构和学术团体的作用。例如,国立传染病研究所、日本细菌学会等针对不断变化的新情况持续开展研究,制定和更新相关管理指南,并在实践环节提供专业指导意见。但是,日本尚未在全国建立自上而下的疾病控制预防体系,尽管在厚生劳动省的管理下,国立传染病研究所承担了“中央疾病控制预防中心”的一部分职能,但其在当前的架构下发挥的作用仍然有限。
再次,日本在大力推动新技术发展的同时关注社会学研究,关注技术的安全性、伦理和环境评价,开展广泛的公众意见咨询。在立法、监管和治理的各个环节,注重信息搜集和公开,通过多渠道平台推动公众知识普及和意见交流,不断强化全民防灾意识和行动自觉。
最后,日本近年在国家生物安全战略防御能力建设方面不遗余力,重视发展军民两用生物技术,推进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设施建设,加强专业技术人才培养和防卫国际合作。日本对外反复强调国家防卫的危急形势,以保护国民和防范恐怖袭击为由不断加强防卫装备建设。鉴于日本近年来在历史问题上的消极动向和国内政治的右倾化趋势,其战略意图和相关动作值得重视和警惕。
日本是我国的主要邻国之一,与我国同为亚太地区的重要经济力量,随着全球步入后新冠疫情时代,日本在生物安全领域的战略取向和行动也会影响到地区安全环境。在此背景下,我国应当参考借鉴日本在生物安全战略规划和法律法规体系建设方面的先进做法,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加快建立完善符合我国国情的生物安全法律法规框架和强大的公共卫生体系,加强生物安全科技创新体系和上下游产业体系建设,同时重视发展与日本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在公共卫生领域开展互信合作,并共同为欠发达国家和地区提供必要的发展援助和技术支持,推动地区乃至世界健康和平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