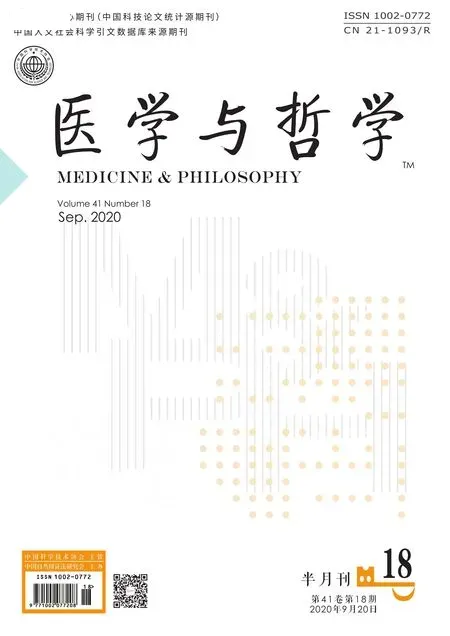身体概念的生命伦理学分析*
2020-02-16雷瑞鹏邱仁宗
雷瑞鹏 邱仁宗
随着生物医学技术的应用,提出了使用人体及其部件的哲学和伦理学问题,在科学家、哲学家及管理者之间也存在不同意见的争论。本文将集中讨论身体对人为什么重要、身体是什么、身体属于谁、身体部件商业化以及身体作为生命礼物等问题。笔者要指出的是,在撰写这篇评述性文章中,英国学者Alistair Campbell[1]1的著作《生命伦理学中的身体》(TheBodyinBioethics)对我们的帮助最大。
我们遇到过不少的案例,例如,一位贫困农民为了救治自己患血癌的女儿而愿意卖肾;同意医院对自己去世的独生女儿尸检,但后来发现医院留下了女儿的舌头,而有的家属发现医生留下了病人的骨头标本;在改革开放初期某省卫生局领导号召农民“卖血脱贫”等,这些案例提出的问题有:穷人卖肾救治重病孩子为什么不可以?医生尸检后留下标本为什么不可以?某省发展血液经济“卖血脱贫”有什么不对?这些都涉及身体是什么的概念性问题以及如何对待身体的规范性问题。
1 身体为什么那么重要
2003年,英国一对夫妇得知她们已经去世的女儿的舌头仍然保留在给她治病并作尸检的医院里,非常震惊,但医生认为非常自然,英国组织专门委员会对其进行调查[1]13-14。这个案例可以提出这样一些见解和问题:尸体及其部分与无机物一样都是由原子、分子等组成的客体而已;科学的观点(舌头不过是物质)与老百姓的观点(舌头是象征)的分裂应该如何看待?家属的反应是感情用事吗?理性的不带个人色彩的看法有什么问题?
身体似乎很重要。例如,有一些歧视与身体有关,如肤色、高矮、外形;隐私的一部分是身体的隐秘部分;身份标识也是与身体有关,如生物特征识别(biometrics);美容术很时髦,如做双眼皮、隆鼻、隆胸、断骨增高等都是因为对自己身体某些特征不满意而做手术;人人都要衰老,那是身体各系统的退化,包括眼睛、牙齿、皮肤、脑、性功能等;死亡也与身体有关,如死后器官如何处理,是否同意做尸检,是土葬还是火化等。那么身体是什么?不过是心的容器(container for the mind)[2]吗?
2 身体的特点
笛卡尔是现代科学医学之父,提出“我思,故我在”;心身两分,身体类似机器,如钟表;人(person)的独特性在于心,身不过是容器;人(human person)是“机器中的幽灵”(the ghost in the machine)[3]。这种观点的积极方面:将人体去神圣化,人体可以被观察、研究、干预,从而促进了解剖学和病理学的发展。“一打开尸体,疾病的黑暗面像黑夜一样被照亮并消失了。”[4]但这种观点强调心、精神、理性的超验的自我,轻视身体。
认知科学提出“赋身的认知”(embodied cognition),认为智能、行为是与脑、身体和世界的相互作用中出现的;提出“赋身的行动者”(embodied agent),认为在人工智能中一个智能的行动者通过处于环境内的物理性身体与环境相互作用。显然,不管是认知还是行动都不在身外,也不在环境、世界之外。同样,自我也不在身外,不在其他自我之外,不在环境之外。它们三者具有内在的联系,它们之间是相互渗透的,是有漏洞的(leaky),非局限于内部的(uncontained),也不能局限于内部的(uncontainable)。理性主义者希望有一个纯粹的身体,使得能够进行纯粹的思维,这是神话。我们不能避免与他人、与我们居住的环境之间的互动联系[5]7。
许多哲学家往往只看到身体对人的负面影响,甚至称“身体是坟墓”。从柏拉图到基督教,都认为身体是精神或灵魂的囚室或坟墓(soma sema)[6],身体的欲望是罪恶的温床,感官是骗人的,掩盖了实在的本性(类似中国哲学家王阳明所说的“去人欲,存天理”)。要是能摆脱身体及其引诱,能够清楚地、不带感情地思考,那我们的心、精神或灵魂那有多好啊!与这些哲学家不同,康德说[7],没有被感知对象的概念是空洞的;没有概念的被感知对象是盲目的(Concepts without percepts are empty; precepts without concepts are blind)。鸽子想:要是我能摆脱空气的阻力该飞得多快啊,但摆脱空气就飞不了。
现在的医生也轻视人的身体,将病人看作一部生理机器,无需注意病人的想法。诊断和治疗关注可观察到的病变和定量化的测量,而不是处于痛苦中的活的病人。病人自己的经验和主观声音在医患关系中已不重要。人们在呼吁能否建立一种赋身的医学(embodied medicine),使得医学更为人道、考虑到完整的人性,兼顾精神和肉体两方面[5]147。
在人的发育中身体的作用十分重要。身体不仅包括维持一个人的生存和繁衍所必须的有机体系统,也是脑的发育、自我和身份的形成所不可缺少的。婴儿刚出生时的脑是一块内部没有神经结构的基质,唯有靠脑与身体的相互作用,以及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才逐步建立其本身特有的神经结构和心理结构,才逐渐形成自己特有的人格身份(personal identity)或自我(self)。所以自我是赋有身体的(embodied self)[8]。
3 身体是什么
现今人的身体已经成为“大生意”。随着器官和组织移植的迅速扩大,细胞技术的发展,以及对靶向药物不断创造新的治疗奇迹的希望,身体和它的部件已经成为医疗工业越来越感兴趣的问题。我们已经看到了“身体集市”(body bazaar)的出现,在这种集市中,所有形式的人体组织都具有商业意义。于是就提出了身体是什么的问题:身体是财产,是商品,还是生命的礼物?
3.1 身体是财产
Alistair Cooke(1908年~2004年)是英国出身的美国著名记者,2005年圣诞节前夜人们发现他的腿骨已经从他尸体上取走,并以7 000美元价格卖给一家公司作牙科植入物用[9]。这里涉及同意、欺骗还有盗窃等问题。那么即使本人死前同意,没有欺骗,将身体作为“资产”出售,在伦理学上是否可接受?如果死后出售可以接受,那么生时出售是否也一样?这决定于身体这个实体(entity)究竟是什么,它有怎样的道德地位,以及由此产生的规范性含义。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我们的身体及其部件:是我们的财产?是可买卖的资源,可为了金钱而摘除其部分出售?还是别的什么?笔者先讨论第一种观点:我的身体是我的财产。
说一个实体是财产是什么意思?可以有两种看法:一种是自然主义的看法。例如,自然界(上天或上帝)将土地提供给所有人,人通过劳动获得财产,无人认领的原料与人的劳动结合将个人所有权的权利给予付出劳动的人。另一种是社会建构主义的看法。财产权利是一种社会安排,由治理当局决定,满足社会一致同意的需要,如发展生产力或公平分配资源。这将财产概念与社会目标联系起来[10]。我们认为,在财产的概念中,这二者的要素兼有:自然性是财产的必要条件,有效原料是人加工的原料,但最终还是来自自然。实体经济中的财产是所有财产的基础。但社会性是一个实体成为财产的充分条件,经过你的劳动后是否成为你的财产最后决定于社会安排。在奴隶制条件下,经过奴隶的劳动加工的自然界的原料最终不是奴隶的财产,而是奴隶主的财产[11]。
可是说一个物体或客体是财产,意味着财产所有者拥有诸多的权利[12],这些权利有:(1)拥有的权利(the right to possess);(2)使用的权利(the right to use);(3)处置的权利(the right to manage);(4)用以作为收入的权利(the right to income);(5)通过出售、抵押或馈赠转让所有物的权利,以及毁坏它的权利(the right to capital);(6)无限期拥有的权利(the right to security);(7)物件可传给持有者的继承人或后嗣,如此无限期下去(transmissibility):(8)所有权没有时间限制(absence of term);(9)防止损害的责任(duty to prevent harm);(10)拥有的实体可因处理债务或破产而正当地取走(liability to execution);(11)实体如果不再为所有者拥有(如其被放弃)可被他人拥有(residuarity)。可以将财产所有权特征归结如下:排他使用的权利、毁坏的权利,以及转让的权利[10]。那么,我们将我们的身体与财产的这些特征比较一下,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其一,第1、2、3、6、8、9条权利同样适用于身体及其部件。其二,但第7、10、11条不适用。“只要我活着,我的身体作为整体不能转让、取走,不能传给我后嗣,不能放弃,不能让别人所有,不能为还债而离开我。活着时只可以转让一个肾和一部分肝、血液、组织、细胞、基因。”其三,对第4、5条有争议:有人认为身体及其部件是商品,就提出了身体及其部件是否是财产的问题。即使我们可以把身体及其部件看作是财产,也不能解决买卖身体部件争论的道德问题,其中包括我们身体及其各司其功能的部件的道德地位问题。
将我们的身体看作是我们的财产这种看法存在如下的局限:第一,我们并不像拥有物质东西(如衣服)一样拥有自己的身体。没有身体就没有我:不能转让、放弃、取走。自杀、自愿受奴役就是放弃了身体,也放弃了自我。第二,我们的身体不是“我们的”。它们与其他人处于相互依赖、相互联系和相互掺和之中。从怀孕开始就是如此,我们依赖生活环境,与之互动,从这种关系中获得生命,一直到死亡(空气、食物、细菌)。我们的身体是个“漏筛”[13]。第三,即使作为一个整体不应被看作财产,我是否仍然可以用财产概念描述人们对他们身体部件的权利?考虑人体组织的地位有三个层次[13]:(1)整个身体:所有拥有和使用的权利都是不可转让的;(2)有功能的身体单元:血液、器官、细胞可移植到另一个人体内,所有权概念也不适合,它们可以在信托关系中被持有,如医院,那是为了确保移植到另一个人体内,对此医院有信托义务,不能将它们视为可买卖的物件;(3)人体材料的产物,如从克隆胚胎获得的细胞系或干细胞,是人的劳动产物,产生财产权,这些允许买卖。这样唯有付出劳动的科学家才可获得财产权。
3.2 身体是商品
一个实体成为商品必须具有三个特点[14]:(1)可转让性(alienability),即可出售、抵押、出租、放弃或毁坏;(2)可互换性或替代性(fungibility),即可在市场上交换,而所有者不丧失价值,如卖掉旧车购买新车,旧车以前的价值与新的价值(购买新车价格的一部分)是等价的;(3)可通约性(commensurability),即可根据共同的尺度(如货币)将实体的价值分等级。
但人本身是目的,不能仅仅视为手段。将人、人体商品化的根本错误是将人仅仅当作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那么能将人体部件视为可转让的商品吗?存在着强有力的社会政治力量将人的所有方面(身体)商品化,这种力量来自于自由市场哲学(市场原教旨主义)。身体有些部件可转让、可离异,是否也可用货币交换和通约?不管是整个人体,还是有功能的部件,不具可通约性。根据什么给它们定价呢?康德指出,人是无价的,即它没有价格,人的器官、血液和配子也是无价的。无价的实体就不具有可通约性,因此就不能成为商品。如果你硬将它们作为商品对待,就必然出现市场失灵的情况,凡是将配子、血液、器官作为商品进入市场进行交换,都必然出现市场失灵的情况,即不存在帕累托的效率:进入市场的交换者,至少有一人受益,而无人受害[15]。而在人类器官组织细胞市场,往往是病人、供者大受其害,而受益者是中介公司和医生,大发横财。
如果我们承认身体不仅是靠父母,而且要靠他人和社会的帮助下发育、发展,那么这种理念本身就含有我们不能将自己的身体看作仅仅是自己的私有品。人的身体最终应该回归社会和回归自然。
4 身体究竟是谁的
在自由主义思潮占优势的西方社会,不管是学术界还是老百姓,认为有一样东西是别人不能触及的,即我们的身体。他们的法律和政治传统是,我们有权拒绝他人触及我们的身体,即使我们的拒绝会伤害到那些需要我们个人的服务或身体部件的人;可是,我们又没有权利随心所欲地利用我们自己的身体以增加收入,即使这样做并不一定伤害他人,甚至在事实上我们这样做也许有利于他人。这是英国爱丁堡大学政治理论教授Cécile Fabre[16]1-39提出的自由主义身体理论中的矛盾之处:身体好像既是我的,又不是我的。Fabre的分析是从西方一些国家的法律、法规出发的,这些法律、法规一方面规定,我有权拒绝他人接触、获得和利用我的身体部件或我的身体,例如,未经我的同意不可在死后利用我的器官做移植或我的身体供医学生学习解剖用,或在我活着的时候强迫利用我的身体甚至其一小部分(如组织、基因样本)做科学研究,将我的血液输给他人,将我的肾移植给肾功能衰竭的病人,或利用我的子宫代孕,不能强迫与我发生性关系(即猥亵、性骚扰、强奸)。这体现了我对自己身体的绝对的独占的权利。但另一方面,这些国家反对我因贫困在死后出卖器官或出卖活体肾给急需的病人,也反对我暂时出租我的性器官和子宫给需要我服务的人,同时又增加我收入。似乎他人或代表我之外的人、政府或立法机构可以就我的身体的使用做出与我的决定相左的决定,这就意味着我对自己身体并没有绝对的独占的权利。这不是存在着一个明显的不一致和矛盾吗?也许我国新颁布的《民法典》实际上也存在这个矛盾:虽然第一千零三条规定“自然人享有身体权。自然人的身体完整和行动自由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侵害他人的身体权”;但第一千一百零七条规定“禁止以任何方式买卖人体细胞、人体组织、人体器官、遗体”。这两条之间实际上存在不一致,即自然人的身体权或身体行动自由是有条件的。Fabre试图建立一个我对自己的身体拥有高度限定的(highly qualified)权利以解决上述二者之间的不一致或矛盾,这不仅具有实践和政策的意义,既涉及到出卖器官、性工作、商业代孕是否应该合法化问题,还涉及到理论问题,即平等自由派(egatarian liberals)与绝对自由派(libertarians)之间的争论问题。所有自由派都认为自由是最为核心的价值,但绝对自由派(曾称为“自由意志论者”,笔者认为这个术语并不确切且难以理解)所承诺的自由要比其他自由派更广,他们对政府或权威抱着极端怀疑态度,实际上主张一种对个人不干涉和放任(laisses-faire)的政策。而平等自由派则认为平等也是一个核心价值,因此他们与绝对自由派在许多政府治理政策上有分歧,如税收,平等自由派认为,为了分配公正的目的,对于通过利用我们的身体获得的收入,我们并没有独占的权利,因此政府向我们收税是可以得到辩护的。而绝对自由派则反对这种强制性的税收,他们争辩说,如果其他人可以有权不顾我们的意见得到我们部分的收入,那么他们可以根据同样的理由也有权不顾我们的意见得到我们的身体了。Fabre认为,如果我们为了分配公正的目的而采取强制性税收政策确实会推出,我们并没有承诺个人对自己的身体有绝对而完全的权利。而拒绝个人对自己有绝对而完全的权利并一定推出要牺牲个体自主性的核心价值。理由有二:其一,通过提供个人服务而履行帮助他人的义务要服从一些条件,这些条件为义务履行者留有一些空间来追求他生活的美好;其二,这种义务与个人有权出卖他身体的部件或为性和生殖的目的而出租自己的身体,从而增加他们的收入以实现这种生活美好的观点是相容的。这意味着,其也与下列的观点相容的:有义务为他人服务的个体也有权利购买他人的身体部件,以及为了性和生殖的目的而租用他人的身体从而使他人得到好处,当然要在他人的同意之下。Fabre[16]72-97主张征用器官,即在出现大批器官功能衰竭的病人,而缺乏可供移植的器官将使大量病人死亡的危机条件下,可以通过法律程序征用死后器官,这与征税是一回事,都不是把自我所有权(self-ownership)作为公正理论的组织原则。其论证说,财产概念用于人是毫无意义的:我们是人(person),将人看作财产是完全不合适的。这一点与笔者上面讨论的观点是一致的。
5 身体部件的商业化
身体既不是财产又不是商品,那么身体部件(parts of the body)呢?
5.1 器官交易
由于器官移植技术的改进,有效地压制免疫的药物、抗感染药物的发明和广泛应用,但同时由于引致器官衰竭的因素一直在增加(如吸烟、饮酒),器官移植供不应求的问题更为严重。美国每年有11.4万人在等待器官移植的名单上,每天有20人死于得不到移植的器官。我国大约有30万人在等待器官移植的名单上。于是器官交易、贩卖现象非常严重:移植旅游或器官移植商业化已成为全球产业,2006年产值600亿美元;在互联网上可提供一条龙的器官买卖,购买世界另一头的匿名供体器官非常容易;买主来自澳大利亚、以色列、加拿大、美国、日本、沙特阿拉伯,而卖主来自巴基斯坦、印度、巴西或玻利维亚。结果造成非常严重的问题:(1)剥削。剥削是外科医生、中介利用卖主的无权地位使他们的牺牲得不到相应补偿。卖主是穷人,买主是富人,卖主无权决定定价和拿多少。对此类剥削,还有人提出支持的论证:其一是两害取轻论证:即使有剥削,出卖器官可以济贫[17];其二是延伸论证:我们允许人们从事危险职业(采矿、救活)、危险的运动(赛车、登山),推而广之就应允许卖器官[18]。(2)伤害大大超过受益。许多出卖器官者经济状况未能长期改善,但健康状况恶化了。96%的卖肾者为了还债,但卖肾后平均家庭收入减少1/3,增加了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数;86%报告卖肾后健康状况恶化,79%不建议其他人卖肾。(3)违反同意原则。1/3卖肾者说,医生没有把充分的信息告知他们;超过2/3的卖肾者说,在手术前没有得到任何的健康咨询;术后回来作健康检查的不到1/2。91%卖肾者处于经济异常窘迫的情况,受到经济力量的强迫(还债、家人有重病),自主性严重削弱,其同意往往是无效的。器官出卖者的情况不同于无任何威胁的理性决策者。而同时器官买卖不能保证器官的质量,供体为了出售器官很可能会隐瞒他的真实病况、遗传病史、家族病史等。(4)加剧人们在生死面前出现的不平等,有钱人可以购买器官而获得再生机会,而贫穷的人只能在绝望条件下去出售自己的器官。设想一个母亲为了自己的孩子生存下去,出卖了自己一个器官。这样做应该允许吗?主张器官买卖的人说,她出卖了器官,不就改善了她孩子的境遇了吗?如果一个社会竟然让一个家庭只能用出卖器官来改善境遇的话,那么这个社会本身就成了问题。所以器官买卖加剧社会本来存在的不平等以及贫富之间的鸿沟。(5)危害社会秩序。由于器官商品化,就可能有人用不正当的手段摘取器官,并出现一些以金钱为目的残害人类生命以攫取器官的黑社会。(6)对利他主义的威胁。器官市场合法化将给自愿系统釜底抽薪,在过去本来愿意捐赠的人得知有来自市场的供应后就不再捐赠了。美国一项研究表明,经济刺激仅对20%可能的捐赠者有影响,其中12%表示更愿意捐赠,5%不愿意,其余没有决定[19]。(7)器官商品化贬低了人的道德地位。身体部件虽然可转让,但不是可交换和可通约的,如果它们像物体那样,价值可在商品市场确定,那就把我们的身体降低为仅仅是客体,不能尊重其作为我们的人格身份——赋身自我一部分的特殊地位。在捐赠我身体的部件帮助别人时,我对其他人的福利和生存做出了个人贡献。但在我把我的身体仅仅视为收入的手段时,我通过我的身体部件的工具性使用,贬低了我的人格。
我们首先应该认识到,人处理自己身体的自由有两个限制:一是不能伤害他人,二是不能损害人的尊严。如果一个人处于利他主义的高尚动机,捐献自己的器官,那么既有利于他人,又维护了人的尊严。但人能不能自由出卖自己去做他人的奴隶,或出卖自己的肉体去卖淫?上述论证就可能导致这个结论:做奴隶或卖淫是他/她的自由,别人无权干涉。但这个结论违背人们的道德直觉。伦理学家一致认为,人的尊严不允许任何人出卖自己去做他人的奴隶。女性主义者指出,卖淫是社会性别不平等的结果,而卖淫本身又加剧了这种不平等。
如何以合乎伦理的办法解决这个危机呢?器官移植是一项成熟的技术,在美国器官移植已经挽救了230万人的生命,我国也起码挽救数十万人生命。鉴于因可供移植器官的稀缺而导致器官衰竭病人死亡的人数每年达1万~3万人,在等候名单上的数十万甚至数百万器官衰竭病人继续备受疾病煎熬,而这一健康问题并非单靠病人及其家属以及卫生机构能够解决,政府乃至立法机构必须介入,因此应定义其为一个公共卫生问题。缩小可供移植器官供求失衡的措施之一就是建立并扩大可供移植的器官库。这类器官库类似群体免疫力一样,是公共品。作为社会成员的我们每一个人以及代表社会的政府和立法机构有责任来建立和维护这类为全社会成员服务的公共品,这是我们一项每年挽救数万生命、改善数十万甚至数百万病人健康的不可推卸的道德义务,并建议将这种道德义务转化为法律义务。器官捐献应坚持自愿原则,这是贯彻知情同意的伦理要求。但自愿原则和知情同意要求,本身有多种形式。作为一个公共卫生问题,面对着每年可能因器官稀缺而死亡的数万病人以及数十万甚至数百万病人在等候器官时备受煎熬的紧迫情况,建议采取可选择拒绝的推定同意制度,即病人在死亡前(包括因车祸突发死亡者生前)的任何时候没有书面的或有证人证明的口头明确表示拒绝捐献,可推定为同意捐献。此项可选择拒绝的推定同意制度仅限于公民逝世后的器官捐献,不涉及任何活体器官的捐献。在特定情况下,可允许的活体器官捐献必须遵循经典的、严格的知情同意程序。在扩大可供移植的器官供应的同时,要努力缩小对器官的需求。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预防器官衰竭,其中最重要的是预防和治疗对具有精神活性的可滥用物质(如尼古丁和酒精)的依赖和成瘾,为此要进一步改革医疗卫生制度,将成瘾的治疗和预防纳入现有的医疗系统内,禁止在电视台播放含酒精饮料的广告等[20]。
5.2 人体组织和细胞的商业利用
近年来,医学和科学共同体以及生物技术和药物制造公司对人体组织的需求规模越来越大。美国已形成了一个人体组织市场,称作“body bazaar”。人体产业是170亿美元生物技术产业的日益增长的部分,包括1 300家生物技术公司。这些公司提取、分析人体组织,将它们转化为产品,获得巨大经济利益。他们对皮肤、血液、胎盘、配子、活检组织以及遗传材料的需求日益扩增。平常作诊断用的血液用来研究疾病的生物学过程和遗传基础;婴儿包皮细胞用来制造人工皮肤的新组织;脐带血成为干细胞来源;从已死婴儿肾中提取的细胞系可用来制造抗凝剂;人的DNA可用来运行计算机,因为CATG字母代表的四个化学物质比二进制提供了更多的排列变化。挖掘人体组织宝藏衍生了新型犯罪——生物海盗行为。2008年,美国新泽西州生物医学组织服务公司老板前牙医Michael Mastromarino在纽约法庭被判有罪,他伙同墓地负责人取走待下葬或火化的尸体的部件,如胳膊、大腿骨、皮肤、心瓣膜和静脉,将其产品卖给提供牙科植入物、骨植入物、皮肤移植物等的公司,他们从1 000多具尸体上收集人体部件或组织,有些尸体患有艾滋病或其他传染病,约1 000人接受了这些组织。Mastromarino被判18年~54年徒刑。其他地方也发生太平间助理出售婴儿尸体的器官和脑、医学院病理尸体解剖室主任出售脊髓、火葬场未征得家属知情同意出售身体部件的事件[1]75。
合法获得和使用的人体组织究竟有多少呢?1999年在美国至少有3.07亿件人体组织标本,每年以2 000万件的速度增长。为推进医学研究的目的而自愿捐赠的组织,现在成为许多方面(除了最初捐赠者)参与的获利的来源,这是否是一个问题?如果有同意,也没有对最初捐赠者造成伤害,为什么我们应该对此关注?
美国国会通过的Bayh-Dole法令为人体组织和细胞系的商业化打开了方便之门,只要具有新颖性和使用了技能和劳动就行。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Moore案例,1990年,加利福尼亚州高等法院就“Moore诉加州大学董事会”一案做出判决,其中心是人体组织的财产权问题。1976年,John Moore被诊断患罕见的、致命的多毛细胞白血病。他遵照就诊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中心的David Golde医生的建议切除了脾脏。他接受的治疗是完全合适和有效的。Golde一开始就发现Moore的血细胞有潜在的商业价值,因为他的血细胞有非同寻常的性质。后来的7年中,Moore被要求定期从西雅图的家到医学中心,提供追加的骨、血、皮肤、骨髓抽取物和精子。他被告知这些样本为确保他身体继续健康是必要的。然而事实上,Golde及其助手正在开发一种不死的细胞系,称之为“Mo”。他们于20世纪80年代初申请专利,1984年被授予专利,Golde及其助手Quan是发明人,加州大学董事会是代理人。他们与两家私人公司协商商业交易。1990年专利的潜在商业价值估计达30.1亿美元。1983年,Moore才发现此事,那时他被要求签署同意书,与他以前签的非常不同,这同意书要求他和后代把从他的血和骨髓开发的细胞系可能获得所有权利都给予大学。他拒绝签署,在知道了有关“Mo”细胞系专利后,他对加州大学董事会、两位研究人员和公司提出法律诉讼。1990年,加利福尼亚州最高法院对下列两个问题做出判决:(1)Golde未能告知他的研究计划及其经济利益是否违背了他的信托义务;(2)Moore是否有权分享从“Mo”细胞系获得的利润,作为对侵犯他财产权个人赔偿。对第一个问题判决是肯定的,对第二个问题的判决是否定的。这个案例的判决表明:(1)拒绝病人对自愿给予医院和研究人员身体部件提出的所有权要求,即使他们使用的目的也未告知。经他同意取走组织时,他对自己细胞所有权的利益就放弃了。这个同意并未知情,也不影响这个结论。(2)生物医学研究是公共利益,给予捐赠者已放弃样本的所有权,对公共利益有破坏性作用[1]76-79。
6 生命的礼物
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死后人体不可避免地要分解,但我们所爱的人的尸体对我们有特殊意义。什么是我们与死者身体关系的性质?我们感谢死者给我们的礼物:知识、生命和回忆[1]133-144。
首先,死者的身体是知识的礼物。例如,尸体解剖可评估内外科治疗的有效性、检查诊断的准确性和死亡原因;提供新的未知疾病的知识;检查环境因素在疾病中的作用;考查治疗的医源性作用;保留的材料、储存的切片和标本用于研究;促进医学进步,培养未来的医生。然而,尸检率一直降低,其中有病人的原因和医生的原因,需要进行调查研究。
其次,死者的身体是生命的礼物。例如,将死者的器官移植给器官衰竭的病人,使他们可以活几年至几十年,实现自己的理想,为家庭和社会做贡献。
最后,死者的身体是回忆的礼物。伦敦的自然博物馆收藏的人类尸骨标本达19 950件,时间跨度为50万年,46%来自外国。2007年,董事会决定将17具塔斯马尼亚土著人的尸骨归还澳大利亚政府,后者作为塔斯马尼亚土著人中心的代表接受这些遗骸。但保留了在归还前进行观察和测试的权利。这是一项妥协:英国科学家为一方,他们要对遗骸进行研究;另一方为土著人,他们要他们的祖先有一个适当的安息所。塔斯马尼亚人认为现在与过去纠葛在一起,他们与祖先有心灵上的联系,对土著人文化的尊重,必须体现在对他们祖先遗骸的尊重上。他们认为,他们的祖先必须葬在他们人民的土地上。“叶落归根”,我们的文化也有类似的观念和信念。
我们的身体提醒我们,我们与我们其中一部分的自然界的关系既壮丽辉煌,又具灾难性。人已经并将继续使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发生大规模变化,其方式和规模完全不同于其他生物的影响。弗洛伊德说,人类有一种死亡之愿(death wish),回归到无机物的强烈冲动。我们剥削自然资源的集体努力已经威胁到生命赖以存在的系统。我们的身体还提醒我们,我们人是“安居本土”的(earthbound),这是指我们对地球的依赖性,一切有机生命(包括人类生命)唯有依赖地球才能继续;同时,地球是我们的最终安息所:我们由此进化,在死亡中我们回归为其组成成分。我们要确保对身体的尊重,正如上面所谈的,我们的“离身”部分(disembodied)(心、精神、智能)给予我们的能力,远没有增强和保护我们的身体,反之使身体失去尊严,走向毁灭。我们要化解身心分裂,承认拥有多样性的人性的共同性,而且恢复我们身体与被大规模改造的自然界的可持续关系。没有这种关系,就没有人类意识的地位,为了人类“心”的荣耀而轻视“身”,必将有受惩罚之日[1]152-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