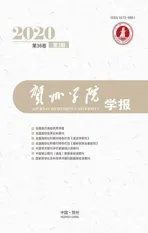清代桂林科举家族研究
——基于《清代朱卷集成》
2020-02-16胡可杰
胡可杰
(广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1)
清代科举家族的研究首推张杰的《清代科举家族》,他认为“科举家族是指清朝世代聚族而居,从事举业人数众多, 至少取得举人或五贡以上功名,在全国或地方产生重要影响的家族”[1]24。利用《清代朱卷集成》等资料,对科举家族的经济基础、人文环境、日常生活、社会流动、地域变化、家族影响等方面进行研究者不乏其人。方芳在《〈清代朱卷集成〉研究——以进士履历档案为中心》一文中,通过对进士履历进行系统的统计,展现了科举家族的地域分布、科举家族的联姻特点[2]。杨振的《从〈清代朱卷集成〉看清代江西的宗族与科举》,通过《清代朱卷集成》探讨宗族与清代江西科举之间的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3]。在此,以《清代朱卷集成》中广西桂林籍中式者的履历为研究对象,对桂林科举家族的基本情况与家族联姻等方面进行考证分析,探讨其经济基础、社会影响。不当之处,敬请专家学者指正。
一、《清代朱卷集成》 中有关桂林科举的基本情况
顾延龙先生主编的《清代朱卷集成》,1992年台北成文出版社出版,一共420 册。此书收录清代从康熙到光绪年间的乡试、 会试、 五贡等朱卷8264份。其中会试卷1616 份,另有武会试卷4 份;乡试卷5186 份,另有武乡试卷34 份,五贡卷1576 份[1]6。朱卷是指清代在乡试和会试中,应试者用墨笔书写试卷,为防止考生舞弊,墨卷由誊录生用朱笔誊录,再送试官评阅,称朱卷。《清史稿·选举志三》:“士子用墨,曰墨卷。誊录用朱,曰朱卷”[4]3148。还有考中举人、进士的士子会自行刊印自己的试卷并送人。清末商衍鎏在《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中提到“新科举人进士自刊其闱艺分送亲友者, 谓之乡试会试朱卷。因闱中誊录用朱,卷为主考所阅取中,是即闱卷之意,虽以朱卷称之,实为墨印而朱耳”[5]87。朱卷内容包括科举类别、考试年份、考生姓名以及考生家谱、师从等情况。其中,家谱记录极其详尽,有的甚至追及一世祖者,还有师从按照授业顺序排列,内容也非常详细。因此,朱卷为清代科举制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古代广西作为西南边陲地区,文化教育相对于中原地区落后很多,在科举上取得的成就也相差甚远。但在广西,桂林作为古代广西的首府,是全省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中心。因此,桂林在广西科举考试取得的成就上, 也是广西其他地区所不能比拟的。对《清代朱卷集成》的研究可知,清代广西士子乡试卷88 人,会试卷32 人,占《清代朱卷集成》乡试卷的1.7%,会试卷的2%。广西桂林籍的士子,在乡试卷中有39 人,会试卷有20 人,占广西全省的44.3%和62.5%。桂林府中又以临桂占比最多,乡试、会试卷中试者分别占69.4%和50%, 两项占比均有五成或五成以上。从中可以探究出广西与桂林地区在科举人数分布的不均衡。

表1 桂林各县朱卷情况一览表
根据张杰教授对“科举家族”的定义,为了增加可比性与准确性,“在计算每个家族的实际人口时,采取明清刑律规定的五服制度,只计算高祖以下人口”[1]37。为了能够让计算更加精确,笔者将定义“从事举业人数众多,至少取得举人或五贡以上功名的家族”,都精确为至少2 人以上。笔者将《清代朱卷集成》中广西桂林籍的士子进行统计见表1,乡试卷中的邹崇德、秦步月、汤宏业、俸肇祥、莫炳贤、阳顗、吴肇邦,会试卷中的李务滋,未能满足“科举家族” 定义的条件, 得出桂林科举家族约占85%,因此,科举家族的成员与普通家族成员相比,考取功名概率更大。另外,对《清代朱卷集成》中桂林籍的朱卷研究发现,有许多士子是出自同一家族。如临桂的陈钟珂、陈钟瑞、陈畴熙、陈守睿、陈守模、陈奎昌为一家族,系乾隆时名臣陈宏谋之后;临桂的周炳蔚、周鸿钧、周廷揆、周绍刘、周绍昌与代办两江总督周启运同为一家族;临桂的龙维栋、龙应中与状元龙启瑞同为一家族;临桂的白銮锵、白振钧同为一家族;临桂的朱得寿、朱湘与“岭西五大家”之一的朱琦同为一家族;永福县的李骥年、李光卓兄弟一门。一门多人中科举,这对家族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清代桂林科举家族的形成原因与社会影响
科举家族的形成,是由多方面因素组成的。首先,宗族观念是形成科举家族的先天条件;其次,经济基础是科举家族形成的基础,有了经济基础才能解决生存问题,才能投入更多的时间、精力、金钱到科举考试中去;最后,家族的文化传统是科举家族发展的重要因素。科举家族对于地方的社会发展也有着推动作用。
(一)经济基础
科举考试道路是个漫长的过程,花费的不仅是士子青葱岁月, 还有围绕科举所产生的大笔费用,可以说经济状况是士子科举考试的前提。对于无立锥之地的贫苦农民来说,要去参加科举考试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但是,对于累世科举的科举家族来说,相对就会容易些。在张杰的《清代科举家族》中,有一段康熙十六年(1677年),江西道监察御史何凤歧的奏折,内容是关于“一个童生仅参加县府两试的费用就要10 两银子,在清初10 两银子通常可以买到10 石粮食, 相当于一个3 口之家农民的全年口粮,甚至是全部家产”[1]69。
在《清代朱卷集成》中对于家庭的经济条件屡见记载。如光绪乙未(1895年)科进士,桂林府全州县的赵炳麟家族。赵氏家族的始祖赵廷礼是宋翰林院大学士,任广东储粮道,由浙江金华府兰溪县迁居全州。直到七世祖开始,在朱卷上开始有了科举功名,即明岁贡生。到九世祖是这样记载的:
九世祖希尹,字乐耕。明典膳,诰赠奉政大夫,勅授员外郎。生平乐善好施,慕范文正公之为人,置义田三百亩,以供享祀。又置学田以资来学者。膏火里有贫不能婚葬者,举囊以助。乡邻有忿争者,质之于公,片语立折人以方之。王彦方云:会岁凶,公出粟赈济,所活者数万人[7]404。
从上可知,赵氏家族在明中后期的时候,经济条件已经相当优越了。家族有“乐善好施”的义举,比如“置义田三百亩”“置学田”“救助穷困者”“出粟赈灾”等,每一项义举都是声势浩大的大项目,其财力可见一斑。而且从十世开始,家族就陆续有人中式举人或是中式进士,家族更加兴盛发达,成为当地有名的科举大家族。由于家况殷实,像十世祖赵孟豪“幼承家训,读书以古人自期。弱冠中明嘉靖庚子第五名举人,丙辰三十六名进士”[7]404-405。这样的科举大家族在生活上自然是没有了后顾之忧,只需潜心学习,最后取得科举功名。
家族优越的经济基础还体现在科举功名的获取,通过捐纳成为“太学生”,太学生也称国学生或者监生。《清史稿》中有明确记载“监生凡四:曰恩监、荫监、优监、例监。荫监有二:曰恩荫、难荫。通谓之国子监生”[4]3100。捐纳成监生之后,就可以直接参加乡试,或者到京城的国子监去学习参加科举。如果没有殷实的经济基础, 怎会去捐纳获取功名呢?所以,科举家族的繁荣发展,还需要有经济基础作为前提的保障。
(二)文化传统
科举家族对文化的重视, 主要体现在兴办族学。科举家族为了能够让家族不断发展,尽可能地让家族成员都接受教育,读书应考,来达到教育族人,取得科举成功,光耀家族的目的。广西灵川周廷揆家族的家训中就体现了兴办族学的目的。《周氏家训》云:“送子求学,增知博学;若中及第,擢升显赫。”读书科举,勤勉治学,学风传承,是江头村人所代代相传的家训。家祠等家族活动场所,往往是族人组织教育的场所。灵川周氏家族的爱莲家祠除了用于祭祖外,爱莲家祠被周氏家族办成培养周氏子弟的学堂, 就是为了让周氏子弟能够读书应考,培养优秀人才。
族人在科举中取得成就, 往往可以反哺家族,他们在家族教育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清代朱卷集成》中有详细记录师生关系,中试者会将教过自己知识的老师或者主持考试的科考官员的名字写在朱卷上。师承关系可以分为“受业师”与“受知师”,“亲受指示讲读者为受业师,入学及中举、中进士、复试、殿试、朝考阅卷者为受知师”[5]87。科举家族教育族人的启蒙老师往往是家族中已在科举考试中取得一定成就的人或是家族姻亲人物,至少是科举生员出身,他们会将自己的科举经验言传身教于族人。例如灵川周氏,周廷揆的受业师有胞兄周廷冕(举人)、岳叔况瀚(举人)[8]243-244;周炳蔚的受知师有家叔周冠、姻叔秦舸南[9]373;还有临桂龙氏,状元龙启瑞的儿子龙维栋, 其受知师有姑丈况桂森(进士)、表兄邹学健(郡庠生)、从堂兄龙维桢(举人)[9]269;进士韦业祥的受业师有况瀚(举人)、姨丈况桂森[8]6等。由于各个家族相互之间结为秦晋之好, 也会出现同一个老师会教授不同家族的学生。这不仅加强了族学的师资力量, 而且也可以巩固发展各姻亲家族之间的关系。周绍昌的岳丈卢秉政是进士, 从小就受到卢秉政的学业教导,“幼蒙教育”[10]413。还有周绍昌的年伯秦焕为进士。年伯即为与父辈同一年考上的人。他在周绍昌的教育中起到重要作用,“蒙取案首入泮,素承训迪,得以少有成就”[10]416。
(三)社会影响
任何地方、家族的持续发展离不开教育,教育是根本。因此,要发展教育事业,必须需要有大量优秀的教师。科举家族的成员多从事教育活动,成为当地教育的中坚力量。通过教书育人以及撰写大量文化著作,一方面,提高了作者的知名度;另一方面,推动了桂林甚至广西文化的发展。
1.从事教育活动
清代教育体制“有清学校,向沿明制。京师曰国学,并设八旗、宗室等官学。直省曰府、州、县学”[4]3099。在各地兴建学校或者书院,书院山长往往是在科举上取得优异成就, 在当地有一定影响力的人来担任,根据《清史稿》所记载:“各省书院之设,辅学校所不及……儒学浸衰,教官不举其职,所以赖以造士者,独在书院。其裨益育才,非浅鲜也”[4]3119。同时又有义学,社学。这么多的教学机构,需要大批的教师,而科举家族拥有大量的优秀教育人才,是地方教育所需师资的主要来源。
在书院讲学的人基本上是举人、进士出身。师资力量的高低决定了书院对科举士子求学的吸引力。书院山长也叫“讲席”。山长是由地方官选聘,负责书院的教学和管理。担任书院山长之职者,一般是取得功名,学识渊博,而且在地方享有较高的社会声望。乾隆二年(1737年)朝廷下诏:“书院讲席,令督抚学臣悉心采访,不拘本省邻省,亦不论已仕未仕,但择品行方正,学问博通,素为士林推崇者,以礼相廷,厚给廪饩,俾得安心训导”[11]395。被称为“岭西五大家”者,有吕璜、朱琦、彭昱尧、龙启瑞和王拯,这五人在桂林素有名望,在文学上颇有造诣。吕璜曾主讲榕湖、 秀峰等书院,“教人先行而后文,践履笃实,为诸士先,治诗古文辞皆有法”[12]90。朱琦曾主秀峰书院,“尤善古文辞,与永福吕璜齐名”[12]65。王拯着重研读典籍,以明礼修德。以桂林四大书院秀峰书院、宣成书院、榕湖书院、桂山书院为例,大部分的桂林籍科举家族都曾在四大书院学习,如周璜、曹钏、靳邦庆、周干臣、王恩祥、王拯等,培养了很多优秀的科举人才。
科举家族成员在地方任职时, 会积极参与地方文化建设,不仅建立书院,而且还会参与讲学。周廷揆父周启运,在德安府任职期间“爱士如渴,尤以振拔寒畯为要,添置汉东书院号舍,每课期集生童扄试,并拟作以为程序,士子多所有成就”[13]365。还有蒋兆奎(举人)、王亦曾(进士),前任阳朔知县兼主寿阳书院讲席[14]329。杨璐枝(举人),前永福县知县、掌教凤台书院[15]26。地方官重视地方教育,带动士子参与科举应试, 有力推动了当地教育事业的发展。
2.科举家族的文化著作
科举家族成员都有着较高的文化素养,士人著述极多。通过文学著述不仅可以扩大文化影响力,而且还可以将科举制艺编著成书以传于子孙后代。这也是家族文化成就的充分体现, 在某种意义上,也反映了当地社会文化的发展水平。在《清代朱卷集成》中多有中试者家族热衷于著述行世,将清代桂林籍的朱卷中有关著述统计。
通过表2 可知,第一,在著述活动中,作者的科举出身多为举人、进士,功名与文化层次高,往往其著述的质量较高,如朱琦的《怡志堂诗文集》《来鹤山房》等著述,文学造诣非常高,“文能兼方苞、姚鼐之长,而扩其所未至,诗格雄浑,不立纲宗而自成体势,为广西五大古文家之一”[16]46。举人陆辅清的曾祖陆锡璞,生平著述有《七经精义切要》《格言偶存》《浅艺夜学浅语》《陆宣公奏议》《陈文恭手札节要》行世,“公以纯儒为循吏,至今人读其遗书,观其政绩,咸钦仰焉”[14]243。这样的评价也是对其著作造诣上的一种肯定。第二,往往越是科举大家族,一家数代或同代数人的论述著作就会更多。例如灵川周氏家族,周廷揆、周绍昌,祖辈4 人,有13 部著作之多,为《集成》中桂林籍科举家族之最。这也是家族源远流长的文化水平的表现。第三,有些著述为经典典籍的注解或是自己阅读感悟,如卿彬的《洪范参解》《律吕参解》《离骚注》《古诗十九首注》《千字文注》,唐仁的《周易观玩编》《春秋左传分编》等。而且大多数著作都具有较强的学术性与应用价值,例如胡德琳的《碧腴斋诗》《存燕诒堂诗文集》《东阁间吟》《西山杂咏》《书巢尺牍》。科举家族的文化著作不仅提升作者的知名度,也不断推动了当地文化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
三、桂林科举家族的联姻特点

表2 桂林籍朱卷著述情况一览表
在《清代朱卷集成》里有非常丰富的联姻资料,在士子的朱卷中会写上该士子本人、母亲、胞姑、姐妹等联姻家族的背景资料。这对于研究其本家族以及联姻家族婚姻关系、婚姻观念,都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社会是讲究人情世故,一个人甚至一个家族的发展都需要一张巨大的关系网,“科举家族”的发展也离不开层层关系网。在家族联姻上,科举家族会倾向于与自己家族地位相近的家族,即讲究门当户对,“联姻双方家庭由功名所体现的文化层次相对接近”[1]138。桂林科举家族的联姻特点为多核辐射的联姻模式。
具体而言,桂林的科举家族形成了以几个大家族为核心,向外辐射的联姻模式,即以灵川周廷揆家族、临桂龙光甸家族、临桂张其镃家族、永福李骥年等家族为核心联姻,以临桂况祥麟家族、临桂朱琦家族、临桂陈宏谋家族、永宁韦业祥家族为次核心联姻。
灵川县周廷揆家族。该家族为濂溪周敦颐之后裔,注重科举兴族,是当地著名的科举家族。周廷揆父周启运官至江南盐法分巡道兼江宁布政使、代办两江总督事。虞候官林文忠则徐“叹为循良第一”[17]637。周启运、周廷揆为进士,其祖父履泰、长兄廷冕为举人,即有“一门两进士,三代四举人”之美名。其家族通婚情况如下,周启运,其长子廷冕娶临桂龙氏之女结亲[19]378,“三子廷揆娶的是临桂举人况祥麟孙女、廪贡生况洵长女”[8]241,“长女嫁给灵川举人万方泰次子万启华,次女嫁给临桂进士朱琦之长子朱方达,四女嫁给永宁举人韦恩霖长子进士韦业祥”[8]240。周廷揆的族侄周绍刘其祖母万氏为举人万方泰之女[18]168;族侄周绍昌长姐适前贵州巡抚林肇元的次子林世焘(举人)[10]414。
临桂龙光甸家族。龙光甸为举人,其子龙启瑞为状元,其孙龙维栋、胞侄曾孙龙应中为举人。龙光甸女、龙启瑞胞妹嫁给永宁举人韦恩霖[8]5,龙应中的胞长姑母嫁给朱寿康(朱琦胞弟)次子朱成彦,三姑母嫁给进士周干臣,其胞长姐嫁给朱方达长子朱圣俞,胞次姐嫁给张瑄次子张其镃[19]376。
临桂张其镃家族。张其镃父张瑄为进士。张其镃的祖母陈氏为灵川陈宏谋家族的陈兰策孙女、陈逨熙女[20]407,其母陈智熙孙女、陈其昌女[20]410,张家与灵川陈宏谋家族多次结为秦晋之好。还有张其镃的妻为临桂龙光甸家族,系龙启鹏孙女、龙启瑞堂侄女、龙维椿次女[20]410。
永福李骥年家族。李光卓与李骥年俩兄弟的曾祖父李树乔为乾隆时举人,曾祖母陈氏是陈宏谋胞兄陈宏诚之孙女、侄子陈钟璠之女[15]20-21;祖父李熙垣为恩贡生,其父李吉寿为举人,其母龙氏是龙乐园女,龙恩浩胞妹、举人龙致泽胞祖姑[15]22-23,李骥年的妻子刘氏是桂林藉状元刘福姚的胞姑母[21]62。胞兄鸿年为举人、光卓为进士、鹖年为经元(举人)、麒年邑庠生,胞弟光年邑庠生、凤年俱业儒、伊年俱业儒。家族有多人中举,是为典型的科举家族。
以上分析可知,多核辐射的联姻家族,多与本县或是邻县的科举家族互为姻亲。这有利于巩固家族间的裙带关系,有利于家族势力在省内与桂林地区的稳固和扩张。灵川周廷揆家族与临桂龙光甸家族、临桂况祥麟家族、灵川万方泰家族、临桂朱琦家族、永宁韦业祥家族等联姻;临桂龙光甸家族与永宁韦业祥家族、临桂朱琦家族、临桂张其镃家族等联姻;临桂张其镃家族与灵川陈宏谋家族、临桂龙光甸家族等联姻;永福李骥年家族与灵川陈宏谋家族等联姻。灵川周氏、临桂龙氏、临桂朱氏、永宁韦氏形成牢固的四边形, 四边形里又相互交叉联系,而且基本与桂林科举大家族进行联姻,甚至可以通过联姻亲戚关系联系到临桂张其镃家族、灵川陈宏谋家族,形成牢固的联姻模式,也扩大了家族与姻亲关系外的科举家族的关系,这反映了科举家族在联姻上强烈的地域意识。
其他的科举家族,永福秦献祥家族,其母李氏为永福李熙垣孙女、李葆祺女、李光卓与李骥年嫡堂妹[14]373-375;其三妹嫁给举人张琮第五子张其镇[14]375,张琮是张其镃胞叔[20]407。周瑞清的妻子况氏为况祥麟孙女、况洤女、况桂桢胞妹[22]308。这些家族也基本能与桂林科举大家族产生联系,利于小科举家族的发展与影响力的扩大,可谓是一举两得。
综上所述,《清代朱卷集成》中有着大量的人物史料、科举史料,利用其履历进行挖掘归纳分析,可以了解清代桂林科举家族的地域性、 社会影响、文化创作以及科举家族在婚姻、 仕宦等各方面情况。一方面,清代桂林作为广西的首府,是全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全省科举文化最为集中的区域,清代广西4 个状元陈继昌、龙启瑞、张建勋和刘福姚都是出自桂林,为桂林科举家族繁荣发展提供了环境氛围,这是外部因素。另一方面,桂林的许多科举家族有着较为殷实的经济基础,并且都崇尚科举功名、重视族人教育,通过大量的族人培养,考取功名,反哺于家族的发展、扩大家族的利益,这是内因。同时,各个科举家族的发展又带动了桂林,甚至广西的文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