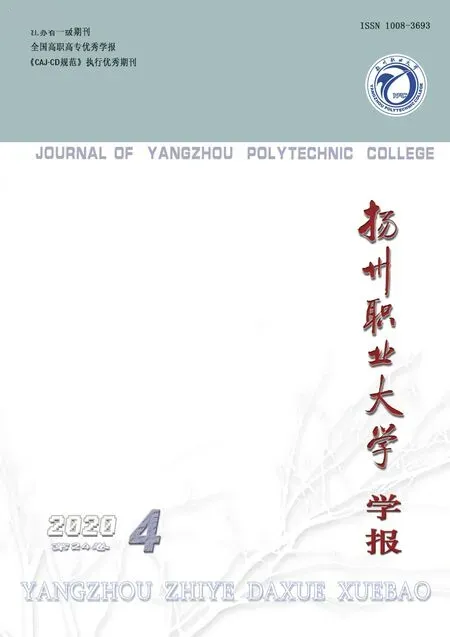《扬州画舫录》中女性群像掠影
2020-02-15尤微
尤 微
(扬州职业大学, 江苏 扬州 225009)
李斗,字北有,号艾塘,扬州仪征人,才情隽茂。虽幼年失学,疏于经史,却好游山水,广交诸方好友,通诗歌文赋、音律、曲艺,亦懂建筑工造、数术和历法,是一个博学多才、“文理兼修”的才子。李斗生活于清中叶的扬州,乾隆年间,扬州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运河水陆的交通优势,发展成为一座依托南北经贸往来而繁荣显赫的商业城市,资本融汇、巨贾云集,也因此极大推动了扬州文化艺术的蓬勃发展。这盛极一时的繁华给李斗创作《扬州画舫录》提供了绝佳的历史机遇,在这部十八卷的文人笔记中,李斗充分发挥了他的灵性和特长,“时泛舟湖上,往来诸工段间,阅历既熟,于是一小巷一厕居,无不详悉。又尝以目之所见,耳之所闻,上之贤士大夫风流余韵,下之琐细猥亵之事,诙谐俚俗之谈,皆登而记之”[1]5。
《扬州画舫录》自乾隆六十年(1795)刊印以来,以丰富的信息量和诗意的表达受到读者广泛推崇。纵观全书,扬州城的繁盛既带着文人骚客的墨香,也饱含士农工商的烟火气,从乡野到市井,从琴曲戏文到街谈巷议,芸芸众生像中,也出现了许多女性的身影:她们有的是幼年学戏的戏子名伶,有的是茶肆饼铺的勤劳老板娘,有才色双全的名妓,也有身世坎坷的小妾,还有贞妇、烈女,甚至还有走街串巷的江湖奇人。学界目前尚未有针对此书中女性形象的整理,这些女子群像,有百种面貌,亦有万般喜悲;她们是扬州城无比灿烂的烟花,也是扬州城“无名”的共建者。从这些女子的经历中,我们幸许能一窥清朝盛世之下女性的命运。
1 名伶与歌女
作为以商业经济支撑起来的城市,扬州文娱行业的繁华也是自古有之。乾隆年间,无数女性的身影活跃在扬州的画舫、戏班和青楼当中,将白天和黑夜都点缀得熠熠发光。在《扬州画舫录》中便有不少这些戏班成员的身影。
在《扬州画舫录》卷五《新城北录下》中,李斗大篇幅介绍了扬州城当时的戏班,既有本地富商私人招募的戏班,也有在全国巡演的流动性戏班。例如天宁寺、重宁寺拥有准备和演出“大戏”的场地和班子,所谓大戏,主要“演仙佛、麟凤、太平击壤之剧”[1]57,而两淮的盐商则常蓄花、雅两部,雅部即为昆山腔(昆曲),而花部则汇集各地的唱腔,包含京腔、秦腔、梆子、二簧等等。扬州在当时是全国曲艺文化的一大中心,吸引了很多地方的戏班来此驻扎演出,与之相应的,蓬勃的文化市场吸引了更多的游客和戏迷慕名而来,推动各戏班间不断增进演出水准,开拓创作思路,提升名角待遇,形成了良性的文化市场运作体系。
封建社会的传统戏曲舞台,一般是禁止女子登台演出的。古代女子学戏并演出,大多见于富贵人家开设的家班,入这类戏班的女子大多年幼而貌美,嗓音清丽婉转,身段灵活窈窕,因为她们的价值更多在于取悦主人,而不是传承技艺,比起演员,她们的身份更接近于“家妓”。到了清朝,统治阶层为了正良俗、清风气,这类私人戏班女乐在清康熙初年被取缔,市井之中也几乎看不到女性戏曲演员的身影,直到同治和光绪年间,京剧戏班才出现了以少女演员为主的“髦儿戏”,但女性出现在舞台上的事实还是会受到主流的歧视。随着社会礼教约束的不断加强,清代大部分女性不仅不能演戏,连出门去看戏都被视为“不问女红”“有伤风化”而被明令禁止。但在乾隆年间,在扬州小秦淮一带,却出现了专招女子唱昆曲的戏班:
顾阿夷,吴门人,征女子为昆腔,名双清班,延师教之。……班中喜官《寻梦》一出,即金德辉唱口。玉官为小生,有男相。巧官眉目疏秀,博涉书籍,为纱帽小生,自制宫靴,落落大方。小玉为喜官之妹,喜作崔莺莺,小玉辄为红娘;喜作杜丽娘,小玉辄为春香,互相评赏。……庞喜作老旦,垂头似雨中鹤。鱼子年十二,作小丑,骨法灵通伸缩间各得其任。……秀官人物秀整,端正寡情,所作多节烈故事,闲时藏手袖间,徐行若有所观,丰神自不可一世。康官少不慧,涕泪狼藉,而声音清越,教曲不过一度,使其演《痴诉点香》,甫出歌台,满座皆叹其痴绝。瞽婆顾蜨(蝶),粥其女于是班,令其与康官演《痴诉》作瞎子,情状态度最得神,乃知母子气类相感,一经揣摩,变成五行之秀。申官、酉保姊妹作《双思凡》,黑子作《红绡女》,六官作《李三娘》,皆一班之最。…是部女十有八人,场面五人,掌班教师二人,男正旦一人,衣杂把金锣四人,为一班。赵云崧《瓯北集》中有诗云:“一夕绿尊重作会,百年红粉递当场。”谓此。[1]107-108
在清朝普遍禁止女子演戏和观戏的风气下,女性演员出现于扬州的曲艺舞台上,并且收获观众好评,一方面能看出扬州当时文艺风向十分先进,风气相对比较开放和包容;另一方面,当时能够留在扬州成为名角、并被李斗记录进《扬州画舫录》的这些女子本身也有异于常人的出挑之处,她们以自身的才华或者突出的个性吸引了人们的目光。
同样作为在公众场合抛头露面的演出者,小秦淮的歌女也是扬州一绝。
自龙头至天宁门水关,夹河两岸……歌喉清丽、技艺共传者,则不能枚举。如白四娘者,扬州人,因县吏朱某曾拯其难,后朱缘事几置法,伊倾家谋救,得充边远军,不至死。[1]107
李斗不光关注歌女们的姿色与歌喉,也注意到了这些女子的个性和品质,白四娘就是一位非常典型的江湖儿女,虽出身低贱,但品行不俗,行走江湖以义气当先,而不是唯利是图,在恩人遭难的时刻能够挺身而出倾力相救,李斗对这样的女子也是赞叹有加。
陈四俗呼为盐豆子,有女梅梅,年十四,真绝色,后为有力者购去,冀北之群空矣。[1]107
歌女和戏子,都属于封建儒家社会“下九流”的行当,从事这些职业的女性虽站在各自的舞台上受到无数观众的青睐,但本身很容易被时间的“浪潮”抛弃和遗忘。没有李斗的记录,也许后世便很少有人能够知道这些女子,她们非常年幼的时就要辛苦学艺,十一二岁便已登台演出,随着戏班剧团到处漂泊,有人年纪轻轻便被人买走,或许是去给人做妾,或许是去下一个戏班落脚。身世浮沉辗转流离,命运都不在自己手中,她们稚嫩或沧桑的咿呀啁哳声,却成为当时扬州城繁华热闹的市井组曲之一。
2 画舫青楼的妓女
歌楼妓馆,多在小秦淮和虹桥。当时扬州在虹桥一带有诸多画舫,一般画舫普通客人便可以租用,主要是在市或会(如正月财神会市、三月清明市、六月观音香市、七月盂兰市等等)的时候供游人登船赏玩。画舫又分堂客和官客,其中堂客指的是妇女,当时妇女也可登船观光游览:“妇女上船,四面垂帘,屏后另设小室如巷,香枣厕筹,位置洁净。船顶皆方,可载女舆。”[1]133有的画舫没有炉灶,饭店甚至还能提供“送外卖”的服务(即“野食”,也叫“饷”),游客可以在城中酒肆订酒菜,饭馆每晚在河堤上将酒菜分送到各个船只。扬州城商业经济的发达,由此可见一斑。
而妓馆也会买棹湖上,以衣妆和堂客船相区分。妓馆的画舫上,随侍“大抵梳头多双飞燕、到枕松之属。衣服不着长衫,夏多子儿纱,春秋多短衣,如翡翠织绒之属;冬多貂覆额、苏州勒子之属”。“船首无侍者,船尾仅一二仆妇。游人见之,或隔船作吴语,或就船拂须握手,倚栏索酒,倾卮无遗滴。甚至湖上市会日,妓舟齐出,罗帏翠幕,稠叠围绕。”[1]138妓馆的画舫,颜色更加绚目,装扮也更加繁复而奢靡。
以烟花之地闻名的扬州,娼妓有官娼和私娼之分。这一类女子也是李斗着墨颇多的,不光留下了她们的名字,李斗还记录了其中一些女性的生平和经历,鼎鼎有名的是妓中才女苏高三和顾姬。苏高三即苏殷,扬州名妓,住二敌台下,冰雪聪慧,盛名在外。据记载,一日,林道源与人校射净香园中,苏殷在一边旁观甚久,揎袖上前请射,三发而三中。林子因作诗记之,一时间和诗者有上百人,阮元亦和诗:“走上花裀卷翠裘,亭亭风力欲横秋。眉山影里开新月,唱射声中失彩球。好是连枝揉作箭,拟将比翼画为侯。何当细马春愁重,银蹬双双著凤头。”[1]105苏殷的休憩之所挂着这样一幅联句:“愧他巾帼男司马,饷我餐盘女孟尝。”题写此联的人是谁李斗未加以记载,而将西汉辞赋家司马相如和战国四君子之一孟尝君与苏殷相提并论,可以想象这位扬州名妓当时人气和声望之高,且在其住所出入集会者多为达官显贵,想必定是颇有独到的才华和人格魅力。可惜这位心气颇高、才学过人的奇女子却是红颜薄命,病中,她自画兰竹帐额,并题绝句:“袅袅湘筠馥馥兰,画眉笔是返魂丹。旁人慢凝图花谱,自写飘蓬与自看。”[1]105在这位女子心中,自家住处再多往来客去,自身依然是孤寂的,年未及三十便病死了。
另一位名妓顾姬,字霞娱,也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女子,尤工词曲,擅解诗文。李斗记载,钱湘舲于谢未堂司寇公席中品题诸妓,以杨小保为女状元,霞娱为女榜眼,杨高为女探花。《扬州画舫录》中存有赵云崧的一首赞诗:“酒绿灯红绀碧花,江乡此会最高华。科名一代尊沂国,丝竹千年属谢家。拇陈酣摧拳似雨,头衔艳称脸如霞。无双才子无双女,并作人间胜事夸。”[1]111说的正是顾姬。
李斗也如实记载了一些妓女的离奇身世和坎坷经历。例如解银儿的故事:一日中秋,诸妓在园中拜月嬉戏,有一教坊乐师方张仙称自己在此工作三十年,能够凭借人影来识辨是谁。诸妓兴致盎然便请他试一试,而当解银儿隔窗经过,方张仙却看到一个长颈长腿的男子紧随其后,并且在男子身后还有一个一丈多高面目凹凸的怪人,裸身光腿,用拳头殴打前面的人。当时已是深更半夜,院中已没有其他男人,于是方张仙大为惊恐翻窗而逃,并将所见之事告诉了其他妓女。解银儿听说这件事后顿时潸然泪下,自言曾有一位公子暗中花五千金向自己养母立下契约要买自己为妾,当时解银儿已有两个月身孕,而公子的族人正巧在那时让其回家,于是公子对解银儿说:“你等我三年,如果我没有再回来,便听凭你自行安排,唯有肚子中的孩子不可受到伤害,否则我死了也会化身厉鬼跟着你。”然而解银儿未能达成这个誓约,又听闻方张仙的诡异见闻,身心恐惧,于几十天后呕血而死。民间传说中的灵异故事往往具有悲剧的内核,而与人情爱相关的坊间奇谈往往带着诡谲色彩和宿命论,也因此更为人所津津乐道。解银儿的故事以文人笔记的形式流传下来,侧面记录下了当时女性作为男性附属品、对主宰自身命运的不可见的制度、权力的崇拜与畏惧。或许读者会将银儿的死与公子临行前的话语相联系,而银儿本人对五千金的卖身契和公子的口头约定是持何种态度已不得而知,无形的性别和阶层的矛盾转化成为了一方“背信弃义”并遭至灾厄的结果。
《小秦淮录》还记录了一位较为特殊的女子,她叫许翠,字绿萍,是当地经营土娼生意的王天福家豢养的小妾,说是妾,其实这家人是预备将她当做暗娼来经营生意的,许翠的出身可以说是低到了尘埃里。年轻貌美的她受到了不少人的垂涎,十五岁时便有人愿花一千金买下她,许翠执意不从,不管主人家如何打骂,她“矢志更坚”,反令客人对其敬佩有加。待许翠十九岁时,王家来了一个年轻漂亮又富有的贵公子,经常往来做客,但从没有过出言轻薄冒犯许翠,许翠因此心生爱慕。后王家因金钱纠纷,被告逼良为娼而入狱,许翠在这位公子的帮助下得以逃脱,也由此开始了颠沛流离的漂泊生活。先是前往江宁,没过多久被一个贵公子强逼胁迫,焦急之下许翠匆忙逃跑,一路不仅饱受疾苦和曲折,还要不断提防着诸如收留自己住宿的主人、搭载自己过河的船家、以及不断追索自己的贵公子的爪牙等等不怀好意的人对自己钱财和美色的觊觎。许翠数次凭借聪明机智脱离险局,面对苦苦纠缠只想占有自己的贵公子,许翠利用缓兵之计,骗贵公子先去找喜轿来抬自己,借这个空档挣脱,并当众明志道:“我虽是娼妓之家出身,但我不会忍受这种蛮横无理的威胁。”并碎瓯而刎,不惜以命来抗争不公。历经磨难的许翠似乎是看清了凡俗人心的种种丑恶,也不再有烟花之意,最终舍弃了身外之物,遁入空门,长斋绣佛。许翠是《扬州画舫录》里非常罕见的拥有独立传记的女性,她出身低微,但生性刚烈,并且敢爱敢恨,也是女性中为数不多的不信命、不认命、只身反抗男性强权的奇女子。许翠一生接触过许多人,人们当她是一件商品,是靠金钱和暴力就能随意支配和玩弄的漂亮玩具,她却能够在这凡尘中保持自我,在一次又一次的危情中凭借冷静和机智转危为安,光凭这一点意志在那个时代便远超其余同性,也因此受到了李斗的关注,李斗通过一篇单独的人物小传表达出了对这位天生丽质又聪慧过人女子的佩服和叹惋。
虽是以男性的视角去记叙和品评这些风尘女子,然而李斗并未讲述群妓的那些脂粉闺趣和香艳轶事,而是如实记录下她们的艺名或闺名,记录下她们或美好或沉重的人生经历,记录下她们年轻时最美的姿容,记录下她们可贵的人品和才华,留给后人感慨思考。
3 贞妇和烈女
在《扬州画舫录》的女性群像和事迹中,李斗着重收集的,还有好些贞烈女子的故事。在卷十五《冈西录》中,李斗转载了清代经学家焦循的两篇文章——《贞女辩上》与《贞女辩下》。起因是为一位巴姓女子,这女子与张绪增的儿子定了亲,然而不幸的是“许嫁未亲迎”,刚许婚未嫁,未婚夫便过世了。这位巴贞女毅然决定继续过门,并代为抚养前妻之子,视如己出。巴贞女的事迹在当时引起了一番讨论,有人便援引归有光的一篇《贞女观》来反对女子这样“守贞”的风气。在《贞女观》这篇文章中,归有光以男性知识分子身份在封建时代明确提出了对“女子订婚而未嫁,夫死则终身应守寡甚至自杀以殉情”这类做法的强烈反对。在宋明理学盛行的时代,归有光的此番言行无疑是非常罕见的,当时社会上下不遗余力地宣扬女子节烈之重要,然而归有光却认为这种行为“乖阴阳之气”“伤天地之和”,并不符合“天地之大义”,自然也不符合儒家思想和先王之礼。
而在焦循看来,贞女烈女的宣传教化是大有必要的,他反驳归有光说古代无未嫁而守寡的烈女这一观点,认为古代兕先氏、召南申女、卫宣夫人等都是贞女的典范;而且当代的烈女之所以数量比古代多,是因为当代议婚时间早,到成礼时间往往要过很多年,因此中途时常会有意外发生,但女子只要订了婚,接受了聘礼,立下婚书,就需要行夫妻之名分,而不是等办完婚礼才有夫妻之实。
李斗在《扬州画舫录》中引用焦循的两篇《贞女辩》,则是站在了归有光的对立面来反驳当时反对巴贞女的言论,力图维护世俗礼教,可见李斗的女性贞烈观与他的友人焦循是相近相通的。
李斗无疑是在为这项礼教辩护,《扬州画舫录》中录入了数位“节妇”“烈女”的姓名和事迹,她们无一不受到了当时官方与公众的普遍认同,作者李斗也对这些女子的行径深感赞赏。
如《新城北录》里孝子妻节妇俞氏,在丈夫过世后,俞氏对婆婆隐瞒丈夫去世消息,并尽心尽力服侍她,“出则麻衣絰带,哀毁尽礼;入则易服婉容,躬亲汤药,母遂康豫如平时。……母日倚门望儿,节妇辄先意承志,百方慰藉,如是二十年”[1]40。在没有能够为夫家生养孩子的情况下,俞氏更加严格地恪守礼教,“养异姓女,赘婿于家,年益老,礼法益修谨。”[1]40此外,李斗还将坊间传闻“雷神奉天帝旨意,嘉奖节妇俞氏,接其飞升上天与丈夫相聚”的小故事也记载进了书中,认为俞氏这样的做法是符合了天道,因此应当成为众女子的模范。
卷七《城西录》记载了郑侠如之女郑贞女的事迹,郑贞女幼年定下过娃娃亲,不料未及过门,未婚夫为救父而死,郑贞女立志以身相殉,在亲族送其过门之后半年,因悲哀成疾病亡,年方十八岁。
在卷十六《冈西录》中,李斗更是以较大篇幅讲述了蜀冈西峰“五烈墓”和侧边王氏贞烈祠的由来。“五烈墓”是为五位烈女而设,池烈女,订婚未嫁而夫死,不愿改许配夫弟,自缢而死;霍烈女,同样订婚未嫁而夫死,自杀以殉。在这二人之后,又有孙大成之妻因为遭客人裸身调戏,自缢以明节;项起鹄妻程氏,夫死,守节一年后,自杀;江宁陈国材妻子周氏,夫死后绝食而亡。李斗所记录下的“五烈”事迹,均是官方定性,并加以褒奖的真实事例,由此不难看出当时对于女性节烈观的要求是非常严苛的,而且不少女性也以死明节为荣。
“五烈墓”的侧旁有一王氏贞烈祠,据李斗记载,王氏之贞烈又与五烈女的贞烈有所不同,王氏的丈夫郭宗富开铺行商,借贷了邻人钱款,邻人借此谋求与王氏相亲昵,王氏转告丈夫,而丈夫却因为借人钱财理短,劝妻子王氏忍气吞声,于是王氏在愤怒之下上吊自杀。后案情大白,王氏被移葬五烈墓之侧,祀之于贞烈祠。
4 扬州市井的女性
除上文提到了那些女性,书中还记载了在街头巷尾靠卖茶致富的茶肆女老板林媪和林姑。女儿林姑清丽可人,声音动听,母女二人靠着勤劳的双手和热情的待客之道将茶肆生意经营得红红火火(《小秦淮录》);乔姥则在虹桥长堤码头上布置长桌,人称“乔姥茶桌子”,露天卖茶,在旺季游人如织的时候,客人喝完茶未付钱就让位,也有周边熟客每日专候乔姥摆茶桌,喝着茶聊天能坐很久很久(《虹桥录下》);还有曹三娘、珠娘等精通武艺、巾帼不让须眉的女子——面对侮辱自己尊严的男性,曹三娘不卑不亢,用自己的实力四两拨千斤,为自己赢得一片叫好声。珠娘原是青楼舞女,后嫁给徐五庸为妾,开始习武,尤其打拳打得好,人们愿称其一声“侠女”(《小秦淮录》);还有专门替人接生的稳婆,开设“王氏收生堂”,凭借着自己的一技之长和丰富经验,于六十岁高龄刻印《达生编》刊行于世,此书后来帮助很多女性和医生了解妇女产前、产中、产后的注意事项和小产、接生、妇婴急救等的医学技巧,客观上减轻了古代医术不发达时生育给女性造成的巨大伤害,提升了妇婴存活率(《小秦淮录》)。从这些记录中不难看出,李斗选取的这些“女性群像”都是些寻常却又着实“异于”平凡人的女性,这些女性得以在扬州生存下去,除了有自身的技能才艺(天生姿色也是谋生手段的一种)的因素,还有扬州这座城的“存在”构成了一系列大前提:开放包容的整体氛围带来了充足的客源,东西南北的文化在这里碰撞交融,见多识广的市民对审美有着更高同时更宽阔的视野。
上文中提到了李斗的“贞烈”观,毫无疑问,他的观念和焦循的观念在今天看来都是有悖人道主义的,是历史文明的一大倒退;但若是将目光放在当年,回到当年的时代背景下,在那时,以绝对的男权话语来建构女性生存的空间和女性生存的规则,恰是那个时代的特点之一。在讲述青楼女子、戏子名伶的故事时,李斗使用了当时男性对女性惯有的“审视”目光——他从不吝啬华美的辞藻,去形容和品评每一个女性的容貌、声音、身形、仪态和才艺,并且将遴选出的女性用“胜”“好”“次”等等词汇加以“分层”和“标价”,以此来描述和彰显这些女性的“价值”;而那些出身清白的良家女子为守贞守节而奉献青春乃至生命,李斗认为她们是“杰出”“优秀”的女性,正是凸显出世俗对“女性美”的又一层价值判断:“美好”的她们必当遵守社会对女性的种种规定——这些规定自然也是由男性创制,并且随着时代推进而变本加厉,甚至女性本身也发自内心去认可这些规定,用不近人情的、近乎严苛的要求约束己身,一旦有违逆,女性群体最先不会原谅离经叛道的同胞,认为她们是给女性群体抹黑,不配拥有“贞节牌坊”和“贞烈祠”。
李斗笔下的女性叙事隐隐呈现出了一种开放和包容,而这种包容无疑是“高高在上”的,来源于当时社会世俗对男性的公众话语权表示绝对肯定和认同的一种自信,不过即便如此,李斗的文字还是做到了一份可敬的真实和温柔。在《自序》中,李斗便坦言自己并非寒窗苦读的寒门子弟,好游山玩水,虽才艺丰富、眼界开阔,然而并无功名在身。以阶级而言,李斗与大部分市井人物并无二般,自然在书写时更加容易流露出些许共情;同时,李斗也是一位出众的词曲作家,长年游历和与戏班青楼打交道的经历,让这位才子对各种才华横溢、冰雪聪明而生之多哀的底层女性多了一份惺惺相惜;此外,李斗在《扬州画舫录》里所著录的人物,都是李斗认为经历异于常人的,记录这些“异闻”也是李斗成书的目的之一,于是,扬州城内这些敢在市井之中抛头露面的和坊间口口相传的“奇女子”们自然不会被李斗所遗漏。
男性对女性的轻视和偏见往往源于社会权力分配的不公。清代的社会权力严重倾斜向男性,社会利益绝大部分也由男性掌握。文洁华教授认为,中国帝制晚期,美丽而忧伤的女性形象是慑于儒家礼教正统和当时社会意识形态的产物。[2]125在男性主导文化价值的大背景下,被男人们高高捧起、赞为“色艺双绝”“优风良俗”的女性的“美”并非女性自我觉醒价值的主动表达,而是男性权力在家庭伦理、社交方式与经济文化领域的不同呈现,这种呈现与社会制度与内外秩序紧密相关联。李斗笔下固然有着许翠这样果敢抗争的女性,但“许翠”有且仅有一人,并且将只身青灯向古佛视作对凡俗诸多丑恶的回避,依然没有能够彻底冲破性别和阶层的樊笼。李斗能够将自己的目光投放在那些平凡朴素、努力生活的市井女性身上,用诗性而不淫猥的语言去写作她们,不啻为立意上的一次开拓,但囿于自身所处的阶级和性别立场,女性文化表达必然是存在局限性和诸多缺憾的。
5 结语
总体而言,当时扬州城相对宽松自由且富庶的经济环境吸纳了各色女性来此谋生,她们谋生的手段也是多种多样,然而她们当中大多数均受困于长期的文化习俗和特殊时代之下传统礼教,没有能够发展出属于女性自己阶层的普遍意识形态和大众文化空间,还只是依照生存的本能和“他者”的规训而存在。《扬州画舫录》中所载的大部分女性都还在为生计所劳碌,她们依然处在时代的边缘,大多没有力量能够执掌自己的人生,在胭脂与金粉的浪涛中挣扎寻觅着人生的方向,她们独特的生存方式共同铸成了扬州城的烟柳繁华,而她们的“美”也无一不在诉说着盛景之下普通女性生存的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