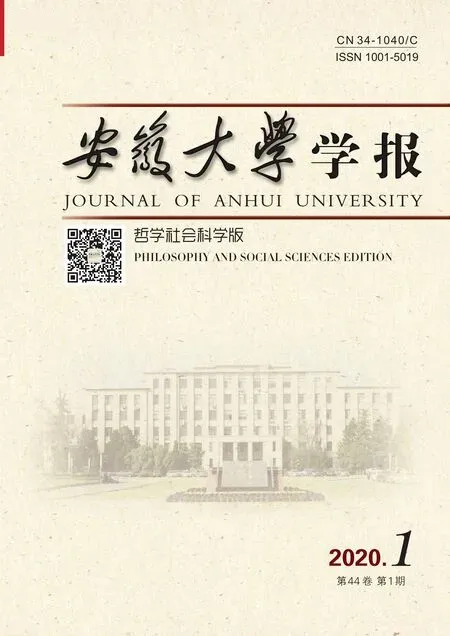明清之际王时敏家族的戏曲活动与江南戏曲生态
2020-02-14郭英德
郭英德
一、“绵绵瓜瓞”:剧迷家族的文化传承
在明清之际,苏州府太仓州(今属江苏苏州)的王时敏(1592—1680)家族是江南著姓望族之一(1)参见吴仁安《明清江南著姓望族史》第二章第八节,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9~166页。王时敏生平,见王宝仁《奉常公年谱》,北京图书馆编:《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66册,影印清道光十八年(1838)太仓王氏刻本,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第327~450页。。而王时敏家族的戏曲爱好则有如“绵绵瓜瓞”,一百数十年传承有绪,延续不断,特别是与明清之际盛行于江南的昆曲艺术缔结了密切的因缘关系(2)本文关于王氏家族戏曲活动的论述,参考陆萼庭《王抃戏曲活动考略》,见其《清代戏曲家丛考》,上海:学林出版社,1995年,第64~76页;刘水云:《明清家乐选考·王锡爵家乐》,见其《明清家乐研究》附录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523~525页;杨惠玲:《太仓王氏家班》,见其《戏曲班社研究:明清家班》下编,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71~273页;周巩平:《江南曲学世家研究》第六章第二节《娄东太原王氏家族(王锡爵家族)》,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3年,第218~240页;刘加华:《明清太仓王氏家族戏曲活动研究》,厦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
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王时敏的祖父王锡爵(1534—1611)致仕家居(3)王锡爵生平,见王衡、王时敏《王文肃公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52册影印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太仓王宗愈刻本,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第1~212页。,从此蓄养家班,醉心词曲,常常邀请亲友,在府中听曲观剧。苏州著名曲师赵瞻云(名淮,字源长),是“曲圣”魏良辅的弟子,擅长歌唱,王锡爵专门延请他为家班教习(4)参见陈继儒《晚香堂小品》卷八《赵瞻云传》,上海:贝叶山房,1936年,第301~302页;王瑞国:《赠曲师苏昆生序》,王祖畲等纂:《太仓州志》卷二七《杂记》上引,《中国方志丛书》第176册,影印民国八年(1919)刻本,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5年,第2024页。。魏良辅的女婿张野塘,善弹三弦,也曾为王锡爵门下客,教家僮习曲练唱(5)参见叶梦珠《阅世编》卷十《纪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221~222页。。王氏家班尤其喜好搬演新剧, 万历三十五年(1607)曾演出汤显祖《牡丹亭》传奇(6)参见徐朔方《晚明曲家年谱·皖赣卷·汤显祖年谱》,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427页。。
王锡爵胞弟鼎爵(1536—1585)也性嗜声乐,在歌坛酒社间从容自得(7)王锡爵:《先弟河南按察司提学副使家驭暨妇庄宜人行状》,王衡、王时敏编:《王文肃公全集·王文肃公文草》卷一一,《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36册,影印明万历间王时敏刻本,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421页。,并将这一癖好“传染”给王时敏的父亲王衡(1561—1609)(8)王衡生平,见徐朔方《晚明曲家年谱·苏州卷·王衡年谱》,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347~392页。。王衡擅长编写剧本,他编撰的《郁轮袍》《没奈何哭倒长安街》《真傀儡》《裴湛和合》等杂剧,流传甚广。时人陈继儒称赞他:“游戏而为乐府诗余,即宋元当行家无以过也。”(9)陈继儒:《太史辰玉集叙》,王衡:《缑山先生集》卷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78册,影印明万历间刻本,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556页。沈德符也称许他:“大得金、元蒜酪本色,可称一时独步。”(10)沈德符:《顾曲杂言》,《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四册,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第214页。
王时敏秉承家风,一生深嗜戏曲,吴伟业称之为“赏音之最”(11)吴伟业:《与冒辟疆》之五,冒襄辑:《同人集》卷四,《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85册,影印清康熙间刊刻、乾隆间修订冒氏水绘庵刻本,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164页。。王时敏虽然没有像他父亲王衡那样创作戏曲作品,但也有散曲二套传世,即【步步娇】套《西田感兴》、【二郎神】套《春去感怀》(12)王时敏:《王烟客先生集·西庐诗馀》,《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册,影印民国五年(1916)苏州振新书社铅印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609页。。
有其父必有其子,家族文化的传承是源远流长、根深蒂固的。王时敏有九个儿子,也大多秉承“剧迷”家风,不仅日常在家中听曲,还常常外出观剧,以此为乐。如顺治五年(1648),长子王挺(1619—1677)点充机户,“乃借此为名,扁舟不时到郡,每去必经旬,寻反观剧,反以此为乐境”(13)王抃:《王巢松年谱》,《丛书集成续编》第37册,影印民国二十八年(1939)江苏省立图书所编《吴中文献小丛书》本,上海:上海书店,1994年,第794页。。次子王揆(1620—1696)到江苏扬州观看《玉簪记》演出,写下《广陵赠歌者》七绝二首(14)徐釚:《本事诗》卷一一,《续修四库全书》第1699册,影印清光绪十四年(1888)邵武徐氏刻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68页。。八子王掞(1645—1728),与同乡剧作家沈受宏为友,常常流连于“歌场妓席,月榭花棚,觥筹谈笑”(15)王掞:《白溇集序》,沈受宏:《白溇集》卷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67册,影印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刻增修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471页。;他与其五兄王抃(1628—1702),“相遇最厚,凡听歌进酒之时,必招余在座”(16)王抃:《王巢松年谱·总述》,第790页。。九子王抑(1646—1704)更是继承曾祖和祖父的家业,于康熙二十年(1681)合成家班,屡有演出(17)王抃:《王巢松年谱》,第802页。。
王时敏诸子中,最有戏曲成就的“剧迷”是五子王抃(18)王抃生平,见盛敬《太学巢松王君传》,《王巢松年谱》卷首,第790页。参见陆萼庭《王抃戏曲活动考略》,《清代戏曲家丛考》,第64~76页;秦婧:《明末清初诗人王抃研究》,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王抃继承祖父王衡的传统,擅长剧本写作,其三兄王撰(1623—1709)称他“曲谱宫商格调新”(19)王撰:《挽诗十首》之四,王抃:《王巢松年谱》卷末附录,第804页。。从康熙十二年(1673)起,十年间,王抃先后编撰杂剧《玉阶怨》《戴花刘》,传奇《筹边楼》《舜华庄》《鹫峰缘》《浩气吟》《一朝泰》等,大多由家班演出(20)盛敬:《太学巢松王君传》,王抃:《王巢松年谱》卷首,第790页。。
从文化传统来看,明清之际的王时敏家族作为“剧迷”,并不仅仅将戏曲作为一种娱乐性艺术来观赏,而更多的是将戏曲活动作为一种“文明”的艺术符号。王时敏的曾祖父梦祥(1515—1582)就喜好“玩梨园戏”,曾说:“此最琐琐,亦足以观成败,见哀乐。”(21)王锡爵:《先考爱荆府君行实》,《王文肃公全集·王文肃公文草》卷一一,第413页。王锡爵以赞赏的笔调记录他父亲这段“剧评”,因为他明白,他父亲表达的是儒家“小道可观”的传统文艺思想(22)《论语·子张》:“子夏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论语注疏》卷一八,《十三经注疏》,第2531页。。由此可见,王时敏家族坚信,守望戏曲便是守望文明。而文明的守望,不仅允许痴情不改,而且应该传承不绝,因为这是文化世家的根基。
二、“丝竹陶写”:王时敏家族的厅堂演出
据王时敏的同乡好友吴伟业记载,王时敏晚年居乡时,除了绘画、作书以外,还常常“召集梨园老乐工,丝竹陶写”(23)吴伟业:《王奉常烟客七十序》,吴伟业著、李学颖集评标校:《吴梅村全集》卷三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781页。。因为家资雄厚,庭院宽敞,王时敏家族的戏曲演出场地大多是府第或园林的厅堂,而演出场合则大多是节庆与寿诞。明清之际的戏曲演出场所,有广场、寺观、水台、厅堂、茶楼等等,而文人士大夫的观剧活动更喜好厅堂演出,因为厅堂演出可以呈现更为高超的演出技艺。
早在崇祯十六年(1643),为欢庆元宵节,王时敏就曾请苏州名班至府第中演戏。当天演出的是折子戏,其中《炳灵公》一出(沈璟《一种情》中《冥勘》一出),名角宋子仪表演极其精彩,“观者无不叫绝”(24)王抃:《王巢松年谱》,第793页。。顺治三年(1646)春,王时敏延请琵琶名家白在湄及其子彧如,在位于苏州郊外的南园弹唱新声,同场观赏者有原中常侍姚在洲、吴伟业等。他们花下置酒,听弹琵琶曲,悲凉凄切,更忆及前朝旧事,不禁相与哽咽。吴伟业为此写作了《琵琶行》长诗(25)吴伟业:《琵琶行(并序)》,《吴伟业全集》卷三,第55~57页。。其后几年,由于遭遇天灾人祸(26)参见陈永福《明末清初乡绅经济生活的变迁——苏州府太仓州王时敏的事例研究》,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编:《北大史学》第15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51~181页。,王时敏家境窘困,少有演出。但是在顺治十八年(1661)以后,王时敏家族的厅堂演出又相当频繁。这一年八月十三日,是王时敏七十岁生日。正月初旬,亲朋子侄恳请“预祝”,“四方知交及诸戚党来贺者,接踵而至,开宴累日”(27)王宝仁:《奉常公年谱》卷三,第414页。。王家专门延请当地著名戏班“申府中班”到府中(28)关于申时行家班,参见程宗骏《明申相府戏厅家班考》,《艺术百家》1991年第1期。,“张乐数日。第一本演《万里圆》,时人黄孝子事,见者快心悦目,真千古绝调也”(29)王抃:《王巢松年谱》,第796页。。
家居常熟(今属江苏)的钱谦益十分敏锐地感受到,王时敏七十寿诞的家宴演剧,“非寻常燕饗而已,君子于是蒇国成焉,占天咫焉,又用以颂丰芑、歌燕喜焉,不可以莫之识也”(30)钱谦益:《王奉常烟客七十寿序》,钱谦益著、钱曾笺注、钱仲联标校:《钱谦益全集》第五册《牧斋有学集》卷二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949~951页。。钱谦益所谓“蒇国成”“占天咫”,称颂的是王锡爵“股肱国本,眉目清流”,“食报于子孙”;而所谓“颂丰芑、歌燕喜”,则揄扬的是王时敏“士食旧德”,即“故家遗俗,孟子盖三叹于易世,而况昭代之孙子乎?”
正是有见于此,钱谦益虽然年届八旬,未能亲身前来祝寿,却应弟子归庄、周云骧之请,撰写《王奉常烟客七十寿序》,以想象性的笔调描写王时敏寿宴演剧时的盛况:
升其堂,所藏弆而供奉者,神庙之宝章御札,如藏《河》《洛》之图,而抱鼎湖之弓也。御其宾筵,嘉肴旨酒,上尊养牛之殊锡,而郢醪蓬鲙之遗法也。考钟伐鼓,丝肉递代,歌钟二八,清商一部,元臣之所娱宾而送老也。巾车南园,其芍圃则谢家之红药,其菊篱则韩公之晚香;泛舟西庄,梧桐之萋菶者犹在,朝阳而鸣凤之羽,犹翽翽于高冈也。……凡百君子,与于燕会者,相与念国恩,仰旧德,颂丰芑而歌燕喜,忠孝之心,有不油然而生矣乎?
序文生动地描述了祭祀、酒宴、演剧、观赏的一系列活动。在全文结尾,钱谦益自道,撰写这篇“用史法从事”的寿序,是希望王时敏的子孙“亦将取徵诗史”,记录下“易世”的这一段精彩场景。于是,一场“济济多士”的厅堂演剧活动,便以其独具一格的文化风貌,铭刻在历史碑记上。
康熙二年(1663)仲春,王时敏延请著名曲家苏昆生,教习家僮演唱昆曲(31)王宝仁:《奉常公年谱》卷四,第420~421页。苏昆生生平,参见陆萼庭《苏昆生与昆腔》,《清代戏曲家丛考》,上海:学林出版社,1995年,第33~52页。。康熙四年(1665),同乡青年剧作家黄祖颛(字顼传)编撰《迎天榜》传奇,王时敏“命名优谱其声词”,召集当地名人雅流,一起在厅堂观演。“每一升歌,辄举座起舞,目顼传。顼传岸帻踞上座,引满而酌,一时人以为荣”(32)陆世仪:《迎天榜·序》,黄祖颛:《迎天榜》传奇卷首,《古本戏曲丛刊五集》影印清康熙间刻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黄祖颛(1633—1672),字顼传,康熙十一年(1672),同王抃一起北上应顺天乡试,病,卒于是年八月二十二日。。
康熙十年(1671),王时敏八十大寿,吴三桂的女婿王永宁,特地“携小优来演剧,里中颇为倾动”(33)王抃:《王巢松年谱》,第799页。。此后,王抃顾念父亲年事已高,“更思所以娱之”,从康熙十二年(1673)冬开始,就着手编撰一部又一部戏曲作品,由家班伶人在厅堂演出,“以博高堂欢”(34)盛敬:《太学巢松王君传》,《王巢松年谱》卷首,第790页。。如康熙十四年乙卯(1675),王抃四十八岁,元宵节后,在九弟王抑的厅堂中,演出自编新剧《舜华庄》。次年丙辰(1676)八月,任职翰林院编修的八弟王掞请告归里,几位兄弟公宴于王抃住所鹤来堂,演出新剧《筹边楼》,观者如堵(35)并见王抃《王巢松年谱》,第800页。。
王时敏去世后,其家族的戏曲演出仍然持续不断。如康熙二十一年(1682)九月底,因丧服已除,在鹤来堂,由王抑家班演出《浩气吟》。其后全苏班又补演《鹫峰缘》,“诸优摹写尽致,颇得作者之意,亦一快事也”。康熙二十二年(1683),王忭兄弟又在鹤来堂演出《浩气吟》(36)并见王抃《王巢松年谱》,第802页。。
值得注意的是,在明清之际“传奇十部九相思”的时代风气中(37)李渔:《怜香伴》传奇卷末收场诗,《笠翁十种曲》,清康熙间刻本。,王时敏家族对戏曲观赏的爱好却与众不同,他们更属意于故事有本有原的历史剧或现实剧。据《王巢松年谱》等记载,王府所观演的剧目,如张凤翼《虎符记》、顾大典《葛衣记》、李玉《七国记》、黄祖颛《迎天榜》,及王抃《玉阶怨》《戴花刘》《舜华庄》《筹边楼》《浩气吟》等,都是历史剧;如李玉《万里圆》、王抃《鹫峰缘》等,则是现实剧。

三、“寄托写怀”:王时敏家族的剧本写作
对历史剧与现实剧的酷爱,实际已经成为明清之际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戏曲活动的一个重要的地域文化特征,不独王时敏家族如此。活跃在苏州一带的李玉、朱佐朝、朱素臣、张彝宣等戏曲家,都是编撰历史剧与现实剧的高手。与此相同,王时敏家族不但喜好观赏历史剧和现实剧,其剧本写作也体现出鲜明的历史精神和现实指向。王士禛称赞王抃剧作“不但引商刻羽,杂以流徵,殆可谓词曲之董狐”(41)王士禛:《分甘余话》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97页。。董狐是春秋时晋国太史,以秉笔直书著称于世,孔子称他是“书法不隐”的“古之良史”(42)《左传·宣公二年》,《春秋左传正义》卷二一,阮元:《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0年,第1867页。。王抃撰写的戏曲剧本,就大都充满着丰沛的历史感受和现实情感。他自称:“胸中傀儡,自当以热酒浇之,且杯在手中,正可以发摅胸臆,虽不敢自拟焦生,而其义则余窃取之矣。”(43)王抃:《自述》,《王巢松年谱》卷首,第791~792页。按此自述作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时人称他“寄托写怀,为词家所推重”(44)盛敬:《太学巢松王君传》,王抃:《王巢松年谱》卷首,第790页。。例如,盛敬《太学巢松王君传》记载:“(王抃)事太公,先事迎旨,已无不至。顾念春秋高,更思所以娱之,搜求古人,谓惟李文饶,文章才略,堪拟太公,遂于丙辰初夏,著《筹边楼》传奇,以博高堂欢。演之日,观者如堵,无不啧啧称孝。”(45)王抃:《王巢松年谱》卷首,第790页。“丙辰”为康熙十五年(1676)。据《王巢松年谱》记载,前一年四月,王抃已有意谱“李文饶事”为传奇。王鉴(字元照,号湘碧,1598—1677)得知后,特邀约他至染香庵,同老伶工林星岩商酌,“间架已定,因家中为病魔所缠,几及半载,遂至不能握管,束之高阁。直待次年始成”(46)王抃:《王巢松年谱》,第799页。按《筹边楼》传奇有清康熙间刻本,原中国国家图书馆藏,今未见。。
李文饶即唐人李德裕(787—850),字文饶,赵郡赞皇(今属河北)人。其父为中书侍郎李吉甫(758—814),因此德裕未参加科举,早年即以门荫补校书郎,历仕宪宗、穆宗、敬宗、文宗。至武宗时,入朝为相,执政五年,多有建树,拜为太尉,封卫国公。宣宗继位后,因位高权重,至贬为崖州司户,病逝于贬所(47)李德裕生平,参见傅璇琮《李德裕年谱》,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王时敏的仕途虽然未曾像李德裕那么显达,但他也是以门荫入仕,与李德裕相类。而且他胸怀远志,但最终仅官至太常寺少卿,可谓未尽其才。《曲海总目提要》卷二二“筹边楼”条评价道:“时敏,宰相之孙,以任子官清卿,不由科目。而李德裕乃宰相吉甫之子,起家门荫,为会昌名相。故抃以德裕比其父,盖为任子吐气,而借以称觞祝寿也。”(48)《曲海总目提要》,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967页。“任子”是汉代高官子弟凭借父兄官禄而得官的制度,后世借以称荫袭制度。王抃撰写《筹边楼》,正是善颂善祷,称扬其父的远大志向和经济才能,以彰显他的孝心。
筹边楼位于今四川理县杂谷脑河岸的薛城镇,唐文宗太和元年(830),李德裕任剑南西川节度使时创建。德裕在楼上四壁绘制地图,“按南道山川险要与蛮(南诏)相入者图之左,西道与吐蕃接者图之右。其部落众寡,馈餫远迩,曲折咸具。乃召习边事者与之指画商订,虏之情伪尽知之”(49)欧阳修:《新唐书》卷一八○,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331页。。这是李德裕“御戎守边”的一大举措。王抃的剧作以“筹边楼”命名,无疑隐含着对其父王时敏在明末时的政治抱负的认可和褒扬,深意自在言外。因此,时隔二十余年,王士禛还津津称道此剧,说:
吾宗鹤尹兄抃,工于词曲。晚作《筹边楼》传奇,一褒一贬,字挟风霜。至于维州一案,描摹情状,可泣鬼神。尝属予序之,而未果也。今鹤尹殁数年矣,忆前事,为之怃然,聊复论之如此,将以代序。且以见传奇小技,足以正史家论断之谬诬也。(50)王士禛:《香祖笔记》卷一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229页。
“维州一案”,指太和五年(831),吐蕃维州副使悉怛投降李德裕,宰相牛僧孺在朝中加以阻挠,以为唐朝方与吐蕃修好,相约罢兵,应当守信为上,以免吐蕃问罪。于是文宗诏李德裕,缚送悉怛归吐蕃,悉怛被诛于边境。此事李德裕终身以为恨(51)参见刘昫《旧唐书》卷一七四《李德裕传》,第4519页、4523~4525页;欧阳修:《新唐书》卷一八○《李德裕传》,第5332页。并见《旧唐书》卷一七二《牛僧孺传》,第4471页;《新唐书》卷一七四《牛僧孺传》,第5231页。。显然,娴熟于明清之际史事的王时敏家族和王士禛等人,很容易从“维州一案”联想到明王朝和清朝之间延绵多年的战事。所谓“一褒一贬,字挟风霜”,“描摹情状,可泣鬼神”,正包含着他们内心深切的朝代兴亡感伤。
而王士禛所说的“传奇小技,足以正史家论断之谬诬”,也道出了戏曲独特的文化功能。吴伟业评李玉等人的时事剧《清忠谱》传奇,也说:“而事俱按实,其言亦雅驯,虽言填词,目之信史可也。”“按实谱义,使百千岁后观者泣、闻者叹。”(52)吴伟业:《清忠谱序》,李玉等:《清忠谱》卷首,《古本戏曲丛刊三集》影印清康熙间苏州树镃堂刻本。王时敏家族在戏曲活动中回望历史,沉酣现实,借助于故事有本有原的历史剧或现实剧,更能激发起观剧者、评剧者“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的情感共鸣。于是,戏曲文本所蕴含的深刻的文化寓意,就在写剧、观剧、评剧活动中得以昭明显著。
同时,王抃的剧作也昭示出士人个体的牢骚情感。其友人黄与坚《巢松乐府序》评论道:
巢松王子,生长华胄,有轶群之才,所如不偶,将悒郁以终老。其牢落之概,具见于诗,而又措思于乐府。所著《舜华庄》诸本,靓深妍婉,则丽人之含情也;激卬慷慨,则老臣之挟策也;萧散超脱,则异僧之说法也;悲愤凄凉,则义士之捐躯也;困穷错愕,则薄夫之蹇遭也。才情所至,波诡云谲,乌能规规墨墨以测之?顾其载事也,直而不肆,怨而不伤,温柔敦厚,有诗教焉。此以乐府合于诗,巢松之所以特胜也。(53)王抃:《巢松集》卷首,《四库未收书辑刊》第8辑第22册,影印清钞本,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1999年,第392~393页。
在王时敏诸子中,王抃颇负才名。其生母徐夫人在世时,常说王抃出生前夜,自己梦见紫薇花开,芬芳可爱,兆示着儿子日后必成大器(54)王抃:《王巢松年谱》,第790页。。康熙二年(1663),吴伟业曾说:“太原诸昆仲,怿民为有用之才,必宜使之一遇。”(55)王抃:《王巢松年谱》,第797页。然而,王抃二十岁步入科举之途后,曾八次参加南闱、北闱乡试,屡遭败绩,最终也只是一介“国子生”。而他的家庭又变故频仍,长子兆新患严重精神病,长媳忽染怪症,次子兆建才庸质钝,老妻总闹别扭(56)参见王抃《总述》,《王巢松年谱》卷首,第790~792页。。数十年里,王抃一直穷愁潦倒,出乡不足以命世,居家不足以安乐,他不能不深深地恨叹:“一经犹在知谁托,四壁徒存强自支。”(57)王抃:《自叹》,《巢松集》卷三,第426页。此诗作于康熙二十三年(1683)。“名场得丧堪长叹,世路艰难已备尝。”(58)王抃:《邀潘凝祉司马小饮以诗见赠次答》,《巢松集》卷六,第448页。
王抃的戏曲作品,就是在这种心境下酝酿、宣泄而成的。叶燮评论道:“于是无聊感慨之概,任志之所往,假言语为发泄,以曲尽其致。于是天地万物,无不可供其陶铸,极其性情念虑之所之。”“昔三闾大夫不得于君,其忧愁之思,托之美人香草,思蹇修而不可得,无不藉夫妇以明志。怿民其亦此物此志也夫?”(59)叶燮:《巢松乐府序》,叶燮:《己畦集》卷九,《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44册,影印清康熙间叶氏二弃草堂刻本,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107页。对于王抃来说,戏曲活动无疑是士人认定个体价值、追问生存意义的最佳媒介。而他的朋友,如黄与坚、叶燮等,也在他的剧作中品读出他骚动不安的内心世界。所以康熙三十四年(1695)秋冬,太仓诸生毛师柱撰《王鹤尹邀观一朝泰新剧感赋》诗,感慨道:“世事谁能料,悲欢一曲中。泰来翰有日,钝极岂无功。谱处花生笔,看时气吐虹。当筵浮白者,拨触几人同。”(60)毛师柱:《端峰诗选》“五言律”卷,《四库未收书辑刊》第8辑第22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1999年,第671页。此诗作期和《一朝泰》剧作本事考证,参见秦婧《明末清初诗人王抃研究》,第10页。
四、“游于艺”:戏曲生态的营造与戏曲艺术的新变
孔子曾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这里所说的“艺”,指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戏曲艺术是“乐”之一支,自然属于“艺”的范畴,观剧便成为古人涵养道德、培植仁义、施行教化的重要媒介。清顺治十五年(1658)春,王抃撰《观剧歌》,写道:
春城杨柳千株绿,尽日游人看不足。歌舞高台竞赛神,自是吴中旧风俗。吴中风俗爱嬉游,月夕花晨次第收。翠阁呼卢消美酒,画船秉烛听清讴。娄江景物方萧索,地僻民穷偏海角。何处歌喉缥缈间,宝马珠帘恣行乐。九十春光花正开,香风弦歌逐人来。拍残檀板黄幡绰,拨尽琵琶曹善才。平津家乐时名重,老向侯门作供奉。就中声伎孰最优?依稀记得王与宋。绕梁裂石发新声,摹写当场更入情。老去徐娘还似少,亡来楚相却如生。芦管吹残法曲变,徵歌斗伎非吾愿。廿年不睹汉官仪,衣冠优孟还堪羡。君不见亚子功成百战身,自涂粉墨伴伶人。乐工子弟今安在,事业消沉碧草春。又不见上皇御宴《霓裳》作,蜀道归来尽非昨。空传一曲《雨淋铃》,梨园白发看花落。人生欢乐亦何常,赵舞秦讴枉断肠。漫湿青衫陪白傅,懒将误曲问周郎。虽然生长繁华地,时艰胜事应难继。屠龙逐鹿总徒劳,世路悠悠尽如戏。(61)王抃:《巢松集》卷一,第395~396页。此诗同卷稍后,有《悼亡妾六首》。按《王巢松年谱》,顺治十五年九月初四日,王抃妾李氏病故,“余有悼亡诗十六首”,第796页。故《观剧诗》当作于顺治十五年春。
《观剧歌》一诗借助于观剧者的感受,生动地描写了明清之际江南戏曲生态的营造与戏曲艺术的新变。在江南春天迎神赛社的活动中,王抃观赏戏曲演出,享受到“香风弦歌逐人来”“绕梁裂石发新声”的听觉愉悦,“摹写当场更入情”“衣冠优孟还堪羡”的视觉感受,以及“时艰胜事应难继”“世路悠悠尽如戏”的情感激荡,真可谓百感交集,意味深长。
首先,从《观剧歌》中“拍残檀板黄幡绰,拨尽琵琶曹善才”的表述,我们可以推知,王抃所聆听和悦赏的应该是明清之际流行于江南一带的昆曲演唱。在戏曲艺术的时代变迁中,能否原汁原味地保存、延续具有“古风”的昆曲演唱艺术,这是营造江南戏曲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
王时敏家族有着悠久的昆曲演唱传统,如前所述,魏良辅的女婿张野塘曾教习王锡爵家班,魏良辅的高足赵淮也曾是王家的座上常客。而更值得称说的是王时敏家族与苏昆生及其弟子的交谊。顺治十二年(1655)以后,苏昆生到苏州太仓,王时敏称许说:“为魏良辅遗响,尚在苏生。”(62)吴伟业:《楚两生行(并序)》,《吴梅村全集》卷十,第246~247页;吴伟业:《与冒辟疆书》其五,冒襄:《同人集》卷四,第164页。康熙二年(1663)冬,他特地延请“苏昆生教家僮时曲,为娱老计”(63)王宝仁:《奉常公年谱》卷四,第420~421页。。但是,苏昆生擅长昆曲清唱,“于阴阳抗坠,分刌化度,如昆刀之切玉,叩之栗然”,这种唱法与“啴缓柔曼”的吴中“新声”判然有别,因此“非时世所为工也”(64)吴伟业:《楚两生行(并序)》,《吴梅村全集》卷十,第246页。,“不免为吴儿所困”,“流落江湖,几同挟瑟齐王之门矣”(65)吴伟业:《与冒辟疆书》其五、其六,冒襄:《同人集》卷四,第164页。。
苏昆生的高足顾子惠,独得苏昆生之传,“辨别开闭呼吸,分析清浊阴阳,深得三昧,更能于字母翻切,不爽毫毛,乃秦青、韩娥之后身,非寻常善歌者所可同日语也”。他十三岁就得到王时敏的赏识,与王抃等兄弟相善。王抃有诗称道:“少得师传更出蓝,行云响遏擅江南。”(66)王抃:《题顾子惠小像并序》,《巢松集》卷六,第450页。
苏昆生一生坚守魏良辅嫡传的昆曲唱法,汪汝谦称他为“典型宛然”,意即“正宗清唱家”(67)汪汝谦:《春星堂诗集》卷五《松溪集》,清光绪间刻《丛睦汪氏遗书》本。参见陆萼庭《苏昆生与昆腔》,《清代戏曲家丛考》,第37~38页。。吴伟业也称他:“一生嚼徵与含商,笑杀江南古调亡。洗出元音倾老辈,迭成妍唱待君王。”(68)吴伟业:《楚两生行(并序)》,《吴梅村全集》卷十,第247页。在明清之际的江南,苏昆生这种对“古调”的执着持守,原本就包含着“古道良自爱,今人多不弹”的独特的文化意味(69)吴伟业:《与冒辟疆书》其六,冒襄:《同人集》卷四,第164页。。因而江南士人往往对昆曲艺术保留一种由衷的挚爱,欣赏昆曲演唱,也往往逗引起江南士人的感伤情怀。如剧作家吴绮赠别苏昆生,道是:“最喜是中原故老,犹记取《霓裳》雅奏。相怜处,把繁华往事,灯下说从头。”“沧桑一转眸,云雨双翻手。……抛红豆,叹知音冷落,向齐廷弹瑟好谁投。”(70)吴绮:【尾犯序】套《赠苏昆生》,吴绮:《林蕙堂全集·艺香词钞》附填词,《清代诗文集汇编》第68册,影印清乾隆间衷白堂刻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407页。王抃赠别苏昆生,也说:“江南流落李龟年,今夕相逢共绮筵。檀板拍残银烛泪,玉箫吹起画楼眠。秋风鄂渚将军幕(曾留左帅幕中),夜月明湖处士船(与汪然明最相善)。此地近来丝竹断,闻君一曲倍凄然。”(71)王抃:《吴德藻招饮席上赠苏昆生》,《巢松集》卷二,第407页。
其次,戏曲艺术的装扮服饰和舞台动作,直接作用于观众的视觉。在明清易代之际,戏曲舞台艺术中最具有“文化象喻”意味的要素,无疑是戏曲服饰,于是戏曲服饰的观赏也成为戏曲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观剧歌》中,王抃自言“徵歌斗伎非吾愿”,而唯独有感于“廿年不睹汉官仪,衣冠优孟还堪羡”,对戏曲服饰尤为注目,这并非偶然。
在顺治初年强制推行“薙发易服”之后,江南地区的汉族人将“大明衣冠”视为故国文物典制的象征,产生了一种深入骨髓的眷恋心理(72)参见冯尔康《清初的剃发与易衣冠》,《史学集刊》第二辑,1985年,第32~42页;林丽月:《故国衣冠:鼎革易服与明清之际的遗民心态》,《台湾师大历史学报》第30期(2002年6月),第39~56页;樊学庆:《辫服风云——剪发易服与清季社会变革》,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这种眷恋心理在现实中难以表述甚至不可表述,便转而寄托在历朝相传的戏曲服饰之中。于是戏曲服饰便成为汉族文化身份的独特“喻体”,正因为如此,王抃在观剧时,目睹“衣冠优孟”,油然而生的是对“廿年不睹汉官仪”的深深感叹。与此相类,清顺治九年(1652)清明时节,桐城(今属安徽)人方文在宋琬署中观剧,有诗云:“久不见袍笏,优伶尚汉官。酒多情易感,曲罢漏将残。令节惊相问,中心黯自酸。一生开口笑,只是傍人欢。”(73)方文:《清明日饮窦计部署中观剧有感》其二,《嵞山集》卷五,《续修四库全书》第1400册,影印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王概刻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64页。顺治十七年(1660)五月,陈瑚在如皋冒襄水绘园中观剧,也发出过同样的慨叹:“曲曲明珠转玉盘,声声吹向碧云寒。无端愁杀江南客,袍笏威仪见汉官。”(74)陈瑚:《和有仲观剧断句十首》其三,冒襄辑:《同人集》卷六,第267页。
明代的戏曲艺人,集唐宋以来歌舞、散乐、南戏、杂剧的服饰之大成,形成了一整套程式化、符号性、装饰性的“戏服”规制,独具一格。这套“戏服”规制,并不讲究历史人物服饰的历史具体性,而是以戏曲人物的角色特征为基础的,因此具有“共时性”的特点。入清以后,舞台艺术中常规使用的“戏服”,并不因为清朝官服制度、常服制度的变更而有所改变,而基本上仍然以明代汉族常服为基础(75)参见宋俊华:《中国古代戏剧服饰研究》,第106~111页、270~276页。。因此,在现实生活中,以明代汉族常服为蓝本的“戏服”就与人们日常穿着的满族服装形成极其鲜明的反差(76)尤侗《年谱图诗》中的“草堂戏彩图”,可以作为典型的图像示例。《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73册影印清康熙间刻本,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第646页。。早在明朝建立之初,就倡导恢复汉族礼仪,改革冠服制度,“诏复衣冠如唐制”(77)洪武元年二月明太祖诏令,《明太祖实录》卷三○,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62年中研院史语所校印本,2016年,第525页。参见张志云:《礼制规范、时尚消费与社会变迁:明代服饰文化探微》,华中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第44~51页;张佳:《新天下之化:明初礼俗改革研究》第二章“重整衣冠:洪武时期的服饰改革”第一节,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52~76页。,于是在明代的日常服饰中已经注入丰沛的“汉文化”传统。而在清代,尤其是在清代前期,戏曲演出中以明代汉族常服为蓝本的“戏服”,自然而然地被赋予“汉文化”符码的独特意味,成为士人寻求、确认或追忆文化身份的“象喻”,从而引起“今—昔”对比,唤起士人潜在而深邃的“文明”情感(78)参见葛兆光《大明衣冠今何在》,《史学月刊》2005年第10期,第44~45页。。
因此,在清初的观剧者如王抃等人看来,戏曲演出中扑入眼帘的“戏服”,绝不仅仅是戏曲演员身体的穿着之物,更是“前朝”历史、社会乃至精神的承载之物和象征之物。“游于艺”的戏曲观演活动营造出一种独特的文化生态,足以使他们在艺术幻觉中暂时远离“新朝”的生存现状,徜徉于“前朝”的文化氛围之中,沉湎于传承久远的“文明”。
于是,由昆曲“正声”的演唱和演员“衣冠”的呈示,激发起激烈的“文明”情感,在王抃观剧时,汇聚而成“时艰胜事应难继”“世路悠悠尽如戏”的情感洪流,一发而不可收。在清初王时敏家族“游于艺”的戏曲活动中,士人作为群体往往引发出追念故国、感慨今昔的情感。
顺治四年(1647)以后,王时敏在太仓城以西十里的归村,修葺西田别业,以为隐居之所。于是,“西田主人”“归村老农”便成为王时敏遗民身份的“转喻”符码,吴伟业说:“盖追念国恩,感怀今昔,虽居赐第,游尘寰,屡思从樵牧自放。”(79)吴伟业:《王奉常烟客七十序》,《吴梅村全集》卷三七,第780~781页。而王时敏家族及其友朋在西田的游赏宴乐活动,也成为“胜朝遗老”文化记忆和情感交流的触媒(80)参见耿晶《道心精微》第三章“西田卜隐——‘遗民’与‘居士’的性相融和”第一节“指陈与象征——身份辨别及意义确认”,中国艺术研究院2012年博士论文,第51~59页。。归庄记述道:西田落成之年,“先生适花甲一周,于是远近大夫士争赋西田诗以致贺”,“诗则五、七言古风、律、绝诸体悉备,人则自江南及浙、闽、楚、蜀千里之外皆有”(81)归庄:《王氏西田诗序》,《归庄集》卷三,第184页。。因此,康熙十九年(1680)王时敏的去世,在象征性的意义上宣告了一个“胜朝遗老”时代的消逝,虽然这种“胜朝遗老”情怀仍然绵延不绝。恽格撰《哭王奉常烟客先生》二十四首,其一云:“相韩家世旧青箱,牢落先朝老奉常。纵使云霄参玉树,白头遗恨已沧桑。”其九云:“典型南国表群伦,绮季商岩与结邻。只眼乾坤遗老尽,从今海内竟无人。”(82)《西庐怀旧集·诗简》,《王烟客先生集》附录,第683页。
易代之际士人的出处,原本就是一个极其艰难的选择。而王时敏像西汉初年绮里季等“四皓”那样,在“故国臣”和“避秦人”的双重身份中游刃有余,的确显示出一种独特的政治智慧和生存智慧。而王时敏自身对这种双重身份的确认,恰可在听曲观剧这种“游于艺”的活动中得到深切的慰藉和尽情的排解,正所谓:“何处却逢开口笑,梨园一部管弦中。”(83)沈受宏:《王奉常烟客先生八十寿言四首》其二,《白溇集》卷一,《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67册,影印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刻增修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476页。
要之,在明清之际王时敏家族“游于艺”的戏曲活动中,动听的昆曲音乐、悦目的演员服饰和赏心的情感内容,无不成为具有独特的隐喻意义的“文化符码”,在士人们聆听、观赏、品评戏曲艺术的时候,激发和强化他们的历史记忆与文化想象,从而构建一个别具一格的精神家园。这一精神家园,不仅仅为王时敏家族所独有,而是明清之际江南士人群体共同建构和游赏的文化乐园。它无形中成为明清之际江南独特的戏曲生态,孕育和滋养着戏曲艺术的繁荣发展,推进了戏曲艺术文化品位的提升和表演技艺的新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