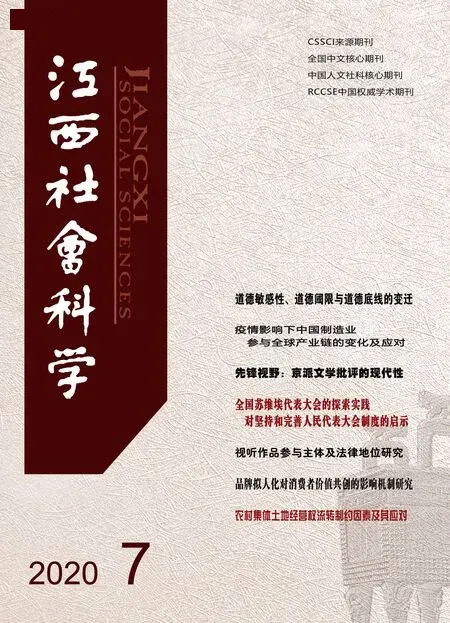人伦与规范:传统蒙书中的道德养成
2020-02-12班高杰
■班高杰
“蒙书”是我国传统启蒙教育中进行道德教化的重要载体,主要以未成年人(十五岁以下)为教化对象,进行以“明人伦”为核心道德规范教育。“明人伦”旨在教导童蒙对差序格局的认知,礼仪规范的习得是对“礼”所倡导之秩序的遵从。道德养成通过“明人伦”“知礼仪”的详细具体的行为规范践履,从小处、细处着手,养成童蒙的道德品质。
《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道德理念和规范,我们要大力弘扬传承中华优秀文化,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贯穿于启蒙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各领域”。同时,“以幼儿、小学、中学教材为重点,构建中华文化课程和教材体系”,既要编写中华文化幼儿读物,又要创作系列绘本、童谣、儿歌、动画等。传统启蒙教育无论是在教材编写,还是在价值引导行为塑造等方面都可资借鉴的地方,尤其是以“蒙书”为载体的启蒙道德教育,能在“明人伦”与“习礼仪”的过程中,养成童蒙良好的道德品质。
“蒙书”是我国传统启蒙教育中进行道德教化的重要载体,主要以未成年人(十五岁以下)为教化对象,进行以“明人伦”为核心道德规范教育。在以“蒙学”为载体的道德教化中,传统宗法社会倡导的价值观虽未被明确提出,但以默认的前提隐而不彰,散见于童蒙教育的各个环节。“明人伦”旨在教导童蒙对差序格局的认知,礼仪规范的习得是对“礼”倡导的秩序的遵从。传统启蒙教育中的道德养成,着力于通过详细具体的行为规范,从小处、细处着手,养成童蒙的道德品质。
一、我国传统启蒙教育的道德指向:蒙以养正
“有人斯可教,有教斯可学,自开辟则既然矣。”[1](P379)我国历来有重视教育的传统,拥有源远流长的儿童启蒙教育历史。早在虞舜原始时期,我国就已经出现类似于现代小学的机构。《礼记》记载:“有虞氏养国老于上庠,养庶老于下庠。”(《礼记·王制》)早在三千多年前,我们的先人就提出对儿童要及早教育,引导他们走上正道,认为这是神圣的事业。《周易》明确记载:“蒙以养正,圣功也。”(《周易·蒙》)启蒙教育作为教育的起步阶段,不仅对个体的发展具有奠基性的意义,而且对整个社会和国家都具有重要意义。
在此后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启蒙教育一直未有间断,无论是官学还是私学,启蒙教育都占据一席之地。中下层儒者参与启蒙教材的编写,宋明之际更有经学大儒亲自编撰童蒙书籍,以供童蒙识字、修身、养德。朱熹更明言,小学阶段“知其事”,是为大学“明其理”铺垫,小学阶段是在为大学阶段打下“圣贤的坯璞”。道德品性的养成与行为规范的训练,是启蒙教育的主要活动。通过道德教育和教化活动的实施,儒学也实现了“自上而下”的教化目的,真正体现了“切于日用而不自知”。从上层精英阶层的意识形态贯彻到百姓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这个过程也是儒学世俗化的过程。
所谓蒙学,是一个特定层次的教育,特指对儿童进行的启蒙教育,包括教育的目的、教学的内容、教学的方法等多方面的内容。这一教学旧时在书馆、乡学、村学、家塾、冬学、义学、社学等名称不同的处所进行。[2](P2)因此,蒙学就是传统社会人们开展的启蒙教育,同时也包括开展启蒙教育使用的蒙养教材,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小学”。蒙养书就是为了实施启蒙教育而编成的教材,也称为蒙学读物、启蒙教材、蒙学教材、语文教育教材、童蒙书、古代儿童读物,尽管称呼不同,但这些教材的实质内容大多相似,涵盖的范围也较为广泛。
在启蒙教材的编撰过程中,中下层儒者功不可没,正是他们用世俗化和通俗化的语言编写多种蒙学读物。在这些启蒙教材中,后世儒者对历代圣贤的嘉言进行改编,力图把蒙学读物中的内容和知识通俗化、趣味化,满足儿童的阅读需要。宋明之际,上层知识分子也参与撰写相关的童蒙读物,如朱熹及其弟子、王阳明及吕坤父子等人,也都撰写了以供童蒙学习的读物,如:朱熹的《小学》《童蒙须知》,朱熹弟子真德秀的《教子斋规》,王阳明的《训蒙大意示教刘伯颂等》,吕坤的《小儿语》,方孝孺的《幼仪杂箴》,等等。
启蒙教材的分类,因其数目众多,种类繁复,不同学者分类也多有不同。无论是识字教材还是历史教育教材,抑或诗歌教育类教材,都必然渗透着伦理道德的教育,绝非不讲道德的纯粹识字教材,这也是传统启蒙教育的显著特点。
“一阵乌鸦噪晚风,诸生齐放好喉咙。赵钱孙李周吴郑,天地玄黄宇宙洪。《三字经》完翻《鉴略》,《千家诗》毕念《神童》。其中有个聪明者,一目十行读《大》《中》。”[3](《序》,P2)这首诗描述的读书场景,正是儒家教化实施过程的真实写照。启蒙教育以儒家经典为核心,向童蒙传授人文知识,进行伦理纲常教化。梁漱溟认为,中国人偏重于孝悌礼义的教育,而西方人则更偏重于自然科学的教育。[4](P340)在传统启蒙教育活动中,中国历来注重对童蒙进行人伦道德的教化,以尚德为启蒙教育的核心。蒙学教化和传统文化息息相关,二者紧密相依,因此,人伦道德在我国传统启蒙教育中是核心内容。启蒙教育的核心就是伦理教育,知识的传授与培养反而在其次,所谓“有余力,则学文”,正是如此。由此可见,我国古代的童蒙教育以帮助幼童养成圣贤人格为教育宗旨,力求培养童蒙知情意行之能力。
与向往来世的宗教学说相比,儒家学说更关注经验世界的人伦规范,强调社会生活中的伦理和道德。道德至上是我国传统文化最基本的特征,因此,在我国传统社会中,人们通常会以道德为标准对人对事进行评价。在传统社会中,所学即是“学为人”,成为有德之人,正如陆象山所云:“今所学果为何事?人生天地间,为人当尽人道,学者所以为学,学为人而已,非有为也。”(《陆九渊集》卷三十五)启蒙教育的任务就是让童蒙知晓生而为人,要尽“人道”,“人道”就是人伦日常,就是切于日用的人伦规范。伦理道德教育是我国传统社会中童蒙教育的核心,而“明人伦”则是伦理教育中的首要问题。
二、“明人伦”:道德养成的核心内容
“明人伦”是道德教化的目的,也是道德养成的核心。孟子云:“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孟子·滕文公上》)我国早在夏商周时期就规定,所有学校的教育目的都是为了使学生“明人伦”:“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孟子·滕文公上》)孟子认为,明人伦就是造就道德的人,圣人忧虑,人如果不受教育就近于禽兽,所以教以人伦以区别之。明人伦一方面是出于人之为人的道德规定性,另一方面则是养成个体对名分的道德自觉。儒家推崇君臣上下的等级秩序,最重名分之说,个人只有做符合自己名分的事,才能显示其在日常人伦中的地位和意义。“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中庸》)在其位尽力做好本分之事,不必外求诸多与之无关之事,即说明君子所言所行应合乎其名分,籍其名分以行事。
所谓“人伦”,即“人道”,由孟子明确提出,指的是制约和约束人与人之间基本关系的道德规范。人伦指向的是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孟子对此做出经典的“五伦”解释:“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对“五伦”的内容做出规定,孟子并非第一人。若从思想渊源上考察,孟子“五伦”思想源于《尚书》的“五教”。据《尚书·舜典》记载:“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而所谓“五教”,主要内容就是“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左传·文公十八年》)。孟子的“五伦”较之“五教”,其伦理关系范围显然是扩大了,除却家庭关系的三伦(由于家国同构,君臣一伦可看作父子一伦的延伸),朋友一伦则指向家庭之外的社会关系。此外,在《礼记·祭统》里则讲到十伦,即鬼神、君臣、父子、贵贱、亲疏、爵赏、夫妇、政事、长幼、上下。这里所谓十伦,其实是十种关系,并非都是人伦纲常。至于对五伦中道德主体的规范要求,儒家经典的阐述稍有不同。《大学》明确指出:“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人交,止于信。”后世视孟子五伦为定论。如《礼记·丧服小纪》所说:“亲亲、尊尊、长长,男女有别,人道之大者也。”《中庸》里把“五伦”称为“天下之达道”。
“伦重在分别”,别的是“父子、远近、亲疏”,“明人伦”要求人们建立一个分尊卑上下等级的社会秩序。宗法家族是传统社会中的核心,因此,在我国古代传统社会的五伦关系中,每一伦的关系都与宗法家族息息相关。差序格局是伦理关系的特征,“伦”即是差等次序。费孝通说:“我们儒家最考究的是人伦,伦是什么呢?我的解释就是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5](P30)“推”之一字是差序格局中最重要的作用逻辑,通过以“己”为中心,外推“己”与“群”等各种关系,就能够推己及人、推己至家国天下,做到人同此心。
“五伦”关系的确定,奠定了传统社会基本的人伦关系。围绕“五伦”关系,经学大儒董仲舒进行了价值观的理论建构,提炼出“三纲”之说。所谓“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其实就是把“五伦”之中的三种伦常关系绝对化,使一方绝对服从于另一方。“三纲”逐渐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统治社会的重要工具,对后世的影响不可谓不大。贺自昭所谓“以常德为准而竭尽片面之爱或片面的义务”,道尽了三纲的本质。在“三伦”即父子关系、君臣关系、夫妇关系中,对伦理双方都有一定的道德规范要求,在父子伦理关系中,伦理要求即是父慈而子孝;在君臣伦理关系中,道德规范表现为君礼而臣忠;在夫妇伦理关系中,道德规范表现为夫妻和睦相敬如宾。“三伦”确定为三纲之后,原来的父子、君臣和夫妇之间相对温情的伦理关系荡然无存,从而成为一种绝对服从的纲常,服从于权威、纲纪及名分。绝对服从强调的是一方对另一方的绝对恭顺。“臣事君,子事父,妻事父,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韩非子·忠孝》)“顺”是绝对服从的表现,同时也直接与国家兴亡息息相关。
在蒙学典籍中,对童蒙进行“明人伦”的教育是首要任务。朱熹经常教育其门人:“后生初学,且看《小学》之书,那是做人底样子。”《小学》的基本精神是讲明伦、重敬身。朱熹一生教书育人,尤其重视对童蒙的道德教育。在亲撰的《小学》内篇中,他列立教、明伦、敬身和稽古四卷,意在明确“立教”的目的在“明伦”,“明伦”之要在“敬身”,稽古则是“摭往行,实前言,使读者有所兴起”。[6](P489)“明伦卷”以五伦为本,分列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之别,长幼之序,朋友之交,对童蒙提出详细甚至繁琐的要求。在蒙学典籍中,对童蒙进行人伦教育具体有哪些规范要求,通过如下分析便可窥其一斑。
首先,“明人伦”强调五伦三纲的突出地位。蒙学教育的对象为儿童,因此,传授知识要注意理论深度,若理论性过强,则不便儿童理解。一般的蒙学典籍只需明白告诉儿童是什么(教之以事),至于为什么(穷究那理)则是大学阶段的事情。因此,人伦教育只要儿童明晓何为五伦以及伦常具有的重要意义即可。如《幼学琼林》卷二之祖孙父子篇,提出:“何谓五伦: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妇。”《重订三字经》对“五伦”关系的先后次序作了规定:“五伦者,始夫妇,父子先,君臣后。”《重订增广贤文》中强调了五伦的重要:“农工与商贾,皆宜敦五伦。”由“五伦”观念而生发出的“三纲五常”传统道德标准在蒙学读物中也有明确表述。如在《三字经》中:“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曰仁义,礼智信,此五常,不容紊。”“父子恩,夫妇从,兄则友,弟则恭,长幼序,友与朋,君则敬,臣则忠。此十义①,人所同。”《千字文》中有“盖此身发,四大五常”的表述。
蒙学注重在“明人伦”方面教育童蒙,这与传统社会宗法结构不无关系,同时也是因为小学教育与大学教育紧密相连。在科举时代,小学教育服务于科举考试,为当时社会培养知识精英阶层。童蒙阶段通过“教之以事”,使儿童“依此规矩去做”,培养出“圣贤坯模”和“圣人素质”,以便“大学去穷究那理”。在“小学”阶段只有“小学存养已熟,根基已深厚,到大学,只就上面点化出些精彩来”[7](P125)。
其次,“明人伦”确立详细具体的人伦规范。蒙学读物把人伦道德化为具体的行为规范,详细具体规定如何孝于亲、忠于君、悌于长等。五伦的先后次序,《中庸》的界定是“君子之道,造端于夫妇”,夫妇一伦是人伦之始。然而,在中华传统伦理体系中,孝无疑居首要地位,“百善孝为先”。若移孝为国家效力,则为忠,因而忠孝并提并占据正统地位。
反复强调五伦的意义,对童蒙的言行举止做出具体的要求,最终目的在于强化君、父、夫的权威,形成绝对权威。董仲舒论证“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天出阳,为暖以生之;地出阴,为清以成之”(《春秋繁露·基义》),把君、父、夫的权威诉诸天。直到宋代儒学时期,这样的神学论证已经无法使人们信服。基于此,朱熹又提出一个更系统化的理论体系,他以“天理”来论证“人伦”的合理性。朱熹言“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以广大高明的“天理”来论证“人伦”有其形而上的理论基础,从而也就为“人伦”寻找到了外在力量。孟子也曾经提出“易子而教”的思想,维护父亲的威严,这些思想都是为了强调父亲在家庭中的权威性。君、父、夫一旦确定绝对权威,所有不遵从的行为都被归为不忠不孝的行为。比如“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君主对臣子有着绝对的处置权力。同样,父亲对子女有着绝对的处置权力,丈夫对妻子也有着绝对的处置权力。
传统社会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对臣子、子女和妇人的束缚愈加严格,最后出现愚忠愚孝也就不足为怪。针对童蒙进行明人伦教育,可以教导童蒙以“礼”处理人际关系,养成对伦常名分的道德自觉。在差等次序的人伦关系中,“三纲”是其核心内容。在童蒙道德养成的过程中,“明人伦”是道德养成的核心与主要目标,强调“人伦”的重要性也是强调童蒙对伦理纲常“天秩天序”的遵从。童蒙时代打下坯璞,为“成人”奠定基础。但是,过度强调纲常伦理,违背了童蒙的天性,容易扼杀童蒙的才智。
三、“知礼仪”:行为规范的日常训练
童蒙道德品质的养成,理应从小事开始。对童蒙的基本生活行为进行规范约束,特别是对年龄较小的儿童来说,更应该从细小的事情上做出要求,规范其言行举止。传统社会对童蒙的教育非常细致,给出具体详细的规范,以便落实到童蒙教育中。传统蒙学教育服务于封建社会的等级秩序,对童蒙的道德教育要具备适用性与可操作性,让童蒙在行为规范中养成对差等次序的遵从。蒙书主要通过儒家伦理道德约束规范童蒙言行,以故事典籍中的人物和行为指导儿童,具备很高的可行性,便于童蒙认识和实践。
小学阶段,童蒙重点学习的内容包括“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如朱熹在《童蒙须知》中要求,“夫童蒙之学,始于衣服、冠履,次及语言、步趋,次及洒扫、涓洁,次及读书、写文字及有杂细事宜,皆所当知”,就提到儿童的举止,要求童蒙必须做到:“凡著衣服,必先提整衿领,结两衽纽带,不可有缺落。”“凡脱衣服,必齐整摺叠箱箧中,勿散乱顿放,则不为尘埃杂秽所污。”对童蒙的穿衣提出细致入微的规定,可见生活中其他细节的要求也异常繁琐。语言举动方面,需要童蒙做到“语言详缓,不可高言喧哄,浮言戏笑。父兄长上,有所教督,但当低首听受,不可妄自议论”。即使自己的兄长父亲言行并不合理,也不可直接告知,在当时需要沉默,认为是兄长或者父亲一时大意才如此,或者没有考虑周全所致。洒扫涓洁的目的是培养童蒙养成清洁的行为习惯。朱熹认为,对童蒙而言,应该重点养成学习的习惯,比如读书,要声音洪亮,所读要和书中内容完全一致,不可多字亦不可少字,要反复诵读,从而朗朗上口,最终熟记在心。读书方面需要有着良好的行为习惯,另外,还应该养成好的学习方式。朱熹强调,学习有三到,分别是心到、眼到和口到,他表示:“三到之法,心到最急,心既到矣,眼口岂不到乎?”朱熹还规定童蒙在饮酒、如厕、饮食、夜行等方面的细节。繁琐的生活细节要求,目的是培养童蒙尊师敬长、爱护器件、用心学习等的良好品质。
明代屠羲英在《童子礼》中详细列举了儿童在家中应有的举止,包括盥栉、整服、叉手、肃揖、拜起、跪、立、坐等。《弟子职》则规定了学生对待老师应有的行为举止,比如受业、应客、馔馈、洒扫、执烛、退习等,都要有规矩。各种规定非常严格,到了严苛的地步,比如塾课方面,相关的典籍包括《家塾常仪》《塾中琐言》《变通小学义塾章程》等,规定非常繁琐且严密。清代崔学古在《幼训》一文中,单单针对童蒙的吃饭就做出详细的要求:“毋先,毋后,毋择,毋翻,毋邻(谓取邻簋食也)。”吃饭不要翻动菜肴,不要挑拣,更不可越过别人去取旁人之餐。吃饭不可把筷子含在口中,不可伸出舌头接食物,要做到“嚼无声,咽无疾,啜无流”,吃完要把筷子收好,才可以起身。要求童蒙严格按照这些规定去做,同时,师长也可以监督管理其行为。不足的是,如此繁琐的规定,在现实中操作不易变通,不利于儿童个性的培养。另外,再详细的要求,也会存在挂一漏万的现象,无法包罗生活中的各种现象。
“非知之实难,将在行之。”(《左传·昭公十年》)通过教育能够让儿童逐渐了解道德规范,但是,知道并不代表能够做到,要想在日常生活中履行这些道德规范更是难上加难。《弟子规》告诫童蒙:“不力行,但学文,长浮华,成何人?”即要求童蒙要通过具体的行动和感悟学习道德规范。《重订增广贤文》指出:“学不尚实行,马牛而襟裾。”认为应该将典籍中的伦理道德落实在具体的行动中,这是成为圣贤之人的必经之路。所以,蒙学教育非常重视对童蒙的礼仪教导,这有利于儿童形成良好的品德举止。
判断行为是否合理,需要按照一套完整的标准进行判断,在封建社会中,这套标准便是儒家强调的“礼”。童蒙时期需要遵守的各种道德规范来自于“礼”。儒家学说中倡导的“礼”含义非常多。结合十三经进行分析,其中有《仪礼》《礼记》和《周礼》均专门对“礼”进行详细的记载,后人将其视为《三礼》。《仪礼》对各种等级群体的行为做出具体的要求,《周礼》详细论述政治制度,《礼记》从哲学的角度分析《仪礼》的礼节。《礼记·哀公问》有云:“民之所由生,礼为大。非礼无以节事天地之神也,非礼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在位也,非礼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之亲,婚姻、疏数之交也。”这里就可以看出“礼”在中国古代儒学中的重要性。孔子提出的“仁”学,其实质也是以礼为实现“仁”的前提。
基于“礼”的规范系统包含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属于伦理规范系统,目的在于调整人伦,这是宏观角度的“礼”;第二个层面属于道德规范系统,目的在于规范人的道德言行,这是微观角度的“礼”。[8](P267)伦理规范系统来自于等级秩序,强调“亲亲”和“尊尊”,指出不同等级之间有着尊卑和亲疏的关系。道德规范系统重点提升个体的修养道德,要求每个人能够反省自己,规范自身。一般而言,“礼”具体体现为两个方面,分别是道德规范和政治制度:一方面,“礼”强调的是个人修养品行;另一方面,“礼”成为治理国家的手段。《礼记·礼运》中的“是故礼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别嫌,明微,傧鬼神,考制度,别仁义,所以治政安君也”,提到君主统治的主要手段就是礼,“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以为民坊者也”(《礼记·坊记》)。礼能够被古人看重,主要根源在于,礼是维护等级制度的主要手段。
“礼”对于规范人的言行举止以及在齐家治国上发挥着关键的作用,所以,儒家学者给出详细的礼制,对人的思想言行等进行规范约束。孔子将毕生的精力都放在“克己复礼”上,希望整个社会遵守周礼,发挥周礼的作用。孔子认为礼是形式,礼的内容源自于仁,所以他强调:“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论语·八佾》)将礼和道德有机结合在一起,礼才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荀子也对“礼”进行了详细介绍,他通过《礼论》这一篇章,全面阐述在治理国家方面“礼”的功能。“礼”的功能体现为两种,分别是“别”和“养”。封建社会区分社会中人的地位以及贵贱等级,即是“别”。“曷为别?曰: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荀子·礼论》)在“别”的基础之上,“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荀子·礼论》),又提出“养”的说法,“养”即是对人的物质欲求的满足。
针对童蒙反复进行礼仪规范教育与训练,不仅可以促使童蒙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和行为习惯,通过将典籍中的道德规范内化成童蒙的言行模式,还可以让童蒙初步了解亲属尊卑等级制度,避免日后行为僭越等现象的发生,为此后的人格养成发展做好准备。童蒙时期形成的习惯会对其一生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陶行知认为:“人格教育,端赖六岁以前之培养。凡人生态度、习惯、倾向,皆可在幼稚时代立一适当基础。”[9](P104)这也正是传统社会对童蒙进行礼仪规范教育的意义所在。
四、结语
以蒙书为载体的传统启蒙教育,把社会主流的伦理观、道德观、历史观及价值观,通过道德教化的途径传递出来,把儒家思想的微言大义化为童蒙易知的揖让言辞,密切联系儿童的生活实际,比较通俗且易知易行。很多经典的蒙学读本(如《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等),荟萃了前人及那个时代的经典文化,构成传统蒙学相当完整的知识体系、思想体系、价值体系和艺术体系。通过自上而下的教化,传统启蒙教育完成了从上层精英文化到中下层伦理生活化的转换,也实现了上层意识形态到民众价值观的传达。传统启蒙教育中的道德养成,注重文道结合、因材施教、教学相长等教育思想和教学原则,教材编写符合儿童心理特点,读起来朗朗上口,童蒙可以反复吟诵。我们对未成年人道德品质的养成教育,在传统启蒙教育中都可以找到相关的论述与表达。鲁迅曾说:“倘有人作一部历史,将中国历来教育儿童的方法、用书,作一个明确的记录,给人明白我们的古人以至我们,是怎样被熏陶下来的,则其功德,当不在禹下。”[10](P255)我们对传统文化进行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可以从中借鉴对未成年人进行道德养成教育的途径及方法。
注释:
①“十义”是指儒家宣扬的十种伦理道德,《礼记·礼运》说:“父慈,子孝;兄良,弟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