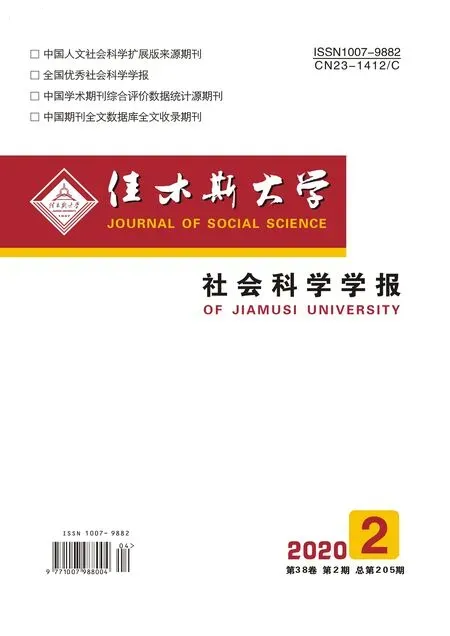权力场域下犹太人身份的存在结构解读*
——菲利普·罗斯《美国牧歌》的身份研究
2020-02-11黄新川
黄新川
(福建商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一、引言
长篇小说《美国牧歌》是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 1933—2018)其所创作的“美国三部曲”中的第一部。《美国牧歌》中所反映的叙事内容是犹太裔在美国社会文化和思想的影响下,逐渐变得现实化和美国化。他们在行为规范上背离和抛却了“上帝的选民”的集体身份,孜孜不倦地追求着“美国梦”,由此造成了个体身份和集体身份认同的偏差。他们渴望获得美国式的自由,但同时又背负着沉重的犹太裔集体身份,在自我的个体身份困惑中充满了彷徨和困惑。由此可以看出,罗斯笔下的犹太人物拥有着这两种身份意识的反差,这样的反差心理造就了罗斯笔下对自我身份困惑而迷茫的犹太裔族群。通过文本细读,笔者发现在这篇小说的文本中有三组相互关联和互补的结构,分别是失语与缺位、迷失与困惑、反思与认知。
结构原指同一物各部分、各要素、各单元之间的关系或本质联系的总体。[1]122在文学作品中,结构是故事表层之下的一组关系,叙事文本的内在组织和系统在结构的对称中彰显意义,不是二元对立的关系,而是开放、立体的关系。然而,结构概念虽有多义性、语境关联性和渗透性,但它主要是在秩序和系统的意义上,比手法和形式更为广泛,是一组关系或关系的组合。[2]439小说的叙事文本是一个多层次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意义存在于叙事人物身份的关联之中,表现为一组相似或平行的结构方式。在两者的相互关联中,这个意义才能被感觉到。因此,从失语与缺位、迷失与困惑、反思与认知这三组相互关联中分析是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
二、失语与缺位
这里的失语,并不是指医学意义上的大脑言语功能受损害而引起的语言困难,而是指菲利普·罗斯的小说《美国牧歌》中主人公赛默尔·利沃夫及其女儿梅丽在叙事进程中的身份存在状态。以后现代主义的角度来思考,这种状态的本质是权力的较量。福柯对于权力的界定有如下所述:权力就是力量之间的关系,或者说,力量之间的各种关系就是权力的关系。[3]154
在小说中,父亲利沃夫“用人们理智地对待孩子的现代思想将她养大,一切都容许,一切都谅解,而她却恨透了。”[4]57在梅丽十几岁时,她患上了口吃。梅丽的口吃象征着男权主流话语力量对女性话语力量的禁忌和压抑。利沃夫试图挣脱一个犹太裔与生俱来的所受到的束缚,摆脱这一身份,当面对他人,包括他的女儿时,他表面上看似友好,实则内心充满隔阂。他果断地展现自己的不同,以期作为一个犹太裔能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和话语权。而且,利沃夫对梅丽过于理智,他对梅丽的情感由爱到恨。在梅丽看来,父亲要求的完美、理智和压抑自我是一种情感上的捆绑和束缚,她只是被父亲表面温和与关怀的隐性拘禁在一个封闭的空间内。布罗茨基曾细致地分析道“在一个封闭的空间——比如说一座房子——里的矛盾冲突,通常都会演变为一场悲剧,因为这个长方形的空间本身就会助长理智(reason),约束感情(emotion)的发展。”[5]227在此环境下,梅丽的父母对有的东西那么关注,梅丽有时却认为这种东西很无聊,所以她的成长过程很艰难。梅丽父母觉得梅丽的口吃让他们颜面尽失,因此他们千方百计地治疗梅丽的口吃,然而梅丽的口吃日益严重。她常常被关在房子里,感觉每天在这房子里就像软禁一样。而且,为了阻止梅丽去纽约会见朋友,利沃夫不厌其烦地劝说她,尽管这看起来没有希望,他还是不断地畅谈和倾听,保持理智。这场战斗似乎不会终结,他很有耐心,只要发现梅丽太出格便画线约束。除此之外,梅丽对自己的族裔身份也感到困惑。她感觉自己是在圈外,天生的畸形人,以不受约束的方式行事。她认为自己是美国文化的一部分的同时,又清楚地意识到犹太人身份的特殊性和唯一性。这对父女之间的共同语言不复存在,这表明了一种对话的缺位。实际上,梅丽和这十年的岁月使父亲利沃夫独有的美国梦思想分崩离析。梅丽在这场和父辈的权力战争中获得了话语的权力,但她将利沃夫拉出向往许久的美国田园梦,抛入进美国梦的困境中。
在笔者看来, 这实质上是权力场域下的理性与非理性的斗争。利沃夫代表着一个被美国文化所吸收和理性化的犹太裔美国人。他处于一个理性的地位,被世界普遍接受和认可,将处于失语状态的个体边缘化。这个层面的权力争夺在社会秩序中始终是理性占上风。个人的命运充满了悲惨的色彩。在《美国牧歌》中,利沃夫和他女儿梅利之间的冲突和对抗反映了犹太人复杂的内心世界和在美国多元化背景下的存在状态。
菲利普·罗斯在其长篇小说《美国牧歌》的创作中,通过描写塞默尔·利沃夫及其女儿梅丽的权力争夺,对犹太人的理性进行了反思。对于罗斯,作为第三代美国犹太人,他没有经历过大屠杀,因此有可能摆脱犹太受害者的心理和历史包袱,并以更自由的方式来描写犹太人的生活。但罗斯对犹太人民族心理也有深刻的理解,用文学作品来揭示犹太人在文化融合中的异质性。
三、迷失与困惑
为了实现美国梦,赛默尔·利沃夫通过辛勤劳动,购置了位于新泽西的上层社会白人社区里的一栋石头房子,因为这石头房子的环境能够反映出他们家族的价值观。这个石头房子由两百多年前英国新教徒所建立,象征着美国主流的社会地位,它似乎不可动摇,犹如利沃夫的美国梦一样。为进一步实现梦想,利沃夫一意孤行地娶信奉天主教的多恩为妻,尽管他和多恩有非常不同的宗教信仰。随后,利沃夫和他的妻子搬进了象征着美国梦的石头房子,以这种方式,利沃夫满足了自我,实现了自我,又不心存内疚地直接融入美国文化当中。例如,有一次过感恩节,亲朋友聚到一起,利沃夫站起来敬酒,他说他是个不信教的人,但当他看到这一桌人,他就知道有什么东西将光辉洒到他身上。然而,自从伊甸园以来,各个家庭都似乎有不安分子,梅丽,作为利沃夫家庭中的一个不安分子,摧毁了利沃夫的田园诗般的美国梦里,充当了爆破手,炸毁了当地的邮局,正如小说中所叙述的那样:
那是他们不得不进行的有关纽约的最后一次谈话。虽很艰难,但他很有耐心,态度坚决,终于起作用了,奏效了。如他所愿,她再没有去纽约。她接受他的建议,留在家里。随后,她把客厅变为战场,把莫里斯顿高中变为战场。一天,她出去把邮局崩飞了,一同毁灭的还有福雷德·康伦医生和村里的百货店。那是一座木结构的小房,前面挂着社区的公告板,还有一只后桑纳可水泵和金属杆,商店主人诺斯·哈林姆每天早上都在上面升起美国国旗,打从沃伦·甘梅利尔·哈定就任美国总统以来就未断过。[4]95
梅丽炸毁邮局的冲动行为间接地粉碎了父亲的“美国梦”。 梅丽从悲悯转向暴力,通过炸毁邮局的极端方式引起人们对越南战争的思考。在这个承受很大压力的完美主义的犹太家庭中,整个家庭和利沃夫真正关心的一切都是表面,但表面背后的危机他从来没有感受到和意识到。当梅丽的投炸弹行为将他从自我感觉良好的田园梦中惊醒以后,他才才开始自我反省。这种自我反省也是他很久才学会的。如果说有什么比扪心自问更糟糕的事在生活中过早出现的话,那就是扪心自问来得太迟。爆炸的受害者是他本人。更不幸的是,他的妻子多恩在丈夫利沃夫遭遇命运的变故时,转身投进美国正统白人沃库特的怀抱,进一步从精神上将他的田园牧歌梦彻底粉碎,使他陷入悲惨的境地中。
其实,不仅仅是塞默尔·利沃夫,许多犹太人也陷在“美国梦”中失去自我,甚至企图摈弃他们的犹太人身份以寻求与主流社会同化,陷入了无根的状态,迷失自我。什么是自我?按照威廉·詹姆士的说法,自我就是一个人所拥有的一切,而每一个拥有都涉及身份问题[6]9。身份不是孤立存在,一个人如果面对的完全只是自己, 可以将自己幻想成任意身份, 那么身份就可以随意变化。自我的任何社会活动, 都必须依托一个身份才能进行。自我是各种身份的出发点, 也是各种身份的集合之处,一旦自我消失(例如死亡, 例如昏迷,例如“随波逐流”),拒绝思考自己为何采取某种身份, 这些身份感觉也就无以存身。
四、反思与认知
利沃夫割断了自己的犹太裔文化根基,摈弃了自我的集体身份和文化记忆,将模仿他人的作为自己的生活信条。为了实现美国梦,他穿着美国人的服装,听着美国人的音乐,迈着美国人的步伐,甚至连梦也做着美国人的梦。其实,他生活在模仿他人的世界中,沉湎于美国梦的虚幻景象中,将自己的犹太裔集体身份抛掷脑后,甚至进行选择性的遗忘。利沃夫活着就要模仿他人并且其存在的方式就是做别人而非自己,这是一种对于民族身份漂泊性的摈弃和决裂,处于一个既不在内部,也不完全的外部的临界位置。这么多年来,正是这两种不同的身份位置之间的来回切换,让罗斯既是犹太裔,又是美国人,一具躯体内居住着两个身份。在美国文化的影响下,利沃夫已经混淆了自身的存在感。他是一个已经归驯的美国移民从内心深处意识到自己并不属于美国这大社区,和美国本地人不属于共同的文化,唯一共有的就是语言,或许还带有不同的口音,代表着不同的文化根基和生活经历,包括阶级、教育、族群。但不管身在何方,都要有自己内心的操守和评判。
无可否认的是,犹太历史这一概念一直在犹太裔的心中,和犹太人生活的现实一样从未停息,甚至比现实更震撼人心。美国梦的同化造成了一些犹太人失去自我,忘记了自己的身份,摈弃了自己的犹太血统,甚至试图摈弃自己的犹太人身份来寻求与主流社会的同化。进入社会要求犹太人摈弃犹太人的共同身份,而对于同化的强调也导致了作为一种决定性群体特征的犹太自我憎恨现象[7]7。对此,萨特认为寻求同化的人会处于无尽的自我审视之中并最终形成一种既陌生又熟悉、挥之不去的人格[8]78。事实上,如果一个人不能做自己,一切都将注定要毁灭与失败。因此,在美国文化的背景下的犹太人应恢复其在文化和身份的双重夹击下的自我,完成了个人的身份认同,建立精神支柱和感受身份认同。
在文化学的范畴里,作为一个文化群体的相对稳定和天生的自我表现,集体认同能够区分本族裔和他族裔,并保持和加强集体记忆来塑造、维护和巩固这一身份。个体的身份是个体通过识别集体身份而获得。身份的过程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需要不断确认、塑造、维护和巩固。如今,在世界文化群体混杂的环境下,集体身份蕴含多种同时存在的身份,这与个体身份产生张力,甚至会造成个体的身份认同危机。从身份建构的角度来看,个人身份的建立离不开个人与群体之间的沟通和联系。这也是一种身份建构的方式。独立的个体身份也具有实现其存在价值的重要意义。因此,美国犹太族裔应在自己的生存焦虑中,完成了对他们的集体身份和个人身份的反思和认知。
五、结语
罗斯关注的重心在于犹太人的身份建构,紧扣犹太人身份认同问题。作为一个犹太裔、美国人和作家,这三重身份以及他们之间的次序,在今天的社会环境下仍然具有思考的意义。
针对战后美国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犹太精神匮乏或信仰摇摆的现象,菲利普·罗斯在失语与缺位、迷失与困惑以及反思与认知的三组结构中,直面这种飘摇不定又具有生命力的犹太人,表达了他对作为美国犹太作家的美国多元文化背景下犹太人身份缺失的深刻思考。同时,罗斯也意识到犹太族裔走出身份和精神困惑的必要性,这对于坚持和维护犹太人身份以及整个人类的道德行为具有重要意义。
社会在不断发展,犹太人也在不断发展。美国犹太人的环境经历与他们的时代密切相关,不同的环境经验决定了不同的文化身份。当个人在历史环境中拥有丰富的历史记忆,体验民族的历史记忆,充分实现本民族的文化价值,很大程度上就可以在异域环境中找到精神和情感的归属,完成深层文化认同的建构:在犹太历史的长河中,听到犹太人的声音,在美国主流社会中,听到犹太人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