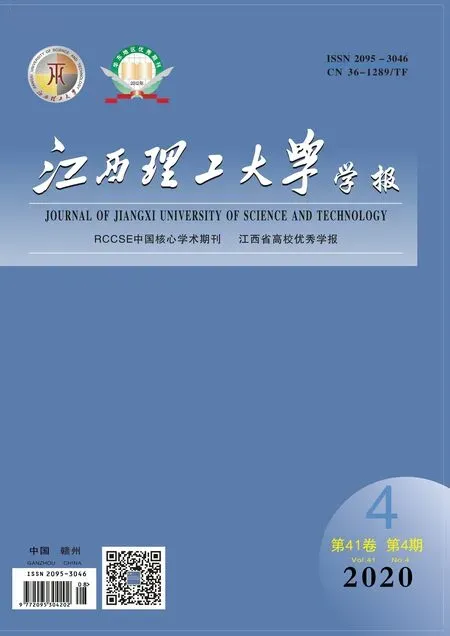赣南客家民俗体育文化元素与广场舞融合的可行性分析
2020-02-11金慧惠
金慧惠
(江西理工大学应用科学学院,江西 赣州341000)
赣南自古以来有“南抚百越,北望中州”之称,既是闽粤赣客家人内迁定居落籍的集中地,又是部分客家人继续内迁的出发地。千百年来其特有的地理环境、生产方式、宗教信仰、民风民俗造就了大量内容丰富、形态各异的地域性民俗体育活动,且世代相传、经久不衰。赣南客家民俗体育是我国古老体育文化活化石,也是农耕文化、祭祀文化的精髓[1]。其作为传统文化的有机部分,是一种具有深刻文化内涵与广泛文化外延的文化生产力[2]。随着时代、生活理念及文化环境的改变,应赋予其新的内涵以便更好地传承与发展,发挥其特有的社会服务性能。当今社会随着日益提高的生活水平,越来越多的人载歌载舞,在城乡一隅抒发着自己对健康、幸福生活的追求与展望。广场舞就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蓬勃发展。把赣南优秀的客家民俗体育文化元素与当代人们最为流行的健身娱乐方式相融合,无疑是一种大胆的尝试,不仅能丰富广场舞的形式而且更易引起当地百姓的共鸣,同时,也起到了保护和传承赣南民间民俗体育文化的功效。只有做到在继承与创新中求发展,赣南客家的民俗体育传统文化才会被赋予真正存在的价值与意义。
一、赣南客家民俗体育文化元素剖析
赣南地处丘陵地带,客家先民通过采、种、渔、猎、伐、耕、桑、茶求生山林,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中,跑、跳、攀、爬成了日常必备的生存技能。为了缓解身体的苦累和精神上的枯燥,客家人逐渐运用简单而有效的“跳”“舞”等方式调节日复一日的艰辛生活。随着社会的演变进程,这种调节发展形成丰富多彩的民艺民俗体育活动,如:采茶灯、花棍舞、蚌壳舞、踩花灯、秧歌、罗汉舞、傩舞、旱船、盾牌舞、春牛舞、马灯舞等。在千百年来的民俗信仰活动中,客家人通过这样的形式来驱邪避害、祈福来年的风调雨顺。
(一)赣南客家民俗体育文化的形态特征
赣州地区地域宽阔,民俗体育种类繁多且富有特色,常见的有于都禾杆舞、甑笊舞,瑞金金狮舞,兴国马刀舞,宁都盾牌舞、洗马舞、蚌壳舞,石城鹤蚌舞,大余罗汉舞,会昌海青(道教),龙南单双扇舞、鸳鸯狮舞,上犹螃蟹舞、茶篮灯等等。可谓区县各异,乡乡有品。其中罗汉舞是大余南安镇祈神求子的民俗体育活动,俗称“罗汉送喜”[3],由“罗汉”“猴子”“罗汉崽”三种形象二十多个角色表演,动作编排严密、结构严谨;有“搭牌坊”“高车滴水”“双狗对爬”等动作,极具幽默性。宁都盾牌舞是模仿古代士兵操练的舞蹈,相传为明代著名将领戚继光所创。表演时两军对垒,舞者左手执盾牌,右手握长或短兵器;盾牌形状有圆、椭圆、燕尾、长方等,风格特点是动作幅度小,频率快[4];讲究快、猛、狠、准、齐、稳、轻七个方面,运动法则是“功架不倒”才能“疾而不乱”;表演者不仅要具备深厚的毯子功技巧,如“虎跳”“抢背”“加冠”“叠筋”等,而且还要掌握舞蹈技巧“前飞燕”“后双飞燕”“吸腿转”“大跳”等,体现了客家人在外生活不易、粗犷尚武的情形。甑笊舞又称“划龙船”,流传于都银坑乡,主要是用来祈祷六畜兴旺的祭祀活动。表演者人数往往不少于二十七人,角色有艄公、艄婆、灶背王、舞通天旗者、舞狮毛狗者、划桨者各一人,舞三角旗者四至六人,其余皆为敲甑笊者,成员为男性[5]。基本步法为“进两步退半步”,要求屈膝,身直,步子大,一进一退,一起一蹲,动作粗犷、古拙,颇具章法。队阵保持圆圈,成员面向圆心,并朝一个方向旋转,随着甑笊敲击的分量逐渐加重,大家身体甩动幅度逐渐增大,配上激昂的号子,击打声由缓渐急,号子声一浪高过一浪。旁观者也为之振奋,纷纷参与舞蹈,愈舞人愈多,气氛高涨热烈。据说患风寒者参与欢舞,出身大汗,就能病愈,因此深得乡人喜爱。蚌壳舞流传于石城小松乡一带,每年元宵节,当地人通过蚌壳舞,祈福村民安康。舞蹈以姑娘蚌舞、村童戏耍为主,渔夫各种“划水”“鱼游”“撒网”动作穿插其间,互相嬉耍。禾杠舞也是产生于当地村民上山砍柴的情景,常用的禾杠斜插地上或杠在肩上、拿在手上,并不时旋转、变换,耍出种种花样,一边用柴刀敲打禾杠更换队形,一边男唱女和对唱山歌,是客家人载歌载舞、热爱生活的真实写照。竹杠舞是会昌洞头乡畲族传统舞蹈,持竿者身着漂亮的民族服饰,姿势有坐、蹲、站三种。舞者以“小跳步”和“踏步蹲”为基本步伐,在竹竿分合的瞬间,敏捷地进退跳跃,手脚顺着左右进退的韵律不断转圈,动作轻快明朗[6]。
诸多民俗体育活动充分体现了赣南独特的地域环境与农耕文化,是客家人求福、祭祀、祈祷的独特方式,反映客家人团结、尚武、勤劳、乐观的生活态度。表演运用道具模拟各种场景,融合了灯彩、军事、农作、舞蹈、说唱及地方吹打等元素,舞蹈动作粗犷优美,阵形流动变化万千。它不仅保留了古老汉族固有的优秀文化传统,还融会了畲、瑶等族的优秀文化和风俗,从而使得赣南客家民俗体育文化千情万种、独具特色,成为汉民族文化中光彩夺目的一页[7]。
(二)赣南客家民俗体育艺术形态的时代变迁
民俗艺术展演和民间信仰活动都是社会发展的产物,随着社会生存环境的改变,民俗体育活动也将产生量与质的改变。在早期,盾牌舞只局限于一对一演练,动作单一,侧重防守,后来逐步演变成二、三、四对一的攻防组合,并根据出灯的需要,结合一定的情境,编成了综合性舞段,在灯彩表演中有序进行。而鲤鱼灯最初只有简单的环节,如“积塔”“搭门”“上水”“钻泥”“过跋”等,舞时并不连贯,后经艺人不断创新和完善,将各个环节按故事情节、内容情景的需要进行艺术加工,增加“巡场”“出洞”“咬尾”“三盏球”“跳龙门”等环节,对表演者的动作要求更灵活轻捷,刚柔相济。表演者通过脚下细踏、碎步小跑,手腕的轻微颤动,步履轻盈,身子前俯窜腾、高低跳跃,把群鱼逐浪、团结一致、百折不挠、纵跳龙门表现得淋漓尽致,使鲤鱼舞整体内容不断趋于饱满,主题更鲜明。石城蚌壳舞在创编初期,只有渔夫的四角撒网、蚌壳姑娘运用外壳钳夹渔夫进行戏耍的动作,伴奏仅有锣鼓、唢呐,较为单调。历代艺人增添了人物、动作,如渔夫各种形态的“划水”、河鱼“鱼游”嬉戏、蚌壳姑娘的数量及各种动态舞姿;在画面构图上,加强队形调度,通过这些因素提升舞台艺术,增强演出效果。倒采茶是在“茶篮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集体歌舞。早期的茶篮灯也只有四人:一男舞宝伞灯,二女舞茶篮灯,一个老令婆(彩旦)穿插打诨,场面单调乏味,舞灯者女装男串,缺乏特色。但随着赣南茶业的日益兴盛,茶篮灯也慢慢成为茶贸往来时不可或缺的节目。首先,灯具和人物增多,茶篮由两只增为四只,另增添四只上扎八仙造型的“净瓶灯”。其次,人物由原来“一丑二旦夹个老令婆”四人,增到“一丑四旦八仙唱彩婆”的十三人。茶童(丑)舞步以“中桩步”为主,更融入如“钻山洞”“双踩步”“臀部花”等象形动作元素。茶女(旦)则以“碎踩步”“横碎步”“十字步”为主要舞步,配上各种手帕花(如右手虎口夹手帕,在腹前、胸前或头前上方做内挽花及绕∞形)及绣花、摘茶等动作。随着灯彩在业界的影响效应加大,各乡村和族祠也陆续成立了自己的灯队,以树威望,希冀在众多茶商交易中获取一席之地。
旧社会赣南民俗活动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逐步发展,每个灯彩的发展历程背后都隐约能看到当地商贾、大绅的背影。按过去习俗,耍灯的一般都是男子,即使有些灯中设有女角,因女性受封建枷锁禁锢,也不能“抛头露面”,如蚌壳舞中的蚌精、《茶灯》中的茶女也都由男子扮演。直至辛亥革命以后,男人剪长辫,女人放小脚,提倡男女平等,女性才开始参与灯彩活动。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妇女彻底解放,才正式走上舞台。赣南灯彩是一项热闹非凡的民间艺术活动,往往与龙灯混合展演,神秘而隆重。被信仰观念笼罩的舞灯者,情绪激昂,跑跳翻滚,十分活跃,在人神共舞中祈求风调雨顺,四季平安。随着当今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赣南灯彩民俗已逐步成为城乡人民活跃文化、娱乐生活,抒发喜悦之情的一种歌舞形式。
二、赣南客家民俗体育文化元素融入广场舞中的可行性分析
赣南传统民俗展演对道具、场景和参与者专项素质、协调性等要求较高,而现代广场舞则灵活简单、方便操作、通俗易学。如何将两者有机结合、融为一体?首先,应把握赣南民俗文化的根源和赣南地域舞蹈语汇,艺术性地去挖掘代表赣南客家民俗体育文化的标志性符号,与广场舞融合,并应注重当地人的生活习惯、文化背景,展现出赣南形象、赣南风情、赣南精神。其次,应从基本动作入手,以简单易学的指导思路进行舞蹈动作编排、演练和反复认证。最后,必然遵循的原则是创造性转化、创新型发展。文化内涵是舞蹈的生命之根,强化对赣南客家民俗体育文化原有资源进行反复遴选、提炼,对其进行分解、转变和重构,并进行创新性地利用和拓展,最终糅合到广场舞的编排中去,才能使广场舞富含客家民俗特色,具有深厚的赣南客家文化内涵和良好的操作性。
(一)形体元素与广场舞融合运用分析
客家先民自西晋起避乱南迁来到赣南,在岭上依山建房,开山凿田,过着“竹笕水,脚碓米”“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生活。客家先民日常劳作,形成了上山弯腰蹲屈、下山负重前倾、双手旁置以系平衡的身态;长期的山区生活,形成了屈膝、拧跨的习惯。一条扁担走天下的客家人有淳朴、厚道、坦荡的性格特征,这决定了男人动作朴实、粗犷、简练,女人轻快、细腻、柔美。赣南民俗体育是具有浓烈民族特色的艺术。如:赣县的云灯,其表演主要体现在一个“悠”字上,以左右摇摆云片似的“扭身步”为舞蹈的基本动作,配合以优雅、轻盈、缓慢的“双晃手”“张合片”“送片”“推磨”等动作[8],走出“窜花”“双出水”“圆串形”等队形,充分展现云彩悠悠飘浮的动态,给人以清雅柔逸的美感。这些形体元素节奏缓和、清雅舒适,融入广场舞不仅愉悦身心,提高中老年人的协调能力,而且还可以塑造美好的身体曲线。花灯表演多有“转灯”“举灯”“小蹬步”“小晃灯”“圆场”“踏步”等动作,舞姿时而对转,时而摆成圆圈,颠、颤、晃、摆的动律始终贯穿于每个环节。“摇”与“屈”,分别是客家女性、男性从事劳动的生活特征。艺人结合脚跟着地的“小脚步”和前脚掌着地的“拧步”,突出女角“摇”的神态,如春风摆柳,如檀香青烟,静稳轻柔[9],如鲤鱼摆尾,娇柔俏丽。而男性则多以屈膝的高桩、中桩、低桩表现男角的稳重、矫健的形态。这些动作难度适中,都非常适用于广场舞,可以分别对肩、颈、腰、胯、膝进行全方位的锻炼。广场舞锻炼时间较长,这样把局部与整体练习交错设计,既保证了一定的运动负荷又能兼顾群众的体能承载。赣南客家民俗演艺在形体节奏、动态控制上显示出扭、摇、屈、甩、摆、涮、颠、颤、晃等独具魅力的舞蹈形体动作差别。这些元素不仅具有大众化、群众性,而且对身体素质的要求不高。在突出赣南客家民俗体育传统性上进行提炼加以创新,将技巧部分分解成若干元素进行单项强化训练,融于广场舞将增添其动态之美及表现力,并给当地广场舞注入新的生命与活力。
(二)动作元素与广场舞融合运用分析
广场舞主要以健身为目的,参与人群多数没有舞蹈基础,要汲取、融入赣南客家民俗体育动作元素创作广场舞,动作结构不易太复杂,选择类型尽量多样化,以满足不同年龄阶段、不同层次人群的需要。安远作为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赣南采茶戏”的发源地,为了更好地保护与传承这一民俗体育文化精品,通过传统与现代有机融合的方式,创编并推出动作简易、难度适中、舞姿优美的“采茶戏广场舞”。在欢快活跃的赣南民歌《斑鸠调》中,“春天马格叫(呀哈嗨),春天斑鸠叫(呀哈嗨),斑鸠(里格)叫(咧)起,实在(里格)叫得好哇(一呀一子哟)……”赣南客家妹子右手持扇在头上、胸前或腰间舞着千姿百态的扇子花,“时而挽扇、时而抖扇、时而倾扇、时而翻扇、时而转扇、时而绞扇、时而扑扇、时而抢扇、时而簸扇”;左手随着右手的动作前后、左右、上下协调自由摆动;身体则配合着乐曲变换着动作、舞姿,用流畅的舞步、巧妙的队形、多变的节奏、大胆的创意,给人以高尚的艺术享受。赣南客家民俗体育元素与广场舞融合创造了典范。“采茶戏广场舞”成功的秘诀就在于撮取赣南客家独特的文化符号“矮子步、扇子花、单水袖、帕花”,营造了舞台的氛围。通过选取屈、蹲、转、耍、摆、摇、滑、搓、缠、绕、遮、飘、卷、甩、摆、吊、抛等肢体动作元素,再配上表演者丰富的表情、神态,不仅恰到好处地表现了客家茶农生活、生产的真实写照,而且还从不同侧面反映出客家人勤劳淳朴、积极进取、乐观向上的精神状态,使许多单凭乐器渲染很难完成的情景表现得淋漓尽致。因此,在筛选赣南客家民俗体育动作元素时,应尽量撮取客家独特的文化符号,坚持简单易学的原则辅以适当难度系数。如:赣南著名的摆云、窜花、摇彩等系列动作辅以优美的舞蹈形态,进行符合时代的适当创编,使其呈现的整体效果越来越多元化,并不断融合当代人审美标准的元素,艺术地展示了赣南客家人丰富多彩的生活。
(三)音乐元素与广场舞融合运用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流行音乐盛行,相对来说本土很多民间传统音乐都濒临失传。在广场舞配乐中广泛渗透民间音乐元素,广场舞将会作为一种积极主动的元素,推动我国民间音乐的传承。广场舞队大多由民众自发组成,表演形式简洁欢快,舞曲往往是大家所熟悉的,旋律轻快,动感十足。赣南客家演艺活动很主要的一个特色就是载歌载舞,与广场舞有异曲同工之妙。兴国山歌就最具代表性,在休闲娱乐活动中客家人即兴演唱和自由对唱,这种载歌载舞的形式自由、生动、活泼,通俗易懂。还有赣南茶灯、狮灯、马灯、鱼灯、船灯、荷灯等,这些灯彩与当地的民间舞蹈、民歌曲调巧妙结合在一起,营造出欢乐祥和、幸福平安、歌舞升平的喜庆氛围。除此之外,采茶戏、东河戏、南北词道情、古文以及表现美好爱情的十更里、九连环、十杯酒、骨排歌等曲调朗朗上口,节奏不紧不慢,语言刻画细腻,舞蹈与音乐密切结合,载歌载舞相互烘托[10]。可以结合广场舞动态主题编入“斑鸠调”“南北词”“风俗歌”“古文”等歌曲元素,并结合会昌花鼓、于都唢呐等传统乐器伴奏,营造情绪热烈、旋律欢快的赣南客家舞曲,融于广场舞尽情欢娱、演绎强烈的律动视觉及听觉效果。赣南民俗音乐元素是多姿多彩的,其中许多优秀元素经过简单地加工就可融入广场舞配乐中,无论是在调式、旋律还是节奏等方面都具有显著的客家风格和赣南地方特色。
(四)队阵元素与广场舞融合运用分析
广场舞是老百姓参与性较强的表演艺术形式,表演往往以集体形式出现,少则十几人多则几十人乃至上百人,场面欢腾红火。作为集体性舞蹈,除了动作优美、齐整以外,精致、灵动的队形变换也是广场舞表演不可或缺的部分。赣南客家民俗演艺常常出现于传统节庆、祭祀祈福,向来人声鼎沸,热闹非凡,习惯即兴发挥,但其内在的演绎形式始终坚守着一定的程式和规制,特别是在一些大型传统演艺活动上,这一点尤为突出。如在盾牌舞展演的队形结构上,其构图的变化,有八字形、荷包阵、四门阵、五方图、花牌阵等,在内在配合上始终依存着线条转变的次序,队列之间穿插快速、转换巧妙。较为复杂的要数采茶戏和马灯舞的阵队搭配,常以塔形花、葫芦花、品字花、圆形花、五梅花、双圈花及咬尾、千字状、五叶状、双打箍、绞绳子等为主,表演队形时散时聚,变幻无穷,图形、舞姿、灯具与音乐融为一体,场面蔚为壮观,令人应接不暇。把赣南民俗队阵元素融入广场舞可以较大程度丰富广场舞队形转变方式,增强动态表现力。融入队形设计上要根据人数细化设计方案,人数不多的情况可以考虑运用简单线条,如:斜线、直线、交叉线转变至三角形、棱形、五角形或复合多边形,从一个基本队形,通过错落有致地交叉、替换,变成另一个队形。如果人数较多可以按多重空间连线,如:波浪形、双圈、塔形、五梅等,通过旋转、分离、集中等进行队形转换,产生不断移动的舞蹈画面,使得整个队伍形成多重流动感,让人耳目一新。
(五)服饰、道具元素与广场舞融合运用分析
赣南客家很多民俗体育活动都巧妙地运用了服饰、道具元素,以增强表演的艺术性和表现力,如长绸、大襟、手帕、袖筒、罗帽、围裙、茶蓝、甑笊、禾杆、马灯等等。广场舞通常在空旷的广场演练,人数较多,融入赣南客家特色服饰、佩件装饰、图案等,或是借用民俗演艺道具,可以更好地彰显现场的气氛,使舞者身心愉悦,表现形式更趋于多样化。服饰是广场舞主题风格的直接体现,合适的服饰可以将广场舞动作衬托和表达得更好,具有提高整体舞台效果的作用。在选取赣南客家服饰的款式结构、首饰佩件、装饰图案融于广场舞的服装款式进行设计时,要根据广场舞的内容和塑造人物的形象出发,考虑服装、音乐与动作之间的关联性,以各种形式和色调去渲染角色的意象和情绪,烘托出不同舞蹈的不同感情色彩[11]。如三脚戏的服饰具有“头带一把抓(罗帽)、身穿三花衣、腰系白堂裙、脚穿灯笼裤”之特点[12];在采茶戏中,蓝衫、大红对襟长衣、翠绿彩裤、镶边对襟短装、扎绸缎巾是必不可少的搭配;而排银八仙的狗头帽、缀红绒球的绣花鞋及各色绣花的长短围兜,形成了赣南采茶舞蹈独特的风格特点[13],这些元素都可作为广场舞服饰创意的来源。
如果服饰是华彩,蕴含着客家情韵,那么道具则是渲染主干的墨迹。赣南民俗演艺通常运用道具来渲染气氛,如扇子、花棍、花灯、茶篮等等。在采茶戏中就惯用扇子来表达喜怒哀乐,常见为:心悦风车扇、怒气收折扇、悲哀哭头扇、乐极抛甩扇、自豪摇摆扇、潇洒风流扇、心烦滚球扇……全南瑶族则是运用花棍在身体的上下、前后、左右等多个方向抖动和转棍,结合步法及队形变化,形成一片壮观热闹的场面,来描摹赣南瑶族的生活情态。以赣南客家原生态的民俗道具为原型,用艺术的方式提纯、渲染、升华,呈现更贴近当代审美取向的道具元素,无疑是广场舞创编的一种补充效应。
三、结 语
不同的文化、不同的风俗习惯形成了不同地域的锻炼人群对舞蹈的选择,赣南客家民俗体育是赣南人民世代相传,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文化表现形式,深受当地群众喜爱。这些民间艺术形式凝聚着千百年来赣南客家先辈们的文化和精神,串联着赣南客家历史文化的时光转换,被誉为“赣南客家民系记忆的背影”。将传统的客家民俗形体、动作、音乐、队阵、服饰、道具等元素融入广场舞进行合理改进与创意,在保持赣南客家民俗体育特色的基础上,设计与创编赣南客家特色广场舞的表现形式,将吸引更多当地人的关注与参与。这不仅丰富了广场舞的舞蹈形式与内容,同时也促进了赣南客家民俗体育文化的继承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