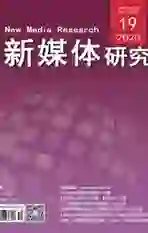媒介技术下“自我”与“他者”之间交流的困境
2020-02-04马娟
马娟
摘 要 随着社交媒介技术的日益发展,人们自我相处和与他人交流的方式随之发生了改变,我们误以为交流的便捷可以让我们远离孤独,但是随着这种社交网络的连接越发紧密和无缝隙,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却越来越觉得孤独。在媒介技术下生存的我们不能使我们的独处更具价值,也会经常遇到当我们渴望与别人建立关系时,明明很临近的人,我们会觉得远隔千山万水。奇怪的是,远隔千山万水的人又让我们觉得彼此很临近,这便是媒介技术带给我们的关系的错位。文章对自我交流和与他人交流的这两种情况做了分析论证,希望引起人们的关注,从而能够更加理性看待媒介技术在我们生活中的角色定位。
关键词 社交媒体;自我;他者;交流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0360(2020)19-0008-03
媒介技术迅速发展的当下,交流的方式已经变得更加方便快捷,交流的形式也越来越多样化。人们沉浸在媒介技术进步带来的交流的美妙和神奇的体验感之中,但即便技术已如此发达,人们对交流的渴望似乎并没有因此而得到满足。每一次媒介技术的更新换代,又都会引起人们对新的交流方式的体验感的又一次追逐,交流的使命好像是单纯的为了完成技术在其身上进行的一次次的实验,而忘记了人们为何交流的初衷。从古到今,人们都在渴望着通过媒介技术的发展来消除距离带来的隔阂和陌生,使远距离的交流越来越接近于“在场”的交流,认为距离本身就是唯一导致交流困难的因素。于是在这场追逐中,人们逐渐开始忽略交流本身的意义,转而寻求的是一种对“在线”的奇妙体验感。正如韩炳哲在《他者的消失》中所说的那样,“切近和疏远是辩证对立的。消除了远并不等于产生了近,相反,这恰恰也摧毁了近。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完全的无差别性。数字化的无差别性消除了切近与疏远的所有表现形式。”[ 1 ]因此,当我们沉迷在社交媒体营造出来的虚拟世界中无法自拔时,是不是也该偶尔回到现实世界来重新审视自我与周围的交流究竟处于何种状态,而不是一味沉迷。
1 对“自我”交流的忽视
在如今这个喧闹嘈杂的媒介环境下,人们很难静下心来倾听自己的内心,内心也早已失守。媒介技术几乎入侵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角角落落,我们似乎置于一个社交媒体条件下的全景监狱,我们对媒介技术毫无抵抗力,甘于被其控制或者奴役。“透明化和超交际夺走了保护着我们的内心世界。是的,我们是自愿放弃了内心世界,甘于受数字化网络的奴役,任由它们穿透、照透、刺透我们。”[ 1 ]韩炳哲看到了媒介技术对人带有侵略性的一面,每个人就好像是这座技术监狱里的“囚徒”,一言一行都被媒介技术所记录和利用,使我们变成一个个毫无差别和个性可言的人形木偶。与此同时,我们习惯了喧闹,习惯了将目光放在周围的事物上,而忽视自己的存在,对自我的认识也越来越模糊,因为我们将自己毫无保留的交付于媒介技术。
1.1 独处中的“第三者”
美国传播学家德弗勒等人在1975年出版的《大众传播学诸论》一书中提出了“媒介依赖理论”。他们在研究媒介系统、社会系统与受众系统三者之间的互动依存关系时发现,受众通过使用大众传媒获得特定的满足或达成一定的目标,而且在他们缺乏其他替代性方式的情况下,就很容易对大众传媒形成依赖[2]。
从当下来看,人们对媒介技术的依赖程度已经远远超出了人们对身边任何人或者任何事物的依赖。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在日常生活中难以离开手机,任何场合、任何时间,手机都如影随形。没有手机在手时的我们面对周遭时,会出现不安、焦虑等心理,即“无手机焦虑症”。国内外多项心理学研究表明,手机依赖和手机使用成瘾会像药物依赖一样,使人产生心理和行为障碍[ 3 ]。
这种对媒介的过度依赖,使我们毫不自知的沉浸在媒介技术带来的丰富多彩的世界中。每天都有应接不暇的新鲜事物走进我们的视野,我们和自己的独处因此变得更加困难,也不再那么纯粹。甚至我们开始害怕独自面对“孤零零的自己”,我们总想用声音和画面来填补独处时的空间,让“自我”至少在形式上不是孤单的。于是,在任何场合和任何时候我们的独处过程必须借由手机屏幕来完成,人们却也习以为常。只要有手机在,独处便成了最容易甚至也是最喜欢的事。这种看似好像是人在主动利用碎片化的时间不断的获取各种外界的信息,来帮助自我完成对自己和周围事物的认知的行为,在很大意义上其实是被动的。就如韩炳哲在《他者的消失》中所说的那样,“人们没有理解任何事情。然而知识却是基于理解的。大数据使思考变得多余。我们不假思索地任自己沉湎于‘事情就是这样”[ 1 ]。
1.2 没有“他者”,何谈“自我”
媒介技术带来的对遥远事物的临近感,让人们渐渐的不再认为自我的内在交流是必要的,它被我们与那些和我们自身毫无关联的事物的交流所替代,然而自我交流的过程却是任何媒介技术都无法帮助我们完成的。自我交流是我们面对其他一切交流的目的,当我们在自我交流的过程中发现了问题或遇到了障碍时,我们才需要通过其他的交流来寻找答案。可以说自我交流是目的,与他者的交流则是手段。当我们放弃或者忽视了“我”与“我”的交流时,我们所进行的其他交流也不能为我们带来任何的益处。
黑格尔说:“只有在一个他者的自我意识中,自我意识才能够达到满意的程度。”[4]也就是说我们每时每刻与“自我”在一起,但却没有通向“自我”的特权,我们要依赖别人才能认识自我。韩炳哲在《他者的消失》一书中说到,“数字化的全联网和全交际,并未使人们更容易遇见他者。相反,它恰恰会便于人们从陌生者和他者身边经过,无视他们的存在,寻找到志同道合者,从而导致我们的经验视野日渐狭窄。”[ 1 ]就是说当我们对“他者”越来越疏远,越来越模糊时,实际上我们也同时疏远了“自我”,我们不再关心内在的“自我”,放弃了与其交流。独处的时间被一种‘狂看的形式,即“毫无节制的呆视”所霸占,无时间限制的消费视频和电影,就是对现在的真實写照。各种网络综艺、电视节目等视频内容,使人们应接不暇,被这些花样翻新但实则完全相同的内容所吸引,直到失去了自我意识,自我相处被“自娱自乐”所侵吞,独处不再是我们与“自我”亲密交谈的机会也不再是一件能产生智慧的事。
2 与“他者”交流的无奈
媒介技术的发展为不在场的交流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它延伸了人的听觉和视觉甚至感觉,让距离不再成为阻碍交流的因素。但人们并不满足于此,仍在探索着更多的可能性。彼得斯在《交流的无奈》中说到:“看不见的东西,渴望愈加迫切;我们渴望交流,这说明,我们痛感社会关系的缺失。”[4]本以为我们整天游走于各类社交媒介,对于交流的渴望会被满足,社会关系的建立不再成为我们的困惑,可事实并非如此。
2.1 “在线”与“在场”的转换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社会学教授雪莉·特克尔通过研究发现,媒介技术带来更加便利的沟通的同时,也弱化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些人甚至因此而丧失了面对面交流的能力。从形式上看,社交媒介促使人们之间的联系似乎更密切,但实际上却让人们更焦虑和孤单。《群体性孤独》中说道:“我们为了连接而牺牲了对话。大家都熟悉这样的场景:家人在一起,不是交心,而是各自看电脑和手机;朋友聚会,不是面对面坐着叙旧,而是拼命刷新微博、微信;课堂上老师在讲,学生在网上聊天;会议中,别人在报告,听众在收发信息。”[2]她将这种状态称之为“群体性孤独”——大家似乎在一起,但实际上沉浸在自己的手机屏幕中,与周围的人并没有任何具体实在的联系。我们不再期待从别人身上获得安慰,转而向技术求救,将更多的期待给了技术。因此我们一旦脱离我们所依赖的媒介技术营造的这种虚拟社交空间,孤独感和失落感就会随之而来。
雪莉·特克尔为我们描述的上述场景在今天无处不在,我们无时不在感受。互联网和媒介技术的不断发展确实对人际交流带来了很多有益的影响,空间和时间的界限早已被打破,人们的社交圈也在不断的扩大。而梅隆大学的罗伯特·克劳特也早在1998年就发现,人们花在虚拟社交上的时间越多,与身边的人面对面沟通的时间就越少,媒介技术的渗透减少了我们的社会参与以及面对面的交流[ 3 ]。讽刺的就是,我们原以为是用来深化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技术,却让人们又与“孤独”产生了关联。
2.2 既是“连接”也是“剥夺”
现在我们将越来越多的时间和精力花费在手机和电脑上,回到现实中就变得冷漠,不善言谈甚至根本不愿参与线下社交。根据特克尔的理解,原因可以简单概括为三个方面。
其一,是互联网给我们提供了舒适便利的“浅层社交”,让交流成为一种迅速且简单的事。面对面社交与线上社交存在巨大差别,前者既存在很多不确定性且处理起来较为复杂,会带给我们交际的挫败感和无助感;线上社交风险可控,主动权在自己手中,还总能带给我们满足和愉悦。
其二,由于互联网是虚拟的社交平台,所以带给我们的友谊也只是虚假的想象。我们经常说到的所谓的“朋友圈”就是如此,这种命名方式一方面充满了亲密感,它默认了大家都是以“朋友”的方式在交往。既然能滥用“朋友”这个称呼,一方面也说明它只是在掩饰实质上的空洞和匮乏。特克尔认为,互联网社交的本质是一种单薄的、没有厚度的交往,为我们带来的只是碎片化的弱连接[2],也就是说这种虚拟的亲密关系一旦回到现实是很难经得住考验的。现在每个在社交媒体上的好友列表里至少都拥有几百位甚至上千位所谓的“好友”,在虚拟的网络中每个人似乎已经成为社交场中游刃有余、收获颇丰的“交际小能手”。这种热闹的表象背后,却暗含着一个悖论:我们的好友列表里可以拥有几百或上千个所谓的好友,但在遇到突发状况需要帮助时,大部分人的唯一选择就是他们的家人,那些停留在好友列表里的似乎只能是留在虚拟世界中的关系,无法延伸到现实。
其三,线上社交的时间占据了面对面与周围人交流的时间。如今,人们几乎都将社交的“主战场”放在了互联网上,所以我们与周围实实在在的人产生了疏离感和距离感也不足为奇。
苏格拉底在《斐多篇》的末尾对文字这种媒介的批评,在如今看來是一种预言。与当下人们对不断发展的新媒体技术的担忧以及对传播形式不断转变的担心十分相似,彼得斯在《交流的无奈》中谈到,“苏格拉底对文字的抱怨——削弱记忆力,缺乏互动,任意撒播,脱离说话人的灵魂——和20世纪末人们对电脑的担心、15世纪末人们对印刷术的担心,都不无相似之处。各种方式对人们亲临现场机会的剥夺,一直是人们对交流观念进行反思的一个起点。”[4]如今,我们面临的问题也是如此,我们沉浸在技术带来的幻觉中,渴望拉近与“他者”的关系,但却忽视和放弃了与周围人面对面的交流带给我们的近距离的接触的机会,让我们痛感社会关系的缺失。
3 结语
通过从“自我”交流和与“他者”交流这两方面来阐释如今我们所面临的交流的困境,这并不是说技术的发展使我们既无法做到真正的与“自我”的交流还带走了我们与“他者”的交流,从而否定媒介技术带来的进步意义。相反,技术为交流做出的贡献是我们有目共睹的事实。不是主张要放弃技术,而是我们应该将技术摆在合适的位置,不能“为技术是从”,要平衡好人与技术之间的关系。彼得斯在《交流的无奈》中提到,“媒介是不能喜爱的,只能够使用。我们作为匆匆过客的危险,就是混淆使用的东西和喜欢的东西”[4]。所以说,技术只是我们的手段和工具,我们不应该被工具本身而吸引就忘记了最终交流所要达到的目的。我们一直在不停地感受媒介技术带给我们的愉悦的体验,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我们为此付出了什么,正如韩炳哲在《他者的消失》中谈到的,“数字媒体磨平了他者的‘相对。实际上它们夺走了我们思念远者、触摸邻人的能力。它们用无距离代替了切近和疏远”[ 1 ]。当下的数字时代是人与技术共生的时代,主动权还是应该掌握在人自己手里。但大部分时候我们还是会不由自主的被技术牵着走,因为我们信任和依赖技术从而放弃了自己的智慧或者产生智慧的机会。所以当我们看到技术在进步的时候,也该提醒自己需要不断进步才能成为技术的主人,这种进步的体现方式就是我们自我感知的能力是否已被剥夺。
参考文献
[1]韩炳哲.他者的消失[M].吴琼,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
[2]雪莉·特克尔.群体性孤独:为什么我们对科技期待更多对彼此却不能更亲密[M].周逵,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2014.
[3]单波,叶琼.阅读《在一起孤独》:网络社交自我的不确定性与可能性[J].新闻大学,2019:45-59.
[4]彼得斯.交流的无奈:传播思想史[M].何道宽,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