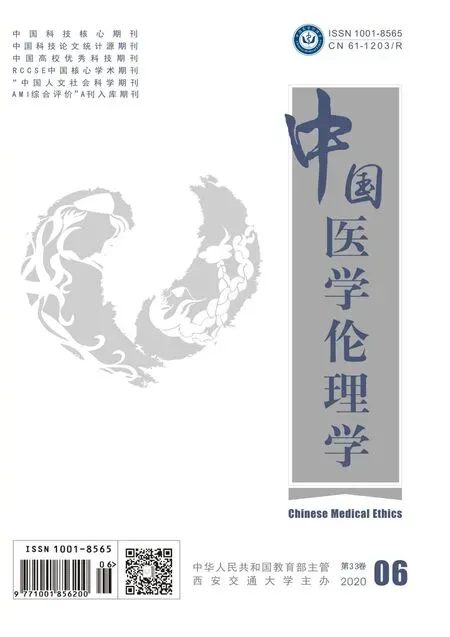当前供精辅助生育面临的伦理新问题及对策
2020-01-20吴红萍马彩虹
吴红萍,李 蓉,刘 平,马彩虹,乔 杰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生殖医学中心,北京 100191,hongpingwu@263.net)
人类生育力下降,不孕不育症等困扰已经成为影响人类生殖健康的主要问题。据世界卫生组织资料显示,平均每7对夫妇中就有一对育龄夫妇罹患不孕或不育症。辅助生殖技术(ART,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y)的出现为这些患者带去了福音。然而,自1978年在英国诞生世界第一例试管婴儿以来,辅助生殖技术一直面临着伦理纷争[1]。存在的最大挑战是性与生殖的分离( separation of sex from reproduction)[2],这对传统家庭中亲子关系的形成造成了巨大冲击[3]。尤其在配子捐赠技术中,卵母细胞和精子捐赠(供精)技术的使用会人为产生与传统家庭生育子代的亲子关系不一致的遗传学亲代关系。父母与子女的血缘关系与社会关系分离,从而会产生更加复杂的关系,这一直是伦理讨论的热点。在配子捐赠技术中由于精液及精液冷冻技术相对卵母细胞在资源获得和技术实施等方面相对简单,使得利用精子库精子供精在临床应用中相对容易,涉及人群数量更多,面临的伦理问题影响面更为广泛。
根据北京市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质量控制和改进中心资料显示[4],北京市2013—2015年行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卵胞浆内单精子注射(IVF/ICSI)助孕治疗的不孕不育患者病因构成中,男方因素约占40%,其中无精子症患者约占5.5%~6.2%。据统计,中国约有近百万家庭需要借助捐精生殖达到生育后代的目的[5],使用人类精子库的精子进行ART是无精子症患者可选的治疗方式。在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之前,供精生育的伦理热点集中在以下几方面:①家庭关系再确立,谁是出生孩子的合法父亲;②匿名的供者与子代知情权之间的权衡[6-7];③子代婚配近亲风险防范[8-9];④被决定出生的子代可能的权益,如继承权、抚养权等[10]。
在中国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之后,接受供精的家庭可能生育多个子女,除了上述的伦理困境外,将会产生更加复杂的关系。其中涉及多个遗传学亲代与社会学父母的关系以及供受者之间多个子代婚配伦理问题,这将使得供精辅助生育伦理面临更多新的问题。本文将从供精受者家庭角度出发,围绕伦理问题进行讨论。
1 当前ART广泛应用的伦理挑战
生育一个子代的供精受者家庭与供者之间每个家庭只有一个子代,受者子代父源遗传物质来源与供者、与供者子代为一代亲缘关系,两者之间二代子代也存在亲缘关系。
生育2个或以上子代,供受者之间的亲子关系,将有如下三种可能性:①1名供精受者的2名子代同时来源于同一名供者,同时供者也有两名后代;②2名子代中1名精子来源于供精,另一名来源于夫精;③供精受者家庭两名子代来源于不同的供精者。
在供精受者的两名子代父源遗传物质来源于同一名供者的情况下,尽管仍然存在与社会学父亲不一致的问题,但是这种关系在供精受者家庭中,面临的伦理挑战将会导致供精所面临的亲子关系认同、继承、赡养以及子代近亲婚配风险增加等问题。
1.1 近亲婚配概率增加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及人类精子库管理办法》规定[11],1名供精者的精液最多可使5名女性怀孕。在这种情况下,5名受者家庭中共可能产生10名左右的子代,供者家庭将存在2名左右的子代,这将可能有12名左右直系子女与父系遗传物质同源,同时子代又产生子代,将会有24名二代子代存在的可能性。此时将大大增加近亲婚配的风险。按照中国对近亲婚配的认定,二代子代为三代同源,婚配最好在五代之外方可有较小概率增加纯合遗传疾病的风险。有文献表明[12],供精者的后代有可能并未如我们所料分散在大基数人群中,而是由于某种地域性的原因,使得男性不育症高发,不育夫妇集中在相对较窄的区域,使得供精生育的后代有可能生活在相对较窄的区域中,这就从另一个方面增加了近亲婚配的风险。因此,在实施该类技术助孕时应明确告知其风险,如有需要,在子女到适婚年龄可协助排查子代近亲婚配的风险。
1.2 家庭中不同配子来源产生的子代可能的风险
两名子代一名精子来源于供者,另一名来源于夫精的情况。在这种情境下,来源于供精出生的子代将有可能处于不利地位,面临身份不认同的风险、继承权受歧视的风险以及由于此种身份所造成的认知及行为改变的风险。目前没有针对供精家庭中同时存在供者和夫精子代关于行为、心理等相应的文献研究。然而,一项在收养与非收养后代智商与学校表现的meta 分析表明,相较于非收养后代,收养后代在智商方面有较高的表现,而在社会交往方面落后于非收养后代[13]。较弱的社会交往能力同时与人的行为与心理健康相关,提示供精出生的子代可能处于不利的社会地位。因此,在与已有一名捐赠配子子代出生后再寻求助孕生育自己后代的夫妇沟通时,应注重强调此种风险的存在,引起患者夫妇的重视,尽量保护供精出生的子代利益。
1.3 供精子代知情权的争议
两名供精出生的子代来源于不同的供者。在这种情形下,受者家庭的两名子女的父源遗传物质分别来自于不同的供者,此时,该家庭将面临比较复杂的家庭伦理关系,即两名子代遗传物质来源于不同供者,并且与社会学父亲不同,即该家庭同时存在三名“父亲”。目前,我国仍采用匿名捐精方式招募供精者,供受者双方互盲,目的是保护供受者双方的隐私。但直到目前,仍存在着这样的呼声——供精出生的子代有知晓自身来源的权利。在一些国家尤其是北欧各国鉴于此种情形,已实施实名登记的配子捐献制度[14-15],或者要求使用供精的家庭在后代年满18岁后告知后代自己的遗传信息。在这种情形下,供精面临的社会、法律等多方面问题存在更多争议[16],如供精出生的孩子是否会寻求供者的信息以认祖归宗,或者由于家庭的变故致使供精出生的孩子受到遗弃,或者在一些特殊情境下,如重大疾病等情况需要血缘物质的支援,此时,来源于多个供精者的后代将面临知情权等困境。我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伦理原则》强调[17],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应考虑“有利于患者的原则”,同时也强调“保护后代的原则”。美国生殖医学联合委员会ASRM也出台相应的行业协会观点伦理指南[18],指出实施辅助生殖技术助孕除了要尽量帮助患者获得后代,同时医务工作者应考虑更加复杂的家庭关系所带来的伦理困境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种后果,并与患者进行充分沟通和知情告知,使患者夫妇充分了解和理解这种助孕方式可能带来的相应后果。
2 对策与实施
各辅助生殖机构已经意识到当前ART临床广泛应用所面临的挑战,并适时调整应对措施,在本着尽量不复杂化家庭关系的原则下做好相应的处理。
2.1 重视配子捐赠技术伦理审查操作规范的制度建设
配子捐赠技术一直是辅助生殖技术中伦理管理与争议的焦点,各机构应高度重视配子捐赠技术的伦理管理,按照辅助生殖技术伦理原则及技术规范,结合本机构实践,建立标准操作规程,对该项技术进行切实可行的管理与监督。
如建立常规生殖医学伦理委员会监督管理制度,科室常规伦理培训制度、讨论制度,在遇有特殊情况时的伦理审查制度,并遵循PDCA的管理循环模式进行知识总结与制度更新,培养并加强生殖医学医务工作者的辅助生殖伦理意识与能力,使其能够随时应对变化并在发生变化时找到应对策略。
2.2 加强学科建设,切实帮助患者解决技术层面问题
生殖医学机构应加强学科建设,提供必要的检查及诊疗手段,帮助患者明确诊断、理性选择。
供精人工授精的适应证包括除不可逆无精子症外,还有一部分是严重少精子症、弱精症和畸精症或者严重遗传性疾病等。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一些手段,如显微外科睾丸切开取精术、男性精子优选术[19]、胚胎种植前遗传学诊断、单基因疾病阻断的胚胎筛选等技术已经可以帮助这部分患者获得自己的遗传学后代而不需要选择精子库精子。如果条件所限,也应告知患者去了解以上技术及供精技术的利弊,帮助患者理性选择,尽量减少在一个家庭中出现不必要的既来源于供者后代,又来源于夫精的后代,以降低人为产生后代供养差异的可能性。
另外,在供精体外受精胚胎移植(IVF-D)中患者有冷冻胚胎的,应做好患者的解冻胚胎移植周期的处理,提高解冻移植周期成功率,减少在一个家庭使用多人供精产生后代的可能性。
2.3 加强多方联动,推进政策修订
在供精人工授精周期中,用精机构一般与精子库保持联络并及时给予用精结局反馈[20],在出台“二孩”政策之后,可以考虑与精子库商议再次发送与前次生育相匹配的精源,或者由精子库联络早前的供精捐献者,在完善必要检查化验后再次捐精,以不复杂化同一家庭的伦理关系。
另外,虽然目前中国的供精管理相较国际上一些国家政策较为严格,如一些国家允许供精者可使10个家庭产生后代,但为与中国传统公序良俗原则相匹配,也避免在较窄地域范围出现三代或者四代的近亲婚育,可考虑建议精子库一名捐献者的精子尽量发往不同的省市机构使用,在此基础上则可以考虑增加一名捐献者产生多名后代的可能性。
同时,加强与相关伦理、法律、社会学专家的沟通与合作,为患者提供切实有保障的信息咨询,并推动各个层面相应法律法规的制定与修订,全方位保障患者、后代与捐赠者的权益。
3 结论
总之,在进行辅助生殖助孕时,医务工作者应帮助患者尽量尝试生育自身后代,如果经过尝试仍不能助孕成功而需要选择捐赠配子助孕,则应与患者夫妇进行充分的沟通,使患者充分了解其中存在的子代健康及伦理风险,以便理性选择。
在使用供精辅助生殖助孕生育二孩的治疗中,各辅助生殖机构应重视实施辅助生殖技术助孕所面临的伦理复杂性,开展相应研究,关注不同遗传亲代出生后代的福祉问题,同时应关注多子女亲代未来近亲婚育的伦理风险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