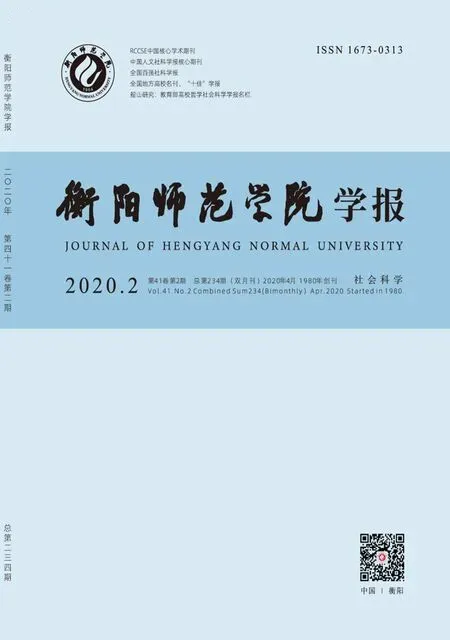胡寅正统观析议
2020-01-19刘小勤
刘小勤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广州 510225)
胡寅(1098-1156),字明仲,一字作仲刚,或作仲虎,学者称致堂先生,是南宋初年著名的理学家、政治家和文学家。胡寅与其父胡安国,弟胡宏、胡宁等共同创建了湖湘学派,对闽学和婺学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胡寅对政治的发展演变、王朝的兴衰更替,有着很清醒的认识。他说“天道周如循环兮,治与乱必因续”[1]15,认为一治一乱乃历史发展演变的规律。那么,它的原理是什么呢?或者说权力为什么失?又为什么得?胡寅的正统观可以说是对这些问题的探索。
一、北宋正统观概述
梁启超说:“正统之辨,昉于晋而盛于宋。”[2]而宋之“正统”论是在唐宋以来儒道复兴运动中出现的[3]。北宋时期,由于刚经历史上最黑暗的五代十国,这个时期用欧阳修的话就是“于此之时,天下大乱,中国之祸,篡弑相寻”[4]499,“置君犹易吏,变国若传舍”[4]2,“五十三年中间,易五姓十三君,而亡国被弑者八,长者不过十余岁,甚者三、四岁而亡”[4]2。由此,人们对赵宋政权合法性的论证提上日程,导致正统论兴起。北宋最早论述正统观念的是《册府元龟》。此书以五行说作为基础,认为历代王朝的正统地位是“乘时迭起”,是“上承天统”,属于接近政治神话的正统观。北宋中期的张方平继承了《册府元龟》中的五行思想,认为“夫帝王之作也,必膺箓受图,改正易号,定制度以大一统,推历数以叙五运,所以应天休命,与民更始”[5]94。张方平说的正统就是三代汉魏晋东晋北魏北周隋唐,认为这些朝代的更迭都合五德之运。这一观点颇具迷信色彩。
自欧阳修开始,人们就对这种五德终始说进行批判了。欧阳修在研究了历朝历代的发展变化之后,认为“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由不正与不一,然后正统之论作”[6],也即提出了两个判断正统与否的标准:“居正”和“一统”。司马光则认为君主存在之意义在于除社会之乱而保生民,他说“天生烝民,其势不能自治,必相与戴君以治之。苟能禁暴除害以保全其生,赏善罚恶使不至于乱,斯可谓之君矣”[5]110。他认为判断君主统治的合法性依据就在于是否有统一天下之事功,说“臣愚诚不足以识前代之正闰,窃以为苟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皆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实也”[5]110。司马光的保生民和一统天下其实是统一的,因为只有一统天下,社会安宁,才能使生民避免战乱从而全其生。
章望之对欧阳修给予霸道得天下者以“正统”之名表示强烈反对,并用“王霸之辨”驳欧阳修。他说:“予今分统为二名,曰正统、霸统。以功德而得天下者,其得者正统也。尧舜夏商周汉唐我宋其君也;得天下而无功德者,强而已矣,其得者霸统也,秦晋隋其君也。”[5]106他特别不满于欧阳修把秦和魏列于正统,认为这是善恶不分。他说:“予以谓进秦得矣,而未善也,进魏梁非也。凡为书者,将有补于治乱也。秦魏梁于统之得否未有损益焉可惜者,进之无以别善恶也。”[5]106
苏轼又著《后正统论》三篇,旗帜鲜明地支持欧阳修关于正统“居正”和“一统”的说法:“正统之论,起于欧阳子。为霸统之说,起于章子。二子之论,吾与欧阳子,故不得不与章子辨,以全欧阳子之说,而吾之说又因以明。”[5]103苏轼认为判断政权的正当性不应以道德作为标准,说章望之以善恶而非魏,其实是“未知夫名实之所在也”[5]106。由此他提出判断正统与否的标准就是“有天下云尔”[5]103,即注重现世之功业,因为有个统一而强大的政权,可以使得天下有法可依、有制可循,才能使生民免于战乱而全其生。
其实,苏轼对“得天下云尔”为正统的说法也是有点无奈,他说:“且吾岂不知居得其正之为正,如魏受之于汉,晋受之于魏,不如至公大义之为正也哉!盖亦有所不得已焉耳。”[5]105就是说,肯定是要以“正”判定“统”的,只是这个“正”是“天下之正”,而章望之的“正”是“一身之正”。他说:“且章子之所谓正者何也?以一身之正位正耶?以天下有君为正耶?一身之正是天下之私正也。天下无君,篡君出而制天下,汤武既没,吾安所取正哉?故篡君者,亦当时之正而已。”[5]104
可以看到,北宋关于什么是正统有两种倾向:其一,慢慢摆脱了自汉唐的五德终始和天人感应的神秘色彩,基本上以天下“一统”为标准;其二,以“居正”作为标准,只是对“居正”之“正”是君主之一身之正还是天下之正则有争议。正统观发展至南宋,一来由于天理观的发展成熟,二来由于所剩半壁江山的逼仄,使得正统观又有一个很大的转型。就如饶宗颐所说,历史始终螺旋式地上升,其实是有杆秤的,所谓“历史之秤谓之正”[5]7,这个秤星如果不是如朱维铮所说的“道德批评”[5]7,那么是什么呢?
二、胡寅“以天德居天位”论正统
熊十力说:“凡政治哲学上大思想家,其立论足开学派者,必其思想于形而上学有根据。”[7]古典儒家政治道义的形上学依据是天、天道、天命、圣德。当儒学发展至宋代,进入了哲理化的阶段,即理学阶段,政治哲学的形上学根据就是“理”“气”“性”或者“心”。胡寅先以“气-理”的逻辑结构,考察了“气”与“物”、“物”与“理”、“理”与“心”等关系,突出了君主居天位的天德,从而论证君主权力之合法性。
1.胡寅“气”的宇宙本原
首先,天地有终始,起始于“阴阳之气”。对于天地宇宙的形成,孔孟二圣没有相关论说。那么天地宇宙有没有始源呢?胡寅说:“阴阳者,天地之气也;造化者,天地之事也;乾坤者,天地之性也;覆载者,天地之德也。”[8]477他认为:阴阳乃是天地之气,造化乃是天地之事,乾坤乃天地之性,而覆载是天地之德;而天地、日月、四时、万事万物乃由“阴阳之气”形成,“阴阳之气,分为天地,凝为日月,转为四时,散为万物。升降、晦明、消息、聚散,皆气之运,未有能外之而独立者也”[1]628。阴阳之气,分为天地,日月为气之聚,万物为气之散,所谓升与降、晦与明、消与息、聚与散都是气的运化,没有能够脱离气之运化而独立存在的事物。天地万物为气之积,而天与地是积“气”最多的:
“天者,积气之极,非有形色。今以物观之,轻清之气必上浮,重浊之质必下坠。天地,物之最大者也,故知天者积气之极也。日月星辰,积气之有光耀者也。风雷电霆霜露雨雪,气之感触变动升降聚散而为之者也。如此观之,岂不简易明白,人可共知乎”[1]779。
胡寅认为天与地是积气之最大者,日月星辰是积有光耀的气而成,风雨雷电霜雪露水是由于气的升降聚散感触变动而成,所以宇宙万物之本原就是“气”。
其次,人乃“气之最秀者”。胡寅关于“气”的宇宙生成论,其目的是要落实到人。他说:
“盖通天下一气耳,大而为天地,细而为昆虫,明而为日月,幽而为鬼神,皆囿乎一气,而人则气之最秀者也。”[1]431
他认为天地万物乃气之所生,大至天地,小至昆虫,日月鬼神皆为气运之所然,气之明就是日月,气之暗则是鬼神。而人,是得气之最秀者。不过,由于禀气之不同,所以人又有愚智勇怯之不同。他说:
“人之禀气不同,或昏、或明、或巧、或拙,或静、或躁,或刚、或柔,千条万端,非一言可尽也。脍炙人所共嗜,而有好食疮痂者。昼夜人所共由,而有俾昼作夜者。方王泽将息,佛教未来,凡趋静厌事之流,亦为山林之行,往而不返。如接舆、荷蒉、长沮、桀溺,乃其所见偏蔽,舍此取彼,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文王之道,圣人不取也。”[1]650
人由于得气之最秀,所以能与天相互感应。那么,岁有丰凶之别,人有生老病死,国家有兵革之难,自有天地以来就在所难免,都是大气化运、人事所致。于此他将宇宙本原和人作了勾连。
2.胡寅理气一体的本体论
天地万物乃气之所积,而气之运化聚散则是顺理而行。胡寅说“若非形气,必无可见之理”[1]718,认为假如没有“形气”,那么就没有可见之“理”,所以“理”蕴含于万事万物之中。而且“理”并非虚,而是实,胡寅说“要知万理无不实,聚散一致此焉悟”[1]36。胡寅的“理”继承了胡安国关于“道”的讲法:“冬裘夏葛,饥食渴饮,昼坐入息……只此是道”[9],说“饥而食,渴而饮,动静皆然,天理之自然也。然众人由之而不知,故饭蔬饮水,箪食一瓢,虽孔、颜之乐,不为之变焉”[1]649。显然,他们的“道”或“理”已经上升到形而上的本体层次。
首先,天理内化于经验世界,是物理。胡寅认为天理是宇宙生成之理。胡寅说:
“天地之间,形运于气。气,阴阳也,絪緼浑沦,未尝相离,故散为万物,消息而不穷,形气合而理事著……阳推五福,以类而升,阴推六极,以类而降,灾祥以类而应,万物以类而聚,是故君子慎所类焉,不使类之乱也。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以类相从故也。天之报施,无言可闻,无象可见,而理不可诬,或大或小,或迟或速,未有不以类而应者也。”[8]271
他认为天地之间都是气的运行。气有阴阳,阴阳二气相互交感,则化生天地万物,由此产生了日月、寒暑、岁时、古今,也产生了各种类别的人,善的、恶的、圣贤的、愚蠢不肖的等等。阴阳推动的五福、六极,都因类而升而降,所以灾祥祸福以类而应,万物以类而聚。积善之家会有吉祥嘉庆,不积善之家则会留有祸害,这种天之施报,虽然听不到,看不见,却是“理”所当然。宇文泰问苏绰阴阳造化之始,胡寅顺着苏绰的话头说:天地造化,虽然五经并没有记载其有始无始,但是“易有太极,是生两仪,既曰生,是其始矣。天下未有不可知之理也。异端之学,不知天地、日月、星辰、风雨、雷霆之故者,以理为障也”[8]477,就是说太极生阴阳两极,继而生天地万物,其实是天理之使然。
其次,天理内化于人间社会,是人理。胡寅认为高高在上的天理,内化于经验世界,则是物理;内化于人间社会,则是人理。那么,对君主权力的合法性也就有了天理的角度,因此朝代更替就是“顺乎天而应乎人”:
“在《易》之‘革’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未闻应天也。应者,对感而为言;人事作于下,则天理应乎上,岂曰天感乎上,而人应乎下欤!为是言者,不知天之为天矣。故《易》惟曰‘顺乎天’,顺天者,顺理也。”[8]436
之所以有汤武革命,因为它顺乎天、顺乎理。他说,在三代之时,因为尧、舜、禹、文、武、周公对于百姓是既养又教,没有夭亡疾病之灾,没有兵革杀戮之祸,父子子孙连续十代都处在太平之世,社会规模达到一千万户以上,就因为“王者代天理物,于是为尽矣”[8]754。
胡寅又说:“天常者,天命在人之常理也。常理者,父子、君臣、夫妇之大伦也。父道、君道、夫道,于伦为尊。子道、臣道、妇道,于伦为卑。卑屈于尊,理不可易也。”[1]760
他认为父子、君臣、夫妇等种种人伦都是常理。在人伦中,父、君、夫处于尊位,而子、臣、妇则处于卑位,卑位屈于尊位。这上下等级的严格确立,使得社会礼义必有所措。这是不可易之理,并非人以智巧强而为之。这样,胡寅就在本体的基础上把君主的合法性树立起来了。他说“若不申著君臣之义以立国政,则乾纲解纽,贼乱迹接,人欲放肆,天理沦灭,亦何所不至哉”[1]492,“子拜父、臣拜君,自有天地以来未之有改,所谓天之常理,国之典宪也”[1]762,认为大臣拜君主,自有天地以来从没有更改过,这是天之常理,国家之典宪。
再次,圣人“以天德居天位”。胡寅之父胡安国花一生之力注《春秋》,认为《春秋》所记载就是天子之事。胡安国表示,当周道衰微,诸侯放恣,人欲肆虐天理毁灭的时候,孔子就是天理之所在,他笔削春秋,重新树立五典、无礼、五服,五刑,借鲁史以寓王法,以拨乱反正,所以“圣人以天自处”,即圣人虽然无其位,却能托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权,遏人欲于横流,存天理于既灭。仲尼之所以能“以天自处”,因其就是至高无上的“天理”之代言人。胡安国说:“仲尼一言威重于三军,亦顺于理而已矣。故天下莫大于理,而强众不与焉。”[10]胡寅继承了父亲圣人“以天自处”的观点,说文王“虽身不有天下,而后世推原得天下之始,则自为西伯时,实受天命矣”[1]432,认为文王之所以尚未有天位,却是享国五十年,因为其有德而圣,继而有位。
《易传》既有“圣人之大宝曰位”说法,也有“崇高莫大乎富贵”的说法。胡寅说,那都不是以利益以言之,而是以德以言之:“中天下而立,负黼扆而朝,所谓天位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非私富也,天生民而立之君,非私贵也;以天德居天位,贵为天子,而富有天下,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也,岂为一人之身而有是哉。”[8]346-347
所以圣人有德而王。那么孔子的“以天自处”和后周宣帝的“自称天元,后称天后,居称天台,制称天制,敕称天敕,杖称天杖”[8]539有什么不同呢?也是“以天自处”吗?胡寅先解释孔子的“以天自处”,说孔子只是怕人们名实不副,所以给天冠之以“王”的名,将“王”系之于天。“孔子所云者,高明无私之理也。名不可拟,而理乃可,则是理也,叙之为五典,秩之为五礼,章之为五服,用之为五刑”[8]539,假如宣帝能够尽此高明无私之理,当然可以称天王。问题是其权力却是僭伪而来,“惟不顺乎理也”,所以五典、五礼、五服、五刑皆亡,怎么算是“以天自处”呢?所以孔子以至圣之资,加王于天,作《春秋》,代周室赏罚之权,载治国平天下之理,“两汉而下,自非大无道之君,未有不致敬孔子者,以其为人伦之至尔;敬其人,当遵其教,法其事,然后不悖于道;徒敬其人而不遵其教、法其事,则于道必悖。故有天下者,用《春秋》之法,以‘天王’为号,则名正理备,而尊不可以加矣”[8]470。胡寅又说“古圣人有同是道者,尧、舜、文王而已矣”[8]100。胡寅论证了权力来自圣德,也使得一直以来的天命崇拜转向了圣德崇拜。
不过,胡寅所认为的“以天德居天位”的圣人和君主乃为一体,因为君主有其位必须有德,所谓“天理固自若”。他说:
“称皇帝,据中土,虽无其德而有其位也。夫有其德而无其位者,人必以位期之;居其位而无其德者,人亦必以德望之。天人一也,故虽昏庸之君,垂亡之世,天理固自若也。”[8]1081
他认为君主必须是有圣德而有其位,这乃是天理之彰显。对于有圣德而没有位的,百姓必定期望其得位;对于居其位而没有圣德者,百姓也必定希望其能有道德,天理一如既往,依然如此。不管是说朝代更替必须顺乎天理,还是说君主有位必须有其德乃是遵乎天理,都可看到胡寅将“天理”视为社会发展的历史法则和人文价值,同时也是一种历史的责任和使命,更是君主统治合法性的重要依据。
胡寅构建了一个气化宇宙系统,而人“得气之最秀者”,认为人是最具灵知的气化之物。不管是自然还是人类社会都是顺理而行。在人伦社会之中,王者代天理物,是天地间具备能动性和自觉性的力量,使万物各安其位、各适其宜,由此奠定了统治天地万物的合法性。而且,由于自中唐以来道统意识的发展,“道高于君”“以道事君”对宋代天理观有很大影响,胡安国的“圣人以天自处”和胡寅的“以天德居天位”对君主形成了某种程度上的约束。只是胡寅又把君主和天德有机整合,使得君主统治权力具有了天理的合法性,从而给现实的赵宋王权合法性作了论证。
三、以文化论正统
宋廷南渡,地域从之前的整个中国落为只有长江以南,对于金国,已经没有唐太宗当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的大国心态,由此,南宋诸子对于华夷问题已经变得非常严谨。就像葛兆光所说的那样,宋代的政治合法性或者正统学说来自于外界(夷狄)的促使,并没有内在的质疑[11],所以胡安国他们热衷于夷夏之辨。胡寅也从学理上论证夷夏之不同,以文化的优越性论证华夏文明立于中原大地之合法性。
首先,以“气”区分华夷。天地与人皆由气所生成,但由于禀气之不同,不仅导致人之不同,中国和夷狄也有所不同。胡寅说:
“天无不覆,地无不载,而中国,夷狄之不可同处,亦非人为,乃天地之气,有淳正偏驳之殊也。”[8]621
“天地虽大,然中央者,气之正也。以人物观之,非东夷、西戎、南蛮、北狄所可比也。天地舆人均是一气,生于地者既如此,则精气之着乎天者亦必然矣。”[1]642
胡寅认为天地之气有着淳正和偏驳的不同。处在中央之地的中国,其气是为淳正,而夷狄之气则属偏驳,所以中国和夷狄当然不同。只是,华夷并不是天生不同,那圣人为什么会内华夏而外夷狄,以戎狄为贼而以中国为贵?他说:
“天之生人,有华夷之分乎?曰:否。然则圣人内华而外夷,贱戎狄而贵中国,无乃与天异乎?曰:使夷狄而为中国之事,是亦中国矣;惟其不仁不义,贪得而嗜杀,非人理也,故贱而外之,恶其以所行者乱中国而沦胥也。曰:天之生人,无华夷之分,则夷狄何为不仁不义、贪得而嗜杀,与人理异乎?曰:均五行之气也,而有圣哲,有昏愚,非天私于圣哲而靳于昏愚也;均覆载之内也,而有中国,有夷狄,非天美于中国而恶于夷狄也;所钟有粹驳偏正之不齐,则其分自尔殊矣。”[8]245-246
他认为:夷狄到华夏大地,使用华夏的文化习俗,就会成为华夏族;夷狄之所以是夷狄,就在于其不仁不义,唯利是图,贪婪而嗜杀,不合人理。而夷狄和中国乃是因气有偏驳,各异类别,所以有圣哲和昏愚之不同,这造就了天地中央和四方在地理、制度和文化等的不同。显然,中国之气纯粹而正直,夷狄之气则驳杂而偏邪,中国与夷狄之别是非常显然的。
其次,中国有仁义而夷狄无大伦。由于气之不同,中国行仁义而出圣哲,夷狄则贪婪嗜杀而无大伦。胡寅说:
“中国之为中国,以有仁义也。仁莫大乎爱亲,义莫大乎尊君,仁义立然后人理存,天道顺。若子不顾其亲,臣不顾其君,惟利害是论,苟利于己则从之,是以小人夷狄自处,何以治小人而服夷狄哉。”[8]261
胡寅在评论晋史时说,石勒派遣使者来和晋朝修好,因为石勒曾掳晋朝怀帝和憨帝,所以晋成帝严词拒绝,下诏焚烧使者带来的礼物。他很肯定成帝的做法,认为中国之所为中国,就在于有仁义。成帝不忘宗国之愤,不弃君父之怨,有仁义然后存人理,顺天道;而夷狄之人,却是唯利是图,不仁、不智、无礼、无义兼之。这就是中国和夷狄最大的不同。
再次,华夷是主从、首足的关系。古圣贤向来内中国而外夷狄,认为中国与夷狄的关系,是一种内外的关系。胡寅引贾谊的话说“天子者,天下之首也,蛮夷者,天下之足也”[8]1046,认为华夷是头和手足的关系,所以即使契丹再强,也是蛮夷,河东再弱小,也是中国。对于契丹作册书,任命石敬瑭为大晋皇帝的事,胡寅就认为实在不可。他认为,契丹作为夷狄却反而居上,实在是人道之大变,天理之反常,就像孟子说的“吾闻用夏变夷,未闻变于夷者”。华夷关系既是首足关系,也是主从关系,胡寅说:“君令臣从,父令子从,夫令妇从,中国令夷狄从,理之正也。一失其理,则君听于臣,父听于子,夫听于妇,中国听于夷狄,而天下不任其乱矣。”[8]1048
面对蒙、金逼国的紧急局势,胡寅对华夷关系变得极其严谨,反复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强调区分华夷,贬斥夷狄,认为夷狄人面兽心,野蛮不知礼仪,不服王化,残忍暴虐。但是胡寅并不是否认夷狄存在的合理性,而是认为华夏与夷狄在文化上有着大不同,华夏由于有着发达的文化,相对于夷狄有着巨大的优越性,也引领着文化发展的方向,从而树立赵宋偏安政权的合法性和正统性。
四、胡寅以“天之公也”论正统
宋明理学与汉唐儒学最大不同在于将“天”提升至本体层面,对于统治政权正统的论证也从神魅到了天理。由于天理的抽象性和普世性,“公”自中唐慢慢地发展成为一个颇具独立性和抽象性的价值,从一个伦理性很强的概念发展至公共性很强的概念,使得士人对人主之天位的理解不再域于“一姓之永祀”,而认为是来自天下之“公”,极大地影响了宋代及后世明清社会的政治哲学。胡寅非常明确地提出了天下福祉并非只为一姓之私,而是为天下之公。
首先,以“天之公”论政权之正统。胡寅说:
“惟天为大,惟天为公,惟天聪明,惟天威怒,故有天下国家者必畏天,以帝王虽大,未若天之大也,王法虽公,未若天之公也,一人虽聪明,未若天之聪明也,人主虽威怒,未若天之威怒也。天无不覆,而帝王有不及覆者矣,故曰未若天之大也。天无非理,而王法容有不尽理者矣,故曰未若天之公也。”[8]309-310
天是至高无上的,所以君主必须对天心存畏惧,因为帝王之大肯定比不上天之大,王法之公也比不上天之公,人主之聪明也比不过天聪明,人主之威严也比不过天之威严,相对于天之覆盖所有、天之无非都是理而言,帝王依然是有所不能覆盖的,王法依然是有不尽理的地方。天是那么的至高无上和完美之至,“故有天下国家者,必畏天道”[8]310。胡寅又沿用孔子的话说“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认为“王者奉三无私以劳天下,可谓民之父母矣”[8]782,即君主只有秉天地日月般之公心以服务于天下,行天下之公义,才可以说是百姓之父母。由此可看到胡寅将“公”的价值作为判断君主统治合法性的重要要素。
其次,权力为天下之公,而非一姓之私。胡寅说:
“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治其乱,养其生,成其性而已矣,非为它也。自羲、农以来,天下非一姓所御,以天言之,惟德是辅而无私亲,以人言之,惟惠之怀而无私与;若其淫虐肆于民,上弃天地之性,则天人同疾,而伐之者至矣。”[8]387
他认为,君王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天生百姓,以君主治百姓之乱、养百姓生活,这些都是顺性而已。自伏羲、神农以来,天下就不是只为一姓之君王所控制,以天而言,天只选择公正无私、品德高尚的人;以民而言,民只选择对自己有惠泽的人。假若君王对民骄奢淫逸,那就是抛弃天地之性,会被上天与百姓一起诟疾,而征伐者也会随之而至。这是为什么尧会把位传给舜而不是传给儿子丹朱、舜把位传给禹而不是商均的原因,一定要选贤人为君王,所谓“尧、舜以天下为公,选贤而付,故乱不生”[8]984。
胡寅认为君王要因天下之公而选贤与能,大臣不管进言还是论事,也要以公天下为取向。唐太宗在封陈叔达为礼部尚书时说,之前罢叔达相很感到内疚,因叔达在武德年间曾为他慷慨进言、排危解难,他时刻铭记在心,如今让叔达担任礼部尚书,算是作为报答。可陈叔达却很淡然地说“臣当日之言,非为陛下,乃社稷之计耳”[8]630。
五、胡寅正统观的特点及对其评价
宋廷南渡,地域从之前的整个中国落为只剩半壁江山,而且异族还在步步紧逼。赵宋已经没有唐太宗当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的心态——那是一个身处多娇江山、心怀天下的大国心态,而且还得以夷狄为非,努力地为赵宋统治中原大地的合法性而论证。时代不同,心境不同,胸怀不同,当然眼界也不同。概而言之,胡寅的正统观有三个特点。
第一,有着浓郁的理学色彩。胡寅继承了北宋以来的理学之风,以天理论证君主权力之正统,所谓“天理固自若也”。既在至高的宇宙本体层面论证了赵宋统治的权威,又将北宋以来正统观中的“居正”之“正”即君主的道德提升至天理层次,成为君主得天位的“天德”。
第二,有着浓郁的时代特色。胡寅以“气”、仁义、首足区分华夷,将文化之别折射于空间之别,以文化之正统论证政权之正统,最终证明华夏文化居于中原大地之合法,彰显南宋君主统治的正统。就像葛兆光说的,也正由于夷夏之辨,宋代“中国”意识凸显,成为了近世民族主义思想的一个远源[11]。从先秦以来的天下主义转向民族主义,虽然只是民族主义的萌芽,但那也可以说,这实在是因外族进逼这个时代因素的促使才有的历史性转变。
第三,“天下之公”符合开阔而远大的古今之通义。胡寅虽然没有顺着北宋欧阳修、苏轼等人所谓“一统”之空间之义,却继承了他们论证“一统”的思想基础,即保护生民之生命。他非常明确地提出天下福祉并非只为一姓之私,而是天下之公,表达了他类似苏轼的“有天下云尔”,即认为现世之功业给予生民免于战乱而全其生的良善愿望。在政治专制思想专制的宋王朝,这体现了思想家们处于狭缝中对天理的仰望和对民生之关怀。
胡寅以天理之“正”、文化之“正”和天下之“公”论正统,既夯实了北宋以来以“正”论“统”的理论,又呈现出从形上学理据到社会政治价值的系统性。后来王船山关于正统的“古今之通义”就是指“生民之生命”,把百姓的生命财产作为一切政治制度最根本的政治原则,由此修正了儒家向来的致善主义,认为判断历史之秤的秤星已经不只是“道德”,还包括了更为广阔更为客观的生民之性命与福祉,即是以“公”而不是以“善”作为政治价值,对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想萌芽有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