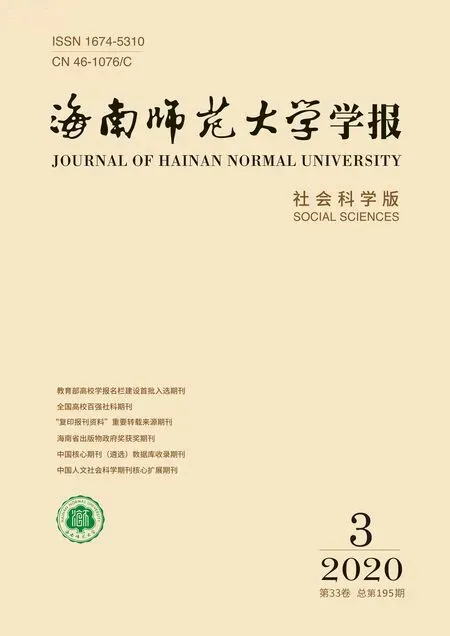灿烂的城市与暗淡的乡村
——陈力娇小说的空间叙事
2020-01-19黄大军
黄大军
(牡丹江师范学院 文学院 ,黑龙江 牡丹江 157011)
黑龙江作家陈力娇是一位极富才情、极具个性的小说家。她以勤于笔耕、敏于探索的创作姿态开疆拓土、铸就传奇,现已发表作品300余万字,相继推出中短篇小说集《戏园》(1996)、《平民百姓》(2002)、《非常邻里》(2010)、《青花瓷碗》(2012)、《我们爱狼》(2013),小小说集《不朽的情人》(2007)、《赢你一生》(2009)、《爸爸,我是卡拉》(2010)、《米桥的王国》(2014),长篇小说《草本爱情》(2006)、《红灯笼》(2019),散文集《面对世界举杯》(2013)等10余种。陈力娇的创作视域囊括小说、散文、文学评论等多个方面,尤以小小说成就最为突出,曾折桂全国小小说优秀作品奖、小小说金麻雀奖。在小说界,她以小小说、中短篇小说以及长篇小说诸体兼备、争奇斗艳的创作蜚声文坛,堪称新世纪小说园地内成长起来的一株根深叶茂、华盖擎天的大树。对于陈力娇的小说,有人关注其笔下的“地母情怀”,有人肯定其婚恋叙事,有人赞誉其个性化的艺术创造,有人发掘其文本的人性畸变等。笔者认为,这种关于作家作品阐释的多样性,表明陈力娇不仅是一位复杂的、有创造力的实力派作家,更是一位前景广阔、体量厚重的优秀作家。
一、以空间书写城市:陈力娇小说的空间转向
放眼世界历史进程,“城市的发展和世界的城市化是现代时期最令人瞩目的事实之一。”(1)孙逊,杨剑龙:《阅读城市》,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第4页。一个世纪前,世界上只有十分之二的居民生活在城市中,而现在,全球大多数人都已栖居城市。中国城市化起步较晚,不仅落后世界平均水平50年,甚至落后某些发展中国家20年。伴随着20世纪90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确立和逐步完善,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步入加速发展时期。到2018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已达到59.58%,这说明中国正在实现从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的转变,城市在中国社会日益扮演主导性角色。这一方面体现在城市生活方式在当今社会中已取得支配性地位,另一方面则体现在城市精神与城市理想正向城市以外的地区无限蔓延。空间学家发现,“城市的根本属性是空间性。空间性的关键是人的集聚”(2)[美]爱德华·索亚:《以空间书写城市》,强乃社译,《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特别是“工商业,金融和行政机构及活动,交通和通讯线路,新闻、广播电台、剧院、图书馆、博物馆、音乐厅、歌剧院、医院、大学、高等教育机构、研究和出版中心等文化和娱乐设施,职业团体以及宗教和福利机构”(3)孙逊,杨剑龙:《阅读城市》,第5页。在城市的集中,让“我们身处同时性的时代中,处在一个并置的年代”,福柯称“这是远近的年代、比肩的年代、星罗散布的年代。”(4)包亚明:《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8页。在这个空间纪元的时刻,人们发现由时间发展出来的世界经验远少于由空间所形成的世界经验,“空间在当今构成了我们所关注的理论和体系的范围”(5)包亚明:《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第18-19页。,“我们时代的焦虑与空间有着根本的关系,比之与时间的关系更甚。”(6)包亚明:《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第20页。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理解现代世界与现代生活,空间视角自有其理论优势。
陈力娇既有乡镇生活经验,又有城市生活经验。在乡村与城市之间,陈力娇不存在任何价值两难与认同困境,她是斩钉截铁的城市主义者。在中国现当代小说城市话语的百年流变中,虽有批判话语、认同话语与反思话语等多副面孔,但与乡土小说繁花似锦的美学实践相比,城市小说作为“被压抑的现代性”只能暗香浮动、伺机待发。这与城市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起的正面价值和引领作用是不对等的。个中原因,固然与中国农民文化传统强大,城市发展缓慢有关,其实也与作家对城市的个人体验与主观评价大有关系。正是后者,成就了陈力娇走近城市、融入城市、写好城市的冲动与意志。早年,陈力娇写过一篇题为《城市离我越来越近》的文章,不加掩饰地道出了个人的城市梦想。如其所言:“我向往城市,向往高层次对话,向往现实的高雅化。”(7)陈力娇:《城市离我越来越近》,《文艺评论》1998年第1期。在这一点上,陈力娇显现出了艺术家的敏感神经与十足的文化现代性。她说自己的家乡明水县固然四通八达、襟怀宽大,但与一百八十公里以外的哈尔滨、齐齐哈尔、大庆等周边城市相比,不仅政治、经济、文化与交通相形见绌、不可企及,而且这个家乡就像一个瘦弱的孩子,在向周边城市不断输血之后,自己只余留一片空寂、空虚与空白。如其悲叹的那样,“我对家乡实在没什么特别的感受,家乡对于我只是荒芜、贫瘠、缓慢、固执不前,有的只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绵延不断的愤怨。”(8)陈力娇:《城市离我越来越近》,《文艺评论》1998年第1期。正是这种苦涩、沧桑的家乡经验让其将寻找精神家园的目光转向了城市与远方。作为城市现代性的忠实勘察者,陈力娇通过从多种多样的城市使用者——“当地人”或“外来户”身上搜集故事,一方面对城市人与城市空间的关系加以观照,另一方面则对城市语言、文化意义与权力关系的建构、表现和复制做出解码。因此,其文学经验是与地方城市发展的具体状况相辅相成的,更是与市民百姓的柴米油盐、喜怒哀乐息息相关的,其创作提供了东北城市生活的翔实地图与景观大全,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当代城市叙事的地理与内涵。
正是在关注城市与城市生活方式的向度上,陈力娇小说的认识论与方法论都呈现出“空间转向”的鲜明特色,这使其小说的建造方式以及试图表达的理念别具一格。作为一位对空间极度敏感的作家,陈力娇“不仅仅把空间看作故事发生的地点和叙事必不可少的场景,而是利用空间来表现时间,利用空间来安排小说的结构,甚至利用空间来推动整个叙事进程。”(9)龙迪勇:《空间叙事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40页。
陈力娇小说注重让人物在城市的特定风景与空间中穿行与驻留,这样的空间场景包括家宅、街道、市场、网吧、酒吧、歌吧、公园、幼儿园、售楼中心、酒店、烧烤城、洗衣店、台球室、4S店、医院、咖啡屋、电脑学校等地点与场所。“城市包含着物质生产和消费的纪念地与高大建筑,也包含着娱乐、游戏、休闲和节日等等的空间。”(10)[英]安杰伊·齐埃利涅茨:《空间和社会理论》,邢冬梅译,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71页。何为城市的空间本质,是摩天大楼还是贫民窟,是高档会所还是寻常巷陌?显然,陈力娇对城市景观有个人的特殊体认,也有自己的独特选择,即对于城市,她较少描写豪华酒店与灯光大道,而是书写街道与住宅小区这种最有城市元气的地方,是藏身在主干道和次干道后面的市民生活能量场。马笑泉先生指出:写好“街道的内部,在小饭店、小旅馆、小发廊、小菜市场、按摩房、麻将馆、洗脚屋、网吧、桌球室、歌舞厅里”(11)马笑泉:《城市小说的生成》,《长江文艺评论》2018年第5期。的消闲时光,就写出了城市的生命体征,就写活了一个城市。陈力娇正是如此。如《宅男》的故事发生于家宅和网吧的虚拟空间;《月光族》中的爱情游戏离不开售楼中心的空间参与;《蝴蝶欲飞》在洗衣店上演一幕幕分分合合的青春悲喜剧;《阳光灿烂的午后》以烧烤城为空间背景;《你是谁的远方》的典型环境在牡蛎渔馆与幼儿园两个地点游移等等。对城市意象与城市形态的这种选取,不仅构成作家表达城市经验的工具,而且通过这些空间手段,“社会关系以及相应的社会关系引发的变化得以发生。”(12)[英]安杰伊·齐埃利涅茨:《空间和社会理论》,邢冬梅译,第75页。陈力娇正是在这里向城市与空间做出发问,即“谁的城市?谁的空间?”
陈力娇从空间危机角度切入城市本质、揭示城市生活真相,凸现了个人对城市现象与城市问题的现代性反思。德波拉·史蒂文森指出,“城市文本是被体验的,因而被人们以数不胜数的、高度个性化的方式加以解读。”(13)[澳]德波拉·史蒂文森:《城市与城市文化》,李东航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75-76页。在陈力娇笔下,城市是一个宏伟而充满刺激的空间,处于永不止息的变迁之中,是一个活生生的复合体,一个依据使用和体验而建构起来的多重场所,城市生活复杂多变,拥有“许多魔法、幻景、仪式和超越性的内容”(14)[澳]阿德里安·富兰克林:《城市生活》,何文郁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13年,《前言》第2页。。在城市化社会和空间时代,人的生存困境与精神危机多为空间问题的深层折射。陈力娇的小说角度多样,涉及的空间议题丰富多彩,她笔下的城市“提供了自由,同时也潜伏着危险。”(15)[澳]德波拉·史蒂文森:《城市与城市文化》,李东航译,2015年,第71页。《宅男》中的网络世界为“儿子”提供了心灵创伤的避风港,但对其的无限沉溺又带来了亲情的枯萎与爱情的隐忧。《月光族》中的三角恋情由地下转为地上,由于房子归属问题的困扰,主人公“我”离婚后还要隐忍与情敌和前妻同住一个屋檐下,抬头不见低头见,两屋一厨六十平米的空间让这种别扭关系度日如年。《青花瓷碗》中,女主角“她”和丈夫的赌友老穆之间发生的征服与改造的人生故事,前一段发生在乡下,后一段发生在城里,这种空间流动与空间转换带来的人物变化,与作者高扬城市启蒙理性、直面田园生活失落的文化价值观密不可分。
一言以蔽之,陈力娇在“用文学对话时代、唤醒人类共通情感和价值判断的主动探寻中,体现出了强烈的激情与现实主义关照”(16)刘小波,童剑:《深度介入生活与现实主义的勃兴——近年长篇小说创作概观》,《扬子江评论》2018年第4期。。她的小说通过对空间类型的精心设定,以及对空间区隔、空间占用、空间生产、空间冲突、空间转化、空间隐喻、空间权力、空间正义、空间记忆、时空分离、时空压缩等空间话语的灵活运用,让现代性的核心场所——城市,焕发出迷人的风姿;让现代空间的主体——城市人,呈现出新型的社交特征;让现代价值理性——以城市生活的方式获得深度表述。
二、以空间透视人性:陈力娇小说的空间生产
正如有学者所强调的:“人性在人的日常生活中反映出来……而且……以最精确的逼真加以复制。”(17)[美]伊恩·P·瓦特:《小说的兴起——笛福、理查逊、菲尔丁研究》,高原,董红钧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第49页。瓦特结合文学进一步解释道:“只有时空环境都是特殊的,理念也才能是特殊的。同样,只有小说中的人物被置于某种特殊时空的背景之中,他们才能是个性化的。”(18)[美]伊恩·P·瓦特:《小说的兴起——笛福、理查逊、菲尔丁研究》,高原,董红钧译,第15页。陈力娇深谙时间概念总是与空间概念融为一体的事实,熟知“不管在哪种形式的公共生活里,空间都是根本性的东西;不管在哪种形式的权力运作中,空间都是根本性的东西”(19)[美]爱德华·索亚:《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陆扬等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91页。。基于此,她以空间设置实现意义增值,以空间生产达到人性揭秘,极大地扩展了小说的社会内涵与心理蕴含。在新空间的探寻与建构方面,陈力娇以新感性空间、新部族空间与新关系空间三种空间形态的聚焦与创设,建立起城市书写的基本舞台与背景氛围。在空间策略的使用方面,陈力娇借助空间转移、空间区隔、空间冲突等基本手段,让城市小说的新质大量呈现,让人物描写与情节塑造更紧致、更高效、更有创造性。
在新空间的创设方面,基于空间与人、空间性与人性之间的内在关联,陈力娇小说实现了以新空间的书写达到人性书写的审美诉求,这表现为如下三个方面。
其一,透过新感性空间探察城市新人的精神危机与心理困境。在20世纪的最后25年,“信息时代的到来使城市失去了原来的意义”(20)[美]曼纽尔·卡斯泰尔:《信息化城市》,崔保国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导论》第1页。,新技术革命所引发的不仅是生产方式、发展模式与社会结构的巨变,更催生了城市的变化与城市新人的出现,人文历史的另一种可能因赛博空间的出现而揭开了大幕。陈力娇对信息化社会出现的这一新空间形式极为瞩目,并通过《宅男》《爱情演练》等小说进行了呈现,在分享空间解放含义的同时也号准了它的症候。《宅男》讲述的是一个只靠QQ交流维系父子日常生活关系的另类故事。儿子因父亲伤害过母亲,怀着深重的成长创伤成为躲在网络空间的一名网虫,一切生活都依赖虚拟网络。现实空间成为禁忌空间。父亲忘记带自家钥匙,按门铃、打手机都没用,唯有上网吧用QQ联系。儿子拒绝走出家门,不想失去甲壳般的坚硬,凭借封闭的物理空间他获得了安全感,倚仗无限的网络空间他安置了心巢。这就是网络社会崛起、信息化城市来临之际出现的生活异变:在一般规则、生活节奏、个人模式、生活空间、主要隐喻等方面,网络化生存的确能够兑现某种形式的自由与解放,但这种移居本身就隐含着被赛博空间殖民化的危险。
其二,透过新部族空间展示城市亚文化群体的生活方式及情感体验。在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城市生活中,各种亚文化群体与亚文化现象构成了整个城市文化最富活力的组成部分。陈力娇的《月光族》《阳光灿烂的午后》等小说就是以他们为对象的。小说《月光族》中的“月光族”指的是挣钱不多、月月花光的一类青年男女。这是城市新人的另一种类型。他们不奢谈爱情,在社交上带有一种放浪的、酒神狂欢的倾向,有感觉就上床,没感觉就分手,活的粗枝大叶、随随便便。在公司老板的撮合下,主人公“我”与售楼小姐典小曼闪恋、闪婚,“五分钟搞定,一天上床,一个月怀孕。”在随后抚养孩子、典小曼出轨、二人闪离等事件中,二人没心没肺、我行我素、活在当下、不拖泥带水的现代性格表现得更加突出。但作者并未脸谱化这群“月光族”,尤其是对“月光族”鼓峰,作者对其友善、自立的一面不吝笔墨,他不向有钱的叔父屈膝,而是假扮人妖赚钱,这使“我”都不无震动;同样,“我”明知道孩子不是亲生子,依旧坚持抚养的行为,也见出月光族们大度、磊落、有承担的一面。凡此种种,无不展现了作家陈力娇十分宽容的现代情爱观与对城市新人的尊重和理解。
其三,透过新关系空间探寻现代人的自由及其可能。城市“依靠规模让人际交往更多元、社会结构更开放,让各种对立思潮得以汇集和发展,这为人的个性发展与自由人格的形成提供了可能。”(21)黄大军:《西方空间理论的美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95页。陈力娇的《旋转门》《粉红色讹诈》等作品在这方面做出了可贵探索。小说《旋转门》如暗夜静开的玫瑰,向我们描绘了一种温情而暧昧的男女社交形态。作品中,私企职员王点娃和城管局长佟城是一对精神知己,两人的相遇带给彼此的是一种希望与清欢,一种信任与守望。正是城市这个充满可能与意外的地方让二人戏剧性地发生交集。王点娃地位卑微,因姐夫被打,师专同学方小红介绍自己的情人城管局长佟城出面平事,二人结识。王点娃和方小红长相相像,但方小红物质充裕,生活开放,丈夫在外时就找临时搭档享受性爱。两人一个放荡不羁,一个清纯如水。王点娃的知情知义感动了佟城,佟城视其为心灵朋友,无钱无势的王点娃也“特别需要有人能帮她撑起一方天”。这种心扉的突破与情感的依赖,带有某种精神纯粹性。所以,当佟城做官出事,他留下四十万干净钱为老母养老送终时,所托之人不是性伙伴方小红,而是精神同道王点娃。从这类小说可知,陈力娇的创作具有超越实用理性,超越道德纲常,洞察人性多维空间的努力与意图。
在空间策略的使用方面,陈力娇小说利用多种空间策略,让人物与人性获得充分展示,实现了以空间强度拷问人性真谛的创作旨归,这在如下三个向度有着具体展现。
其一,通过空间转移完成人物变化。陈力娇的《青花瓷碗》在这方面有着出色呈现。小说有两个板块。在乡村板块中,女人因为赌徒丈夫一输再输,使得大汉老穆一周来家四五次,不说吃住,有时就连内衣内裤都扔给她洗,“大汉的频繁来家有时让她产生幻觉,恍惚觉得大汉就是丈夫,丈夫才是大汉。”最后一次是丈夫把女人输给了大汉,大汉对她动粗,女人不从,之后大汉拿走了女人视为生命的传家宝——青花瓷碗,女人以命相索未果。故事随即转入了城市板块,曾经窝囊受气、隐忍可怜的小女人摇身一变成为杀伐决断的“女汉子”,她与大汉斗智斗勇,最终以在城市开菜店,与大汉一起过日子为筹码,将其成功改造,不仅追回了古董,而且过上了幸福生活。对于“女人”这个形象,如何理解其性格的“突转”乃是解读关键。笔者的结论是空间转变带来了性格转变。在乡村这个凝固、压抑的空间,性别的男阳女阴对应空间的内外之别,女人因属于家庭生活而世界狭小,经济不独立,沦为被动与依附的“第二性”,现代城市文化则极大地摧毁了这一性别制度与经济制度,女人不仅可以与男人一样具有平等权与工作权,也可以发挥更大的改造世界、征服世界的主体能量,这是《青花瓷碗》中的女人进城后之所以由鱼肉变为刀俎,由悲剧主角变为喜剧主角的根本动因。
其二,通过空间区隔展示精神创伤与人性隔膜。人类空间可分为社会空间、家庭空间与个人空间三种。每个人有多种角色,人物也处于多个空间之中。角色之间可能是排斥的,空间区隔就成为身份困境的表征。《你是谁的远方》讲述了离异男人吴直街和两个女人的婚恋情感故事。吴直街的未婚妻唐米乐也是二婚,两人感情世界都曾铭刻下创伤,再组家庭必然会讨价还价、小心翼翼。为了让吴直街幸福,曾经和吴相好的单身女人草图牺牲自己,暗中接管了吴的孩子。草图开着牡蛎渔馆,负责到幼儿园接送孩子。而吴则作为继父按时接送唐的女儿。无疑,这种夫妻关系的隔膜与狭隘是令人绝望的。由此形成了牡蛎渔馆、幼儿园、唐米乐的家三个禁闭空间。唐米乐的家属于私人空间,具有封闭性,但牡蛎渔馆和幼儿园却是公共空间,具有开放性。因为要瞒着唐米乐,二者才成为了隐蔽地带与隔离空间。不过,这很快就引起了唐米乐的注意,她想方设法试图突破空间区隔查明真相,于是双方之间发生了空间争夺与空间保卫的激烈斗法,这就形成了特有的矛盾空间与故事张力。“空间是卷入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的过程。”(22)[英]安杰伊·齐埃利涅茨:《空间和社会理论》,邢冬梅译,第75页。陈力娇的许多故事灵感都来自空间区隔,并借以抵达了常人难以企及的人生角落与人性暗陬。
其三,通过空间冲突隐喻伦理危机与人性扭曲。陈力娇将人际冲突、人性碰撞与空间冲突加以融汇,形成了篇章结构上诸多具有迸发力的点、线、面。比如《宅男》中父子共享的房厅,龟缩在个人屋子中的儿子仅在父亲外出时才戒备地使用,因为那不是他自己的。这一细节生动地说明了儿子的心门把守得有多紧,儿子的网络沉迷又有多严重。又如《旋转门》中,姐夫王诸明因觊觎王点娃的美色遭拒,就常在早上霸占卫生间施以颜色。而王点娃到同学方小红家以解燃眉之急,特别感慨的不是别的,而是“方小红家两个卫生间,一个人用,没人和她抢,这让王点娃产生隔世之感,好像是到了一个极乐的世界,如果放张床,她在里面住她都乐意。”如此,作者寥寥几笔就将城市贫富差距、阶层分化的严峻现实表现得淋漓尽致。再如《蝴蝶欲飞》中,女孩儿边小莺有着难以抹去的成长创伤,当她在草坪里种花时,不同的花草与位置,就构成了她对家庭关系的想象与象征。土豆花是父亲,黑色罂粟花是母亲,红色花的美人蕉是她自己。现实中,母亲伤害了父亲和自己,所以,当黑罂粟花长到土豆花近前时,为了保护土豆花(父亲)不受影响,她甚至连牺牲美人蕉(自己)的存活都在所不惜也要将其移植到别处,因为她同情父亲、更爱父亲。透过这一空间意象,我们看到的是“人性摆脱了不痛不痒、波澜不惊的庸常状态,显现出大爱大恨、尖锐奇崛、惊涛拍岸般的异常样貌。”(23)汪树东:《平民世界的人性畸变与生命温情——论陈力娇小说的人性图景》,《文艺评论》2013年第9期。
三、以空间抵达超越:陈力娇小说的空间救赎
当有人问及陈力娇为什么写作时,她坦言道:“寻找我完美的、绚丽的、洁净的精神家园,我的灵魂的栖息之地。”(24)陈力娇:《青花瓷碗·代后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第304页。在陈力娇笔下,这样的精神家园有时是城市,有时是乡村,有时来自母性的包容与奉献,有时来自主体的突围与觉醒。这不仅赋予陈力娇的小说创作以丰富的超越与救赎维度,更赋予她以现实主义为主导的创作以浓重的理想主义色彩。普鲁斯特曾说:“一部作品并非出自日常生活中的那个‘我’的产品。而是出自一个更深刻的‘我’。”(25)张燕玲:《有我之境》,北京:作家出版社,2018年,第4页。陈力娇正是本着这样的专业精神,“重新探寻文学的真实,重新在理想与现实间找寻自己的文学立足点”(26)张燕玲:《有我之境》,第6页。,并主要从下述四个方面入手,让作品充满拯救力量、闪耀人性之光。
其一,城市世界对乡土中国的引领。有人曾说:“没有城市,文明就很少有可能兴起。”(27)[美]罗杰·M.基辛:《当代文化人类学概要》,北辰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40页。而到了今天,“城市的影响已经超出地理的边界,事实上不可能把乡村生活方式同城市剥离开来。”(28)[英]艾伦·哈丁,[英]泰尔加·布劳克兰德:《城市理论》,王岩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9页。这是历史发展与社会变迁的最新现实,尤其是在城市化进程相对迟缓的黑龙江区域如何书写美丽的城市、正面的城市更是一个不容回避的课题。陈力娇的许多小说都内含着一个“乡下人进城”的叙事母题,如《青花瓷碗》《你是谁的远方》《豆腐妈妈》《放飞》《城市上空的鸟》等。在这个主题模式中,陈力娇的城市之思虽然也包含着对城市化负面效应的反思,但总体上看,城市在这些作品中是作为救赎之地出现的。倘若将陈力娇的城市书写放置在新世纪以来“乡下人进城”小说的总体格局中来考察,这一点就会更加分明。研究者竺建新就曾撰文批判道:“新世纪‘乡下人进城’小说对乡下人的失范行为作了逼仄的书写,……失范书写的偏激化,缺乏‘度’和‘道德感’,构成了道德价值观层面上的不足,暴露了此类小说创作的局限性。”(29)竺建新:《论新世纪“乡下人进城”小说中的“失范书写”》,《当代文坛》2016年第4期。陈力娇则不然,她在城市认同的维度上对城市的救赎功能展开了积极探索:一种情况是乐观主义的表达,如《青花瓷碗》和《城市上空的鸟》。在此,城市给了乡下人以发展的空间与舞台,它带给人以希望、幸福与期待。另一种情况是进城的乡下人在城市空间完善了人格,实现了成长,发展了能力,纵使人生前路依旧晦暗不明,但他们心中充满憧憬,他们的精神世界充满韧性,他们已经成为自己的主人、生活的主人与城市的主人。这样的作品包括《你是谁的远方》《豆腐妈妈》《放飞》等。
其二,边地空间对城市空间的修复。美国历史学家艾恺认为,“现代化是一个古典意义的悲剧,它带来的每一个利益都要求人类付出他们仍有价值的其他东西作为代价。”(30)[美]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31页。城市的胜利是经济理性、功利主义与消费主义的全面胜利,为了对抗城市扩张的现代性恶果,以审美现代性修正启蒙现代性、以边地对抗城市成为当下文学的救赎大纛。陈力娇的《你是谁的远方》和《豆腐妈妈》等作品也属此列。作为与城市对立的一种地理想象,边地“奇特而另类,充满原生和古典味,它特殊的地缘、血缘和族缘结构,它的粗犷、妖媚、宁静与苍凉,足以把现代生活中的人的生命感觉重新激发”。(31)刘大先:《“边地”作为方法与问题》,《文学评论》2018年第2期。陈力娇作为东北地域和地理环境中长大的北方儿女,对边地空间、边疆生活有着天然的亲和性,她笔下来自草原的游牧民族后裔草图(《你是谁的远方》),来自黄土高原的拾荒姑娘七喜(《豆腐妈妈》)就融入了这种深浓的边地情结与文化认同,成为作家坚守人性尺度、重建精神高地的最后依托。这类边地空间原始、淳朴、辽阔、博大,而作为它所孕育的儿女,也同样有着草原般的胸襟,高原般的志气,野草般的生命力与适应力。草图在城市以开牡蛎渔馆为生,七喜在城市以卖豆腐为业,她们经济独立、性格开朗、敢爱敢恨、单纯美好、舍己为人,集游牧与农耕文明的美德于一体,成为城市文化健康发展的重要参照,成为修复城市空间的拯救力量,更成为作者表达怀旧情绪、缓解生存焦虑的信仰所系与精神净土。
其三,母性空间对男性空间的包容。作为一位女性作家,陈力娇的性别身份影响着她的人物塑造与空间想象。研究者郭淑梅对此有着精彩分析:“在一个需要高尚精神引领的世界上,她选择了人类亘古蛮荒传递下来的母性精神。在以女人为主角的小说《青花瓷碗》《你是谁的远方》《豆腐妈妈》《放飞》《天使花园》中,她都有意识地塑造出一类甘于奉献的女人,她们身上有一种像土地一样厚实可靠的品性,包容大气坚定不移。”(32)郭淑梅:《陈力娇小说的“地母情怀”——评中短篇小说集〈青花瓷碗〉》,《文艺评论》2015年第7期。《放飞》中的刘灯盏就是这类女性之一。她在谷稗子离婚、孩子幼小无人照顾时,和他组成了新家,几年后丈夫有了外遇,和一位女医生爱得如火如荼,作为受害者,她没有采取激烈方式,而是在看到丈夫因“失恋”而寻死觅活时,想的只是如何帮助他,如何让那位女医生来看他,如何让一度分手的二人断钗重合。灯盏来自乡村,与传统和大地相连,那个空间仍有许多前现代因素在流连徘徊,受现代文明影响程度较之城市缓慢迂曲,“爱情观念保持着纯朴、美善的一面。”(33)雷鸣:《都市化语境与新世纪长篇小说“边地历史”叙事的话语逻辑》,《青海社会科学》2018年第3期。在灯盏看来,男人就是她的“一切”,“她的‘一切’都好,她就没有什么不好的。”在感情上,她有主见,相信缘分,“缘聚就好,不管谁和谁”,所以,她不会阻挡丈夫,而要将其放飞,“飞远了就飞远了,不飞远他会回来。”由此,灯盏重情重义、坚定独立、博大宽广的一面跃然纸上。这就是陈力娇笔下的女性空间,辽阔、高远,一派蔚蓝,在其面前,男性的天空是低的,一片空荡。
其四,内部空间对外部空间的抵抗。文学既是镜,也是灯。作为镜,文学让人认识外部世界,作为灯,文学照亮人的精神空间。面对社会转型与都市进程的裹挟,现代人比以往任何时期都亟需认识自我,成为自我。在海德格尔看来,“要成为我们自己,必须听从良知的呼唤,它呼唤我们脱离常人,回到我们自己。”(34)张汝伦:《现代西方哲学纲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11页。在陈力娇笔下,这种良知可以是一种坚韧的信念与传统,可以是一种现代式的关怀与大爱,还可以是一种人性的自我复苏……总之,不论是哪一种,都是个体的主体性、个体自由与个体的自我意识的构建力量。由此,陈力娇超越“非此即彼”的现代性模式,以“或此或彼”的方式推动主体的内在性不断占有生存真理。《青花瓷碗》与《放飞》中的女主角都对祖训恪守如初,并以之作为在现代社会中的安身立命之本,前者中的“女人”始终牢记爷爷“命在碗在”的教诲,后者中的刘灯盏以老母亲关于缘分的告诫立身处世,二人都凭借强大而有生命力的民间理念活出了色彩、活出了尊严,更活出了自我。《城市上空的鸟》中的平跳,则出于“谁有不正当的事,它都要给正过来;谁有为难的事,它都要帮助”的大爱,帮助蓑衣和米多改变两人难以自拔的不正常关系,让世界变得明媚、美好。《阳光灿烂的午后》中的恶少杨土,恶行累累、罄竹难书,然而即便如此不堪的人,“在想掐死董小桥儿子的一刹那间,他想起了自己的妈妈,还未泯灭的人性复苏了:他终于停止了罪恶的活动。”(35)闫续瑞:《个性化的艺术创造——读陈力娇的〈青花瓷碗〉》,《文艺评论》2013年第9期。这就是在写作上执着于精神家园寻找的陈力娇,她立足自身感受,想象世间万物,在外部空间挤压内部空间的浮华年代,高举文学大旗,冲锋在前,以内部空间的无比坚固,完成文学精神的续写与淬炼,发出响亮的独唱,使自己站到了当代文坛的前排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