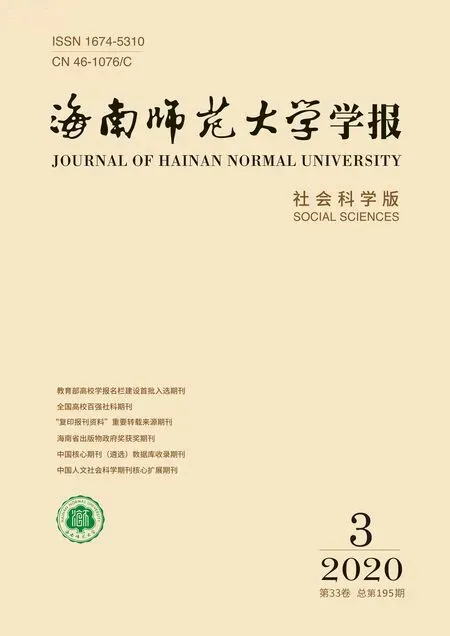论鲁迅乡土小说的建设性
2020-01-19朱崇科
朱崇科
(中山大学 中文系(珠海),广东 珠海 519082)
杨义先生颇有洞察力地指出:“鲁迅是我国现代文学中把平凡而真实的农民,连同他们的褴褛的衣着、悲哀的面容和痛苦的灵魂一道请进高贵的文学殿堂的第一人”。(1)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第171页。这从整体高度上指出了鲁迅乡土(农民)书写的开创性与独特地位。一直以来,学界对鲁迅乡土小说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并且随着农民地位和角色的攀升而有所起伏,比如强调文学为工农兵服务的时期,这种指引性思潮导致在分析鲁迅对农民阶层劣根性的批判时也减轻了力度,转而更强调鲁迅广博的同情心或否认其笔下人物的农民身份。不必多说,这是有悖于鲁迅先生的本意的。因此,有论者对鲁迅关于农民起义/战争的持中看法引人关注,如沈庆利指出,“总起来看,鲁迅对农民战争和农民起义的正面评价相对较少,而是更多地看到了它的负面影响与负面作用。鲁迅更多地从文化心理学的角度, 把农民战争和农民起义作为特定的历史文化现象,加以独到而深邃的剖析和批判……鲁迅集中批判了农民战争的野蛮性和残忍性,以及与原始宗教的密切联系。”(2)沈庆利:《黑暗时代的双刃剑——试论鲁迅的农民战争观》,《鲁迅研究月刊》2001年第6期。
同样,其他相关研究倾向也值得注意。比如,比较鲁迅与其他乡土书写者(包括后继者)的关系,如沈从文、莫言、贾平凹等等,尤其是高晓声,论述尤多。当然,也有将之与外国作家进行比较论述的,如和托尔斯泰、赛珍珠等。有论者指出:“鲁迅和赛珍珠是对中国农民心怀大爱的作家。在关注农民的政治态度、宗教意识、家族观念、现实苦难以及农村妇女所遭受的悲剧命运方面,他们的视角有许多相似之处。但由于二人在切入文学的机缘、观察社会的视角、关注现实的焦点等方面存在差异,他们的农村题材小说又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艺术风貌。”(3)张春蕾:《鲁迅与赛珍珠笔下的中国农民形象》,《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百年乡土文学(尤其是小说)书写农民范式的更新与递进(4)有关研究可参丁帆著《中国乡土小说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也有论者开始质疑鲁迅乡土小说书写的诸多可能缺陷,比如描述的隔膜、相对粗放,无法及时更新并细描农民的时代变迁、各种命运与可能性,鲁迅的乡土小说实践在他们眼中似乎已是落伍的冬烘生产。另一方面,也有论者批评鲁迅乡土小说书写的抽象或理念强加性。比如《祝福》中的底层妇女祥林嫂何以生发近乎终极关怀的疑问:“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那么,也就有地狱了?”“那么,死掉的一家的人,都能见面的?”(5)鲁迅:《祝福》,《鲁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7页。
实际上,以上观点或多或少呈现出学界对鲁迅乡土小说的误读,尤其是在此类书写中鲁迅彰显出的难以替代的建设性/超越感,而这种建设性部分超出了某些论者的理解力。简单而言,作者鲁迅与其乡土文学书写对象之间有种复杂的张力,而这个张力中的繁复逻辑亦可称为“乡土哲学”。一方面,鲁迅对乡土(农民)经由知识分子理路/中介往往具有深切的认知、同情与理解,而这种同理心(小说中往往是对其破落户身份的再现)与关怀往往超出了自然主义的书写或现实主义的细描;而另一方面,鲁迅对农民却有着审视(热切而理性的高度)乃至批判。相较而言,鲁迅之于乡土(农民),既有了解之同情,又有高度的省察。
一、再现的同理心
有论者指出:“鲁迅的思想世界是多元的、立体的,而不是单极的、片面极端的。在鲁迅的灵魂深处,尤其是童年的生命体验中,传统中国和中国国民在偏僻的农村呈现为一种‘桃源乐土’和‘纯朴农民’认知图景。这种与‘病中国’之‘中国病人’截然相反的思维模式,在《社戏》、《故乡》等作品中得到不同程度的显现。这种缘于中国本土的‘桃源乐土’之纯朴农民;认知图景。恰与体现西方‘他者’现代性思想的‘病中国’之‘中国病人’认知图景构成了对立的两极,共同呈现在鲁迅的文学形象世界之中。”(6)张丽军:《鲁迅想象农民的两极审美认知图景》,《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或许鲁迅关于乡土世界的描述远比二元对立(淳朴与病人)复杂,但不容忽略的是,鲁迅在他的小说实践中的确表现出一种再现的同理心。
(一)《故乡》:回不去的故乡
《故乡》中的乡土其实是一个相对复杂的场域:以农为中心,但亦有“士”(“我”)、“商”(杨二嫂为代表)存在,但更令人悲哀的是“农”居于底层。杨二嫂的人品(“人设”)败落其实已经隐喻了与“农”密切相关的乡村商贩的生计艰难。之前,作为“豆腐西施”——女神的她可以从容度日,“我孩子时候,在斜对门的豆腐店里确乎终日坐着一个杨二嫂,人都叫伊‘豆腐西施’……那时人说:因为伊,这豆腐店的买卖非常好。”(7)鲁迅:《故乡》,《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05页。后来的杨二嫂势利、小气、功利,甚至借诋毁他人(闰土)来谋取蝇头小利,“杨二嫂发见了这件事,自己很以为功,便拿了那狗气杀……飞也似的跑了”。(8)鲁迅:《故乡》,《鲁迅全集》第1卷,第509页。
当然,《故乡》中真正的主角则是闰土,鲁迅通过两种方法呈现出闰土的内在精神理路变迁或下降。一个层面是将少年闰土与中老年闰土进行对照,可以强烈地彰显出农民生存环境的艰难与不易,外表变成了老年人,对话时候的表情是:“他只是摇头;脸上虽然刻着许多皱纹,却全然不动,仿佛石像一般。他大约只是觉得苦,却又形容不出,沉默了片时,便拿起烟管来默默的吸烟了。”(9)鲁迅:《故乡》,《鲁迅全集》第1卷,第508页而导致此前后变化发生的外在理由是,“母亲和我都叹息他的景况: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都苦得他像一个木偶人了。”(10)鲁迅:《故乡》,《鲁迅全集》第1卷,第508页。
另一个层面则是将中年的“我”与中年闰土比较。在某种意义上说,少年时代的“我”与少年闰土的交往更多的是城乡互补视域下的互相欣赏。因为儿童往往强调玩耍游戏交朋友而超越了世俗礼教与传统规范的拘泥,进而可能显得亲密无间;而中年时候的比较则成了世俗化成人世界的清醒直面。鲁迅也并没有放过借此彰显同理心的机会,中年的“我”更想借助儿时的美好回忆来修补成人见面的尴尬,而中年闰土则是呈现出遭受现实消磨后的服输与麻木。但更令人关注的是鲁迅的自我反省,如小说文末所言,“闰土要香炉和烛台的时候,我还暗地里笑他,以为他总是崇拜偶像,什么时候都不忘却。现在我所谓希望,不也是我自己手制的偶像么?只是他的愿望切近,我的愿望茫远罢了。”(11)鲁迅:《故乡》,《鲁迅全集》第1卷,第510页。这段话表现了自我的深切反省,当然亦有对闰土的苦难理解式同情。另外也可以把这种关系理解为启蒙者与被启蒙者之间的平视姿态:摸索的启蒙者那渺远的希望(其实等于绝望)和闰土的自我麻醉与解脱并无本质差异。(12)参见拙文《认同形塑及其“陌生化”诗学——论鲁迅小说中的启蒙姿态与“自反”策略》,《福建论坛(人文社科版)》2008年第1期。
(二)《药》:痛苦与愚昧
对于底层民众,鲁迅在再现时呈现出相当复杂的情感取向,一方面对其生存艰难颇多理解,而另一方面又对其愚昧加以反拨乃至批判,但这背后往往夹杂了脉脉温情与缕缕关怀。
《药》书写了底层民众的不易。华老栓为了获得治疗肺痨的偏方,深夜前往杀害革命者的刑场买人血馒头,虽然付出较高价钱(一包珍贵的“硬硬的”洋钱)却还是满怀希望。“老栓倒觉爽快,仿佛一旦变了少年,得了神通,有给人生命的本领似的,跨步格外高远。而且路也愈走愈分明,天也愈走愈亮了。”(13)鲁迅:《药》,《鲁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63-464页。华老栓维持生计终究是辛苦的,何况年纪已很不轻,但独子华小栓依然病逝,即使他吃了革命烈士夏瑜的人血做成的馒头。
鲁迅以悖论的笔触描写了两位丧子的母亲痛苦相通(一个是病逝、一个被砍头,皆非善终):儿子被斩首的夏大妈一开始感觉“羞愧”,但看到夏瑜坟上的花环却又在欣慰之余心生迷信。鲁迅在文中既展示了他“听将令”的革命人道主义和宣扬集体主义精神,但同时又坚守科学性的原则与现代性启蒙的底线,所以他不会满足夏大妈廉价的精神需求,“他们走不上二三十步远,忽听得背后‘哑——’的一声大叫;两个人都竦然的回过头,只见那乌鸦张开两翅,一挫身,直向着远处的天空,箭也似的飞去了。”(14)鲁迅:《药》,《鲁迅全集》第2卷,第472页。作为小说家的鲁迅自有其独特性,他既批判夏瑜的革命事业的脱离群众(包括母亲)以及底层的愚昧,但同时又同情底层的苦难以及革命孤独语境中的高贵性。
二、厚实的批判力
鲁迅给人深刻印象之一就是他厚实的无所不在的批判力,这一点在其小说书写中亦有精彩表现。如前所述,鲁迅一方面有再现的同理心,另一方面却是建基于其国民劣根性批判伟业上的尖锐挞伐。有论者指出,“鲁迅写农民起义军的破坏性、奴隶性和皇权主义,这三者奴隶性根源,是核心,其他二者都是从这条根上生发出来的。奴性,农民阶级有,封建地主阶级包括皇帝在内也都有,所以说它是封建社会国民性中劣根性的核心。鲁迅用了毕生的精力挖这条根,目的是将其拔掉。”(15)王春来:《鲁迅笔下的农民起义军》,《鲁迅研究月刊》1995年第2期。这可谓是整体论,结合鲁迅小说,又可分论之。
(一)奴性及其生产机制批判
这是鲁迅所有文类都会涉及的命题,也是其毕生关怀并践行批判的议题之一。而在鲁迅小说实践中,这也是贯穿始终的主题关怀。
1.《风波》:超稳定结构下的困窘。这篇经典文本可以有多种解读或主题蕴含,但从奴性视角考量,其传神地揭示了长期以来奴性是如何生成并有效惯性运行的。村民们固然相当愚昧,他们无法理解中华民国成立之后的允许剪辫和之前封建王朝清朝强调留辫的关系,自然也无力批判复辟的辫子军张勋的倒行逆施与反动性,他们更习惯于表面的和谐与稳定,哪怕是被盘剥和噤声。
相当耐人寻味的是,治理基层的乡绅赵七爷却也只是借助略知一点皮毛的《三国演义》,他的知识结构依然是反动和没落的:张大帅是燕人张翼德的后代,如果赵子龙在世,世界就太平了,甚至在辫子事件后还假公济私企图打击报复一度对他不敬的村民七斤。而更令人悲哀的是,底层农民的被统治结构和互掐悲剧却一再延续。六斤依然成为奴性制度的牺牲品,即使在中华民国成立多年后还是被裹了小脚。当然九斤老太、七斤、七斤嫂、六斤家庭内部之间的复杂张力也令人感叹。(16)参见拙文《茶杯里的波澜:〈风波〉重读》,《鲁迅研究月刊》2017年第5期。
2.《理水》:共谋与迎合。文化山上的闹剧可谓既旧又新,“旧”是因为这是古老的大禹治水神话(所谓庄严的工作)的另一面存在,“新”则是其中灌输了鲁迅的强烈主体介入,而新编其实是有现实指向的。
考察大员们的工作程序中有需要下民代表回话的环节,但下民代表难寻。由于长期的隔离和等级分化统治,下民们往往怕官,不愿做代表,包括“头有疙瘩的那一个”,在威逼利诱(尤其是前者)和众人义正词严的围攻声讨下,“他渴睡得要命,心想与其逼死在木排上,还不如冒险去做公益的牺牲,便下了绝大的决心,到第四天,答应了。”(17)鲁迅:《理水》,《鲁迅全集》第2卷,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91页。结果他从战战兢兢的小民变成了“瞒和骗”传统的捍卫者,不仅颠倒黑白、苦中作乐,而且把这种困境加以美化,变成了自力更生、喜气洋洋的榜样示范,“‘吃得来的。我们是什么都弄惯了的,吃得来的。只有些小畜生还要嚷,人心在坏下去哩,妈的,我们就揍他。’大人们笑起来了,有一个对别一个说道:‘这家伙倒老实。’”(18)鲁迅:《理水》,《鲁迅全集》第2卷,第392页。不仅如此,他还拉虎皮做大旗,发动集体造假且媚上。从某种意义上说,上述操作完整地呈现出奴性生成机制运行中的复杂逻辑,既有思想上的钳制和单一灌输(帮闲的知识分子助纣为虐),又有自上而下的威逼利诱,同时更有底层在因应这种操作中的共谋与媚上。
(二)功利与物化取向批判
简单而言,奴性统治为了满足特权(者)需求,势必加重底层原本相对匮乏的物质需求,这既降低了底层对政治、民主等重大事件的关注,以及对精神解放的追求,又让他们更长于满足基本的生理追求,而变得更功利与物化。但鲁迅对此主题的处理却又是辩证的,一方面他承认物质之于生存的重要性,有唯物主义的一面,另一方面,他又大力批判物化。
《奔月》中的夷羿力图让厌倦了乌鸦炸酱面而欲望强烈的少妇嫦娥换换口味,早起跑了更远的路打猎,却误将老妇人的老母鸡当成是鹁鸪猎杀。这个老妇人在精神上具有荒芜而轻信的特征,比如指责夷羿抢了逢蒙的功劳,“哈哈,骗子!那是逢蒙老爷和别人合伙射死的。也许有你在内罢;但你倒说是你自己了,好不识羞!”同时她却对自己老母鸡的折价相当清醒且干脆利索,“赔。这是我家最好的母鸡,天天生蛋。你得赔我两柄锄头,三个纺锤。”(19)鲁迅:《奔月》,《鲁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75页。而且兑现前还要以箭作抵押。同时,鲁迅也借此表达神仙夷羿的尴尬:他也并未超越物质的羁绊,同时也反证他的英雄迟暮——他已经不适应这个时代了。
同样值得关注的物化哲学篇目则是《采薇》。伯夷叔齐颇有气节,然而终究却死于物质、精神的双重打击:一方面是日益恶化的物质饮食和身体状况,最后只能吃薇;另一方面则是捍卫气节的虚妄与伪善,被鹦鹉学舌的下女阿金展开了致命一击。值得深思的是,下女阿金彰显出对物质精神流动的多重辩证:她的主人小丙君原本是趋炎附势的贰臣,不仅毫无气节,还颠倒黑白,诋毁并间接杀死了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而且阿金还继续以流言话语(20)参见拙文《论鲁迅小说中的流言话语》,《中山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伤害死去的二老,编排他们贪心——气节一度感动上天,以鹿奶饲之,却因想吃鹿肉而被神鹿抛弃从而被活活饿死。这个谣言恰恰可以看出其卑劣的(农民)本性——狭隘、物化、缺乏格局与追求。
三、绵密的文化性
如前所述,鲁迅的乡土小说中有一种超越感和哲学关怀,部分彰显出其背后铺排的绵密的文化性,这也正是鲁迅屡遭误解的原因之一。
(一)《祝福》:何以终极关怀
我们可以从多个角度解读《祝福》,比如政权、族权、神权、父权共同绞杀了祥林嫂;或者祥林嫂死于“集体谋杀”,小说中的所有人物都是凶手,等等。但从文化角度看,祥林嫂却是死于灵魂在不同文化冲突之中的无法安放。
无知的祥林嫂是被命运推着走或随波逐流的下层妇女,她勤劳朴实却命途多舛,只是想做一个安分守己的农村妇女,守着自己的小幸福即可,但却无法满足。比如被逼二嫁,她起初不从,后却认命。祥林嫂一生中最好的时光有两段:一是嫁给贺老六后未发生家庭变故前的时光,“母亲也胖,儿子也胖;上头又没有婆婆,男人所有的是力气,会做活;房子是自家的。——唉唉,她真是交了好运了。”二是二嫁前来鲁四老爷帮工的阶段,“人们都说鲁四老爷家里雇着了女工,实在比勤快的男人还勤快。到年底,扫尘,洗地,杀鸡,宰鹅,彻夜的煮福礼,全是一人担当,竟没有添短工。然而她反满足,口角边渐渐的有了笑影,脸上也白胖了。”(21)鲁迅:《祝福》,《鲁迅全集》第2卷,第14页。这不是简单的劳动让人快乐和美丽的翻版,而是摆脱礼教束缚之后的自食其力和任劳任怨。
但文化冲突或者准确地说,是不同人物对待不同文化的不同标准和态度将之逼上了绝路。一个民间来源是同阶层的柳妈的迷信——女人事二夫到阴间要被分身。祥林嫂只好捐门槛祈求替代消灾,却被雇主——四婶的“官方”残忍否定,于是她身心俱疲,失魂落魄,日益变成行尸走肉,临死前她才更关注“终极关怀”。丸尾常喜犀利地指出,“参与祭祀的准备,给她一种实感,表明在这个共同体所规约的幸福的末端,确切无疑地将她也连在了一起。虽说是帮忙,但只要能与祭祀相关,就一定意味着她还是这个由祭祀、受祭祀的关系构成的强固的单位集合体社会的一员。”(22)[日]丸尾常喜:《“人”与“鬼”的纠葛:鲁迅小说论析》,秦弓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第194页。
易言之,安放肉身的文化尴尬与亲子阿毛的血浓于水让她无所适从,所以才会发问,但最终也没得到圆满解决,而在万众祝福的节日里孤单惨死。这不是鲁迅有意让这一故事学理化、文化化,而是祥林嫂无力摆脱宿命和文化压迫,想寻求一种解决之道。
(二)《离婚》:文化围剿的反思
此篇小说的女主人公爱姑可以被视为家境殷实、性格泼辣的农村妇女形象,她当然有她的性格悲剧。“爱姑性格的悲剧在于,她对压迫她的封建统治和封建礼教并没有本质的认识,而却又幻想用个人的力量去反抗压迫,这反抗本身就注定了必然失败的结局。但是,爱姑的形象,毕竟预示了一个新时代的成长转换已经开始。”(23)李希凡:《深深地培植在被压迫农民的沃土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1期。问题在于,我们更应该看到小说中更绵密的文化批判——乡绅阶层如何以繁复文化围剿这个捍卫权益的泼辣少妇。
其中最强势的层面就是官威(官本位)。等级化,并制造奴性氛围,比如慰老爷等令众人仰慕的人对七大人众星拱月,而且七大人面对爱姑可能使用的女性撒泼手段早有准备和对策。当爱姑企图使用女人的策略时,七大人一声“来——兮”,“立刻进来一个蓝袍子黑背心的男人,对七大人站定,垂手挺腰,像一根木棍。”(24)鲁迅:《离婚》,《鲁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55-156页。爱姑的气势立刻瘪了下去。
其次就是以文化打压爱姑。比如七大人把玩腐朽没落的“屁塞”“水银浸”,用满口的专业术语来给爱姑下马威,这是古典知识(国粹)的围剿。同时又借助西化代表——尖下巴少爷进行理论逻辑恫吓(收服),面对爱姑要继续上诉的宣言,七大人不慌不忙早有对策,“莫说府里,就是上海北京,就是外洋,都这样。你要不信,他就是刚从北京洋学堂里回来的,自己问他去。”(25)鲁迅:《离婚》,《鲁迅全集》第2卷,第154页。爱姑最后也感慨万分,承认失败。从文化威权的角度来看,爱姑的失败在所难免。
(三)《阿Q正传》:乡土社会的寓言性
有论者指出:“阿Q 这个典型形象是非常复杂的。作为一个农民的受害者,他不但有不觉悟、落后的一面,也有勤劳、质朴的一面,不但有不进行正面抗争、用精神胜利法自我慰藉的一面,也有向往革命、敢于革命的一面。我们分析阿Q性格是不可以忽视任何一面的。鲁迅所鞭笞的,是农民的落后,而不是落后的农民。”(26)刘梦溪:《论鲁迅对农民问题的探索》,《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3期。阿Q形象的复杂性似乎远非普通农民形象可以概括。
首先阿Q具有一定的身份流动性,不是简单和土地捆绑的传统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他实际上是打短工的流民,甚至偶尔也可以流窜到城里去。
其次,阿Q的性格因此显得驳杂,“农”外有“商”,又因为流动开了些眼界,头脑又相对活泛,于是愤懑且不平,当然亦有游手好闲、好吃懒做的缺点。
第三,阿Q无论如何又是个底层民众,因此在遭受了侮辱和损害时总有自己的疗治/应对方式——精神胜利法。
在我看来,鲁迅的伟大之处在于,他苦心孤诣深入挖掘底层人士的精神追求与关怀,不是由外向内的强加,而是内外对流,结合有关人士的身份、际遇凸显出其对应的劣根性、正当性诉求,乃至最后升华为可能的第三世界国家文学实践的“国族寓言”。
四、幽微的超越感
有论者指出,“高晓声的批判是基于对农民的同情理解,而鲁迅的批判则更多是内心的焦虑和愤慨,这样就使高晓声的作品缺少鲁迅的深刻,无法触及灵魂的深处,更难以达到鲁迅所具有的普遍性,不仅是农民的心路历程,也是国民的灵魂开掘,从文学和农村的角度思考,鲁迅的意义是永恒的……而鲁迅的作品正如他当时所看到的那样,由于他的主题的深邃,用心的深长以及客观条件的局限,他的作品只是局限在知识分子的狭小圈子里,而难以深入到广大农民之中。”(27)王吉鹏,赵月霞:《鲁迅、高晓声对农民心路探寻的比较》,《北方论丛》2003年第2期。从某些层面看,上述判断不乏之处,鲁迅的乡土小说实践中有不少幽微的超越感,超出了后人对其进行的各色限定,而这种超越感又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一)《明天》:真情跨过丧礼
作为农村寡妇的单四嫂子与其周围世界在文本中呈现出繁复张力,虽然她被多次描述为“粗笨女人”。患病的宝儿最终未被救活,但单四嫂子的行为及其母子真情却令人印象深刻。在疗救宝儿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周围世界的冷漠:中医何医生的误人子弟与敷衍塞责,蓝皮阿五的猥琐无聊等等。
而在宝儿去世后,各种丧葬仪式与程序进行得有条不紊、甚至近乎无可挑剔,我们依然可以从中读出单四嫂子内心的空虚——于她,宝儿意味着双重内涵。一方面是怀胎十月并含辛茹苦抚养的宝贝儿子,而这种倾力付出也得到了宝儿的感恩与小小梦想:“妈!爹卖馄饨,我大了也卖馄饨,卖许多许多钱,——我都给你。”(28)鲁迅:《明天》,《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78页。另一方面,作为身处男权社会的寡妇,单四嫂子的明天(未来)就在宝儿身上。在宝儿去世办丧事的场景中也可看出单四嫂子的真诚,尤其是和周围人完成任务的机械刻板相比。甚至鲁迅都忍不住让她顿觉空虚寂寞,还给她留下了做梦的安抚空间,“于是合上眼,想赶快睡去,会他的宝儿,苦苦的呼吸通过了静和大和空虚,自己听得明白。”(29)鲁迅:《明天》,《鲁迅全集》第1卷,第479页。
(二)《社戏》:超越乡村伦理
此文中呈现出鲁迅对中国戏曲的取舍和价值判断。文章伊始,鲁迅即表达了对中国戏的厌烦与反思,并借日本人的论述表达观感,“中国戏是大敲,大叫,大跳,使看客头昏脑眩,很不适于剧场,但若在野外散漫的所在,远远的看起来,也自有他的风致。”(30)鲁迅:《社戏》,《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89页。而故乡的社戏作为对照恰恰展现出其可读性与独特性。
梁漱溟指出,“中国所有文化,多半是从乡村而来,又为乡村而设,法制、礼俗、工商业莫不如此。”(31)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全集》第二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50页。疗治中国国民的劣根性大抵也要多管齐下,而从广袤的乡村开始则势在必行。在我看来,鲁迅在《社戏》中以回忆的视角描述了少年时期乡村看戏的美好经历。或许戏本身并不最吸引人,而是一帮少年摆脱束缚、集体划船、远观表演而后返回,途中宵夜的美好体验,令人记忆犹新。其中既有乡间朴实自由风格对传统长幼次序伦理的跨越,又有损己利人的利他精神传递(比如阿发希望采自己家的好蚕豆煮来吃)。这一切都是鲁迅“立人”理想的重要民间精神资源之一,可谓是一种对症下药。
(三)《一件小事》:担当与脊梁
从严格意义上说,小说中的车夫和老女人都未被明确说是农民,但作为农业大国,底层人士的身份往往与农民息息相关。“跌倒的是一个女人,花白头发,衣服都很破烂。伊从马路上突然向车前横截过来;车夫已经让开道,但伊的破棉背心没有上扣,微风吹着,向外展开,所以终于兜着车把。”(32)鲁迅:《一件小事》,《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81页。令人感动的是,车夫却自有其担当感,“扶着那老女人,便正是向那大门走去。”(33)鲁迅:《一件小事》,《鲁迅全集》第1卷,第482页。
而在文末,鲁迅还呈现出文化教育与小事的对照性:“几年来的文治武力,在我早如幼小时候所读过的‘子曰诗云’一般,背不上半句了。独有这一件小事,却总是浮在我眼前,有时反更分明,教我惭愧,催我自新,并且增长我的勇气和希望。”(34)鲁迅:《一件小事》,《鲁迅全集》第1卷,第483页。从此视角看,鲁迅对践行和脊梁精神的高度重视与嘉许,而这些恰恰是另一种内在的超越感。我们应该不分职业贵贱、阶层性别等等把这些精神都注入到民众的血液中去,更好地改造自己与奔向美好的未来。
五、结语
鲁迅的乡土小说实践自有其建设性,坚持自然主义或现实主义的学者/作家极易从进化论的角度得出鲁迅过时的整体判断,或者是批评其书写的相对粗线条,乃至不真切。但其实鲁迅迄今为止仍有乡土文学书写者值得大力借鉴的高妙优点,其中包括再现的同理心、厚实的批判力、绵密的文化性与深远的脊梁精神提倡。唯其如此,鲁迅的乡土文学书写才可称得上是源头与集大成者,如人所论:“尽管他对中国农民走向觉悟表现了更多的悲观倾向,但他却以更清醒、更深刻、更彻底的现实主义精神,在他的乡土小说创作中表现了真实的中国农民的心灵世界,从而也让世人看到了带有极强的农民性的中国民众的精神本质。鲁迅从启蒙主义立场出发,在其小说创作中以中国最底层的农民为视点,看到了文艺最应关注的群体,同时也就看到了中国走向世界最大的问题所在。同时,他的小说创作也为后来的作家关注农村、描写农民树立了光辉的典范。”(35)江卫社,叶峻:《中国农民:鲁迅乡土小说文化批判的视点与指向》,《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鲁迅的超越性确实值得我们仔细探勘与认真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