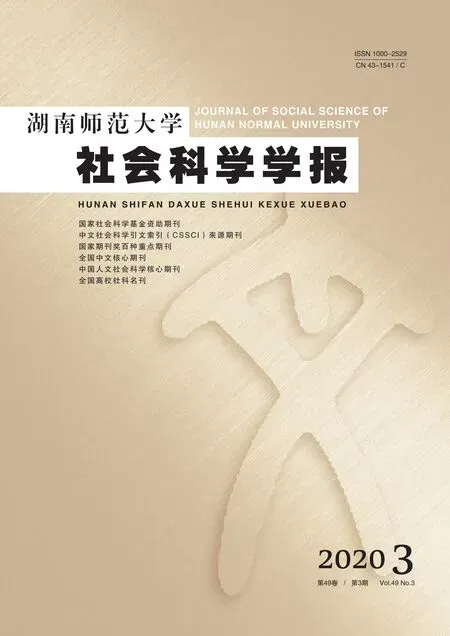社会凝聚力的人文化成:“诗可以群”的传播文化学解读
2020-01-19禹菲
禹 菲
诗歌由于其易记易诵且形式为人们喜闻乐见,自古至今一直是一种优位的传播媒介,作为中华元典之一的《诗经》则是华夏民族最早的价值观载体①。“诗可以群”之语出自《论语》。《论语》20篇中有8篇14处出现“诗”字,无一例外皆是就《诗经》而言②,而不是通指一般诗歌。《左传》所记各诸侯国卿大夫间“赋诗”“诵诗”皆指《诗经》,并非指赋诵他诗或自作诗。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春秋时期,世间文献尚少,《诗经》是那时最具经典意义的文献,士大夫言论动辄称“《诗》曰”“《诗》云”。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曾评论《荷马史诗》在希腊社会中的地位说:“那时的时尚是,一个人必须诉诸于荷马才能证明自己的全部知识(无论属于什么领域)的正确性,正如基督教作家诉诸《圣经》以证实自己知识的正确性一样。”[1]《诗经》在春秋时期的地位也有同样的情形[2]。加拿大传播学家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提出“媒介即讯息”,即人类拥有了某种媒介,才有可能从事与之相应的传播和其他社会活动。诗歌可以说是人类最早、最重要的传播媒介,经典性的诗歌尤其如此。
作为中华文明的瑰宝,《诗经》的深远影响缘于其内容的丰富性与表现手法的多元化,也与其独有的教化功能与传播效果相关。《论语·阳货》篇述孔子之语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通观整段话,其中的“诗”,是指《诗经》,因而孔子论《诗》所讲的“兴”“观”“群”“怨”的意涵,皆可从《诗经》的内证中获得解释。关于《诗经》,孔子连说四个“可以”,其隐含的意思是,通过《诗经》这一经典文本的媒介可以达到某种建设性、补救性的目标。
历代学者对于“诗可以群”的讨论不少,多集中在对“群”字的训诂上,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种解读:(1)将“群”解读为“群居”,如,何晏《论语集解·阳货》引孔安国之语说“‘可以群’,群居相切磋”。(2)将“群”解读为“和而不流”[3]。(3)将“群”解读为“合于众”,如,元代唐元说:“孔子论诗可以群,夫合于众之谓群。”(唐元:《筠轩集》,明正德十三年张芹刻本)现代学者杨伯峻则将“群”解释为“合群性”[4]。先秦时期学者对“群”字已经有很明通的理解,“群”字作名词用,是指人类之团体,如《荀子》卷六《富国篇》谓:“人之生,不能无群。”[5]“群”字作动词用,有聚合之义,如《荀子》卷三《非十二子篇》“群天下之英杰”[5]中的“群”字是聚合的意思。所以,孔子所说的“诗可以群”,其意是《诗经》具有聚合人群的功用。到汉代,“诗”上升为经,列为士子必读书目,因此成为千百年来的官方意识形态的标准教科书,其教化功能更是得到历代统治者和儒家知识分子的推崇[6]。用现代语言说,《诗经》能起到熔铸社会共同体凝聚力的作用。诗歌的创作有其目的性,被搜集整理成经典文本,并被配上乐曲,使其在人们广泛传唱、“寓教于乐”的传播形式中达到凝聚人心、整合社会等目的。《诗经》社会整合功能的发挥是日积月累和潜移默化的,本文借用“人文化成”的概念,体现和强调其影响的长期性与浸润性。“人文化成”出自《周易·彖辞》“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语用在本文中,是要表达这样一种理念,即凝聚力是一种无形的力量,“百姓日用而不知”,它不是刻意“建构”的,而是通过社会共同体在长期的教化过程中潜移默化形成的。
《诗经》是中华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其阐释与译注亦属集体创造过程,体现着共同参与和意义共享的传播特征。美国学者詹姆斯·凯瑞(James Carey)认为,从19世纪“传播”一词进入公共话语,美国文化中就存在两种不同传播观,一种是传播的传递观(a transmission view of communication),另一种是传播的仪式观(a ritual view of communication)。如果说传播的传递观其核心在于讯息在地理上的拓展,那么传播的仪式观其核心则是将人们以团体或共同体的形式聚集在一起的神圣典礼[7]。这一观念框架强调传播过程中的文化共享,并强调其在社会维系中的作用。传播的仪式观可以为《诗经》这种共享文化的传播功能研究提供思路。故本文以传播仪式观为框架,运用文本分析法研究《诗经》宗教信仰、民族史诗、燕饮礼仪和抗灾解难内容中的社会凝聚力化成机理,并在总结其共同体建构和社会整合功能的基础上,提出《诗经》传播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一、共同体建构:宗教信仰的凝聚力化成
传播的仪式观有着明确的宗教起源,且从未完全脱离宗教隐喻。从人类文化传播史看,世界各地区的文化都是以宗教为开端的。原始时代人们知识未开,生存能力低下,当面对强大的自然力量和严重的自然灾害时,幻想有超越自然的神秘力量来强化自己和拯救自己。在早期人类由氏族、部落、部落联盟,发展成民族国家的过程中,为防范和对抗强大异族的侵犯,会改造或改进原始宗教,使之更适应本民族文化精神的需要。于是能裁判人间是非、赏善罚恶的最高神明和本民族的最高保护神应运而生,相应的神庙、宗教教义、宗教组织、宗教祭祀等也随之完善,由此建立起社会共同体的共同信仰,且不容许任何外来民族的亵渎。对本民族共同神灵的虔诚崇拜,无形中增强了本民族持久而强大的凝聚力。宗教文化的凝聚力甚至超过其他思想文化的凝聚力。
宗教传播可以促使某种社会共识的达成,通过表达和强化共同信仰,宗教仪式创造了一种特殊的社会聚合和集体认同方式。懂得了宗教凝聚力的道理,再去读《诗经·周颂》中的宗庙祭祀诗,便会懂得其政治目的乃在于增强周族自身的凝聚力。《礼记·坊记》说:“修宗庙、敬祀事,教民追孝也。”追孝先祖,一方面表达对先祖的缅怀,以及继承祖先功业的决心,另一方面也在告诉同祖同根的族人要团结一心、守望相助。从社会整合的视角来看,后者的意义更为重大。
周人最高神是“天帝”,而祖先神是周文王。据周人说,周文王生前,天帝就很青睐他,曾传告他(“帝谓文王,予怀明德”),文王去世后,又无时不在天帝旁侧(“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表明文王在天神中据有很高的位置。按周代的礼制,主祭之人应是周王朝的现任君王,参加助祭的是分封在各地的诸侯国国君。这是规格极高的祭祀活动,能参加这样的祭祀活动是一种荣耀,在这种典礼中能排在前面,更是至高的荣耀。虽然,这不是全国民众参与的祭祀活动,但参与者乃天下各路诸侯,能凝聚、团结、稳定这些人,也就等于安定了天下。《周颂》首篇《清庙》,写的就是周王室在太庙举行的祭祖大典活动,祭祀的对象是周文王。《清庙》这首诗应是祭祀官在祭典开始时向天,也是向众人的呼告语,起着沟通人神志意的作用:“於穆清庙,肃雍显相。济济多士,秉文之德。对越在天,骏奔走在庙。不(丕)显不(丕)承,无射(厌)于人斯。”在可以与天神沟通的庄严的宗庙中,在伟大的文王的神位面前,各路诸侯郑重宣誓,要继续秉承周文王之德,团结在中央王朝的周围。周人得天下,本就是借助各方诸侯的力量,这可从《尚书·牧誓》武王的誓告中看出:“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在周人伐商的过程中,参战的还有其他异姓诸侯。因此,在周人克商之后,对这些有功的诸侯都进行了分封。这些有功的诸侯去世后,会被作为先臣陪同先王一起享受祭祀,这种祭祀制度即“配享”。如《孔丛子》卷上《论书》所说:“古之王者,臣有大功,死则必祀之于庙,所以殊有绩、劝忠勤也。”周人举行祭祖大典时,会对那些建国有功的先臣一同加以祭祀纪念。这样做的意义,在于劝导他们的子孙后代,特别是异姓诸侯能勤于政事、忠于周王。《周颂·烈文》这首诗就是为异姓诸侯而作:“烈文辟公,锡兹祉福,惠我无疆,子孙保之。无封靡于尔邦,维王其崇之。念兹戎功,继序其皇之。无竞维人,四方其训之。不显维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这不仅是对有功先臣的祭祀,也是对当世诸侯臣子的告诫,意谓莫在封国谋私利,当以崇王为本职。由此诗可以看出,周人以宗庙祭祀活动为媒介,强调了异姓诸侯与周王族之间增强凝聚力的重要性。
新王即位之际,较易发生政治动荡,因而新王与老臣的关系要处理得当。郑玄说:“新王即政,必以朝享之礼祭于祖考,告嗣位也。”[8]新王即位后要祭庙告祖,向先祖之灵禀告自己承继王位的事实。而此时诸侯来助祭,承认时王继位的合法性。《周颂·敬之》就是周成王即位时的宗庙祭祀诗。《敬之》一诗全文如下:“(前段)敬之敬之,天维显思。命不易哉!无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监在兹。(后段) 维予小子,不聪敬止。日就月将,学有缉熙于光明。佛时仔肩,示我显德行。”诗的前段六句是群臣进谏成王之辞,告诫刚即位的新王以及周贵族子孙要警惕再警惕,要懂得天命得之不易,天能赐给你“大命”,也能夺走“大命”,关键在于你能否修德,不要以为老天离人很远,实际上老天在监察着人间,人所做的一切上天明察秋毫,无不知晓,并会给予相应的福祸奖惩。后段六句是成王答对群臣之辞,成王自称小子我尚年幼,没有阅历,不能深懂“敬之”的至理,但要坚持每天学习,日久天长,终会慢慢接近光明之道,希望众臣和元老能辅佐自己担起重任,经常把美德和治国大道向我开示。这首诗以宗庙祭祀活动为媒介,强调新君与旧臣之间增强凝聚力的重要性。
作为一种古老的传播现象,宗教通过一整套象征性符号影响着人们的认知与情感活动,并通过共同意义的提供和规制化仪式发挥着社会整合功能。需要指出的是,一般的宗教大都具有排他性,例如在上千年的历史中,基督教与伊斯兰教曾发生多次大规模的宗教战争,即使基督教内部不同的教派也互不相容。但中国追孝先祖的宗教却是一种世界上最为宽容的宗教。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最不人道的是剥夺他人祖先享受后世子孙祭祀的权利,当时叫“覆宗绝祀”,所以,尽管周武王将商朝灭了,还要分封商纣王的儿子武庚以续殷祀;武庚反叛被诛,又封微子于宋以续殷祀。这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思想在宗教祭祀上的反映,正因为有这种思想,所以自古以来就有《尚书·尧典》中所说的 “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由此可见,华夏民族的上古宗教所传播的就是核心凝聚力或称宗族组织凝聚力,以及惠及外族的“公天下”的社会凝聚力。
二、记忆共享:民族史诗的凝聚力化成
记忆共享是民族认同感形成的前提,史诗的传播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顾名思义,史诗是一种以诗歌唱诵形式讲述本民族古老历史的文学。一些古老民族在未有文字之前就有了这种史诗形式,人们以传唱的形式讲述本民族的古老历史和先贤对世界的认知。古巴比伦有《吉尔咖美什》史诗,古希腊有《荷马史诗》,古印度有《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史诗。在中国少数民族中藏族有《格萨尔王》史诗、蒙古族有《江格尔》史诗、柯尔克孜族有《玛纳斯》史诗。这些史诗皆篇幅宏大。相比之下,《诗经》中讲述商族、周族的史诗篇幅甚小,因为篇幅较小,更便于人们在重要的聚会场合集体唱诵,也更利于本民族文化遗产的保存及本社会凝聚力的增强。
《诗经·大雅·生民》一诗,叙述周人始祖后稷的故事。后稷之母姜嫄踩了天帝留下的大脚印而怀有身孕,生下后稷。因而《生民》之诗说:“厥初生民,时维姜嫄……履帝武敏歆……载生载育,时维后稷。”姜嫄以处女之身受孕,以为不祥,把后稷弃置于各种环境中,结果出现了各种灵异,使后稷受到保护而安然无恙。姜嫄是远古姜姓部族的女子,其时应是母系氏族时代,只知有母,不知有父。后稷的出现,可能正是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的转变期。后稷长大后热爱农业种植,无论种豆、种谷、种瓜,都获得大丰收,因而《生民》诗中说:“蓺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穟穟,麻麦幪幪,瓜瓞唪唪。”帝尧时封后稷,后稷亦为司稷,后与司为一字,为官名。后稷对农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由此成为周人获得天命的早期源头,因而《毛诗序》说:“《生民》,尊祖也。后稷生于姜嫄,文、武之功起于后稷,故推以配天焉。”[7]
《公刘》也是周族的史诗之一。后稷去世,其子不窟世袭农官。可能遭遇了王朝的政治衰乱,不窟为了避祸,逃奔到了戎狄之间生存。到了不窟之孙公刘这一代时,公刘带领部族脱离戎狄,来到豳地发展。公刘是周族发展史上早期的一位关键人物。《史记·周本纪》评论公刘说:“百姓怀之,多徙而保归焉。周道之兴自此始。”[9]司马迁认为周道之兴应该是从公刘这一代开始的。《诗经·大雅·公刘》说:“笃公刘,于豳斯馆。涉渭为乱,取厉取锻,止基乃理。爰众爰有,夹其皇涧,溯其过涧。止旅乃密,芮鞫之即。”公刘是一位草昧开创之君,他在周人心中的形象,是一位仁爱、笃厚的首领,他虽为首领,却非常质朴,与人民同呼吸共患难,带领人民在皇涧、芮水两岸建造房舍,过上康乐的生活。清人顾镇《虞东学诗》说,《公刘》“六章皆冠以‘笃公刘’句,盖自不窟失官,再世不振,惟公刘克笃前烈,开周家一代忠厚之治”(顾镇:《虞东学诗卷九·大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绵》也是周族史诗之一。周族自公刘以后,又过了许多代,出现了公亶父③,一位周族的伟大祖先。公亶父是周文王的祖父,周武王克商后,他被追谥为“太王”,他在周族发展史上是一个关键性的人物,《鲁颂·宓宫》说:“后稷之孙,实维大(太)王,居岐之阳,实始剪商。”认为周族代商而君临天下的事业,是自公亶父开始的。公亶父时代,周边夷狄势力强大,经常侵伐骚扰周人所居之豳地。公亶父考虑到与夷狄硬拼,将会使大量人民失去生命。于是决定离开豳地,带领周人远徙,另寻安居之地,最后来到了周原。周原北依岐山,南临渭河,西傍汧(音千)河,东近漆水,由此形成天然的防御屏障,更主要的是这里土壤肥沃。在这里,公亶父娶了姜族的女儿太姜。这一婚姻,使公亶父得到了姜族的支持。周族得以在周原定居下来。此即《诗经·大雅·绵》中所说:“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周原由此成了周族的发祥地。在公亶父的率领下,周族逐步发展起来,并有了较强的军事力量,这为他的子孙王季、文王的功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皇矣》也是周族的史诗之一,它叙述了太王的三个儿子太伯、虞仲和季历的美好品德。三个儿子中季历最为贤明,两位哥哥主动让位弟弟,离开周邦去建立虞国。太伯、季历这一代非常团结,虞国成为配合周邦发展的国家。《诗经·大雅·皇矣》中写道:“帝作邦作对,自大伯王季。维此王季,因心则友。则友其兄,则笃其庆,载锡之光。受禄无丧,奄有四方。”《皇矣》还记述了王季之子周文王亲自指挥的讨伐密须和崇国的两场战争。其中讨伐崇国的战斗打得非常惨烈,崇国军事力量很强,城墙高耸牢固。周人久攻不下。天帝给予周文王启示:“帝谓文王:‘询尔仇方,同尔弟兄。以尔钩援,与尔临冲,以伐崇墉。’”要文王联合兄弟友邦,谋划商量,用钩援、临车、冲车等武器装备来攻伐崇国,最终打败了崇国。《皇矣》叙述了周人灭商前关键的两次战争,并把周邦讨伐崇国的战争说成是天帝的意志,宣扬周人发动讨伐战争的合理性。
《文王》也是周族史诗之一,歌颂的是周王朝的奠基者周文王姬昌。因为周文王是上古历史上伟大的圣王之一,《诗经》编纂者遂将《文王》一诗列为《大雅》之首。姬昌继任周邦国君之后,继承周人先祖后稷、公刘开创的事业,遵循祖父公亶父和父亲季历制定的法度,厚爱仁者,尊敬老者,慈爱幼弱。平日以礼接待贤能之人,使天下许多贤士都来投奔归附于他,其中包括气节很高的伯夷和叔齐,以及殷商王朝的贤大夫如太颠、闳夭、散宜生、鬻子、辛甲等人。在众多贤者的帮助下,周族的势力越来越大,文王的威信越来越高。诸侯们有了纠纷,不去找商纣王解决,却来求文王评判。其中著名的故事就是“虞、芮之争”。据说虞、芮两国首领在田地归属问题上有争执,就来到岐周找文王评理。来到周邦之后,发现“耕者让其畔,行者让路”,百姓以礼让为俗。两国首领见此情形感到羞愧,没等到见文王,就互相礼让起来,争端自行解决,两国都归附了文王。诸侯们听说之后,揣度道:“西伯也许就是受命之君吧。”《文王》一诗是周人在宗庙祭祀时的祝颂诗。此诗开篇即说文王死后成为天上的大神:“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诗中还强调,虽然周族受到天帝和文王在天之灵的福佑,但周族人还是要时时警惕:“无念尔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命之不易,无遏尔躬……仪刑文王,万邦作孚。”《文王》一诗明确地提出了本族的历史使命:“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而要实现这种历史使命,就要求周人和天下人“仪刑文王,万邦作孚”,这是周族和天下各族能形成强大凝聚力的重心所在。
《诗经·周颂》中还有其他关于周族的史诗,但以上五诗所述已可勾勒出周族所经历的千百年历史,历代周族祖先筚路蓝缕的创业精神、忠厚礼让的做人品德、坚韧不拔的民族性格,以及周文王的伟大感召力量,使得周族人感到自身肩负着“其命维新”的神圣历史使命。而借助史诗的唱诵,能在无形中增强民族的自豪感和凝聚力。这种基于共同历史感召而聚合在一起的个体可能互不相识,但他们却因共享着一种有道德意义的历史而形成具有凝聚力的社群。由群体成员的个体经验综合而成的共同记忆是群体在生产实践与社会生活中的物质与财富成果的抽象化呈现,承载社会记忆与共享经验的民族史诗在个体心理构图和群体认同体系的建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三、仪式展演:燕饮礼仪的凝聚力化成
仪式是利用一套象征性符号体系进行展演,以期达成意义的一致[10]。程式化的展演结构和仪式流程形成于重复性的传播实践,也在某种程度上通过符号体系的积淀、传承和共享规制的建立起到化成凝聚力的作用。“酒”文化及以其为中心的礼仪规制在不同文化情境中都发挥过独特的社会整合功能。人类的社会生活,自古及今,东西方千差万别,但也有许多近似的地方,比如东西方都很早就发明了酒。早在公元前7世纪,古希腊就有了“酒神节”,人们在这个节日为酒神狄奥尼索斯大唱赞歌。在古代中国,虽然没有酒神和酒神节,但对酒也相当地重视。古人将天上的一颗星命名为“酒星”,将西部地区的一眼泉水命名为“酒泉”。而酒与朝代更替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如中国历史上的夏商灭亡就与当时统治阶层纵酒有关。这种历史教训使得周初统治者格外矛盾:一方面发布《酒诰》严禁酗酒;另一方面,周初统治者又深知正常、恰当的燕饮活动可以联络君臣感情、增强全国上下的凝聚力。因而周人朝野一直谨慎地对待燕饮问题,也制定了繁复的礼仪加以规范。音乐的演奏、诗歌的唱诵便是礼仪的重要内容,无论诸侯的燕礼,还是乡党社会的乡饮酒礼,都少不了歌诗奏乐活动。因此,原是诸侯国君燕飨群臣和嘉宾的歌乐,后来也成为上下通行的歌乐,只是有在朝称君臣,在野称宾主的区别。如《小雅》中的《鹿鸣》《四牡》《裳裳者华》《常棣》《伐木》《天保》《鱼丽》《南山有台》等都是常用于燕飨的诗歌。这种燕飨活动以及燕飨时所演唱的歌乐、所要传达的意思,就是增强族群政治高层或社会底层的凝聚力,并且使这种政治目的在上下愉悦相处时不知不觉地实现。
最典型的燕饮是《小雅》首篇《鹿鸣》,“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在古人看来,鹿是一种高雅的动物。鹿见到美草,呦呦相呼,要同伴来分享,比喻国君所宴请的嘉宾都是贤人。宴席上不仅有美食,还有高雅的音乐。接后的四句写道,“吹笙鼓簧,承筐是将。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周”是忠信的意思,“行”是道路,这句诗是说:喜爱我的贤人,向我开示忠信之道。《鹿鸣》所描绘的是君臣推心置腹相交、和乐融融的景象。上海博物馆藏《孔子诗论》说:“《鹿鸣》以乐始而会,以道交,见善而效,终乎不厌人。”[11]以演奏《鹿鸣》的音乐开始聚会,其意义在于表达君臣之间以道义相交,这种道义之交终其一生也不会厌烦。所以,《鹿鸣》所展示的燕饮不是酒肉饱腹、大快朵颐的快感,而是君臣一心、以道相交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体现。
《诗经》中《鹿鸣》以下几篇都是国君宴请群臣嘉宾时演奏、歌唱的诗篇。如《四牡》一诗为君王感谢使臣之诗,使臣终年旅途劳顿辛苦,“岂不怀归,王事靡盬,不遑宁处”正是这些使臣的写照。《裳裳者华》的“载驰载驱,周爰咨询”则说使臣因为对外交事务有深度了解,因而成为君王的重要谋臣和智囊。《常棣》则极言兄弟恩深,异形同气,死生苦乐,休戚与共,“死丧之威,兄弟孔怀”暗喻君臣、宾主之间的关系亦如“兄弟”关系。《伐木》一诗说:“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出自幽谷,迁于乔木。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朱熹注此诗说:“以‘伐木丁丁,鸟鸣嘤嘤’而言鸟之求友,以喻人之不可无友。”此诗作为朝野燕饮之诗,暗喻朝廷君臣之间、乡党邻里之间应该是好朋友的关系,应守望相助。
以上五诗,是朝廷人君燕飨群臣、乡党主人宴请宾客所唱诵之诗。其后有群臣、宾客答谢宴会主人的唱诵诗《天保》。苏辙《诗集传》卷九说:“《天保》下报上也。人君以《鹿鸣》之五诗,宴其群臣。《天保》岂以答是五诗于其宴也皆用之欤?”[12]《天保》诗中多是臣下祝愿其君的颂辞,如“受天百禄,降尔遐福”“如南山之寿”“如松柏之茂”等等。这种唱诵一方面是宾客对主人宴请的感谢,一方面也是臣下向君上表忠心,由此增强君臣上下或乡党邻里之间的凝聚力。
在《诗经》305篇中,许多诗与酒和燕饮有关,其中有一篇专门强调燕饮礼仪的诗《小雅·湛露》,据说是天子燕飨诸侯之诗。这首诗中的“厌厌夜饮,不醉无归”,表示天子待诸侯恩深义重,“岂弟君子,莫不令仪”告诫诸侯不能真的喝醉,喝醉了就会忘其形骸,乱德失态。所以这首诗“于褒美之中,而寓规戒之意”。
有鉴于历史上夏桀、商纣纵酒亡国的历史教训,所以西周时期的人们讲究饮酒有节制。周人理想的燕饮状态是,既能做到宾主尽欢,又能看到君子们的嘉美德行。反之,若有人在燕饮时喝醉了,且有失礼、失态的行为,就会被人看不起。正因为如此,周人制定了许多繁琐的饮酒礼仪,《礼记·乐记》说:“先王因为酒礼,一献之礼,宾主百拜,终日饮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备酒祸也。”[13]宾主相互劝酬一次,就要进行繁多的仪节动作,互相拜来拜去,所以终日饮酒也不至于醉。仪式是一种象征性的和富于表现形式的行动,一种制度化的创造特殊时空的手段,个体在其中可以体验到自己是这个共同体中的一分子[14]。燕飨诗的传播和燕饮礼仪的普及在带给人们参与感和体验感的同时,也起到了提升群体认同感和增强社会凝聚力的作用。
四、情感嵌入:抗灾解难的凝聚力化成
中国是一个有数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在其文明发展过程中经历了许多次大的灾难,在这些灾难面前,中国人表现出了不屈不挠、愈挫愈勇的精神气概。曾经研究过世界26种文明类型的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对中华文明充满了赞许,他说:“如果我们再研究一下黄河下游的古代中国文明的起源,我们发现人类在这里所要应付的自然环境的挑战要比两河流域和尼罗河的挑战严重得多。”[15]这种自然环境对居住在这里的中国先民构成了严重的“挑战”。
中国古籍《尚书·尧典》中记载:“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舜帝派大禹治水,大禹率领各氏族人民治水十余年,获得大成功。那时,“天下万邦”,氏族众多,但各氏族为了一个共同的“治水”目标,融合在一起,治水成功之后,大禹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文明国家——夏朝。自从有了史前大洪水的经历,以及后世无数次大灾难的经历,华夏民族成员认识到一个真理,即只有“大一统”下的社会共同体才能应对自然界的大灾难,由此中国人把“大一统”作为本民族的核心价值观之一。
大禹率领各氏族人民战胜水灾,因而成为不同氏族共同景仰的英雄,这在《诗经》中多有反映。如《诗经·商颂》现存五篇,其中就有两篇提到大禹,《商颂·长发》中说:“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国是疆,幅陨(员)既长。”《商颂·殷武》中说:“天命多辟,设都于禹之绩。”再如《诗经·鲁颂·閟宫》中说:“奄有下土,缵禹之绪。”鲁国是周公封国,周人认为本族继承了大禹的余绪。还有《诗经·大雅·文王有声》“丰水东注,维禹之绩”,《大雅·韩奕》“奕奕梁山,维禹甸之”,《小雅·信南山》“信彼南山,维禹甸之”等诗都把大禹奉为前世伟人,颂赞他的伟大功绩。这种不同氏族对共同尊奉的英雄的纪念与缅怀,化成了强大的社会凝聚力。
《诗经·小雅·鸿雁》是一首典型的救难诗。《毛诗序》说:“《鸿雁》。美宣王也。万民离散,不安其居,而能劳来还定,安集之,至于矜寡,无不得其所焉。”郑玄《笺》补充说:“宣王承厉王衰乱之敝而起,兴复先王之道,以安集众民为始也。”[8]周厉王暴虐无道,人民外逃,过着颠沛流离的痛苦生活。周宣王即位后,整顿朝政,兴利除弊。为了救助流离失所的人民,周宣王派出使臣招徕流民返归故里,或者就地营建邑屋加以安置。诗中说:“之子于征,劬劳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鳏寡。”这是颂扬使臣们的辛劳与仁爱。周宣王的这一举措,招来两种不同的声音,诗中特意评价了两种声音说:“维此哲人,谓我劬劳;维彼愚人,谓我宣骄。”意思是说,那些明白人知道这些使臣们辛劳的社会意义,那些糊涂虫说这是耗费资财,张扬夸耀,那就让他们说去吧。周宣王这种救难德政,发挥出了巨大的社会凝聚力,使得已经衰落的周朝再度复兴,史称“宣王中兴”。
《诗经·国风·卫风·木瓜》也是一篇与救难有关的诗篇。《毛诗序》说:“《木瓜》,美齐桓公也。卫国有狄人之败,出处于漕,齐桓公救而封之,遗之车马器物焉。卫人思之,欲厚报之,而作是诗也。”[8]当年,狄人攻占卫国,杀卫国君主卫懿公,在都城中烧杀抢掠,卫国一部分人逃至与宋国接壤的黄河边。先是宋桓公派人救援卫国人,将他们安置在宋国境内的漕邑,并派兵守卫。后来齐桓公也来救难,带来车马器物等大批物资,还派来三千士兵保护卫国人。齐桓公还以诸侯盟主的身份,动员各诸侯国帮助卫国人重建家园。卫国人对齐桓公十分感激,出于感恩的心理,写下了这首诗,诗中说:“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齐桓公这种及时出手救苦救难的行事风格,也在当时盟国间起到了巨大的示范作用,增强了盟国之间的凝聚力。
利益攸关的灾难,在给群体成员带来共同的恐惧体验时,也为群体成员团结一致、共渡难关的信念达成提供了语境。于是,对自然的畏惧和对共同风险的恐惧将势单力薄的个体连接在一起,抗灾解难的英雄故事激发起成员的感恩心理与患难与共的集体情怀,共同情感的维系和情绪共鸣在群体凝聚力的化成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五、余论
寻找认同与故乡,是人类本然的宿命[16]。《诗经》的形成与传播在我国古代的民族认同感建构和社会凝聚力提升方面都起到过不可忽视的作用。“诗可以群”,人们在传播《诗经》的同时,也在共享着一种仪式和文化、一种精神沟通和群体认同。传播的仪式观将传播的最高境界视为“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的、有意义的、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8]。诗的创作与传递无疑在这张文化之网中发挥着重要的功能。《诗经》的传播助力着民族共同体的建构,也在某种程度上刻画和彰显了共同体的群体记忆、仪式规制、情感特征和信仰价值。
在《诗经》的传播过程中,传者和受者都成为参与者,建构和体验着共同的仪式,并通过对共同符号的解读和分析增强了群体认同感和社会凝聚力。“社会凝聚力”问题是现代哲学、社会学、政治学和传播学的一个重要课题。在古代,并没有“社会凝聚力”的类似概念,当然也没有关于此问题的理论探讨。但这并不意味中国古代不存在“社会凝聚力”的问题,只不过它的形式不是某种抽象的理论思考,而往往表现为充满感性和活力的具体的行为方式。从上述讨论可见,《诗经·颂》的部分主要是宗庙诗,通过强化宗庙信仰来增强凝聚力;《诗经·大雅》的部分主要是民族史诗,通过史诗唱诵来增强凝聚力;《诗经·小雅》中有许多燕饮诗,通过强调燕饮礼仪规范的方式来增强凝聚力。《诗经》中还有分散在《颂》《雅》《风》各部分的灾难诗,通过强调抗灾解难的方式来增强社会凝聚力。这些内容对我们今天的启迪是:社会凝聚力的化成和增强,需要有其具体的“着力点”,而不是空谈理论就可以做到的。
凝聚力如何化成和增强?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重要问题,古人并没有大张旗鼓地宣传“社会凝聚力”如何重要,而是根据民族文化心理,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来对待它,其中最有效的就是通过本民族的共同信仰、共同历史、共同生活、共同忧患来化成和增强“社会凝聚力”。这种共同的信仰、历史、生活、忧患,向上升华,就成为了《诗经》。在上古时期,甚至文字还没有发明的时候,《诗经》成了讲述本民族共同的信仰、历史、生活、忧患的最主要载体。人们以《诗经》作为媒介进行传播,可以达到传递信息、沟通思想、交流情感,以及解决问题、规范行为的目的。以《诗经》为媒,增强社会凝聚力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因而,“诗可以群”,从社会凝聚力“人文化成”视角来进行现代解读,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
注释:
① 先秦关于《诗》《书》《礼》《乐》《易》《春秋》的排序,以及孟子“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孟子·离娄下》)之语,可以说明这一点。
② 《诗经》是汉代才有的名称,在先秦称为《诗》或《诗三百》。
③ 《史记》中说:“古公亶父复修后稷、公刘之业,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古公亶父”实际是自司马迁以来对“公亶父”的误称,“古”是古昔之义,“公”是当时周人对首领的称呼,“父”是男子之美称。正确的称呼应该称为“公亶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