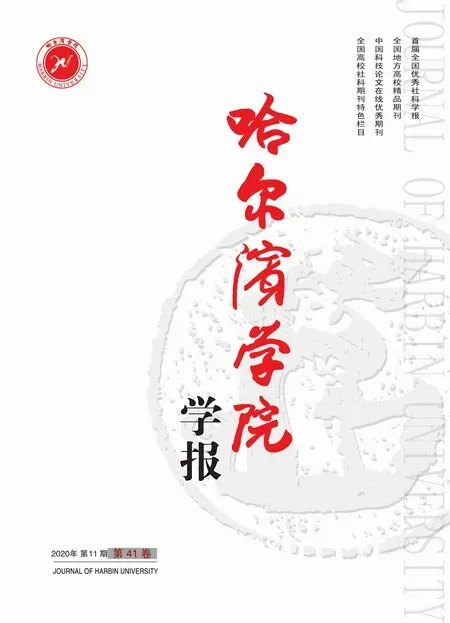灾难文学审美维度的呈现
——论《云中记》的灾难美学
2020-01-19张思远
张思远
(辽宁师范大学 文学院,辽宁 大连 116081)
汶川地震之后文学界用“井喷”一词形容当时的文学创作。这些文学作品多以诗歌为主要题材,同时大多以歌颂祖国、歌颂集体主义、歌颂汶川人民、歌颂英雄主义为抒情主体。支宇曾言:“当太多的写作者轻而易举地将真实人生经验转化为共性化的情感抒发的时候,灾难写作的话语形态和精神内涵就显得过于同化和模式化了。”[1]这种模式化的产生是因为大多数创作者没有掌握灾难文学的叙事方式,没有处理好灾难发生后“即时性”创作和“延时性”创作之间的关系,缺乏灾难意识,导致了其作品抒情主体、话语形态、主题内涵呈现出了单一化、模式化的特点。事实上,面对自然灾难和灾难给人带来的巨大身体和精神的创伤,文学应该从何种角度入手,才能够展现灾难文学应该具有的审美特质,是我们一直积极探索和思考的问题。在重大自然灾难发生之时也必然伴随着大量的伤亡,文学面对着巨大的伤亡数字,应该以何种姿态和审美视角去书写,现实中存在的悲剧如何呈现在文学作品之中供人欣赏品读,这些问题是在对灾难书写之前需要厘清和明确的问题。而小说《云中记》厘清了这些复杂的因素,找到了新的路径写灾难和死亡,呈现了中国当代灾难文学书写应具有的审美维度,弥补了中国灾难文学的缺失。
一、恐惧之美
“死亡恐惧自古有之,在当今社会尤甚”。[2]自人类诞生伊始,对自然灾难就有着敬畏与惧怕之情,这样的情感直到现在依然存在于人类的内心深处。因此,在进行灾难文学书写时,技艺高超的作家会着力展现灾难发生时的惨烈情状,让阅读者身临其境感受灾难发生时的恐惧。《云中记》中有很多描写地震发生时场景的片段:“14时28分。潜伏的巨兽咬断了岩层的牙齿,剧痛产生力量,闪电一般蹿过层层叠叠的岩层,在云中村东边几十里,蹿出了地表。那一刻,地震发生!大地从自身黑暗力量感到恐惧的快意,浑身颤抖,隆隆咆哮。”[3](P98)“共同的回忆中,有一刻,那越来越大的,像是有无数拖拉机齐齐开进的轰隆声突然静止了。世界静止了。接着大地猛然下沉,一下,又一下,好像要把自己变成地球上最深的深渊。而另一些人感到的不是下沉,而是上升。大地上蹿一下,又猛地上蹿一下好像把自己变成比阿吾塔毗还高的雪山。”[3](P99)“然后,声音就起来了。撕心裂肺的哭叫声响成了一片。当尘土散开,哭叫声笼罩住了整个村庄。”[3](P100)以上对地震发生时场景的描绘,让读者体会到了最真实的代入感,感受到了地震爆发时的恐惧。恐惧作为人类情感的一种,其本身具有审美特性。“恐惧是现在人的生存体验,也是审美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美学范畴。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认为恐惧(畏)作为现身情态就是在世的一种基本方式。”[4]然而,并不是全部的人都有机会经历自然灾难并直接的面对和体味恐惧。处在自然灾难中的人类会感受恐惧、绝望、痛苦,而那些没有经历过灾难的人可以作为一个旁观者的角度以阅读的方式感受灾难,这种阅读带给了读者以全新的体验。
《云中记》中对大地的剧烈运动的描写,除了能给人以代入感,让人感受到灾难来临时的恐惧之外,它更强调了在恐惧中发现人类自身,直接的面临生存的意义。随着社会不断的进步,现代文明不断的发展,一个独特的生存个体开始被各种社会角色所裹挟,人们在各种社会关系之中生存,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逐渐被社会关系所替代。即使在云中村这个小村庄中,随着现代化文化进入村庄,每个人都开始逐渐的丧失了本我。当人类开始逐渐忽略自己的自然属性时,面对灾难也就有着更大的恐惧感。但是这种恐惧感可以使现代人混乱的生命意识回归,重新感受生命的本质意义。在地震发生时“他们都大张着嘴,还没有发出声音。有人茫然地看着自己的腿在墙的另外一边。有的人惊讶地看到自己怀抱着一块沉重的石头,血从胸腔里涌出,像是要淹没那块石头”。[3](P102)灾难降临之时,经历灾难的人都作为一个自然生存个体存在,他身上的所有社会角色褪去,回归了生命最本真的状态,灾难和灾难中经历的恐惧本身就是对人类自身本源性的一种救赎。因此,一部灾难文学作品是否表现出恐惧蕴含的深层含义,是衡量其是否具有审美性的重要标准之一。
二、悲剧与崇高之美
约翰·德莱登曾经这样解释过悲剧和崇高之间的关系,必须是伟大的人物做出的伟大的行为,才能构成悲剧行为。具有悲剧精神的人物对异己力量注定失败的反抗是具有悲剧性的,但是在明知道会失败的前提下仍然选择反抗,这种精神就是崇高的。悲剧若要具备审美的美感就需要在悲剧中体现出人格的崇高。我们感受到,当人抛弃了世界、社会与众人的评价所赋予的利害关系,而完全凭借着自身纯粹的自觉,甚至不惜对生命的放弃来达到自我价值的认同时所体现的悲壮,它是对人性中的自私和邪恶最有利的回击。一部灾难文学作品,只有表现出这种悲壮感和崇高感,才能被称为是一部优秀的作品。《云中记》中阿巴回到云中村,在云中村祭祀亡灵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但是他没有选择回到移民村,而是不顾外甥仁钦的前途,毅然选择和云中村共同消失。面对强大的自然力量,阿巴深知自己是渺小的,但是他仍然选择面对死亡,寻找自我,因此阿巴放弃生命选择和云中村一起消失的这个举动之所以让人震撼,之所以让人欣赏,不是因为它具有悲剧的美感而是因为具有崇高感。
灾难文学需要如何构建崇高之美?具有崇高之美的人是在与受难者有共性的同时又具有独特性的悲剧人物,这个人物的思想、行为能够形成完整的叙事体系,其不需要是一个勇于牺牲的高尚英雄式的人物形象,但要能体现出人物形象的立体性,最重要的是他们能够让人们感觉到这个人物在精神上是完整统一的,能够净化和抚慰生者的精神,让人懂得寻求生命存在的价值。毋庸置疑,阿来在《云中记》中成功的构建了一个具有崇高之美的人物,即阿巴。阿巴他有些天真,又有些偏执,曾经还是一个失去记忆的“傻子”,但是读者看到了一个人在面临灾难时的真正的姿态。“阿巴徒手把一块块通红的木炭抓起来,投入香炉。木炭烧灼着阿巴的手指,阿巴还是不管不顾,徒手把一块块燃烧的木炭投入了香炉”,[3](P101)“香炉里的香烟升起来,他呼喊回来!回来!他击鼓摇铃,声声呼喊:回来!回来!他要安抚灵魂,安抚云中村,不让悲声响起。”[3](P103)巨大灾难的发生,让阿巴意识到自己“非物质文化”的身份,他不知道祭师应该怎样安抚灵魂,他用自己的独特的方式做着法事。阿来曾说到,地震这样巨大的灾难,反而激发了许多人的觉醒,只有在那种极端的环境中,一些人突然发现自己跟别人的关系中占据主动,并承担起责任。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带来一种超越个人的崇高感、沉重感。阿巴用祭师的身份去祭奠逝去的生命,甚至选择和云中村一起消失,阿巴祭祀的过程和最后选择死亡的方式蕴含着悲剧感和崇高感,这种具有悲剧感和崇高感的死亡覆盖了十年前地震造成的仓皇而惨烈的死亡,在这个角度来说他不仅在安慰着死难者的亡灵,净化着生者的灵魂,同时也在自然力量下找到了自己存在的价值。
三、返乡之美
一部优秀的灾难文学作品,关于灾后“返乡”的叙述是至关重要的。这样的返乡叙述一般具有心理疗伤的意义。很多情况下,如若不需要特别切入角度(比如亡灵叙述),那么对于灾难叙述一般是由经历过灾难的人来进行叙述的,他们的记忆能够重返发生过惨烈灾难的家乡,说明他们可以重新和故土产生精神上的联系。一般的灾难文学作品,在展现“返乡”时大都是通过回忆的方式,事件的讲述者不一定回到了灾难的发生地。但是《云中记》是不同的,阿巴回到了云中村,每一个死者的形象都在他的回忆中一点点复活,让我们看到了灾难发生之前云中村每一个家庭的生活是怎样的温馨。在这里,阿来通过阿巴的回乡,通过阿巴对逝去者的回忆,让我们知道了“生者如何经历死亡经验,并且如何面对死亡经验而重新活着”。[5]阿巴的返乡给生存者一个一同返回故乡的机会,通过这种方式给依然生活在苦痛中的人以救赎。
一个重大灾难的发生,对一个国家、民族、个人的影响都是巨大且深远的,一个地区的文化、精神在地震之中以及之后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是文学应该去关注和探讨的问题,而一部作品要想通过灾难去探索生存在这里的个体人性发生了怎样的变化,重新建构这个地区的文化和精神,那么这部作品必须有“返乡”叙事。这里的返乡叙事也蕴含着重建的愿望。在《云中记》中,除了阿巴回到了云中村外,还有两个人带着不同的目的回到了云中村,一个是央金还有一个是中祥巴,阿来通过这三个人返乡的不同目的,从生命、伦理、道德等方向探讨这场大不幸的自然灾难的人文含义。央金为了拍参加比赛的宣传片回到了云中村,进入云中村后,她的悲伤或许大部分都是真的但是当她以利益为目的回到云中村的那一刻也注定着她对云中村和村中的死难者的缅怀并不纯粹。相比央金来说,中祥巴的回归更具有消费苦难的意味,他甚至没有踏上云中村这片土地,而只是坐在热气球上在天空中遥望云中村。文中写到:“阿巴都来不及对这从未见过的新奇事物感到好奇了。他也无从得知这怪物的名字。没有名字的东西那就只能是:一个怪物。”[3](P366)这里的“怪物”有着深层含义,一方面蕴含了传统和现代之争的深层主题,更主要的是点出了以中祥巴为代表的,经历过灾难的生存者为了利益消费苦难这一现象,在文中他并没有说明谁对或者谁错,只是给读者展示出了在这一现象背后,关于道德的、人性的、生命的很多值得思考的问题。阿来的写作是明朗而又贴近现实的,他将灾后现实存在的问题,通过小说中人物“返乡”的方式表达出来,脱离了以往灾难文学的偏于记录事实弊端,体现了灾难文学应具有的美学意蕴。
综上,灾难文学主要以灾难为书写对象,灾难书写也就必然要表现现实的悲剧。然而,文学书写不能仅仅表现现实悲剧而忽略文学本身应具有的美学意蕴。《云中记》虽以惨重的四川大地震为背景,但其充分表现出了灾难文学的书写美感,体现了灾难文学特有的审美特质。因为,无论是自然灾难还是社会灾难,在其发生后对于国家、民族、社会、个人都有着深层次的影响。灾难的发生重新考量人的价值,发现人性的契机。不应单纯的进行英雄式的歌颂,把悲剧变成“喜剧”,而应承担在灾难中发现社会问题、挖掘人性的责任,理智且清醒的前进。从这个角度来说,阿来的《云中记》在中国灾难文学创作史上是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