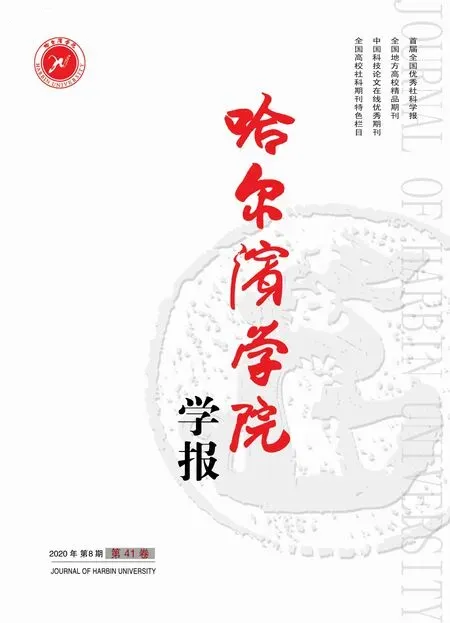张华与西晋文坛
2020-01-19杨兴龙
杨兴龙
(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文学与传媒学院,甘肃 成县 742500)
西晋的最高统治者本非文人出身,他们也不太重视文学事业。司马懿父子忙于篡夺,不暇文事。武帝在文化上只是提倡儒学而已,对文学事业也没有深远的考虑。惠帝不慧,更不必言。他们“既未曾作出任何理论性的提倡或引导,亦无可能在文学创作上率先垂范”,[1](P248)总之,没有对文学发生任何正面的、积极的影响。晋武帝司马炎在即位之初,下诏大弘俭约,禁乐府靡丽百戏之伎及雕文游畋之具。但平吴之后,“天下乂安,遂怠于政术,耽于游宴”,[2](P80)对戚属臣下过于放任纵容,导致整个社会丧失道德规范,建安时期那种积极向上、建功立业的精神荡然无存。西晋时期,文学基本上处于放任自流状态,传统的政教精神弱化,文士们的政治道德理念和社会责任感淡薄,他们多关心自身得失。
曹魏实行的“九品中正制”最终导致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西晋时士族与寒门的对立与矛盾已相当突出。为了缓和这两类人之间的矛盾,司马炎崇尚儒术,采取了举寒素政策,通过举孝廉、秀才、寒素等名目,使一些寒门士人凭借修德求仁、博学属文以应荐举而进入仕途,张华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脱颖而出,由寒门而致显位的。张华是魏晋时期继曹氏父子之后大力倡导文学的重要人物,西晋一代,真心实意倡导文学的是张华。笔者试从以下三方面谈谈张华与西晋文坛的关系。
一、大力奖掖提携文士,促成了太康文学的繁荣
西晋政权的篡夺性使得有气节的文人对其不齿,心理上一时难以接受。新建王朝出于统治的需要,不得不眼光向下延揽人才。张华正是适应了这种政治需要,为朝廷大力延揽人才,得到了西晋统治者的认可。
张华是西晋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有治国之才,历仕两朝事二帝:魏末被荐为太常博士,除著作佐郎,迁长史,兼中书郎;晋武帝时,因力主伐吴有功,进封广武县侯,惠帝时任太子少傅、中书监,拜司空。永康元年(300),被赵王伦矫诏杀害,时年六十九岁。
张华少自修谨,学业优博,少年时就博得同郡卢钦的赏识,《魏志·卢毓传》注引虞预《晋书》曰:“(张华)家单少孤,不为乡邑所知,惟钦贵异焉。”[3](P653)徐广《晋纪》曰:“张华少自牧羊,而笃志好学。初为县吏,卢钦奇其才,数称荐之。”[4](P958)《晋书·张华传》记载:“华少孤贫,自牧羊,同郡卢钦见而器之。”[2](P1068)卢钦是东汉大儒卢植之孙,魏司空卢毓之子,“世以儒业显,钦清淡有远识”。[2](Pl255)张华之学业优博,及其“少自修谨,造次必以礼度”的儒者风范当受卢钦影响极大。在卢钦及郡守鲜于嗣的荐举下,张华声名日盛,时任方城侯的乡人刘放看重张华的才华,并将女儿嫁给了他。张华在政治思想和文学创作上受其岳父刘放的影响极大。张华据《逍遥游》中“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创作了《鹪鹩赋》,“陈留阮籍见之,叹曰:‘王佐之才也!’”[2](P1069)并由此获得了较高的声誉。总之,与刘放的联姻以及阮籍、卢钦、鲜于嗣的推荐都对张华的仕途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曹魏时张华才学出众,已经很有名气,武帝时,尽管张华为官清正,时誉很高,有台辅之望,却长期受到压制,惠帝时因他出身寒素,“进无逼上之嫌,退为众望所依”,[2](P1070)颇受贾后、贾谧信用,成为朝廷的重臣。张华的一生,入仕前生活较为艰辛,入仕后官运亨通,作为一个落魄官宦子弟,无依无靠,凭自己的努力位至三公,可谓是寒门子弟的楷模。
张华步入仕途后,利用其政治威望大力奖掖提携文士。《晋书》张华本传记载:“华性好人物,诱进不倦,至于穷贱侯门之士有一介之善者,便咨嗟称咏,为之延誉。”[2](P1074)《晋书·范乔传》载:“张华领司徒,天下所举凡十七人。”[2](P2432)其实,张华所举之人不止十七人,有人统计被张华称许或举荐的文人武将达三十一人,[5](P11)其中大多数为文人。有由魏入晋的的文人、蜀地文人、吴地文人,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寒士。文人中著名的有束皙、成公绥、挚虞、左思、陆机、陆云、陈寿和李密。蜀地文人较吴地文人入洛早些,因他们大多积极向西晋政权靠拢,政治处境相对要好一些。吴地文人被北方人视为亡国之余,他们入洛后,北方人大都不屑与之交往,且不时遭到北方高门大族的奚落、侮辱,而张华却对他们极力褒奖,称他们或为“东南之宝”,或为“南金”,或为“凤鸣朝阳”。对陆机、陆云两兄弟评价极高:“伐吴之役,利获二俊。”[2](P1472)由此可见,张华爱才惜才,开明大度,不拘泥于礼法世俗和细枝末节,打破了地域观念和世俗之见,看重人才的整体素质和真才实学。被他称许或举荐的人才后来成为了西晋政坛、文坛的中坚力量,为西晋王朝输入了新鲜血液,可谓贡献卓著。对于这些文人成就,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曰:
晋虽不文,人才实盛:茂先摇笔而散珠,太冲动墨而横锦;岳湛曜联璧之华,机云标二俊之采;应傅三张之徒,孙挚成公之属,并结藻清英,流韵绮靡。[6](P674)
钟嵘在《诗品·序》中叙述建安至西晋诗史的发展情形说:
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托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尔后陵迟衰微,迄于有晋。太康中,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勃尔复兴,踵武前王,风流未沫,亦文章之中兴也。[7](P12-14)
西晋“人才实盛”及“文章中兴”的局面,张华功不可没。由于张华爱才、惜才、荐才,在他周围聚集了一大批文人。且有意识地培养人才,《世说新语·文学篇》注引《文章传》曰:“机善属文,司空张华见其文章,篇篇称善,犹讥其作文大治,谓之日:‘人之作文,患于才少,至子为文,乃患太多。’”[8](P1074)张华的文学观念和创作特点也影响到这群人,并通过这群人影响到太康文学。张华与他们一起促成了太康文学的繁荣。
二、注重文学的抒情性,完成了汉魏诗到晋诗的转变
中国古代文学历来重视政教内涵,自孔子以来形成的“诗骚”或曰“风雅”的政教传统在西晋已被弱化。西晋作家对于国家、民族、社会、时政似乎相当淡漠,他们没有建安士人的那种功业心与进取心,多关注自我价值和个体情感,使得文学的抒情性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宗白华说:“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9](P189)难怪乎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说:“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6](P287)从“言志”到“言情”是汉魏晋文学的发展趋势,张华则是这一过渡过程的关键人物,他承前启后,完成了汉魏诗到晋诗的转变。
晋以前的诗论主要强调“诗言志”,汉代虽然有人意识到了“情”在诗歌创作中的作用,如《毛诗序》就提出“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吟咏情性”,但同时又提出“发乎情,止乎礼义”,[10](P30)文人抒情时却又受“礼义”的约束,在“言志”上有所松动,但仍未放开。而魏晋文学则从诗教的束缚中彻底解脱出来,陆机顺应时代潮流,一反诗文创作传统,倡导“诗缘情”,这比“诗言志”更符合诗歌的本质特征。
陆机虽然提出了“诗缘情”这一重要命题,但西晋主情主义理论的发端和首创之功应归于张华。陆云在《与兄平原书》中云:“往日论文,先辞而后情,尚絜而不取悦泽。尝忆兄道,张公父子论文,实欲自得。今日便欲宗其言。”可见,陆机兄弟在文学创作上起初是主张“先辞后情”的,在采纳张华父子的意见后,才转而主张“先情后辞”。刘勰在《文心雕龙·定势》中如是评论:“夫情固先辞,势实须泽,可谓先迷后能从善矣。”[6](P531)张华的主情主义诗学思想是陆机“诗缘情”的先声,他的“先情后辞”的诗学观直接启发了陆机“缘情绮靡”的理论,从“诗言志”到“诗言情”的转变是由张华完成的。
张华的主情主义诗学思想充分体现在他的诗作中。《太康六年三月三日后园会诗》云:“于以表情,爰著斯诗。”《答何劭》云:“是用感嘉贶,写心出中诚。发篇虽温丽,无乃违其情。”他认为诗歌是用来“表情”的,要抒发内心的真实情感,“发篇虽温丽,无乃违其情”是其“先情后辞”主张的最好阐释,即“情”是文学创作的动因,是文学创作的内容;“辞”则是表现情感的媒介,是内容的载体。“表情”才是写诗的目的,“情”是中心,“辞”是为“情”服务的,所以辞藻的“温丽”应与诗中所抒之情是相互协调,不要重辞违情。张华还将情辞并重扩展为情文并重,他在《励志诗》中说:“体之以质,彪之以文。”指出情和文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二者不可偏废。这种思想“既是日后理论家注重‘情文’关系的起点,又为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1](P22)陆机把“缘情”与文采的“绮靡”并列,强调其联系,“但不及张华的阐述有辩证性与倾向性。沈约《宋书·谢灵运传》称‘以情纬文,以文被质’,在理论上分清‘情文’二者的主次,并提出其间的辩证关系,这是张华理论的进一步发展”。[11](P23)
张华的诗作情思细腻深婉,多写日常琐细的生活,抒发人间常情,包括恋情、柔情、离情、哀情等,笔触细腻,抒写真切。钟嵘云:“其源出于王粲,其体华艳,兴托多奇,巧用文字,务为妍冶,虽名高曩代,而疏亮之士,犹恨其儿女情多,风云气少。”[7](P122)这主要体现在他的五言诗中,如《情诗》《感婚诗》《杂诗》等。因受《诗品》的影响,20世纪以前对张华的诗作评价一直不高,张溥曰:“壮武文章,赋最苍凉,文次之,诗又次之。”[12](P142)沈德潜云:“茂先诗,《诗品》谓其儿女情多,风云气少,此亦不尽然。总之笔力不高,少凌空矫捷之致。”[13](P126)20世纪以来,对张华诗作的评价有所改观,游国恩先生的《中国文学史》称:“张华的《情诗》艺术性较高”,“写情真实动人,表现也较朴实,没有繁缛的堆砌毛病。”[14](P264)徐公持先生认为:张华的诗“是在效法张衡《同声歌》、繁钦《定情诗》等,非直接写男女情爱,而是有所兴托。”[1](P275)显然,徐公持先生的认识更进一步,指出了张华的诗模拟张衡、繁钦,而且其诗有所兴托。魏晋时期的作家大都有模拟创作的经历,至于徐先生所说的“兴托”,这是完全有可能的,与屈原的《离骚》一样,《情诗》是张华受到打压后郁闷心情的外现。
《文心雕龙·明诗》云:“茂先凝其清。”[6](P67)张华“情多”的诗歌主题取向影响了一个时代,重真情成了西晋诗歌的一个重要特点。自张华倡导诗歌的抒情性以来,文学的抒情性受到空前重视,陆机、潘岳、左思、张载、张协、刘琨等人的诗都是重真情的,他们把各种各样的情感都抒写得淋漓尽致。如陆机悲情作品,“人生何所促,忽如朝露凝,辛苦百年间,戚戚如履冰”(《驾言出北阙行》),“人生诚行迈,容华随年落”(《君子有所思行》),“天道有迁易,人理无常全”(《塘上行》),“虎啸深谷底,鸡鸣高树巅。哀风中夜流,孤兽更我前。悲情触物感,沈思郁缠绵。伫立望故乡,顾影凄自怜。”“夕息抱影寐,朝徂衔思往。顿辔倚嵩岩,侧听悲风响。清露坠素辉,明月一何朗。抚枕不能寐,振衣独长想。”(《赴洛道中作诗二首》)抒发了他的生命之叹、命运之忧、羁旅之愁、乡思之苦。潘岳的《悼亡诗》、左思的《咏史》、张载的《七哀诗》等都是写亲情和抒发忧愤之情的代表作品。
三、关注诗文创作中词句的雕琢和华丽,开启了西晋繁缛绮靡的主流文风
西晋统治者在文化领域内采取了比较宽松的政策,学术自由发展,文士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写作,尽情地披露各自对人生的理解、志向和欲望,诗文多崇尚绮丽,崇尚繁缛,炫耀词采。[1](P246)刘勰《文心雕龙·明诗》云:“晋世群才,稍入轻绮,张潘左陆,比肩诗衢,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略也。”[6](P67)魏晋以前的作家创作时注重作品的内容,建安以后,文士有意识地追求语言的艺术。晋初的宽松政策使文士逐渐淡化了文学的教化功能,转而关注其内心情感,追求词句的雕琢和华丽,形成繁缛绮靡的一代文风。张华是西晋最早崇尚繁缛、推重技巧风气的文人,具有开拓之功。
刘勰在《文心雕龙·事类》中说:“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明理引乎成辞,徵义举乎人事,乃圣贤之鸿谟,经籍之通矩也。”[6](P614)张华是晋初重要的诗人,他的《励志诗》《晋凯歌》《游猎篇》《游侠篇》《轻薄篇》用典颇为繁多。在《励志诗》中,涉及的古代典籍有十几种,这些典籍不是简单地堆砌罗列,而是适当化为己用。张华之后,此风大盛,陆机、左思在诗歌中普遍用典,南朝自颜延之开始,用典更成为时代风尚。
刘勰《文心雕龙·丽辞》载:“至魏晋群才,析句弥密,联字合趣,剖毫析厘。然契机者入巧,浮假者无功。”[6](P588)张华十分重视对偶艺术,他的诗文中许多句子对仗工整,丽辞与情韵结合运用得也很好。如“语昔有故悲,论今无新喜”(《门有车马客行》),“北里献奇舞,大陵奏名歌”(《轻薄篇》),“巢居知风寒,穴处识阴雨”(《情诗》),“微风摇茝若,层波动芰荷”(《杂诗》),“高飞抚凤翼,轻举攀龙鳞”(《上巳篇》),“窈窕初茂,玉质始盛。容华外丰,心神内正”(《感婚赋》),“金刚玉润,水洁冰清……志邈留侯,心迈二疏”(《魏刘骠骑诔》),等等。其精工已不减唐人,后人对此多加赞赏,明人谢榛在《四溟诗话》中说:“张华曰‘洪钧陶万类,大块禀群生。’……以上虽为律句,全篇高古,及灵运古律相半,至谢脁全为律矣。”[15](P1151)徐公持在《魏晋文学史》中称赞其《封禅议》:“作为骈文,写得纯熟,对偶运用,颇为流畅,功力不浅。”[1](P279)
当然,张华的丽辞偶句也未必全是这样,明人许学夷曰:“张茂先五言,得风人之致,题曰《杂诗》《情诗》,体固应尔。或疑其调弱,非也。观其《答何劭》二作,其调自别也。但格意终少变化,故昭明不多录尔。”又“茂先五言,似对非对,中以渐入俳偶,至如‘居欢惜夜促,在感怨宵长。’‘道长苦智短,责重困才轻。’则伤于拙矣。”[16](P93)有的可作适当调整,宋人范晞文《对床夜语》说:“张茂先:‘穆如洒清风,涣若春华敷。’又:‘属耳听莺鸣,流目玩鯈鱼。’以对言之,则当曰‘清风洒’、‘听鸣莺’也。”[15](P409)有的是为对偶而对偶,将一句拆成两句说,不免牵强,流露出雕琢的痕迹。如刘勰在《文心雕龙·丽辞》中有言:“张华诗称‘游雁比翼翔,归鸿知接翮’;刘琨诗言‘宣尼悲获麟,西狩泣孔丘’:若斯重出,即对句之骈枝也。”[6](P589)明显看出张华的诗文在对偶上的雕琢重复。有研究者指出:“作为较早关注对偶之人,张华诗中出现此类瑕疵在所难免,然这并不妨碍其对句艺术的指示。张华诗歌创作中偶句的增多,反映出此时诗人对诗歌外在形式美的追求,已经成为他们诗歌创作的自觉活动。”[17](P90)由于张华的努力探索和带动,到太康时期,丽辞骈偶成为作家们的自觉追求,陆机、潘岳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尤其是陆机。清叶矫然《龙性堂诗话初集》中云:“六朝排偶,始于士衡。”[18](P956)六朝诗歌排偶张华已开启之,然其诗句对仗之精密华美则是始自陆机,如:“清川含藻景,高岸被华丹”(《日出东南隅行》),“幽兰盈通谷,长秀被高岑”(《悲哉行》),“灼灼桃悦色,飞飞燕弄声”(《壮哉行》),再如其《悲哉行》《猛虎行》《齐讴行》等诗歌,几乎全篇用偶。沈德潜《古诗源》评价陆机时称:“遂开出排偶一家,西京以来,空灵矫健之气不复存矣。”[13](P133)这一风气至南朝日盛。
张华的诗歌创作讲究文辞藻丽,虽未达到“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程度,但其用心经营随处可见。如其《游猎篇》与曹植《名都篇》均写游猎,但《游猎篇》显得精巧华丽。讲究藻饰的结果,势必导致雕琢词句、洗练文辞。王夫之《古诗评选》云:“张公始为清俊以洒子建、仲宣之朴涩,矫枉过正,而导齐梁卞佻。”[19](P168)又说:“茂先处三国之余,托体华亮,前不欲为陈王之烦重,后不肯同孙楚、夏侯湛之卤莽,乃欲开宋齐之先,作唐人之祖,风会所趋,盖自是而一变。”[19](P167)说明张华在魏晋诗坛上有承前启后的作用。
许学夷在《诗源辩体》中谓:“茂先如……‘佳人处遐远,兰室无容光’,‘巢居知风寒,穴处识阴雨。不曾远别离,安知慕俦侣’等句,其情甚丽。”[16](P94)清人何义门谓:“张公诗惟此《励志》一篇,余皆女郎诗也。”[20](P888)此评就《情诗》感情之绮丽而言,实不为过。曹旭把张华的诗风特征概括为“清丽靡嫚,兴托多奇”。[21]他们都看到了张华诗作繁缛绮靡的一面,张华的诗风对后来的鲍照、谢瞻有直接影响。繁缛绮靡表面上追求文学作品语言华丽美好,其实质是对长期以来的“重文轻质”的反动,是对文学的形式美认识的深化。
综上所述,张华是西晋文坛“执牛耳者”,他长期位居枢要,在当时士大夫中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他是汉魏诗到晋诗转变过程中的关键人物,在诗歌史上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他是西晋尚繁缛、重技巧风气的第一位代表,在文学创作方面有开拓之功。他的绮丽文风为西晋主流文风的形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对西晋文学乃至南朝文学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