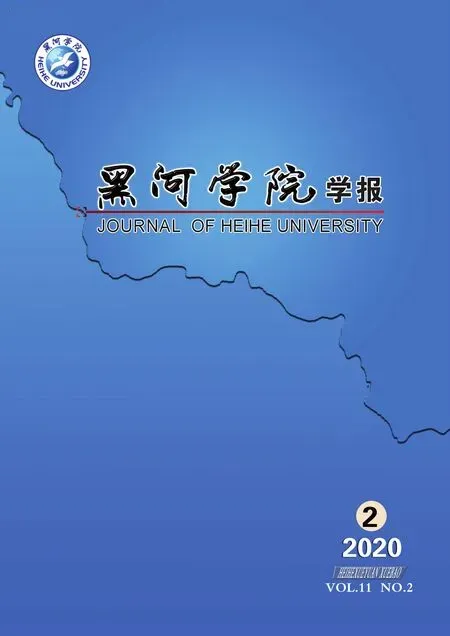近十年《大唐三藏圣教序》研究综述
2020-01-18陈可凡吴晓涵
陈可凡 吴晓涵
(1.河北大学 历史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0;2. 湖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2)
《大唐三藏圣教序》(以下简称《序》)是贞观廿二年,唐太宗应玄奘法师请求,为其所翻译的佛经所作的总序,皇太子李治又亲自撰写了《皇太子臣治述圣记》(以下简称《记》)。《序》和《记》留存于世主要有石刻本的《怀仁集王圣教序》、褚遂良的《雁塔圣教序》和《同州圣教序》,还有王行满书写的《招提寺圣教序》,纸本主要有《怀仁集王圣教序》的宋拓本和敦煌文书中的唐代“御制经序”。学界对《大唐三藏圣教序》及相关内容的研究已有不少成果,也已有学者做了相关的叙述,因此,本文主要对2009年以来近十年的研究进行介绍。
一、关于《序》和《记》
这里所说的《序》和《记》的研究主要指的是《序》与《记》的写作始末及《序》《记》对唐代佛教发展的影响两个方面。
1.《序》和《记》的写就始末
卢芳玉《大唐三藏圣教序考》对《序》和《记》的写就始末进行了系统梳理。文中借《大唐三藏玄奘法师表启》和《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对唐太宗与玄奘法师的书函往来的记载,指出《瑜伽师地论》的译成,是太宗对玄奘所求“写序”一事态度转变的关键[1]。而郝松枝《〈大唐三藏圣教序〉与唐代佛教的兴盛》则持不同意见[2]。郝文认为,《序》和《记》的写成,尤其是太宗《序》的写成有另一段曲折的经历,涉及佛教兴衰部分内容的下文将谈到,此不赘述。郝文认为玄奘为求得太宗为其新译佛经做序,多次上表太宗,第一次上表被太宗以“学浅心拙,在物犹迷”为理由拒绝后,又再次向太宗上表,并在表文中叙述了自己被拒绝后的失意与彷徨。在经过多次努力后才最终感动太宗,如愿得到《序》文。两文中对《序》和《记》的写就原因所作的解释虽不冲突,各有侧重,但皆不甚清晰,各有逻辑不通的地方。罗丰《王字传统的构建与流行:关于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碑〉的再讨论》也对玄奘法师的“求序”做了详细论述并指出最后是由于长孙无忌和褚遂良等人的斡旋才使得太宗答应赐序[3]。
2.《序》和《记》对唐代佛教的影响
此方面的研究目前仅有上文提到的郝松枝一文做了讨论。郝松枝认为,唐代素有抑佛崇道的传统,玄奘西行尚且得不到太宗的支持,但玄奘却有心通过西行求经来振兴唐朝的佛教,并为满足太宗对西域的好奇心,在翻译佛经的同时,夜以继日地完成了《大唐西域记》,附以求《序》的表文上呈给太宗。从这里可以看出《序》和《记》的写成,对唐朝佛教来说称得上是起死回生的一剂良药[2]。
二、褚遂良的《雁塔圣教序》
《雁塔圣教序》由褚遂良正书,万文韶刻书,是《大唐三藏圣教序》最早的石刻本。今立于西安慈恩寺雁塔南门前,左为太宗撰《大唐三藏圣教序》,右为高宗撰《大唐三藏圣教序记》(即前文《皇太子臣治述圣记》)。两石皆刻于永徽四年,《序》比《记》稍早。
1.书法技艺及其内涵
朱友舟的《字里金生,行间玉润——褚遂良〈雁塔圣教序〉解析》共四篇文章,按字形结构分类对《雁塔圣教序》的结字特点进行解析[4]。李梦媛《婉媚遒逸 貌如婵娟——褚遂良〈雁塔圣教序〉书法欣赏》则从《雁塔圣教序》在唐楷中的地位及各代书家对其评价出发,综合论述了《雁塔圣教序》的书法艺术特点[5]。闵健《浅析褚遂良〈雁塔圣教序〉碑的线条及点画的韵味》从碑刻中褚字的线条和点画赏析《雁塔圣教序》的书法韵味[6]。李鹏《褚遂良书法艺术的内涵解读》则从执笔法、运笔法和章法等方面解读了《雁塔圣教序》的艺术内涵[7]。
2.其他研究
路远《〈雁塔圣教序碑〉之褚遂良署衔何以不同》认为,褚遂良书《雁塔圣教序碑》的时间是高宗时期,在书《序》碑是用太宗时官衔、在书《记》碑时则用高宗时官衔是出于对两位皇帝分别称臣的意图。既满足了高宗新帝立威的需求,又不失对已故太宗皇帝的尊崇,恰到好处、入规入矩[8]。李梦媛《褚遂良〈雁塔圣教序〉补笔修正考》对《雁塔圣教序碑》中的补笔原因和补笔痕迹做了论述,认为褚遂良补笔是为了减少贞观年间首次书写的《序》中的行书笔意,让其成为具有更多庙堂气息的铭石书。而在碑上留下补笔痕迹则是为了体现对两代皇帝的纪念[9]。高喜锋《论褚遂良晚期书风的形成与道家“虚实相生”思想的关系——以〈雁塔圣教序〉的书法风格为代表》认为《雁塔圣教序》中褚字相较于欧字和虞字更多地表现了舒展与自然,是受到道家“虚实相生”“空灵”思想的影响[10]。
三、《怀仁集王圣教序》与《大唐三藏圣教序》敦煌写本
《怀仁集王圣教序》是唐咸亨三年(672年)由弘福寺僧释怀仁集王羲之书而成。碑成,出立于长安修德坊弘福寺,北宋始被移至西安碑林。碑文除了太宗的《圣教序》、高宗的《述圣记》、皇帝答敕、太子笺答外,还有玄奘所翻译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以及润经的大臣姓名和官职。
1.《怀仁集王圣教序》综合研究
罗丰《王字传统的构建与流行:关于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碑〉的再讨论》从碑石的构造形式、碑石的制作和流传过程、文本产生的背景、怀仁集字所带来的影响和《集王圣教序碑》所代表的王字传统的确立五个方面详细论述了《怀仁集王圣教序》的相关内容,观点引人深思,可读性极高[3]。
另外,较全面的综合性研究还有以下两篇硕士学位论文。陈翰婴《〈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研究与我的创作》系统介绍了初唐的书风、刊刻过程、传世拓本、集王字碑,以及集字来源和集字标准[11]。董存建《〈集字圣教序〉研究》则先是系统梳理了《怀仁集王圣教序》的国内外相关研究情况,再系统分述了《集字圣教序》的刊刻、版本考证、历代对《怀仁集王圣教序》的研究和师法,最后论述了集字来源[12]。在集字来源部分,董文比《〈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研究与我的创作》一文更多关注到了除《兰亭序》以外的集字来源,如“王书刻帖”。
2.《怀仁集王圣教序》书法艺术研究
黄明海、邱志文《论对比手法在书法结构中的运用——以〈集王羲之圣教序〉为例》以《怀仁集王圣教序》为例,讨论了线的位置、线的方向、线的长度和线的形状四个方面对书法结构中对比手法的应用[13]。周治锐的硕士学位论文《王羲之书法艺术单字空间造型的研究》从《怀仁集王圣教序》的单字空间造型入手,论述了“王字”点画造型、结字造型、字内空间布白及笔法等方面的特点,进而阐述了行书标准化对后世的影响[14]。
3.宋拓本《怀仁集王圣教序》
王湛《北宋拓〈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赏析》介绍了现存《怀仁集王圣教序》宋拓本的各种版本和其中的精拓本,并详细阐述了国家博物馆藏宝熙、沈乙盦(一说为沈盦)跋本的递藏历史,考释了其钤印者和审定者,说明了其损益情况和考据价值[15]。王湛另一文《国博藏北宋拓〈集王圣教序〉》通过介绍《怀仁集王圣教序》北宋拓本的考据上的依据,阐述了分辨《集序》北宋拓本与南宋拓本的方法并系统介绍了国家博物馆藏王际华跋本[16]。仲威《〈集王羲之书三藏圣教序〉北宋拓本两种》详细介绍了《怀仁集王圣教序》传世的北宋善拓两种:国家博物馆藏本和上海图书馆藏本。考据了上述两种拓本的递藏历史等内容,并阐释了分辨《集序》南宋拓本和明清拓本的方法[17]。冯小夏《〈怀仁集王之书圣教序碑〉及其早期拓本研究》通过七种北宋拓本的对比研究,认为前人提出的个别拓本考据未必具有普遍适用性。同时,拓本研究对石刻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18]。冯小夏《〈怀仁集王圣教序碑〉与故宫藏北宋拓本一种》整理了北宋拓本共二十七种[19]。
4.《怀仁集王圣教序》的其他研究
张天茹《〈集王圣教序〉在宋代兴盛的原因初探》认为宋代重文轻武的国策、对唐代书风的继承和书家的推崇是《怀仁集王圣教序》在宋代兴盛的三个主要因素[20]。郁建伟《书法集字现象研究》通过集字分类、唐宋集王行书整理和对比、清代碑帖集联的兴起三个方面对由《怀仁集王圣教序》所开创的集字现象做了系统的论述[21]。王玉池《现存〈唐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碑〉为复刻等问题》质疑《怀仁集王圣教序碑》的真实性,认为其并非怀仁集字的原作,而是唐代翻刻的作品。但这只是一些学者的观点,限于小范围的探讨,不能成定论[22]。张东华《以〈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论证〈兰亭序〉真伪》先是整理出《兰亭序》比《临河叙》多出来的字,再将这些字与《怀仁集王圣教序》中的字进行对比,论证了《兰亭序》的文本的真实性[23]。
5.《大唐三藏圣教序》敦煌写本
马德《敦煌本唐代“御制经序”浅议》根据敦煌写本所载玄奘译《能断金刚经》的版本性质,认为敦煌本P.2323是《大唐三藏圣教序》和《皇太子臣治述圣记》敦煌写本中时间较早的,但其绝对年代应不早于褚遂良《雁塔圣教序》写本[24]。
四、结语
近十年关于《大唐三藏圣教序》的相关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学者们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不断提出补充和修正,对《大唐三藏圣教序》和《皇太子臣治述圣记》及相关研究做了大量的工作。其研究具有以下特点:(1)研究侧重于对《雁塔圣教序碑》和《怀仁集王圣教序碑》书法艺术的阐发;(2)《怀仁集王圣教序》的拓本研究较全面且以宋拓本为主;(3)研究具有继承性和创新性。但是,已有的研究仍相对集中在一些热门领域,对如《怀仁集王圣教序碑》的明清拓本和《雁塔圣教序碑》的拓本研究较少。再有,对于敦煌写本的研究也没有形成系统。但可喜的是,关于《大唐三藏圣教序》的研究现已形成较完整的体系和范式,并为进一步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