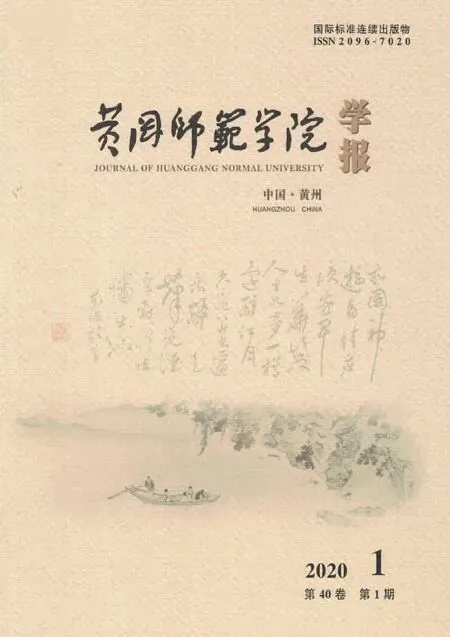闻一多:中国20世纪的全能型诗歌大师
2020-01-18万龙生
万龙生
(重庆市诗词学会格律体新诗研究院,重庆 400012)
今年是闻一多诞生120周年,理当对他进行隆重的纪念。对闻一多的研究,自他1946年牺牲之后已经持续70余年,迄今未曾中断,可谓显学。就在他牺牲一年之后,就出版了他的两本传记①。1948年8月,朱自清、郭沫若、吴晗、叶圣陶合编的四册本《闻一多全集》就由开明书店出版了(1982年8月,由三联书店再版)。1993年12月,经过艰苦的努力,篇幅数倍于此的新版《闻一多全集》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历来所出闻一多著作的各种选本、专著以至各种研究闻一多的学术论著、论文可谓数不胜数。
尽管林林总总,令人目不暇接,目前学界对闻一多的定评不外诗人、学者、斗士(烈士)三个身份的总和,当然应该说这能准确概括他短暂而伟大的一生。不过我认为三者之中应该突出一个诗字,因为作为学者,诗也是闻一多研究的主要内容。即以诗人论,过去因为政治的原因,更多地突出闻一多“爱国诗人”的桂冠,忽略了他在诗歌其他方面重要的、不可忽视的建树。尤其是有一段时间,对闻一多是新月派主将,甚至灵魂一事讳莫如深。有一个显例,就是闻一多的学生、大诗人臧克家也是如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臧克家努力撇清与新月派的关系,与此同时也将自己的老师闻一多从新月派中摘出来,只突出他‘爱国诗人’的政治一面。”②而郭沫若更把闻一多视为堪与屈原并称的“人民诗人”③
而在事实上,考闻氏著述,可以看出,他在诗歌的创作、评论、理论、研究、编选、诗歌活动以至外国诗歌翻译方面都有不容忽视的贡献,范围涉及古今中外。他是怎样的诗人,该如何定位,远非“爱国”、“人民”的定语所能涵盖。本文的意图就是要对闻一多毕生从事诗歌事业的丰功伟绩进行全面的认定,以确立他中国20世纪罕有其匹的全方位、全能型诗歌大师之地位。这无疑是一个意义重大的课题,需要一本专著甚至分门别类的总集才能完成。我只能抛砖引玉,分别提及。希望这一观点得到认同,引起关注,至于进一步的充实与深化,就俟诸来日吧。
一、各体皆擅的诗人
(一)自20世纪之初中国新诗诞生以来,发展至今,整个诗坛存在着三种诗体。一是旧体诗词(今称“中华诗词”)。虽然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曾是横扫对象,但是中华诗词以其顽强生命力不绝如缕地存活,于1980年代开始出现的复兴之势延至今日。李遇春《中国当代旧体诗词论稿》一书④对当代诗词创作进行了详细研究,在深度的鉴赏分析中肯定了当代旧体诗词的存在价值。据《中国文化报》今年(2019年)3月26日报道,中华文化学院(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和《诗刊》杂志社3月23日在北京联合举办了“中华诗词复兴论坛”。
二是新诗中的自由体诗。因为以现代汉语为载体的新诗没有现成的格律可资利用,大多诗人遂采用自西方引进的自由诗。这是整个20世纪中国诗坛的占主流地位的诗体,无须赘言。
三是新诗中的格律体诗⑤。一部分诗界有识之士并不甘愿汉语诗歌长期被自由诗独占,从1920年代就借鉴中外诗歌经验,开始了创建新诗格律的艰苦卓绝的努力,而且已经取得成果。闻一多正是这部分诗人的代表性人物。
(二)以上三种诗体,闻一多都曾写过,并且成绩不菲。这样的诗人是不可多见的。蓝棣之所编《闻一多诗全编》⑥所收比较齐备,就以此为准来进行考察吧。
1.先说诗词。《全编》称为《旧体诗赋》(301-300页),含4篇赋体作品,共计23首(篇),其中大多在《清华学报》发表过。这些1916-1925年十年间的作品应为闻一多20岁前后所写。本文不想对这些作品做过多的分析,因为在闻一多整个创作中诗词的确占不了多大份量。只需指出两点:一是由此可见闻氏古典文学根底之固,功夫之深,这是他一生诗歌事业的坚实基础。二是其中1925年他在从美国归来前夕寄给梁实秋的两首诗最值得重视:“六载观摩傍九夷,吟成鴂舌总堪疑。唐贤读破三千纸,勒马回缰作旧诗。” (《废旧诗六年矣,复理铅椠,纪以绝句》);“艺国前程正渺茫,新陈代谢费扶将。城中戴髻高一尺,殿上垂裳有二王。求福岂堪争弃马,补牢端可救亡羊。神州不乏他山石,李杜光芒万丈长。” (《释疑》)
这两首旧诗曾引起我的注意,写过《新诗格律建设的理性思考》一文予以解读⑦。其摘要曰:“解读这些诗作,对于研究一多先生新诗创作从《红烛》到《死水》的发展,亦即从当时流行的自由体到格律体的转变,对于了解他的以建立新诗格律为中心和旨归的崭新诗学理论,以至于今天研究新诗现状、思考新诗发展,都具有及其重要的作用。”经过对诞生几年的新诗的观察,闻一多已经认识到盲目崇外、背弃传统不可取,必须纠偏救弊,寻求新路。从后来的创作实践看来,他“勒马回缰作旧诗”只是一时兴起,此后再没有染指旧诗,而是决心从无到有,创建新诗格律,走出一条新诗格律建设的新路来。这就是从《红烛》到《死水》形式巨变的动因。
不过,无心插柳柳成荫。“勒马回缰作旧诗”这句诗成为对新文学运动中一个普遍现象的准确而生动的描述。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新诗的确存在的弱点。这一事实充分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以此为题写出了许多论文⑧。现代诗人、作家回头写旧诗的现象,有这么一个警句足以概括,能够流传,也是闻氏之功。
2.次言自由诗。闻一多的自由诗无疑应该以《红烛》为代表。诗家历来对《红烛》评价很高。诗人对自己的创作有严格的要求、自觉的追求。他从批评俞平伯的《草儿》的散漫与《女神》地方性的缺失吸取教训(见下文所谈诗歌评论),又能吸取中国古典诗歌的优点,所以蓝棣之这种评价,我以为是中肯的:“比起当时的白话诗,既意象、境界具体,又富于想象与暗示”,难能可贵⑨。此外,沈用大指出:“翻开《红烛》,迎面扑来的是一种古色古香的气氛,大量运用古典词汇,丰赡又华丽。”其中之佳者“造成一种秀丽的风格,观察入微,构思纤巧”。他转引苏雪林的话说:“闻氏似乎有一个东方的灵魂”,不像别人那样盲目地崇拜欧美的物质文明,因而呈现出许多东方特有的美感⑩。序诗《红烛》的结尾“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已经被人们习称“红烛精神”,常常引用,应该说这是诗人的光荣。诗集最后的组诗《红烛》情真意挚,则是“五四”后新诗中爱情诗的精品。
3.再谈格律体新诗(今名,即按照一定规范写作的新诗。下同)。闻一多意识到创建新诗格律的必要性之后,就在创作中进行探索。《死水》就是这种探索的宝贵成果。2016年闻一多国际学术研讨会我因故缺席,但是论文集收入了我提供的论文《格律体新诗之父》,对闻一多的创作做了高度评价,意谓闻一多在以《死水》为主的后期作品中实践自己关于“创格”的理念,取得了显著的成功。其中有一些堪称经典,垂范后世。一是实现了“句的均齐”,就是一首诗中每行字数、音尺(今称“音步”)都做到一致,而不是为人所讥诮的仅求字数一致而内部节奏紊乱的“豆腐干”,例诗有《死水》《夜歌》《也许》《黄昏》《口供》等。二是实现了“节的对称”,就是诗中各节外形一样,如词的上下阕对称的作品,包括《你莫怨我》《忘掉她》《什么梦》《一句话》等。而《洗衣歌》则是中间6节对称,首尾两节重复,显得更加繁复。这还是仅就形式而言,至于艺术上达到的高度也是新诗历史上的标杆之作。因为这些格律体新诗在新诗史上有开创之功,在艺术是也很成熟,在闻一多三种诗体的作品中,当然是最重要的。
综上所述,说闻一多是20世纪一位三体皆擅的诗人,应无疑义。而这样的诗人若舍闻氏,终其20世纪在中国也难寻难觅。
二、仅仅作为诗人的历史定位
以上主要从诗人所掌握的诗体而言,虽然重要,却仅仅是一个方面。那么,倘若对其作品进行综合考量,闻一多作为诗人,在中国20世纪诗坛该如何定位呢?
江锡铨在《建国前闻一多研究述评》中引用了沈从文《论闻一多的<死水>》一文,沈说:闻一多在“重新为中国建立一种新诗完整风格的成就处,实较之国内任何诗人皆多”,《死水》“是近年来一本标准诗歌!在体裁方面,在文学方面,《死水》的影响,不是读者,当是作者。”这是放在诗歌史中与其他诗人相比较而论,突出闻一多的卓越贡献,我以为并非夸饰之语。
至于“爱国诗人”身份,当然也是题中应有之义。这得听听朱自清的意见,他是公认的关于新诗第一个十年的权威发言人。1935年由赵家璧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八·诗集》就是由朱自清编选的。他为之撰写的《导言》历来被视为新诗第一个十年的科学总结。他对闻一多的论述十分精辟:“他的诗不失为情诗。另一方面他又是个爱国诗人,而且几乎可以说是唯一的爱国诗人。”这里“情诗”当解作“抒情诗”,下面一句“唯一”似乎有些费解。这跟上文说闻一多“喜欢用别的新诗人用不到的中国典故,最为繁丽”有关吧?我理解,除了他有许多人们耳熟能详的爱国名篇,如《我是中国人》《忆菊》《口供》《洗衣歌》《祈祷》《一句话》《太阳吟》《长城下之哀歌》等等以及20年前唱响神州的《七子之歌》,我想还因为他的作品常用中国典故,充满浓烈的东方色彩吧。这“唯一”二字并不是随便加的,在爱国这一点上,闻一多的确是无与伦比的!
闻一多还有一顶“诗圣”的桂冠,当然比“爱国诗人”份量更重,却不如“爱国诗人”那么广为人知。中国现当代诗人中除闻一多之外,谁有过这样的美誉呢?没有。谁又配得上这个美誉呢?也没有。此说最初见于司马长风《中国文学史》,他以一整章的篇幅给闻一多和徐志摩分别加冕“诗圣”和“诗仙”。此说诗评家吕进认同了前半,他与周婷合写了《闻一多:新诗史上的杜甫》一文,指出他“怀抱祖国,热爱草根,珍视传统,是朱自清称赞的‘唯一的爱国诗人’”,“致君尧舜上”的杜甫,与“心里有尧舜的心”的闻一多,他们是何等相似。而在诗歌艺术上,“杜甫律诗杰出的艺术成就,是唐诗成熟的一个标志”;而闻一多“现代格律诗的理论与实践为新诗的发展开拓了新的局面”。也就是说,闻一多在中国新诗史的地位可以与杜甫在唐诗史上的地位相当,于是雄辩地得出结论:闻一多是“新诗史上的杜甫”。我认为此言不虚,完全可以成立。
还有一个“人民诗人”的头衔,这是郭沫若在开明版《闻一多全集·序言》中加上的。因为闻一多曾说“屈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有充分条件称为人民诗人的人”,鉴于闻一多也具备的各种条件,他便得出结论:因为有了闻一多,那“唯一”两个字可以取消了。
如此看来,作为一个20世纪中国的杰出诗人,闻一多在诗歌史上的崇高地位是稳如泰山,不可企及,不可动摇的。
三、目光如炬的诗评家
创作与评论,被视为驱动文学之车前进的双轮,诗歌的发展当然也不能离开评论。在中外诗歌史上,诗人在评论上也有很大建树的并不很多。闻一多却是一开始就双管齐下,创评兼顾,二者皆擅。他不仅跻身于最早出现的新诗人之列,也是最早、最重要的诗评家。
评论的及时性非常重要,意义重大,不用说也有很大难度。《女神》出版于1921年,闻一多为郭沫若《女神》所做的两篇论文,《女神之地方色彩》发表于1922年,《女神之时代精神》发表于1923年。俞平伯的《冬夜》出版于1922年3月,当年11月《冬夜评论》就出版了。20年后,他对艾青和田间的著名评论更可以说是即时的。这些都是至今不失其光辉的诗评典范。
评论必须实话实说,捏拿得当,见解独特,鞭辟入里,不仅对所评作者有启发,其他同行阅后也会得到启发,有所收获。当然也将有助于读者。
《冬夜评论》洋洋万余言,与梁实秋的《草儿评论》合集出版后,郭沫若读后十分膺服,当即写信给闻说:“如在沉黑的夜里得见两颗明星,如在蒸热的炎天得饮两杯清水……在海外得读两君评论,如逃荒者得到闻人足音跫然。”闻一多对《冬夜》亦褒亦贬,采取的是科学的态度。他说在肯定俞平伯音节方面的优点的同时,还以大量的引诗为依据,相当尖锐地批评了《冬夜》中一些“幼稚”、“枯燥”的篇什,指出其抽象、琐碎、累赘的缺失。
对新诗史上不朽之作的《女神》,闻一多的两篇批评至今闪耀着真理的光彩,不失为诗歌评论的典范。他开宗明义就充分、热情地称赞《女神》的动感与反抗精神“完全是时代的精神——20世纪的时代的精神”,作者“不愧为时代的一个肖子”,“喊出了人人心中最神圣的一种热情”,并以大量的诗例予以证实。
不仅止于这样的赞美,闻一多还从另一级角度指出了《女神》地方色彩的不足,并且借此得出一个至今也没有过时、具有指导意义的精辟论断:“新诗迳直是‘新’的,不但新于中国固有的诗,而且新于西方固有的诗……她要做中西艺术结婚后产生的宁馨儿。我以为诗同一切的艺术应是时代的经线同地方纬线所编织成的一匹锦。”正是从这个出发点,道出了对他引为同调的郭沫若的力作的中肯意见,既肯定郭沫若的爱国情绪,又指明他对祖国的文化缺乏理智上的尊重。二者就是地方色彩不足的根源。
闻一多的一些序文,如1933年的《<烙印>序》,1939年的《<西南采风录>序》也是诗歌评论的精品。1943年,在他生命晚期所写《时代的鼓手——读田间的诗》又创造了为一个诗人“加冕”的范例,流传至今。
闻一多的诗学遗产中,诗歌评论的数量不算多,但是却奠定了他作为杰出诗评家的坚实基础。
四、独树一帜的理论家
如前所述,闻一多杰出的诗人、评论家之身份已经毋庸置疑。然而还有一个独特的理论家身份把二者紧紧粘合在一起。
闻一多的诗歌理论前后是有变化有发展的。但是我以为,从无到有,创建、提倡新诗格律是他最重要的贡献。而一个理论家是不是杰出、优秀,就得考察他是不是有自己独树一帜的理论主张,这一主张是不是起到指导性作用,经不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如前所述,新诗前十年,就已经形成了新诗的格律派。而格律派的理论纲领就是闻一多的论文《诗的格律》。它是中国新诗发展史上的里程碑。虽然因为种种原因,近百年格律体新诗理论及创作在其进程中颇多坎坷,几经颠踬,却并未断绝,至今仍有长足发展。尽管目前未能在诗坛形成大气候,但是经过纠偏救弊,俟诸来日,我深信这种符合诗歌文体本质、向有悠久传统的诗体最终一定能够以其成功告慰一多的在天之灵。
闻一多的新诗格律理论历来经过充分解读,说“他是对旧诗实行‘破格’的新诗奏过十年探索之路后,对新诗实行‘破’后之‘破’的第一人”,“将新诗推入了第二纪元”并不过分。此后格律体新诗无论怎么发展,这里都是源头。
其核心内容,我在《格律体新诗之父》一文中归纳出以下五点:
一曰“格律必要”论。以艺术起源的“游戏”说来肯定格律之于的必要性。他进一步引用了BLiss Perry教授的话来予以证明:“差不多没有诗人承认他们真正给格律缚束住了。他们乐意戴着脚镣跳舞,并且乐意戴别个诗人的脚镣。”他还引用杜甫的经验之谈来证明这个“脚镣”说:“老来渐于诗律细。”后来此说却饱受酷爱“自由”的诗人们诟病:他们缺乏常识,显得无知,把“脚镣”这个喻体当做“格律”本体了。
二曰“格律利器”论。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这个用以作诗的“规矩”亦即工具就是格律。闻一多引用韩愈好用窄韵,而因难见巧,愈险愈奇的例子,进一步发挥说:“恐怕越有魄力的作家,越是要戴着脚镣跳舞才跳得痛快,跳得好。只有不会跳舞的才怪脚镣碍事。只有不会作诗的才感觉得格律的缚束。对于不会作诗的,格律是表现的障碍物;对于一个作家,格律便成了表现的利器。”
三曰“相体裁衣”说。闻一多曾经对律诗做过深入的研究,如今他要从事新诗格律建设,却认识到因为语言载体的变化,决不能重走律诗的老路。他把律诗的格律与他要创建得到新诗格律做了令人信服的比较,论定新诗的这种格式是创新,是进化,而不是相反。总之,律诗是无论什么人都穿同一样式的衣服,而新诗的格式却可以依据内容的需要千变万化。
四曰“音节调和”论。闻一多主张一首诗中,“整齐的字句是调和的音节必然产生出来的现象。绝对的调和音节,字句必然整齐。”
五是中国诗歌“建筑美”的发现。中国古典诗词不兴分行排列,建筑美是潜在的,但是新诗一经分行,汉语的单音象形文字这一独特之处便带来了排列组合的美感。除了“句的均齐”形成的建筑美外,还有一种“节的匀称”。后者是词的“格式”带来的,虽然单独一节看起来参差不齐,但是如同许多宋词的上下闕,节与节対称也具有美感。这样两种基本格式,就成为如今格律体新诗的两大类别。
以上五点是闻一多新诗格律理论的精华,也是此后格律体新诗理论发展的基础。影响深远,功莫大焉⑩。
建立新诗格律的必要性、可能性以及具体路径,后来经过几代学者、诗人艰苦卓绝的努力,已经进一步的解决,但是万变不离其宗,《诗的格律》的指引作用是不能忽视的。
五、对中国古典诗歌的潜心研究
郭沫若在开明版《闻一多全集·序言》中说:“闻一多的成就并不限于新诗创作和提倡新格律诗理论。他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和古代文化研究方面所取得的创造性重大成就,引起了学术界和思想界更为强烈而普遍的震动。”在湖北版《全集》中,有关中国古代诗歌的篇幅占了半壁江山,涉及诗史、诗经、楚辞、乐府、唐诗,其工作包括笺注、论述、编选,既通览博涉,又细致入微,汲取前人成果,尤多自己的创见,至今成为定论。如对于歌与诗关系的分析,屈原诗史上“唯一的人民诗人” 的定位等。其中,闻一多着力最多、功劳最著的是唐诗研究,我以为至今无出其右者。其中有许多真知灼见。例如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向前洗清了宫体诗百年的罪,向后和另一个顶峰陈子昂分工合作,清除了盛唐的路”的历史评价,对初唐王、杨、卢、骆“四杰”之间同与异的分析,都是不刊之论。对秩篇帙浩繁的整个唐代诗歌的研究包括校勘、笺释、补遗、诗选、诗人论、作品论、方法论、编年史诸多方面,对杜甫、岑参两位诗人更有详尽研究,涉及到他们的作品系年与人际交游。律诗是发展到唐代方才成熟的诗体,早在1922年闻一多就写了《律诗底研究》宏文,可以视为他唐诗研究的高起点。在列于篇首的一首七律中,他道出了自己研究的动因:“手假研诗方剖旧,眼光烛道故疑西。”他绝不是为研究而研究,而是志在高远,古为今用,有所扬弃。既“剖旧”又“疑西”,他要在中国古诗与西方诗歌之外为中国新诗另辟一条新路。后来他倡导格律体新诗就汲取了律诗“整齐”、“均齐”的优点,其中重要理论“量体裁衣”说又是对律诗“千篇一律”的矫正。
陈凝《闻一多传》详尽描写了闻一多抗战初期在昆明西南联大国文系任教期间专心致志耽于古典诗歌研究的生活状况:他因为“有耐心埋头在古书堆里”被同事们戏称 “何妨一下楼主人”呢。有人问这样做的理由,他答道:“抗战期间各人有各人的岗位。我是教国文的,除了同青年们一块儿讨论学问,自己课余不能不做点儿有计划的研究。我们能拿上枪杆去干吗呢?不能;我们能做政治工作么?没那种兴趣。”因此,他就在自己的斗室里,“一字一字地校正、诠释者楚辞、古乐府、唐诗……”这是些基础性工作,为后之来者提供了研究之便,功莫大焉。如今思之,我们能不为之动容,肃然起敬吗?
六、外国诗歌翻译与十四行诗的引进
闻一多在我国诗歌翻译与外国诗体引进方面的贡献也是不容忽略的。译诗在《闻一多诗全编》⑨中只有7个题目,含以五言古诗翻译的英国诗人阿诺德《渡飞矶》;而湖北版《全集》第1卷译诗则达13题(不含《渡飞矶》);《全集》中又多出一篇在清华读书时以歌行体翻译的阿诺德《点兵之歌》,老师评曰《悱恻动人》。再则,《全编》中《白朗宁夫人的情歌》只有10首,而《全集》中竟有21首之多。细查,方知《全编》中漏掉了1928年4月《新月》第1卷第2号续载的部分。
由此可知,闻一多翻译的外国诗歌虽然偏少,但是很早就开始了,而且与创作同步,说明他对此是重视并爱好的。我们还可以看出,他的译作在音韵节奏方面也十分讲究,是在以翻译践行自己的新诗格律理念。实际上他是在新诗翻译史上,与“新月”诗人们开“以格律译格律”之先河。仅举一例,且看郝斯曼《春斋兰》第一节:
春来了,走出来逛逛,
绕着那丛芜的陂陀,
你瞧,那洼地的近傍,
荆棘底下,一朵一朵,
不是莲馨花是什么?
全诗四节,每一节都是这样的模式,也就是而今格律体新诗“三分法”中的参差(对称)体。就连韵式也每节都是ABABB。
闻一多这样做是自觉的,熊辉指出:“闻一多意识到译诗的形式是对其诗歌形式观念的验证。”
外国诗歌汉译是与新诗的发展相辅相成的。卞之琳1981年发表于《读书》杂志的《译诗艺术的成年》是一篇带总结性的文章,提出了译诗的正确主张:不应把外国的格律诗译为中国的自由诗,起到误导作用;而应该以相应的格律翻译外国格律诗(像杨德豫所译《拜伦抒情诗七十首》和屠岸所译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那样)。在追述外国诗歌翻译历程时,他说:“有意识在中文里用相应的格律体译诗,既有既有实践也有理论的,较为人注意的,早期有闻一多、孙大雨。”这就肯定了闻一多先生的开创之功。
不止于此,闻一多还是在中国翻译十四行诗,进而引进这种世界性诗体的先行者,功不可没。正是他首先把十四行诗音译为“商籁”,介绍给中国读者。许霆《十四行体中国化论稿》指出:闻一多先是1928年3月在致饶梦侃信中使用此名,嗣后又有专文《谈商籁体》谈论十四行诗内部起承转合的结构原理,在《新月》杂志发表。他还“尽量保存原诗的格律”,翻译了英国白朗宁夫人十四行诗情诗21首,自己也创作了新诗史上第3首十四行诗《爱的风波》(改题为《风波》收入《红烛》)。据统计,他创作的十四行诗共有5首。
七、慧眼识珠的选家
编选作品历来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现象。优秀的选本成为文学的珍贵资源,便于存留、阅读、研究。《诗经》就是经过孔子筛选而留下的最古老文学作品。其后有《昭明文选》,使许多精品得以流传。清代孙洙编选的《唐诗三百首》更是家喻户晓,影响深远。而选本之优有赖选家的明鉴。新文学史上最著名的选本当属赵家璧主编,1935~1936年间由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0卷本。而单体作品功劳最大的选家则非闻一多莫属。他的两个诗歌选本都是泽被后世的鸿篇巨构。
开明版和湖北版《全集》都收入了他的《唐诗大系》。开明版仅收诗人64家,然而湖北版乃是以另一篇幅更大的《唐诗》选稿为主(仍名《唐诗大系》),包括256位唐代诗人、数以千计的作品。入选作品少的一人只选一首,而入选最多的杜甫则达99首之多。既突出重点,又照顾一般,显而易见,选家颇费权衡取舍之功。卷末还附有64人或详或略的小传,自然亦费考据之劳。
此外,两种《全集》都编入闻一多编选的《现代诗抄》。湖北版《全集》第1卷是作为附录编入的,并做了如下说明:“《现代诗抄》是闻一多先生在40年代中期编辑的一部中国现代新诗选集,先生生前似未最后编定。”这次没有从开明版照搬,而是“根据先生编选的手稿整理的”,未做任何更动。所选诗作之前列有《新诗过眼录》,主要是入选诗人所出版的诗集,以及三种选集、两种诗刊。还有《待访录》,列入当时闻一多手头没有掌握的书目、刊名。自“五四”文学革命开始,下迄终选之时,共选诗人65家,作品180余首。有的诗人缺席,也许属于战时资料缺乏,诗集“待访”吧。因此之故,不能不留下一些遗憾。但一部未竟之作,毕竟不能苛求。就凭已刊之稿,也可知闻一多用功之勤,涉猎之广,治学之严。这也是他留下的一笔珍贵遗产。入选诗人属于各种风格、流派,可见闻一多并无任何偏见;一些当时崭露头角的青年诗人也能得到闻一多的青睐,足见其眼光之锐敏。一个显例是那时的联大学生、青年诗人穆旦入选作品居然达11首之多。总之,倘要认识前20年的中国新诗,这部《现代诗选》是不能不读的。
根据以上各方面简略的分析,要认定闻一多是中国20世纪罕有其匹的全方位、全能型诗歌大师,已经顺理成章,水到渠成了。我还想简单补充这些事实:闻一多是一位卓有成效的诗歌教育家(上文提到,他就是这样认定自己的岗位,不过说成是“教国文的”),他有许多成才的弟子(例如众所周知的臧克家);他是诗歌组织(如西南联大的南湖诗社)的支持者;也是诗歌活动的指导者(例如从长沙跋涉到昆明途中指导学生的采风活动);还是一个诗歌朗诵者。这些方面比起以上那些重大贡献,似乎微不足道,却可以进一步让我们领悟闻一多一生与诗有着多么密切的关系,诗在他的生活中占有怎样的地位。
可以说,闻一多就是为诗而生,也是为诗而活。他为诗死而后已,诗使他获得永生。当前,中国诗坛的状况并不能令人满意,我想对一多先生最好的纪念,就是要继承他的诗歌遗产,秉承他的诗学理念,完成当代汉诗的格律建设,写下格律体新诗的辉煌诗篇!
注释:
①史靖:《闻一多的道路》,1947年上海生活书店出版;陈凝:《闻一多传》,1947年8月重庆民享书店出版。
②白杰:《<新月诗选>与<新月派诗选>的“历史对话”》,《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年第9期,171页。
③郭沫若:开明版《闻一多全集·序》。闻一多曾曾称屈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有充分条件成为人民诗人的人”,郭沫若本此将闻一多与屈原相提并论,而认为上面引文中的“唯一”二字可以去掉了。
④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
⑤关于以格律规范的新诗,新月派时期并未给予命名;何其芳于1954年冠以以“现代格律诗”之名;2005年,“东方诗风”论坛以格律体新诗名之,如今渐为业界认同。《中国现代诗体论》为之设《格律体新诗》专章(吕进主编,重庆出版社2007初版308-358页)。本文以此统称。
⑥浙江文艺出版社1995年12月初版。
⑦见《重庆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37页。
⑧仅举一例:钟希高《潍坊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其摘要曰:在“五四”后期尤其是“五四”落潮之后,“五四”新文学作家却一改“五四”时期的偏激态度,重新开始创作古诗词,在一定程度上重新肯定了古诗词。古诗词与新文学形成鲜明对比,这样新文学作家创作古诗词就成为一个比较特殊的文学现象。
⑨《闻一多诗全编·导言》,浙江文艺出版社,1995。
⑩沈用大《中国新诗史(1918——1949)》,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