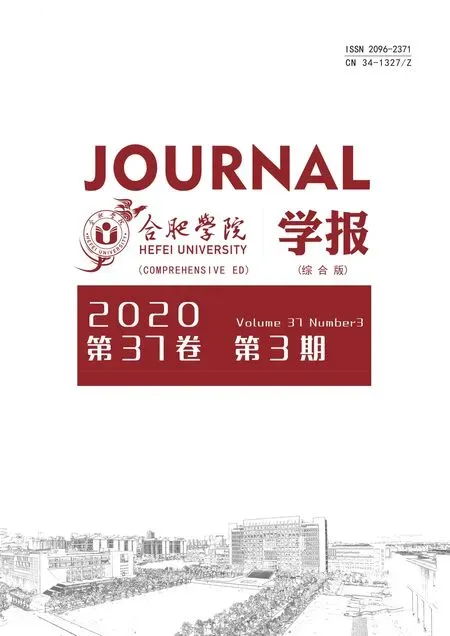断裂的阿里阿德涅之线
——论冯内古特《五号屠场》中的错格
2020-01-18杜学云
马 宁, 杜学云
(1.合肥学院 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学院,合肥 230061; 2.合肥市第四十五中学 英语组,合肥 230001)
0 引 言
《五号屠场》自1969年问世以来,为冯内古特赢得了批评界的广泛关注,也奠定了作者在美国文坛的巨匠地位。国内外对于小说的叙事艺术、人物塑造和主旨思想研究颇多,如虞建华通过对小说叙事结构和其改编电影的分析,阐明了作品的批判基调和精神内核[1];亚当·巴罗斯从残疾文学批评的角度,探讨了比利作为一个精神残疾者的主体性是如何被社会话语决定的[2];也有学者借助新兴的动物研究理论解读小说蕴含的人文深意[3]。笔者认为,《五号屠场》作为一本基于作者本人亲身经历的小说,表现出了冯内古特对于历史叙述的深刻思考,可以看作是冯内古特历史意识的一次公开表达。
小说刻意违背了独白性叙事传统,利用“错格”凸显故事的虚构性,从而提醒读者历史的建构性和文本性。“错格”(anacoluthon)一词从词源上说,意为“反对跟随”,也就是反对跟着一条连贯的道路走到底,亦即“反讽之永久性悬置”[4]。传统的叙述历史将各种事件串连成一个有目的、有方向、有根据的线条,这个环环相扣的单一线条造成了一种回归理性的假象。而冯内古特运用作者介入和自我指涉等手段,刻意打破了叙事的连贯性和统一性。这种整个文本中的“错格”,故意将叙事问题化,从而在书写过去的行为中,将过去向现在开放,鼓励读者去质疑历史的确定性和目的性。这与海登·怀特在《元史学》(Metahistory)中揭示的历史书写的诗学本质和偶然性不谋而合。历史,并非简单的存在于过去,而是和文学一样,也是一种话语。
本文从元史学的角度来研究《五号屠场》一书在叙事上的错格,采用文本细读的方式,以期阐明冯内古特回访过去的历史态度、“过去寓于现在”的历史意识,丰富读者对于文本的多元阐释,从而鼓励历史书写摆脱传统的束缚,寻求更为自由的表达形式。
1 内视角与作者介入:历史的建构性
在《五号屠场》的第二章至第九章,作者采用第三人称叙述了主人公比利·皮尔格里姆的故事。虽然采用了传统的第三人称内视角(inside view),故事却并不像现实主义作品那样,刻意去营造一种一切自然而然发生了的感觉。恰恰相反,在整个叙述中,作者的声音不断介入,迫使读者从故事中抽离出来,摆脱传统叙事带来的逼真性幻觉。这种叙述上的前后不一致,提醒读者意识到文本的虚构性和价值预设。
内视角的采用,原本是为了让读者轻松地跟随故事发展,自觉与主人公产生共鸣,甚至是认同感,形成一种故事天然存在的错觉。尽管文本中还是会有零星的证据,表明其虚构性,但是现实主义作家们大都竭力抹去这些痕迹,来维护作品“客观性”的尊严。然而,冯内古特从未尝试诱导读者去相信比利的故事是单纯存在的。相反,他用明确的“作者介入”(authorial intrusion)来提醒读者这段叙述是人为设计的。
作者第一次大摇大摆地现身于叙事中,是在比利被擒获并运往德国腹地之时。在同行的战俘中,有一个自称“疯狂鲍勃”的上校,他在战争中失去了自己整个团的士兵。此时,作者把自己和自己的老战友插入了这段叙述。他说:“我就在那儿,我的战时老伙伴伯纳德·维·奥黑尔也在那儿。”[5]52后来,当比利的妻子向他询问关于战争的问题时,“一个疯狂的想法出现在比利的脑海里。这个想法中所蕴含的真理让他吃惊。对于比利·皮尔格里姆来说,它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墓志铭——对我来说也一样。”[5]105此处的“我”即是作者的声音。然后,我们看到一张墓志铭的插图,上面写着:“万事都曾美好,一切皆不痛苦”[5]106。至此,作者又一次在叙事中刻意凸显出自己,还额外赠送给读者一幅画得像开玩笑一样的墓碑图片。通过大方承认自己的在场,冯内古特让读者意识到了,原来在故事的阴影里一直有一个叙述者,控制着情节的发展。
作者在比利故事中的第三次闯入比以往更加直白和肆无忌惮。当战俘营中的英国军官招待被俘的美军士兵时,这些可怜人因为肠胃一时无法适应丰盛的食物,“泻得如同火山爆发”。一个士兵说,他几乎把自己都拉空了,除了脑浆子什么都拉出来了。片刻之后,这个士兵说,“出来了,出来了。”他指的是自己的脑浆子。此时,小说白纸黑字地写道,“我就在那里。那就是我。那就是这本书的作者。”[5]109这种叙述者刻意的插入,就像米勒说的,如同来自其他某个星球的陨石,陡然落入了第一层叙述语的封闭大气层中,猛烈动摇了叙述的逼真性[6]。
小说的主人公比利是一个反英雄的形象,“既无力打击敌人,也没法帮助朋友”[5]26。他“瘦高虚弱,身材像可口可乐的瓶子”[5]20,脸上带着小丑般“愚蠢的友善表情”[5]50。这个“长相滑稽”[5]20的家伙所鼓吹的特拉法玛多星球的所谓福音,只是对战争的顺从,是用漠视来应对灾难的逃避主义。如果冯内古特像现实主义作家那样,采用连贯的内视角来讲述比利的故事,读者就会有种与比利一路同行的错觉,从而下意识地同情其遭遇,甚至赞同其行动选择。因为,内视角允许读者通过主人公的眼光去看待事物,这等于是在和角色共享信息,那么读者自然希望角色“拥有好运气,一切顺利,而不去管他本身的品质如何”[7]。鉴于冯内古特对比利的形象塑造,他对这个角色的态度不言自明,所以他定然不希望读者与比利产生共鸣甚至是共谋的感情。于是,他用作者声音的不断闯入,持续打破内视角营造出的幻觉,让读者意识到故事都是从某个视角出发构建出来的,从而最大限度避免了读者对比利角色道德的认同。
由此,我们可以明确地看出冯内古特对于战争的态度,绝不是“被动接受,放弃抵抗”[8],也不是一种清静无为的“寂静主义”(quietism)[9],更不是某些学者所理解的宿命论倾向[10]。比利的顺服和漠然并不能代表作者本人的态度,冯内古特在叙述中的不断闯入也是在提醒读者,他依然在与朗福德之流编纂的官方历史进行抗争,依然在通过高度个人化的讲述来凸显历史的建构性。
高呼“作者已死”的罗兰·巴特曾质疑,在某些特质、某些区别性特征上,历史叙述和史诗、小说、戏剧这些虚构作品的叙述形式到底是否存在差异[11]。巴特发起挑战的其实就是传统史学一直津津乐道的客观性。历史和文学一样,也是一种话语,其叙事模式也受意识形态的影响,也是在赋予过去以意义。尤瓦尔·赫拉利认为,虚构和讲故事作为大规模合作的前提,是我们智人在进化史上最有利也最有力的武器[12]。人类本质上是叙事的动物,而传统的历史叙述总是采用那种单一、连贯的第三人称叙事声音营造一种冷静、客观的感觉。冯内古特通过对这种幻觉的刻意破坏,提醒读者去思考一个问题:既然德累斯顿轰炸这样的历史事件可以用《五号屠场》这样一个虚构作品来再现,那么它是不是也可以用其他任何可能的形式来书写?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传统史学也就只是其中的一个形式罢了;而历史,不论如何讲述,在本质上也都是“创造性写作的一种”[13]而已。
2 元小说的自我指涉:历史的文本性
《五号屠场》一书的第一章和第十章是作者自传性的叙述,它就像是比利故事的一个“封皮”,既在叙事文本之外,又在叙事文本之内。作者在其中讲述了小说的构思、历史渊源、素材收集、创作困境以及重返德累斯顿的旅行,感觉就好像他在一边写作,一边解释和破译自己的小说。这种强烈的“自我指涉性”(self-reflexivity),彻底解构了传统历史叙述的“理性陈述”,进一步向读者展示了历史书写的文本性。
事实上,《五号屠场》对传统叙事的颠覆从书名页就开始了。书名之下不仅有两个副标题“儿童的圣战”“与死亡的责任之舞”,还有一段略显冗长的关于作者本人和小说本身的介绍。在这段介绍里,就已经预示了小说战争纪实和科幻虚构之间的杂糅,“这是一部多少带有特拉法玛多星讲故事的简洁的精神分裂症风格的小说”(Title page)。然后,作者就在第一章里走上台前,揭示“儿童的圣战”一题的由来。这是他对自己战时老友奥黑尔的妻子玛丽所作出的承诺,也是对历史上出现过的儿童十字军东征的戏仿。
作者毫不吝啬地分享个人创作过程,并用自己的声音来评论自己的作品。他原本对小说的设想是一本史诗般的杰作。为了激发创作灵感,他去拜访了战时老友奥黑尔。作者本来想象的是,两个老兵在炉火边的皮椅上把酒畅谈,追忆往昔,怀旧之情溢于言表。而玛丽给他们准备的却是“白色瓷面餐桌旁的两把直背椅子”[5]11,整个场景更像是一个“手术室”,迫使这两个人开始冷静地解剖自己的战争记忆。在他们头顶那个“两百瓦的电灯泡”[5]11之下,任何美化过去的玫瑰色眼镜都不再起作用。玛丽愤怒地对作者说,实际上战争中厮杀的都是一些孩子,他们为了自己都不甚明白的宏大宗旨投身战场,而那些流行的战争小说和电影还在继续隐瞒事实,让战争看上去像成熟男影星塑造的铁血硬汉一样充满魅力。[5]13于是,作者向玛丽保证,自己一定不会写一部为战争涂脂抹粉的小说。当初计划的有着宏大主题的巨著,如今在作者看来也只是“一本差劲的小书”。[5]2
在这本小书中,真实与虚构,严肃与戏谑,地球与外星,相互交织,就像冯内古特自己说的,呈现出一种精神分裂症的状态。所谓精神分裂的状态,其实是一种人格的不统一现象,也就是说主体对时间线概念的掌握是混乱的,无法形成连贯的自我意识。对于人类而言,寻求统一和理性一直是美好理想。但是,这种理想应该是彼岸的灯塔,绝不该是历史叙述的预设领域。历史书写是我们寻求意义迈出的第一步。如果从一开始,就把历史事件纳入意义的闭环,来证明统一性,那么这种证明结果显然是经不起推敲的。传统历史记述常常营造出一种历史客观存在的幻象,每个事件都如同有机体里的一环,不可或缺,没有什么是偶然的。冯内古特在《五号屠场》中用元小说的自我指涉打破了这种幻象。叙事的连贯性被矛盾性取代,文本中的前后不一致,即错格,带来了阐释的多样性和意义的不确定性,统一性也不复存在。
海登·怀特在《元史学》中强调了历史的诗性和文学性。怀特认为,历史学家们用叙事策略把历史事件包装成了历史事实。他们对历史的任何叙述都预设了某种理论阐释或者批评角度,然后运用情节化(emplotment)、形式论证(formal argument)和意识形态蕴含(ideological implication)等方式来加以实现[14]。怀特对历史诗学本质的揭示,让我们看到,历史编纂并非在单纯罗列一系列的过往事件,史学家们总是在看似纯粹的事实性记述中“夹带私货”,那就是关于事件为何发生的解释以及其中蕴含的意识形态。而他们所采用的手段往往就是单一且连贯的叙事声音。
传统历史叙述一般会先预构一个历史领域,然后赋予它开端、中部和结尾,让整个文本显现出一种封闭性和目的性。而在《五号屠场》一书中,冯内古特用元小说的自我指涉,瓦解了传统叙事刻意营造的连贯性和意义感。在小说的第一章,作者就交代清楚了比利故事的开端、中部、高潮、结尾。他说,这本书的高潮应该是埃德加·德比的行刑,因为那太具讽刺意味了。整个城市轰然倒塌,数以万计的生命灰飞烟灭,而一个美国士兵却因为在废墟中拿了一个茶壶而受审,并被执行了枪决。[5]4后来,在比利的故事中,几乎每次老德比的出现都伴随着作者对他结局的剧透。最后,作者也确实按照第一章中所说,安排了老德比的死作为情节上的高潮。这样一个没有任何前期铺垫或后续行动的高潮,简直就是冯内古特甩给传统叙事的一记响亮的巴掌。
通过公开讨论小说的创作预设,冯内古特提醒读者去关注这样一个叙事陷阱:一个事件可以被编排到一组事件中,充当某个角色,或开端,或结局,或高潮,而因其位置不同,所处的“意义等级”也不尽相同。这样的线性叙事,再辅以修辞性文学表现形式,譬如全知的叙述者、丰满的人物塑造、跌宕起伏的情节等等,历史事件就变成了可以理解和阐释的历史事实,并向读者展现一个秩序井然、因果有理的世界。为了避免落入这个陷阱,冯内古特选择了自己独特的方式来记述历史,这种充满自我指涉性的方式“既是颠覆性的又是建设性的”[15],它将非理性、非逻辑和对话性的因素引入到原本单一的逻各斯中,从而产生一种张力,让读者体会到阅读的不安和焦虑,进而去质疑传统叙述的稳定结构和意义谋划。
在《五号屠场》中,当比利踏入一个满是美国战俘的房间时,发现没有一个人说话,因为“关于战争没人有什么好故事可说”。[5]48传统的历史叙述以其诗学本质书写了一个又一个关于战争的“故事”。而在亲身经历了战争的残酷之后,冯内古特坚决反对用这种方式来讲述德累斯顿轰炸。我们的同胞正在冷静地、系统地、大规模地杀害自己的同类,对于这种行动,任何将其变成“好故事”的企图在冯内古特看来都是不可接受的。于是,我们看到《五号屠场》借用自我指涉完成了对传统叙事的反讽和戏仿,通过质疑和揭示自身,引领读者去拷问历史。冯内古特对历史的质疑,并非在消解过去,而是带着审视的目光回访过去,从而厘清历史事件和历史记述之间的区别,让读者正视历史的文本性和虚构性。
3 结 语
在《五号屠场》的第一章里,冯内古特提到了他战后在芝加哥做警务记者的经历。他的第一个报道是某退伍军人意外身亡的事故。当他打电话给报社时,负责做记录的女打字员,让他致电死者的妻子,看看她是什么反应。冯内古特照做了。当他如实汇报的时候,女打字员一边嚼着糖果,一边漫不经心地问道:“这种事让你感到不安吗?”[5]8女打字员对死亡的超然态度让我们看到了传统报道对人的影响。线性叙事制造出的单一意义和确定感让人感到安全舒适,也容易让人对一切漠然接受。所以,对冯内古特而言,关于德累斯顿轰炸,没有比《五号屠场》这种叙述更合适的方式了——只有针对叙事的叙事,才能是超越传统叙事的适当道路。
葛兰西(Gramsci)曾断言,知识分子应当说出关于权力的真话。笔者不知道冯内古特在多大程度上赞同此论断,但是他确实在努力说出自己见证的历史,并揭示过去的事件是如何湮没在诸多历史叙述中的。“治愈”战争留下的伤痕不是冯内古特的关注点,《五号屠场》也不是冯内古特开出的一针“镇痛剂”。他需要读者直视战争的残忍和荒诞。人们回想过去的方式,与思考自身现在和未来的方式有着紧密的联系。因此,试图将战争崇高化、合理化的官方历史无益于人们反思过去,而高度个人化的叙事行为则更适合将那些看上去已经尘埃落定的事件再次引入大众视野,从而让过去向现在开放,使过去寓于现在。
如果我们将历史看作是代达罗斯的迷宫,那么冯内古特并没有像前人一样,试图去寻找那根阿里阿德涅之线,以便将时间穿连起来,制造逻辑上统一的意义。恰恰相反,在《五号屠场》一书中,内视角、作者介入和自我指涉相互作用,形成不同的话语层次,造成大范围的错格,从而完成了对逼真性幻觉的彻底悬置。叙事的阿里阿德涅之线,在这种戏剧性反讽(dramatic irony)的蓄意破坏下,变得支离破碎,弯曲纠缠,就像一团断纱残片。而在这种问题化的叙事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关于历史建构性、文本性和“过去寓于现在”的深刻思考。就像罗伯特·弗洛斯特在诗中所说,“两条路在林中分岔,而我——/我选择了少有人行走的路, /而这就造成了所有的差异。”面对德累斯顿轰炸这样的人类灾难,冯内古特选择了一条完全不同于传统叙事的道路,而造就了小说不同于其他历史文本的所有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