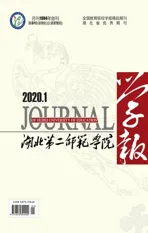多元系统理论视角下转译小说地位之嬗变
——以鲁迅《月界旅行》和《死魂灵》为例
2020-01-18樊腾腾
樊腾腾
(东莞理工学院城市学院 外国语学院,广东 东莞 523419)
一、引言
作为一种古老的翻译现象,转译几乎贯穿人类的翻译史。转译与直接翻译相对,是指非从源语文本译出,而经由一种或多种中间语言进行翻译的行为,又称为间接翻译或“重译”。晚清至20世纪上半叶,伴随着中国的社会激变,思想文化领域异常活跃,翻译活动如火如荼,其影响和意义均突破以往。其中,转译的作用不可小觑,与直译一样,擎起了翻译活动的半壁江山。以“五四”为分界的前后两个阶段(1898-1919年和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转译活动成果丰厚,影响深远,在原因、特点和作用等方面均呈现出迥异的特征,代表了中国近现代翻译史上的两次转译高峰。鲁迅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文学家,更是翻译家,他的转译实践纵贯两次转译高峰,构成了其翻译活动的主体,是转译的代表性人物。在鲁迅转译的众多体裁中,转译小说成就斐然,但通过观察不难发现,前一阶段以鲁迅转译小说为代表的翻译小说对中国彼时小说文学的作用和意义远远小于后一阶段,反映出转译小说在中国小说文学中的地位由低到高的变化趋势。结合多元系统理论关于翻译文学在目的语文学系统中的地位的相关论述,可以对这一问题有更加清晰的认知。
二、多元系统理论与鲁迅的转译小说
20世纪70年代,以色列著名翻译理论家伊塔马·埃文-佐哈(Itama Even-Zohar)提出了研究动态文化和异质文化互动关系的多元系统理论,将翻译行为置于更广阔的社会、历史、文化等视域下进行描述性考察。该理论认为,人类社会的各种交际形式就是由符号支配的社会符号现象,这些符号相互关联组成的系统集合体由若干子系统组成,这些子系统处于开放、多变的动态网络中,即“多元系统”。动态系统内部的复杂性和交叉性使子系统的地位并非一成不变,处于边缘的子系统有可能运动至中心位置,中心的子系统也会被驱赶至边缘位置。整个人类文化可以被视为一个多层次的、复杂的多元系统,小说文学是其中的一个子系统,转译(翻译)小说和本土小说都是其下的子系统。转译(翻译)小说在小说文学系统中并不总是处于边缘位置,在三种情况下,翻译文学可能居于一国文学之首要地位:第一,当一国文学草创阶段,尚处于“幼年期”;第二,当文学处于“边缘”或处于“弱小”状态,或兼而有之;第三,当文学正经历某种“危机”或转折点,或出现文学真空。[1]转译(翻译)小说的地位变化还表现为对本土小说所产生的不同作用和影响上。佐哈认为,翻译文学的地位的变化会带来翻译规范、翻译行为和翻译政策的变化。当翻译取得中心地位的时候,翻译行为是创新的力量,译者很乐意打破本国的传统规范,引入新规范,即“异化”倾向;当翻译文学占据边缘地位的时候,译者多模仿文学系统中业已存在的模式,进行本土化改造以增强译文的可接受性,即“归化”倾向。[2]在中国近现代的两次转译高潮中,转译小说的地位不同,其影响是对本土小说文学规范产生遵从和重塑的作用。
小说是一种通过刻画人物形象,描述故事情节以反映社会生活的“俗文学”,虽然自古以来受到文人的轻视,但晚清以来,在社会剧变和梁启超倡导的“小说界革命”的影响下,小说文学迎来了一个黄金发展期。小说以宽厚的包容性、鲜明的思想性和生动的故事性与表现力,与时代紧密结合,其语言、思想内容和创作手法的变化引领着文学进步的方向,成为最活跃和最具代表性的体裁。因此,对小说的考察有助于洞悉文学的发展趋向。小说的发展与翻译小说密不可分,相互作用。鲁迅的文学创作始于翻译,其中小说翻译的成就尤其突出,大部分作品采用的是转译方式。鲁迅33年的翻译生涯跨越两次转译高潮,其前后两阶段的转译小说对中国小说发挥了截然不同的影响。其中,《月界旅行》和《死魂灵》是鲁迅在两阶段最具代表性的转译小说。鲁迅转译小说在选材及翻译策略和方法都是与社会背景和他个人的思想变化密切相联的。留日初期,鲁迅的救国思想尚在探索阶段,怀揣实业兴国的梦想,热衷于译介反映西方社会进步的科学小说。发表于1903年的《月界旅行》是鲁迅据井上勤的日译本转译的法国作家凡尔纳的科幻小说,是他为数不多的转译科学小说的代表。小说向当时的国人介绍了神秘的、鲜为人知的科学世界,采用传统的章回体小说体例,语言以文言为主,“文白夹杂”。翻译沿用了清末以来的意译法、“编译”法。清末民初,以传奇轶事等为主要题材、章回文言语体的古典小说正逐步解体,新型现代小说尚未成形,《月界旅行》等一批新题材转译小说正在蓄力挑战和打破旧有小说的核心规范,但仍囿于传统,处于与其他类别小说同等竞争的地位。“五四”之后,反封建、反压迫思想深入人心,鲁迅意识到,认识残酷的社会现实,唤起国民内心的革命精神才是挽救危亡的关键。因此,其译介小说逐渐转向反映东欧弱小民族和俄苏社会现实和人民革命斗争的题材上来。《死魂灵》是鲁迅晚年转译自德译本的果戈里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揭露了新兴资产级阶残酷剥削的丑恶及农奴制走向衰亡的历史现实,采用直译法和“新文化”运动以来得以确立的自由体白话文形式,在艺术形式和手段上继续巩固和发展现代小说规范,代表了当时小说的主流创作规范。
以多元系统理论为框架,从历时的角度对比研究鲁迅翻译生涯一首一尾极具个人和时代代表特征的两部转译小说作品,可以窥探中国近现代转译小说在小说文学系统中地位转变的趋势和原因。
三、对《月界旅行》和《死魂灵》在小说文学系统中地位变迁的对比考察
《月界旅行》和《死魂灵》虽然都出自鲁迅之手,但二者面世时间相隔30余年,在译作迭出、潮流变幻的中国近现代译坛,却是代表了截然不同时代特色和风格的两部作品,是转译小说文学随时代发展的缩影,也折射出转译小说地位和影响的变化。总体来说,该阶段的转译小说在中国小说文学系统中的地位呈“边缘-中心”的发展趋势,对中国小说文学的影响从保守趋于创新,这些变化在两部译作中突出体现在题材与思想内容、语言与体例和创作特色三个方面。
(一)题材与思想内容
清末民初之季,中国社会和文化正经历着千百年未有之变化,新旧交锋,对立冲突。复杂、矛盾的社会现实为小说的蓬勃发展提供了沃土。总体上,民元前后的文言小说是处于中国古代文言小说的大传统中,题材上,以传奇、笔记、轶事小说为主,[3]描写封建伦理道德下的才子佳人式爱情、英雄侠客、奇闻志怪等内容,反映了人民反对封建束缚,渴望自由、正义的思想主题。与此同时,在“西学东渐”的翻译热潮中,从西方引入中国的政治、科学、侦探等新题材小说也备受追捧,丰富了传统小说的题材,体现出社会转型期大众多元的价值追求和阅读趣味。1903年,鲁迅转译的《月界旅行》可谓生逢其时,小说描写了美国内战结束后,有个枪炮会社的社长心血来潮,宣布将制造巨炮,并将炮弹射向月球,一位法国勇士主动请缨,预乘坐炮弹开启探月之旅,最终炮弹发射成功,勇士实现月球环游。该故事内容新颖,想象瑰丽,体现了科学的精神和人类奋进的精神面貌,令人鼓舞。鲁迅的译文寓科普于精彩的情节中,表现出他早年所秉持的通过宣传新知,以科技图振兴的救国思想。正如其所言,“故苟欲弥今日译界之缺点,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4]就题材而言,清末民初,传统古典小说的主导地位逐渐下降,新旧题材的各种小说并存,小说题材的新格局尚在形成中。以《月界旅行》为代表的科学小说,与其他题材小说一样,还处在小说文学系统边缘的竞争位置,并未对小说题材的转型产生决定性作用。
新文化和“五四”运动使反封建、反压迫思想深入人心。新文学运动紧密结合时代背景,也为小说的发展指明了方向。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小说处于破旧立新的发展阶段,题材凸显了反封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内容。30年代,在左翼作家鲁迅、茅盾、郭沫若等的号召下,东欧弱小民族和俄苏小说被大量译介,其中的反封建的民族革命和解放等现实主义成为小说创作的主流题材。作为左翼文学的先锋,鲁迅转译的大量俄国小说对其反封建思想的影响最大,集中体现在他对旧封建国民性的无情批判和培养新国民性的思考中。转译于1935-1936年间的《死魂灵》是鲁迅的呕心之作,将其反封建思想表达得淋漓尽致。小说的主人公乞乞科夫是个虚伪狡诈的人,企图向城市名流和庄园主购买死亡农奴名单,并以移民之名申请荒地,再将农奴高价出售,通过买空卖空的方式做投机生意以牟取暴利。后来,图谋败露,乞乞科夫仓皇逃窜。鲁迅通过《死魂灵》向国民昭示了俄国社会的丑恶现实及农奴面临的残酷剥削压榨。30年代,受国内外革命形势和译介文学的影响,以左翼作家为代表的中国小说界兴起以无产阶级和受压迫民众的意识形态为基础,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描写重大现实题材的小说创作潮流。[5]这些小说着重揭露社会现实和批判典型人物,通过挖掘民族性、国民性,以实现唤醒国民、改造中国的目的。小说题材的现实意义、人物群体的阶级代表性和革命性都更加凸显,初具现代性小说的雏形。在《死魂灵》中,鲁迅通过对乞乞科夫入木三分的揭露,描绘了19世纪俄国农奴制末期宏大社会图景中的贵族、农奴主和官僚的众生相,体现出对人物劣根性的拷问及对农奴命运的严重关切和思考,具有强烈的反封建意识。《死魂灵》等现实主义转译小说在题材和思想内容上引领并影响了同时期的小说创作,对中国小说文学的现代转型发挥了重要作用。
由此可见,从《月界旅行》到《死魂灵》,在题材和思想内容方面,从“边缘化的众多竞争者之一”到“主流的塑造者”,转译小说在逐渐走向小说文学系统的中心位置。
(二)语言与体例
清末民初,古典文言小说虽已整体式微,但辛亥革命的前后几年,受文化复古思潮的影响,文言小说迎来了短暂的“末代繁荣期”,1912-1917年间,《小说月报》发表的文言小说远多于白话小说。但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文学领域里白话文取代文言文已是大势所趋。因此,作为对语言变化最为敏感的文学体裁,此时的小说在语言上体现出过渡期的特征,即传统文言、浅近文言、文白夹杂、白话文等各种语言形式杂糅并存,没有一种形式占支配地位。鲁迅转译《月界旅行》也难免受到这种语言趋势的影响,正如其所言,“初拟译以俗语,稍逸读者之思索,然纯用俗语,复嫌冗繁,因参用文言,以省篇页。”[6]最终,鲁迅决定放弃白话,采用文言。所以,《月界旅行》的语言呈文白交杂的特点,前五回以白话为主,从第六回起,文言的比重逐渐增大,但总体上属于改良后的浅近文言,通俗易懂,如:
社长立住问道:“君是谁?”其人答道:“余臬科尔也。”社长大声道:“余欲见君,已非一日,今乃相遇于此,何幸如之!” 臬科尔道:“余亦如是,故来见君。”社长道:“君曾侮我。”臬科尔道:“然。”社长道:“余将举轻侮三条件以问君,君能答乎!”……君如能与余同意,则余亦来觅君。[6]
中国古典小说采用章回体叙述体例,每回的标题以两句对偶句(回目)概括内容情节,以“话说”、“且说”开始,回末有“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的结束套语,每回的故事相对独立完整。鲁迅在《月界旅行》中使用章回体,总共14回都配有回目和结尾套语。因此,《月界旅行》采用当时流行的“改良文言+白话”的语言形式,沿用章回体体例,符合主流的小说创作和翻译规范,并没有独树一帜的革新行为。
1917年,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倡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在文学中的正统地位,废除传统文体,以通俗晓畅的语言书写新文学,文学革命就此拉开帷幕。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颁令将“国语”(白话文)纳入国民学校教育体系,从此白话文成为被广泛认可的书面表达语言。此外,二三十年代,初具现代特征的文人大多身兼作家和译者双重身份,他们的翻译为汉语带来了“欧化”倾向,从外国吸收新词汇、表达法和句型,丰富了汉语白话文的表现手段。所以,具有“欧化”特点的现代汉语在逐渐形成。鲁迅是白话文学的积极践行者,从《狂人日记》开始,他的小说创作和翻译语言一直引领着现代小说语言的发展方向。鲁迅在《死魂灵》中使用的白话文意义明白,略带“欧化”特征,体现出白话文向标准现代汉语过渡的趋向,如:
在十足的半个钟头里,出色的马匹就把乞乞科夫拉了大约十维尔斯他之远——先过槲树林,其次是横在新耕的长条土地之间的,夸着春天新绿的谷物的田地,其次又沿了时时刻刻展开着堂皇的远景的连山——终于是经过了刚在吐叶的菩提树的宽阔的列树路,直到将军的领地里。[7]
以上译文体现了鲁迅的直译观,语句的使用与现代汉语有差别,但整体意思清楚。通过音译引入的新词“维尔斯他”、“连山”、“吐叶”虽然不够规范,也使语言略带异域格调。另外,《死魂灵》采用现代小说的编排体例。
因此,从《月界旅行》使用的浅近文言和章回体到《死魂灵》的“欧化”白话文和现代体例,两部转译小说在语言和体例上从“非主流”到“主流”的转变表明,在中国小说文学发展的转折期及现代小说的肇始期,转译小说在小说文学系统中由“边缘”向“中心”发展的趋势及对系统产生的指引性作用。
(三)创作特色
转译小说还有助于强化中国小说的文学本体意识,输入现代小说的创作手段和表现手法,提升小说的文学性和表现力。晚清至“五四”,虽然新旧题材的转译小说数量庞大,但众多转译小说译自二三流作者甚至无名作品,这就使其中可资借鉴的小说文学性和艺术性特征逊色于相对较少转译的经典名家名篇。这反映出,在现代小说发端的前夕,小说翻译界一力追求绍介新知与趣味性的同时,文学意识比较淡薄,后来常说的“纯文学”的意识与追求,此时相对而言乃是缺失的。[8]清末以来,中国翻译界盛行“林纾模式”,采取以意译和编译为主,对原文大量删除、篡改和增添以迎合中国通俗小说的“归化”策略,其弊端之一就是有些表现小说创作技法的内容被漏译或简单化处理,造成转译小说的文学价值降低,未对小说创作发挥积极的改良作用。鲁迅在转译《月界旅行》时也没有摆脱旧有小说理念和翻译规范,将日译本28章的内容删减合并为14回,故事情节也有调整变动,表明鲁迅对小说文学性的探索尚处于初始阶段,还不具备成熟的小说创作观。
新文学运动从根本上改变了小说文学的面貌,中国小说经历了更新换代,更加讲求思想性、艺术性的现代小说开始萌芽,这其中转译小说的“传输”作用功不可没。新文学的倡导者重视小说的社会功能,号召从西方文学中汲取营养,丰富小说创作手段,提高表现力。很多作者和作品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推动中国小说向现代性发展。鲁迅晚年译介了大量俄苏文艺理论作品,与他的小说翻译实践一同促进了其小说创作,他从小说翻译中了解了隐喻、象征、讽刺等叙事技巧和自然主义等文学思潮,通过消化吸收,逐渐熟练地运用于自己的小说创作中。《死魂灵》是果戈里批判现实主义小说的顶峰之作,其典型手法如抒情、讽刺、幽默、象征等充分体现了小说创作的现代主义倾向。有现代小说之父之称的鲁迅,在自己的译文中对这些小说叙事技巧予以继承和创造性发扬,逐渐发展出独具个人特色的小说创作技法。其中,鲁迅对讽刺的理解和运用非常到位,他曾说,“讽刺小说是贵在旨微而语婉的,假如过甚其辞,就失去了文艺上底价值,而它的末流都没有顾到这一点。”[9]讽刺的关键是借助适度委婉性的语言以传达作者的意旨,如果语言过激,非但达不到讽刺效果,还会降低作品的文学性。鲁迅在《死魂灵》中对讽刺的精彩转译比比皆是,如:
乞乞科夫要和罗士特莱夫表示好意,便摸了一下那狗的耳朵。“是的,会成为一匹好狗的。”他加添着说。
“再摸摸它那冰冷的鼻头,拿手来呀!”因为要不使他扫兴,乞乞科夫就又一碰那鼻子,于是说道:“不是平常的鼻子!”[10]
这是乞乞科夫为了收购死魂灵,而有意逢迎农奴主罗士特莱夫的细节,鲁迅通过描述他夸赞狗的语言,讽刺和揭露了其虚伪、圆滑的资产阶级奸商本质。用平实的语言衬托出令人心酸的事实,是讽刺技巧在鲁迅转译小说中运用的写照。
从《月界旅行》对当时的小说创作手法缺乏革新性贡献,到《死魂灵》中,以讽刺为代表的小说技巧影响鲁迅,进而塑造了写实主义的中国现代小说创作技巧,在创作特色方面,转译小说已经逐渐居于小说文学系统的中心位置,促使中国现代小说创作技巧趋于成熟、完善。
四、结语
鲁迅的小说转译生涯是中国近现代小说转译实践的缩影,《月界旅行》和《死魂灵》则是鲁迅前后两阶段转译活动的集中代表。以多元系统理论为基础,通过分析两部转译小说在题材内容、语言体例和创作特色三方面的演进过程,可以洞悉转译小说在中国近现代小说文学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由“边缘”向“中心”发展的总趋势,有助于对转译小说的历史地位有更清晰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