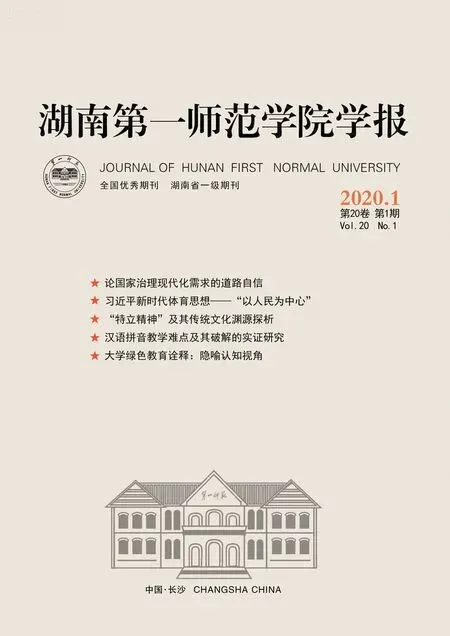略论厨川白村与胡风文艺观之异同
2020-01-17魏邦良
魏邦良
(安徽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安徽 马鞍山 243002)
日本文学理论家厨川白村的文艺理论通过其著作《苦闷的象征》传播到中国。这本名著经鲁迅翻译后曾在中国文艺界风行一时。胡风曾在文章中提及,他的文艺观受到这本书的影响。《苦闷的象征》虽有唯心主义杂质,但胡风舍弃了其中的唯心论,接受了它的“创作论”和“鉴赏论”。
正如胡风所承认的那样,《苦闷的象征》对胡风产生了巨大甚至根本的影响。厨川白村关于文学主体性、创作规律以及创作主体与现实客体之间的相互关联与融合等方面的论述,都对胡风产生了重要启发;该书所使用的一些基本概念,如肉搏、突击、体验、情热等后来也成了胡风建构文学体系的关键词。
一、作家创作时内心涌动着一种“热”
厨川白村认为,文学是苦闷的象征,而这苦闷是因了生命力受到压抑的缘故。他说:“动弹不止的生命力受了压抑和强制的状态,是苦闷,而于此也生热。热是对于压抑的反应作用;是对于action的reaction。所以生命力愈强,便比照着那强,愈盛,便比照着那盛,这热度也愈高。”[1]31
换言之,文学作品要表现出作者内心的感情(所谓“热”),正因如此,有人把文学作品称之为“有情热的观照”。厨川白村这一观点无疑启发了胡风,在其成名作《张天翼论》中,胡风就批评张天翼在创作时“用的是多么冰冷的旁观者的心境啊!冷情就必然虚伪。”[2]49在《张天翼论》的结尾,胡风提醒张天翼,要在生活里找到温暖:“艺术家不仅是使人看到那些东西,他还得使人怎样地去感受那些东西。他不能仅仅靠着一个固定的观念,须要在流动的生活里面找出温暖,发现出新的萌芽,由这来孕育他肯定生活的心,用这样的心来体认世界。”[2]57
在《关于抽骨留皮的文学论》中,胡风再次重申,一个作家不应该在创作时做一个冷静的旁观者:“因而我们反对把青年变成和尚尼姑的‘为人’上的‘冷静’哲学,而要歌颂为民族为人民受苦受难的献身热情(passion),因而我们反对把艺术送进神庙的‘冷静’美学,而要堂皇地拿出战斗的现实主义的立场:‘能杀才能生,能憎才能爱,能生能爱才能文’。”[3]28
厨川白村和胡风都认为,作家创作时不能客观冷静,内心应涌动着一种“热”,但两人对这种“热”的理解却并不相同。对厨川白村来说,这“热”,是生命力遭到压抑后的一种突围与反抗,“是对压抑的反应,是对于action的reaction”[1]31;对胡风来说,这“热”是对人民对民族的爱,是为民族为人民受苦受难的献身热情。胡风盛赞契诃夫,就是因为作为作家的他内心涌动着一种爱,一种热。所以,在其作品中能感受到作者的“仁爱的胸怀”。而且,正因为契诃夫用爱和信念工作,“才能够得到在人生上的,同时也就是在艺术上的‘强’。”[3]220
在厨川白村看来,作家创作时不仅要表现出内心的“热”,还要“将作家所有的生命的内容,即生命力这东西,移附在所描写的东西里”[1]179而“所谓作家的生命者,换句话说,也就是那人所有的个性,所有的人格。”[1]180
厨川白村所谓的“所有的个性,所有的人格”,被胡风延伸为“人格力量或战斗要求”[3]181,在此基础上,胡风形成了他对现实主义的认识:“这种精神由于什么呢?由于作家的献身的意志,仁爱的胸怀,由于作家的对现实人生的真知灼见,不存一丝一毫自欺欺人的虚伪。我们把这叫做现实主义。”[3]39
厨川白村与胡风都强调作家内心的“热”,强调作家的情热与人格,但其中的内涵却有很大的不同。厨川白村之于胡风,更多的是启发而非灌输。
二、不能离开作品的内容谈技巧
厨川白村声称,不考虑读者,不考虑社会反应,而将真实的自我完全展现出来的作家是不多的。不少作家,抱着讨好读者的想法来写作,于是作品便流露出一种“匠气”:“仿佛看了对手的脸色来说话似的讨人厌的模样,在专门的诗人和画家和小说家中尤其多。这结果即成了匠气。”[1]49既然作品着力表现的是作者本人的生命,这种“匠气”当然令人讨厌。越是熟悉“技巧”的作家,越容易让自己的作品产生这种“匠气”。
对于“技巧”,厨川白村的看法是:
所谓技巧者,并非女人们擦粉似的专做表面底细工,乃是给那东西有生命的技巧。一到技巧变成陈腐,或者嵌在定型里面时,则刺激的力即暗示力,便失掉了。他又在弄这玩意儿哩,谁也不再来一顾。一到这样,以作为表现而论,便完全失败,再没有一点暗示力了。[1]179
厨川白村关于技巧的认识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胡风对技巧的看法。1935年,在《关于青年作家的创作成果和倾向》一文中,胡风就批评了一些作家热衷的“技巧”脱离了作品的内容:“在他们的掉花枪的技巧下面并不一定找得出内容上的必要,他们却技巧的把他们所要传达的内容和甚至是有教养的读者隔开了,好像他们的技巧是用来遮饰内容的贫弱……”[4]胡风认为,如果孤立地谈技巧,就会沦为“走江湖的形式主义”。1942年在一篇文章中,胡风再次抨击了某些贩卖技巧的人:“有些人居然振振有辞地把艺术说成了一种技艺,写人有可以传授的‘技巧’,写景有可以传授的‘技巧’,结构也有可以传授的‘技巧’,好像一个作家所需要的只是一个八宝箱,而文坛上也居然有了贩卖这种箱子的巧人。”[3]160即使步入人生暮年,胡风对“技巧”看法也是一如既往,他断言,认为靠技巧可以创作,是把文学庸俗化了[3]622。
胡风与厨川白村对“技巧”的反感与厌恶是相似的。但他俩对“技巧”理解并不完全相同,反感与厌恶“技巧”的原因也不相同。
对厨川白村来说,作家创作是作家生命力的表现,所以不必也不该抱着讨好读者的心理,一旦执笔创作时想着迎合读者的口味,会很容易采用某种通行的手法。如此,作品难免流露出某种“匠气”,而这种“匠气”恰恰会妨碍作者生命力的表现。另外,厨川白村认为,对作家来说,“给东西以生命”的技巧是存在的,但既是“技巧”,就会被很多人反复使用,这样一来,这个陈腐的“技巧”就起不到应有的作用了。而胡风对“技巧”的否定更彻底,在他看来,根本不可能离开作品的内容谈“技巧”,孤立地谈“技巧”就是形式主义。在胡风看来,想用“技巧”掩盖思想的贫弱和感觉的迟钝是根本不可能的。
厨川白村认为,技巧是存在的,但熟练的技巧会带来“匠气”,而“匠气”会影响作品的“生气”。厨川白村说技巧就是给东西以生命的技巧,未对此作进一步阐述。而胡风的思考更为深入、细致,表述得也清晰。胡风反对学习所谓的“技巧”,但却强调要多读世界名著。胡风认为,读世界名著,不是学“技巧”,是学习那些文学大家“怎样从生活实际形成了他的特有的精神状态,他的特有的精神状态又采取了怎样特有的射击姿势,朝向了怎样的射击方向。”[3]81胡风认为,我们从世界名著中汲取一切,本质上是为了培养精神世界,并不是直接朝向文艺创作。因为第一是人生上的战士,其次才是艺术上的诗人。
胡风着眼于人,厨川白村着眼于文。两人均反感“技巧”,着眼点却不同。
胡风主编《七月》时,喜欢用年轻的新作家稿子,很少请老作家为其撰稿。在他看来,老作家们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以圆熟的技巧掩盖感受力的麻木。
三、作家的态度决定了作家的创作
厨川白村认为,文学创作源于两种力的相触相击。一方面有生的苦闷,一方面有战的苦痛。两种强大的力的冲突而产生的苦闷懊恼,便是文艺的基础。“在内心烧着的生命的力成为个性而发挥出来的时候,就是人们为内底要求所催促,想要表现自己的个性的时候,其间就有着真的创造创作的生活。”[1]5正因如此,厨川白村强调,态度决定了作家的创作活动。这里的态度既包括生活的态度,也包括创作的态度。所谓生活的态度,就是不甘于外在的种种束缚,敢于反抗外界的种种压抑和强制,充分发挥一个人的个性,充分反映作者的生命欲求。相反,如果屈服于生活,对各种束缚选择妥协与降伏,那创作的冲动也就消失了。“凡是服从于权威,束缚于因袭,羊一样听话的醉生梦死之徒,专受物欲的指使,而忘却了自己之为人的全底存在的那些庸流,不会尝到人生的深的兴趣……”[1]3
厨川白村认为,生命力受到压抑后产生了苦闷,而“一面经验着这样的苦闷,一面参与着悲惨的战斗,向人生的道路进行的时候,我们或呻,或叫,或怨嗟,或号泣。这发出来的声音就是文艺。”[1]20所谓创作的态度,厨川白村也在书中作了说明:“惟其创作家有了竭力忠实地将客观的事象照样地再现出来的态度,这才从作家的无意识心理的底里,毫不勉强地,浑然地,不失本来地表现出他那自我和个性来。……所描写的客观的事象这东西中,就包藏着作家的真生命。”[1]29而胡风也说:“失去了欲求,失去了爱,作品就不能够有真的生命。记住,由生活到艺术!在生活里面没有感激,在作品里面就不会有力量。”[2]333厨川白村所说的“生命”,被胡风细化为“爱”“欲求”“感激”。
胡风参考、借鉴了厨川白村关于作家应具备怎样的“生活的态度”和“创作的态度”方面的论述。胡风认为,作家对于人生没有积极的态度,“他就不能够和进步的力量呼应或融合;他又怎能够大无畏地看清生活的真理,创造出能够推动生活的作品呢?”[2]327胡风还以鲁迅为例,指出鲁迅的作品就透露出作者的态度:同情、悲愤以及对于这种黑暗现实的反抗。
厨川白村和胡风都强调,作者在作品中要反映作家的主观欲求、主观理想。但厨川白村所谓“主观欲求,主观理想”是指作家受到压抑的自由的天性和个性;而胡风所谓的“主观欲求”,是指作者对现实的洞察,对黑暗社会的反抗以及对光明未来的展望。两者的内涵有很大的不同。
厨川白村和胡风都认为,作家不能屈服于生活。在厨川白村看来,作家屈服于生活,甘于受束缚与压制,不仅无法深刻地认识生活,也失去了创作的冲动。而胡风认为,作家屈服于生活,就会沦为“客观主义”,会使笔下的人物形象成为凡俗的虚伪的东西。
厨川白村和胡风都反对自然主义,因为自然主义作家抱着冷静超脱的态度写作,作者和他的笔下的一切保持着距离,作者写作时没有发挥主观能动性,而是客观地、冷淡地描摹着一切。而厨川白村和胡风都认为,作家创作时要将自己的生命溶入作品中,用厨川白村的话来说,就是“将生命赋给所描写的东西,活跃着的。作为表现的艺术的生命,就在这里。”[1]179
厨川白村把创作过程比喻成母亲生育过程:
作家的生育的苦痛,就是为了怎样将存在自己胸里的东西,炼成自然人生的感觉底事象,而放射到外界去;或者怎样造成理趣情景兼备的一个新的完全统一的小天地,人物事象,而表现出去的苦痛。这又如母亲们所做的一样,是作家分给自己的血,割了灵和肉,作为一个新的创作物而产生。[1]33
胡风也说过一番与此颇为类似的话:
作家的想象作用把预备好的一切生活材料溶合到主观的洪炉里面,把作家自己的看法,欲求,理想,浸透在这些材料里面。想象力使各种情操力量自由地沸腾起来,由这个作用把各种各样的生活印象统一,综合,引申,创造出一个特定的有脉络的体系,一个跳跃着各种情景和人物的小天地。[2]331
显然,两段话都突出了作家主体的重要性。但侧重点明显不同。厨川白村认为,作家必须将自己的生命赋予作品,作者的“自我”“个性”才能通过写作而表达出来,作家因此才能“分娩”出一个艺术的“宁馨儿”;而胡风强调的,作家创作时必须充分发挥主观的想象、综合、引申等作用,方能完成创造这一艰巨重任。厨川白村强调由内到外,“将存在自己胸里的东西,炼成自然人生的感觉底事象”;胡风强调的是从外到内,“把预备好的一切生活材料溶合到主观的洪炉里面”。
厨川白村在论述创作时突出了生命力,胡风却告诉我们,对作家来说,生命力当然重要,观察、调查、搜集材料也同样重要。胡风的观点是对厨川白村看法的必要的补充。
有些作家认为,只有直接经验才能成为艺术家创作的材料。厨川白村批评这一看法简直糊涂之至。他说,倘使如此,那么描写窃贼,作家便该自己去做贼,描写害命,作家便该亲手去杀人了?岂不谬哉!正因如此,在厨川白村看来,作家完全可以根据间接经验来创作:“只要描出的事象,俨然成功了一个象征,只要虽是间接经验,却也如直接经验一般描写着,只要虽是向壁虚构的杜撰,却也并不像向壁虚造的杜撰一般描写着,则这作品就有伟大的艺术底价值。”[1]67厨川白村还以莫泊桑《项链》为例,说,这篇小说来自直接经验还是间接经验我们不必管,“这作家的给与这描写以可惊的现实性,巧妙地将读者引进幻觉的境地,暗示出那刹那生命现象之‘真’的这伎俩,就先使我们敬服。”[1]66
胡风也认为,作家生活经验不足并不影响其文学创作,但胡风持此观点的理由与厨川白村不同。厨川白村认为,只要作品“俨然成功了一个象征”,那么,不管你创作的材料来自直接经验还是间接经验,作品就有了伟大的价值。而胡风则认为,作品成功与否,取决于作家的“本质的态度”,与直接经验、间接经验关系不大。在胡风看来“真实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能够补足作家的生活经验上的不足和世界观上的缺陷”,“如果一个作家忠实于艺术,呕心镂骨地努力寻求最无伪的、最有生命的、最能够说出他所要把捉的生活内容的表现形式,那么,即使他像志贺似地没有经过大的生活波涛,他的作品也能够达到高度的艺术的真实。因为,作者苦心孤诣地追求着和自己的身心的感应融然无间的表现的时候,同时也就是追求人生。”[2]427
厨川白村和胡风都指出,作家完全靠直接经验写作,无必要,也不可能。那么,仅凭间接经验,如何使作品成功呢?厨川白村给出的办法是:“只要描出的事象,俨然成功”,“只要虽是间接经验,却也如直接经验一般描写着,只要虽是向壁虚构的杜撰,却也并不像向壁虚造的杜撰一般描写着”,那么作品也就具备了伟大的价值。然而,厨川白村却没告诉我们,作家只有“间接经验”,怎样才能“却也如直接经验一般描写着”;作家“向壁虚构的杜撰”,怎样才能“并不像向壁虚造的杜撰一般描写着”?对此,胡风给出了答案,就是作家将全部精神力量倾注于对象的追求上面,那么,写妓女,他就得自己变成那个妓女,写强盗,他自己就得出没在深夜的原野和丛林。胡风说,做到这一点,必须有个前提:“一个作家,怀着诚实的心,在现实生活里面有认识,有感受,有搏斗,有希望或追求,那他的精神就会形成一个熔炉,能够把吸进去的东西化成溶液,再用那来塑成完全新的另外的东西。”[3]15于是,作家写杀人犯当然不必自己先去杀人,但他“非有能够体验杀人犯的心理状态的那一份‘社会本能’不成”;于是,道听途说的材料也可以写,“问题在于你能不能用你的精神力量从那些材料里面取出有生命的活的东西。”[3]15
关于如何把生活材料(直接或间接)溶入作品,如何赋予笔下的人物以生命,厨川白村的观点深深启发了胡风,而胡风在接受厨川白村的真知灼见后,经过缜密细致的思考,将这一问题深化了。
四、“精神的伤害”与“精神奴役创伤”
厨川白村说,文艺乃苦闷的象征,所谓苦闷,就是“尽要满足欲望的力和正相反的压抑力的纠葛冲突而生的精神的伤害”。[1]18两种力的冲突产生了苦闷和懊恼,那么,正如前文所引用的那样,经验着这苦闷,一面参与悲惨的战斗,一面奋然前行时所发出的或怨嗟或号泣,或诅咒或赞叹的声音,就是文艺。厨川白村的“精神的伤害”,在胡风笔下成了“精神奴役创伤”。胡风说:
人民的生活欲求或生活斗争,虽然体现着历史的要求,但却是取着千变万化的形态和复杂曲折的路径;他们的精神要求虽然伸向着解放,但随时随地都潜伏着或扩展着几千年的精神奴役的创伤。[3]189
有人不理解胡风这一说法,问:人民一方面是善良的、优美的、坚强的、健康的,一方面又“潜伏着或扩展着几千年的精神奴役的创伤”,这不是把人民看成了“妖魔鬼怪”吗?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胡风引用了马克思的话:
支配阶级的思想,无论在任何时代,都是支配的思想。即,作为社会的支配的物质的力量的阶级,同时就是它的支配的精神的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的诸手段的阶级,凭着那,同时也自由地运用精神生产的诸手段。因此,同时,缺乏这种精神生产的诸手段的人们的思想,一般地是被隶属到这个支配阶级里面。[3]552
接着得出结论:“以为说人民的生活要求里面潜伏着精神奴役的创伤就等于说人民是‘妖魔鬼怪’,那除了证明自己不愿意接近具体的活的人民以外,是不能有别的解释的。”[3]553
在弗洛伊德和荣格的精神分析学说基础上,厨川白村通过“精神的伤害”揭示了人们潜意识中对自由的渴望与社会习俗、规则对人的桎梏、压抑之间的永远的冲突,正是这种冲突带来的“苦闷与懊恼”构成了文艺之源。而胡风基于马克思相关论述及鲁迅有关“国民性”的思考,以“精神奴役创伤”揭示了漫长的封建社会对中国人民的压迫与毒害:“如果封建主义没有活在人民身上,那怎样成其为封建主义呢?用快刀切豆腐的办法,以为封建主义和人民是光光净净地各在一边,那决不是咱们这个地球上的事情。”[3]554
显而易见,厨川白村是借助弗洛伊德理论对人的心理作了深度探索,而胡风则在吸收马克思、鲁迅相关思想的基础上把这种探索与对社会、历史的剖析、挖掘结合起来,从而深刻地揭示了封建社会对中国人民的精神奴役。
谈及艺术生活,厨川白村曾说过这样的话:“将自己本身移进对境之中,同时又将对境这东西消融在自己里。这就是指绝去了彼我之域,真是浑融冥合了的心境而言。”[1]151
胡风借用这种主客观交融的观点来分析、描述作家的创作过程,说:“真正的艺术上的认识境界只有认识的主体(作者自己)用整个的精神活动和对象事物发生交涉的时候才能够达到。”[2]239胡风还引用了法捷耶夫的话证明了这一点:“只是全部积蓄起来的材料,跟一种基本的思想、观念,起了某种化学上的化合。”[2]332胡风后来将这种“化学上的化合”剖析得越来越细致。胡风说,写作过程就是克服过程,你克服着材料,也克服着你本身。“而这指的是创造过程上的创造主体(作家本身)和创造对象(材料)的相生相克的斗争;主体克服(深入、提高)对象,对象也克服(扩大、纠正)主体,这就是现实主义的最基本的精神。”[3]237
厨川白村侧重揭示主客体之间的融合,胡风则指出,两者之间在融合的同时,也相互“克服”,并指出,这种主客体的相生相克,引发了自我斗争。胡风认为,这种自我斗争,正是艺术创造之源。厨川白村认为,两种力(生命力与压抑力)的冲突带来了苦闷,而苦闷产生了文艺;而胡风则认为,主客体的相生相克,是艺术创造之源。厨川白村论述文艺创作时,完全忽视了客体的作用,这是他和胡风非常明显也非常重要的区别。
胡风虽然接受了厨川白村“创作论”方面的某些思想,但对厨川白村的其他一些重要要观点则完全舍弃了。
厨川白村认为,艺术最大的目的是表现作者的个性:“使从生命的根柢里发动出来的个性的力,能如间歇泉(geyser)的喷出一般地发挥者,在人生惟有艺术活动而已。”[1]27“独有艺术,却是极度的个人底活动。就是将自己的生命即个性,赋给作品。”[1]181胡风当然不认可这种说法,在他看来,艺术须表现出一种精神。这种精神的内涵是:作家的献身的意志,仁爱的胸怀,作家对现实人生的真知灼见。两人的分歧十分明显。
厨川白村认为,文艺的出发点是深味人生的一切,把捉住生命的内核。而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是摆脱道理、道德、法则等束缚,甚至要“超脱了健全和不健全,善和恶,理和非之类的一切的估价”。就是说,一个文艺家要站在“善恶正邪利害得失的彼岸”,深味人生的一切。换言之,文艺家必须是个广义的人道主义者,他须不咎恶,不憎邪,有一颗包容一切的神的心,一腔圣者之爱,而且“毫不抱什么成心,但凭了流动无碍的生命的共感,对于人类有不失其温暖的同情和深邃的了解。”[1]142胡风也认为,作家应该是人道主义者,但这个人道主义是反抗黑暗人生的人道主义者,是欢迎新的人生的人道主义者,他们的作品表现出的是对人的关怀,人类解放的精神。胡风所肯定的是一种崇高的人道主义者,当然不是厨川白村笔下所谓的广义的人道主义者:“立在善恶正邪利害得失彼岸,而味识人生的全圆,想于一切人事不失兴味者。”[1]142
在厨川白村看来,文艺家是广义的人道主义者,他像圣者一样,以一视同仁的目光看待大千世界。正、邪、善、恶,在文艺家眼中是没有分别的,它们只是文艺家酝酿文艺之“酒”的元素而已。厨川白村说:“离了这深的人味,大的道德,真的文艺是不存在的。”[1]142这里所谓“大的道德”,其实就是超越善恶的“道德”。这样的观点,胡风当然不会同意。胡风所认同的人道主义,是关怀人的像鲁迅那样“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人道主义,而非善恶不分的人道主义。
厨川白村还认为,文艺不涉功利:“一受功利思想的烦扰,或心为善恶的批判所夺的时候,真的文艺就绝灭了”[1]143这一点,胡风无论如何也不会认同。对胡风来说,文艺是唤醒民众(启蒙)的号角,也是抗击敌人(救亡)的武器,怎能不谈功利呢?而革命文艺,在胡风看来就是“要从自己的道路上分担唤醒人、影响人、甚至改造人,把人吸引到这个大斗争里面去的意识斗争的任务。”[3]546
1984年,胡风的人生已进入倒计时,这一年,他再次撰文谈到了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
二十年代初,我读到了鲁迅译的日本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他的创作论和鉴赏论是洗除了文艺上的一切庸俗社会学。……把它从唯心主义改放在现实主义(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就可以克服文艺创作的自然主义的错误和机械类即庸俗社会学的错误,对作家的生活实践和创作实践怎样结合起来这个主要问题取得健康的理解。[5]259
这番论述表明,胡风接受了厨川白村的创作论和鉴赏论,摒弃了他的唯心主义。在这篇文章中,胡风对厨川白村把创作的动力归到性的苦闷上这一说法提出批评:“没有精神上的追求(苦闷)就没有创作,这是完全对的。但这个‘苦闷’只能是社会学性质的东西,也就是阶级矛盾的社会生活造成的,决不能只是生物学性质的东西。”[5]259
可见,胡风同意厨川白村苦闷是创作动力的说法,但他对“苦闷”的理解却与厨川白村有很大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