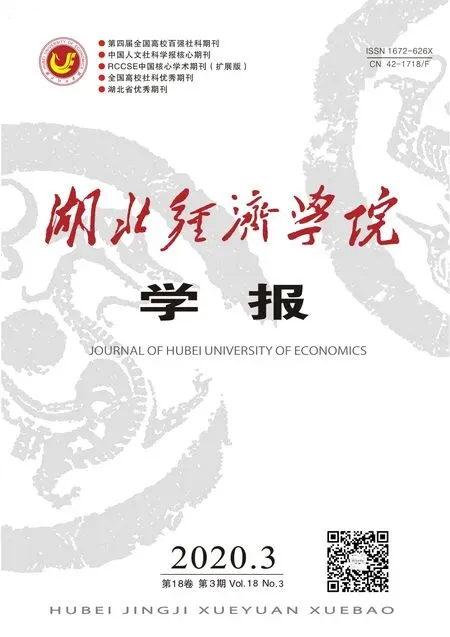科层制、规训及国家人本主义
——论新冠肺炎疫情下世界级传染病象征域之新构
2020-01-17陈剑
陈 剑
(广东海洋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广东 湛江 524088)
2020 年春节前后,一场突如其来的大规模传染病迅速扩散并席卷了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接着是欧洲、美洲及澳洲,逐步演变为世界级重大公共安全危机。这是一种类似2003 年SARS、具有超级传染性的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全球性肺炎。在中国,它引燃国人的恐慌和焦虑,全国上下启动紧急应对战略,发动史诗般的抗疫战争。本文试图在疫情防治背景下重新思考社会学家力求改革的现代科层制、法兰克福学派尖锐批判的工具理性、福柯担忧的规训权力、桑塔格警惕的疾病隐喻以及卢梭的公意、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等,探讨世界级传染病象征域的消极幻见和积极重构。
一、科层技术的失效和改革
根据米兰•昆德拉在《帷幕》中的定义,科层制(Bureaucracy,也译官僚制、官僚主义)是一种剥夺事物本来(生活)面目和个体生存视野的庞大机器化操作模式。它发明了像钟表一样精致复杂的体系,使每个参与者无论能力性情多么不同,都能削平为整饬统一的同质性机构中的一部分,准确执行零件式的规范功能。它要求的“不是一个公务员明白他的行政所负责的问题,而是他带着冷静,完成不同的操作,而不去理解,甚至不尝试去理解在周边办公室内发生的事情”[1]。
因此,科层制推崇的是不加思考的服从和效率,而不是个体自由中的道德准则或文化归属。它是集体大机器,是各级专业部门按部就班地展开工作,是根据可计算的规则而不问对象和毫无情感地处理事务,具有汉娜•阿伦特“平庸之恶”的不思辨气质。在其中,信息失去了建构一个整体可理解世界的交流意义和人文经纬,个人仅仅降格为处理信息、维护机器运作、随时可被替代的高效处理器。
昆德拉从斯蒂夫特赞美田园牧歌理想的《晚来的夏日》跳到卡夫卡笔下小人物在异己机构和层级官员面前战战兢兢的《城堡》,宣布科层制在历史中的全面胜利,宣布人的个性、时间流程、自由和私生活包括冒险奋斗都被行政指令所笼罩,亦可转化为统计学数据。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的兴起加速了科层制的升级化,如同好莱坞爆米花电影迎合市场票房的制片程序一样,它形成了一套套更为缜密有效及应对紧急状态的功利机制。
昆德拉的思想承接自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现代论。后者在《支配社会学》《支配的类型》中指出,随着货币经济、法治体系和近代民主制的成熟,社会管理的科层制理性化,亦即科层技术是现代人不可摆脱的命运。这无关政治体制和支配者,亦即生产资料所有制或统治政党的类别,而是侧重规范和参数、冷冰冰的法理型(legal)支配社会最典型也最先进有效的管理模式。他说:“只有科层制才能为一个合理的法律……之执行(裁判)提供了基础。”[2]47“在所有领域中,‘现代的’组织形式之发展即是科层制行政组织及发展与不断的扩散,教会、国家、军队、政党、营利企业、利益团体、基金会、俱乐部等等,均为如此。……我们调整日常生活的整个形态以适应这个组织架构。”[3]
然而,一旦科层技术在法理秩序中掌控、收编了个人,使其沦为机器齿轮,社会生活也就变得行政化数据化常规化乃至守旧化,削弱了政治文化体验或价值理性所蕴含的反思、批判和变革精神,个性思想和表达逐渐被体制同化,变得微不足道,组织成员和上下级的沟通及行为变得死板、严抠条文和缺乏应变力,以至于科层制“发展愈是完美,就愈‘非人性化’”[2]64;科层行政“倾向于排斥公开性,尽可能隐藏其知识和行动,以逃避批判”[2]86;“群众……提出实质‘公道’的要求,即不可避免地会与官僚行政之形式主义、束缚于规则及冷酷的‘就事论事’发生冲突”[2]54。这些大概是科层制之原罪。放在推崇过度征服自然和经济发展GDP 指标的现代社会来说,就意味着以经济数据及绩效、政绩考核为理性目的的单面思维很可能垄断科层体系,导致其出现一叶障目而谬以千里的行政错误。
回顾疫情发展过程,笔者以为,多国防治工作尤其在早期均存在不利疫情控制的失当行为,譬如英国等国提出的集体免疫政策、美国不平等不到位的检疗措施以及多国将其视同流感不检测不封锁不隔离的轻敌方针,这里除了医疗资源和技术的限制,还有部分原因是科层技术在认知、应对和控制新型烈性传染病方面的失效,主要表现为政府常规管理和科技专家在大灾面前保障民生的应急决策之脱节。
在这里,科层技术触及到马克思人本主义的焦点:人的物化。反思工具理性对人的物化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主题: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强调工具理性的扩张带来工业机械生产的同一性技术体系,它甚至服务于法西斯的高效大屠杀;马尔库塞在《爱欲与文明》中斥责人类屈服于资本主义剥削体系和父权制家庭,因而不得不受控于异化的劳动和爱欲;弗洛姆在《爱的艺术》中指出资本市场的无孔不入使婚恋沦为利己者的商品买卖;他在《人类的破坏性剖析》中披露剥削性社会促成人的虐待狂和恋尸癖(如希姆莱和希特勒)两类侵犯性格,其偏爱对他者实施掌控或消灭。
诚然,当个体为工业社会体系化的统筹-效率原则所管制,就容易丧失鲜活丰富的生命个性,并可能处于权力的极不负责乃至屠戮下。但这只是现代性的一方面。工具理性的支配者意志或群众化路线同样可以兴利除弊。如果说现代科层制是一种政府或企事业单位的工具理性,侧重人员的专业技术水平和机构的严格组织控制。那它不仅是以资历和业绩进行考核评聘、将个体计数培训编排的物化系统,同时也是生产管理必需的中立而高效的工具。在全球性疫情防治中,我们不可能退回原始或封建的社会支配类型,而是如何在科层制之上发展一种扶植民权和健全人性的生命政治,令其准确全面及时地保障民生。
实际上,在疫情的大战场上,相比于常由大财团和资本主义私有制操纵的西方代议制民主,中国的优势不容小觑,那是公有制经济组成、集体主义精神、唯物史传统、基建行动力、现代化中医、高度集中的中央行政权、公务人员和科技专家的联合同心、和平友爱的民族性以及“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指导方针等,这一优势体现在政府强有力的隔离控制、检查治疗以及各级工作人员的团结奉献、人民群众的参与配合中,也势必将在日后的全球性经济文化竞争互助中脱颖而出。
总之,倘若将科层制看作一种工具理性化、行之有效的技术模式,那它也是现代生产力和社会管理不可或缺的利器或本质形态。它不应与民间活动权益、公民的个性尊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命运共同体等人文主题或政治导向相背离,两者应互为表里,抑或前者尊重后者的优先权,接纳文化、经济、大学各学科等诸多力量的具体参与、监督、引领甚至深层改造。这才能创造出有关疾病治理的良性积极的象征域。
二、传染病的二元论隐喻:排斥VS 规训
福柯的知识考古学为科层技术的诞生提供了新的视角,昭示了以传染病为象征的社会治理的两大隔离结构:《疯癫与文明》讲述理性如何分离并降服其对立面疯癫、使之从古代文化或审美事实沦丧为病理学对象的文明单一化进程,它采用的是以麻风病为起源的排斥式隔离;《规训与惩罚》论述规训如何替代展演君权的肉体酷刑和灵魂控制的惩罚技术学、上升为权力生产肉体的现代程序,它行使的是以大瘟疫(如鼠疫)为起源的规训式隔离。
在文艺复兴时期,那些囚禁疯人、漂泊在城镇之外水域中的愚人船是理性开始掌控、区隔并战胜疯癫的标记。自从17 世纪语言真值、人格善值和18 世纪科学真值大幅度提升,正统和异端、文明和野蛮、人性和兽性、理智和谵妄等二元逐渐划清界限、泾渭分明,服从于理性的大一统辖制。福柯追溯了笛卡尔的“我思论”和古典主义悲剧《安德洛玛克》剧末俄瑞斯忒亚回光返照式疯癫灵光,回忆起古希腊悲剧中集体审美和洞察力的呓语风采,那时的逻格斯没有阴面,命运的名字叫疯癫。恰如粉墨登场的当代俄狄浦斯,福柯戴上知识分子和历史学家的假面,试图在学术或文艺领域发出类似谵妄心像、失援自语的未分化理性之异声,审视疯癫那段被否定、迫害、展演、封杀最终贬为医学矫正/抹除对象的失语史。
笔者以为,这一段从愚人船到19 世纪初精神病院建立的“理性胜利史”对应或铺垫于《规训与惩罚》中规训社会建立前的灵魂惩罚史,是通过启蒙人道主义的表象传播对心灵塑型定界、奠基现代人格的历史转折。换言之,权力生产的规训社会必须以将精神病人等非理性者排斥在外的道德-理智人口为基本资源,排斥先于规训,也涵于启蒙。排斥与规训是两种迥异却互为巩固的人口隔离技术,一者为了压制异端,一者为了生产正统。
颇具意味的是,福柯对精神病及精神病院这一历史真相的认识起源于麻风病,对规训制度和监狱职能的认识起源于城市大瘟疫。在他笔下,疾病治理预示和承载着文明理性机制的发展趋向和管理原型。麻风病人类似被共同体施行放逐式管理、难以治愈的精神病人,瘟疫患者则接近需要通过监狱和法律防范并规训、短暂隔离却仍有机会回归生产的普通公民。“麻风病人引起了驱逐风俗,在某种程度上提供了‘大禁闭’的原型和一般形式”;“瘟疫引出了种种规训方案。它不是要求将大批的人群一分为二,而是要进行复杂的划分、个人化的分配、深入的组织监视和控制,实现权力的强化和网络化。”[4]222
可以说,《疯癫与文明》和《规训与惩罚》分别叙述了两类疾病隔离结构。前者是以麻风病为起源的驱逐或排斥结构,其目标在于借助二元划分、规避外来污染源的大禁闭模式,建立并捍卫一个纯洁共同体。它将“患者遗弃在一个永恒流放的封闭空间”,令其“消失不见或被人遗忘”[5]。后者是以城市瘟疫为起源的规训隔离结构,其目的是通过解析和分配,在精密的分割战术和层级网络的监视、书写、治控中避免混乱无序状态,实现一个规训整饬、高效生产的社会。它将患者置于自身和权威人士的不断审查中,作为融入社会的手段发挥作用。
在福柯笔下,疯癫及作为其象征的麻风病并不同于其他如反动、贫穷、流浪、痴呆、放荡等非理性,那些是理性内部常被隐匿的丑闻或症结,而是一种最恶劣的、兽化的、虚无的“少数派非理性”,是理性必须加以利用、篡夺话语权的对立物。疯癫不仅在文艺复兴开始被驱逐,在古典时期沦为彰显神恩神罚、表现宗教真理的展演工具,而且在19-20 世纪的精神病理学中俘为必须用科学、心理学、伦理学手段加以矫正和清除的客观疾病,知识仿佛对其“已了如指掌,因而视若无睹”[6]。这或能说明精神医学只是古老隔离技术及其道德桎梏的翻版,是现代理性主义的狂妄和迷信,它杜绝任何其他形态的生命体验和激情突破,无视疯癫及其悲剧精神中蕴含的深刻的价值、信仰、文化或社会危机。
不同的是,犯罪与过失犯罪、游惰、愚笨及作为其象征的瘟疫召唤的是现代理性技术的规训,那是理性必须不断深化认识、引导并加以档案采集、规范和锻造的“多数派非理性”,它不是单纯被嘲讽、压制、扑灭的“另一星球事物”,而是理性视为一体共存并亟需纪律调控改善的赘生物。监狱、工厂、兵营、医院等连续性机构都是这一权力规训的组织形式。
因此,理性/疯癫不同于守法/犯罪这组二元论。前者是标志文明圈禁和地界的民俗禁忌学,它和正统/异端、生命/死亡、性别/模糊性别、主权者/牲人等政治经济学意义上严格划分的二元论一致。霸权一元坚持对边缘一元施行排斥式的话语权掌控,进而消解后者存在,其目的是将人的规范性乃至附属性特征确立为人的本质。后者代表文明内部的生物社会学治理,它和大人/小孩、启蒙/愚昧、环保/污染、常规状态/例外状态等文教层面互相交汇的二元论一致,主导一元坚持对次导一元施行规训治理,进而显现调节后者,其目的是巩固强化人的规范性特征。这两种二元论并非不可转化,随着文明地界和生活经验的扩大,一些被排斥的异端可以逐渐消除禁忌色彩,进入正统的理性地盘,趋近“例外的常规化”。这一步骤并非一蹴而就,甚至可能更深重地压制异端。但传染病是文明中转型最为成功的异端之一,甚至它是政治反抗和变革的肇因,譬如艾滋病,很难说它只是“高危群体”的污名化而非正名化。同样,新冠肺炎真的是中国政府的“切尔诺贝利时刻”吗,抑或是对国际政治偏见的抗议之声?
回顾2020 年全球新型冠状肺炎的疾病防治,隔离表现出诸多形式。一方面,它可以是人道主义的治疗式隔离、国家全景敞视主义式隔离、国家意志下的全员检查分配式隔离、工商行政医疗科研教育等层级式隔离、世界范围的流动控制式隔离,这都是现代规训式隔离,也只有此类隔离才能应对世界级传染病的危机,这亦对应福柯笔下由规训权力和人口权力结合而成的生命权力(biopower),是国家对个体生命包括性爱繁衍、生产生存进行全面整体的筹划调控。当然,在疫情中它是自我证成化的生命权力。另一方面,它也可以是种族主义的恐慌和驱逐、民主恋物癖、地域歧视、身份政治等,这是古代排斥式隔离。它丢弃了大传染病在历史教训中积累下的现代治理共识,偏重在意识形态上妖魔化疫区及其居民,乃至上升到对其道德、文化、民族、政体的诋毁。这种污名化策略绝不对应福柯笔下“让人活或不让人死”的生命权力,反倒接近列维纳斯、阿甘本、阿多诺等在纳粹集中营中发现并指控的生命政治,它圈禁奴役虐杀少数人种,令之沦为无尊严、无交流、丧失良知的物,即牲人(homo sacer)、非人(nonhuman)、次人(subhuman)、活死人(living dead)等赤裸生命。
在这场全球性天灾下,中国作为第一个疫情受害国率先实施了封锁隔离、层级检查和防控治疗等措施。传统春节活动的禁止、居民的闭不出户、国家的免费检测收治、各省市交通管制和经济停顿、无数不可记名群众的互助和善举、各级领导干事与医护人员的身心付出乃至生命的牺牲等等,这些都表明从武汉到湖北到整个中国都为这场疫情阻击战付出了难以想象的艰辛努力和代价,正是这种毫不推诿、严防死守的鏖战精神为世界各国争取到了后续战场的优势及宝贵时间和经验。然而,这些理应赢得掌声泪水的奉献并不能瓦解那些将我们骂作“中国病毒”“亚洲病夫”“黄祸”“疾病卵化器”①的排华敌对情绪,这情绪甚至威胁到部分海外华侨华人的居住生活与身心安全。同时,我们自己也有一些同胞将意外流落在外的武汉或湖北人看作过街老鼠般的“麻风病人”,另一些同胞则非法穿越疫区或谎报信息。
福柯指出,19 世纪一个奇怪的现象是把曾经的“麻风病人”(疯人、妓女、乞丐等)当作瘟疫受害者,实施大一统却精密区分的拘留、记录和监视,“个人化的规训战术被运用到被排斥者身上”[4]223;而21 世纪的一些国家官僚或群众,居然在世界级传染病面前能把瘟疫受害者当作避之不及的“麻风病人”②,妄想对之实行种族主义和地域歧视下的非防治性驱逐和侮辱。这种做法无非是排斥式隔离的倒退,如同认为只要将战事报信者当疯子关押起来就可打赢战争一样。但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发展迅猛的大国显然无法装上一条狭小的“愚人船”,相反,它的规训手段和科技资源倒可以给其他国家提供模范引导、借鉴学习和雪中送炭的温暖支援。
三、国家人本主义和世界共产主义隐喻
古代麻风病以及如今新冠肺炎和疯癫的形象之亲缘,并不源自它们对理性社会造成的不可挽回的威胁破坏,而是源自人类应对陌生、紊乱、扩散、疑似有害事物的恐慌幻想,源自其在阻止疫情蔓延方面的无能,在理解协调接纳干扰事物方面的决策失误,源自理性的狭隘脆弱及其对自身的捍卫、粉饰与正名,这些都是理性对传染病象征域的污名化构建。苏珊•桑塔格将其称为“疾病的隐喻”。她力求从文化建构的角度分析或解决“排斥性隔离”的问题。
20 世纪70 年代,身患乳腺癌的她在与疾病艰难斗争的同时,感受到周遭文化、制度对自身及其他病患的尖刻恶意,她意图为疾病在历史中的意识形态罪债翻案,洗刷其承载的宗教训诫、人格污蔑、异国形象学、国际阴谋论和种族主义幻象等,她写下两篇论文《作为疾病的隐喻》《艾滋病及其隐喻》,揭示疾病从来不是如其所是之物,而是饱含了政治压迫和道德攻击的话语战术。
桑塔格的隐喻概念来自亚里士多德《诗学》,即以一物之名指称另一物。当人类将疾病与道德、政体、军事等非必要关涉物挂钩时,就不仅将疾病或病毒,而且将病患、特殊群体、地域国家视为同时需要排斥和打击的耻辱对象,回归了古老麻风病的驱逐而不治愈的隔离结构。她主要论述了结核病、癌症、艾滋病、梅毒等,从道德政治宗教文学等视角来考察其多余的文化意味,进而批责疾病在科学认知之外不利诊治的四类恶性隐喻:
一是疾病被赋予神秘主义、超自然主义或宗教的警示和报应,它是上天降罪或魔鬼附体的结果,常上升到对个体或先祖罪行、集体腐朽生活的谴责,这尤其体现在群体性流行病的文学影射中。比如薄伽丘在《十日谈》中将当时的欧洲黑死病看作城市公民生活不检点的天惩。二是疾病被赋予患者道德人格和生活方式的羞辱化或美学化功能。它被看作个人精神癖性及其罪责的象征,甚至是身体无意识地接纳或渴望死亡(死亡本能)侵入生命的自行结果。一个人得什么病或不得什么病具有普遍必然性。比如肺结核被视为浪漫精神和世俗环境扞格不入的贵族病,癌症被视为激情冷却、顺服环境、气流淤积为废物的理性病。三是疾病被赋予政治或文化理性主义的载体功能,人们借其寓意展开对社会政治的攻击和对理想社会蓝图的构想。比如反民主派人士(如波德莱尔)将民主称作梅毒,癌症则被当作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畸形增长或能量压抑的负面标靶。四是疾病被赋予针对特殊人群或地域国家的政治军事化战略。比如艾滋病是使癌症相形见绌的新恐怖,它延续了“反癌细胞入侵战”中殃及病患的军事隐喻,强加给吸毒、性倒错等“高危群体”咎由自取的身份歧视以及各种“异国污染源”的阴谋控诉说。
桑塔格意以疾病本质论来取代隐喻论,将疾病从饱含鞭挞、禁忌、攻击乃至诗化的承载物中解救出来。但被她忽略的是,人类的疾病防治不仅关系到医学营养学调治下的身体康复,同时也囊括了涵盖政治文化经济自然各方面社会关系和环境状态之治理发展。在权力机器的统辖下,疾病不得不和其他领域的事物共谋融合,孕育出恩斯特•卡西尔在《语言与神话》所说的语言生成性的“基本隐喻”(radical metaphor)[7]。常态隐喻是已知词汇库中固定概念之间的替代和位移,基本隐喻则是人文语言的新创,可追溯到原始人在精神激动的印象中创造“瞬息神”名称和膜拜仪式的思维能力。这类原始思维推动着人类在新型实践表达中发生的范畴创造。它不是以一物指称另一物,而是精神力量在面对陌生事物时发明的新语言及其操作模式。这接近拉康的象征域,它是词与物之上人类不断创作更迭的实践文本肌理。
笔者据此认为,疾病不可摆脱隐喻,如同生命不可消灭诠释。隐喻不同于建制机构化的政法文教,仍是治控疾患的上层建筑的冰山一角,其核心是健康,包括生命、社会、环境健康的人类学身体指南等。它不应是个人疾病的消极想象,而是人类生存大环境中对共同面临、难以解决的疾病灾难的文学美学伦理学政治学的积极象征域之新构。其中一环是应对群体性疾病尤其是全球性传染病防治的各国政府管控模式。对此,笔者提出国家人本主义和世界共产主义新形态两个洋溢变革活力的疾病新隐喻。
在2020 年抗击新冠肺炎中,我国虽在前期行动上有一些迟缓,但仍具有扶利本国国民和他国国民的模范带头作用。这种国家行政层面上的以人为本即国家人本主义,与从欧洲文艺复兴发源的崇尚个人才智情感美德、主张个性解放、反对强权压迫的人本主义不同,国家人本主义是一种侧重考虑宏观治理、国际政治、民族兴盛、地球生态的威权型人本主义,它具有更多的国家主权意识、集体主义精神和民族文化认同。它意味着不可因为着眼大局就抛弃对国民或其他需帮助人物的关怀,也不可因为关怀具体人物就无视国家层面的以人为本。它信仰主权者权利和责任、个人利益和共同体利益之间的统一,此即卢梭的“公意”。但公意是从个人自由意志在共同契约的权利转让中推导出共同体意志,以致这两个意志常不可调和,不得不宣布公意必要时可扼杀私意。国家人本主义与之不同,是将国家主权及其行政范围视为个人自由和公民权利获得保障和不断提升的奠基,它们并无意志上的直接交汇或冲突,而是借助法理、经济、教育等公共治理方式及相关的中间社团组织展开交流。
哲人阿甘本在其《由无稽的紧急情况带来的例外状态》③一文中表示意大利政府通过夸大新冠肺炎疫情的危害来传播恐怖,在伪造的合理性中强制施行例外状态,剥夺民权和自由。这里自然有福柯《规训与惩罚》的背书。但这类诉诸个人自由乌托邦的无政府主义对于世界级灾难究竟有何裨益?对比国人的大局作风,我们看到意大利人民与之呼应的保卫自由的集会示威。
在世界级传染病的爆发下,与其看到疫情防控对个人自由的扼杀,发表时髦的现代性危机之断言,不如看到脱离国家强大主权和现代规训是自取灭亡之路,我们当大声疾呼“要福柯也要疫苗,要规训也要自由”。只有沿着国家人本主义的思路,才能解决现代社会个体和集体的自由困境;只有建设一个值得个人交托和信赖的人权保障型政府,才能跳出群众和国家机器信任危机的“塔西陀陷阱”。
另外,一旦国家人本主义上升为各国政体之上的国际人本主义,就有可能创造出各国主权牵线并联合治理的世界共产主义新形态。这里所说的共产主义并非吉亚尼•瓦蒂莫笔下的后形而上学语境化的“诠释学共产主义”,也不是齐泽克设想的各国政府和人民在抗疫中无条件的团结协作④,而是在这一世界性危机中意识到并将在未来予以巩固的公有一体、息息相关的地球经济共同体。说到底,这一危机不是由资本私有制来促成的劳动力增长,而是由国家公有制及其联合来予以解决的劳动者调护。不管是面对全球灾难的国际援助、物资分配、疫苗开发、流离者庇护,还是在灾难启迪下将由国家合作开展的环境保护、专利技术和资源共享、生产合作互助、政府协同治理、世界法构建等,都意味着各国政府必须将地球和人体视为共同的生产资料,不能一味由各国大小资本独占开发,而须在新的危机语境中重新商榷、计划和配置国土和身体的使用权、收益权乃至所有权,进而改变私有制生产关系。这或将带来一种并行于资本市场经济和国际自由贸易的新型公有制经济,那将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经济基础。
总之,只有各国从国家人本主义迈向世界共产主义,在普世性的科学法治环保的大环境中展开大合作,才能实现最终的以人为本,代表世界人民的利益和先进生产力。它的敌人只有两个:将一部分发展中个体进行排斥式隔离的经济关系;将一部分发展中国家进行排斥式隔离的国际政治。
四、结语
在种族主义、宗教狂热、地方排斥主义、专制反动势力的围攻中,如何实现人权、自由、宽容、团结、科学等世界性理想,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迎接的严峻挑战。命运共同体这个词本意味着每个人每个国家当下的共同处境和危机,意味着扭转历史决定论和漠不关心乃至对立的个别化原则,巩固和平公正的世界秩序,消除内部的怀疑分裂互斗消耗,推进主权者的共存共荣。2020 年的新冠肺炎疫情与其说是命运设下的不可逾越的种族藩篱,不如说是命运敞开的令人类团结协作的光荣之路。
萨特曾在《今天的希望》中号召地球人恢复人与人之间原初的兄弟关系,他在主观性林立的狭隘集体和全人类的兄弟团体之间布置了一个解放运动的过度环节,这为当时的阿尔及利亚人民武装反抗法国殖民主义增添了理论支持[8]。如今,我们同样需要打破藩篱,消解排斥性歧视和暴力,才能从共同的“危机之战”迈向“兄弟之爱”、从“共赢主权者”迈向“世界大同”。
注 释:
① 可参考丹麦《日德兰邮报》刊登的将中国五星红旗画作五颗冠状病毒的讽刺漫画;《华尔街日报》2020 年2 月3 日发表的《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一文;美国特朗普总统的贸易主管Peter Navarro 的反华言论等。
② 自1951 年联合国会议上通过《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以来,国际社会不懈关注和治理难民问题,要求各国加强团结合作,制定并落实对难民的接纳、安置、援助、保护、遣返等政策,保障其经济和社会权利,减除难民产生的根源。国际难民署将国内流亡失所者(IDP)和由于自然灾难逃离本国的人也纳入有权获得庇护的难民。如此看来,因疫情而流离在本国或他国暂时无法归家的灾民具有难民的属性,理应受到同样的人道主义待遇和援助。
③ 参见https://ilmanifesto.it/lo-stato-deccezione-provocato-da-unemergenza-immotivata/。
④ 齐泽克在其有关疫情的评论《清晰的种族主义元素到对新型冠状病毒的歇斯底里》中指出,当全球性灾难发生,那种唯一可以解救武汉末日式图景的政治理想,是“一种无条件团结和全球协同反应”“一种共产主义新形式”。参见www.rt.com/op-ed/479970-coronavirus-china-wuhan-hysteria-raci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