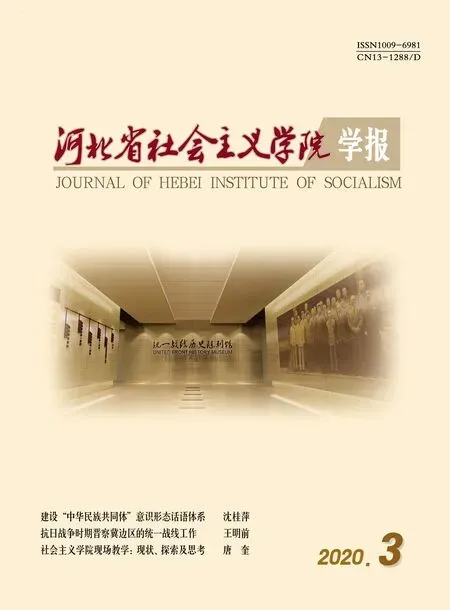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态话语体系
2020-01-17沈桂萍
沈桂萍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北京 100081)
当前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新时代。自从2013年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发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讲话以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统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进的指南。2018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被写入新修订的《宪法》。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思想基础。2019年,中共中央部署了全面系统深入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目标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成为统领民族工作的核心话语,而且成为引领民族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话语。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态话语体系,需要澄清民族意识形态领域内某些模糊认识,纠正偏差认识,深化中华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同体意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共识、凝聚人心、凝聚智慧、凝聚力量。
一、摒弃“主体民族”话语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越来越多的各民族同胞走出传统聚居地在全国各地流动,越来越多的地方成为多个民族同胞共同居住、共同学习、共同工作和共同生活的地方,各族同胞在广
泛的领域内深入而密切地互动,交往交流交融,大大深化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多民族混居杂居化正在悄然地改变“民族地区”话语体系,其中“主体民族”意识和话语越来越与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社会结构不符合。但是,长期以来,总有人自觉不自觉地使用“主体民族”这个词语。比如,有的人把人口占绝对多数的汉族说成是中国的主体民族,这里的“主体民族”等同于“人口占多数的民族”;有的人把在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说成是“主体民族”,这里的“主体民族”就等同于“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虽然这个民族人口并不一定占自治地方人口多数。
笔者查阅我国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以及其他民族工作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没有找到“主体民族”这个表述。恰恰相反,在所有官方正式发表的中国民族政策白皮书中,论述中国民族基本构成时,标准的表述通常是,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由于汉族人口占绝大多数,其他55个民族人口相对较少,习惯上把汉族以外的55个民族称为“少数民族”。各民族不论人口多少、历史长短、经济社会发展程度高低、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异同,都一律平等。
这里,“少数民族”仅指“人口数量相对较少”,而不是政治经济社会地位的不平等状况或处于弱势地位的定位,各少数民族都是国家的主人,不是客人。把人口占多数的汉族说成是“主体民族”,不仅容易误读成主导中国社会的强势民族,而且很容易把55个少数民族理解成“客体民族”或者“弱势民族”。那种把汉族当成中国的“主人”,把少数民族当“客人”,把汉族说成“主体民族”,少数民族说成“原著民族”“客体民族”等等,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极其有害的。
“各民族一律平等”是我们党和国家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重要内容,即“主张和坚持一切民族地位一律平等,反对任何民族享有特权;主张和坚持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语言文字及一切社会生活领域内的权利完全平等,并无条件地保护一切少数民族的权利;主张和坚持实现各民族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事实上的平等,即不仅要在法律上对民族平等要有明确的规定,而且要在实践中加以实施和保障;主张和坚持一国之内的各民族都应该平等地履行相同的义务”(1)。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民族平等观指导下的中国民族史学、中国民族理论研究,形成了各民族共创中华的“民族关系史观”。主张“我国各民族在历史上既有和平与交流,也有对立与战争,但民族关系的主流是各民族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团结越来越巩固,最终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奠定了现代多民族统一国家的认同基础”(2)。“这一理论避免了大汉族主义的偏颇和同化论的局限,既全面反映了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进程,也抓住了这一进程的主要趋势,尊重历史,符合现实,为现代中国的国家认同提供了坚实的客观历史基础,因而是较汉族中心论更为优长的中华民族理论。”(3)
与上述汉族是中国“主体民族”观念相对应,我们在边疆民族地区的实地调研中发现,在人口快速流动的现代化浪潮中,双向人口急速流动正在解构传统的民族地理分布结构。在各种争议中,民族地区的去“主体民族”化也在悄然发生,与正在发生的现代化同频共振。但仍然有一些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公民表达出“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是自治地方“主体民族”的意识,并显示出对这种“主体民族地位”的某种追求。到底什么是自治民族的主体地位?是不是有超越其他民族公民之上的主导地位或更多的权利?调研中受访的人士并没有给出明确的诉求。
在民族区域自治法中,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各项制度安排,通常使用“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比如,“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中,除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代表外,其他居住在本行政区域内的民族也应当有适当名额的代表”,“自治区主席、自治州州长、自治县县长由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公民担任”。
这种表述明确告诉我们,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赋予某些民族实行区域自治的权利,但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不等于主体民族,没有超越法律规定的高于其他民族的特权。在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各民族公民一律平等,民族区域自治不是某个民族独享的自治,民族区域自治地方更不是某个民族独有的地方。各级自治地方戴了民族的“帽子”,就要这个民族担负起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更大责任。在自治地方,各民族享有平等的法律地位。因此,无论在法律层面还是政策层面,都没有“主体民族”表述 ,也不存在主体民族。
在国际视野中,“主体民族”建构论,往往被看成是大民族“同化论”的翻版,也正因为如此,“主体民族”概念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诟病。从世界各国处理民族多样性的普遍方式看,尊重多元文化,强调公民权利平等,建设“公民国家”,而不突出“主体民族”性,是各国普遍的选择。比如,哈萨克斯坦独立初期,一度强调哈萨克“主体民族化”,但很快意识到这种“主体民族”话语的缺陷。进入21世纪,哈萨克斯坦正式放弃“主体民族化”,全面建构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哈萨克斯坦人”意识(4)。我们国家从梁启超提出“中华民族”,到费孝通论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再到党的十九大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是对汉族作为中国“主体民族”的否定,也是对自治地方某个民族的“主体民族”地位的否定。
今天,国内大多数学者也都自觉摒弃“主体民族”论,“就像我们不能把中国说成是汉人国家(Han—Chinese State)一样,我们也不能把新疆、西藏、内蒙古、宁夏、广西说成是维吾尔族的、藏族的、蒙古族的、回族的和壮族的单一族群的自治地方”(5)。现实生活中尽管“主体民族”话语不是主流社会思潮,更不是法律和政策话语,但潜在的“主体民族”意识时而会显现出来。这种意识既不符合中华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客观历史——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民族及其先民共同开拓了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共同创造了悠久的中国历史、灿烂的中华文化,共同缔造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这一过程中结合成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也不符合各民族之间“地理分布上的交错杂居,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谁也离不开谁”的现实格局。特别是有些人的“主体民族”意识,还隐含了某种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思想倾向,很容易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进行政治性动员。“疆独”“藏独”就是典型的“主体民族”极端化误读的表现。因此,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导民族意识形态话语建构,需要摒弃各种似是而非的“主体民族”话语。
二、 重构“跨境民族”话语
我们知道,中华民族具有政治性和文化性两个属性。政治性主要表现为,作为“国家民族”(6)的中华民族,指的是全体拥有中国国籍的中国公民共同体,不仅包括大陆范围的中国公民,也包括港澳台、侨居国外的中国人,“在世界各地有几千万海外侨胞,大家都是中华大家庭的成员”(7)。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包括五部分人的伟大复兴:全国各族人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海外侨胞。铸牢这五部分人的中华民族意识,目的是团结一心、共同奋斗,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这就是说,中华民族不包括原来拥有中国国籍、现在加入其他国籍的华人。这些人有的生活在国外,有的可能生活、工作在中国境内,虽然他们心向祖国,但已经不拥有中国国籍。这些人加入住在国国籍后,作为住在国公民,根据入籍国家的法律规定,对入籍国家承担公民责任和义务,不再对中国这个“祖国”承担公民责任和义务。他们在公民意义上不属于中华民族成员(8),这是由中华民族作为“国族”的政治属性决定的。
中华民族还有文化属性,主要指所有传承中华文化的族群文化。加入其他国家的华裔族群,特别是移民后获得住在国国籍的第一代华人,对原来的“祖国”还有很深的感情,他们的社会交往、心理认同还不能完全与中国分开,中国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事情,都会在他们身上有所体现。他们对加入国籍的国家文化认同,以及入籍国主流社会对他们的文化接纳不是一两代人可以完成的。因此,他们以中华文化为纽带相互抱团,逐渐形成华裔族群。有的华人社区传承了中华文化,但这些“唐人街”文化,已经或正在经历与所在国异质文化相互交融后的重构历程。有中华传统文化部分形式,但由于祖国的中华文化也正在经历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所以,其他国家的华人族群文化与祖国的中华文化已经分殊化,世界各地的“唐人街”文化只能是中华文化的一块碎片,不能等同于中华文化。
同理,中国境内边疆地区有些少数民族,由于各种原因,分布在国境线两侧,学者们把他们称为“跨境民族”(9),比如蒙古族、哈萨克族、朝鲜族和俄罗斯族等,中国大约有30多个这样的民族。分布在中国境内、拥有中国国籍的这些少数民族成员,他们作为中国公民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一员,他们的文化也在与中华文化交流交融中逐渐具有了中华文化的特质。文化人类学对这种现象称为“文化涵化”(10),说的是一种文化进入另一种文化环境中,经历了文化重组。在中华文化沃土中成长起来的中国边疆各民族文化,经历了中华文化的全面洗礼,已经成为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地缘因素,这部分群体的政治立场、社会文化生活往往遭到来自国境线另一侧的影响。铸牢这部分群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于边疆的稳定、国家的长治久安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意义重大。但理论研究中常用跨境民族历史、语言、文化习俗、宗教等话语叙述,将境内外这些族群整合在一起,用“跨境民族”指称,强调同根同源,隐含境内外文化心理认同。这种“跨境民族”话语对这些边疆少数民族如何融入中国社会、在文化习俗方面的中华文化化,如何承担中国公民的法律责任与义务等等方面的关注度还很不够。宣传报道层面关于这些族群的跨境话语叙述,往往强调跨境特色在内外交往中的作用,对这些族群与我国各族同胞一起共同抵抗外敌入侵、投身中国革命和建设、共同致力于中华民族整体发展的叙述也重视不足。这些重要的历史事实,常常由于过于强化“跨境民族”而显得黯然失色。
这种“跨境民族”受境内外两种力量的影响,两种力量的作用力来自不同方向,甚至是来自完全相反的方向,会引导这部分群体的心理认同走向不同的方向。台湾学者吴启讷指出了大陆民族理论关于“跨境民族”话语的风险(11)——强化“跨境性”,淡化“中华民族”性,有可能冲击这些民族从内心深处生发出“中华民族大家庭一员”的心理认同。今天我们要在边疆少数民族群体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必要重新审视“跨境民族”话语,加大对这部分群体社会生活、文化习俗的中华文化化研究,将“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作为这些民族(族群)研究的叙事前提,围绕这个前提重构学术话语体系。并在宣传报道和政策实践上弱化这种跨境意识,强调中国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强化中华民族意识,通过缩短文化距离,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心理认同。
事实上,作为中国公民,这些民族毫无疑问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一员。作为文化群体,无论是传统上世代居住中国境内的蒙古族,还是近代陆续迁入中国的朝鲜族、俄罗斯族,都经历了中华文化化历程。特别是在百余年来投身中国革命和国家建设的历程中,无论是公民个体还是族群整体,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方面都与境外的同一族群走向分殊化。“跨境民族”话语不仅在理论结构上是不严谨的,而且在实践指向上强化跨境性,很容易成为国家建设的隐形消极因素。
国际范围时起时伏的泛民族主义思潮是典型的“跨境民族”政治化。如要求蒙古国与中国、俄罗斯联邦的蒙古人聚居区合并的“蒙古统一”运动,其基点是主权独立的蒙古国;哈萨克斯坦的“哈萨克斯坦回归”运动,内容是“主体民族”号召“同胞”回归“历史祖国”;“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思潮,已经成为“疆独”政治动员的理论依据。显然,“跨境民族”话语,对于中国国家建设是有风险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亟需重构这种似是而非的“跨境民族”话语。
三、建构“中华文化是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话语
自从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命题后,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主体,建设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成为新时代文化建设的重要使命。在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论述了中华文化与各民族文化的关系。他说,中国有五千年文明史,各民族及其先民共同缔造祖国悠久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今天的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兼容并蓄的共同体,把汉族文化等同于中华文化是错误的,把本民族文化自外于中华文化也是错误的;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由于种种复杂因素,人们对中华文化认识还有诸多偏差,对中华文化作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也有潜在的抵触。最典型的表现是,有的人将中华文化窄化成传统文化,甚至窄化成儒家文化;还有的人自觉不自觉将汉族传统文化等同于中华文化,将少数民族文化自外于中华文化;或者将蒙古、哈萨克族等所谓的“跨境民族”文化自外于中华文化。有人认为,作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中华文化,指的是各民族文化共同性内容,不包括个性内容。有人认为,我国各民族群众信仰的伊斯兰教文化不是中华文化一部分,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等传统文化内容不属于中华文化。还有的人看不到56个民族文化之间的有机联系,认为中华文化就是56个民族文化的总称或总和,56个民族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加在一起就是中华文化。
我们认为,以上种种中华文化观都有偏差。 “不能想象,一个民族文化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层面属于中华文化,传统的民俗文化层面不属于中华文化。而把56个民族文化简单加在一起解读中华文化,淡化或忽略各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兼容并蓄性,割裂了各民族文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有机联系,实际上虚化了中华文化。”(12)
中华文化是古往今来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各民族及其先民共同创造的,是各民族文化兼收并蓄的文化共同体。从历史阶段划分包括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2016年“七一”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阐释了中华文明的结构并指出,在五千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这就表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各民族先辈投身中国革命缔造的革命文化,以及当代各族公民共同缔造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精粹。这也表明,在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新时代,“民族文化”边界日益模糊,通常所谓的民族文化,主要指表现在居住、饮食、婚姻、丧葬、礼仪、节庆习俗层面,以及各民族语言文字作为载体的多媒体层面。这实际上是各民族传统文化,不是各民族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创造的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的“新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当代形式,是各民族传统文化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实现的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主要表现为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载体的,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思想的,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道路、制度为主要表现形式的中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就是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华文化的繁荣发展既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条件,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标志。“而中华文化是中国各民族文化之集大成,也就是确立反映全国各族人民共同认同的价值观‘最大公约数’,这是最深层的认同。从这个意义上说,构成中华文化的各民族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一个也不能少’的要素,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一个也不能少’的动力。”(13)
2019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时再次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各民族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共同努力奋斗。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中华民族走向包容性更强、凝聚力更大的命运共同体,共建美好家园,共创美好未来。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让我们深刻地体会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应该重点关注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去中国化”意识、去“中华文化”化意识,铸牢各族同胞共同当家作主权利义务意识,铸牢各族同胞“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经济利益共同体意识,铸牢各族同胞“互相嵌入式”社会共同体意识,铸牢56个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命运共同体意识。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目标的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有必要重构民族宣传话语,建设整体叙述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态话语体系。
注 释:
(1) 参见:杨须爱.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自信——基于对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西方多元文化主义民族政策的几点比较[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6).
(2) 此一观点的代表性论述可参见:翁独建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一书的绪论部分。这一民族关系史的中华民族历史叙事模式明确表明要抛弃汉族中心的中华民族史观,而从中国历史上各民族在普遍而日趋密切的联系发展过程中共创中华民族的角度来叙述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可参见:苏航.“汉族中心”还是“汉族核心”: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新探——兼评新清史的内亚王朝史观[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社科版),2019(9):16.
(3) 参见:苏航.“汉族中心”还是“汉族核心”: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新探——兼评新清史的内亚王朝史观[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社科版),2019(9).
(4) 参见:李琪.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民族政策取向:从“主体民族化”到“国家民族”之构建[J].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1):85-92.
(5) 转引自:沈桂萍.当代中国特色民族与宗教政策创新研究[M].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14:170.
(6) 原载郭正林(中山大学),余振(香港浸会大学).族群意识与国家认同:新疆维汉关系问卷分析[EB/OL].香港中文大学网站/中国研究服务中心,http://www.usc.cuhk.edu.hk/PaperCollection.
(7) 参见:周平.民族国家与国族建设[J].政治学研究,2010(3):85-9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63.
(8) 参见:李旭东,牛雅婷.【暑期学校】郝时远教授访谈录[EB/OL].(2019-08-04)[2019-05-10]“人类学之滇”公众号.
(9) 跨境民族指“在漫长历史时期中形成的、现阶段被国家边界所区隔,分布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交界地区,毗邻而居的同一民族”。参见:施琳.何以为邻——“跨境民族”之关键概念辨析与研究范式深化[J].西亚非洲,2019(3):39.
(10) 文化人类学理论中的文化涵化(acculturation),也译作“文化摄取”、“文化本土化”、 “文化本色化”。指的是由于文化接触而形成的文化融合、文化交流的情况。参见:庄孔韶.人类学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290.
(11) 参见:吴启讷.“跨境民族”与中华民族的建构[J].文化纵横,2017(6):115-116.
(12) 参见:沈桂萍.讲清楚中华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社会主义学院工作条例》学习体会[N].中国民族报,2019-02-01(005).
(13) 参见:郝时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民族工作[J].民族研究,2017(06):1-11+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