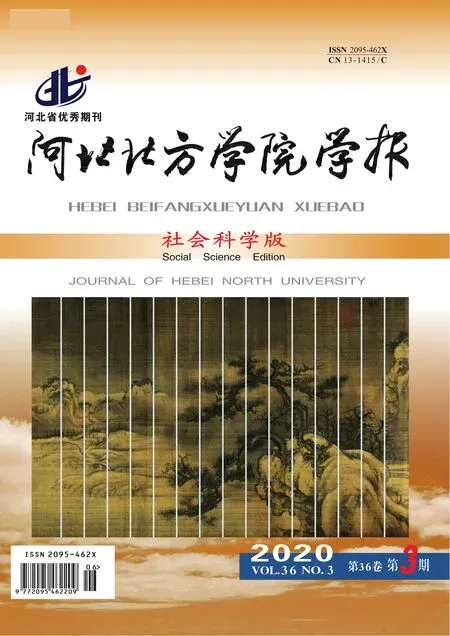钱玄同汉字改革思想刍议
2020-01-16和笑寒刘晓明
和笑寒,刘晓明
(1.河北北方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北 张家口 075000;2.河北北方学院 文学院,河北 张家口 075000)
近代汉字改革运动肇始于清代,对20世纪以来的中国社会影响深远。钱玄同自青年起濡染其中,并将此作为毕生追求且建树丰盈。但其对汉字改革的方向、具体方针及举措的态度并非一以贯之,期间经历过几次较大的思想转变。自清末受老师章太炎的影响关注汉字改革起,到民国二十四年(1935)草成《第一批简体字表》的近30年间,对汉字的拼音化、国语罗马字的创制和简体汉字的字源取舍等问题,钱玄同的思想历程表现出由理想到务实的循序渐进的转变。这些思想上的改观一方面是其本人对研究问题的不断精进深入而发生蜕变所致,另一方面也是当时中国思想界与文化界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诸多思辨起伏的真实映照。
一、钱玄同的早期汉字改革思想
光绪三十二年(1906),钱玄同入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师范科,同年于东京拜会章太炎,对其学说大为折服并自称学生,遂成章门入室弟子。此时,章太炎正在日本举办“国学讲习会”,并讲授中国传统文化与改良课程,堂下门客学生接踵于道,钱玄同在其中颇受器重[1]。章太炎身兼清末民族民主革命领袖与古文学术大家的双重身份,其学术思想自然充斥着丰盈的民族主义色彩。对待汉字改革,章太炎力主改革的首要目的是促进教育与开化国人。这与自甲午战败以来国内的主流汉字改革主张一脉相承,皆认为中国国民文化不发达的主要障碍是汉字繁难,致使民众识文者寡。若使民众普遍接受先进思想与技艺,必须能读书识字。而改进汉字,使其简单易学就成为最切实的紧要。章太炎认为,汉字依托自身稍加改良就可以弥补其在识认与使用上存在的各种弊端。在增强汉字的简易度方面,“欲使速于书写,则人人当兼知章草”[2]110。章草字体为旧草书,笔划简约,易书写,其缺点是潦散难辨。为解决这一问题,章太炎补充道:“若欲易于察识,则当略知小篆,稍见本原。”[2]111在他看来,篆字为初识字者的门径,因“日、月、山、水诸文,婉转悉如其象……一见字形,乃如画成其物……凡从鱼之字,不为鱼名即为鱼事;从鸟之字,不为鸟名即为鸟事,可以意揣度得之”[2]111。解决了汉字易写与易辨的问题后,章氏还指出应建立一套“审音之术”,编排36个声母,22个韵母,“皆取古文,篆(小篆)、籀(大篆)径省之形,以代旧谱,既有典则,异于乡壁虚造所为,庶几足以远行”[2]112。钱玄同颇为推崇章太炎的汉字改革方案,认为章的观点乃是“天经地义”,“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3]。钱玄同也认同汉字改革应立足于本国文化之根本,万不能引外来新语言代替国语。他强调:“愚谓立国之本,要在教育,果使学术修明,必赖文字正确……文字一灭,国必致灭亡……我国文字发生最早,组织最优,效用亦最完备……夫文字者,国民之表旗,此而摒弃,是自亡其国也。”[4]73由此可知,钱玄同当时对汉字改革的认知源出其师,“保存国粹”是他早期汉字改革观的核心要义。
戊戌维新运动失败后,以吴稚晖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主张废除汉字,用所谓“万国新语”①代替;劳乃宣与王照等人虽不同意废除汉字,但拟自发创造一批简易“切音字”并推行使用。然而,钱玄同不认同这两种作法。对此,他提出自己的汉字改革主张——“废楷用篆”。即:在书写方面,“字必以篆为主,若必作隶,必宜改从篆体作楷”,间或以草书与隶书为补充。“至于四体之中,无论作何体,总不能写《说文》以外之字。”[5]159在音韵方面,不可不复古,赞成以《广韵》为标准读音。由此可见,钱玄同当时并未脱离章太炎汉字改良的整体思路。“(我)比太炎先生还要顽固得多……以为国故本身都是好的,凡非汉族的都是要不得的,凡是汉族的都是好的……同是汉族的之中,则愈古愈好。”[3]钱玄同赞赏明代儒家所提倡的“复三代古音”,不仅把汉字与汉语复于明代,且将复于汉唐,甚至复于三代。
二、从“发扬国故”到“汉字革命”的思想转变
结束在日本的学习后,钱玄同于宣统二年(1910)回国,先后在浙江嘉兴与海宁等地教书。这一时期,他在学术领域逐渐脱章而自立。宣统三年(1911)初,钱玄同在浙江吴兴谒见今文经学家崔适,并在其建议下学习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等著述。之后,钱玄同坚定地相信之前学习的古文经学实为刘歆所伪造这一论断[6],并重新审视所谓旧文化体系在国家中的地位与价值。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的专制政体,使原有的民族革命失去了革命的对象。但民国的建立并未将旧文化、旧思想、旧传统以及旧道德一并剪除,这些“旧”反被划入“国粹”的行列,并被认为是排满之后恢复华夏与发扬种性的矩矱。这一现实使钱玄同的认知判断从质疑古文经学发展到对儒家文化的全面质疑:盖经中所言尧、舜、禹、汤、文、武之圣德,诚多孔子所托,非必皆为事实,然必有其义[5]199。他指出,尧舜实则是上古人想象出来的,后被孔子等利用来“托古改制”,这其实早就被韩非戳破,只不过汉代以后的学者将错就错,把这些“伪事”当作信史传递迭代,以至遗祸[7]。既然圣贤皆是人为臆造出来的,那么中国的整个儒学体系就等同于建立在谎言的基础上,中国士大夫恪守了两千年的所谓“国故”“国史”及“国粹”也自然失去公信而沦为谬谈。钱玄同渐渐认识到长期根植在国民心中的守旧迂古的思想对民族与国家实有大害,是造成中国百年来裹足不前的症结所在。“你看满清入关的时候,一般读书人依旧高声朗诵他的《四书》《五经》八股及试贴。那班人的意见,大概以为国可亡,种可奴,这祖宗传下来的国粹是不可抛弃的。”[8]真正促使钱玄同与旧学术体系决裂,并毅然决然走上“废孔学”与“剿道教”的激烈反传统之路的导火索是民国五年(1916)的洪宪复辟。“因为袁世凯造反做皇帝,并且议什么郊庙制度,于是(我)复古的思想为之大变。”[5]126钱玄同认为,民国肇造已经把中国推进到了国家社会的层面,若继续任由宗法社会的旧文化“绳民国的国民,则真是荒谬绝伦”[9]。他后来回忆道:“玄同自丙辰春夏以来,目睹洪宪皇帝之返古复始,倒行逆施,卒至败亡也。于是大受刺激,得了一种极明确的教训。知道凡事总是前进,绝无倒退之理……故治古学,实治社会学也,断非可张保存国粹之招牌,以抵排新知,使人人褒衣博带,做二千年前之古人。”[10]因此,至民国五年(1916)年末,“钱玄同已经完全放弃了保存国粹的主张。当他看到胡适倡导文学革命之后,立即投书《新青年》,以一个古文大家而支持文学革命,由一个革命派中的保存国粹主义者,一变成为新文化阵营中的冲锋陷阵的勇士”[11]。
从民国六年(1917)起,钱玄同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频频向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投稿。也正在此期间,他提出著名的打倒“选学妖孽,桐城谬种”的口号,亦明确了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革命对象,即旧文学与旧文字。钱玄同最早向《新青年》建议杂志所刊文章应一律改成左行横排排版,之后又鼓励杂志编者大胆尝试白话文,要做“白话文章的试验场”[12]。民国七年(1918),钱玄同成为《新青年》的轮流编辑人之一。依托该新文化运动的主阵地,他进一步提出更为激切的“汉字革命”理论。首先,废除汉字,代以世界语。钱玄同在民国七年(1918)3月4日致陈独秀信中提出:“中国文字论其字形,则非拼音而为象形文字之末流,不便于识,不便于写;论其字义,则意义含糊,文法极不精密;论其在今日学问上之应用,则新理、新事、新物之名词,一无所在……此种文字,断断不能适用于二十世纪之新时代……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与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4]171对废除汉字后的入替者,钱玄同力主使用曾被他所排斥的“世界语”②。他认为“世界语”是属于全世界人民所通用的语言文字,而不似其他文字仅囿于某一族群,使用“世界语”是最简便且最迅速地使中华文化融入于世界的方式[13]。其次,废除文言,代以白话。钱玄同认为自己从幼年起受了20年的腐朽教育,是一个纲常伦理压迫下的牺牲品,并指出《四书》《五经》《参同契》与《黄庭经》一类古文会让青年学子“觉其句调铿锵,娓娓可诵,不知不觉,便将被其文中之荒谬道理所征服”[13]。对于被奉为古文经典的“十三经”,钱玄同批评它们是不伦不类且杂七杂八的“怪物”,只不过是13本古代的书而已[14]。他亦曾对刘半农讲,中国的旧文旧字只有送进博物馆这唯一一点价值[15]。但直到新文化运动勃兴后,全国小学儿童的教科书依然使用文言文。钱玄同对此极为不满,遂于民国七年(1918)因公推而担任中国首次“国语教科书编辑会议”的编辑主任,并亲自编写白话文教科书。后北平孔德小学改用的白话文教材,开头两册就是钱玄同亲撰[12]。此后,他进一步明确提出:“(我)不仅主张用白话文来做初级教育和通俗教育的教科书,尤其主张用彼来著作学理深邃的书籍。”[4]212再次,创制“国语罗马字”,将其作为彻底废除汉字前的预备性文字。钱玄同从务实的角度认识到,汉字即便将来可以废除,但汉语不可能一时尽废,在废汉字与废汉语之间必须经由一个过渡阶段。“汉语一日未废,即一日不可无表汉语之记号,此记号,自然以采用罗马字拼音为最便于写识。”[4]170“中国拼音字用了罗马字母,采用西文原词,真如天衣无缝,自然熨帖。”[4]171民国十一年(1922),钱玄同发表《汉字革命》一文,对“汉字的罪恶”大加挞伐,同时再次申明使用“国语罗马字”来拼写汉语是最为可行的“补偏救弊”的盛举[16]。
三、专事推进汉字简化运动
“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场文化激进主义的风暴,钱玄同作为主将深耕其中。但这场风暴逐步偃息后,钱玄同的思想也随之归于理性,这促使他的汉字改革思路再一次发生转变。钱玄同反思了“汉字革命”的根本目的终究还是要促进中国的现代化教育,要使国族与社会从教育事业中获益。“教育是教人研求真理的,不是教人做古人的奴隶的;教育是改良社会的,不是迎合社会的;教育是教人高尚人格的,不是教人干禄的。”[17]由此可知,钱玄同不再主张激进的实用主义观点,而是寻求一条更具可行性的改革之路。正如他在《减省汉字笔画的提议》中所言:“我以为拼音文字,不是旦暮之间就能够制造成功的,更不是粗心浮气,乱七八糟把音一拼,就可以算完事的……这拼音新文字的施行,总还在十年之后。如此,则最近十年内,还是用汉字的时代……既然暂时还不得不沿用汉字,则对于汉字难识难写的补救,是刻不容缓的了。”[4]212
“五·四”运动后,钱玄同将大量精力放在推行简化汉字上。他提出,汉字拼音化是汉字改革的治本之法,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是治标之法。治本固然重要,“但现行汉字在学术与教育上作梗,已经到了火烧眉毛的地步,不可不亟图补救的办法。我们不能等拼音的新汉字成功了才来改革,所以治标的办法,实是目前最切要的办法”[18]。钱玄同一方面明确提出汉字改革的方针与举措,另一方面着力于汉字改革的亲躬实践。从民国十二年(1923)起,钱玄同潜心编纂《国音常用字汇》,积10年之功至民国二十一年(1932)始成。此乃中国汉字改革史上的大举,为之后经年屡次探索的汉字简化方案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与借鉴。民国二十三年(1934),国民政府教育部委托钱玄同起草“简体字谱”。钱受托后在第二年(1935)6月编成《第一批简体字表》,共捡选简化汉字2 300余个。他在给黎锦熙与汪怡的信中申明其编辑“简字之原则”:“所采之材料,草书最多,俗体次之,行书又次之,古字最少……所集之体,字字有来历,偏旁无一字无来历,配合之字,或间有未见如此写法者,然亦必一见可识,绝无奇诡之配合。”[19]
民国二十四年(1935)8月21日,中华民国教育部向全国公布《简体字表》,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批由政府颁行的规范简体字,也成为后继的汉字简化事业的样板与基础。
晚近中国激扬百年的汉字改革历程是整个华夏文明向现代化踽步前行的缩影。文字作为文明的最忠实载体,其绵亘最久、表达最利、识辨最易而变更最缓。脱胎于中国数千年农耕文化的象形汉字,若要在形、义与音等方面进行全面改革以使其具有国际观瞻,何其难也。然戊戌以来,中国的语言学家迎难而上,且能够在汉字改革事业中有所收获并开基立业,钱玄同无疑是其中举足轻重的一位。钱玄同是思考者更是行动派,其汉字改革思想每每蹙乎急转又间杂自我否定,他每一次的思想转变都会落实到实际行动中,而这些落实恰恰是时至今日汉字使用中的诸般现状。对钱玄同汉字改革思想的梳理还需经过较长的时间沉淀才能更加清晰,但这并不妨碍研究者努力在现阶段进行一些有益的尝试。
注 释:
① 即世界语。由波兰人拉扎鲁·路德维克·柴门霍夫于1887年发明。
② 钱玄同有时用“新体国文”这一称呼来代替“世界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