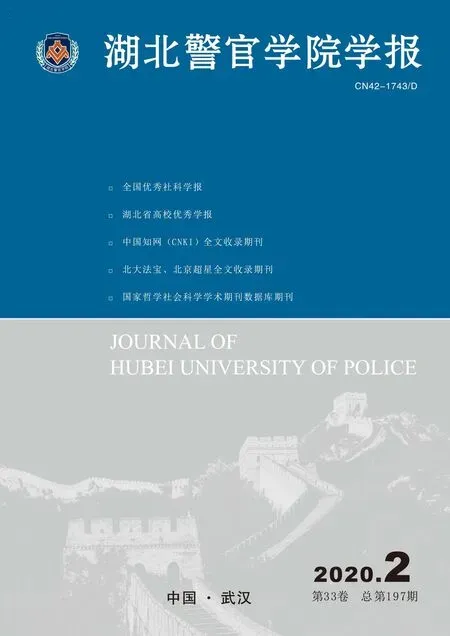碳排放权交易的监管主体之比较研究及对我国的启示
2020-01-16闪涛
闪 涛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湖北 武汉430073)
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碳排放权交易作为一种行之有效的环境治理方式,普遍被英国、美国等发达国家以及欧盟、联合国等国际组织采用。其在实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环境目标方面取得了积极效果,我国也于2012年正式启动了碳排放权交易的试点工作。在碳排放权交易领域的研究工作中,许多学者从经济、政治等方面作了大量基础性研究,法学领域研究主要关注碳排放交易制度中的具体制度设计方面,鲜有从监管主体角度去探讨。碳排放权交易要获得有效实施,一方面有赖于规则的设计和制度的建立以促成市场的形成以及价格的发现,另一方面取决于监管机构的监督与管理。监管主体的设置是碳排放权交易获得顺利实施及取得良好效果在组织上的保障。碳排放权交易并非自发形成的市场化交易,而是政府综合运用行政手段与市场手段人为“孵化”出来的交易与市场。因此,监管主体的设置将直接影响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运行。鉴于此,本文通过比较研究英国、美国以及欧盟在碳排放权交易中监管主体的设置,结合我国的监管主体现状,探讨我国碳排放权交易监管主体在设置上的现实合理性以及进一步改革的必要性,为我国碳排放权交易监管体系的进一步完善提供思路。
一、碳排放权交易监管主体设置的国际经验
(一)英国碳排放权交易的监管主体
英国碳排放权交易的实践以英国《气候变化法》(Climate Change Act 2008)的出台为标志,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气候变化法》出台之前,英国已经于1998年始开始施行碳排放权交易制度(UK Emissions Trading Scheme);自2008年11月26日《气候变化法》实施,英国的碳排放交易制度开始和欧盟的碳排放交易制度进行融合与对接。因此,英国在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监管主体上亦呈现出相应的调整。
1.第一阶段的主要监管主体
第一阶段的主要监管主体有二:(1)环境、食品与农业事务部(Department for Environment,Food and Rural Affairs)。该部门为英国的内阁部门(a ministerial department),隶属于英国的最高行政决策机构——内阁,由内阁的国务大臣领导,享有完整的行政决策权,主要负责有关英国环境、食品及农业事务的政策与法规的制定。①https://www.gov.uk/government/organisations/department-for-environment-food-rural-affairs/about,2019年6月15日访问。在1998年开始的碳排放权交易实践中(正式交易自2002年开始),其负责制定各类碳排放权交易的规则性文件,其中最主要的是《UK Emissions Trading Scheme-Consolidated Scheme Rules》。②http://webarchive.nationalarchives.gov.uk/20090908171815/http://www.defra.gov.uk/environment/climatechange/trading/uk/pdf/trading-consolidated.pdf,2019年6月15日访问。(2)环境署(Environment Agency)。环境署为“执行性的非部委公共机构(Executive Non-Departmental Public Bodies)”,对环境、食品与农业事务部负责,③http://www.environment-agency.gov.uk/aboutus/default.aspx,2019年6月15日访问。但其权力来源于1995年的《环境法》,享有与环境保护相关的各种监管与行政权能。④http://www.legislation.gov.uk/ukpga/1995/25/contents,2019年6月15日访问。在碳排放交易制度中,其是碳排放交易规则的执行者和监管者,职能与权限包括对加入碳排放交易的主体进行行政指导、碳排放的许可及配额的发放、碳排放的监测以及对违反规则的处罚。⑤http://www.official-documents.gov.uk/document/hc0506/hc02/0201/0201.asp,2019年6月15日访问。
在上述监管机构中,环境、食品与农业事务部是碳排放权交易的主管部门,监管为其职能之一,具体监管事务交由环境署及其下属机构执行。
2.第二阶段的主要监管主体
第二阶段的主要监管主体有二:(1)气候变化委员会(Committee on Climate Change)。经过1998年至2008年英国在碳排放权交易方面的实践,英国在2008年出台《气候变化法》,在监管主体方面的变化之一便是成立了一个独立于政府部门的气候变化委员会(Committee on Climate Change)。对于其职责和权限,《气候变化法》第二部分给予了专门规定:一方面是就应对气候变化以及相关减排措施为政府部门提供专业性的意见,另一方面是就政府及其部门对其已经制定的各项减排目标以及措施的落实与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根据气候变化委员会2008年至2009年的年度报告,其具体职责包括:其一,为英国碳预算的水平提供建议,该建议将对自2008年至2012年英国每5年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的最大排放水平进行定义;其二,评估政府在实现气候变化目标方面的进展并向议会提交年度报告;其三,根据英国政府或其授权部门的请求,在与碳预算有关的方面从科学、经济与政策等角度对气候变化进行独立的分析;其四,对英国气候变化风险评估和政府适应性计划的准备工作进行检查;其五,与对气候变化感兴趣的个人与组织分享各种成果;其六,对英国议会、能源与气候变化部部长及爱尔兰、苏格兰和威尔士的环境大臣与部长负责。⑥http://www.official-documents.gov.uk/document/hc0809/hc07/0732/0732.asp,2019年4月15日访问。(2)能源与气候变化部(Department of Energy&Climate Change)。能源与气候变化部于2008年成立,主要是将环境、食品与农业事务部中气候变化管理的工作和商业、企业和管理改革部(Department of Business,Enterprise and Regula-tory Reform)中的能源管理工作合并而成立的新的部门,用来提高气候变化政策与能源政策的协调与适应性并提高行政效率。①http://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1827182,2019年6月15日访问。其主要职责涉及能源安全、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可再生能源等诸多方面。②https://www.gov.uk/government/organisations/department-of-energy-climate-change/about#corporate-reports,2019年6月15日访问。根据能源与气候变化部近几年的年度报告,在控制碳排放以及碳排放权交易方面,其对内行使能源与环境领域的行政管理职能,对外执行欧盟有关气候变化及减排方面的政策与制度,其中包括将欧盟层面的碳排放权交易规制转化为国内法律。
在上述监管机构中,气候变化委员会凭借其独立性与专业性加强了碳排放权交易的实施力度与监管力度,能源与气候变化部更加集中地行使碳排放权交易的行政管理职权,其中的监管职责交由其下属机构完成。
3.其他监管主体
非盈利组织UKE missions Trading Group于1999年应英国政府的要求而建立,旨在建立被监管企业与政府之间对话、沟通和交流的平台,并协助英国政府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推进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实施:(1)英国碳排放交权交易计划第二阶段与第三阶段的实施;(2)监测、报告、核证以及认证;(3)金融、国际机制与链接;(4)英国气候变化协议;(5)碳减排能效计划。作为非盈利的公共组织,其在监测、报告、核证及认证的过程中实际上履行了部分监管职能。成立10余年来,UKE missions Trading Group不仅成功协助英国政府实施国内的碳排放权交易计划,也成功指引英国的碳排放权交易计划与欧盟的碳排放权交易计划进行对接。③http://www.etg.uk.com/,2019年6月17日访问。
(二)欧盟碳排放权交易制度中的监管主体
1.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
欧盟委员会是欧盟处理日常事务的常设行政机关,为独立于成员国政府之外的欧盟超国家政治机构,代表和维护欧盟整体利益而非某一或若干成员国的利益。欧盟碳排放交易制度的产生与发展主要归功于欧盟委员会在气候变化与环境保护方面卓有成效的工作。
首先,从组织机构的角度讲,狭义上的欧盟委员会由成员国各委派一名代表组成,现有27名成员。除欧盟委员会主席外,26名副主席和委员(Commissioner)各负责一个政策领域,其中包括一名负责环境事务的委员。其次,欧盟委员会下设三大类共计36个“总司”(Directorates General,DG),其中包括1973年成立的环境总司(DG Environment),职责是为欧盟委员会提供环境保护方面的立法建议,保证欧盟环境法切实得到遵守并纠正成员国违反欧盟环境法的行为,必要时可以提起诉讼。同时,环境总司下面一共聘请了31个非政府组织性质的团体。④http://ec.europa.eu/dgs/environment/index_en.htm,2019年6月17日访问。最后,为了更有效地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以及参与和协调在气候方面的国际事务,欧盟委员会于2010年2月又成立了气候行动总司(Directorate-General for Climate Action,DG CLIMA)。⑤http://ec.europa.eu/dgs/clima/mission/index_en.htm,2019年6月17日访问。
从工作内容上来看,欧盟委员会主要在以下两项工作中推动了碳排放交易制度的建立:一个是环境行动规划。迄今为止,在欧盟委员会的建议下,欧盟自1973年起总共制定了六次环境行动规划。其中,《第五个环境行动规划》提出了通过市场手段来实现环境保护的目标,《第六个环境行动规划》进一步明确了市场手段的运用,①http://ec.europa.eu/environment/newprg/archives/intro.htm,2019年6月17日访问。这为碳排放交易制度的建立提供了充分的政策依据。同时,为了落实《第六个环境行动规划(2002-2010)》,欧盟委员会的环境总司自2000年启动《欧洲气候变化规划》(European Climate Change Programme,ECCP)。该规划的参与方包括欧盟委员会的相关部门、成员国政府部门、工业、环保组织和科研单位的代表。该规划分成11个工作组,其中一个工作组即为“Emissions Trading”,②http://ec.europa.eu/clima/policies/eccp/first/index_en.htm,2019年6月17日访问。并提出了建立碳排放交易制度的立法动议。③Proposal for a DIRECTIVE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establishing a scheme for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allowance trading within the Community and amending Council Directive 96/61/EC。
2.欧盟理事会(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欧盟理事会又被称为部长理事会,为欧盟的决策机构,拥有欧盟绝大部分的立法权。欧盟理事会除了“总务和对外关系理事会”外有8个专门理事会,其中包括“环境理事会(Environment Council)”。
对于欧盟的环境保护事项(环境政策、法规和规划等),欧盟理事会具有全面和决定性的影响与作用。其与环境有关的职权包括:制定环境法律(条例、指令和决定)、决定国际环境协定的缔结、协调各成员国的环境政策。正是基于前述欧盟委员会的各项提案,欧盟理事会在征询其他欧盟机构的建议后才能作出相关决定。
在环境立法的程序上,欧盟理事会就不同事项分别采取普通立法程序与特别立法程序进行表决。普通立法程序由欧盟部长理事会和议会共同作出决定,从欧盟碳排放交易制度的主体文件——Directive 2003/87/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13 October 2003 establishing a scheme for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allowance trading within the Community and amending Council Directive 96/61/EC中可以看出,欧盟的碳排放交易制度是由欧盟理事会与欧洲议会通过共同决定的形式作出。
3.欧洲议会(European Parliament)
欧洲议会是欧盟的立法、监督与咨询机构。如果说欧盟委员会代表的是欧盟整体利益,欧盟理事会代表的是各成员国政府的利益,那么欧洲议会则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欧洲民众。它是各成员国在遵循共同民主程序和选举日期的原则下,通过各国自行的各种比例代表制和选举方式从所有有被选举权的公民中直接选举出来的。
在环境事务方面,欧洲议会目前主要通过下设的环境、公共卫生和食品安全专门委员会(Environment,Public Health and Food Safety)来履行职责。该专门委员会是所有欧洲议会下设的委员会中享有最广泛的立法性权利的委员会。在碳排放交易制度的形成与运行中,欧洲议会主要通过该机构来审议欧盟委员会提交的各项报告,分析、建议并提出意见。
欧盟委员会、欧盟理事会及欧洲议会从不同角度通过其下的“总司”“工作组”“理事会”和“委员会”等下属机构对碳排放权交易的不同方面进行监管。
(三)美国区域性碳排放交易制度中的监管主体
美国于2001年3月单方面退出《京都议定书》,到目前仍未能在联邦层面建立全国性的碳排放交易制度,但形成了若干个区域性的碳排放交易制度,主要有区域温室气体倡议(Regional Greenhouse Gas Initiative,RGGI)、西部气候倡议(Western Climate Initiative,WCI)、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hicago Climate Exchange,CCX)、加州气候行动注册处(California Climate Action Registry,CCAR)四个区域性的碳排放交易制度。加州气候行动注册处为一州内部的碳排放交易制度,而芝加哥气候交易所是以会员制为基础形成的交易平台和交易制度,且已于2010年12月31日结束交易,在监管主体上并无太大参考意义。在剩余两个区域碳排放交易制度中,区域温室气体倡议的制度最为完整与成熟,故本文仅以区域温室气体倡议为样本进行分析。
2005年12月,美国康涅狄格(Connecticut)、特拉华(Delaware)、缅因(Maine)、新罕布什尔(New Hampshire)、新泽西(Newjersey)、纽约(NewYork)、佛蒙特(Vermont)等 7 个州签订了区域温室气体倡议(Regional Greenhouse Gas Initiative,RGGI)框架协议,形成了美国第一个以市场为基础的区域性限额交易(cap-and-trade)型温室气体排放贸易体系。RGGI是一个以州为基础的区域性应对气候变化合作组织,并没有一个最高的决策机构。2007年9月,RGGI各签署州授权成立一个名为RGGI,Inc.的非营利性公司,任务是为签署州的碳减排计划提供行政和技术服务的支持,具体包括:(1)开发和系统维护以监测排放源的数据,并跟踪二氧化碳配额;(2)运行一个拍卖二氧化碳配额平台;(3)监测有关二氧化碳配额的拍卖和交易市场;(4)为签署州提供在审查申请排放抵消项目的技术援助;(5)为签署州评估和修改州的RGGI方案提供技术援助。因此,其仅享有一定的监督权,即监测拍卖市场和配额的交易。①http://www.rggi.org/rggi,2019年6月23日访问。RGGI碳排放交易规则(Model Rule)的建立、保障与运行,最终取决于各州的政治意愿和政策执行力。
在州政府层面上,首先仍是由州政府向州立法机关提出议案并经立法机关通过方能生效和执行。在完成立法后,各州政府实际上的执行与监管机关为各州的环保行政机构及能源监管机构,如康涅狄格州(Connecticut)的监管机构为The Connecticut Department of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DEEP),②http://www.ct.gov/deep/cwp/view.asp?a=2690&q=322476&deepNav_GID=1511,2019年4月23日访问。德拉华州(Delaware)的监管机构为Division of Waste&Hazardous Substances,③http://www.dnrec.delaware.gov/whs/awm/Pages/aboutagency.aspx,2019年6月23日访问。缅因州(Maine)的监管机构为 The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DEP),④http://www.maine.gov/dep/about/index.html,2019年6月23日访问。纽约州(New York)的监管机构为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⑤http://www.dec.ny.gov/energy/rggi.html,2019年6月23日访问。其他州虽在名称上有所差异,但均为环保行政机构。
因美国联邦政府仍然没有出台全国范围内的碳排放交易制度,所以在联邦政府层面尚无统一的监管机构与监管体系。但有学者指出,未来全国范围内的碳排放交易市场的监管机构将来自于以下机构部门: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U.S.Commodity Futures Trading Commission,CFTC)、证券交易委员会(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SEC)、联邦能源管制委员会(Federal Energy Regulatory Commission,RERC)和环境保护署(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EPA)。
环保组织在推动美国进行碳减排立法上有重大作用。2007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审理马萨诸塞州诉环保署[Massachusetts v.EPA,127S.Ct.1438(2007)]一案中,最终判决原告胜诉,支持了原告关于温室气体是环保署应该规制的空气污染物的主张。而原告则包括了十二个州(马萨诸塞、加利福尼亚、康涅狄格、伊利诺伊、缅因、新泽西、新墨西哥、纽约、俄勒冈、罗得岛、佛蒙特和华盛顿州等)政府、三个州地方政府(波士顿市奥克兰市及芝加哥市)、一个美属领土(萨摩亚群岛)政府和若干非政府组织(包括生物多样性中心、食品安全中心、美国保护法基金会、环境倡导者组织、环保协会、地球之友、绿色和平、国际技术评估中心、国家环境托拉斯、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塞拉俱乐部、科学家联合会和美国公益研究集团)。
因此,在区域层面上,由RGGI,Inc.总体上对参与各州的碳排放权交易进行监管,各州具体的监管职责交由各州的环境保护部门及其下属机构。其他环境保护组织主要通过各种形式的参与对所涉及的碳排放权交易进行监管。
(四)共同特征
通过以上对英国、欧盟及美国在碳排放交易监管机构设置上的介绍可知,碳排放权交易制度产生于气候变化应对,是全球气候变化应对的一个方面。上述国家与国际组织均是在气候变化应对框架下形成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监管体系的,具体体现出以下几个共同特征:
第一,机构的设置具有立法依据。不论是英国的气候变化部、能源与气候变化部、环境署还是欧盟委员会、欧盟理事会及欧盟议会内部设立的环境保护部门以及美国各州的环境保护部门,其成立之始即具有明确地立法上的依据与授权,从而保证了各部门建立及实施碳排放权交易的合法性。
第二,将碳排放权交易作为环境治理的一种措施。英国、欧盟及美国的碳排放权交易的监管部门均为环境保护部门。这是因为英国、欧盟及美国普遍接受了全球变暖或温室效应的主因系人为过度地排放二氧化碳。二氧化碳不再是可以无限制排放的无害气体,而是在过度排放情形下具有有害性的气体。正是基于对二氧化碳与全球气候变化之间的因果关系的认识,限制二氧化碳的排放即为一种环境治理的目标,而碳排放权交易便是为了达到该目标而采取的环境治理措施。既然将二氧化碳归属于环境问题,那么按照政府职能分工的要求,该环境治理职能应主要归属于环境保护部门。
第三,普遍重视通过非政府组织发挥作用。不论是英国的以UK Emissions Trading Group为代表的各类非政府组织还是欧盟行政机构内部的各类咨询与顾问团队以及美国的各类环境保护组织,他们在碳排放交易制度中充分发挥了自身具有的专业性、民意广泛性以及沟通有效性等优势,通过为政府提供咨询意见、起草各类报告、代表各类团体与政府沟通、代表政府参与对被管制企业的指导等方式,提高政府政策制定与实施的效率,降低被管制企业对制度实施的阻碍程度。
这些特征与西方各国兴起的公共行政改革的背景是紧密相连的。公共行政改革主要的特征为国家行政的收缩与社会公行政的发展。国家行政机关已经不是唯一的行使行政权力的主体,其行政权部分地交由社会公共组织来行使。碳排放交易制度中非政府组织与政府之间的合作集中体现了这一公共行政改革的成果。
二、我国碳排放交易监管主体的设置
2007年6月12日,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成立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及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国发〔2007〕18号),①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7/content_686012.htm,2019年5月8日访问。成立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及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小组现任组长为李克强总理,成员几乎包括了国务院的所有部门。领导小组下设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务院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均设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具体承担领导小组的日常工作。
2011年10月29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厅发布《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的通知》(发改办气候〔2011〕2601号)。随后,各试点地方陆续开始碳排放权交易的筹备工作。例如,广东省人民政府于2012年9月7日公布的《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东省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粤府函〔2012〕264号)第四点“保障措施”第(一)项“加强组织领导”规定,“省发展改革委作为全省碳排放和碳排放权交易的主管部门,负责统筹协调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①http://zwgk.gd.gov.cn/006939748/201209/t20120914_343489.html,2019年9月14日访问。天津市人民政府于2013年2月5日公布的《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天津市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津政办发〔2013〕12号)第三点“保障措施”第(一)项“加强组织领导”规定,“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发展改革委,由市发展改革委主要负责同志任办公室主任,具体负责试点工作推进落实”。②http://www.tjzfxxgk.gov.cn/tjep/ConInfoParticular.jsp?id=38237,2019年9月14日访问。《关于<上海市碳排放交易管理办法(草案)>的起草说明》明确提出,“根据《办法(草案)》,碳排放是指二氧化碳气体的排放,包括直接排放和间接排放。同时明确规定市发展改革委是碳排放管理和交易工作的主管部门,负责对主体范围、配额分配、碳排放报告与核查等碳排放管理和交易工作进行综合协调、组织实施和监督管理,并明确有关机构具体负责本市碳排放交易的日常管理工作”。③http://sh.eastday.com/m/20130712/u1a7516885.html,2019年9月14日访问。其他省市,如湖北省、北京市、深圳市均有类似的办法与规定。
综上,我国目前尚未通过立法设定具有碳排放权交易行政监管职权的行政机关履行具体的监管职责。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是一个议事协调机构,不能直接制定规章制度和发布行政命令。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在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的领导下开展具体的节能减排、气候变化应对与碳排放交易的主管工作。在国家层面,监管职责具体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内设资源与环境保护司承担;在地方层面,则由地方发改委或发改局及其下属机构承担。
(一)目前碳排放权交易监管主体设置的合理性
现阶段,从国际环境、国内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对温室气体的界定三方面分析,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在国家气候变化领导小组的领导下,通过其内设部门及地方下属机构对碳排放交易实施监管,有一定的合理性:
第一,从国际环境角度而言,应对气候变化是一个全球问题。中国政府于1992年签署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93年批准了该公约。中国于1998年签署并于2002年批准了《京都议定书》。我国设立相关机构的初衷是为了衔接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项下的相关工作,包括国际谈判与合作、研究国内宏观政策与战略等方面。这些工作内容也反映在前述两个机构的任务与职责中。而碳排放交易制度产生于气候变化问题,是欧美发达国家为了应对气候变化问题而采取的一种新的市场化的环境治理手段,因而研究与设计碳排放权交易制度自然也成为了前述两个机构的职责之一。
第二,从国内经济社会发展角度而言,我国仍然是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处在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在一定时期内,碳排放绝对总量仍处于上升趋势,这也是为何我国一直强调“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原因之一。目前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我国并不承担强制性的减排义务,而通过何种措施与手段去应对气候变化仍处在探索的过程中。气候变化问题以及碳排放权交易制度涉及工业、农业、科技、环境、能源等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尚无法完全交由任何一个专门的国务院部门实施和运行。因此,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具体负责,有利于从战略全局去规划与统筹碳排放交易制度涉及的各方面工作。
第三,在对气候变化的认识上,英国、欧盟、美国等均将二氧化碳气体视为一种环境污染物或者大气污染物,故由环境保护部门专司其职,而我国则不然。2012年3月18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草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气候变化应对法(建议稿)》(以下简称“建议稿”)在北京发布。建议稿第十三条规定,“属于大气污染物的温室气体,由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价格等行政主管部门制定排污收费条件和标准。不属于大气污染物的温室气体,由国务院发展与改革部门会同国务院税务等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碳税征收条件和标准。超过核定豁免排放配额排放且不能通过企业内部减增挂钩、市场交易手段取得不足的排放配额的企事业单位,除了依法缴纳碳税外,还应当就不足的排放配额向当地发展与改革部门缴纳温室气体排放配额费”。可以看出,目前我国政府倾向于认为二氧化碳“不属于大气污染物的温室气体”。而之所以这样分类,一方面与二氧化碳的本质属性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与我国所承担的非强制性减排的国际义务有关,因为如将其定位为大气污染物,我国将面临更大的要求承担强制性减排义务的国际社会压力。
(二)对我国碳排放权交易监管主体设置予以进一步改革的必要性
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及其内部机构与地方下属机构实施和监管碳排放交易,是在国际国内各种因素相互作用下的一种权宜之计。从行政法的角度出发,监管主体的设置仍需要进一步改革与完善。行政监管主体是行政法上很重要的一类行政主体,是“指行政法律关系中与行政相对人互有权利义务的另一方,是以其行政法上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而独立行使行政权力并承担法律责任的主体”。具体而言:
从行政监管法律关系的角度来看,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作为统领全局的宏观调控管理部门,并不宜与被监管主体发生直接的法律关系。在碳排放权交易的监管中,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及其内部机构与地方下属机构的主要职能在于如何协调和解决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实施与目前的经济政策、产业政策以及能源政策等方面的关系,而不是直接作为碳排放权交易的监管部门与具体的减排企业产生法律关系。这种监管主体的设置将更容易导致权责脱节、争权诿责等问题,增加部门之间协调的成本,也给碳排放权交易的实施增添了行政管理障碍,进而增加了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实施的行政成本,降低了行政效率,最终影响降低排放、改善环境等目标的实现。
监管主体的核心在于法定的监管职权。监管职权属于行政权的一部分,而“行政权是指由国家或其他行政主体担当的执行法律,对行政事务主动、直接、连续、具体管理的权力,是国家权力的组成部分……,行政权的内容以事权为核心,管理行政事务的需要为行政权的存在提供了正当性依据,是设定行政权的基础”。不论二氧化碳是否属于污染物,其本质上仍然是一种在超量排放的情形下对气候变化会产生消极影响的温室气体。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自2003年成立起,主要针对经济事务享有宏观调控权,而环境问题为社会事务,由环境保护部作为监管主体更具有行政权上的正当性。
从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要求来看,国务院于2004年3月22日发布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提出应“合理划分和依法规范各级行政机关的职能和权限”。目前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内设的职能部门总计28个,管理范围几乎涉及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所有方面,故被称为“小国务院”。在这28个司中,与碳排放交易直接相关的机构包括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司与应对气候变化司。将其与环境保护部的职能相比较,①具体参见国家环境保护部的网站 http://www.mep.gov.cn/zhxx/jgzn/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网站 http://www.sdpc.gov.cn/znbm/default.htm。二者存在诸多重叠与交叉之处。而这种现象与2013年党的十八届二中全会和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提出的转变政府职能与“减少部门职责交叉和分散”的要求仍存在差距,因而需要进行改革。
三、完善我国碳排放权交易监管主体设置的构想
对于碳排放权交易监管主体的设置,有学者提出,“我国宜单独设立正部级的能源和气候变化委员会,由其统一领导和部署应对气候变化工作”。这说明已经有学者看到了目前监管主体设置的不足。但笔者认为,新设立一个专门部门履行监管职责固然是一种思路,但牵一发而动全身,操作起来存在较大的现实困难,可能不符合我国现阶段的国情。本文认为,我国碳排放交易监管主体应逐渐转为国家环境保护部及其下属机构,理由如下:
首先,从监管专业化趋势来看,监管机构的“监管”仅限于经济体系中的特殊事项,或者对某一特定产业进行监管。监管过程复杂多变,监管事项具有高度的技术性、专业性、复杂性,而传统行政部门缺乏监管的专业知识和能力,无法达到监管专业化的目标。监管机构是基于监管技术性、专业性因素而产生的一种公务分权方式,因而其区别于传统行政部门的首要特征是“专业监管性”。自然环境及气候变化领域内的问题具有较强的科学性与复杂性。例如,就二氧化碳是否是导致全球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各国科学界争论了近半个世纪才逐步统一认识。具体到碳排放交易领域,不论是信息的采集、标准的制定、排放的监测与核实还是与其他温室气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因素等问题,均需要具备较强的专业知识才能够及时发现、研究并加以解决。欧盟及英美等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监管机构设置充分体现了专业化监管这一发展趋势。不仅如此,相关政策与制度的设计也在很大程度上获得了众多专家咨询组织与民间组织的专业知识的支持。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在行政能力上更加偏重经济体制与经济事务,而在环境保护与其他环境事务上,国家环境保护部更具有专业上的能力与优势。
其次,从环境治理经验来看,我国实际上从上个世纪80年代就已经开始探索利用排放交易进行环境治理。1988年3月,原环境保护局颁布《水污染物排放许可证管理暂行办法》,同年确定上海等18个城市为水污染排放许可证试行单位。1991年,原环境保护局决定在16个城市进行大气污染物许可证制度的试点工作。1994年,包头、开远、太原、柳州、平顶山、贵阳、本溪、南通、上海和天津等城市最早进行了大气排放交易实践。同年,原环境保护局宣布排污许可证的试点工作结束,开始在全国所有城市推行排污许可证制度。经过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对排污许可交易的摸索,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将有效经验推广到二氧化硫排放总量控制及排污交易领域。2002年3月,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与美国环保协会开展合作,在山东、山西、江苏、河南、上海、天津、柳州启动“推动中国二氧化硫排放总量控制及排污交易政策实施的研究项目”。这是迄今为止中国政府启动的最大规模的排放交易的示范工作,各参与省市相继完成总量分配、交易规则制定和案例试点。此后,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与人民银行、银监会、财政部以及各省市环保部门通过多种途径的交流与协作,不断推进环境金融与财政政策、交易平台的搭建、各类污染物排放许可交易试点等各项工作并取得一定成效。
通过以上我国在排污许可交易领域的实践可以看出,我国环保部门在排污许可交易实施、监督、制度建设、能力建设方面均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因此,在碳排放权交易的各项工作中,充分利用环境保护部门在该领域的实践经验将有利于避免行政资源的浪费,增加制度推进的成效并减少试验错误的概率,降低试错成本。
再次,从环境保护中公众参与的趋势与成熟度来看,“伴随着‘新公共管理’改革的蓬勃发展和行政民主化浪潮的逐步推进,加强公共行政领域的公众参与已经成为世界性趋势”。碳排放权交易的监管属于公共行政的一部分。英美等发达国家在环境治理领域的实践揭示,其监管体系经历了一个由政府机构全面管理到政府与非政府公共组织合作治理的发展过程,政府将部分监管事务逐渐交由非政府的公共组织行使。公众参与监管一方面能够形成对行政主体单方监管的监督作用,保证行政主体依法监管,另一方面亦有利于行政主体与被监管主体之间达成充分的信息交换,提高监管效率,降低监管阻力。中华环保联合会于2006年发布的《中国环保民间组织发展状况蓝皮书》显示:截至2005年底,我国共有各类环保民间组织2768家。其中,由政府部门发起成立的有1382家,占49.9%;民间自发组成的有202家,占7.3%;学生环保社团及其联合体共1116家,占40.3%;国际环保民间组织驻内地机构68家,占2.5%,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和东部沿海地区。根据国家民政部发布的《2012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生态环境类社会团体达到6816个,①http://cws.mca.gov.cn/article/tjbg/201306/20130600474746.shtml,2019年9月14日访问。这还不包括未注册登记的民间环保组织。尽管我国环境保护的公众参与仍存在诸多问题,但相对于其他行政监管部门公众参与的发展程度来看,环境保护中的公众参与基础较好。
最后,就国际经验而言,欧盟、英、美在碳排放权交易的监管机构均为负责环境事务或环境保护的职能部门,说明欧盟和英美等国首先把气候变化问题归为环境问题进行治理。而碳排放权交易本质上是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过程中采用市场手段解决环境外部性问题,以缓解气候变化给全球环境所造成的消极影响。从长远角度看,将二氧化碳定性为污染物是大势所趋,因而碳排放交易是一种环境治理措施,由我国的环境保护部进行监管更符合国际经验,也更有利于我国在国际舞台上与其他国家展开谈判、沟通与合作。
通过以上分析并结合当前我国实际情况,笔者认为我国碳排放权交易监管主体设置分为短期与长期两个阶段进行完善较为科学与合理。(1)短期阶段。目前,试点省市的碳排放权交易工作在各省市政府及其发改办的领导下有序推进,2013年各试点城市初步建立交易规则、交易平台并开始进行碳排放权交易。究竟各省市的试点效果如何,存在哪些问题,需要如何改进,仍有待于进一步实践的检验。因此,笔者认为在碳排放权交易仍处于试点及观察阶段的情形下,对现有的以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为监管主体的设置不宜作大调整,以保持政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同时为下一步的深化改革、完善制度提供重要参考。根据发改委发布的有关通知,我国碳排放权交易的试点阶段在2017年接近尾声,目前正处于从试点省市向全国统一建设的过渡期,相应的监管职能亦从发改委转移至在2018年新组建的生态环境部。(2)长期阶段。当前正处于由试点阶段向全国统一建设阶段的过渡期,碳排放权交易的各类主体,包括监管主体、交易主体及其他第三方机构都会积累一定的经验,亦会发现各类问题。此时,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应当对初期的试点进行总结与评估,并及时启动气候变化应对法的立法工作。在立法的过程中,应当对监管机构的设置作出适当的调整。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应主要从战略、政策以及碳排放权交易与相关经济领域如何协调等宏观方面发挥其指导作用,逐步退出微观领域的监管职能,而将具体规则的制定、执行与监管逐步整合到新组建的生态环境部,形成宏观调控与微观管理相互区分与协调的监管框架。在这一发展完善过程中,应当创造有利的体制与机制,充分发挥社会公共组织在碳排放权交易中的宣传、指导、服务及监督功能,形成以环境保护部门为核心的政府机构监管为主与各类环保公益组织、环境保护协会等社会公共组织监管为辅的现代监管主体架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