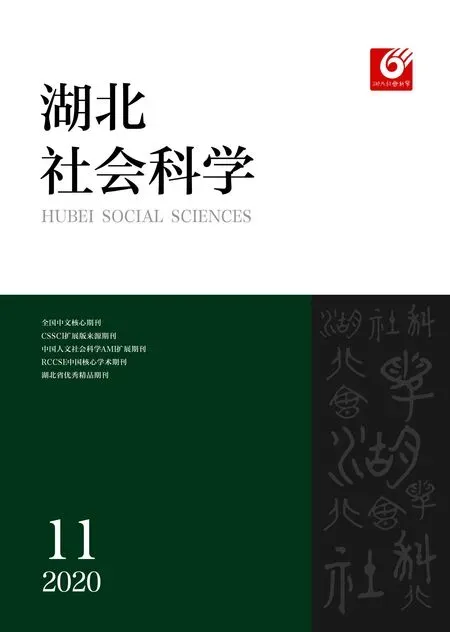试论《单子论》中的自为主体性实体观念
2020-01-16余绮
余 绮
(北京语言大学,北京 100083)
莱布尼茨的哲学思想涉及神学、逻辑、认识论、物理学、心理学、政治、宗教等领域,而支撑他们的则是莱布尼茨在全部哲学思考上所致力寻求的形上学原则,即表象世界自身的实体。而有关莱布尼茨的“单纯实体(simple substance)”思想的文本论述则集中于他逝世两年前的《单子论》手稿(成文于1714年),可以说是其晚期形上学思想的凝结点,在此之前的《新系统》(出版于1695年)、《神义论》(出版于1710年)等著作都未对“实体(substance)”这一概念做确切深入的论述,[1]仅是从不同侧面讨论相关的表象世界的关联。由此使得《单子论》成为莱布尼茨哲学思想整体中一个隐含的制高点,本文正是力图辟清《单子论》中展现出的单纯实体即单子与其复合表象之间在形上学层次上的关系,从而为剖开莱布尼茨全部哲学庞杂的思想图景提供一个有力的切入点。
《单子论》90条内容主要着力于解决表象世界与其自身形上本原的关系如何进行有效界定的问题。但这一界定并不是完全为了给出一个完全定型了的、客观的形上学图景(如带有强烈体系性表征的笛卡尔、斯宾诺莎的形上思想),这样一种定在的理性形上学观念,意味着偏离给予性之能动主体,而且同时也就意味着这一观念实际上只是一种世界自身本原的一个理性表象而已。而莱布尼茨则强调,自己对表象实体的一系列界定,只是一种形上学假设,但本文认为这一假设亦非经验性的可能性推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实在本原自身所具有的纯粹能动本性所带来的一种纯粹观念的体现:可能性的意义,贯穿于莱布尼茨对表象、单纯实体、人、上帝的含义界定中,他给出的表象终极图景——最好世界理论以及人类共同体组成的上帝之城,也是建立在能动单子本原基础上的一种特定可能性世界,而非不具备形上学眼光的伏尔泰所理解的一种经验偶然的当下表象现实的人类世界图景。
因而我们在解读《单子论》时,应当以一种前后内在融贯的观念去整合全部文本信息的内在含义,而不应仅仅着眼于一种僵化定形、前后顺次论证的条块理论眼光,来分析具有主体自为能动性的单子实体在其整体意义上的观念图式。譬如单子(monad)这一实体概念的意义,实际上贯穿于文本中出现的“单纯实体”(simple substance),“复合物”(compounds),“隐德莱希”(entelechy),被生成物(created being),“自然世界”(natural world),“道德世界”(moral world),“上帝”(God)等,前后一系列特定表象实体的意义阐明中。文中单子与表象的关系起初的界定,与随后对表象进行的多层次角度的展开解说,基本上是直接完全一致的。应当说,整个《单子论》就是围绕“单子”而系统地展开一个有机思想整体——这取决于我们是否认同莱布尼茨所演绎出的具有思辨性的现实自身之观念,也即主体性实体。
从笔者的角度来看,《单子论》全文的结构性表征比较明显,莱布尼茨对实体也即表象自身自为主体性的演说大致可分为描述性的意义建构或定性(第1—46条)以及这样一种纯粹实体观念的意义应用或其现实充实两个层面(第47—90条);而其思想内容的核心线索,则指向表象自身实在性之自为主体性在表象与其本原根基之间所具有的同一内在张力性关联下所进行的意义澄清;质言之,即是由当下直接表象转入自为存在根据单子,再由单子与表象的同一关系一方面深入界定现实表象层次的合理秩序图景,另一方面则顺承完整具体地定性实体的真实含义或相对于表象层次所具有的特质——从笔者的观点看,后两者乃至于全文,都有机地交融于表象本身作为一种自为主体性纯粹实体的多层次一致自为性的自身意义澄显统一体中,或说绝对主体的自我辨析阐发过程中。综上所述,本文将以一种综合性诠释演绎的方式,揭示出贯通在《单子论》整个文本中的内在思想主体之逻辑图景。
一
在前半部分中&1—18首先就引出了复合表象之实体即单子的主体性内涵,并进而对其自为表象能力做出初步的澄清界定,把单子具体化为具有基本知觉能力的“隐德莱希”(entelechy)这样一个更显主体性意义的实体概念。
应当承认,莱布尼茨并未在这里乃至全篇提出“主体”这一概念,但主体或自为主体性,却构成我们由莱布尼茨所说的复合表象上升到单纯实体层次认知的一个关节点。关于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莱布尼茨本人是这样论述的:“单子仅只是单纯实体,后者成为诸复合物……一个复合物仅只是单纯实体的群集或聚合”。(Monadology.1,2,)也即复合物是由单子或单纯实体构成的,二者是事物本身与其自身表现的同一关系,单纯实体自身复合为复合之物,显然这意味着二者是事实本身所具有同一性纯粹内在关联的两个层面或两种特定表象,前者相对于后者具有根基性或某种一贯性。而关于单纯实体的特质莱布尼茨首先只是给出了一些相关于复合之物的否定性描述:没有部分,因而也不具广延和形式,没有可分性,不会分解,或自然地形成、消灭。(Monadology.1,3,4,5,6)由此表明尽管复合之物是由单纯实体性单子生成的,但单子自身并非是复合之物自身的一个部分,二者并非同一个层次,或说性质上是要划分开的。复合之物自身的特性是其实存之可分性,即复合现象自身不具有纯粹一在的性质,它的每一部分总还必然具有自身特有的复合性,或说凡有形之物总是被它者形成的,自身又总是被分化为它者,因而成形之物自身实际上是被动受限或受统摄的,处于自失状态,因而不具有自身自在的实在性;但复合物自身却又的确是在不断地被构成而实存着,那么它就只能是由与其自身具有内在同一性关联的纯粹实体作为复合物本身或说统摄着的主体不断自为生成的。在这里,实体自身生成复合物形式,二者是一个事物,但实体自身不是复合物,或更准确地说,复合表象自身。
那么,莱布尼茨所试图界定的组成复合之物的纯粹单子,也就不应当被认为是构成复合表象的一部分。复合表象的特质,规定了其结构上的部分之形式就还是复合的即被生成的,有形的任一形式总还是被形成的(form is to be formed);因而我们在形成单纯实体(simple substance)的概念时,并非是把它当作表象的一个实在有形的“实体”,或与能动思考主体相对的一个定在客观对象性实体形式(包含在笛卡尔那里由上帝生成的实存性定在精神实体);而是相对于所谓客观现实实在性的表象层次而言,具有某种超越性、然而是本身与之相互内在同一关联着的纯粹实体,是真正表象着的东西,或说表象本身、本体,也即统摄性的、自己本身自为地生成着的或说复合着有形表象之物或说之表象化的纯粹实体。因而对莱布尼茨的实体准确的界定即是,自身能动地生成着实存表象的一种自为性实体——能动性主体。
而正因为这一纯粹主体性实体是自为能动而不断成形的,所以关于单纯实体之形成,或说单纯地复合成无限可分的、而又与之具有内在同一关联的有形复合物或复合表象,也就是可理解的了,继而由此引出了表象层次的变化因素乃至主体自身真实的能动精神特质。
与单子的纯粹性和表象的复合性之间的对立相应,纯粹的能动性与有形的运动变化之间的关系也须加以澄清:后者作为被统摄之构形物的某种状态显然亦是一种被动表象,即机械运动表象——由定在客观的空间形式组合定形,这与纯粹的单子特质是不相符的,因而单子作为真实的主体性纯粹实体不存在所谓内部变化、外部属性、并行实体关系等外在的表象层次相互间的复合抽象性关系;恰恰相反,单子是真正自为能动地生成这些现实表象关系自身的实体本身,是自身整全的能动性主体,莱布尼茨由此提出单子是封闭无进出窗口这种形象的类比赋形说法(Monadology.7),而这样一种类比推定的认知方法随后将会在其整个形上学体系的阐发中显明为具有合法性甚至必然性的。
至于单子自身的能动性,则正好体现于其自身自为而实现的种种现实表象变化,或说某种实存表象力,这就构成了单子实存的特性,并使其有别于单子自身绝对纯粹能动之源的主体性本性,继而开出无限其他同样自为能动地生成着的、现实表象着而实存的特定表象力之主体性单子;作为纯粹实体,单子间的关系显然不具定形的量化关系,而应当是具有纯粹能动本性但又真实自为生成而实存着的单子自身之自我绝对主体性纯粹本性直接地自为现实分裂着所形成的纯粹内在关系——简言之即是由实存着的形式化其本身之纯粹普全主体性的“一在”直接自为地否定实现为能动的个别多样化,而由于这里根本不存在外在的形式结构抽象表象关系,每一后者又都直接是纯粹的“一在”,并且是自为能动而实存着的单纯实体也即单子,因而我们可以说单子自身现实自为能动地变化着,同时纯粹的单子其本身又自为能动地分化为具有无限不同表象力的现实实存诸单子,而彼此间也是直接具有内在同一性关系的,由此我们可以理解莱布尼茨所说的单子之间差异律之必然实存具有其形上学根基(Monadology.8,9)。但无论是单子自身的无限变化还是单子间各自表象力的无限多样性变化,都是由它们本身纯粹无形式而绝对为一的主体自身自为的实现,因而彼此间又是具有内在同一性关联而连续着的,这就是通常所谓的连续律(Monadology.10)。
总而言之,能动的主体是自我差异且纯粹地表象化着的——自否定为多,而纯粹普全的单子,即是莱布尼茨所说的自然变化的“内在的本原(inter⁃nal principle)”,或不变的东西,正是这一不变的本原,统摄着自身能动的一系列内在一致性连续、逐渐的变化,或作为纯粹的单元,而包容自为的繁多性——后者本身即是前者自身的特性(Monadology.11,12,13)。对于这种自身包容变化和多样性的纯粹能力或一种实存过渡流动状态(passing condition),莱布尼茨对之界定为:知觉相应的单子,类比于知觉着的灵魂,则成为精神性的能动实体或“隐德莱希(ent⁃elechy)”,即具有自足完满性的内在活动的源泉,或“无形体的自动机”(incorporeal automata)。这样一种纯粹能动本原主体的自为活动,不断地产生着一系列特定实存表象力,也即知觉,继而知觉间的变更,产生出了欲望,后者实际上是纯粹实体作为绝对主体的一种自为能动性的实存表征。
欲望总是寻求自身能动性本身所本然地具有的自足完满能动性的圆满发散实现,但这一本然发散的能动活动,直接地就意味着自身现实化为种种特定的知觉表象力系列,从而就有别于纯粹的绝对能动主体性,陷入自失状态。因而莱布尼茨所说的欲望,不是与外在有形实存表象相对立的一种个别经验能力活动,而是表象本身即纯粹绝对能动主体性单子或隐德莱希自身,自为自否定着的某种缺失性能力状态的一种表征,但同时又恰恰是其自身纯粹能动性本然地就要在当下现实中本身又趋向于充实性实现的一种相对超越性的张力体现;或者我们可以说,前一种表征,是由表象指向纯粹本原主体自主性的消极的自否定,后一种张力体现,是由表象本原指向自身现实实存自为性的积极的自否定,显然二者又是同一的,并且正是莱布尼茨形上学思想在处理现代哲学的主题——实体与表象二元关系时,所立以之为根据的、核心性的自为主体性思想,这一思想与莱布尼茨所要辨明而加以批判的机械性表象实体形上认知思想是正相对立的。
此外,隐德莱希的这种一贯的自为自否定性,同时就使得它自身总是具有一定的完满性、自足性的,因而是作为一种被统摄着的、被生成的单子(created Monads)或泛而言之的被生成物(created being)而直接实存着,但很显然,实存着的单子,只是尚未自我充实而去实现本身完满性之绝对主体性的某一特定状态,由此便引出了莱布尼茨在《单子论》19—30条中,对单纯实体之实存能动表象力特质以绝对主体为根基而进行纯粹单子自身自为的上升分层式的辨析界定。
二
首先单纯实体的一般实存状态,即仅仅具有知觉,被莱布尼茨界定为单子或隐德莱希,具有欲望、情感、记忆的单纯实体,则是知觉表象力更为清晰的灵魂,实际上也就是自身本然的纯粹能动主体性之实存状态更充实完满。因而,生成着的表象更细微、更接近表象本身纯粹的能动主体本原,表象自身也随之更具精神能动性——质言之,即是趋向于纯粹自主性的自为表象化。
譬如,记忆力即是为灵魂提供一种具有一定自主性的连接性(consecutiveness)表象化:由于每一自为实现的当下现实状态都是由之前的纯粹能动性主体实体生成的,而后者又总是自为而直接地处于特定实存表象化状态,由此便形成了一系列主体纯粹自为而具有一致性的前因后果的表象状态序列,也即前述能动的纯粹一在自否定为内在一致性的纯粹多样化系列,具有记忆力的动物灵魂即是带着一定的纯粹一在主体性而自觉地由自身前一知觉状态表象自为能动地期待着与之相似化的自身当下知觉状态表象,也就是由能动主体之纯粹一贯性而自为地形成的清晰一致知觉表象关联,就动物而言我们也可以说是其实存着的能动主体本原发散出的能动意志力之自我一贯现实化的知觉表象(Monadology.22,23,25,26)。但这种关联性的表象序列始终限于实存表象状态层次,也即是受控于自为能动性不断实现出的无限可分复合有形表象,因而只具有一定的细微相似性,并且相对于纯粹能动本原潜在地要实现出的整全表象界而言则表现出偶然性。而具有理智表象力的人的理性灵魂(ratio⁃nal soul)或心灵(mind)较之动物与人共有的这种经验性现实化认知则更具主体能动本原性,即超越于无限复合表象层次而归复于纯粹能动表象力统摄性根源,也即表现出完全纯粹一致的必然性和永恒性的反思性表象认知能力,理性由此上达对我(当下实存表象化经验域之统摄性纯粹精神主体)、我们(对经验个体化主体的进一步能动超越性溯源所获得的统摄性纯粹精神主体)、一般实体——隐德莱希(更具一般本源性的纯粹能动精神主体)、上帝(一切现实实存的根基性纯粹实体即绝对主体)这一系列表象自身实体之纯粹能动主体性的特定表象化显现层次或反思所形成推理对象(Monadology.28,29,30)。
因而我们的理智推理活动,无论是局限于表象间现实个别经验层次,还是相对表象自身层次具有超越性,它都保持着自我同一性而逐步纯粹化为一系列主体层次,也都贯穿着根源性的绝对能动主体性之自为一致性内在关联。在这里就转入到了莱布尼茨在随后的31—46条中,对相应的充足理由推理原则和矛盾推理原则,以及事实偶然真理和推理必然真理的相关阐发。
三
根据前面对莱布尼茨的形上学思想的初步分析,我们在澄清这两类推理原则和真理时,必须要加以强调的是,它们并非浅层次的指向外在对立客体的认识论思想,而是在于,对能动的形上学单纯实体与其自身无限多样复合表象间的关系,依照自为主体性的内在张力性关联所作的进一步批判性辨明,目的就是为了澄清出根源性的纯粹能动实体所包含的真实意义,从而真实地呈现出绝对主体本身。因而这里的两个特定方面的认识论,实际上是立足于纯粹主体性单子自为地生成的现实复合表象这一基本有效出发点,力图进一步深化形上学实体思想图景。
其中,矛盾原则即是推理对象自身保持自我同一即为真,自身相反包含矛盾即为假;充足理由原则,即是任一实在或其陈述表象之为真,在于它自身实存根源自足地保证其当下表象化特质的实存性,而排除其他与之相左的可能复合表象的实存性(或通常所说的为什么事情本身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很显然,前者在对表象的深入认知推理中,并未涉及纯粹能动主体自身自为地无限多样化的实存表征,而是由表象本身的自为生成性纯粹主体出发,不断扬弃超越自身的无限自为性(消极的自否定)所可能实现的表象化多样性,从而始终保持着能动主体的稳定的自主性状态。这在推理中虽然显现为具有一贯必然性的“抽象”还原分析,但在主体自身纯粹自为能动的界定前提下,事实上则意味着实存表象本身自为能动之本质或根基这一主体性的纯粹归复之绝对化,直至“分析”成为无须并且不能下定义、证明的最为单纯原始的观念或公理性(即纯粹理智观念自身的同一陈述)这种特殊主体,也即完全没有自为表象化之自失状态或倾向,彻底扬弃纯粹主体本身之自否定所造成的无限能动可能性从而保持自身纯粹为一的这一特质的绝对自主性主体。具备这种本质完满性的纯粹实体观念,不仅是必然的,而且是绝对的根源性之为一的存在,此即形上学终极单纯实体上帝,或最高的理智性精神实体——必然性推理的永恒真理及其纯粹理念,因而就处于上帝的理智中;与之相关地,上帝亦成了一切实存表象、(自为或自否定实在的)可能性、本质自身的终极精神性根源,这意味着,上帝在这里实际上是纯粹的绝对能动的实在存在(real ex⁃istence)本身,它的自为能动可能性之发散,直接地就是有绝对必然根基之生成的当下实存,因而它的本质绝对地等同于存在而不含任何可能的复合表象外在受限关系。
由于这一结论是从排斥任何外在限制表象、否定、矛盾而具纯粹必然性的矛盾原则之一贯推理而自我显现出的纯粹观念性界定,因而莱布尼茨认为他提供了一条先天地认识上帝存在的理路(Monad⁃ology.31,33,34,35,43,44,45,46)。根据莱布尼茨的形上学思想基本出发点,我们不难看出在这一所谓的先天矛盾推理中,并非是完全否定现实实存表象的抽象认知理论,而是立足于自为性的表象事实本身之纯粹实体自身一贯性的深入推论。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是关涉事实本身的一种推论形式,但它相对于纯粹实体作为能动主体自为生成的无限繁多表象事实域,表现出某种一贯的超越性。
与此相反,充足理由原则立足于表象本身之纯粹本原实体的自为主体性表象化特质,而同样具有某种“一贯性”或具有一致性的前因后果表象化状态序列,换言之,即是依据事实本身主体的一贯自为能动性,不断扬弃被统摄的受限事实表象,或说自身之外所可能生成复合的表象,并趋向于自身实存能动性根源从而给予自身现实存在绝对自足的表象力(积极的自否定),此即事实推理所要达到的终极因(final cause)。然而,尽管这一推理具有相对于当下个别表象事实自身的超越性,进而深入到作为纯粹的自为能动性表象力本身(积极的自否定),并前后一致地依循事实本身的能动表象化因果序列,而表现出自我超越建构性,但只要推理未能深及表象着的事实本身之纯粹能动的自主性表象力根源主体,而局限于直接自为的现实化复合表象倾向,就始终受控于能动性根源主体自身自为的无限能动表象化;并且由此反使得每一推理对象复合事实自身,在其坚持事实本身自为能动性的现实化表象倾向的推理过程中,被动地自发形成一种外在生成复合事实的无限可能性空间,从而使得指向事实自我本原之确立所进行的推理,始终只是效果因(efficient reason),诸如牛顿的机械力表象性因果序列,或者再进一步深入到事实本身之纯粹的能动精神性层面,如灵魂主体,而形成前后一系列细微的心理倾向、秉性(disposition),但这种推理(也即前面所说的动物和人共有的经验性认知)所获得事实本身的原因,都只能是更深层次事实本身的偶然现实化表现,因而是无法满足自身推理所依据的充足理由律的偶然真理。
实际上,实存着的无限复合表象事实自身,或者这种事实性推理自身,又的确是依存于被自身现实化能动性所遮蔽的自身的必然性实存根源,只是自身自为地否定了本身而处于无限自失不完满状态。因而,莱布尼茨提出“充足的理由或终极理由应当存在于这个偶然事实的系列之外,尽管这个系列可以是无限的”(Monadology.37),也即超越于事实本身的自为表象化现实层次,而回复到纯粹的事实本原或说具有绝对能动性特质的根源性主体,它绝对地统摄着自身的无限可能的自为表象化实存序列。前述纯粹的根源性之为一的存在,自身个别化为无限可能的多样性的一致序列,一切可能的实存表象于此便获得了来自自身纯粹本原的终极理由支撑,而这同样意味着这一事实终极因,实际上即是包含着一切可能实存因而自身是必然的、普遍的、充足的、绝对完善的、独一无二的上帝;上帝自身作为自为能动地实存事实之终极根源,是一个以纯粹自主能动性贯穿着的自为表象化实存序列,是一个纯粹的能动性存在序列,一切生成于其中的被生成物(created being)自身,则以种种惰性表现出的不完善性作为其所获得的特有本质,而有别于自身的能动根源,即上帝。但这一上帝观念终究是依循着事实表象自身的实存本原这一根本观念进行推理而自我形成的,因而莱布尼茨认为,他亦对上帝的存在做出了后天证明。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这两种推论理路及其真理以及上帝存在的两种论证,都是以表象本身的自为主体性纯粹实体观念为核心,从两方面表象角度所进行的阐发,因而是彼此交融于单子自为主体性之内在张力的意义有机体中,进而由此中给出上帝这一形上学终极纯粹实体的界定。此外,这两方面推理所获得的上帝观念,显然并非是抽象的神秘个体这种事实表象——如前所述,它自身作为绝对能动性的根源主体,实际上是一个纯粹化的存在序列,这就必然地引出了莱布尼茨对上帝创生世界流变过程的论说与演示,从而整体上转入了《单子论》下半部分关于形上学纯粹实体观念的意义应用和现实充实。
四
《单子论》中关于世界自身存在的创生流变图景,主要集中于第47—52条。莱布尼茨给出了一个有名的总括性论述:“只有上帝是原始的统一体或源初的单纯实体,一切被造的或派生的单子作为产物都可以说是凭借神性的刹那性连续闪耀而生成的。”(Monadology.47)笔者认为,在这一表述中,上帝之为原始的统一体,或说是源初的单纯实体,都意在强调上帝是自为地生发着序列性实存表象统一体的绝对主体性纯粹实体。这种源初纯粹实体,与其自身生成的被统摄的纯粹实体之间,显然是同一绝对主体自为能动本性的自我内在张力性关联,是纯粹能动的一在与其自身个别化实存一在的自否定创生关系。
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单子论》英文译者Dr.Robert Latta推测,莱布尼茨对于上帝这一终极单子实体创生个别单子的过程,既没有用过于分离性的创造(creation),也没有用完全同一性的流溢(ema⁃nation),而是采用了“闪耀(fulguration)”这一特殊词汇,这是出于试图保持单子的个体性及其与上帝的本质统一性而选用的介于前两者之间的中性表达。[2](p243)笔者认为这是莱布尼茨以自然表象界本身实存着的某种特殊的奇妙表象所具有的超验特质,而对上帝的创生所作出的类似化之赋形:关键不在于如何给出一幅具体有形的上帝创世图景,而在于理解,上帝作为绝对主体的本然的纯粹能动性,与其本身直接的自为无限连贯着的现实能动性,这二者之间的特殊表象化生成关系的一种理性观念的内在意义——至少要排除低层次的复合性表象间有形的时空关系的介入。
此外,在莱布尼茨那里,上帝作为纯粹绝对主体而成为莱布尼茨形上学实体观念体系的拱顶石,就其自身而言,并非是一个相对于其他表象层次完全突出独立的个体抽象对象,它自身是作为表象世界的纯粹根基才显现出自身的特质,而这一根源性的纯粹能动主体性特质,因之恰恰完全体现于它对自身自为主体性本性所纯粹直接地创生的世界所具有的自我统摄性作用;与此等同,实存着的自为单子自身相对于上帝之为绝对单子的创生,实即上帝的自我创生,或整全存在的自我创生。
具体而言,这一统摄性的创生实存的纯粹观念,在上帝那里被划分为三个内在关联着的维度:凸显绝对主体意义的权力是万物之源,凸显主体自身即为具有统摄性、自主性而纯粹一贯的实存之本质意义上的知识,知识在上帝那里是包含一切纯粹实存细节的普遍必然观念,最后是上帝自身纯粹自为能动的现实化因而使得每一个别化的现实细节都复合最佳原则(principle of best)的意志(Monadol⁃ogy.48);其中后两者,可以被视为绝对主体之权力的自我本然能动性的充实化表象特质,而意志则是权力在自我充实流化过程中纯粹现实化纯粹主体定在,知识则集中体现了绝对主体自为表象化自我内在张力性关联的核心观念。三个方面有机地充实了绝对主体这一形上学纯粹观念顶拱石。
而在被创生的纯粹序列性诸单子那里,单子自身的能动对外活动或被动性,则被解释为其本身具有完满性的纯粹主体性自为地清晰或晦暗的知觉表象力,至于单子间的表象力优越性,及一般相互表象性关联作用,实际上则是单子本身源自绝对单子即上帝自我创生时,所带来的每一单子自身所具有的纯粹主体性之一贯先天观念性的自为张力性所带来的内在自我关联;由此便导出了,单子超越现实表象因而更具自主性的特定清晰自为能动表象力,与脱离纯粹自主性而直接自为地现实化为特定被动晦暗表象力,这二者之间的互生关系。这种互生关系既直接地呈现于每一纯粹单子的内部关联,又间接地体现于具有自为现实化表象力特质的实存单子之间的关系——质以言之,即前述主体性之积极的自否定趋向,与消极的自否定之趋向之间,在绝对能动主体自身统摄下,呈现出内在一贯性。由此我们可以理解莱布尼茨的这一段演述里的形上学思想立足点:“相应地,在被创生物之间,能动性与被动性是互生的(mutual),因为上帝在对比两个单纯实体时,在每一个当中发现有令(oblige)他(Him)使另一个适应于它的理由,由此在从某些方面称之为能动的从另一个角度看则是被动的(what is ac⁃tive in certain respects is passive from another point of view);说它是能动的,就其能够以我们在其中所清晰的认知到的去阐明另一个当中所发生的,而说它是被动的则在于针对其中所发生的解释却是出现于另一个当中被清晰地认知到的。”(Monadology.52)
总而言之,上帝作为绝对纯粹的实存,本源自为地创生出了具有一贯内在关联的序列性现实能动表象力的单子,这是整全实存或世界本身依据自为主体性纯粹的自我创生式的理智观念,而非中世纪上帝创造万物这种经验表象性的外在变易创造关系。莱布尼茨由此在53—59条中,进一步对实存世界的这种自为关系性质作出具体充实化界定。
五
首先,需要对世界或宇宙,与世界本身的关系,作出澄清:“既然在上帝的诸观念中存有无数的可能宇宙,并且由于他们当中只有一个能成为真实的,那么对于上帝的这一选择就必定有一个充足的理由使得他决意于这一个而非其他的。”在这里,我们同样需要撇清经验表象化理解的偏见:很显然真实的世界或世界本身,并非是与被统摄着而生成的无限可能复合表象世界处于同行并列的地位,而是处于纯粹必然的实体本原地位,即具有纯粹自为能动性的主体,它相对于自身现实生成着的无限世界复合表象而言具有纯粹超越性、根源性,是真实的世界本身,也即绝对主体上帝。而上帝这一纯粹能动观念自为能动地生发出的无限可能世界表象,自身恰就是被统摄于这一根源性的世界本身——即其充足理由,也就是所谓诸可能性中唯一真实实存的世界,在这一统摄性的纯粹根源可能世界之外,任何有关世界本身的观念,都只可能是空虚抽象的外在偶然虚假表象,或说内在纯粹主体性实体支撑的经验性外在赋形组合之世界表象;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世界本身纯粹自为的表象是虚假无意义的,后者甚至还分享有一定的适宜性完满性,但在其自身根源处,则是具有上帝的智慧、善良意志和绝对权力这样完满性的纯粹世界本原。
根据前面进行的分析,上帝这些绝对自主性特质的纯粹自为运用,即是上帝自身或世界本身的自我创生,这同时意味着完满的绝对主体自身直接地自为能动自我实现,由此生成的无限个别主体即纯粹单子,因与之具有同一关系而彼此普遍无限地相互适应关联着,在这样一种本源意义支撑下的纯粹单子,被莱布尼茨称为“宇宙的一面永恒的活着的镜子(living mirror)”(Monadology.53)。然而这类“活着的镜子”,毕竟直接是以现实的、自为能动着的特定表象化趋向,作为其实存特质的,因而,与绝对主体性单子实体具有一贯性内在关联的序列性个别化诸单子,又是各自从其不同的表象化视角呈现着那唯一绝对的宇宙本身,或毋宁说,唯一的宇宙本身这一纯粹观念或理智观照之念,能够绝对自为能动地表象化而生成为无限个具有特定观照之点的宇宙:“然而如此多的这些不同的宇宙正是独一无二的宇宙(single universe)依照每一单子的特殊视角(special point of view)而具有的诸多透视景观(perspective)”。(Monadology.57)这样一种具有自为主体性的世界,自然包含了一切可能的多样性、一切可能的秩序、一切可能的完满性,并且可以说是这些性质本身的一种纯粹统摄性观念,而不单单是量的无限复合性堆积。所以莱布尼茨认为,关于世界本身及其普遍和谐这一形上学纯粹实体假设,恰当地高扬了上帝的伟大。
此后在这一世界自为性关系的根本观念下,莱布尼茨在《单子论》最后一部分中,逐步分层地对世界自身的诸表象化特质进行意义充实性演说与界定:由一般的实存单子,扩及到包含身心关系的表象界,再到统摄着自然世界的道德世界——上帝之城,最后集中于上帝作为建筑师与君王立法这样的自我两重统一之神性,从而再次演绎出上帝的崇高、神圣,以及实存世界之和谐完满性的终极形上学根基。
六
首先,就实存单子而言,在绝对主体性单子或世界本身自我生成时,单子之间的纯粹自为统摄性根源意义上的内在关联,就已然先天地决定了每一单子清晰的自为能动性表象力特质,以及它们以一种晦暗的方式或潜在的纯粹主体性表象力而与整全无限实存之间形成的本然关联,莱布尼茨也至此才凸显出单纯实体的表象力本性:“……单子的本性是表象化(whose nature being to present)……单子之为受限的,并不关涉他们的对象,乃在于他们对他们的对象所持有知识的各种不同方式上(即不具永恒必然性的不同视角的具体表象化——笔者注)。单子们都以一种模糊的方式力争实现无限性(the infi⁃nite),整全;但他们却由于他们的不同程度的清晰知觉而是受限的分化开的。”(Monadology.60)
这就意味着,诸多单子所生成着的无限复合表象,直接地就依其绝对主体性整全而成为彼此内在互通关联着的有机整体:每一形体、每一有形运动,都依其本身所具有的特定实存自主性自为表象力,而成比例地延及其他形体、运动并互相影响着,这一相互间的内在关联或影响力,又以表象本身的根源性绝对主体为支撑而贯穿于整全无限表象界——一叶落而知天下秋。莱布尼茨由此还特意引述了古希腊医学家希波克拉底“万物一致”的这种古代有机的整全实存思想。
继而,这种以一贯自主性支撑着的、自为的有机表象化具形到单纯实体上,即是成为具有“隐德莱希”的生物,或者具有灵魂的动物。它们自身自为地表象化为有机且有序的躯体,同时又以后者而将整个有序宇宙表象于自身纯粹主体性的灵魂当中;进一步地,每一自为主体性生物的隐德莱希或灵魂自身,亦非一个经验个别表象实体,而是在其本身的根源性主体的支撑下,同样有机地贯通于宇宙本身的每一个可能的表象化角落:“由此显现出这样的情形,每一个活着的形体都有一个统摄性的隐德莱希,后者处于动物中即是灵魂;但这一活着的形体的那些肢体部分则充满着其它的生物,植物,动物,其中每一个都同样有它们统摄性的隐德莱希或灵魂。”(Monadology.70)这样一幅有机的世界整体图景,被莱布尼茨称为“自然的工艺”或“神圣的机器”,这就更凸显出了真实实存世界本身之为自我创生着的纯粹自为性绝对主体或上帝所具有的根基性意义。
此外,莱布尼茨由此还进一步澄清了这一有机整体图景中,可能存在的关于身心所属关系的经验表形性误解,即认为“每一统摄性的灵魂都有一定量的或一部分物质,后者专属于它或永远依附于它,并且因此而拥有其它一些永远为它所役用的低级生物”(Monadology.71)。这种实体与表象间复合有形关联,实际上是一种被统摄着的赋形经验性观念,这种观念显然忽略了二者间一以贯之的统摄性绝对主体本然的自为能动性。与此相应,不仅每一躯体及其每一肢体,都以其自身本然地所蕴含的绝对主体性而无限地流变着,并由此再现了古希腊赫拉克利特万物皆流变的生机性思想;而且同样地,每一实存灵魂主体,也都直接不断地自为能动表象化为连续生变着的躯体,而绝不会以抽象的精神实体这种现实个别形象而存在;进而,经验性的生死表象,被纯粹化为纯粹自为性主体连续无间断的能动表象化序列中的特定环节:或者是纯粹实体之主体性相对于受统摄的表象层次本然地所具有的自为超越性张力(生),或者是实体自身直接的这一现实自为表象化相对于纯粹主体性的自我遮蔽性缺失(死),而二者皆是单纯实体本身所具有的主体性特质的纯粹自否定所引起的双重表象化状态,也就是单纯实体主体性的两种本然的自为过渡化表象状态。
因而灵魂主体在其本身纯粹的绝对主体性无限自为表象能力支撑下,不仅直接地与自身的现实表象化躯体成为实存统一体,而且还在这一无限连续过渡性自为生变表象化序列过程中,始终一致地与有形躯体保持同一性关联——其中的灵魂自身,因保持纯粹主体的自主性而遵循终极因规律(law of final cause),以目的统摄种种方法手段而表现为欲望活动;而有机变化着的有形躯体,因其为纯粹主体的自为性表现而遵循效果因规律(law of effi⁃cient cause),以生成着的复合表象而表现为形体运动。这样,灵魂主体凭自身主体性的两重性,得以从两个层面表象着同一个整全宇宙,从而真正成为宇宙本身的“活着的镜子”。
然而,单纯实体之纯粹主体性自身的这一切实存自为表象化特质,在其绝对能动根源那里(也即具有实存完满性的绝对主体或上帝),则扬弃了生成为个别化的有形躯体表象的现实意义,因为,绝对主体或上帝作为纯粹的实存根源,绝对永恒地自我生成着;而上述单子主体,在其本身的绝对主体性无限自为表象能力支撑下而显现出的自为序列性现实表象力无限过渡性生变进程中,同时就存在着超越于形体表象化层次而起纯粹统摄性的、一贯着的主体性单纯实体,即具有自我反思能力的理智心灵,它的特定现实表象化实存形态,即是理性动物、人类。
人类的心灵就其本身而言,超越了被创生宇宙中具有现实有形表象化趋向的一般的“活着的镜子”或感性灵魂,它与绝对主体上帝保持着一种具有纯粹同一自主性的主体自我关联,因而是造物主本身或神性的影像(image of deity),即上帝之为绝对主体,自身在人的理智心灵中以某种推理观念的形式而亲在显现,也即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纯粹统摄性理念。这种理智观念的自为能动性,不仅能够以其纯粹的自主性而认知宇宙的体系(即前述理性推理中的一系列理智观念、原则),而且正因自身是纯粹的本原,所以能够直接通过自为的工艺创造而现实地模仿宇宙本身或上帝。因而人的心灵单子,就其自身自主性特有的小宇宙而言,就像作为一个微小的神而实存着。
进一步地,上帝与人的纯粹精神实体之间的同一自主性亲在关系,便与上帝与其他受限于表象层次的被造主体性单子实体间的自为生成关系,彼此分化开来——前者被莱布尼茨类比赋形为当时社会中实存的君王与臣民的关系,乃至是现实中更具同源种系的父子直系关系。而由这样一种伙伴关系(kind of fellowship)自我联结而成的纯粹精神主体共同体,即是上帝之城(the City of God),后者作为绝对主体纯粹自为能力的自我一贯自主性关联共同体,自然地分有与上帝一致的完满性,即上帝自身具有终极完善性的自我意志之一贯纯粹定在显现,或说绝对能动的纯粹一在主体,在自身个别化的同时,仍保持着纯粹自主本性的纯粹多样化而形成的特定纯粹内在关联有机体:它必定是上帝自身完满性的一贯化特定实存表现,是统摄自然表象层次世界的道德世界,因而是最完善的城邦,具有真正普遍的最完善的君主,和忠诚地信服、爱戴它的臣民。上帝自身特定的善良意志、荣耀、神性,因之集中地汇聚于伦理性的上帝之城,不过上帝的智慧或权力,则分散地实现于对其自身无限自为能动表象化实存世界内容的普遍现实统摄上,并不具备绝对主体自身的一贯自主性这种纯粹特质,或说有别于自身纯粹的统摄能力性质本身。事实上,服从终极因的个别灵魂主体,与其自身表象化而服从效果因的躯体,这二者间的自为同一关系,对于作为纯粹自主性主体共同体的上帝之城,与绝对一贯的主体自身能动现实表象化的无限物理自然世界,这二者之间同一关系而言,是一种一致性的实存缩影。
根本层面来看,一方面是根源性的绝对主体,作为建筑师而实存地表现出自身无穷自为能动表象力神性,另一方面则是绝对主体作为自主性的君主,纯粹地表现为统领着纯粹精神主体之共同体王国的神性。其中,后者作为道德世界自身直接地就是终极因,它统摄着自身直接受控于现实效果因或机械运转机制的自然表象化世界;而这两重世界又直接地统一于根源性的绝对主体即上帝自否定所凸显出的自身本然的双重主体性身性(identi⁃ty)——纯粹绝对的自主性,与无限能动的自为性。这样一来上帝作为君主立法者对自身作为建筑师的统摄性关系,便成为纯粹自为的自我立法统率关系,实际上也就是上帝作为一切实存根源自身特定的、兼且纯粹的自我创生关系,这自然地就由此引出实存世界之为最完美世界的前定和谐结论。
根据前述分析,这一普遍和谐世界,显然不单单是现实经验着的表象世界。后者处于被统摄着的无限复合生成表象层次而以有限的完满性或不完善性为本性,莱布尼茨认为,现实自然世界的秩序(应当包含经验图式化理解的表象性人类社会形象),应是满足于纯粹精神实体作为终极道德因的各种要求而不断地消损或更新;但如同前述灵魂主体单子之于无限过渡生变着的现实表象化躯体间的自为同一关系,纯粹自主性的精神实体,自由自为行动能力所导致的善恶,必将由其自身的绝对一贯的自主性或神性作出先天的奖惩,或说是纯粹精神主体的绝对理智观念的自我立法奖惩;而这一先天的奖惩,由于自身的纯粹自主性特质直接地就区别于不同特质层次的自为表象化现实世界,同时又以一种绝对自主统摄性的自身主体性,而必然地要自为实现于自身现实表象化世界机制下的无限生变序列中。
在这样的世界本身之真实图景里,世界的一切奖惩秩序,都应当是出自与上帝保持一致的善人的安康,那么我们人类,就应当以我们的统领——上帝,这一绝对主体自身的意志或终极因,作为我们自身意志的全部目的而归附于它,只有后者才能成就我们自身的幸福;换言之即是,人类应内省自身的纯粹普全的绝对主体理念,以其自主性神性为原则向导,而自为和谐地在表象世界中追求自身的终极伦理幸福。莱布尼茨认为,这样一种形而上的关涉世界本原的纯粹理智观念,自然是所有现实可能性表象中最好的可能实存世界,与此同时,这一最好世界本身的纯粹观念,由于相对于无限偶然复合表象层次具有超越性,而使其真实性难以为具有现实经验局限性的人类所充分认知。然而,我们毕竟可以通过纯粹理智推理,或对上帝之崇高神性的忠诚信仰,或者是,透过莱布尼茨这一具有自为主体性内在张力的单子论神性体系的纯粹自我理念演绎,从其哲学视角窥斑见豹,从而以自我主体之纯粹自主性为根基,由自身的现实经验人性,自由而自为地导向自身本源之普遍神性,最终趋向自身人格的完满,或说神性的实现。
结语哲学史语境下莱布尼茨《单子论》的地位及影响力
纵观上述,我们对《单子论》全文主体思想的辨析和澄清,单子之于表象本身的自为主体性单纯实体的自我内在张力,统领了整个单子论思想之有机整体。莱布尼茨的这一主体性形上学,不仅超越了在笛卡尔那里局限于经验性主体的三重实体,还超越了在斯宾诺莎那里自封于绝对主体而自身单一的自为表象世界图景,这一图景反使主体自身再次沦为特定偶然经验性表象观念层次上的、完全丧失其主体性的唯一绝对实体。此外,在莱布尼茨的这一极富自为能动性的单子主体哲学中,已然潜含着康德那里先验地统摄着经验表象的主体理念之认知哲学,与绝对自为实践理性主体之道德哲学的统一,以及黑格尔那里绝对实体本身的绝对能动主体的本性,本然地自否定内在理性张力而自为地生发出的纯粹逻辑学形上体系;然而前者的先验主体认知理念与其自身的自主性实体,直接就地陷于双重表象化的自我辩证矛盾,从而导致主体中的神性超越维度处于自失状态,后者宏大的绝对理性形式体系,直接地导致主体本身内在主体性实存张力的现实维度处于自失状态。
诚然,我们不仅需要澄清,在莱布尼茨这一思辨形上体系中,诸如单纯实体、知觉、心灵、上帝之城乃至上帝这一系列理智观念有关的经验表象化误解,并将之理解为具有形上学本根实体意义的纯粹观念,以及,实存的绝对主体性本原自身在人的纯粹主体理智活动中,以观念的形式直接自为能动地同一化亲在;此外还需承认,在莱布尼茨的这一先验主体性观念主义哲学中,仍存在着纯粹观念自身确定性假说体系的粗糙与不完善性,乃至存在本原自身之为纯粹观念在形上学意义上的贫乏性;然而我们更应揭明的是,莱布尼茨立足于现实表象世界本身所作的内在超越性形上学假设的深远有效性:一方面,莱布尼茨自身在晚年已承认他的形上学体系只是一个供进一步批判交流的思想平台,[2](p13)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他的这一主体内在自为张力,不仅为上帝的实存和信仰作出有效辩护,而且还挖掘出人内在的自由与神圣而纯粹的主体维度,从而显证出相关于本来就不确定的经验实在表象域自身而本有的真实超越性、前瞻性、甚至潜在的革命性,以及世界本身之形上学纯粹本原所特有的、相对于表象才表现出的一种上升与发展着的真实力量。
质言之,正是莱布尼茨作为当时理性主义哲学的集大成者,反而对理性的客观定形思想取向所作出的扬弃,以及对纯粹能动绝对主体的超越性信仰精神取向的极大发挥,使得他得以摆脱当其时种种主体性哲学体系的各种缺失,尽可能完善充实地澄明辨析出复杂的表象层次世界本原意义上的主体性形上学纯粹观念。最后,就莱布尼茨对待自己的哲学事业的态度而写出来的表白话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哲学家自身这一主体当中的形上学观念:“我的体系……并非是一个完备的哲学主体,而且我并非试图要给出一个他人所寻求的万物的理由。我们必须逐步地前进从而使我们得以坚实地进展着。我从一些原则开始,并希望能够满足诸如那些困扰着 Bernier先生的大部分怀疑。”[3](p13)可以说,莱布尼茨的这一态度,正是本文在试图澄清《单子论》文本内在思想体系时的立意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