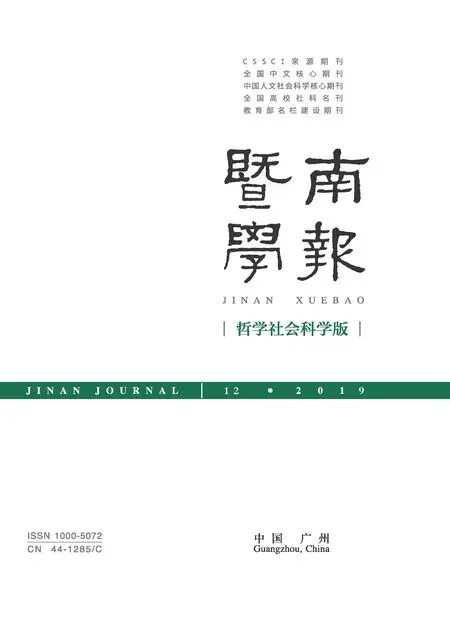“钓术”、“治术”与“道术”
——“作赋以讽”与宋玉《钓赋》的创作
2020-01-16邓国均
邓国均
战国时期,宋玉是屈原之后楚国最重要的辞赋作家,文学史论著亦常以“屈宋”并称。《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说:“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宋玉的辞赋创作,对于现实政治和社会的批评力度虽然不如屈子之作,但从其今存多数作品来看,仍然表现出较为明显的“讽谏”意识,是“作赋以讽”的先行实践者。保存于《古文苑》中的《钓赋》,便是这样一篇主题鲜明、意蕴丰富的杰作。作者将道家、儒家思想与“铺采摛文”的赋体笔法相结合,通过对不同“钓术”内容的铺叙和转换,巧妙地实现了对“楚王”的“讽谏”意图。今以对《钓赋》真伪的考察为基础,对其思想文化内涵与其“讽谏”主旨的关系略作论述。
一、《钓赋》的真伪及其主题
《钓赋》是否为宋玉所作,是开展相关研究首先面临的一个问题。班固《汉书·艺文志》载:“宋玉赋十六篇”,并自注云:“楚人,与唐勒并时,在屈原后也。”由于体例所限,《汉志》并未著录宋赋的篇名。梁代萧统所编的《文选》,所选宋玉作品包括了《风赋》《高唐赋》等一共七篇,但并未收入《钓赋》。初唐时编成的《隋书·经籍志》,虽然载录“楚大夫《宋玉集》三卷”,但亦未著篇名。今见《钓赋》全文,乃见于无名氏所辑、南宋章樵等人作注的《古文苑》中。鉴于此种文献载录状况,因此有不少学者怀疑《钓赋》恐非宋玉所作。
《古文苑》所收宋玉作品,包括了《笛赋》《大言赋》《小言赋》《钓赋》等一共六篇。明人胡应麟说:“《钓赋》全放《国策》‘射鸟者对’”;“《古文苑》所载六篇,惟大、小言辞气滑稽,或当是一时戏笔,余悉可疑”。清人崔述根据六朝时期的《雪赋》《月赋》等作品,认为“假托成文乃词人之常事”,“《神女》《登徒》亦必非宋玉之所自作”。以此观之,《钓赋》亦可以列入“假托成文”之范围。近代以来,或许是因受“疑古思潮”的影响,宋玉赋作受到了更为广泛的怀疑。如陆侃如研究认为,《楚辞章句》和《文选》等书所收宋玉赋作,只有《九辩》和《招魂》二篇“或者真是宋玉作的,其余十篇都有伪托的嫌疑”。其所著《宋玉评传》则进一步指出,“《钓赋》的结构上,大约是从《风赋》脱胎来的”,其中的“殷、汤以七十里”等句,“显然抄自《孟子》”,因而认为该赋可能属“后人伪托”之作。刘大白则根据《风赋》《高唐赋》等存在某些与“周秦古韵”不合的情况,而认为《文选》和《古文苑》所收宋玉赋,“都是后人托古的作品,没有一篇是真的”。游国恩则认为:世传宋玉真正“可靠的作品”,其实“只有《九辩》一篇”;《钓赋》等不但出于“可靠性极薄弱的《古文苑》”,而且在叙事方面又多有雷同之处,“显然是后人展转摹仿”之作。除此之外,郑振铎所著《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亦认为:宋玉作品除《九辩》和《招魂》外,“自《风赋》以下,便都有些靠不住”。胡念贻虽然肯定《文选》所收《风赋》和《高唐赋》等五篇作品为宋玉所作,但又认为《钓赋》文中的“利禄为饵”等句所体现的价值观念,“战国以前还没有这样明确地提出来”,故而对这几篇作品都持“存疑”态度。姜书阁也认为,《钓赋》与《大言赋》等见于唐人所编的《渚宫旧事》,其与《襄阳耆旧记》所载《高唐对》之“以故事而叙入者相似,(编者)显然并未视为宋玉作品”。这些论述从不同角度指出了《钓赋》存疑的原因。
但另一方面,肯定《钓赋》为宋玉所作者也不乏其人,其在汉魏以来的流传轨迹,亦大致可以考见。刘勰《文心雕龙·诠赋》说:“荀况《礼》《知》,宋玉《风》《钓》,爰锡名号,与诗画境。六义附庸,蔚成大国”,就表明他不但读过《钓赋》,而且很肯定其在赋体文学发展史上的价值。就《钓赋》的具体内容而言,《列子·汤问》篇“詹何以独茧丝为纶,芒针为钩,荆筱为竿”数句,晋人张湛注中的“夫饰芳饵,挂微钩,下沉青泥,上乘惊波”等语,李诚就认为“几乎全抄自《钓赋》中登徒子的话”。《文选·七发》“若庄周、魏牟、杨朱”一句,唐代李善注说:“《宋玉集》曰:‘宋玉与登徒子偕受钓于玄渊’”,所引内容与《古文苑》所载《钓赋》首句相合,可见《钓赋》为唐时流传的《宋玉集》所收。唐初欧阳询所撰《艺文类聚·人部》亦收有《钓赋》一文,但部分文字与《古文苑》所载《钓赋》内容有较大出入,文末还少了“今察夫玄渊之钓”以下一段。高秋凤根据这种内容上的差异,指出《古文苑》所载《钓赋》“不是采自《艺文类聚》”,而“应是采自《宋玉集》”,前人多以为《古文苑》所载宋玉诸赋是“抄撮类书”之说,都是“不正确的”。由《隋书·经籍志》所载“《宋玉集》三卷”,可知《宋玉集》应当编成于隋唐以前。郑良树根据两汉以来赋家、学者所袭用、引述或编录宋玉赋的情况,认为“隋唐时三卷本的《宋玉集》应该保存得相当完整”。郑氏还进一步指出:此书“大概亡于唐代中叶或末叶”,《文选》和《古文苑》分别选录宋玉七篇和六篇作品,“可能是促成《宋玉集》亡佚的主要原因”。由此看来,《古文苑》所收的《钓赋》,源出于隋唐前已经编成,且流传较广的《宋玉集》的可能性是极大的。
《古文苑》所收诗文,均为唐代以前的作品,宋人多以此书为唐人所编。南宋时期的韩元吉记叙其成书过程说:“世传孙巨源于佛寺经龛中得唐人所藏古文章一编,莫知谁氏录也。”稍后江师心所作的《古文苑序》,亦云:“《古文苑》,唐人之所集,梁昭明之所遗也。昭明曷为遗之?盖以法而为之去取也。唐人曷为集之?盖思古而贵于兼存也”,不但指出了《古文苑》的编纂时代,也指出了编纂的原因。今人曹景年研究认为,《古文苑》的成书可能存在着一个不断增补、修订的过程,其中保存的大量珍稀文献当属唐人旧稿,另外三篇石刻文则为宋人所加。从这些论述来看,唐代学者从《宋玉集》中选择《文选》所未收的宋玉辞赋作品,编入《古文苑》的可能性是很大的。高秋凤研究认为 :《古文苑》所载《钓赋》的首句“玄渊”作“元洲”,“洲”应是“渊”之形误,表明其不避唐高帝李渊之讳,则《古文苑》编者所见之《宋玉集》,“必定是隋以前的旧本”。由此可见,《钓赋》的文献来源不但颇为清楚,而且可靠性也很高。因此清代学者严可均所辑《全先秦文》,即将《钓赋》编入宋玉名下。稍后的刘熙载亦相信,《风赋》《钓赋》等为宋玉所作,这种认识不是没有道理的。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批简帛文献的出土,为考察《钓赋》的真伪提供了更多有力的证据。1972年4月,考古工作者在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号汉墓发掘出土了一批竹简,其中有二十余枚辞赋作品残简,其首简背面上端署有“唐革(勒)”二字,赋文中又载有唐勒的话,因此整理者将其称为“《唐勒赋》残简”,并认为其作者可能是战国时期的楚人唐勒。汤漳平赞成该赋作者为唐勒说,但又认为“‘唐勒赋’应是唐勒所有赋作的总称”,而“这是一篇以描写御术为主要内容的赋作”,因此其篇题“似应作《御赋》”。李学勤则根据《古文苑》所收《大言赋》《小言赋》的“体例”,认为该赋的作者“应当就是宋玉”,“按照宋玉传世各赋的标题,《唐勒》最好称为《御赋》”。朱碧莲也赞成此赋为宋玉所作、篇名应拟为《御赋》的说法。关于银雀山一号汉墓的年代,考古学者认为其上限“不会早于建元元年(前140年)”,下限“不会晚于元狩五年(前118年)”,因此可以推知墓主当为西汉初年人,与唐勒所生活的战国晚期相去不远。同墓出土的《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均为先秦古籍,因此尽管学者对《御赋》为何人所作的看法尚不一致,但大多数人肯定此赋应为先秦时期的作品。
《御赋》残简与《古文苑》所载《大言赋》《小言赋》《钓赋》等作品在思想主题、结构模式等方面呈现出较多的相似性,因而促使学者重新思考传世宋玉赋的真伪问题。由于《御赋》残简0184号简上有“唐勒与宋玉言御襄王前”的字句,而此赋在文体方面又呈现出“韵散兼用”“主客问对”和“铺采摛文”的“散文赋”形式特征,因此此前学者认为的《钓赋》等作品内容中存在的“本国本朝人无须称说国名朝名”“战国时代不可能出现较为成熟的‘散文赋’”等说法都不攻自破了。至于《风赋》《高唐赋》《神女赋》《小言赋》等似乎存在某些与先秦古韵不合的情况,胡念贻《宋玉作品的真伪问题》、朱碧莲《宋玉辞赋真伪辨》等论著都对其进行了考辨。汤漳平则将《御赋》残简与《古文苑》所收《钓赋》等作品进行对比,认为它们“都是同一时代的产儿”。郑良树对宋玉作品真伪问题的研究史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回顾与梳理,发现从前怀疑宋玉赋为伪作的理由“的确存在著许多问题”。高秋凤也在全面考察《钓赋》真伪及各家所持论据的基础上,认为《钓赋》“不是赝品,它确实是战国宋玉所撰”。既然此前怀疑该赋为伪作的理由都难以成立,而《御赋》残简的发现,又证明战国时期确实存在着这样的“散文赋”,则自《文心雕龙》以来认为《钓赋》为战国时期的宋玉所作的看法,就应该予以重新肯定。
《御赋》残简的出土,不但廓清了《钓赋》真伪问题的许多迷雾,也使人们更为清楚地看到,先秦时期确实存在着一类以“事理”为题材的赋作。除《御赋》《钓赋》外,《庄子·说剑》篇和《史记·楚世家》所载“楚人以弋说楚王”故事,似乎都属于这一类。这两篇作品在文体上也表现出较为明显的“辞赋化”倾向,明人谭元春即认为《说剑》篇“祗似战国陈轸、犀首辈之言,枚、马、子云辈之赋体”;今人伏俊琏则认为《说剑》篇“带有故事赋因素”。《史记·楚世家》所载故事,明人孙鑛又称其为《弋说》,清代姚鼐所编《古文辞类纂》,则将其归入“辞赋类”。与《御赋》《说剑》《弋说》等分别以“御术”、“剑术”、“弋术”为主题相似,宋玉《钓赋》亦以“钓术”作为贯穿全篇的思想主题。作者在吸收春秋以来儒、道思想的基础上,通过对不同“钓术”内容的形象描绘和巧妙转换,对汉代盛行的“作赋以讽”进行了一次先期的生动实践。深入分析这篇作品所具的儒、道文化背景,实是准确把握其思想主题和创作主旨的关键。
二、“钓术”与道家之“道术”
《钓赋》的开篇说:“宋玉与登徒子偕受钓于元洲,止而并见于楚襄王。登徒子曰:‘夫元洲,天下之善钓者也,愿王观焉。’”接下来“登徒子”和“宋玉”分别向“楚王”讲述了“元洲之钓”和“尧舜禹汤”等“大王之钓”,通过对这两类“善钓”者不同“钓术”的对比,作者肯定了“大王之钓”所具的重要意义,从而委婉地向“楚王”表达了自己的“讽谏”之意。《钓赋》的题材选择和上述文本结构、叙事逻辑等,与其所具的道家、儒家思想背景是密切相关的。
《古文苑》所载《钓赋》文中的“元洲”,实应为“玄渊”。《文选·七发》:“若庄周、魏牟、杨朱、墨翟、便蜎、詹何之伦,使之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李善注云:“《淮南子》曰:‘虽有钩针芳饵,加以詹何、蜎蠉之数,犹不能与罔罟争得也。”高诱曰:‘蜎蠉,白公时人。’《宋玉集》曰:‘宋玉与登徒子偕受钓于玄渊。’《七略》曰:‘蜎子,名渊,楚人也。’然三文虽殊,其一人也。”从李注所引《宋玉集》可知,“元洲”原作“玄渊”,“洲”应为“渊”字之误,“元”则可能为宋人“避宋帝始祖赵玄朗讳”所改。“玄渊”又名“便蜎”“蜎蠉”“蜎渊”“环渊”“便嬛”“蜎子”“涓子”等,《史记》《汉书》均有关于其生平行事、著述活动的记载。《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自驺衍与齐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驺奭之徒,各著书言治乱之事”;又云:“田骈、接子,齐人。环渊,楚人。皆学黄老道德之术,因发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论,环渊著上下篇。”同书《田敬仲完世家》亦载:“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驺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汉书·艺文志》则载有“《蜎子》十三篇”,并自注云:“名渊,楚人,老子弟子。”唐代颜师古注说:“蜎,姓也,音一元反。”东汉应劭《风俗通义·姓氏篇》则云:“环氏出楚,环列之尹,后以为氏。楚有贤者环渊,著书上下篇”,清人张澍注说:“环渊即嬛渊,亦即蜎渊也。”可见《钓赋》所称“玄渊(环渊)”,乃是一位道家学者,其人大概生活于战国中后期,早年为学于楚,后东游齐国稷下,与田骈、慎到等知名于时,并著有《蜎子》等书。
汉初枚乘所作《七发》,称“便蜎、詹何之伦”为“方术之士有资略者”,西汉末期刘向所编的《列仙传》则云:“涓子者,齐人也,好饵术”,“后钓于荷泽,得鲤鱼,腹中有符。隐于宕山,能致风雨”。北魏郦道元《水经注·睢水注》亦载:“芒、砀二县之间,山泽深固,多怀神智,有仙者涓子、主柱,并隐砀山得道。”因“环渊”曾游学于齐,故《列仙传》称其为“齐人”。综合《史记》《汉书》《列仙传》和《水经注》等书记载,可知“玄渊(环渊、蜎渊)”其人实兼有“学者”和“隐士”的“双重身份”,所谓“仙者涓子”,则不过是道教在发展过程中对道家人物故事进行“神仙化”的改编而已。除研究学术外,他在社会生活方面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即“善钓”或“乐钓”,《列仙传》和《水经注》所谓“钓于荷泽”、“山泽深固”等,都直接或间接地表露了这层意思。《淮南子·原道》篇说:‘虽有钩针芒距,微纶芳饵,加以詹何、蜎蠉之数,犹不能与罔罟争得也”,自是将其视为明于“数术”的“善钓”者;三国时应璩《与从弟君苗君胄书》所云:“弋下高云之鸟,饵出深渊之鱼。蒲且赞善,便嬛称妙,何其乐哉”,则又凸显了“善钓”所包含的独特生活意趣。南宋章樵《古文苑注》解释“元洲”之名说:“元,妙也。洲,水边洲渚。言精于钓,故托元洲为名。”其说虽因不明“元洲”为“玄渊”之误,而不免有牵合之处,但将“玄渊(环渊、蜎渊)”之名与其“钓鱼”活动相联系,则又颇为准确地指出了“善钓”对于“玄渊”其人思想和生活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因此《钓赋》的篇首虽止“宋玉与登徒子偕受钓于玄渊”一句,但已为全文设置了一个颇为深厚的道家文化背景,并为下文的叙事和议论垫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
从上文对于“玄渊”思想及其行事的考述,可以看出《钓赋》题材选择与其人物设计的内在关系。故其下文即通过“登徒子”之口,对“玄渊之钓”进行铺陈描绘:“夫玄渊钓也,以三寻之竿,八丝之线,饵若蛆螾,钩如细针,以出三尺之鱼,于数仞之水中,岂可谓无术乎?夫玄渊,芳水饵,挂缴钩,其意不可得,退而牵行,下触清泥,上则波颺,玄渊因水势而施之,颉之颃之,委纵收敛,与鱼沈浮,及其解弛,因而获之。”“登徒子”对“玄渊之钓”的称羡之情溢于言表,这一段描写虽然着墨不多,但颇为生动传神,写出了“玄渊之钓”的独特之处和用心所在。因其下文所写重在“尧舜禹汤”等“大王之钓”,故又借助于“宋玉”之口而对“玄渊之钓”予以排抑:“今察玄渊之钓也,左挟鱼罶,右执槁竿,立乎潢汙之涯,倚乎杨柳之间,精不离乎鱼喙,思不出乎鲋鳊,形容枯槁,神色憔悴,乐不役勤,获不当费,斯乃水滨之役夫也已。”此处虽因着眼点不同而将“玄渊之钓”称为“役夫之钓”,但若将两段文字合而观之,则可以看出“玄渊之钓”所蕴含的道家文化精神,实与《庄子》《列子》等书多有相通之处。
《庄子》《列子》书中均载有不少与“钓鱼”相关的寓言故事。如《庄子·秋水》篇:“庄子钓于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愿以境内累矣!’”故事中的“庄子”因不愿出仕,故述以“楚有神龟”之事,而称“吾将曳尾于涂中”。此篇虽然未涉及“钓术”内容,但“庄子”之“钓”与其“隐逸”之志相关联,其行事实与“玄渊”有相似之处。《庄子·外物》篇所写“任公子之钓”,则应当可视为一种特殊的“钓术”:“任公子为大钩巨缁,五十犗以为饵,蹲乎会稽,投竿东海,旦旦而钓,期年不得鱼。已而大鱼食之,牵巨钩,錎没而下,鹜扬而奋鬐,白波如山,海水震荡,声侔鬼神,惮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鱼,离而腊之,自制河以东,苍梧已北,莫不厌若鱼者。”“任公子”之“钓”,因为志在于“大鱼”,故设以“巨饵”“长竿”,待以“期年”之期。其下文又进一步申论说:“已而后世辁才讽说之徒,皆惊而相告也。夫揭竿累,趣灌渎,守鲵鲋,其于得大鱼难矣。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是以未尝闻任氏之风俗,其不可与经于世亦远矣。”由此而言,则文中所谓“大鱼”,实为“任氏”不追求短期近效的“经世”之“大志”;所谓“任公子之钓”,实为一种与“玄渊之钓”有所不同的特殊“钓术”,其在本质上乃是一种“经世”之道或“治世”之术。可见,这一寓言故事在思想主题和创作主旨方面均与《钓赋》有不少相似之处。
枚乘《七发》将“詹何”与“便蜎”并举,《列子·汤问》篇则载有詹何“善钓”的故事:“詹何以独茧丝为纶,芒针为钩,荆筱为竿,剖粒为饵,引盈车之鱼于百仞之渊、汩流之中,纶不绝,钩不伸,竿不挠。”张湛注说:“詹何,楚人,以善钓闻于国”,“鲲鱼,其大盈车”。可见“詹何”所钓亦为“大鱼”,钓“大鱼”而“纶不绝,钩不伸,竿不挠”,亦可见其“钓术”的独到之处。于是“楚王闻而异之,召问其故”,“詹何”遂向“楚王”讲述了自己的“学钓”经历和“钓术”奥妙:“臣闻先大夫之言,蒲且子之弋也,弱弓纤缴,乘风振之,连双鸧于青云之际。用心专,动手均也。臣因其事,放而学钓,五年始尽其道。当臣之临河持竿,心无杂虑,唯鱼之念;投纶沉钩,手无轻重,物莫能乱。鱼见臣之钩饵,犹沉埃聚沫,吞之不疑。所以能以弱制强,以轻致重也。”此段文字对于“钓术”的阐述,不但具有颇为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容,而且更引人注意的是,“詹何”将话锋一转而向“楚王”指出:“大王治国诚能若此,则天下可运于一握,将亦奚事哉?”可见这一“善钓”故事,亦具有相当明确的“讽喻”目的。
《庄子》《列子》所写“任公子”和“詹何”故事,虽然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其所写“钓术”,实与《钓赋》中的“玄渊之钓”有不少相通之处。《钓赋》中“宋玉”向“楚王”讲述“玄渊之钓”的情形说:“精不离乎鱼喙,思不出乎鲋鳊,形容枯槁,神色憔悴”,与《列子》书中“詹何”所说“临河持竿,心无杂虑,唯鱼之念”其实非常相似,都说明“善钓”者在“垂钓”过程中需要用心专一、聚精会神;“任公子之钓”虽然“期年不得鱼”,但仍不改其志,亦可以看作是其“用心专一”的体现。《钓赋》中“登徒子”所说“退而牵行,下触清泥,上则波颺,玄洲(玄渊)因水势而施之,颉之颃之,委纵收敛,与鱼沈浮”,则又表明“善钓”的另一奥妙,是要因“势”而为、与“鱼”沉浮;“任公子之钓”在遇到“大鱼食之”时:“牵巨钩,錎没而下,鹜扬而奋鬐,白波如山,海水震荡,声侔鬼神”,过程中自然也少不了对“水势”与“鱼力”的把握和考量。《钓赋》对于“玄渊之钓”的描写虽然较为简略,但其所具“用心专一,聚精会神”、“因‘势’而为,与‘鱼’沉浮”等行为特征,与《列子·汤问》篇“詹何”所谓“投纶沉钩,手无轻重,物莫能乱。鱼见臣之钩饵,犹沉埃聚沫,吞之不疑”其实非常相似,实已达到一种心物交融、物我为一的精神境界,“詹何”称此种状态为“尽其道”,可知所谓“钓术”实已臻为一种哲学层面上的“道术”。
《庄子·外物》篇对于“任公子之钓”的描写虽然较为简略,但其书中对于某些生活技艺的描写,与《列子》所写“詹何”之钓则多有相似之处。如《养生主》篇所写“庖丁解牛”的故事,就颇具典型意义。篇中“庖丁”自述其“解牛之道”说,“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导大窾,因其固然,技经肯綮之未尝,而况大軱乎!”又如《达生篇》所写“善游者”:“孔子观于吕梁,悬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鼋鼍鱼鳖之所不能游也。见一丈夫游之。”其人自述其“蹈水之道”说:“吾始乎故,长乎性,成乎命。与齐俱入,与汩偕出,从水之道而不为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同篇所写“痀偻者承蜩”故事,亦与之相似:“仲尼适楚,出于林中,见痀偻者承蜩,犹掇之也。”其人自述其“承蜩之道”云:“吾处身也,若厥株拘;吾执臂也,若槁木之枝;虽天地之大,万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侧,不以万物易蜩之翼,何为而不得!”“孔子”听后称赞说:“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其痀偻丈人之谓乎!”类似寓言故事在《庄子》《列子》中还有不少,但其故事情节和思想主旨则基本相似,都是由“技”而进乎“道”,其人所具之特殊“技艺”,实际上均可看作是其所具“道术”之体现。
《庄子》书中所写“道术”的体现者,如“庖丁”及上述“善游者”“承蜩者”等,亦大多具有“用心专一,聚精会神”“因势而为,与物沉浮”等精神和行为特征,与“玄渊”“詹何”等“善钓”者高度相似。《庄子》本有一种得“神”而遗“形”的思想倾向,从上引寓言故事来看,《钓赋》文中的“宋玉”称“玄渊”其人“形容枯槁,神色憔悴”,其实正可以看作是其内在精神高度凝聚的体现。“玄渊”之钓“因水势而施之,颉之颃之,委纵收敛,与鱼沈浮”,与“庖丁”解牛之“依乎天理,批大郤,导大窾,因其固然”、“善游者”之“从水之道而不为私”,以及“承蜩者”之“处身也,若厥株拘”、“执臂也,若槁木之枝”亦极为相似,都具有一种“无私”“无我”的特点,如此方能达到一种“心物交融、物我为一”的精神境界。从上文对于“玄渊”思想及其行事的考述,可知《钓赋》所写“玄渊之钓”,实可以视为一种“隐者之钓”;其“钓术”所体现的哲学文化内涵,乃是《庄子》、《列子》等书所推崇的道家之“道术”。
从《钓赋》所载“玄渊之钓”的“因势而为,与鱼沈浮”等行事方式,自然可以生发出一种如《楚辞·渔父》所谓“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歠其醨”的处世态度;或如《庄子·渔父》所谓“处阴以休影,处静以息迹”、“法天贵真,不拘于俗”的人生哲学,然而《钓赋》的创作主旨乃在于“讽谏”世主,故而篇中通过两类“善钓”者的对比,进而转向了对“尧舜禹汤”等“王者之钓”的描述,这也正是《钓赋》在叙事结构和思想主旨方面不同于道家诸子寓言的创新之处。
三、“钓术”与儒家之“治术”
《庄子》《列子》所载“任公子”“詹何”等“善钓”故事,虽然“钓术”和“大鱼”等事象已颇具象征意蕴,但其借由“钓术”而对“经世”之道、“治国”之术等进行论述,仍然未完全脱离“钓鱼”活动本身。《钓赋》描写“玄渊之钓”也说:“委纵收敛,与鱼沈浮。及其解弛,因而获之”,可见其叙事仍然具有一定的现实性。《钓赋》下文正是借由其开篇所铺设的这种叙事的现实性,指出“玄渊之钓”其实“乐不役勤,获不当费,斯乃水滨之役夫也已”,转而肯定“尧舜禹汤”等“大王之钓”所具的“非常之乐”和重要意义。
《钓赋》文中对于“玄渊之钓”的非议,主要是从“所得”甚少的角度而言的,其实体现的是一种以“功利”为标准的价值观。《淮南子·原道训》的相关论述,与《钓赋》的这种价值观亦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夫临江而钓,旷日而不能盈罗,虽有钩箴芒距,微纶芳饵,加之以詹何、娟嬛之数,犹不能与网罟争得也;射者扞乌号之弓,弯棊卫之箭,重之羿、逢蒙子之巧,以要飞鸟,犹不能与罗者竞多。何则?以所持之小也。张天下以为之笼,因江海以为罟,又何亡鱼失鸟之有乎?”此篇讨论“钓术”,最后其实亦落实到“天下”大事上。其将“垂钓”与“弋猎”并举,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钓鱼”之所以成为早期文学中一个较为常见的题材,应与上古先民的“渔猎”生产方式相关。《周易·系辞下》说,“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察法于地”,“作结绳而为罔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包牺”也即“伏羲”,由于上古时期的伏羲氏族与“渔猎”生产的密切关系,在后世某些神话传说或图像史料中,伏羲也便成了“人首鳞身”或“人首蛇身”了。随着社会生产的进步,“渔猎”活动的重要性有所下降,“钓鱼”也逐渐从古人获取食物的生存目标中解脱出来,成为一种兼具休闲娱乐、修养身心、颐神益智的社会文化活动。若从物质、功利的角度看,“垂钓”之得可能确实不如“网罟”之获灿然可观;但若从精神、文化的角度而言,则“网罟”之得又似乎不如“垂钓”之获深厚而丰富。《钓赋》正是基于“钓鱼”活动所具的这种内外矛盾关系,而从物质、功利的角度对“玄渊之钓”予以排斥,为下文肯定“尧舜禹汤”等“大王之钓”的精神、文化价值拓展了更大的空间。
《钓赋》对于题材内容的选择,与上文所述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御赋》,以及《庄子·说剑》和《史记·楚世家》所载《弋说》等“辞赋化”的篇章多有相似之处,其所涉“钓鱼”“驾车”“击剑”“弋猎”等内容,亦均与上古先民的生产和生活密切相关。因为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先民在此过程中也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生活经验,亦由于其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较为常见,而这类活动本身又具有较为丰富的生活意趣和文化价值,故而适宜作为一个哲学和文学创作的题材,尤其适宜作为一个讲述某些事理时的“譬喻”对象。由于时人对于“钓鱼”、“驾车”、“击剑”等活动的熟知,因此作者在对其进行铺陈描绘或譬喻说理时,便可以部分地或完全地脱离这类活动本身,而快速进入作者所事先预设的论题。
《钓赋》中“宋玉”与“楚王”的对话,便是基于这样一种历史背景和生活基础:“宋玉进曰:‘今察玄渊之钓,未可谓能持竿也,又乌足为大王言乎!’王曰:‘子之所谓善钓者何?’玉曰:‘臣所谓善钓者,其竿非竹,其纶非丝,其钩非针,其饵非螾也。’王曰:‘愿遂闻之。’玉对曰:‘昔尧、舜、禹、汤之钓也,以圣贤为竿,道德为纶,仁义为钩,禄利为饵,四海为池,万民为鱼。钓道微矣,非圣人其孰能察之!’”“宋玉”所述“尧舜禹汤”之“钓术”,自然与“钓鱼”活动本身相去悬远,无怪乎“楚王”听此而叹曰:“迅哉说乎!其钓不可见也。”“宋玉”则进一步对此种“钓术”之奥妙与功用进行详细阐述:“其钓易见,王不[可]察尔。昔殷汤以七十里,周文以百里,兴利除害,天下归之,其饵可谓芳矣;南面而掌天下,历载数百,到今不废,其纶可谓纫矣;群生浸其泽,民氓畏其罚,其钩可谓抅矣;功成而不隳,名立而不改,其竿可谓强矣!若夫竿折轮绝,饵坠钩决,波涌鱼失,是则夏桀、商纣不通夫钓术也。”合而观之,“宋玉”实际上向“楚王”讲述了两类“钓者”:一类为“尧舜禹”等传说中的上古“圣王”和“商汤”、“周文”等“开国之君”,一类则为“夏桀”、“商纣”等“波涌鱼失”的“亡国之君”,而其所谓“钓术”,实际上乃是上古以来的王者“治国”之术。就此而言,《钓赋》的思想主旨,与《庄子·外物》和《列子·汤问》篇以“任公子之钓”“詹何之钓”譬喻“经世”之道、“治国”之术并无根本的不同;但另一方面,《钓赋》又通过对“玄渊之钓”和“尧舜禹汤”之“钓”的对比,而实现了“钓术”所象征的思想文化内涵,由“玄渊”所代表的道家之“道术”,向“尧舜禹”和“商汤”、“周文”等所代表的儒家“治术”的转变。
《钓赋》文中所列举的“尧舜禹”和“商汤”“周文”等人物,本是战国时期的儒家学者孟子、荀卿等所常道的“古圣先王”的典型。如《孟子·公孙丑下》载孟子之言说:“我非尧、舜之道,不敢以陈于王前”;同书《滕文公上》亦载:“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同书《离娄上》则云:“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不可法于后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可见在孟子看来,“尧舜之道”即“先王之道”的代表,“先王之道”亦即“圣人之道”,其思想实质是“仁政”和“德治”;“商汤”、“周文”之所以兴起,亦主要是因为“重德”和“行仁”。《孟子·公孙丑上》说:“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因为他们实行“仁政”和“德治”,故而为天下民众所归往:“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因为“得民”,所以“商汤”、“周文”能够得“天下”。《孟子·滕文公下》又云:“尧、舜既没,圣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夏、商两朝的“桀”“纣”便被看作是这类“暴君”的代表,《孟子·离娄上》分析指出:“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桀”、“纣”等因为“暴虐不仁”而大失“民心”,因为失去“民心”而最终失去了“天下”。从这些论述来看,《钓赋》将“殷汤以七十里,周文以百里,兴利除害,天下归之”视为真正“善钓”的体现,正是对孟子“以德行仁”的“仁政”思想的一个形象譬喻;而“夏桀”、“商纣”等“竿折轮绝,饵坠钩决,波涌鱼失”,则又生动地说明了“王者”失去“民心”的巨大危害。
战国时期的另一位儒家学者荀子,其政治思想则与孟子略有不同。孟子主张法“先王”而行“仁政”,荀子则主张既法“先王”之道,亦取“后王”之术。如《荀子·儒效》篇说:“儒者法先王,隆礼义,谨乎臣子而致贵其上者也。”同篇又将“法后王,一制度,隆礼义而杀诗书,其言行已有大法”者称为“雅儒”。具体而言,荀子政治思想主要包括了隆“礼义”、尊“道德”、尚“贤能”、用“庆赏”、严“刑罚”等内容,如《荀子·王制》篇云,“贤能不待次而举,罢不能不待须而废,元恶不待教而诛”;“故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欲荣,则莫若隆礼敬士矣;欲立功名,则莫若尚贤使能矣”;“无德不贵,无能不官,无功不赏,无罪不罚”;“全道德,致隆高,綦文理,一天下,振毫末,使天下莫不顺比从服,天王之事也”。值得注意的是,孟子论政体现出一种重“仁义”而轻“利禄”的思想倾向,如《孟子·梁惠王上》载其对“梁惠王”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荀子则颇为看重“利泽”在“王道”之中的重要性,如《富国》篇说,“量地而立国,计利而畜民,度人力而授事”;“儒术诚行,则天下大而富,使而功”;《王霸》篇则云,“汤武者,修其道,行其义,兴天下同利,除天下同害,天下归之”;“百姓贵之如帝,亲之如父母,为之出死断亡而不愉者,无它故焉,道德诚明,利泽诚厚也”。由此而言,《钓赋》文中所谓“兴利除害,天下归之,其饵可谓芳矣”、“群生浸其泽,民氓畏其罚,其钩可谓抅矣”,实又显示出其“治术”理论与《荀子》思想的内在关联。
孟、荀儒学思想虽然有上述不同,但在对“民”的重视方面则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如上所述,孟子认为“商汤”“周文”之所以兴,主要在于“得民”;荀子亦反复强调“爱民”“利民”对于“王道”政治的重要性,如《王制》篇说:“王夺之人,霸夺之与,强夺之地。夺之人者臣诸侯,夺之与者友诸侯,夺之地者敌诸侯。臣诸侯者王,友诸侯者霸,敌诸侯者危。”《君道》篇则云:“故有社稷者而不能爱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亲爱己,不可得也”;“故君人者,爱民而安,好士而荣,两者无一焉而亡。”孟子、荀子的此种“民本”思想,反映在宋玉的《钓赋》中,则为“得鱼”或“失鱼”:“商汤”“周文”等因“得鱼”而得“天下”;“夏桀”“商纣”等则因“失鱼”而失“天下”。其篇中所说“昔尧、舜、汤、禹之钓也,以圣贤为竿,道德为纶,仁义为钩,禄利为饵,四海为池,万民为鱼”,实可以看作此种儒家“治术”思想的总纲;而其篇末所云“王若建尧、舜之洪竿,摅禹、汤之修纶,投之于渎,视之于海,漫漫群生,孰非吾有?其为大王之钓,不亦乐乎”,亦是在强调“得鱼”的重要性,实际上是以儒家“民本”学说作为全文的思想旨归。吴广平研究认为:宋玉“继承了孔子的‘德政’思想和孟子的‘仁政’思想”,主张“以民为本,推行仁政,以德治国”;刘刚则进而指出:宋玉思想“与同时代的荀子的新儒学比较接近”,因为荀子“义与利并重,礼与术兼用”。从上文分析来看,宋玉所受战国时期儒家思想的影响,在《钓赋》中体现得较为明显,并表现出一种兼融孟、荀儒学思想的倾向。

四、结 语
清人章学诚说,“古之赋家者流,原本诗骚,出入战国诸子”,“虽其文逐声韵,旨存比兴,而深探本原,实能自成一子之学”。近人刘师培则将早期辞赋分为“写怀之赋”“骋辞之赋”和“阐理之赋”等三类。从题材类型上看,宋玉《钓赋》正是较为典型的“阐理之赋”。就《钓赋》所蕴含的思想内容看,“玄渊之钓”所代表的道家之“道术”,多注重从一己之身心体验出发,通过对心与物、天与人关系的认识与推求,从而达到一种“心物交融、物我为一”的精神境界,由此而衍生的道家之“治术”,如《钓赋》文中所说的“因势而为”“与鱼沈浮”等,亦是此种宇宙观、世界观的具体体现。尧舜禹汤等“大王之钓”所象征的儒家“治术”,则大多基于“古圣先王”的历史经验,以“爱民”“利民”“得民”等作为施政目标,以“仁政”“德治”等作为其思想旨归,这即所谓“先王之道”和“圣人之道”。《钓赋》文中的“钓术”,正是此种不同的“治术”“道术”的象征。《钓赋》也正是通过对不同“钓术”“道术”内容的巧妙转换,准确地实现了对“楚王”的“讽谏”意图。因此明人陈第评论宋玉的辞赋创作说:“体制颇沿于其师,风谏有补于其国。”清人浦铣亦认为:“宋玉《钓赋》,可为讽谏法,当与庄子《说剑》篇参看。”两者可谓从不同角度,指出了宋玉的《钓赋》等作品,对于辞赋文体功能的开拓及其在思想史上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