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执:每个持续写作的人,一定有他非写不可的理由
2020-01-13蒯乐昊
蒯乐昊

两年前,郑执的短篇小说《仙症》,在“匿名作家计划”比赛中获得了首奖。“匿名作家计划”是由理想国、文学期刊《鲤》和腾讯大家等平台联合发起的一个旨在“以透明致敬匿名”的文学奖项——无论是文学大家还是无名小卒,在这个赛事里都会被封卷匿名评选,以保证奖项的公正,对抗小圈子的人情操作。
这像是一场无差别格斗,参赛者在年龄、性别、题材上均无限制,只需严格遵守一条规则——必须以匿名的方式呈现自己的短篇小說,评选委员会由5名初评评委与3名终评评委组成,在匿名面具揭开之前,终评评委的密室讨论,会以全程直播的方式呈现在观众面前。
“很多借《仙症》一篇才初识我的朋友,满怀期待地购回我几年前的旧作(多指比上一本长篇《生吞》更早以前的两本集子),阅后大失所望,惊呼‘写出《仙症》的作者竟然还写过这种东西——说实话,这也在我意料之中,幸好这两年学着脸皮厚了不少,搁前几年得找堵墙撞半死。”在新近出版的同名小说《仙症》一书的后记里,郑执这样写道。
为了生存,他也写过挣快钱、不走心的网络文学,他也确实有写出爆款的能力,而这次是他的重新出发之作。当然,不管作者如何试图跟过去有所区别,《仙症》收纳的六个故事依然带着强烈的郑执属性:外冷内热,长于叙事,绵密而紧致,在逻辑构建上呈现出一种近乎偏执的榫卯感,也像一个重勾拳连续出击的选手。小说集里最后一个中篇《森中有林》是在疫情出不了门的时候写的,6万字,在北京自我隔离,听起来是双份的隔离。他每天早上起床,先照把镜子,跟自己说,这次写作对自己就一个要求:要脸。
现在骗子都这么有文化了吗?
很多人了解郑执,是从他在“一席”的演讲开始的,作为小说家,他已经小有名气。东北青年作家群体似乎形成了一道新的文学景观,他和双雪涛、班宇,常常被放在一起谈论,被戏称为“东北文艺复兴三杰”,或者加上贾行家,成为“东北F4”。
在“一席”上,郑执分享了两个故事,一个是关于他的父亲,一位市电容器厂销售科副科长,如何在东北的工业萧条期,靠经营一家抻面馆撑起了全家的生活,又如何在商业化的浪潮里被席卷走了辛苦攒起的全部身家。另一个故事是关于“穷鬼乐园”,东北最廉价的酒馆,十块钱可以买五个扎啤,从早喝到晚,这是那些被生活欺负过的人们最后的避难所。有的人把自己喝死了,有的人东山再起去了远方。如果站在一个足够远的维度看,这两个故事也许就是同一个。
郑执的文学天赋在中学就初露苗头,可是他偏科太严重了,理科成绩全年级垫底,加上早恋、贪玩,自暴自弃。语文虽好,但他不晓得这种好有什么用,就像少年仗剑而不自知。
“我们中学是一个很有名的重点学校,重理轻文。我青春期最剧烈的精神困苦,就在那几年,我后来跟我妈聊过这事,我说虽然你们没有这个意识,但当时哪怕我身边有个叔叔阿姨之类的长辈,是从事文艺工作的,能直接点拨我一下,说郑执适合干这行,我也许就不至于那么困苦。我只知道我喜欢写,我善写,但我一直不知道能拿它来干什么。”
东北每年都要下几次大雪,只要一下雪,老师就会组织学生一起扫雪,“那段时间我只要一走进教室就会变得非常压抑,我就故意消极怠工,故意让老师罚我一个人留下。等他们都进教室之后,我就一个人站在雪地里,也不知道在干什么,抬起头任雪花冲撞在我的脸上,脑子一片空白。”
最长的时候,他曾经连续三个月不说任何一句话,妈妈甚至带他去看了心理医生。
高考第一志愿落榜,郑执没想到他的命运竟然在这里发生了反转,当时有几所香港的大学在辽宁开展自主招生,要求全英文面试,英语成绩占总成绩的一半。郑执的中文跟英文还不错,老师就推荐他去试一试,结果一试即中。“当这个录取成绩传出来之后,我突然从一个失意的落榜考生,摇身一变成了本地媒体大肆报道的素质教育成功典型,很魔幻。”
他的长篇小说处女作写在19岁。高考前一个月,他已经彻底放弃了复习,破罐子破摔,“那时候幼稚,就觉得我的青春期还挺复杂的,也经历了一些事,好想表达,就突然开始在草纸上瞎写。”
他不知道写作有什么用,如果说写作有用,那也就是写给好朋友看吧。中学里的同窗一毕业就会四散各地,有去北京、香港,有去新加坡和美国的。他们问郑执,你还没写完吗?等你写完了我们也看不到了,不如你贴网上连载吧,走到天南海北都可以看到。
故事在搜狐读书频道写到一半,他在香港的一个哥们儿把文稿给自己的爸爸看了。那位父亲是做版权保护的,算是行业中人,他觉得郑执写得不错,应该写完。这给了郑执很大的鼓励。“从那时开始我就突然态度严肃了,我觉得我应该认真把它写完,写完就去出版社投稿。”
怕错过重要信息,他把沈阳家里的电话留给了编辑,那段时间,他三天两头从香港给家里打电话,其实是想听到好消息。“有一天刚好只有我爸在家,我说,爸,你今天有没有接到什么人的电话?我爸想了想说,有,一个骗子,我给撂了,他说要给你出书,现在骗子都这么有文化了吗?”
命运有时候也像一个编剧
当时郑执在香港的TVB实习,TVB要开普通话台,要招主播,郑执和一个女生朋友去应聘,应聘之后,TVB说项目还在筹备,让他们开工干活,一边学剪片子一边等消息。“剪了三个月,实习工资很少,那时候我把电影剪辑软件Premiere什么的都学会了,结果发现不对,TVB的主管又已经在面试广院科班出身的主播了。我说那你啥意思?你拿我们当苦力?”
他不会说粤语,TVB主管不会说普通话,想吵架还得带上翻译,他拉着那个女孩一起去,嚷嚷着要辞职。制片人说你要辞职的话你记住TVB从此封杀你,以后你毕业了再也不能来TVB找工作。他记得制片人指着他鼻子骂:你呢种人将来喺社会上一定扑街。而他逼着女同学翻译骂回去:老子回去当作家了!老子不上街就不会扑街!
他倒粗中有细,女同学一时义愤也想跟着辞职,他骂完还转头劝女孩别辞,“你跟我不一样,你是学电影电视专业的,再坚持一个月你就转正了。”女孩听了他的,没辞,第二年选上了港姐。
命运常常就是以这样的面目出现。郑执从TVB拂袖而去的时候并不知道,家里的生意已经完全倒闭了。父亲跟朋友合伙做生意,贩了一批爆米花机去秘鲁,结果被中间人骗了,血本无归,紧接着又买了不靠谱的股票,靠一碗一碗面攒下的家底就基本归零了。他只是在旺角街头临时起意给爸爸买一双带气垫的名牌好鞋,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给父亲买礼物。几天后,他接到了母亲的电话:父亲病重,他得回家。
“结果当我走进病房那一刻,我蹲下想给他试穿这双鞋,我才发现由于并发症,他的脚已经比原来宽了两倍,鞋的码数并没有错,但他已经完全穿不上了。一个儿子一生中唯一一次给父亲买的礼物,就这样作废了。”父亲已经癌症晚期,大夫很明确地告诉家属,病人只剩下最后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郑执并不迷信,但是冥冥之中,总有一些巧合让他心惊。父亲亡故之后,为了继续在香港的学业,他借下了高利贷,一毕业身上就背着二十几万的债,利滚利增速惊人。当时他在香港一家出版社当编辑,收入扣掉高昂的房租,连生活都不太够。他每天喝大酒抵抗抑郁,超市里的酒按价格分类,最上面的最贵,而他总是一进去就直奔最底层的酒架,有时候促销,39元能买两瓶——因为总喝最差的酒,最终把自己喝进了医院。
这似乎是他在精神上最接近父亲的时刻。他短暂地戒了酒,并写了一个以父亲为原型的长篇小说。一年后,这篇小说被一家影视公司买走了影视版权——钱在他的银行卡里只停留了半小时,就被他迅速地换成了港币,打给了高利贷公司。因为那笔钱不多不少,刚刚够他还清所有高利贷。就好像是父亲在另一个维度里,拉了他一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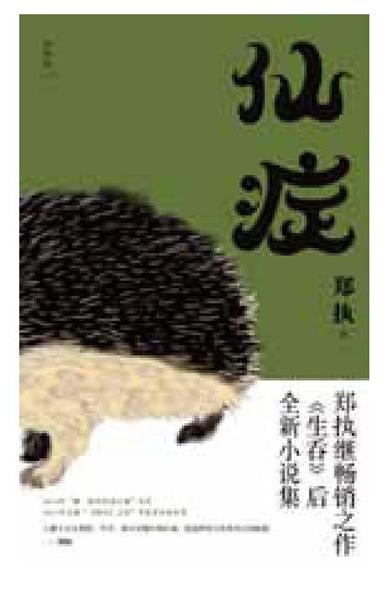
大年三十,爷爷穿墙而过
选择《仙症》作为新书的标题,不仅仅是因为匿名作家奖项作品带来的知名度,更因为这个带有几分神秘色彩的题目,又含着疾病的隐喻,似乎凝炼了小说集里全部故事的气质:它们是现实的,贴地的,烟火气的,但在某一个瞬间又是超现实的,仿佛飞升了起来。
幻想自己在潜艇服役的精神病人,在私奔当天变成食人熊的男孩,临终希望得到宗教慰藉的父亲,突然不举的健美先生,破绽百出的婚姻男女,加起來一共只有五只眼睛的一家四口……郑执并非刻意写“症”,他在意的是人世的畸零。
狐黄不过山海关,自来迷信在东北就有极好的群众基础,这是萨满的遗存。《仙症》里的王战团,因为吃了“狐黄白柳灰”中的“白三爷(刺猬)”,一生都没有起色。他们受困于生活,也受困于难以解释的外力,这跌跌撞撞的人间呈现出一种超乎善恶的面目,而人在命运面前无解。
在台湾学习了戏剧的郑执回到北京,用当影视编剧的收入,养活自己的纯文学写作。他也见惯了影视圈里的迷信习俗,“影视,按古话是梨园行,在中国传统行业里面属于捞偏门的。”捞偏门就得求庇佑,就得有所敬畏。就得信。至于他自己呢?他陷入了沉思。
他记得在他两岁半的时候,大年三十的早上,他见到他的爷爷从玻璃窗里穿窗而过。“我清楚地记得那是我所有人生记忆的开启点。他是一个虚幻的影子,从玻璃穿过来,然后摸了我,就是一个很温馨的回忆,没有任何害怕。神奇的是我本来也不知道爷爷长什么样子,但我就知道他是谁。”
他说,幸亏家里当时有他的妈妈和奶奶为他作证,不然大人一定会认为他在撒谎。妈妈和奶奶发现他在家里围着房子乱跑,奶奶家靠扎花圈为生,房子里放满了花圈。奶奶还熊了他一句:你满屋瞎跑啥呢?跟狗子似的。他解释说:我领着爷爷看看咱家新房子呢。
女人们瞎得汗毛倒竖。郑执的爷爷在他出生前就去世了,他是家里最小的孩子。爷爷临走前就两个遗憾,一是没能见到最疼爱的小儿生娃,二是没等到家里的拆迁房,一辈子没住上楼房。“他回来就是要同时完成这两个心愿。”
“我小时候表达能力天生就很好,我说我看见我爷了,我爷特别高,穿一件深蓝的衣服,有4个兜,领子是这样的。奶奶跟我妈说,她爷死前火化穿的可不就是他那身中山装么?我爷爷是一个非常帅、爱美的人,身高一米八几,他临走前特意跟我奶奶嘱咐,不要穿装老衣,太丑了,穿得像僵尸似的,我要穿那个我最喜欢的中山装入火炉。”
18岁时离开沈阳去香港,出发前跟奶奶告别,奶奶拿了照片给他瞧。“就是那种摄影店里的合成照片,底下其实是孙中山和宋美龄的身子,上面给P上我爷爷奶奶的脸。”那是他第一次看到爷爷的照片,“完全就是我小时候看到的样子。”
电影和文学的拔河
这是无法解释的奇情,小时候因为家中扎花圈,他认识的第一个字,就是花圈中心的“奠”。大了学写书法,要写繁体字,才发现自己的姓氏“郑”,繁体字(鄭)里左边就是一个“奠”字。
即便如此,他依然是一个不语怪力乱神的人,相比于神鬼之说,他更相信人世间的秩序和正义。灰色地带见得越来越多,但他对黑和白依然怀有一种少年式的信仰。他之前一个17万字的悬疑长篇《生吞》,写的就是这种黑白之争。虽然黑有时会占上风,但是白会抱着一种宁为玉碎的决心与黑同归于尽。这种对正义的理解,到了《森中有林》变得更加浑成。
他对通俗怀有执念,那也是更符合他文学审美的东西——浅近、质朴。像他这几年开始喜欢的史铁生、汪曾祺、余光中——“他们没有故意写得深奥,这才是最好的中文。”
即便是面对电影行业也是如此。拍出一部忠于个人审美的文艺片并没有那么难,难的是让大多数人get到。从这个意义上说,好的商业片比文艺片更难,好的通俗小说,比不在乎读者懂不懂的纯文学更难。换言之,表达自我是容易的,但在表达自我的同时,找到与他人的最大公约数总是更难。他写《生吞》,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赌气式的自证。因为他的哥们儿在喝大了酒之后问他:郑执你也写了这么多年,你写过一个畅销的没有?就那种一说标题,大家就都看过的那种……
“所有写东西的,谁不希望自己的东西被更多人读呢?那种写完要锁在柜子里,死后还要让朋友把稿子烧掉的,说实话我不是特别理解。”
他能很清楚地报出自己在文学阅读上的师承:蒲松龄、爱伦·坡、余华、川端康成、马克·吐温,再加上一部分的福克纳和一部分的海明威……这也似乎能简单粗暴地跟他身上的一些标签相咬合:悬疑,惊悚、社会写实、致力于冷冽短句的硬汉派,但这并非他在文学追求上的全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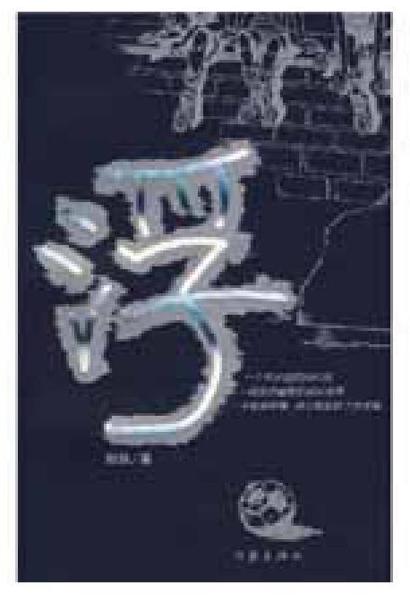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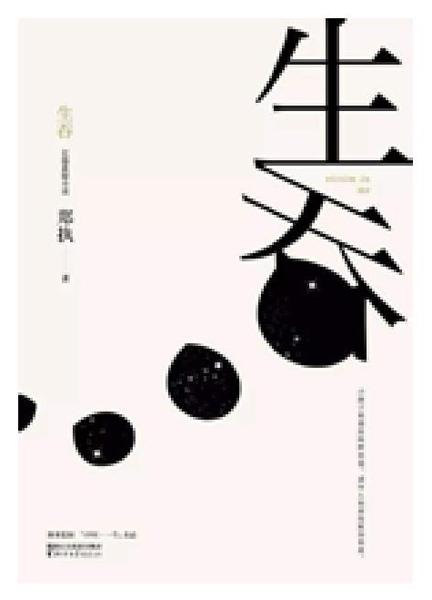
做影視编剧的经验,反过来也会影响他的小说,他的小说是公认的便于改编——《生吞》、《仙症》也都已经在影视化的过程之中。戏剧传播中该有的戏剧冲突、情节节奏、人物设置,甚至对话台词和场景感,他玩得很纯熟,他有很强的逻辑感,这种要把故事编圆的冲动有时候过于强烈,他的小说因此呈现出一种紧密的编织质地,有类型片的结构和气息,对于阅读者来说,这是十分容易沉浸其中的一张网。
还是小说更自由,更个人化,相比之下,电影创作像是一种集体劳动。开一个会,吵八百回。“这件事儿就没有办法,说好听一点是大家不在一个审美体系内,说难听一点,审美就是分高低。高的跟低的不能互相说服,就只能干生气。”
导演里头,他迷是枝裕和以及李沧东,李沧东新近中文出版的小说《烧纸》,他特意细细读了。“他的电影特别有文学性,所以一听说他在文字上也有输出,我就马上找来看。他的文学水准在导演里是一等一的,但把他放在作家里看,就觉得还是写得小。作为玩票可以,写得也有意思,你要带上电影的滤镜去读他的文字,几乎可以想象出来每个镜头他要怎么拍,但作为专业作家去考量,可能就没那么好,没那么够看,他的笔墨不如他的影像般配他的叙述。”
这是一种独特的审视,来自一个一只脚踩在文学而另一只脚踩在影视里的写作者。而这种审视,每时每刻,也必将发生在他自己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