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痛不欲“生”中国无痛分娩进程录
2020-01-13邓郁方沁程馨雨夏勉陈媛媛
邓郁 方沁 程馨雨 夏勉 陈媛媛

广州妇女儿童医疗中心麻醉医生(中)和助产士在为产妇配药,做无痛分娩术前准备。图/本刊记者 大食
2017年8月31日20时,陕西榆林市第一医院绥德院区,产妇小马带着腹中已过41周胎龄的宝宝,从5楼坠下,母婴双双殒亡,留给世人无尽的叹息。
小马当时的身体状况是否符合她要求的剖宫产指征,事故的具体始末和双方担责,至今仍不明晰。但可以确定的是,因为产痛到了生无可恋,最终导致小马迈出悲剧性的那一步。
如果她当时能用上无痛分娩,一切会不会是另外的走向?
已经去世三年的当事人及其家庭、事发医院,都无法再回答这个问题,但它并非一个无谓的追问。
世界卫生组织(WHO)早已把孕产妇死亡率作为衡量社会发展和文明程度,以及国民健康素质的重要指标。但很多人是从榆林事件之后,才惊觉“产痛真的能致命”。社会也终于意识到,为产妇减轻痛苦,是对生命个体的尊重,也是生育文明的进步。
2018年11月,国家卫健委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开展分娩镇痛试点工作的通知》,2019年3月,913家医院成为首批分娩镇痛试点。在试点运行一年多后的2020年年终,这些医院正面临着第一波的考核“验收”。
接受本刊采访的多位麻醉学专家相信,中国产妇的“无痛分娩时代”正在到来,并对前景审慎乐观。而我们所关注的则是,一个并不高难的镇痛技术,为何在中国迟迟没有大规模推行,使得九成产妇难以享受到舒适的分娩?借由这回管窥一豹的采访,我们能够看到:文化与医学观念的分歧、团队配合度、麻醉科医生的人力掣肘、收费与医保、医院管理者的意识,共同决定了这个早就该改变的局面。
一根导管带来的“轻盈”
从1980年代至今,中国陆续引入椎管内镇痛技术、静脉镇痛、经皮神经电刺激疗法(TENS)、心理疗法、导乐等不同的分娩镇痛方式,目前统称和采访所涉及的“无痛分娩”,基本指的是使用广泛、效果确切的持续硬膜外镇痛技术。
原理和常用的剖宫产麻醉一致,即在产妇腰段脊柱硬膜外放置一根导管,连接输注泵后,持续给药,但药物剂量不到后者的八分之一:“所有痛觉的产生,都是先传导到脊髓,再从脊髓上传到大脑。椎管内麻醉就是从脊髓的位置把信号阻断,不再进一步传导到大脑。”经过医生评估,只要没有颅脑高压征、凝血功能障碍、药物过敏史、败血症、腰部局部皮肤感染这些禁忌症,产妇都可使用这项技术。
真的可以立马无痛?
那些尚在待产,或还未怀孕,或者已经生产、但没有使用过镇痛的女性,很难不生此疑问。
知乎的相关提问里,八成以上的亲历者都给予了肯定的回答。本刊记者在为期一个月的实地采访里,也有三四位产妇,回答惊人的一致:“真是生命之光!人类之光!”
另一句频率很高的描述,当数“从地狱到天堂”。
通往那个宁静境界的路径,其实很短,一般麻醉科医生用5到10分钟即能完成。
11月18日晚间,在浙江温岭妇幼保健院产房无菌手术室,麻醉科医生梁刚正在给产妇小青讲解:“打无痛针不痛的哈,腿弯起,尽量抱着膝盖”。
让宫缩袭来的产妇把腰背弯成“虾米”状,并不简单,但产妇都会尽量配合医生。“这样能将后背充分舒展,椎关节的间隙扩张至最大。”梁刚解释。
在助产士的协助下,梁刚给小青进行了背部消毒。小青弓着腰,嗓子里发出“嗯……啊……”的呻吟——又一阵宫缩来了。这意味着麻醉科医生要迅速把握好时机。
铺上无菌洞巾,确认好穿刺位置后,梁刚开始给小青打局部麻醉:“有点胀,一下就好哈。”接下来,他把穿刺针打到硬膜外腔,再将一根细细软软的管子通过穿刺针放置到硬膜外腔,留置并牢牢固定在产妇的后背,管子一头连接着控制泵。他设置好泵的给药参数,简单教会了小青一些注意事项。
就是这么一根直径不到两三毫米的导管和其中的镇痛药物,改善了千万产妇的生育质量。

广州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助产士在为产妇讲解镇痛泵的使用。图/本刊记者 大食
打完无痛针,小青和同在待产室的另两位产妇躺在床上,平静地休息。我们没有再打扰她们。更多人在事后分享了那种独特的生理变化,“后背有冰凉感,慢慢出现下肢、臀部发热发胀,直至感觉消失。”“觉得自己好像浮在温暖的河流里,浮在水面上。”
專家指出,硬膜外分娩镇痛也会有低血压等不良反应,但几率非常低。由于用药剂量很小,而且硬膜外用药并非静脉,进入妈妈血液循环微乎其微,药物很快就会代谢掉,无痛分娩对哺乳没有负面影响。很多产妇担心的产后腰疼或头疼,目前也没有科学论证与硬膜外操作有关。
漠然与领悟
关于产痛,一千个产妇能给出一千种描述。譬如:像潮水般涨了退,退了又涨上来;身体被粉碎,骨头都快被拉开;感觉肚子和腰在被人用锤子使劲锤,拿刀子捅;就像腰被掰折一样,可怕的是掰折之后几分钟又会重复……
即便看过再多书或道听途说,实际的疼痛感依然远远超出预期。
但对于她们的遭遇和感慨,并不是人人都领情——也包括和她们同样性别的过来人。
“大家都生孩子,怎么就你怕疼呢?”此种论调屡见不鲜。在国内多家医院产检区做随机访问时,一位准爸爸表示,“产痛是人类的正常生理现象,你没办法的。”还有老人觉得,“女人疼一疼,对身体五脏六腑有好处的。”
“我是人工引产的,点了缩宫素进产房,到下午一两点宫缩就特别疼了,我说徐老师赶紧给我打上无痛吧,我受不了了。那會儿也不需要接泵,我也懂一点,自己就给推上了,等宫口开全之前,我就一点痛感都没有,(被她们扶着就)上产床了。”
也是在上世纪90年代,武汉协和医院麻醉科医生姚尚龙出国参加美国麻醉医师协会年会,接触到了分娩镇痛技术,耳目一新。回来后他便临床尝试,“做了有两三千例,也发表了文章。”但因为新观念还未深入人心,难以推行下去。2000年,南京妇幼保健院尝试推行分娩镇痛;2001年8月,北大医院规模化开展无痛分娩,并从次年2月起开办培训班向全国推广这项技术。因为“以身实验”成功,曲元成为这条路上坚定的探索者。
2008年,时任美国西北大学芬堡医学院麻醉学副教授胡灵群有感于国内产妇的生产状况,发起“无痛分娩中国行”,带领近千人次的美国医护人员来华,与国内一百多所医院合作,推广分娩镇痛,宣扬现代产房理念。同一年,北京妇产医院麻醉科教授徐铭军也发起了“康乐分娩镇痛全国推广项目”,加上北大医院2018年发起的“常春藤·无痛分娩基层行”等,类似的推广和教学培训活动在各地风生水起。
“规模化之后,也要得益于麻醉技术的发展。”说到这里曲元才露出一丝微笑。“因为分娩镇痛发展至今的一大特点就是,药物低浓度使用时会产生感觉神经和运动神经阻滞分离,明白吧?我只是把你的疼痛感觉阻滞掉,而运动神经没有被阻滞,实现专业指导下‘可行走的分娩镇痛。”(对于这一点,中美医学界目前还存在异议)
新技术的应用总会有曲折,何况分娩镇痛这样涉及不同学科的项目。
“产科也分两派的,因为它毕竟是药物镇痛。产科最大的顾虑就是说产程延长了,或者因有创性穿刺、并发症之类的。2000年前后,我们院产科有一个医生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一篇文章,说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生孩子是属于自然过程,产痛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要镇痛应该主张非药物性镇痛对吧?这种说法盛行一时,到现在也还有这么想的。

北大妇儿医院麻醉科主任曲元。图/宋词
而且他们老觉得产房是他的地盘,你们过来打无痛好像抢了他的饭碗似的。如果你真的把剖宫产率降下来了以后,产科的利益的确受一些损失,它的剖宫产补贴怎么办?这也是一个具体的问题。”
曲元说的现象,在从大城市到基层的不少医院中都得到印证。“麻醉科的工作性质是比较被动的,一旦做了无痛,胎儿胎心不好了,产科很容易扣在麻醉头上,就把好事变成坏事了。”
2014年12月,《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享受无痛分娩产妇比例不足1%》的文章。专家估计目前全国平均值大约在10%到20%之间。曲元最近去四川、内蒙等地基层帮扶,一些地方剖宫产率还在七成到九成。“高剖腹产率造成一个问题,产科观察产程的这些基本功都不会了,武功废了。你说一家医院剖腹产都到90%多了,还要助产士干什么?”她质问道。
“逆行人”
和曲元相比,四川乐山医生吴健雄的无痛分娩之路,更像一次艰难的“逆行”。
2007年,刚从一家县级医院跳槽到乐山市妇幼保健院,吴健雄开始接触到专业的产科麻醉。
他记得在西南医科大学上学时,《临床麻醉学》的最后一章有几页讲到分娩镇痛技术,但写得不细。后来他在丁香园网站、新青年麻醉论坛上陆续看到一些讨论,包括专家在论坛里发的帖子,跃跃一试。
两年后,当护士的妻子程静怀孕,夫妇俩都希望能“正生”(顺产),他也渴望能亲手给妻子推上关键的一针。没想到临产那天B超查出孩子枕后位,最终只能剖宫产。“有剖宫产的指征,没办法。算是一个小小的遗憾吧。”
但在剖宫产手术前,吴健雄到底还是为妻子实施了无痛操作。“一个是减轻了疼痛,还有一个就是剖的时候,就没有再做穿刺了,更加有效和安全。”他几次跟本刊记者强调,“大家一般只知道无痛分娩可以消除产妇疼痛和疲劳,但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在紧急情况下,需要剖宫产时,通过置管处给药,可以免去了再次椎管穿刺的过程,节省了手术前的准备时间。等于是为分娩增加了一道安全保险。”
他渴望能在所在的医院推行这项技术,让更多产妇体会到“福利”。但医院并不支持。他干脆辞了职,考到几十里外的犍为县妇幼保健院。
吴健雄说,换到如今的年纪,恐怕不会那么鲁莽,但当时就有些年少冲动。“从市里跳到县里,很多人都不理解,妻子也说我固执。犍为的医院会不会同意我的想法也是未知数。但我就是想在这方面有所作为,对自己的业务能力也很自信。”
2013年以前,犍为县的剖宫产率已近80%。“好像大家都觉得剖宫产比正生更安全。你想嘛,时间更短,医生劳动强度低。加上收益也不一样,剖宫产几乎都比顺产要多一倍到两倍的收入。”犍为妇幼保健院一名领导解释。
“有些家庭,明明产妇身体条件很好,到医院就奔着‘剖而来。他们觉得,有资本做得起剖宫产,是很值得炫耀的一件事——看,没本事的人才做顺产呢。”说起这,吴健雄直摇头。特地挑选黄道吉日吉时动手术,被称为“择期剖宫产”,至今在全国医院都有。
2016年,全国的“降剖行动”风潮也刮到了大西南。四川省提出各医院必须把剖宫产率降到50%以下。
那几年,吴健雄每晚都住在办公室,到周末才能见上孩子。在领导眼里,这个年轻医生很执着,也有点“社恐”。“他好像没有别的爱好,一门心思钻到这个里头。碰到不懂的地方就在网上咨询胡灵群。每完成一个病人的镇痛,就会跟团队分享总结。但除此以外就不太说话,好像闲聊都是浪费时间。”院领导回忆。最近五年,犍为县妇幼保健院的分娩镇痛率平均能达到七成,今年截止到10月,镇痛率在83%以上。

曾在四川犍为县妇幼保健院工作5年、大力推动无痛分娩的吴健雄,如今在乐山市中医院工作。图/雷宇
吴健雄遇到过17岁的少年孕妇,也处理过年过半百、孙儿在旁的高龄产妇。给17岁姑娘做无痛前,助产士原本还有点迟疑,“宫颈有点水肿,可能有点恼火(麻烦、困难)哦。”吴健雄没有太多顾虑,用分次注射,最后小姑娘顺利生产。原本观望或抵触的同事,观念都改变了。
他一直记得胡灵群说过的一句话:“如果你不去做,怎么知道不会改变呢。总要有人做。”
“想象一下,夜里,为她们打上这一针,和助产士共同完成镇痛的管理。第二天早上醒来,一个新生命降临。产妇、丈夫,家人们看着你的眼光都不一样了。这就是做无痛分娩最大的成就感。”吴健雄说道。
“形骸欲散仍难觅”
吴健雄的个例透着理想主义色彩,现实却分外骨感。
“麻醉科医生人力严重不足啊。”我们在采访的每家医院,都会听到这样的声音。
中国目前麻醉科医生数量约9万左右,若按照英国每万人口拥有2.8个麻醉科医生、美国每万人口拥有2.5个麻醉科医生的比例,全中国至少还有30万的缺口。而国内外科手术量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长,远超麻醉科医师数量的增长速度。
“我现在基本睡在医院,做完一台麻醉手术,抓紧时间休息一下,随时又要开始下一台,只有凌晨2点到5点可以睡个整觉,其余时间就要随叫随到。”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麻醉科医生李潇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透露,自己一个星期和爱人只能见一两次面。
一般非紧急的手术,多半是病人预约好的;但生产这件事无法确定时间,现实中一半以上产妇都是夜里“发动”,医生值“无痛班”,意味着通宵熬夜。南京妇幼保健院麻醉科主任沈晓凤告诉本刊记者,他们一个麻醉科医生最多一晚“打了37个无痛”。

四川犍為县妇幼保健院的无痛分娩团队。图/雷宇
武汉协和医院麻醉科医生凌楚眠和网友分享过:“分娩镇痛试运行时,为24小时值班制,麻醉科医生在产科随时待命,往往一天一夜要打超过两位数的无痛,下了班可以说形骸欲散,累得不成人形。近日随着规培同学的成长,班制才演变为12小时制。漫漫长夜大家好梦安眠时,科室工作微信群常常蹦出无痛分娩的工作信息……”
而在人手更少的医院,渴望打无痛的产妇往往被告知,“麻醉科医生在其他手术室,过不来”,常常痛上五六个小时才等来,甚至等孩子分娩也没等来(打上无痛)。有的医院只有白天提供无痛分娩,夜里则停掉。
这当中,综合医院是难中之难。调配时,分娩镇痛往往被挤压掉。“综合医院接收高危产妇多,做这些手术都做不过来;顺产分娩量不大,放人(麻醉科医生)进去不划算。”徐铭军介绍,“很多医院历来觉得,分娩镇痛是可做可不做的一件事,也没什么经济效益。在这样的背景下,就不愿意做了。”

浙江温岭妇幼保健院无痛分娩团队。图/余日迁
胡灵群建议,在人力安排上,可以用换位、重组和补位的方式。“白天有人去产房,晚上让麻醉科医生进驻产房,有非产科急症时再去手术室。再就是将从事剖宫产麻醉的医生组合在产房或就在产房手术室,重组合理利用。”但在国内,能从产科麻醉特别是分娩镇痛的角度出发,来做这样的安排的,屈指可数。
“需要麻醉科医生处理的时候,他是随叫随到的。但不必拘泥于24小时都待在产房。过分强调这点的话,倒会限制很多医院分娩镇痛的开展。”中国医师协会麻醉学医师分会会长米卫东说。
本刊记者走访获悉,在过去的20年里,许多公立医院为了激励医生,每做一例分娩镇痛,会给100到400元不等的奖励。但这笔奖励是发放给包含麻醉科医生、产科医生、助产士等在内的整个团队,有时还是二次分配、平均到人。“你想,辛辛苦苦做一例,从头盯到尾十几个小时,才得几十块,有时甚至都没给到自己头上,谁想做呢?”有医生吐槽。
从北大妇儿医院病房楼上六层,手术间旁一间五六平米的值班室,便是曲元待了十多年的工作和休息区间。一张办公桌紧挨着金属上下铺,旁边小桌上堆着打印机和二三十个医生的保温杯。看到记者过来,本来和她一道待在里头的四五位年轻医生纷纷离开,给我们腾出地儿来。
“我们招的学生大部分是来自于北医8年制的学生,但已经连续两年招不到新人了。”曲元叹道。“没有人来报考麻醉科了。科室人员断层非常明显,除了像我们这拨五六十岁的高年资医生,干活的大部分是规培生和外地进修生。我们医院对SCI(科学引文索引)要求还特高,发的分值不够高的,很难留下。又要人,没人考,进来还难留,这就是个恶性循环。”曲元称。
在犍为干了五年多后,和妻儿长期两地分居的吴健雄考虑再三,不得不告别自己心仪的产科麻醉,到了乐山市中医医院工作。
犍为妇幼保健院只得四处挖人,最后挖来了原嘉阳红会医院的董加梅医生。“对方不愿意放。我们还是通过市卫健委,交了一笔‘赔偿金才要来人。”上述院领导介绍,“再招一个(熟手)要好几年。2017年我们好容易招到一个新人,当年考上研究生人就走了。全国妇幼保健院的分娩量其实在所有医院生产总量里是大头,但对学生而言,妇幼保健院的吸引力要小得多,有点能耐的都往大城市和综合医院跑了。”
与此同时,社会对于麻醉科医生的认知还停留在“打一针麻药”的层面。
米卫东最近刚做完一个针对100万民众的线上问卷调查。“我问,你认为麻醉科医生是医生、技师、护士,还是其他医务人员?有1/3都不知道麻醉科医生是医生。我再问,手术过程中和做完以后,麻醉科医生可以离开吗?有一半以上认为麻醉科医生是可以离开的。”在另一项针对麻醉科医生的职业现状调查里,他提的最后一个问题是:你会让你的子女选择麻醉吗?回答“会”的不到1%。“我们医生自己都没有认可这个职业,感受不到它的价值,对吧?”
高级全科医生——这是米卫东对于麻醉科医生的定位。“实际上绝不只是打一针,手术过程里可能会打几百针。更多的药物是维持病人的心跳、血压、呼吸脑功能、肾功能等各种生命体征,要根据病人的身体变化随时调整药物组合,就跟飞行员一样,仪表一波动,他就得去处理,才能保证飞机正常航行。我们做的就是维持生命,保驾护航。”

浙江温岭妇幼保健院,麻醉科医生梁刚在产房24小时值班,查看实施分娩镇痛后的状况,为产妇调整镇痛泵用量,并指导注意事项。图/余日迁
“无痛”的争议,与助产之功
像分娩镇痛这样的护航,偶尔也有偏差,或者说“舵手”们也会意见不一。
因为产痛而“失去思考方向”的大包,一开始就打定主意要无痛分娩。但在漫长时间的煎熬和等待里,她只感受到了两小时左右的“轻盈”。
“感觉无痛只撑过了4指宽(约4至6公分),后面该怎么疼,还是怎么疼。”她没有多问麻醉科医生,“好像有安全考虑吧,后面就不给我加(药)量了。也可能每个人痛感不同。我比较敏感。”
在一家基层医院,一位产妇在使用分娩镇痛、加了缩宫素后,饱受了长达六七个小时的疼痛。她不明白为何自己和其他人的体验如此不同,“也许是我体质的问题?”产后的她告诉本刊记者。
“胎位因素、打了缩宫素,都会使疼痛有所变化。但这些,麻醉科医生都可以调整。也包括穿刺、置管時机和手法不当,埋管子没埋对、胶布没固定好,效果就会没那么好,这是考验专业水准的地方。”徐铭军说得掷地有声。“可以说,要实现‘完全无痛,技术手段并不难做到。我们认为,产妇的疼痛感从9分要降到3分以下,这个镇痛才算过关。”

“无痛分娩中国行”项目发起人胡灵群教授。图/受访者提供
所有受访的麻醉科医生都指出,硬膜外镇痛是一个相对常规和成熟、并非高精尖的技术,难在后期管理:麻醉科医生打完针后,不能一走了之,要对母婴状况进行全程监测,有问题时助产士随时呼叫麻醉科医生解决,实现“质控”。
曲元由此感叹:“助产士是非常伟大的,我认为他们是护士里技术含量最高的一群,相当于半个医生,而且也特别辛苦。因为穿刺操作、扶体位、导管的固定、麻醉药物核对,麻醉医都要跟他们来积极配合。打了镇痛针以后,产妇的血压、体温、胎儿胎心、可能的并发症等,也都是靠助产士密切注意和发现。”
2007年前后,徐铭军曾经对本院的助产士和后勤人员做过一个调查,“推行分娩调查后,是否增加了你的工作量?”
“早期设计这个问题,我们想当然地认为肯定是减轻工作量的,你想啊,产妇打了无痛之后不吵不闹了,大家耳根子清净了,不是少很多麻烦?结果问卷一收,答的都是‘增加。助产士得开静脉通道,还得帮你摆体位等等。而且她们说,过去听她(产妇)吼叫的音量大小,就可以根据经验来判断宫口开的过程。现在好,一打镇痛以后,也不叫了,心里没底了,得时不时地去做内检查宫口。这不增加工作量对吧 ?但10年以后我们再做同样的调查,好多助产士答的就不一样了,因为镇痛经验越来越丰富,配合也更默契了。”
现实中,到今天也依然有医院要求,产妇一定要宫口开3指宽才能上无痛,开全之后(甚至开到6至8指宽)又会停掉麻药,造成了“掐头去尾”、“镇痛不全”的局面。
从前“开3指才打”,多半源于产房管理,以及对于“产程延长”的顾虑。自从两年前,国家卫健委随试点方案一同发布《分娩镇痛技术操作规范》,其中已明确,“产程开始后,产妇有要求,在产程的任何阶段均可开始实施椎管内分娩镇痛。”产妇因此不必忍受生产开始时的疼痛,舒适程度大大提高。
那么在分娩的最后关键时刻,产妇到底要不要感受到痛,要痛多少?这在各个医院的分娩镇痛团队实践中,并不统一。
张光波、胡灵群和美国德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心陶为科教授等医生坚持认为,必须给予百分之百、不打折扣的“全程无痛”。
宋兴荣等人则认为,不应该强调绝对的“无痛”。“理论上有10%-15%的产妇是可以耐受自然分娩的疼痛的,不要造成过度医疗。”他和徐铭军都表示,在第二产程(宫口全开到婴儿娩出),麻醉科医生可以控制,让产妇仅存留一点痛感,又不影响睡眠休息和体验。“每一次宫缩来,产妇都能有体会,胎头旋转下降的过程,也能感觉到,宫口全开时能更好地配合助产士分娩。”
米卫东总结,全产程镇痛比较被推荐。“有利于整个技术的实施和产妇的感受。但如何操作,在每个医院自己的掌握了,没有统一的一定之规。”
无论是哪种论点,这个环节里最凸显的是助产士的耐心和功力。
11月19日零点,温岭妇幼保健院的助产士晨娅该下班了。但我等了将近40分钟,她才过来。在接生了当班的第4个宝宝之后,她需要填写新生儿情况记录,总结一天的工作。见到晨娅时,她刚摘下帽子,头发湿湿地贴在头皮上,呼吸还有些急促。
半个多小时前,记者尚不知道她的名字,只在分娩室里看到她和同事在指导产妇:
“加油!很好——再来——”
(一人给产妇擦汗,晨娅在为产妇抹碘伏)
“呼气,屁股翘起来!
(陪产的产妇家人和另一名助产士抬起产妇的腿,等待下一次宫缩)
“再用力……加油……来,休息一下。脚放松一下。”(晨娅用手给产妇的腿部按摩,接着鼓劲。已经能看到小婴儿露出些许的毛发,产妇宫缩平均两分钟1次)
“深吸气——呼气——用力!这次特别好!
此时晨娅铺好洞巾,为下一步孩子娩出和缝合做准备。当宫缩来的时候,晨娅用手保护着会阴尽量不要撕裂,指导她呼吸,当宝宝大半个头露出来时,另一助产士马上嘱产妇呼气,并嘱产妇在宫缩间歇稍微屏气用力,她们说,这样可以减少会阴的撕裂。
几分钟后,闭着眼睛的新生儿带着长长的、灰蓝色的脐带,从妈妈的身体里来到这个世界。
晨娅说,哪怕一两个月以后再问她这天晚上的4个孩子的情况,她基本上还是能回忆起来。“真的,因为你必须要记得。”
推行分娩镇痛,一开始晨娅和同事是不太适应的。“相当于从产妇非常努力的自我感觉,到变成更需要我们助产士的鼓励与指导,需要摸着她宫缩让她用力,过程是完全不一样的。现在我们已经知道,最后就放緩进程,不要过早用力。一旦产妇那种(排便感)不强,可以让她改变体位,坐起来站起来,或者趴一会儿。再利用手摸宫缩或子宫张力,觉察到宫缩时,指导她们呼吸。一般多重复几次,或者更多次,都能完成顺产。”
2018年,国家卫健委统编教材《妇产科学(第九版)》采用了新产程定义:使用椎管内分娩镇痛的初产妇和经产妇,其第二产程时间分别为4小时和3小时。
产程的修改对生孩子的改变和意义在哪儿?
米卫东等人指出,此前,不少医院会把第二产程长于两小时的算为医疗事故。宫口一旦开全,无论胎头位置有多高,就开始要产妇用力,结果产妇筋疲力尽,胎头却迟迟不下,因此往往要经受器械助产(产钳)和会阴侧切,或者来一个不必要的剖宫产;助产士也会在第二产程为产妇停镇痛泵,导致镇痛失效。“现在有了新产程做后盾,就不用那么拘泥于两小时了。”
“等待是美德。”梁刚在视频里引用过这句他从胡灵群那里学来的箴言。“对麻醉科医生,对助产士,莫不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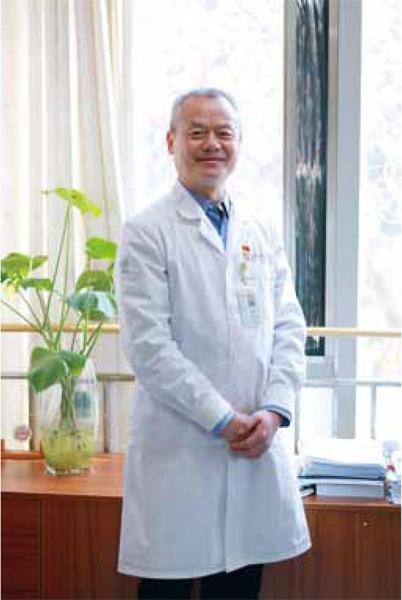
中国医师协会麻醉学医师分会会长米卫东。图/本刊记者 梁辰
领导意识与收费政策
2020年12月初,本刊记者从相关部门获得的数据显示,经过两年试点,在913家医院当中,有专职分娩镇痛麻醉科医生的医院,由464家增加到了2020年的582家。已有51%的试点医院在产房内设立了紧急手术室,38%的医院建立了麻醉科产前评估门诊,70.3%的试点医院建立了完善的分娩镇痛质控管理制度,并进行定期考核。有近六成的医院对分娩镇痛工作在绩效分配方面有倾斜,其中近90%的绩效分配较试点工作前有提高。
在记者到访的温岭妇幼保健院、犍为妇幼保健院,分娩镇痛率近年已经稳定在50%以上。北大妇儿医院、北京妇产医院、广州妇儿医疗中心都在七八成甚至更高。在这些地方,无痛分娩的积极开展能带动一定时段里分娩量和口碑的双赢,证明并不是一个“不划算的业务”。

北京妇产医院麻醉科教授徐铭军。图/本刊记者 梁辰
只是,医生和产妇们最关心的收费和医保,还不算明朗。此前有些医院对无痛分娩的收费只有麻醉剂使用的收费,对麻醉师的人工占用没有收费标准。“没有收费项目,只能挂靠收费,一是钱给得很少,再就怕上面一查,说是乱收费,这就很尴尬了。”徐铭军说。
截止到2020年底,北京已有省级批复统一价格(分娩镇痛1950元,不包括耗材);上海、江苏、浙江、天津、湖北、云南等六省批准按特需服务,物价备案;广东等14个省份尚无省级统一批复,各地自行定价处理。
徐铭军认为,应该把无痛分娩纳入舒适化医疗的一部分。“除非生育保险的医保总额要扩,如果总额不增长的话,纳入医保以后,反而出问题了,本来顺产一个三千多,再加上无痛一两千,(医保)要倒贴钱,怎么搞?北京就是这样,大家心一热,提出无痛分娩走医保,后来发现用力过猛,给(从医保序列里)拽出来了。”
为何要限制顺产的总额?与政策有很大关系。某综合医院的医生在受访时直言,“生小孩的生育保险,国家是控制得比较低,要不谁还生?现在我们这儿是三千多一个,今年调过一次,调高了五六百块钱,但还是不高。有时候我们会说,天哪,我们做个剖宫产手术,还不如人家割个阑尾、切个痔疮,呵呵。但是我们也能理解,国家要发展,要多生一点宝宝。”
还是有一丝丝的口子在打开。自2020年4月1日起,无痛分娩被纳入了广州生育保险目录,在一级定点医疗机构选用无痛分娩的产妇可报销4100元住院费用。“广州的工作做得很细,阴道分娩和镇痛是分开收费的。值得学习,但需要和多个部门协调,任重道远。”现任国家卫健委能力建设和继续教育麻醉学专家委员会主任姚尚龙称,他和同仁多次向政府呼吁,希望能提升生育保险额度,将无痛分娩纳入基本医疗,保障产妇的权益,实现真正舒适而普惠的分娩。
2018年12月,胡灵群在一席做了演讲《分娩之痛已经到了不得不谈的时候》,让这一话题走入大众视野。回首这十来年的推广之路,胡灵群说:“大家都以为通过一个人,一个学科可以搞定无痛分娩。不是的,这是一个团队协作,特别是医院的vision(视野和眼光),长远规划。”徐铭军和米卫东想法更直接,他们认为,人手少是永恒的,但最主要的还是转变观念意识。“分娩镇痛在我国有这么大的阻力,非技术因素占了主导地位。最关键的还是看省市一级的政府部门和医院领导,有没有按照国家文件那些条目重视麻醉科室,和分娩镇痛这件事。”
本该是一次意义丰富的旅程
无痛分娩,看似只和一部分待产女性有关。但细细想来,这项技术一旦普及,必将改变几代人的生育观和生命品质,以及家庭内部与医患之间的关系。
几个月前,梁刚在短视频平台上开了账号,到现在制作了将近100个有关生产和无痛分娩的科普小视频。
镜头里,他用最平实的语言解释:“顺产是先苦后甜;剖宫产是先甜后苦;无痛分娩嘛,是前后都甜。而且剖宫产不能陪产。无痛不但可以陪,还能陪得他(激动到)泪流满面。”
走廊上,他脚步匆匆,“今天打了5个无痛。每次打无痛就会走得快一点,因为这样大家(产妇们)就会少痛一点。”
父亲节那天,他把自己“扮作”产妇,把双腿架在分娩室产床两侧,一步一步地教产妇在第二产程怎么用力。
“来。宫缩来了。脚蹬住,打开骨盆、屈大腿,鼻子深吸口气,屏住,抬头看肚脐、腰贴床,双手抓把手,往下用力‘拉粑粑……10秒。换口气,深呼吸,屏住,同样动作往下用力,一个宫缩用力2至3次,10至20个宫缩宝宝差不多就出来了。你,学会了吗?”
分娩室的助产士们帮梁刚录下了这个视频。一个大男人模仿产妇的样子,做的还有板有眼,这既让她们乐不可支,又心生佩服。
浏览过视频的产妇们纷纷留言:没见过这么温柔的醫生。在医务科主任张维维看来,梁刚触觉敏锐,善于发现和创造美好,“这在常有职业耗竭的医生里,会磨失掉,他却没有,总是那么有热情。”

浙江温岭妇幼保健院,麻醉科医生梁刚经常利用业余时间拍摄和制作短视频,科普无痛分娩知识,在网上和线下都获得了积极反馈。图/余日迁
梁刚喜欢说的一句话是:“分娩本来就应该是一次温柔的,充满爱、勇敢和期待的,意义丰富的旅程。”
这样的旅程,不该是产妇一个人的孤身之旅。
犍为妇幼保健院的助产士鲁旭梅,个子高,说一口爽朗的乐山话。每收治一位产妇,她都会主动介绍:“你好,我是护士鲁旭梅,是你的责任护士,今天全程到产后两小时,都是我陪着你。”
刚刚24岁的鲁旭梅说,干这行,要能感同身受,去体会产妇的心理。“初产妇怕痛的很多。担心侧切啊,担心孩子过大,担心顺产下不来。你要增加她的信心。有些容易‘惊抓抓(惴惴不安)的,要不断去安慰她们。我们都理解宫缩很难受,那我会跟她们说,你可以把每次宫缩,都当成和宝宝见面的机会,这样她们就没有那么恐惧了。”
在记者接触的几家产科,护士长和助产士们大多爽朗、活跃,精力强健,爱笑、爱打趣。也许天性如此,也许在漫长的与产妇的接触里,她们被锻造出了亲和与同理心,还有一颗“铁胆”和对危机状况的不惧。
相较之下,家人,特别是初产妇的亲人们,要学的更多。
在南方一家专科医院产检处,本刊记者随机采访了8个家庭,只有一位准爸爸听说过无痛分娩,但也仅限于“就是打一针吧”。
采访温岭妇幼保健院那天,我们邀请一位等待妻子产检的易先生,试试孕妇学校教室里一台特别的设备——分娩阵痛体验仪。电源打开,将两个电极贴贴在腹部两侧,调节机器增加电流刺激,就能体验数值从0到120的不同层级的痛感。
29岁的易先生并不排斥,很有点“勇夫”气概。数值升到18时,他告诉我们感到了肌肉的颤动。“有点痉挛,还可以忍受。”几分钟过后,他脑袋有了轻微晃动,看得出在努力控制自己。再往后,他忍不住脑袋往后仰,膝盖也不禁抖动。数值升到38,“像针扎一样啊……”到44,他额头已经汗如豆粒,没法说话。
到60左右,他终于要求停止。这时妻子也过来了,看着丈夫,又有点想乐,又想象到自己临产时,是不是也是这般模样,表情有些忐忑。

四川犍为县妇幼保健院,无痛分娩的产妇开心地抱着新生儿。图/雷宇
易先生话不多,末了吐出一句:“到时只要她提,就给打(无痛)吧。”
网名“五岁”的产妇生女儿小河之前,也听说过这仪器。“要知道模拟的时候只是几分钟,但是女人生产的过程少则几小时、多则几天啊。”
她原本想象不出来,婴儿头那么大的东西,怎么样通过狭小的产道,在经过排山倒海的阵痛之后,终于有了深切的领悟。
“麻醉师进来的那一刻,我就觉得好多了。她非常温柔地跟我说,现在你可以上无痛了,打上之后十几分钟就会有效了。虽然看不见她的脸,但我觉得她简直是天使……”
几个小时后,一个粉红色的婴儿被抱过来放在五岁的胸口上。
“孩子闭着眼睛往上爬,开始找吃的。小河,我的女儿,我心里默念着,经过漫长的10个月,我们终于见面了。
两个月之后,她每天早上醒来,看到我会露出天使一样的笑容。她会咿咿呀呀地跟我说话,挥舞着小拳头够玩具。
有一天早上她吃完奶睡了,我在客厅里听着(播放器里)熟悉的歌声,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过去走过的城市,爬过的山,爱过的人,都像前世记忆。
为什么要生孩子呢?我想。人都在以某种方式挣脱虚无,性也好,旅行也好,读书也好,挣钱也好,没有本质的区别。但你诞生了,世界发生了奇妙的变化。一个有你存在的世界是一个全新的世界。”
五岁说,创造生命,就是人能参与的最神奇的事情。
而这件事情,在无痛分娩的加持下,有了更加自尊、平和与美好的途径。“我希望,全中国的妇女都能享受到无痛分娩,我祝福全世界的产妇都能安宁地生产。”92岁的张光波,殷切地握着记者的手叮嘱。
(参考资料:《你一定要知道的无痛分娩》《无痛分娩中国行》公号,《无痛分娩为何在中国难以推行?》。感谢所有受访者,特别是胡灵群、陶为科、吴健雄、梁刚等多位医生对本文的大力帮助,金雅如对本文亦有贡献。除去医务人员,其余受访者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