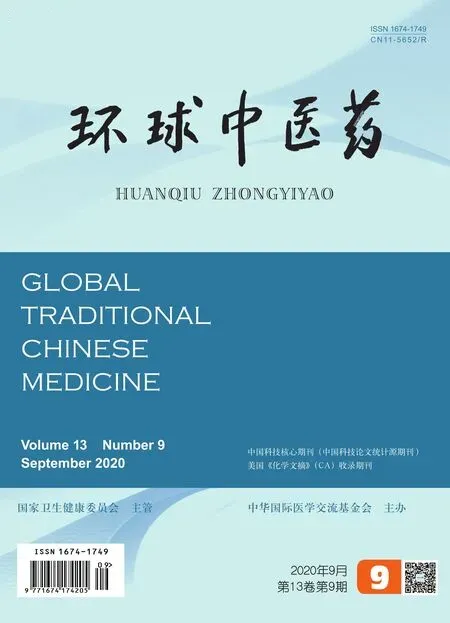方证研究在证候规范化研究及证候类中药新药研发中的作用
2020-01-11曹璐畅李杰许博文
曹璐畅 李杰 许博文
中医辨证论治强调望、闻、问、切四诊合参,随现代医疗模式及人类疾病谱的变化发展,医学理念亦随之而变,“中医有效性”这一问题渐被提出,这就要求中医需与现代医学相结合,向规范化道路发展。与现代医学注重疾病的临床指南相同,中医学亦需要一个以证候为核心,并进行相应的推广与及时更新,为临床诊疗疾病提供一种统一、规范的疗效评价方法[1]。所以,证候规范化研究是中医走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
1 方证研究在证候规范化研究中的作用
方证研究的构成要素为方药与证候,重在研究方、证之间的相互对应关系,其作为辨证论治的简化,亦是临床辨治规范化的研究。方证研究的要素包含证候,证候规范化研究的主题即为证候,二者之间势必存在多种关联:方证研究作为证候规范化研究的前提与依据,可验证其证候规范化研究的证候模型,促进临床疾病证候诊断标准的建立,加速构建证候规范化研究下以单证或证素为基本辨证单位的辨证方法体系,并推动其未来的发展。
1.1 方证研究是证候规范化研究的前提与依据
中医由古至今,随流派发展的思想迥异,遗留至今的辨证方法多种多样,如八纲辨证、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脏腑辨证、病因辨证等,但此等辨证方法临证之时最终都要与方证辨证相结合以处方用药,故方证研究是客观且必要的。若临床总结整理方证与药证的对应关系,探索其中的规律,便初步实现了中医诊断客观化,在此基础上选用临床科研方法相关内容,找到证的量化指标,使方证、药证的识别对应关系更具规范性与准确性[2]。如此可使方证对应更为详明,且可补充中医临床辨证论治内容,充实中医辨证论治体系,为中医证候规范化奠定基础[3]。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方证研究临床疗效确切的基础上对证候规范化研究提出进一步的思考,这种基于临床有效性的探索不仅可推动证候规范化研究的进程,且可促进方证对应理论的发展,故方证研究作为证候规范化研究的前提与依据,是解决中医证候规范化研究的可操作途径之一[4]。
1.2 方证研究可验证证候动物模型
方证相应即方与证在主要的、核心的病机上存在相互对应关系,证候所蕴含的病机与方药所相应的病机需直接对应或间接对应,但究其本质均是强调理—法—方—药间的统一性。吴嘉宝等[5]研究采用以药测证法来评价动物模型的证候属性,其原理是复制出符合中医证候的动物模型,用治疗该证候的方药来验证,若该动物模型符合某证候特征,则该方药应对此动物模型有改善作用。田金洲等[6]认为方证相应体现在证候中的不仅是方剂干预治疗的依据与治疗目标,而且也是方剂的效应基础。证候不仅可反应机体疾病的生理病理状态,亦可作为中药复方治疗的靶位。利用方药药理反证模型是否属某种证候,是动物模型研究的重要方法,可指导中医证候模型的研究。由上可知,在方证相应研究下,以方测证是证候模型验证的重要环节之一。
中医的每一个证候都有相应的方药以对应治疗,证候规范化研究的最终目的即是指导临床精准、高效地处方用药,而方证研究在证候规范化研究的证候模型方面可以起到验证的作用,二者互相关联。
1.3 方证研究推动证候诊断标准的建立
因人而异的辨证论治方法体系是中医临床独具的优势,但证候作为中医辨证论治方法体系的重要元素,在历史沿革下,诸代、诸流派医家分别赋予了其不同的内涵与外延,使其在内容、实用范围及种类等方面或多或少存在不规范现象。这种证候的欠规范导致临床辨证时存在不确定性,因而间接导致临床疗效的不稳定性。因此,进行规范化的临床疾病中医证候研究,建立被公认、能够广泛推广的临床疾病证候标准,是提高中医药治疗临床疾病的根本保证[7]。建立证候诊断标准的过程是在繁杂的症状中抓住疾病的本质,找出具有相同规律的一组症状,并以此区别于其它证候,具有唯一性、排它性的特点[8]。而方证研究若想达到高度契合的程度,亦需主、类方及主、次、兼证间相鉴别,找出方证相应下的主方主证与类方、次兼证间的区别点,以此来达到临床的快速、精确识别。
疾病的临床证候诊断标准需要充分规范、共识化,以避免一证对应多方、一方可治多证的现象出现,缺乏学术严谨性。故方证研究在要求证候规范化的同时,尚可促进证候规范化研究下的临床疾病证候标准的建立。
1.4 方证研究加速构建辨证方法体系
中医证候具有“内实外虚” “动态时空” “多维界面”的特征[9],加之中医理论富有哲学的主观性与模糊性,限制了中医证候走向规范化、标准化[10]。故有学者提出以病位、病性为核心内容,对证候的高维性进行降维处理,以便更好的概括证候,其中典型的是构建以单证或证素为基本辨证单元的辨证方法体系的研究思路[11]。由于临床疾病的复杂性,辨治的证候证型多为复合型,若将复合证型降维划分为单一证型,则其涵盖的病性、病位要素较少且相对固定,亦减少证素组合的不确定性。朱文峰[12]创立以证素为核心的辨证新体系,望构建病域的统一辨证体系,以实现辨证的规范化与标准化。将单证或证素作为研究对象,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提高临床辨治的准确性,也为中医的科学化研究提供了一种新思路。
由上可知,以单证或证素为基本辨证单位的辨证方法体系将病位、病性作为其核心内容,故方证研究由方反向验证,从而定证的病位、病性的研究方法对于以单证或证素为基本辨证单位的辨证方法体系的构建有促进、推动的作用。二者以“证”为连接点,共同推进中医证候规范化研究的进程。
1.5 方证研究推动证候规范化研究的发展
方证以其方证相应性、证候相对稳定性、临床广适性、易于客观化等特点,正以证候的特殊形式纳入证候规范化研究中,并逐步向量化与客观化发展。随着对方证研究的深入探索,在其疗效性评价中必然涉及到方药治疗前后的证候评估与对比,如吕勇等[13]通过观察慢性肾衰竭血瘀证患者的一氧化氮、内皮素、及白介素-6的水平变化与肾功能和中医证候变化的相关联系及其丹参片干预治疗的效果,测定中医证候积分, 分别建立上述指标间的线性关系并实行RCT,结果表示丹参片能改善CRF血瘀证患者血瘀证候。张莉等[14]选取60例初次接受含吉西他滨方案化疗的患者,采取自身前后对照,比较胰腺癌患者化疗前后不同证型的分布,研究表示,化疗后较化疗前肝胆湿热证与痰湿互结证明显减少,脾虚湿滞证、脾肾虚损证与气阴两虚证明显增加。研究结果体现了证候在治疗前后的动态变化和对比,为胰腺癌化疗前后中医辨证治疗方案的制定提供了客观化的依据。
如此,这就要求我们对于证候的界定需要客观、规范、准确,方证研究与证候规范化研究以“证”相联,基于方证理论基础的相对稳定性,方证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定会推动证候规范化研究的进展。
2 方证研究在证候类中药新药研发中的作用
现代中药新药的研发多采取病证结合的方法,这种模式下的新药多适用于某种疾病的某个证型,而中医辨证论治下的中药方剂则以证候为突破点,临床处方用药针对证候而设,如六味地黄丸可用于诸多疾病的肾阴虚证,以其肾阴虚证作为辨治的要点,不拘泥于疾病的种类,符合中医临床辨治的诊疗模式。黄连解毒丸作为首个获得批准临床研究的证候类中药新药在中医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15]。如此,从方证角度研究证候类中药新药,减少了一般证候研究的模糊性与复杂性,对于中药新药的临床研究更为适宜,具有较高的可行性与操作性。
2.1 方证研究为证候类中药新药的研发奠定了基础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CFDA)在2008年颁布的《中药注册管理补充规定》中为证候类中药新药下了定义:“主治为证候的中药复方制剂,是指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用于治疗中医证候的中药复方制剂,包括治疗中医学的病或症状的中药复方制剂。”[16]如此,证候类中药新药的主治为证候,去除了现代医学疾病的概念,更加符合中医药的特色,是一种新兴的新药研发思路。
方证主要探讨方剂与证候间相互对应的关系,基于二者间的联系性与规律性,从方证角度阐释证候类中药新药的研发有着重要的理论依据,可为证候类中药新药的研发奠定基础。不同的方药对于不同的证候所起的疗效迥异,而当方证相应时临床疗效最佳,证候类中药新药的研发即是为了制定出针对某种证候的中药复方制剂,此与方证研究下方证相应理论暗合[17]。证候类中药新药不局限于病种,临床应用时更为细化,具有一定规范性与指导性。以方证作为切入点进行研究探讨更加符合中医思维下的理—法—方—药辨证体系[7],亦适合作为证候类中药新药研究的靶点。将方证研究中的经方、名方作为目标对象,经分析研究,筛选出针对性强、应用指征明确、疗效确切的方剂进行中药新药的开发,可以将中医辨治的优势充分发挥。
2.2 方证研究促进证候类中药新药研发中证候的界定
证候的界定研究是研发证候类中药新药的前提与基础,但在目前证候类中药新药的研发过程中,对于证候的界定尚未达到统一[18]。学者们通过传统望、闻、问、切所采集到的四诊证候信息缺乏客观性与规范性,表述与评判标准欠缺规范化,不利于证候类中药新药辨证标准与疗效判定标准的确立,且可能导致后续疗效评价的差异,致使证候间的对比难以进行。所以证候应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方可进一步确定其研究方案及评价标准。而方证是应用某一方剂的临床指征,反映了患者综合的、特异性的病理状态,是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逐渐摸索出的客观的、相对固定的结论[15],能够将证候类中药新药中的“证候”及其“中药新药”所内涵的中医方剂相结合,在临床疗效上更直接、更密切、更有保障。
因此,若将方证作为证候类中药新药研究的一个切入点,将改善对证候认识不统一的现象,利于推动证候类中药新药研发的进程[19]。且方证中每一首方剂均有其独特的应用指征,在证候类中药新药研发过程当中,将方剂与证候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研究更加符合临床。
2.3 方证研究有助于建立证候类中药新药疗效评价体系
证候类中药新药迅速发展,与以往新药的开发有异,是基于证候的、可以跨疾病使用的一类新药,为现阶段中药新药研究的重点。在证候类中药新药研究中,中医证候既是纳入标准,又是疗效评价指标[15],从方证角度出发研究方剂及其适应证,通过方证的适应证制定证候类中药新药的诊断标准和疗效评价标准,可以摆脱泛泛研究证候而带来的诸多困难,并可尝试以此作为解决证候类中药新药研发的突破口[20]。
以方证为切入点研究证候类中药新药研发,可依据方证的临床症候制定相关的证候评价量表。在一定规范的方法学指导下,制定的针对特定方证的证候评价量表可以作为证候类中药新药研发过程中参考的评价标准[15]。对于证候类中药,证候评价尤为重要,中药干预前后的证候变化是证候类中药新药研究的主要疗效指标,亦可结合循证医学,为临床治疗寻找证据,提高临床评价的可靠性与科学性。中医证候量表的研制方法与研究模式目前备受关注,但尚未形成成熟完善的中医证候综合评分量表共识[21]。但在量表研制时需根据量表应用目的、理论框架概念、维度设置以及条目选择倾向性差异,融入现代数理统计方法进行条目的筛选及其分级量化,尽量减少研究者主观臆测所产生的偏倚,加快相关研究进程[22]。
2.4 方证研究有利于规范证候类中药新药研发下的证候诊断标准
收集望、闻、问、切四诊信息之后,根据临床经验及具有个体化的主观判断得出疾病在某一阶段病因、病位、病性、病势的概括,称之为辨证。此过程主观性较强,不同医者对于证候的命名、诊断均可能存在差异,如此可致后续研究难以进行,所以对于证候诊断标准的规范化、共识化,是证候类中药新药研发过程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17]。证候类中药新药研发下的证候诊断标准的建立过程是在繁杂的症状中找到唯一性、排它性的一组症状,以此区别于其它证候[8]。方证研究即方药与病证之间相对应,方随证立,强调方与证之间的高度相关性,以“有是证,用是方”为基本原则,方剂与证候之间的对应关系在临床上有完全契合、大部分契合、证与多首方剂契合、证与多首方剂相似的不同,如此就需要识别主方、类方,主证、次证与兼证之间的差别。在证候类中药新药的研发中,可以通过中药新药的“方”来反测其“证”,以此来推断中药新药的适应证,并制定其证候诊断标准[23]。但在证候类中药新药的研发过程中,对于证候评价标准的制定目前尚未形成共识,仍需要学者们进行后续研究来解决此问题。
3 结语
方证研究深化现代中医辨证论治思维、拓展方剂的应用范围、推进中医规范化,而且可以增强医者辨证论治能力、拓宽辨证论治的范畴、提高临床疗效,利于中医药传承与发展。通过对方证的研究分析,选出适合新药开发的具有针对性、指征规范且疗效显著的方剂,借此体现中医治疗的优势,故而从方证角度探讨证候规范化及证候类中药新药的研发有重要的意义与发展前景[15]。但在证候类中药新药的研发过程中,对于证候的界定、证候评价标准的制定尚未形成共识[21],其作为中医药走向现代化研究的一种创新模式,不仅有助于中医药的规范化、科学化、国际化发展,亦使临床患者广受中医药方证相应下辨治疗效的益处,为临床研究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