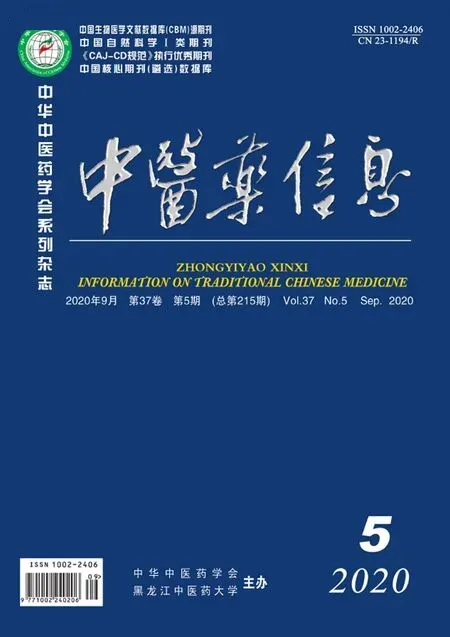王俊志治疗神经性皮炎湿疹样变经验
2020-01-11朱雅楠张海龙
朱雅楠,张海龙
(1.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黑龙江 哈尔滨 150040;2.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40)
神经性皮炎的主要表现为红色丘疹伴阵发性瘙痒,经反复搔抓后可出现皮损苔藓样变及增厚,好发于项部、腰背、四肢、骶尾等处,而部分患者在上述部位亦可出现渗液、血痂、抓痕等类似湿疹样皮损的表现,诊断上模棱两可,王俊志教授将其定义为神经性皮炎湿疹样变。此类患者日益增多,病情缠绵难愈,单纯采用湿疹或神经性皮炎的用药方案效果均不理想,严重影响患者身心健康,故应引起临床重视。
王俊志教授,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皮肤科主任,师从全国名老中医王玉玺教授,从事中医皮肤病研究30余年,孜孜不倦,融会贯通,推陈出新,治疗本病疗效甚佳,现将经验总结如下,以供参考。
1 病因病机
1.1 中医病因病机
王俊志教授认为,神经性皮炎患者,因素体有湿,病情缠绵,日久肝郁化火,进而伤脾,脾虚湿盛,导致湿疹样变。明·王肯堂《证治准绳》载:“夫疥癣者,皆由脾经湿热,及肺气风毒,客于肌肤所致也……久而不愈,延及遍身,浸淫溃烂,或痒或痛,其状不一”。论述了久病产生湿疹样变的病因为脾经湿热。导师总结前人理论经验并结合对大量现代临床患者的观察,重归湿热两邪发生源头,将热邪归于肝火,湿邪归于脾虚。
肝属木,喜条达,神经性皮炎患者日久不愈则产生焦虑、抑郁情绪,而木易生火,患者长期肝气不舒,郁结于内,化火生热。脾属土,喜燥恶湿,对应情志为思,若患者长期忧思不解,则易伤脾,脾脏虚损则更生湿浊。总之,病因大致为神经性皮炎患者,先有肝经生热,后有脾虚生湿,湿热之邪,外蒸肌肤,故产生湿疹样皮损的改变。
1.2 西医病因病机
本病不是专有病名,属于神经性皮炎这一疾病的转归,病因尚不明确。疾病发生湿疹样变,多数患者存在细胞免疫功能异常[1],并与免疫遗传体质有关[2],因此可将神经性皮炎湿疹样变疾病视为免疫功能异常的变态反应性疾病。
瘙痒是神经性皮炎的主要症状。研究显示,“瘙痒-搔抓”这一恶性循环是神经性皮炎发病及加重的主要因素[3]。患者自主搔抓,导致在苔藓样变基础上又出现抓痕、渗出、血痂等湿疹样皮损的表现,可推测疾病具有“皮肤炎症-瘙痒-搔抓-湿疹样变”的致病规律。
2 内治中医辨证
根据以上认识,结合临床观察,王俊志教授认为患病早期虽有湿邪,但多以肝火为主,后期虽有余热,但多以脾湿为主,故将本病分为肝火炽盛与肝郁脾虚两种证型。
2.1 肝火炽盛,湿热相搏
患者神经性皮炎病史,疾病缠绵不愈,进而影响心情,日久肝郁化火,肝经火旺,充斥肌肤而发病。临床表现为病变部位皮肤潮红,灼热,边界弥漫,上覆丘疹或丘疱疹,抓破有渗出,严重则湿烂;伴心烦、急躁易怒、口干口苦、大便干、小便短赤等症状;舌红,苔薄白或黄,脉滑数。方选龙胆泻肝汤加减,组方:龙胆草、黄芩、栀子、柴胡、通草、泽泻、车前子、萹蓄、生地黄、当归和甘草。渗出严重加土茯苓清热利湿解毒;瘙痒严重加苦参、地肤子清热燥湿止痒。
方中龙胆草泻肝火, 清湿热, 直中病机, 故为君药。黄芩入肺经, 清上焦之火;栀子清热解毒,泻三焦之火,为臣药,君臣合用,共奏清利三焦湿热之功。泽泻、通草、萹蓄、车前子清热基础上利水渗湿,导湿热从水道而去,予以湿邪出路,有利于缓解湿疹样变皮损表现;生地黄清热凉血,又善养阴生津,与滋养阴血之当归相伍,使邪去而阴血不伤,以上共为佐药。此外,火郁于内,肝气不畅,遂用柴胡引经以疏之;甘草调和诸药。
龙胆泻肝汤成分,可有效减轻血清中各类炎性因子水平,减轻炎症反应,并通过调节T细胞CD4+、CD8+水平,调控细胞免疫功能[4],导师认为,在此基础上加减运用,即可清热利湿、泻火解毒,又可纠正患者免疫失调情况。
2.2 肝郁脾虚,湿浊内生
本病患者常失治误治,导致病情缠绵不愈,则更添抑郁情绪,日久忧思,使脾失健运,湿浊内生,日久迁延而成慢性湿疹样表现。临床表现为皮肤以苔癣样变为主,干燥粗糙,边界不清,或有渗出,皮损上覆丘疹、抓痕、血痂;伴胸闷、胁胀、腹胀、便溏等症状;舌红,苔白腻,脉弦滑。方选丹栀逍遥散加减,组方:柴胡、白芍、当归、茯苓、白术、牡丹皮、栀子、陈皮、枳壳、苍术、白鲜皮和炙甘草。脾胃虚弱者加山药健脾益气;瘙痒重者加地肤子、蛇床子燥湿止痒。
方中柴胡主入肝经,解郁疏肝,使肝气得以条达,有效针对肝郁病机,故为君药;当归、白芍养血敛阴柔肝,白术、茯苓补气健脾利湿,四药合用肝脾同治,使肝郁得疏,脾虚得健,湿浊得清,共为臣药;牡丹皮、栀子清肝凉血, 共助柴胡抑制气郁之火,苍术、枳壳、陈皮疏肝理气、健脾燥湿,白鲜皮清热燥湿基础上又有止痒之功,以上共为佐药;最后炙甘草补脾和胃、调和诸药。
丹栀逍遥散即能疏肝又善健脾,是治疗肝郁脾虚常用方,苍术提取物——苍术内脂Ⅰ,具有抗炎抗过敏作用[5];白鲜皮可能对效应期T细胞有抑制作用, 阻止其释放各种淋巴因子, 因而抑制了机体对过敏原的过度应激反应, 有助于恢复机体正常免疫系统应答[6]。导师认为,本方加减运用,不仅对抗机体免疫反应异常,又能健脾除湿,兼清郁热,有效的针对久病湿疹样变的病机。
3 外治中西医结合
有诸内必行诸外。王俊志教授认为,虽然免疫异常类皮肤病不能单靠外用药来达到治愈目的,但仍需内外同治,在外用药的辅助治疗下缩短病程,提高疗效。
3.1 中药湿敷
湿敷法又称溻渍法,首见于《刘涓子鬼遗方》,《外科精义·溻渍疮肿法》论其“夫溻渍疮肿之法,宣通行表,发散邪气,使疮内消也”。
湿敷法为皮损有渗出时的主要治疗方法。导师选用龙胆草、生甘草、马齿苋,煎汤冷湿敷治疗。方中龙胆草甘草清热、解毒、收湿,并且具有抗炎、抗过敏作用;马齿苋在祛湿的基础上增强止痒力度。研究表明[7-8],冷湿敷治疗渗出性皮炎具有良好的效果,能够缩短患者的病程,明显减轻瘙痒和缩短渗出时间,减轻皮损,改善睡眠,提高患者机体免疫力。
3.2 西药外涂
3.2.1 糖皮质激素
糖皮质激素在免疫相关性皮肤病的治疗中应用广泛, 在多数疾病的治疗中属于一线治疗药物[9],在皮肤性病上得到广泛应用。本病变融合了神经性皮炎与湿疹两种皮肤科常见疾病的表现,治疗较为困难, 西医常见治疗手段以口服抗组胺药物及外用糖皮质激素药膏为主。
导师一般选用复方卤米松乳膏。卤米松具有强烈的抗炎、抗过敏、止痒效果,在多种皮肤疾病的治疗中都较为常用[10]。实践表明,复方卤米松乳膏治疗神经性皮炎与慢性湿疹效果显著,且治疗过程中出现不良反应机率较低,相对安全。此药多在本病渗液不多或湿敷后进行应用,可快速缓解皮损症状。
3.2.2 代替疗法
患者外用激素药膏后, 常可发生接触性皮炎, 使原有皮损加重, 出现红斑、肿胀、渗出等[11]。久用皮质激素类药膏后,机体肾上腺皮质的正常功能受到抑制,一旦突然停药便可因机体激素分泌量不足而引起病情加重[12]。为了保证治疗有效性与安全性,导师在其还没有出现副作用之前,改用其他不含激素的外用药物进行代替治疗。
在应用糖皮质激素1~2周后,若皮损症状稳定,则改用全蝎软膏[13-14]直接代替治疗。但因患者禀赋差异,部分患者出现停用激素后,病情骤然加重现象,因此代替初期,可用全蝎软膏与复方卤米松乳膏进行交替使用,并逐渐延长全蝎软膏使用时间,再配合内服汤药,逐渐做到完全代替激素治疗。
虫类药物外可走表行皮、宣风泄热,内可入里通络、搜风解毒,在皮肤病的治疗中应用广泛,效用佳良而且可靠[15]。其中全蝎、蜈蚣善祛内外之风,痒自风来,风去痒自止,所以由风燥、湿热引起的瘙痒性以及过敏性疾病均可用其治疗;冰片清热解毒、防腐生肌,可抑制皮肤炎症;凡士林具有湿润黏膜、滋润皮肤之效。全蝎软膏作为虫类药代表,在本科室主要用于干燥性、瘙痒性、溃疡性、渗出性皮肤病,能熄风止痉、攻毒散结、通络止痛、润肤止痒。
4 验案
4.1 验案1
李某,女,40岁,公司职员,2019年5月21日初诊。患者半年前因双手肘、颈后等部位出现皮肤肥厚粗糙,呈阵发性瘙痒而于当地医院就诊,诊断为神经性皮炎,经西医治疗未见明显好转。患者自述患病期间因瘙痒难耐而不受控制反复搔抓,近日皮损处逐渐出现丘疱疹、血痂,抓破有渗出,遂来我院就诊。刻下:皮损肥厚、粗糙、潮红,伴有丘疱疹、血痂、渗出,瘙痒严重,患者情绪焦虑,口苦,怕热,喜冷饮,大便干,舌红,苔黄,脉滑数。辨证:肝火炽盛证。治法:疏肝解郁、清热祛湿。处方:龙胆泻肝汤加减。组方:龙胆草10 g,栀子15 g,黄芩15 g,柴胡15 g,车前子20 g,生地黄20 g,泽泻15 g,通草10 g,甘草10 g,当归20 g,白鲜皮15 g,地肤子15 g,赤芍10 g,牡丹皮10 g,陈皮15 g,苍术15 g。7剂,水煎服,日1剂,早晚饭后30 min温服。外用龙胆草、生甘草、马齿苋煎汤冷湿敷后外涂复方卤米松乳膏。
二诊:自觉瘙痒缓解,大便恢复正常,皮损颜色转淡,肥厚程度减轻,仍有少量渗出。上方加萹蓄20 g,茯苓30 g,白术(炒)15 g,14剂,服法同前。外用龙胆草、生甘草、马齿苋煎汤冷湿敷后外涂全蝎软膏。
三诊:患者皮疹尽消,无瘙痒、渗出表现,未见其他不适症状。口服半月龙胆泻肝胶囊,外涂全蝎软膏,巩固治疗。
按语:本例患者为中年女性,有神经性皮炎病史。患者因皮损症状严重,反复搔抓刺激患处,日久导致湿疹样变。加之此年龄段女性受生活、工作等压力影响,情绪烦躁,气闷不舒,日久肝火旺盛而出现口苦、便干、舌红、苔黄、脉滑数等症状,辨为肝火炽盛证。内治上应疏肝泻火,利湿止痒,以龙胆泻肝汤加减。因患者皮损色红,热像较重,故加赤芍、牡丹皮清热泻火、凉血解毒,瘙痒严重加白鲜皮、地肤子清热燥湿止痒;方中多用凉药,故加陈皮、苍术保护脾胃,以防药寒伤中。二诊:症状减轻,但仍有渗出,故加茯苓、炒白术健脾、利水渗湿,萹蓄清利湿热,诸药合用有利于改善湿疹样皮损表现。三诊:患者诸证减轻,基本痊愈,口服中成药“龙胆泻肝胶囊”巩固治疗。外治上,因渗出较重,用冷湿敷治疗后外涂激素药快速缓解皮损不适。二诊皮损虽仍有渗出,但症状减轻,表现稳定,故在湿敷后换用不含激素的全蝎软膏,保证疗效安全。三诊基本痊愈,外用全蝎染膏润燥养肤,巩固疗效。
4.2 验案2
李某,女,56岁,退休人员,2019年8月17日初诊。患者1年前颈后部、背部皮肤突然发生散在红斑,瘙痒异常,抚之粗糙。自行外用激素类药膏,病情时好时坏,未予重视。3个月前,因皮损逐渐向尾骶部及双上肢外侧蔓延,并出现丘疹伴有渗液,遂于当地医院就诊,以“湿疹”收入院,住院期间静点治疗,并配合“氧化锌软膏”“地奈德乳膏”等。出院后病情虽有好转,但仍有皮肤粗糙,瘙痒等表现。近日病情出现反复,遂来我院以求中医药治疗。刻下:颈后、背部、尾骶部、双上肢外侧散在红斑丘疹,皮肤苔藓样变,瘙痒严重,抓后有少量渗出,伴有心烦胸闷,腹胀,呕恶,肢重,饮食不佳,睡眠尚可,大便黏腻,小便正常,无口干口苦,舌淡红,苔白腻,边有齿痕,脉弦滑。辨证:肝郁脾虚证。治法:疏肝解郁、健脾除湿。处方:丹栀逍遥汤加减。组方:牡丹皮15 g,栀子15 g,柴胡15 g,白芍15 g,炒白术15 g,茯苓30 g,当归15 g,白鲜皮20 g,地肤子20 g,陈皮15 g,半夏15 g,乌梅20 g,枳实15 g,甘草15 g。14剂,水煎服,日1剂,早晚饭后30 min温服。外用龙胆草、生甘草、马齿苋煎汤冷湿敷后外涂复方卤米松乳膏7 d,7 d后与全蝎软膏交替外涂。
二诊:治疗后皮损症状稳定,瘙痒缓解,无渗出,心烦胸闷症状减轻,但出现便稀症状,加干姜15 g,吴茱萸15 g。14剂,服法同前。用复方卤米松与全蝎软膏交替外涂,并逐渐延长全蝎软膏使用时间。
三诊:患者基本恢复正常,未见瘙痒、胸闷或其他不适症状。上方不变,7剂,服法同前,外涂全蝎软膏,巩固疗效。
按语:本案患者患病时间长,先前经西医按照“湿疹”治疗,效果不佳,根据患者对病史的详细描述,可判断患者初起时为神经性皮炎,后因反复搔抓或外用用药刺激使皮损出现湿疹样表现。患者胸闷为有肝郁表现,饮食不佳、大便黏腻为脾虚痰湿表现,结合患者舌脉等客观症状,辨为肝郁脾虚证。内治上应疏肝解郁、健脾除湿,方选丹栀逍遥散加减。因患者腹胀、胸闷枳实行气、宽胸、开郁;呕恶,肢重,为痰湿症状,故合二陈汤,燥湿化痰,其中成分乌梅又可抑制过敏反应,一举两得;痒重加地肤子清热止痒。二诊:患者出现便稀症状,加干姜、吴茱萸温补脾胃、温阳止泻,以防汤方过于寒凉而伤及脾胃。三诊:患者诸证减轻,基本痊愈,又服14剂巩固。外治上,因有渗出表现,则先冷湿敷治疗,并在前7 d外涂激素药膏快速控制皮损表现,又因本案患者病程长,且外用过多种药膏,为避免完全代替治疗使皮损症状出现反复,故在7 d后用全蝎膏与复方卤米松乳膏交替应用治疗。二诊皮损无渗出,表现稳定,故可延长全蝎软膏外用时间,逐渐代替激素治疗。三诊基本痊愈,外用全蝎染膏润燥养肤,巩固疗效。
5 小结
目前,原发疾病发生湿疹样变而导致误诊误治的病例不占少数,临床中应注意与单纯性湿疹进行鉴别。据文献报道[16-17],湿疹样变还可发生在银屑病、手足癣、带状疱疹等疾病上,因此临床中需透过现象看本质,抓住疾病发生的主要规律,切忌千篇一律,墨守成规。
王俊志教授认为,神经性皮炎湿疹样变具有瘙痒难耐特点,患者反复搔抓刺激导致皮损症状恶性循环而出现情绪异常表现,因此在注重药物治疗的同时,也应重视对患者进行心理上的安慰。辨证上,考虑到不是所有神经性皮炎患者都会发生湿疹样变,因此这类患者素体定有湿邪。初期主要责之肝脏,因患病日久,肝郁不舒而致肝经火毒炽盛,加之素体有湿,湿与火热相搏结,泛溢肌肤,而成湿疹样变;后期主要责之脾脏,因日久忧思伤脾、肝火克脾等因素,使脾脏受损更生湿浊,导致湿疹样变日久迁延不愈。选方用药上,清肝泻火不忘护阴,健脾祛湿不忘疏肝,灵活运用经典方剂,并根据患者禀赋异同随证加减,临床疗效显著。
总之,医者应在建立信任的基础上,配合精准辨证,灵活施治,正确选方用药,方能事半功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