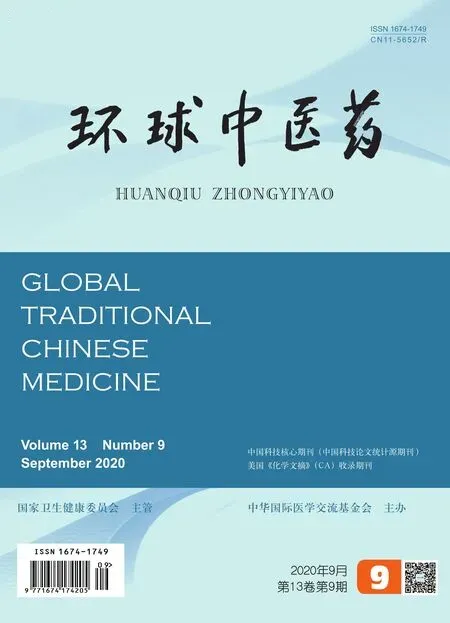刘燕池养阴学术特色浅析
2020-01-11覃骊兰张德龙郑伟灏马淑然
覃骊兰 张德龙 郑伟灏 马淑然
刘燕池,河北定州人,是北京中医学院首届毕业生,曾任北京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院长,现为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医内科学专家。刘燕池教授从事中医基础理论知识教学及临床已有五十几载,始终怀揣着一颗博爱与仁义之心,尽心尽力地救治每一位患者,从而获得北京地区的广大患者的赞赏与支持。在学术上发表论文60余篇,在国内外出版专著及教材45部,主持和参与多项科研课题。在刘燕池教授的影响下,现已成立北京中医药大学“名医工程刘燕池传承工作室”。此外,刘燕池教授还是北京中医药大学研究生院博士后流动站临床学术经验合作导师。
刘燕池教授是第三届“首都国医名师”,其出生于中医世家,幼时便熟读中医经典,家承其父治疗肝病的临床经验,后入北京中医学院系统地学习了中医理论和临床知识,而后待诊于北京妇科名医刘奉五左右,得其宝贵的临证经验,这些经历都是刘燕池教授学术思想的构建与形成的基石。现将其学术思想总结如下。
1 推崇丹溪“阳常有余,阴常不足”
1.1 相火妄动,易耗阴精
朱丹溪在《格致余论》中说到“气阳血阴,人身之神,阴平阳秘,我体长春”,解释了人体之所以不能“阴平阳秘”,正是因为“阳有余,阴不足”。刘教授着重说到,今时之人,好食膏粱厚味之物,沉迷酒色物快于心等不良的生活习惯,都易于导致相火妄动,损耗阴津。所谓相火,在《类经·运气篇》云“相火居下,为源泉之温,以生养万物,故于人也属肾,而元阳蓄焉”,即为肾中元阳之所在,为水中之火,故《内经》云:“相火在下,水气承之。”而相火属阳,其性易动,赖于肾中阴精,不致相火妄动而发挥其正常生理功能。若阴精损耗,阴不敛阳,则易引起相火妄动,轻则情志不舒,重则君相互煽,上扰心神,出现烦躁、狂怒等情志失常症状,还会进一步损耗阴精,病难愈。
1.2 滋养肾阴,还应兼顾它脏之阴
刘燕池教授还强调阴精的损耗是由多种因素引起的。虽以损伤肾中之阴为主,但五脏皆可致阴虚,非独肾也,是因肾受五脏六腑之精而藏之,而肾阴又为人身阴液之本。五脏之阴伤,久而必祸及于肾,而肾阴亏损,五脏之阴皆亏,故《灵枢·本神》曰:“是故五脏,主藏精者也,不可伤,伤则失守而阴虚,阴虚则无气,无气则死矣。”因此,刘燕池教授指出在临证之时,因以“固护阴津”为先,先察何脏阴虚,是否已损及肾阴,在滋养肾阴之时应当兼顾他脏之阴。
2 滋阴之法非独用,而是善用
朱氏曾言“阴常不足,阳常有余,宜常养其阴,阴与阳齐,则水能制火,斯无病矣”,故创大补阴丸[1],方中以龟甲、熟地黄为君药,滋阴益肾,阴复则火自降。而黄柏、知母为臣,苦寒泻火,火去则阴可保。而猪脊髓能填精益髓,可保阴生津。五药合用,以泄相火而补肾阴,共奏滋阴降火,使机体恢复到阴平阳秘的状态而使病愈。
历代医家亦认为其有峻补真阴,承制相火之功,临床应用颇为广泛[2],但刘燕池教授在临床中发现,黄柏为大苦大寒之品,虽泻火之功强,但久用亦有伤阴之弊。而龟甲、猪脊髓虽有滋阴之效,但亦不及麦冬、石斛等药。因此,刘燕池教授认为大补阴丸并未较好体现“滋阴降火”之功。刘燕池教授虽师从丹溪之法但却不泥于其方,在滋阴时,善用生地黄、麦冬等药,性味甘凉之品,可濡养人身之阴。而在降火之时,则应减少过寒过凉药的剂量,如生石膏、黄柏大苦大寒之品,从而避免损阴之患。又如刘燕池教授在热秘患者治疗中,虽未见阴虚之症,仍旧会在处方中加上麦冬、石斛等养阴之药与通下之品同用,即有通腑之效,又无伤津之虞。
刘燕池教授“固护阴津”的学术思想深入其临床用药的方方面面[3]。刘燕池教授虽治疗一切疾病皆会用到滋阴之法,但并非独用,而是善用、妙用,强调辨证论治,从整体上将理论与实际充分结合。
3 滋阴之法在妇科的应用
刘燕池教授“滋阴”的学术思想更多应用在妇科方面的治疗当中,其师承于刘奉五先生,刘奉五先生在治疗妇科疾病时,主要注重肝脾肾与疾病之间的关系。但刘燕池教授在治疗上,更加注重肾脏,这是因为肾精易损难回,因此要滋养肾阴,补其所耗。又如刘奉五先生的“四二五合方”,刘燕池教授在临床上也喜用四物汤养血滋阴,但多加用菟丝子、川续断、九香虫滋补肾阴。此外,刘燕池教授在“瓜石汤”方的基础上[4],筛选出生地、麦冬、石斛等滋阴药,构成心、肺、肾三脏之阴的组方,广泛应用于临床各科疾病。
刘燕池教授强调指出妇科疾病的主要原因大多在于肝肾功能不足,从而导致肾不能藏精,同时肝失疏泄。目前,刘燕池教授在诊治月经不调、先兆流产、子宫肌瘤、产后抑郁等妇科疾病,疗效显著,得到患者的一致认同,且所接待的患者中,其中妇科疾病患者人数位居第二[5]。
4 滋阴之法在肝病的应用
刘燕池教授生于中医世家,其在临床上推崇“滋养降火”的思想可能受到其父刘玉出先生的潜移默化所形成的。刘玉出先生曾为北京积水潭医院中医科的名老中医,在学术方面推崇清代吴瑭所著的《温病条辨》,主要致力于肝病的研究,提倡肝病的治疗,应以“清解”和“清化”为主[6]。强调肝为刚脏,其气其阳易亢易逆,应当以泄为补,慎用温补之品,以免湿热内盛。
刘燕池教授继承了其夫治疗肝脏疾病的临床经验,以清解清化、凉血柔肝为主,慎用温热药,避免伤阴之患。若是需用到柴胡、陈皮等疏肝理气之品,应配以滋阴药如白芍、丹皮等,正是因为刘燕池教授其父的临床思维,为刘燕池教授“滋阴”学术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5 妙用家传验方
刘燕池教授其父还留下了两个临床验方,“肝甲饮”和“肝乙煎”。前者是由茵陈、金钱草、板蓝根、桔叶、佩兰、青皮等药物组成,其功效为清热解毒、化湿退黄,主要用于治疗黄疸型肝炎。后者由金钱草、海金砂、鸡内金、茵陈、佩兰、桔叶、青皮、垂盆草、凤尾草、叶下珠等药物组成,主要用于治疗无黄疸型肝炎。两个方子均有清肝热之效,但在解毒和祛湿侧重不同。至今这两个验方仍是刘燕池教授在治疗肝病的常用方剂,临床亦证明了其有效性,如降低转氨酶、促胆红素升高等。
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人类疾病谱的改变,“肝甲饮”的应用也较前受限。而“肝乙煎”被刘燕池教授逐步开发其应用范围,如配合泽泻、焦山楂、荷叶治疗高血脂症;配合蜂房、鳖甲、牡蛎治疗肝硬化。刘燕池教授将自身所学的知识与实践相融合,并没有收到父辈的影响,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思想。
6 活用中医理论指导临床实践
刘燕池教授虽出生于中医世家,自小受到中医环境的熏陶,后在北京中医学院系统中医知识,在临床实践过程中,善于用结合中医理论知识。刘教授强调到,若临证之时脱离中医理论的指导,则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例如随着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失眠患者也在逐年增加,多为阴阳失调、心肾不交。而刘燕池教授善用于“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理论对失眠进行分析,是因阳热于外、阳不能入于阴,阴亏于内、不能敛阳,从而导致失眠,阴阳不能调和。而对于心肾不交的失眠,历代医家喜用经方交泰丸,但近年发现临床效果并不是很好,主要原因是肉桂温热过甚,助阳太过。常用于治疗失眠的方剂还有归脾汤、天王补心丹,此二者仅适用于虚证,不适用于现代失眠患者。现代临床的失眠皆为虚实夹杂,阳盛于外,阴虚于内。
刘燕池教授强调临证须具体辨证施治,而治疗现代失眠的原则应为养阴生津,清脏腑之火,可用百合、石菖蒲、黄连、竹茹、沙参、麦冬、生石斛加上镇静安神药物。若心悸明显,则酌加生磁石、生龙骨、生紫石英。每于临证之时,唯有将理论与实践结合,才能对病症了然于胸,用药精准。
此外,刘教授致力于发展和完善中医基础理论,补充及完善了中医理论体系。还补充了五行学说的“制化”和“胜复”的调节内涵,增加了五行学说的理论认识和应用价值等多方面的贡献,系统总结了肝病、肾病、胃肠病、过敏性疾病、妇科杂症等疾病的病因病机、辨证论治、用药化裁等规律,推动了中医学科发展及中医诊疗规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