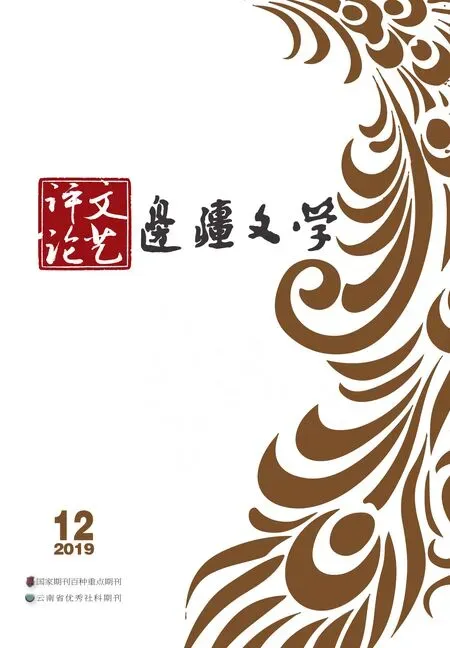曹文轩写作的新探索
——浅析小说《穿堂风》
2020-01-11字春华
字春华
小说《穿堂风》是曹文轩先生自获得被誉为“儿童文学的诺贝尔奖”的国际安徒生奖之后创作的首部作品,作为国际安徒生奖的获得者,且是目前中国唯一获得此至高国际荣誉的作家,曹文轩先生的新作注定会引起广泛的关注与谈论。从曹文轩先生本人创作的角度来说,小说《穿堂风》在写作上也做出了新的尝试与探索,无论是小说的人物性格的塑造、主题思想的表达到篇幅的长短上,《穿堂风》都有了“新风”,具体来说,小说对主人公橡树的成长背景与性格的塑造较为细致深入,层次感较强,同时,也更加关注对人性“暗面”的剖析与拷问;在主题表达上,更为现实深刻与普世,并写出了“成见”下人性的复杂性;在篇幅上,故事情节的推进设计更为直接明了。这与曹文轩先生获奖前的作品相比,可以说,小说《穿堂风》开启了曹文轩先生写作上探索的“新风”。
小说《穿堂风》主要讲述了一个名叫橡树的男孩,很小的时候曾经在父亲的诱导下为父亲的偷窃放过风,也有过偷窃行为,因而他也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那就是被油麻地里的同龄人和大人们孤立了起来。人们的“成见”一旦形成,是很难被改变的,所以,虽然橡树自听了母亲临终前的嘱托后再也没有偷窃过,但此后只要油麻地里出现失窃的事情,大家虽然不说,但还是情不自禁地把怀疑的目标指向了橡树,在炎热难耐的大夏天里,橡树就像一个游荡的孤独的魂,没有玩伴,也没有太多的关爱,在极度孤独中成长的橡树,内心里是渴望被认同的,他也在用自己的方式极力地在油麻地里寻找着归属感,最终,他以将自己和真正偷窃油麻地财物的瓜丘用手铐拷在一起的悲壮的方式证明了自己的清白。在橡树的孤独的成长里,他所面对的“苦难”不仅有来自同龄人的“成见”与隔离,更有来自成年人的“成见”与隔离,这样的“成见”与隔离或隐性或显性地随时围绕在橡树的身边,它比曹文轩先生以往小说中主人公成长经历中所面对的“苦难”更为残酷深刻,也更加难以克服。
小说中,橡树是孤独的,他的孤独是多重的,在对橡树这一人物的塑造上,曹文轩先生也关注与探索到了更广的描写向度与深刻的剖析角度。
橡树的孤独首先源于自己的原生家庭。作为一个孩子,在他很小的时候,喜欢赌博、偷窃的父亲诱导他在偷盗的时候帮着放风,后来,父亲被捕入狱,他也就此失去了与父亲之间的连结,这里父亲的不正确的教育引导本身也已经将橡树与他身边的人孤立了起来,再后来,能正确教育引导橡树的患重病的爱漂亮干净的母亲又去世了,他也就此失去了母爱,家里就仅剩双目失明且驼背的奶奶和他相依为命了,而奶奶又不能真正知道他想要什么,就这样,在缺乏正确教育引导与关爱的原生家庭里,橡树生来就是孤独的。
同龄人是儿童的最好的玩伴,也是儿童最好的学习与模仿的对象,而橡树与同龄人也是隔离的,这也是他孤独的来源之一。炎热的夏天里,油麻地里的乌童家的草棚下有因“风洞效应”而形成的穿堂风,无论外面如何的炎热难耐,奇特的是乌童家的穿堂风却一天到晚地吹个不停,这里也成为了村里孩子们避暑的夏日天堂,他们在穿堂风下快乐地做家庭作业、玩游戏、吃西瓜、下军旗、喝竹叶茶,而唯独没有橡树,因为在他们的心里,早就认定橡树是“小偷”。就这样,橡树就被无形无情地隔离在了同龄人的陪伴与快乐之外了,同龄人的心里也对橡树竖起了一堵隔离的墙,让他独自去孤独,这无形中形成的“成见”与隔离的壁垒是难以打破的,也是残酷的。
橡树的孤独还在与成人的隔离上。在油麻地里,只要有丢失财物的事件发生,人们都会从心底里情不自禁地将目标投向橡树,他们心里又会说:“不是他偷的,又会是谁偷的?”这也是油麻地里的成人们自然地、理所当然地得出的结论。橡树为了排遣他那无边的难以安放的孤独时,他就只能和田野里的鱼、山羊、小兔子说话,但结果往往是背道而驰。当他在河堤上与一只白山羊说话、交朋友、帮它清洗的时候,出现的主人用疑惑的目光看着他,他不知是进还是退;当他在和池塘里悠悠游动的鱼儿说话、想帮它们寻找一个更阴凉的地方时,出现的主人怀疑地盯着他的眼睛反问:“在跟鱼说话?”;当他在瓜田里追赶一只淡棕色的和他捉迷藏的小野兔时,不小心扑到一只西瓜上的时候,出现的老汉把身子挺得笔直对他说:“走开吧!”,这些成人的不问缘由的怀疑是可怕的,是残酷的,也是值得读者们深思的。
面对孤独成长中的“苦难”,橡树只能用极端的方式去证明自己的存在,并用自己极端的方式在油麻地里寻找着归属感,这与曹文轩先生以往写作中所提倡的在少年成长中用“优雅”的态度面对“苦难”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在炎热难耐的大夏天里,为了引起穿堂风里快乐的孩子们的注意,橡树光着脊梁、头戴草帽,故意在没有任何遮挡的田野上穿行。有时,他还会故意蹲下去,让地里的稻子遮挡住自己,再到更远的地方再露出脑袋,“于是,孩子们就在心里猜测:难道,他是从田埂上爬着前行的吗?孩子们手里都拿着咬了一半的西瓜,一直无声地向那里看着。”此外,有一天,倔强的无处安身的橡树危险地爬上了油麻地里最高的一座屋——祠堂上,为自己孤独的心灵找一个安顿的地方。祠堂在中国民间是认祖归宗的最为权威和神圣的地方,也是族群身份的认同和归属的安顿处所在。“他高高地坐在祠堂顶上。远远地看,倒像一只鸟,但是一只不能飞的鸟。”当他被众人从屋顶上劝说下来时,“他没有从别人搬来的梯子下去”,而是“顺着屋后的大树上回到了地面”,这里由于橡树所面对的“苦难”是十分猛烈与难以克服,所以,他只能以极端地方式来面对。
矛盾冲突是推进小说故事情节的关键因素。小说中,橡树除了要面对来自同龄人与成年人的“成见”与隔离外,他也必须要独自一个人去解决孤独的根源所在。在融不进油麻地而只能选择孤独的夜行中,橡树发现真正偷窃油麻地财物的是瓜丘,看到真相后的橡树开始了跟踪与阻止,甚至还被发现的瓜丘用脚踩头,反被污蔑说:“因为你爸爸是小偷,你也是小偷。”面对难以制服的小偷,加上油麻地人们的不信任和怀疑,橡树所要面对的“苦难”更加激烈复杂,这“苦难”既有来自油麻地人们的外在行为的“歧视”,更有来自油麻地人们的心里的“歧视”,这样的设定读来少了曹文轩先生以往小说里所着重呈现出的诗意的温柔,而多了与现实残酷社会与人性的剖析。为了报复纠缠不休的难以摆脱的橡树,瓜丘偷了元福二爷家的白山羊,故意将其栓在橡树家屋后的林子里,来诬陷橡树,看到正在解开绳子想要将羊放走的橡树,不明真相的油麻地里的人们更加坚信橡树是“小偷”,甚至关心他的奶奶都无奈地悲哀地对老天说:“我一辈子没有做过一件对不起人的事情,你为什么要给我这样的儿孙!……”,到此,孤独的橡树已经被逼入到绝境中了,经常出现在曹文轩先生笔下的油麻地里的人们也不再“单纯”。
直到孤独无法忍受的时候,绝境中的橡树决定用决绝悲壮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清白。为了抗争,为了证明,橡树“偷了”奶奶为他储存的用来娶媳妇的钱,到镇里的铜匠铺里打了一副手铐。一天深夜里,橡树用它把自己和正在偷粮食的瓜丘锁在了一起,任凭瓜丘的殴打、拖拽,最终,挣脱不了的瓜丘向油麻地的人们和盘托出了自己的偷窃行为。真相大白后,作为孩子们夏日天堂的有穿堂风的草棚主动接纳和邀约了橡树,但橡树更喜欢到大河边藏在一片树林里的寺庙中,孩子们也更喜欢到田野上玩耍了,而曾经凉爽的穿堂风已经是:“每天都是大太阳。草棚下,穿堂风每天空空地、寂寞地吹过那条长长的过道……”。这样不是美好的大团圆的结局与曹文轩先生以往小说的结局是有所不同的,这也留给了读者更多的解读空间,让小说显得更加的意味深长。
在解决“苦难”的过程中,当橡树感到孤立无援,无处话凄凉的时候,他会到母亲的坟头去哭诉,他也始终记得母亲在临终前用剩余的生命向橡树说了最后一句话:“儿子,答应妈妈,从此以后,不再偷了……”。当乌童在穿堂风下快乐自由玩耍的时候,她会时常想起曾在黑夜里给过她温暖和安全帮助的橡树,心里也默默地想要邀约橡树到穿堂风下,在橡树“偷羊被抓现行”的时候,乌童在迟疑中从心里选择相信橡树。当橡树在抓住了瓜丘的时候,“他想起了乌童家的草棚,心里莫名的升起一股渴望——渴望凉爽的穿堂风。”可惜的是,这样成长中的温暖的力量更多是想象的,少了曹文轩先生以往写作中的小说人物群像所体现出的感人的“人性的悲悯”的大爱的力量。这里,橡树的成长更多的也只能是“自我”的内在式的成长,这也揭示出了在残酷的现实面前,“真正能拯救自己的唯有自己”这样现实而深刻的主题。
通篇来看,小说《穿堂风》与曹文轩先生写出的其他系列小说相比,整体简洁明快,在情节设置上也更加浓烈直接,篇幅字数也相对较少。在小说的主题表达上,曹文轩先生把目光聚焦在了一个因为有过不良行为而备受排斥和隔离的男孩的身上,故事主线读来并不复杂,但在不断推进的故事情节之中,现实的人情冷暖与世间百态以及人性的复杂性却得到了深刻的表达。小说也深刻地写出了每个人都有自己逃不开孤独的时候,也会有不被人理解的时候,这样现实的揭示能够让读者读起来感同身受,也能够让读者对人性的复杂性有更深入的剖析与拷问,从这一主题来看,小说《穿堂风》是“成人式”的儿童小说,也是富有深刻教育意义的儿童小说。
在小说《穿堂风》的后记中,曹文轩先生写道:“‘新小说’不只是指它们是我的新作,还有‘新的思考’‘新的理念’‘新的气象’等其他含义”。从小说《穿堂风》的叙事模式、叙事主题、到表现形式上看,曹文轩先生在写作上都有了“新的探索”。

马云 阳台上的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