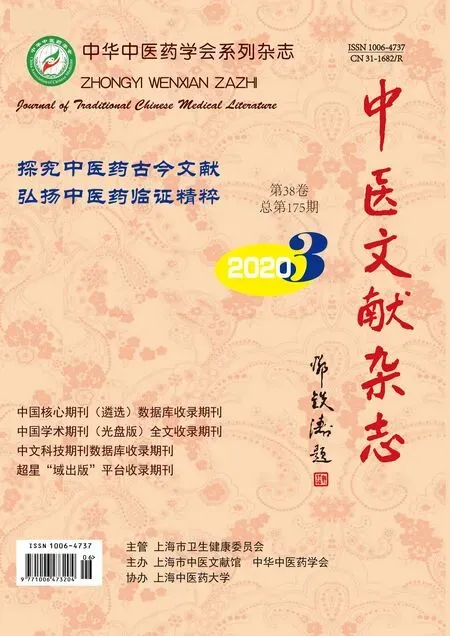朱子文“湿不单见,脾不独虚”论治泄泻特色*
2020-01-10浙江中医药大学杭州30053王洁宜陈明显
浙江中医药大学(杭州,30053) 王洁宜 陈明显 傅 睿 指 导 陆 拯
朱子文(1875—1944年),讳学彬,湖州人氏,16岁赴余杭仓前学医,师从晚清名医葛载初(1839—1909年),苦学五年得乃师治虚劳杂症之薪传,回湖应诊更是孜孜不倦,每遇疑难杂症必翻阅经典反躬自问,常说“为人治病,不能自文其过”“医学深渊,须集思广益,才能精进”。朱氏临床擅治内伤虚损性疾病,对内、妇、时病亦有研究,处方用药灵活而不失章法,终成一代名医。清末民初,朱氏又与数十同道创议发起湖州医药学术团体,是为吴兴医学会之发端,并历任理监事、主席。朱氏先后传授数十人,门人遍及沪、湖等地。唯忙于诊务,无暇著述,朱氏原有保存医案,然多遭散佚,幸有长子朱承汉、长兴董维波、湖州闵望歧、上海沈振元等受业门人随师门诊抄录之医案选录数十则,录于《湖州十家医案》。
陆拯教授早年师从朱承汉先生,每阅医案叹曰:“太先生(朱子文)与朱师(朱承汉)之用药何其相似,看着《湖州十家医案》中太先生的医案,就像回到了当年跟老师抄方的时光。”不可否认,中医在每一支、每一脉的传承中都有其独特的风貌,且保存了很多宝贵的医学技术和经验及理论,迄今仍值得后学挖掘整理。今笔者有幸阅其医案,择其经典案例,整理其治疗泄泻的经验,供各位同道临证借鉴。
论治特色
1.湿不单见,脾不独虚
泄泻是临床中常见的一种脾胃病证,它以排便次数增加,大便溏薄,或急或缓,甚如水样为主要特征,包括现代医学中的急性肠炎、炎症性肠炎、肠易激综合征、功能性腹泻等疾病。西医在临床上多采用控制炎症的药物或止泻药进行治疗,如抗菌药、氨基水杨酸制剂、糖皮质激素、洛哌丁胺等,但是存在复发率高、副作用多等问题[1]。研究显示,中医药可通过调节脑肠互动等有效减少副作用并降低复发率[2],在治疗泄泻上具有很大优势。
五谷、食饮为脾胃功能之所主,对此,《素问·经脉别论》详细描述了其在体内运化输布的过程:“食气入胃,散精于肝,淫气于筋。食气入胃,浊气归心,淫精于脉……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临床中也发现,五谷、水湿不运,易发生泄泻,说明确与脾胃密切相关。朱丹溪对此指出:“泄泻者,水湿所为也,由湿本土,土乃脾胃之气也,得此证者,或因于内伤,或感于外邪,皆能动乎脾湿。”[3]这与《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的“湿盛则濡泻”一脉相承,张景岳也认为:“泄泻之本,无不由于脾胃。”[4]朱子文借鉴朱丹溪、张景岳的认识,指出湿邪偏盛、脾胃失运是水谷并走大肠的主要原因。
朱子文又注意到《丹溪心法·泄泻》中有言“泄泻,有湿、火、气虚、痰积”之不同[5],再结合多年临床经验,认为“引起泄泻的邪气虽以湿邪最为多见,但其他风寒暑热诸邪往往与湿邪相兼侵犯人体”,正如《杂病源流犀烛·泄泻源流》所说:“湿盛则飧泄,乃独由于湿耳?不知风寒热虚虽皆能为病。”[6]另泄泻之由,除风寒暑湿之侵外,还有长期的情志、食劳之伤,秉承张景岳“盖虚寒之泻……实因火不足……实因气不行”[4]的理论,参合四诊所得,这类泄泻不仅仅局限于单纯的脾虚证候,而是多脏腑功能的失调,故常表现出慢性虚损性疾病“迁延难愈、缠绵反复”的特征。由此,朱子文对泄泻疾病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见解,提出了泄泻“湿不单见,脾不独虚”的观点。临床上,泄泻患者多呈现出“寒热交织,正虚邪恋”的复杂证候,其湿邪多兼热、郁、滞、寒,而脾虚多伴肝郁、肾虚。虽然时代变迁,但朱子文对泄泻的认识对当前仍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
2.正邪涩利,活法应用
在泄泻治疗中,朱子文首先区分急性泄泻和慢性泄泻,认为急性泄泻宜速治,慢性泄泻难速愈。其中急性泄泻多由外邪引起,以湿盛邪实为主证,故重在祛除湿邪,兼顾素体;而慢性泄泻多见于脾虚证候,亦与肝肾密切相关,故重在调理脾胃,并治肝肾。
无论急性泄泻还是慢性泄泻为病,往往虚实互见,有邪之处多为正气已虚。面对这类正虚邪恋的复杂证候,朱子文扶正祛邪两者兼顾:七实三虚,绝不骤用补涩,而是先行攻邪之法;七虚三实,绝不漫投分利,首先考虑脾胃元气。朱丹溪曾警示后人:“世俗类用涩药,治痢与泻。若积久而虚者,或可行之;初得之者,必变他疾,为祸不小。”[5]朱子文在治疗急性泄泻时谨防邪气固闭,也从不胡乱投以补涩之剂,如参芪、诃子、赤石脂、罂粟壳、肉豆蔻均在禁忌之列。但在慢性泄泻的治疗过程中,朱子文又深受张景岳的影响,极度推崇其分利禁忌:对于“病久者”“阴不足者”“脉证多寒者”“形虚气弱者”[4],从不滥用分利之法,使用茯苓等利水之品,也会加入灶心土、煨木香温中止泻。
3.祛湿分利,调畅中州
朱丹溪指出,初得泄泻者,“多因于湿,惟分利小水,最为上策”[5],景岳亦言:“治泻不利小水,非其治也。”[4]朱子文对此十分认同,他常祛邪化湿,佐以分利治疗急性泄泻。若因湿热,则清化湿热,喜用生米仁、车前子、茯苓;若因暑湿,则清暑化湿,惯用滑石;若因寒湿,则行温化之法,焦白术、炮姜炭颇为适宜;若兼表邪,则佐疏解,杜藿香、佩兰叶每每应手;若兼伤食者,则施导滞,焦神曲、山楂肉、炒谷芽疗效颇佳。以食泻为例,食泻常伴腹痛,粪臭如败卵且常见未化之食,舌苔浊腻,脉滑沉实。《时病论·食泻》中有提及“缘于脾为湿困,不能健运,阳明胃府,失其消化,是以食积太仓,遂成便泻”[7],指出食泻本在湿,标在滞。根据“急则治其标”的原则,朱子文先祛其邪,采用“消食导滞”之法因势利导,并指出,不除积而一味补正,有助邪之弊,若先清积食使邪有出路,则正气自复,所谓邪去而正自安也。对于热象较显者以枳实导滞丸加减,而热象不显者则以保和丸加减。
朱子文对暑湿泄泻的诊治多有阐发,指出“夏季暑湿当令,素有脾虚内湿者尤为易感”。湿邪复感暑气,浊腻更甚,致束表困脾,束表则肺气失宣,汗无所出,甚则内郁发热;困脾则加重中焦气阻,清阳无法升举,进而食欲不振,呕吐泄泻,临床常见鲜红舌质、黄腻舌苔,滑数或满数脉。针对暑湿泄泻,大多医家会采用芳香辟秽、分利渗湿之法,拟藿朴夏苓汤之类以清暑利湿。但是朱子文认为暑为阳热之邪,传变迅速,临床上观察到暑湿合侵会在脾胃化火化热,酿为热痰,或上扰于心神,蒙蔽心窍,甚至出现神识昏蒙的危急重症,故对出现此类病证,或有热陷心包倾向的患者尤为重视,治以清热解毒、芳香开窍之法,常予紫雪丹合银翘散加减,若身热汗出,烦渴欲饮,加薄荷尖、荷叶清暑泄热,若肢困体重,乏力欲呕,加杜藿香、佩兰叶等化浊达表。
4.肝脾肾泄,匡扶正气
《医碥·泄泻》云:“有肝气滞,两胁痛而泻者,名肝泄。”[8]同时张景岳指出:“关门不固,则气随泻去,气去则阳衰,阳衰则寒从中生。”“阴寒性降,下必及肾。”[4]由此可见,除脾泻之外,另有肝泻、肾泻之属。朱子文在诊治慢性泄泻患者中,并见肝脾肾三者失调颇多,或因脾阳无力,或肝木乘脾,或肾阳受累。而肝泻、肾泻多以脾虚为本,湿滞为标,肝肾并见,本虚标实,寒热错杂,基础治法仍以健脾扶正为要,兼有肝气乘脾者佐以抑肝,肾阳虚衰者助以温肾。其中肝泻常见泄前腹痛伴完谷不化,苔或黄或白,脉弦,其特点是每遇情志刺激而加重。朱子文治疗时重在柔肝体,主以痛泻要方,配用合欢花、合欢皮、绿梅花、香附等舒肝之品。至于气血暗亏、肝阴虚耗者,痛泻要方即不适宜,则另需北沙参、乌梅、甘草之品滋养肝阴。
脾阳不振,往往寒从中生。凡见慢性泄泻患者溏泻频繁,伴有脐腹冷痛,完谷不化,饥不欲食,面黄肌瘦,舌淡苔白,脉缓弱或弦滑,病情迁延反复等证候,朱子文均以理中汤作为基础方加减,且在该方的化裁上独具匠心。若辨证为寒甚于湿,易干姜为炮姜炭;若见气虚阳衰显著,重用焦白术,并加潞党参、绵黄芪;若脾寒胃热,伴泛酸作呕,则加炒黄连;如久病及肾,腰酸腿痛,出现肾摄纳无权,下注津水,则加炒萸肉、炒熟地升下焦之阳运。
案例举隅
1.暑湿泄泻
许某,县下街。其素有湿热,又伤于暑,泄泻不爽,口渴少饮,身热不为汗解,神识昏蒙,舌边尖红、苔黄腻,脉滑兼数,犹恐内陷心营之变,治宜解毒开窍、辛凉达邪、芳香化浊。方药:紫雪丹四分(分冲),银花二钱,连翘二钱,薄荷尖一钱,香豆豉三钱,大腹皮二钱,生楂肉三钱,象贝三钱,炒竹茹二钱,云苓三钱,紫背浮萍八分。
按:叶天士有云:“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该患者病属急性泄泻,其人平素阳盛体质,复感暑热阳邪,暑湿合侵,由脾及肺,导致肌肤郁闭,身热甚却不为汗解。再观本案,虽其脉象尚不细数,舌色尚不红绛,可见病邪还未入心营,但已经初现神志不清的急症,须急予紫雪丹清热解毒、芳香开窍,银花、连翘辛凉达邪,以防生变,另用薄荷、竹茹清暑泻热,再伍象贝、大腹皮等祛痰化浊,以助祛邪之力。在诊治过程中,朱子文明辨预后,防患于未然,有效避免了热陷心包重症的发生。
2.脾虚久泄
秦某,湖城,腹痛腹泻久作,神疲纳钝,食欲不振,苔薄白,脉小弦滑,治以温中健脾、涩肠止泻,拟理中汤加味。方药:炒焦白术二钱,炒扁豆三钱,茯苓三钱,炮姜炭三分,环粟子三钱,猪苓一钱五分,淡甘草四分,炒谷芽三钱,炒陈皮一钱五分,煨木香五分,灶心土一块,潞党参一钱五分。
按:本例泄泻乃慢性泄泻脾阳虚证的典型案例。该患者病属慢性泄泻,观其症状乃脾阳衰弱,寒气内结,脾气不升,属虚寒腹泻。故采用正治之法,主以理中汤加味,可无疑义。惟其人脉象小弦滑,与虚寒腹泻的脉象缓弱者不同,其故为何?盖阴寒为病,亦可见弦脉,若久泻脉弦,如循刀刃,乃胃气已败,病多难治,今脉小弦而滑,胃气未伤,用理中汤治之。又因该患者寒象较著,故易干姜为炮姜炭;气虚腹满,再加入潞党参、炒谷芽、炒陈皮;恐猪苓、茯苓利水太过伤阴,又用灶心土、煨木香温脾涩肠,常中寓变,不拘一格,故疗效肯定。
3.湿热泄泻
何某,机坊巷,湿热互扰阳明,大便溏泻,兼渴、咳、衄,肌热时起吋伏,苔薄糙畔红,法拟清化湿热。方药:金石斛四钱,南花粉四钱,柔白薇三钱,白茅根六钱,银花三钱,川郁金二钱,大豆卷四钱,生米仁四钱,象贝三钱,连翘三钱五分,车前子三钱,鲜竹茹二钱,炒枯芩一钱五分。
二诊,热退泻止,咳而不爽,苔糙,舌畔红,脉弦滑,宜宣上而泄里热。方药:扁石斛三钱,生米仁四钱,经霜叶一钱五分,小川连三分,川郁金二钱,焙丹皮一钱五分,生粉草五分,通草八分,炒子芩一钱五分,橘络一钱,丝瓜子三钱,竹茹一钱五分,川贝母一钱五分(去心)。
按:脾为湿土之脏,胃为水谷之海,湿性重浊腻滞,其为病气机升降受滞,脾胃运化受碍,泄泻之证颇为常见。该患者病属急性泄泻,证见湿热合而内侵,当务之急是清化湿热,故以金石斛、银花、生米仁、连翘等为主药,但要注意到湿热已经扰阳明,进而犯肺,以致便泻、口渴、咳衄、肌热并见。此时津液已伤,再若一味苦寒,则有亡阴之危,急需清降滋润之品降火泄热,如南花粉、象贝、柔白薇等,也无滋腻留邪之虞,而病告愈。针对这种湿热变证,朱子文既谨守病机,又灵动变通,其思路值得借鉴。
总之,朱子文认为,治泄泻者,首先要区分慢性泄泻和急性泄泻,方能明晰思路,明确用药。泄泻的病因繁多,虽其关键在于湿盛脾虚,又体现“湿不单见,脾不独虚”,证候多见寒热交织,正虚邪恋,故朱子文在治疗泄泻中以扶正袪邪为法度,以祛湿、温脾为主要治法,但其用药审慎又不拘泥,如解毒开窍治暑泻,理中加减治久泻,其对于变证的理解和化裁思路值得进一步学习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