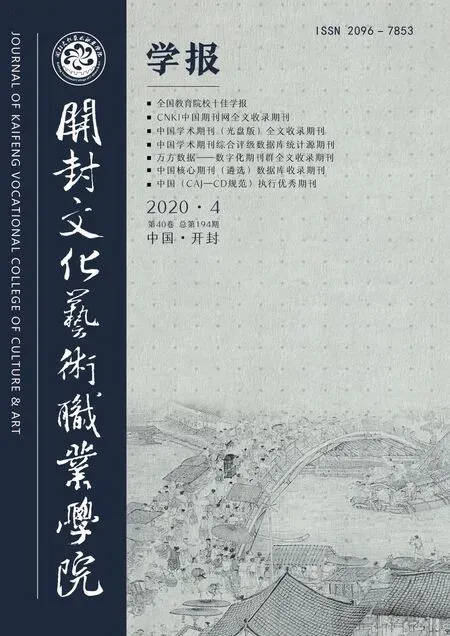《离骚》中植物意象的英译研究
——以许渊冲和杨宪益的译本为例
2020-01-10崔晓亮
崔晓亮
(山西师范大学临汾学院,山西 临汾 041004)
一、《离骚》中的比、兴
王逸曾在《离骚经序》里提出:“《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花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可见,比、兴手法是《离骚》艺术价值的集中体现。理学家朱熹曾在《诗集传》里谈及:“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1]11由此可知,比、兴虽有所分别,但都是借物寓意的手法。
既然比、兴是《离骚》艺术价值的集中体现,那些寄托诗人情感的意象就成了诗歌的灵魂。《离骚》中出现了二三十种植物,借以隐喻、抒情、陈志。研究《离骚》中的植物意象,就是探讨其深刻内涵。
二、《离骚》中植物意象之隐喻
《离骚》中的植物从开篇到结尾分别是:江离、芷、木兰、宿莽、申椒、菌桂、蕙、荃、留夷、揭车、杜衡、菊、薛荔、胡、芰荷、芙蓉、茹、扶桑、藑茅、恶草薋、菉、葹、茅、萧艾、榝,共计25种。朱熹的《楚辞集注》是现今流传最广的楚辞专业文献,筛选集合了前朝诸多名家的注解,当中提到的植物意象可分为三类[2]8。
第一类是江离、芷、兰(木兰)、宿莽等香草植物,这四者幽而芬芳,是君子采摘、佩戴之物。前两者出现在“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脩能。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中,屈原借此抒发自己高洁的情操。后两者更是芳香持久,尤其是木兰,在《本草纲目》中描述为“去皮不死”,与“恐年岁之不吾与”相对应,朱熹称之为“行者之忠善为长久之道”。这类植物意象抒发了屈原注重德行修为、高洁情操,并视之为人间的长久正道。
第二类是隐喻其他君子。《离骚》中提到了申椒与菌桂,原文出处是“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杂申椒与菌桂兮”。“后”即“君王”,意思是曾经的君王德行纯良,选贤举能,身边多是君子。申椒与菌桂这类香草就借以隐喻德行如香草般芬芳的君子。
第三类是隐喻小人。《离骚》中提到了萧艾,原文为“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意思是曾经芳草郁郁,如今萧艾遮蔽。朱熹做注解称萧艾为贱草,借以比喻当时世乱鄙薄,小人当道,陷害贤良,借势乱政。
三、《离骚》中植物意象之英译
北京师范大学的文军教授曾对1992—2012年的楚辞英译研究做出综述,在他的论文《国内楚辞英译研究综述》中提到了10大译本[3],其中最为著名的莫过于许渊冲和杨宪益两位先生的译本。
许渊冲先生被称为中国古诗英译第一人,杨宪益先生的翻译成就则是对《红楼梦》的译介。两位先生都肩负传播中华文化的使命,对传统文化有着深入理解,从文化立场和翻译素养两方面考虑,他们是当之无愧的《楚辞》英译大家,且《楚辞》译本有较高的研究和参考价值。接下来,我们就两位先生对《离骚》中植物意象的翻译进行简要对比。
在许译本中,把上文所述的第一类植物意象“江离”“芷”“木兰”“宿莽”分别译为“sweet grass”“orchids”“mountain grass”“secluded grass”。厦门大学的连淑能先生在关于选词法的九大方法论述中,称这种翻译方法为引申意译[4]83,许渊冲先生在无法找到合适的对等词时,把江离、木兰、宿莽三个具体词引申为概括化的“sweet grass”“mountain grass” 和“secluded grass”, 化实为虚,增加了译文的流畅性,极大减少了西方读者的阅读障碍。然而,为达到原文的意象效果,许渊冲先生加上sweet、mountain 和secluded做定语将三者加以区别,其中,sweet表示甜美,就像西方英译本旧约圣经《雅歌》中第二章第三节以隐喻的形式形容品德超越的所罗门说“his fruit was sweet to my taste”[5]1228,也表达了芳香之意,其后的mountain,secluded做到了词性替换,增加了原文文辞的多样性,同时,结合前文,能够让人联想到屈原是注重内在德行、品性清高的君子。在形式上没有忠实原文,但内容传达效果是统一的。这也是许渊冲先生一贯的翻译思想。杨宪益先生则把“江离”“芷”“木兰”“宿莽”分别译为angelic herbs、sweet selineas、magnolias、winter-thorn。 其中,前两者是采用增词译法,增加angelic和sweet这些积极词汇来传达正面意象;后两者是采用对等译法,不过这种对等更接近于形式对等,而非动态对等[6]159,植物意象内涵的传达虽不及许渊冲先生透彻,但对原文形式的忠实度却更高。对比可知:许渊冲先生翻译时采取的是归化策略,更容易被读者理解;杨宪益先生则采取的是异化策略,更多保留了原有文化特色。两种翻译方法各有千秋。
许渊冲先生提出好的译文要在意境层次最大可能地忠于原文,而非形式上对原文的直译,同时也要尽量接近原文。所以,对于第二类植物意象中隐喻其他君子的“申椒”与“菌桂”,许渊冲先生将其译为pepper and cassia。而杨宪益翻译的风格是异化为主,归化为辅,这也是他一贯采用异化翻译策略的原因。所以杨宪益先生的译本把这类植物意象译为cassia and pepper。在这类意象传达上,两位翻译家的翻译策略差异不大。cassia在英语中是芳香之树,足以传达隐喻之意。但申椒翻译为pepper却很难让人想到其香味四溢,这种现象不仅是翻译的局限,还是跨文化交际之局限。由于文化和语言差异,文化负载词因为特定意象实不可译,所以无法找到它的对等词来完全传达原文的内涵[7](P165)。此处,pepper的翻译就失去了芳香四溢的原本语义,这是两位先生译本的局限,也是跨文化翻译中经常存在的现象,需要译者在翻译注解中稍加阐释,让目的语读者知晓。
许渊冲先生把第三类植物“萧艾”译为weeds stinking strong,杨宪益先生则译为grey herbs。二者都是采用增词译法,增加修饰语stinking strong或grey来表达这种植物令人厌恶,让人明白原作者借此来表达讽刺。当前,有许多翻译家都提倡在翻译时使用加注法,即在文章中加脚注解释说明一些文化负载词,而像许先生和杨先生这种在文内直接通过增加修饰语来传达意象的方法显然就比加注法要高明得多。在这类植物意象的翻译上,两位先生的翻译可尽显异曲同工之妙。
结论
当下,随着中华优秀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传播,中华传统典籍也随之走向世界,翻译人员在翻译特定文化意象词时可以借鉴许渊冲和杨宪益两位大家翻译《离骚》中植物意象的方法。一方面可以采用增词译法,用特定修饰词表达意象;另一方面要意识到“不可译”的问题,理解跨文化交际的困难,寻找折中的办法。尤其在无法找到对等词时,许渊冲先生选用引申意义对特定词语进行翻译的方法值得借鉴。另外,通过对比二者的译文,归化和异化的利弊也能凸显,归化更容易让读者理解,异化更能保留原来词语的文化特色,这与翻译学上最基本的语义交际和交际翻译的矛盾如出一辙。杨宪益的译文偏于前者,译作形式上也更忠实于前者,许渊冲的译文偏于后者,在忠于原文内容的前提下,从读者角度考虑对译文形式进行调整,所以他的译作更能让读者接受。这两种方法各有利弊,译者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采用。
笔者以为,在西方接受中华文化早期,可以效法利玛窦当年在中国传教时的方法,在西学东渐之前,为了打开国人思想,他直接用儒家经典论证基督教教义,从而使《圣经》翻译的起步阶段有一个好的开头。当今译者可以借鉴这种方法,在“东学西渐”早期,为了让读者接受,灵活变通,对形式调整,拉低起点,使译文符合西方读者的口味,让其先去接受,继而产生兴趣。而在后期,可以偏向于采用杨宪益先生的翻译方法,把更加原汁原味的《楚辞》等中华传统文化典籍推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