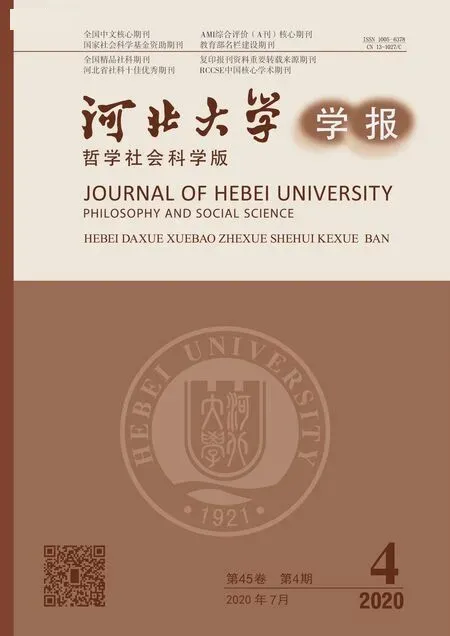儒、商互动与晚明郎署文学权力之下降
2020-01-10薛泉
薛 泉
(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儒(士)、商互动问题,是明代文学史上一个具有深远影响的话题,同时也是研治晚明文学不可或缺的文学、文化常识。目前学界对这一问题的探究,多囿于其对士风、文风之浸染,鲜有涉猎其与郎署文学权力之关系。深入考察儒、商互动的文化意蕴,及其与郎署文学权力下降之关系,不仅关乎对晚明文学历史定位的客观体认,还牵涉对明代文学,尤其是对晚明文学发展、演变历程及其动力的宏观审视与整体把握,因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一、奢靡世风下的儒、商互动
迨及嘉靖年间,由于土地兼并严重,徭役日重,加之阳明心学之浸润、朝廷控制力的减弱,明代工商业渐趋繁盛,市民阶层日益壮大。包括文士在内的明人,生活方式、审美情趣、思想观念等,较之其前,皆已发生很大变化。许多文人士大夫对人生富贵的追求,对物欲、人欲的追逐,不仅不再遮遮掩掩,甚至还有堂而皇之的阐释。王文禄即称: “人恒言富贵,不言贵富,富先贵,何也? 廉子曰:‘财利者,民之心义之和也。’由今观之,贵亦求富而已。”[1]卷二《良贵篇》,第351页结合自身低级官吏出身,王氏将廉子之言普泛化,由民及官,推演出 “贵亦求富” 的观点。有些士人非但对传统儒家所排拒的奢靡不以为然,反而别出心裁,为之注脚。陆楫即言: “彼有所损,则此有所益……若使倾财而委之沟壑,则奢可禁。不知所谓奢者,不过富商大贾、豪家、巨族自侈其宫室、车马、饮食、衣服之奉而已。彼以粱肉奢,则耕者、庖者分其利;彼以纨绮奢,则鬻者、织者分其利。” 奢侈不但无害、不可耻,反可催生出新行业,提供诸多就业机会,有益百姓生计。若人皆节俭,不尚奢华,有人会因此营生成为问题。只要不暴殄天物,奢侈又何妨! 陆楫还引经据典,为奢侈的合理化,寻求理论依据,称此 “正《孟子》所谓‘通功易事,羡补不足’者也”[2]卷六,第640页。嘉靖、万历初人叶权、万历间的王士性等,持论也多相类①(明)叶权撰,凌毅点校:《贤博编》,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9页。(明)王士性撰,吕景琳点校:《广志绎》卷四,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9页。。
与富贵、奢侈观念紧密相关的,是对世俗物欲、色欲的追逐。有士人已毫不掩饰,赤裸裸地展示对此之企羡。如袁宏道《龚惟长先生》所欣羡的五种 “真乐” ,即 “五快活” ,除第三种 “快活” 属精神层面的追求,余皆为物质层面的奢豪企羡。明中后期,追逐人欲、物欲的奢靡风气, “大抵始于城市,而后及于郊外;始于衣冠之家,而后及于城市”[3]卷三《庄氏二子字说》,第85页,快速蔓延至社会各阶层、各行业。张瀚就慨叹道: “二三十年间,富贵家出金帛,制服饰器具,列笙歌鼓吹,招至十余人为队,搬演传奇;好事者竞为淫丽之词,转相唱和;一郡城之内,衣食于此者,不知几千人矣。人情以放荡为快,世风以侈靡相高。”[4]卷七,第139页欲望追逐是无止境的,甚至到不问家之有无的地步: “人之有欲,何所底止? 相夸相胜,莫知其已。负贩之徒,道而遇华衣者,则目睨视,啧啧叹不已。东邻之子食美食,西邻之子,从其母而啼。婚姻聘好,酒食晏召,送往迎来,不问家之有无。曰:吾惧为人笑也。文之敝至于是乎? 非独吾吴,天下犹是也。”[3]卷三《庄氏二子字说》,第85页在 “以侈靡相高” 全民竞赛式的消费潮流中,商品 “原有的‘自然’使用价值消失了,从而使商品变成了索绪尔意义上的记号,其意义可以任意地由它在能指的自我参考系统中的位置来确定。因此,消费就决不能理解为对使用价值、实物用途的消费,而应主要看做是对记号的消费”[5],它已成为社会身份与地位的象征,成为崇富尚虚的时代标识。
不过,物欲、色欲的逐取,在多数情况下还是要 “问家之有无” 的,需以金钱、财力为后盾。这就不能不牵涉与之相关的择业,以及对商贾、商业的看法与定位问题。 “正德以前,百姓十一在官,十九在田”[6]卷十三,第111页,为官致富是士人不二的人生抉择。嘉靖以后,有士人颠覆了这种择业观,对四民之末的商贾及商业,开始重新审视,商贾的作用逐渐得到正视。嘉靖四年(1525),王守仁为苏州商人方麟作《节庵方公墓表》就称: “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以利器,商以通货,各就其资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业焉,以求就其心。”[7]卷二十五《外集》七,第1036页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卷二十九《赠芝麻识破假形 撷草药巧谐真偶》中,蒋生自以为 “经商之人” ,不敢高攀出身仕宦之家的马小姐,马父却道: “经商亦是善业,不是贱流。” 商贾也逐渐得到时人的同情与理解。李贽即谓商贾 “挟数万之赀” ,既要 “经风涛之险” ,还要 “受辱于关吏,忍诟于市易,辛勤万状” ,方可谋利,此 “何可鄙之有?”[8]卷二《又与焦弱侯》,第49页况且,正是由于他们,物品才得以流通,农业生产才更有保障,恰如张居正所言: “古之为国者,使商通有无,农力本穑。商不得通有无以利农,则农病……故商农之势,常若权衡。”[9]卷三十六《赠水部周汉浦榷竣还朝序》,第465页而且,商人也是能 “修高明之行” 的。李梦阳引王文显语即云: “夫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故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10]卷四十四《明故王文显墓志铭》,第1257页汪道昆所谓 “良贾何负闳儒,则其躬行彰彰矣”[11]卷五十五《诰赠奉直大夫户部员外郎程公暨赠宜人闵氏合葬墓志铭》,第1146页,也着眼于此。如此,商贾在四民中的次序,便跃居至士之后、农工之前,即所谓 “商贾大于农工”[12]。由此直接导致事商者大增,有的 地 区 “去 农 而 改 业 为 工 商 者,三 倍 于 前 ”[6]卷十三,第112页。 尤 其 是 徽 州 地 区,竟 “三 贾 一儒”[11]卷五十二《海阳处士金仲翁配戴氏合葬墓志铭》,第1099页,且经商已俨然成为第一等职业。汪道昆就称徽州风俗 “左儒而右贾,喜厚利而薄名高”[11]卷十八《蒲江黄公七十寿序》,第381页。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卷三十七《叠居奇程客得助》亦称: “徽州风俗,以商贾为第一等生业,科第反在次着。” 如此一来,科举失利者,可在家人的理解与支持下,安心事商。冯梦龙《古今小说》第十八卷《杨八老越国奇逢》载,杨八老 “年近三十,读书不就” ,与妻商量,决定弃儒从商,妻劝其 “不必迟疑” 。后来,杨八老历尽艰险, “安享荣华,寿登耆耋” 。对某些士子来说,经商不仅可致富,还有反哺效应,颇益于科举。如农家子弟徐敦,家贫, “试有司不利” ,选择从商,三十岁致富后, “复谢贾事儒” ,昼夜苦读,补为州学生。嘉靖二十六年(1547)中进士,官至南京监察御史[13]卷二十六,第442页。如果没有经商致富为依托,徐敦可能会无法安心读书,猎取功名。这实是一种 “出儒入商”[11]卷四十《儒侠传》,第856页,出商入儒的士商互动行为,为当时不少人所接受。如,休宁人金源有 “两女弟,为苏、汪家妇” , “其可儒者资之为儒,其可贾者资之为贾”[14]卷六十九《金子长家传》,第194页。程所闻之父六虚翁, “子姓二十许人” ,也是 “力任儒则儒,力任贾则贾” 。在他看来, “贾以本富,无淫于末;儒以行先,毋后于文”[14]卷三十五《程翁寿序》,第253页。这样,一家之中可 “儒、贾并兴” ,各有所得。海阳人张于彝,教其三子,因材施教,不拘科举一途,其家即以 “儒、贾二业并兴” ,为人称道[14]卷二十四《张于彝诗序》,第32页。这是根据自家实际做出的选择,能儒则儒,能商则商,就如汪道昆所言: “盖诎者力不足于贾,去而为儒;赢者才不足于儒,则反而归贾。”[11]卷五十四《明故处士谿阳吴长公墓志铭》,第1142页在此,儒、商间的界限,已经变得模糊。于此,苏州商人方麟,看得较明了,他 “始为士业举子,已而弃去,从其妻家朱氏居。朱故业商” 。其友问: “子乃去士而从商乎?” 他笑曰: “子乌知士之不为商,而商之不为士乎?”[7]卷二十五《外集》七《节庵方公墓表》,第1036页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对传统本末观念的一种挑战。
需要特别提及的是, “出儒入商” 的背后,依然着有传统观念的底色。社会对商贾持宽容态度,人们羡慕商贾生活的奢华,并不等于普遍认同 “商贾大于士” 。经商为第一等职业,主要是在一些商贸活跃的地区。在多数人心目中,依然是 “士大于商贾”[12],读书为官仍为人生最佳归宿,徐敦弃商从儒,便是力证。陕西商人王来聘,更是了然于此,他曾数次训导子孙: “四民之业,惟士为尊;然而无成,不若农贾。”[14]卷一百六《乡祭酒王公墓表》,第154页从商是读书无成后的无奈选择,即使在商业发达的徽州地区,也有人如此。休宁人詹杰,令长子经商,次子读书,看似通脱,实则因长子非读书材料。当他得知次子喜好古文辞,而不攻时文时,便怒骂道: “若薄制科业不为,若能舍而自取通贵乎? 今国家方重科第,以笼豪杰殆尽,而吾詹独寥寥焉,使我愧称詹。且吾所以不弃若贾者,何意也?”[15]卷九十一《詹处士墓志铭》,第486页詹杰以詹姓登第者寥寥,深感惭愧。他寄予厚望的次子,偏又喜古文辞,怎不令其怒发冲冠! 他 “所以不弃若贾” ,是要以雄厚的财力作为子嗣博得高第的物质后盾。看来,由商入儒,走仕途经济之路,仍为许多商贾家梦寐以求。汪道昆虽言其乡 “左儒而右贾,喜厚利而薄名高” ,但其骨子里依然 “右儒而左贾” : “夫人毕事儒不效,则弛儒而张贾。既则身飨其利矣,及为子孙计,宁弛贾而张儒。一弛一张,迭相为用,不万钟则千驷,犹之转毂相巡,岂其单厚然乎哉,择术审矣。”[11]卷五十二《海阳处士金仲翁配戴氏合葬墓志铭》,第1099页“弛儒而张贾” ,非长久计,仅为 “毕事儒不效” “才不足于儒”[11]卷五十四《明故处士溪阳吴长公墓志铭》,第1142页之权宜,实属无奈之举。若要 “为子孙计” ,终究要 “弛贾而张儒” 。对多数儒生而言,最终目的是博得一第。然而,因科举录取名额有限,再加之时运等因素制约,即使有足够的才华与财力,成功概率也微乎其微。屡败屡试的归有光,体会剀切: “天下士岁试南宫者,无虑数千人,而得者十不能一。”[3]卷十九《曹子见墓志铭》,第467页蟾宫折桂,难于上青天。袁中道 “望五之年,得此一第”[16]卷二十五《与四弟五弟》,第1069页,已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相对来讲,从商致富的成功率要大得多: “士而成功也,十之一;商而成功也,十之九。”[17]《丰南志》第五册《百岁翁状》,第251页这是士人取其次而从之,出儒入商的重要动因。
正因 “士大于商贾” ,文人士大夫的身份及其所拥有的社会声望,颇为世人看重,一些心有所求的商贾,不惜花费巨资,主动与其结交,尤其是时贤、名流,更受青睐。歙县商人鲍简锡经商浙东,就 “结纳四方名流,缟纻往还,几无虚日”[17]《歙县新馆鲍氏著存堂宗谱》卷二《仲弟无傲行状》,第144页。黄明芳也 “好接斯文士,一时人望如沈石田、王太宰、唐子畏、文徵明、祝允明辈,皆纳交无间”[17]歙县《竦塘黄氏宗谱》卷五《双泉黄君行状》,第86页。黄氏交际圈中,不仅有文人名士,还有王鏊一类的高官、名流。商贾希望借此能进入主流文化圈,或提升自身影响与价值。即便不能如此,也可求得名人诗文、字画等,以附庸风雅。文人士大夫对商人的态度,也今非昔比,从上文王守仁、汪道昆、李维桢等言论,不难感受到。士大夫文人所以乐意与商贾交往,也多有个人利益考量。王世贞与徽商詹景凤的一番对话,颇耐人寻味:
凤洲公同詹东图在瓦官寺中,凤洲公偶云: “新安贾人见苏州文人,如蝇聚一膻” 。东图曰: “苏州文人见新安贾人,亦如蝇聚一膻。” 凤洲公笑而不答。[18]
士、商交往与互动,多基于双方互惠互利,这为詹景凤一语中的,王世贞只好 “笑而不答” ,料其也无以对答。在与商贾互动中,不少文人士大夫的人品、节操也随之势利化、世俗化,甚至堕落,沦为视金钱 “如蝇聚一膻” 之徒。文元发曾叹隆、万间士风道: “昔之士大夫,每持风节,不屑与非类交游;不似今之人,视铜臭之夫,如蝇之集膻也。”[19]商贾求名、士人逐利,成为士、商互动的基础与重要动因。钟惺《题潘景升募刻吴越杂志册子》即云:
富者余赀财,文人饶篇籍。取有余之赀财,拣篇籍之妙者而刻传之,其事甚快。非惟文人有利,而富者亦分名焉。[20]卷三十五,第649页
文人刻书资金短缺,商贾以余赀相助,著述者可流芳后世,出资者也可因之留名。一举两得,各得其所,何乐而不为? 士、商互惠互利,表现多端,此仅其一。
儒、商的互动,使这两个阶层的关系变得密切起来,造成了商而士、士而商,士商相混的现象,模糊了士商界限。这对晚明文学,影响深远。一方面,它促使包括郎署文人在内的文人士大夫的文学写作、文学观念,不断商业化、世俗化。另一方面,它还是 “性灵” 说的催生剂。同时,也使得一些郎署文人开始钟情通俗文学,自动参与到通俗文学的创作、刊刻、批评与传播中。这从内外两个层面,对郎署文学造成重大冲撞,致使郎署文学权力下降①文学权力的内涵,非常丰富、复杂,因行文所限,不展开论析。本文所谓文学权力,主要指文学话语权,故文中二者时而互用。文学话语权是掌控文学舆论、文学导向,以及文学影响的一种特殊权力。还可理解为行动者对有价值文化资本的大量占据与拥有,以及对文学场域中有利位置的占据。。
二、儒、商互动与上层社会适用文体的普泛化、世俗化
“如果说树碑立传的儒家文化向来是由士大夫阶层所独占的,那么16世纪以后的整个商人阶层也开始争取它了”[21]。这也是商贾乐于与文人、士大夫交往的一个重要动机。另一方面,在与商贾的交往过程中,郎署文人应请托,为商贾及其亲人撰写了不少寿文、碑铭志传、序跋之类的文章。现流传下来仅为其中的一小部分,大部分因藏于私家,未刊行于世,或已散佚。仅保存下来的,也颇能说明问题。远且不论,弘治、正德年间,李梦阳就曾与商贾作家有交往,并为之撰写了一些墓志碑传。如《空同先生集》中的《处士松山先生墓志铭》(卷第四十三)、《梅山先生墓志铭》(卷第四十三)、《鲍允亨传》(卷第五十七)、《明故王文显墓志铭》(卷第四十四),就分别为兰阳商人丘琥、徽商鲍弼、鲍允亨,以及蒲州商人王文显所作。《方山子集序》(卷第五十)、《潜虬山人记》(卷第四十七)、《缶音序》(卷第五十一),即为商贾文人郑作、佘育、佘存修诗文集而作。
嘉靖以还,此现象更为普遍,不仅商贾如此。唐顺之曾讽之曰: “仆居闲,偶想起宇宙间有一二事,人人见惯而绝是可笑者。其屠沽细人,有一碗饭吃,其死后则必有一篇墓志。”[22]卷六《答王遵岩》,第276页万历二十九年(1601),李乐所撰《见闻杂记》,进一步佐证了唐顺之之言论: “唐荆川先生集中诮世人之死,不问贵贱贤愚,虽椎埋屠狗之夫,凡力可为者,皆有墓文。此是实事。”[23]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张嘉孚亦言: “世人生但识几字,死即有一部遗文;生但余几钱,死即有一片志文。”[24]卷六《耻志文》这一方面是为附庸风雅,另一方面也是为墓主 “不可俾遂泯泯无传”[25]卷二十九《南京大理寺卿孟公墓志铭》,第247页。受此风淫染,王世贞、汪道昆、李维桢等,也为商贾及其亲人撰写了许多此类文章。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弇州山人续稿》中,为商人撰写的碑铭墓表志传行状,较之李梦阳等人,数量激增。陈建华先生统计,李梦阳《空同集》中有传记45篇,为商人所作4篇,约占总数的9%。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中,墓志铭(包括墓表、神道碑、墓志铭、墓碑、行状)总数有90 篇,为商人所作15篇,约占总数的16.6%。《弇州山人续稿》中墓志铭(种类同上)的总数250 篇,为商人所作44篇,约占总数的17.6%[26]。陈书录先生统计,《弇州山人四部稿》《弇州山人续稿》中,墓志铭(包括墓表、神道碑、墓志铭、墓碑、行状)总数340篇,为商人所作59篇,约占17%。另外,《弇州山人四部稿》《弇州山人续稿》中,还有多篇为商贾作的传记,传主多为徽州、苏州商人[27]。商人出身的汪道昆,为商人及其亲属所作碑铭志传之类的文章,数量更多。《太函集》中,有传记(包括传、行状、墓志铭、墓碑、神道碑)212篇,其中为商人及其家庭成员所作就有112篇(传主本人为商人者77篇;其余为商人家庭成员,如父母亲及妻子等),超过传记总数的50%。另外,还有为商人或其父母亲所撰33篇寿序或赠序,其中大部分都有关于商人生平事迹的记载与描述。无论在汪道昆以前,还是与他生活在同一时期的非徽州籍作家,恐怕没有谁为商人树碑立传如此之多[28]。此类文章多半是 “因贾人之请”[29]3,应其 “好名之心”[30]《煤客刘祥墓志铭》,第429页而作。而且,已有不少商人以正面形象进入了文学作品。如潘处士 “有心计,言利事,析秋毫。然如布帛之有幅焉,毋过取。又立义不侵”[14]卷八十七《处士潘君墓志铭》,第533页;樊傅 “积而能散,振人之厄,好义声闻四远”[14]卷九十六《樊季公冯孺人墓志铭》,第720页;金泮 “多知善谋,察时宜物情,应之屡中,又阔达有大度”[14]卷一百一十四《金仲子暨配孙孺人行状》,第320页。这类商人在 “三言” “二拍” 等小说中,比比皆是。郎署文人为商贾及其亲友大量撰写寿序、墓铭墓表志传行状,使得这些原本多用于上层社会的应用文体,开始走向商贾、市井细民,日渐普泛化、世俗化。
为他人撰写寿文、碑铭墓表志传行状,自唐宋来有收取润笔费的惯习,尽管时遭人诟病。在商业大潮冲击下,伴随着卖文治生行业的兴盛,中晚明文人、士大夫为人撰文,也随之商业化,收取润笔费或公开标价售文,愈发显得天经地义。
就连王世贞之类的高官,也难以免俗。邓俨之子邓仲子 “间而损书币以其姊夫左参议熊惟学之状” ,向王世贞 “请传” ,王欣然应允,为之撰《邓太史传》[15]卷七十三,第291页。这实是一种变相的售文现象,也是一种世俗的商业行为。卖文之收入,对某些人来说,还颇为可观。李梦阳晚年罢官家居, “以其据纷华之地,而多卖文之钱”[30]《李崆峒传》,第606页,生活相当滋润。差者也基本能维持生计,屠隆离职返乡后,主要靠 “卖文为活”[31]卷二百八十八《文苑四》,第7388页。有的名流卖文还明码标价,如张凤翼不屑于以诗文、字翰交接贵人。乃榜其门曰: “本宅缺少纸笔,凡有以扇求楷书满面者,银一钱;行书八句者,三分;特撰寿诗、寿文,每轴各若干。” 尽管如此,不妨碍 “人争求之,自庚辰至今,三十年不改”[32]。随着买方市场的扩大,还催生出卖文代办人或经纪人。如,李维桢 “其文章,弘肆有才气,海内诸求者无虚日,能屈曲以副其所望” ,其 “门下士招富人大贾,受取金钱,代为请乞,亦应之无倦”[31]卷二百八十八《文苑四》,第7386页。
对于求文者说,这是一种文化消费;对应求者而言,不失为一种治生手段,至少也可平添些许额外收入。求文者关注的是能否得到名人之文,供其讲排场,附庸风雅;而对作品质量,一般不甚关心。再说,他们也多缺乏相应的鉴赏能力。应求者于此,多心照不宣,撰文时往往不甚用心,甚至敷衍了事。归有光《陆思轩寿序》即云:
东吴之俗……独隆于为寿。人自五十以上,每旬而加。必于其诞之辰,召其乡里亲戚为盛会。又有寿之文,多至数十首,张之壁间。而来会者饮酒而已,亦少睇其壁间之文,故文不必其佳……故凡来求文为寿者,常不拒逆其意。[3]卷十三,第334-335页
求寿文者,只为寿宴上壁间生辉,赴宴者多 “饮酒而已” ,真正的欣赏者,凤毛麟角。鉴于这种情形,应求者以为 “文不必其佳” ,撰写时也不会花太多心思。因有币贽收入,故 “常不拒逆其意” 而 “应之无倦” ,无形中工作量剧增。撰者为图省心,加之文体特征所限,写作上多流于程式化①归有光《李氏荣寿诗序》: “余尝谓今之为寿者,盖不过谓其生于世几何年耳,又或往往概其生平而书之,又类于家状,其非古不足法也。” (明)归有光著,周本淳校点:《震川先生集》卷十二,第306页。,有人干脆事先为 “活套诗” ,以备随时应付:
受其费者,不问其人贤否,漫尔应之……有利其贽而厌其求者,为活套诗若干首,以备应付。及其印行,则彼此一律,此其最可笑者也。[33]卷十五,第189页
以上说的是严格意义上的 “活套诗” ,至于套用他人成句的写作现象,更屡见不鲜。王世贞有多首寿九十老翁诗作,起句就直接套用白居易 “九十不衰真地仙”[15]卷二十,第333-336页诗句。还有人乃至取先前旧作,易名应酬,忙中出错,贻人笑柄:
张士谦学士……或冗中为求者所逼,辄取旧作,易其名以应酬。有除郡守者,人求士谦文为赠。后数月,复有人求文送别驾,即以守文,稍易数言与之,忘其同州也。二人相见,各出其文,大发一笑。[34]卷四,第33页
有些应求者,特别是那些有名望者,因出于种种原因,不愿或不便亲力亲为,常请人捉刀代笔。徐渭即做过此事: “某自稍知操笔以来,当郡邑诸公于去来赠饯间,靡不来以管毫授者,曰:礼则然也。然礼然而心未必然者,固亦不能无矣,盖彼虽不言,而某固阴察其然也。”[35]卷十九《送山阴公序》,第563页连王世贞之类的名流,也有请人代笔之嫌。屠隆就曾向王世贞请为代笔之役,以贴补家用。就应求者言之,无论亲为还是请人代耕,多 “本无是情,而设情以为之”[35]卷十九《肖甫诗序》,第534页,容易导致 “其所为文者,与其人了不相蒙”[36]。如果再遇上文学素养不高的代笔者,代文质量,可想而知。
总的说来,此类文章 “多率意应酬,品格不能高也”[31]卷二百八十八《文苑四》,第7386页,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郎署文学的写作质量,削弱了其影响力,弱化了其文学权力。
三、儒、商互动与 “性灵说” 的催生及郎署文人对通俗文学的关注
在儒、商互动的过程中,出身于商贾的文士,其个体性格、行为方式、消费理念,不仅影响着郎署文人的写作风貌,甚至还制约着其文学观念的衍化,催生出新的文学观念,从内部自我削弱郎署文学权力。如李梦阳意识到诗歌抒情的重要性,强调 “感触突发,流动情思” ,追求 “歌之心畅,而闻之者动”[10]卷五十一《缶音序》,第1462页的审美效果,就与和徽商佘存修、佘育的交往、互动,甚为有关。王世贞晚年 “自悔” ,所标举的 “性灵” 说,也与商贾影响,有一定关联。苏州为明代商贸发达地区,生于斯长于斯的王世贞,难免会沾染些商贾习气;入仕后,他辗转各地为官,与商贾多有交往,从中获益良多。如,徽商程子虚曾拜谒他, “以文事相命,大出其槖装为贽” 。为刊刻李攀龙全集,王世贞还特请其出资相助: “足下如有意乎不朽于其间,为数卷助,何如?”[37]卷一百二十八《答程子虚书》,第138页他甚为欣赏那些商贾出身的文人特有的气质、性格,称道徽商诗人吴汝义 “好以吟咏自适”[37]卷六十九《吴汝义诗小引》,第157页,称赞苏州商贾张实 “读书猎大较,不好为章句,弃之。北走燕,遴其游闲公子,日驰章台傍,揳琴,揄袂,砧屣,陆愽,从耳目,畅心志,衡施舍。盖期年而橐中千金装行尽,乃归” ,并称 “雅已从吴门豪少年慕说隐君(张实)者” ,主动向其子张献翼 “征其事” ,以为之传[37]卷八十四《张隐君小传》,第321页。这与请托为文,无论在写作动机,还是为文心态上,皆不可同日而语。商贾文人的 “吟咏自适” “从耳目,畅心志” 的性格与作风,也濡染着王世贞,与其 “性灵说” ,有诸多契合之处。
前、后七子郎署官奉行 “文必先秦、两汉,诗必汉魏、盛唐” 策略所导致的拟古寡情,向来为世人诟病,王世贞晚年已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对此进行了反思。他重新评估其早期作品以及李东阳、苏轼之作,并以其推崇的李攀龙拟古乐府为突破口,斥责机械拟摹,谓之 “无一字一句不精美,然不堪与古乐府并看,看则似临摹帖耳”[38]卷七,第1066页,指责其摹拟痕迹过浓。在王氏看来, “剽窃模拟” 乃 “诗之大病”[38]卷四,第1018页,他批评 “后之人好剽写余似,以苟猎一时之好,思踳而格襍,无取于性情之真”[37]卷六十六《章给事诗集序》,第154页,提倡 “遇有操觚,一师心匠,气从意畅,神与境合”[38]卷一,第964页,认为 “未可以时代优劣也”[38]卷四,第1007页。为此,他援引 “性灵” 一词论诗,《艺苑卮言》有曰:
颜之推云 “文章之体,标举兴会,发引性灵,使人矜伐,故忽于持操,果于进取。今世文士,此患弥切。一事惬当,一句清巧,神厉九霄,志凌千载,自吟自赏,不觉更有傍人。加以砂砾所伤惨于矛戟,讽刺之祸速于风尘,深宜防虑,以保元吉。” 吾生平无进取念,少年时神厉志凌之病亦或有之。今老矣,追思往事,可为扪舌。[38]卷八,第1088页
在 “自悔” 少年为诗作文或染 “神厉志凌之病” 的同时,王世贞拈出 “性灵” 一词,别有深意。这一词,多次出现于其论诗中①如《湖西草堂诗集序》: “顾其大要在发乎兴,止乎事,触境而生,意尽而止。毋凿空,毋角险,以求胜人而刿损吾性灵。” (《弇州山人续稿》卷之四十六,《明别集丛刊》第3辑第36册,第616页)《邓太史传》引熊惟学之语,称传主邓俨: “喜为诗,谓其能发性灵,开志意,而不求工于色象雕绘。君子以为知言。” (《弇州山人续稿》卷之七十三,《明别集丛刊》第3辑第37册,第292页)《余德甫先生诗集序》称余曰德: “归田以后,于它念无所复之,益搜刿心腑,冥通于性灵,神诣独往之句,为于鳞所嘉赏。” (《弇州山人续稿》卷之五十二,《明别集丛刊》第3辑第37册,第58页)。王世贞 “性灵” 说的核心,是注重真性情的抒发,它开启了郎署文学向公安派 “性灵” 文学过渡之津梁。而恰恰是公安派以 “独抒性灵,不拘格套”[39]卷四,第187页为旨归,重创了后七子郎署文学: “中郎之论出,王、李之云雾一扫,天下之文人才士始知疏瀹心灵,搜剔慧性,以荡涤摹拟涂泽之病,其功伟矣”[40]丁集中《袁稽勋宏道》,第567页“其(袁宏道)诗文变板重为轻巧,变粉饰为本色,致天下耳目于一新,又复靡然而从之”[41]卷一百七十九《袁中郞集》,第1618页。可以说,王世贞先从内部自我消解了郎署文学权力,之后又遭公安派的猛烈掊击,郎署文学权力大为下降。
公安派兴起后,文人标举 “性灵” ,已成为时尚。郎署文人也难脱其寖染。崇祯十六年(1643)进士郑元勋,在晚明商业大潮的涤荡下,力主 “以文自娱” 说。陈继儒《文娱叙》有曰: “往丁卯前,珰网告密,余谓董思翁云:吾与公此时不愿为文昌,但愿为天聋地哑。庶几免于今之世矣。郑超宗(元勋)闻而笑曰:‘闭门谢客,但以文自娱,庸何伤?’”[42]卷首,第1页“以文自娱” ,同时还可 “悦人” ,郑元勋《文娱自序》云:
文以适情,未有情不至而文至者。侠客、忠臣、骚人、逸士,皆能快其臆而显摅之,故能谈欢笑并,语怨泣偕。彼有隐约含之不易见者,进则为圣为佛,退则一玩钝者之不及情而已。吾以为文不足供人爱玩,则六经之外俱可烧。六经者,桑麻菽粟之可衣可食也;文者奇葩,文翼之,怡人耳目,悦人性情也。[42]卷首,第1页
“文以适情” “怡人耳目,悦人性情” 之内涵,较 “以文自娱” ,稍显宽泛,显然与公安派性灵说有相通处。正如有的研究者所言: “就诗文批评本身而言,文娱说产生的基础是性灵说。创作上独抒性灵的自适态度,与鉴赏上以美为宗的文娱说是相辅相成的。”[43]这进一步从内部削弱了在公安、竟陵冲击下日渐式微的郎署文学影响力,使其文学权力不断下降。
不仅如此,儒、商互动还引起郎署文人对通俗文学的关注,使其自觉参与到通俗文学的创作、编刻、批评与传播之中。由于市民阶层的壮大,商业文化与时俗之浸染,借助于江南地区发达的刻书业,通俗文学迅速兴盛起来。叶盛称: “今书坊相传,射利之徒伪为小说杂书,南人喜谈如汉小王光武、蔡伯喈邕、杨六使文广,北人喜谈如继母大贤等事甚多。农工商贩,抄写绘画,家畜而人有之;妇,尤所酷好。”[44]卷二十一,第213-214页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包括郎署文人在内的不少士人,开始关注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样式,认识到其独特的审美价值。陆深、都穆、文徵明、沈周、祝允明等人, “好藏稗官小说” “其架上芸裹缃袭,几及万籖,而经史子集不与焉。经史子集譬诸粱肉,读者习为故常;而天厨禁脔、异方杂俎,咀之使人有旁出之味,则说部是也”[45]卷二《藏说小萃序》,第576页。戏曲方面, “今则自缙绅、青襟,以迨山人、墨客,染翰为新声者,不可胜纪”[46]卷四,第167页。
前后七子派郎署文人,也难脱此风羁绊。李梦阳、何景明、李攀龙等就关注过民歌、时调,康海、王世贞、汪道昆等,还亲自参与到戏曲、小说创作与刊刻、传播中。尤其是王世贞、汪道昆、屠隆等,更专注于此。
王世贞不仅创作了传奇《鸣凤记》,还有系统的戏曲理论,后独立成册,是为《曲藻》,表现出对通俗文学的高度关注。其中,关于南北曲的用词、各自的长短优劣、戏曲 “体贴人情,委曲必尽”[47]33等问题的阐发,颇有理论价值。汪道昆于嘉靖三十九年(1560)编成《大雅堂杂剧》四种,即《五湖游》《高唐梦》《洛水悲》《远山戏》,并刊刻于自家书坊—— “大雅堂”①刘尚恒:《安徽古代出版史述要》,《安徽出版资料选辑》第1辑,黄山书社1987 年版,第170页。刘学林:《试论徽州地区的古代刻书业》,《文献》1995 年第4 期,第202 页。。屠隆少年时就喜好戏曲,尝自言: “少颇解此技,尝思托以稍自见其洸洋,会夺于他冗。”[48]《栖真馆集》卷十一《章台柳玉合记叙》,第198页其流传下来的戏曲有《昙花记》《彩毫记》《修文记》三种,称为 “风仪阁传奇” 。犹如王世贞,屠隆不仅创作戏曲,还注重理论的归结。艺术上,他大力提倡 “雅俗并陈、意调双美” “虽尚大雅,并取通俗谐□,□□不用隐僻学问,艰深字眼”[48]第11册《昙花记·凡例》,第4页,以为 “传奇之妙,在雅俗并陈,意调双美、有声有色、有情有态。欢则艳骨,悲则销魂。扬则色飞,怖则神夺。极才致则赏激名流,通俗情则娱快妇竖。斯其至乎!” 创作主体上,他强调戏曲创作者应有才,最好是 “通才” “传奇一小技,不足以盖才士,而非才士不辨,非通才不妙”[48]《栖真馆集》卷十一《章台柳玉合记叙》,第198页。这是晚明时期的重要戏曲批评理论。
小说方面,汪道昆亲为《水浒传》作叙②明新安刻本《水浒全传》卷首《水浒传叙》末署曰: “万历己丑孟冬天都外臣撰。” (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王利器校注:《水浒全传校 注》附录,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3941页。)万历己丑,即万历十八年(1589); “天都外臣” ,指汪道昆。沈德符释之曰: “今新安所刻《水浒传》善本,即其(郭勋)家所传,前有汪太函序,托名天都外臣者。” (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五《勋戚》,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39页。,阐释其文学主张。该序文比较系统地探析了通俗小说构思的虚实、章法的繁简、艺术风格等问题,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如汪氏认为, “史又言淮南,不言山东。言三十六人,不言一百八人。此其虚实,不必深辨,要自可喜” , “纪载有章,烦简有则。发凡起例,不难易于。如良史善论绘,浓淡远近,点染尽工;又如百尺之绵,玄黄经纬,一线不纰。此可与雅士道,不可与俗士谈也”[49]3939。胡应麟也给予《水浒传》极高的评价,不仅称其 “拟《琵琶》,谓皆不事文饰,而曲尽人情耳” ,还高度评价了其人物塑造的个性鲜明、拿捏得体: “第此书中间用意,非仓卒可窥,世但知其形容曲尽而已。至其排比一百八人,分量重轻纤毫不爽,而中间抑扬映带、回护咏叹之工,真有超出语言之外者。”[50]卷四十一《庄岳委谭》下,第437页
郎署文人关注通俗文学,从事戏曲、小说的创作、刊刻与传播,不仅分散了其从事正统诗文写作的时间与精力,也降低了其作品所谓 “品位” 。因为,在正统文人(包括一些郎署文人)看来,小说、戏曲为不登大雅之堂的小道、末技,至多也不过有补于正史而已,其关注点多在于正人心、淳教化③(明)李贽:《焚书》卷三《忠义水浒传序》,第110页。(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二十九《九流绪论》下,第283页。。这也从郎署内部,削弱了其所拥有的文学权力。
结 语
作为一个特殊群体,晚明商贾游走于市井与文人士大夫之间,成为联系士大夫与市井的重要纽带。郎署文人与商贾互动,实际上也与市井产生了互动。再说,有些郎署文人本来就与市井有诸多接触。士人逐利、商贾求名,名利互补,是奢靡世风之下儒、商互动的基础与重要动力。儒、商互动,造成士商相混,模糊了士商间的界限,这一方面,促使郎署文人自觉不自觉地调整、改变着自家写作风貌,先前多适用于上流社会的一些应用文体,很大程度上因之而走向商贾、市井之家,逐渐世俗化,降低了其应有的文化 “品位” 。另一方面,它还是新的文学观念 “性灵” 说的催生剂;同时,又激发起一些郎署文人对通俗文学的兴趣,使其主动参与到通俗文学的创作、刊刻、批评与传播流程中。郎署文人与商贾的互动,从内外两个维度,对郎署文学造成了很大冲撞。在山林文学冲击下正在流失的郎署文学权力(已另撰文论之),又受创于商贾、市井文学,郎署文学权力因之大为下降。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标志着晚明文学开始由以传统诗文为主的雅文学,逐渐向以小说、戏曲为重心的通俗文学转型。可以说,儒、商互动与晚明郎署文学权力之关系,为我们观察晚明文学的发展演进,提供了一个相对别致的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