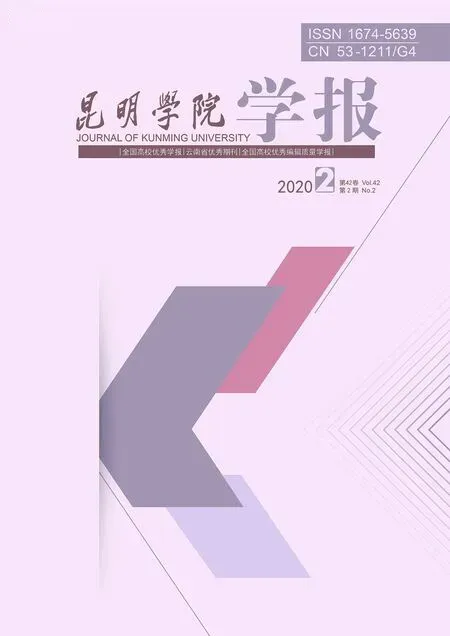从孙悟空的成长历程看《西游记》的成长小说属性
——斗战胜佛是怎样炼成的
2020-01-10范艳妮
范艳妮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北京 100022 )
一
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倡导者否定封建礼教、高呼人的解放,在对“人的发现”进行深入论述之后,更进一步提出了“妇女的发现”和“儿童的发现”。2019年,在五四运动一百周年之际,《儿童文学》杂志主编冯臻在名为《“发现儿童”:五四运动划时代价值的文化支点》的文章中指出:“儿童的发现”作为“人的发现深入展开的必然结果”,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成果性支点,也是儿童文学学科建立的前提,它以“儿童本位”论为支撑,将“儿童需要文学”作为儿童文学的出发点,开辟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儿童文学的新发端。[1]
彼时,随着中国儿童文学进入了觉醒阶段,围绕着“中国古代有儿童文学吗?”这个疑问,文学研究者们进行了探源研究。在这一过程中,《西游记》作为“儿童文学”被“发现”了。尽管《西游记》并非作家拥有自觉的儿童意识进行创作的产物,但各个时代、各个年龄段的儿童对它的青睐,足以证明它在客观上已堪称儿童读物中不容置疑的经典。它适应了孩子不受现实条件制约的思维特性,满足了其内心对最大限度自由的向往,更给了他们以大幻想、大娱乐和大快感。
林庚先生在其《西游记漫话》中这样说道:“《西游记》是一部童话性质的书,我是把它当作童话来读的。”[2]学者韦苇认为,尽管《西游记》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儿童文学,但它确实是“一个不争的伟岸的童话性存在”[3]。学者舒伟更以英国幻想文学作家托尔金的童话观来做参照,将《西游记》作为类似于《魔戒》那样的幻想性作品来重新分析,发现它不仅充分体现了童话之幻想、恢复、逃避、慰籍等因素,还充分体现了童话对人类最基本愿望的满足性,从而认为《西游记》无愧为“中国古典文学中独步先行之童话奇书”[4]。
与上述观点多将《西游记》归类为“童话性质”的作品相比,也有学者认为《西游记》是一部符合成长小说特征的作品[5],而笔者也更倾向于将《西游记》看成一本具有成长小说属性的作品。
所谓成长小说,“是一种展现未成年人在成长过程中,历经各种挫折、磨难,或迷茫依旧,或若有所悟,或得以顿悟的心路历程的文学样式”[6]。成长小说通常探讨人生经验中独立自我的发展,尤其重视什么是自我和如何建立自我这两个问题。成长小说的主人公通常注重追求个人价值,往往有其独特的生存方式和性格,因此容易与现实世界发生冲突,而成长小说主人公就在个人与社会的这种冲突中得到成长。从这个角度来看,孙悟空的成长历程正体现了《西游记》所具有的成长小说的属性。
《西游记》展现了孙悟空与天帝、与神佛从冲突到合作的“天路历程”,在这一历程中,孙悟空从逆天闯祸到自我救赎,从不服约束到遵守规定,从随心所欲到收心敛性,最终封神,位列天班,成为被主流接纳的个体,而这一看似皆大欢喜的结局,也暗含着成长所固有的悲剧性。
二
如果按照年龄段来划分,《西游记》通过描写孙悟空尽情游戏、享乐天真的童年时代,否定秩序、大闹天宫的少年时代以及西天取经、修成正果的成年时代,全面呈现了孙悟空这一主体的成长过程。
孙悟空孕育于一块仰承天地山川之灵气的石头。石猴本无父无母,生于自然,野性天真,率性而为,完全不受传统道德与社会规矩的拘囿。最初的时候,这个顽皮的小猴子还是个十足的孩子,他无忧无虑,只知道尽情游戏。他在花果山“与狼虫为伴,虎豹为群,獐鹿为友,猕猴为亲”,这些行为都正契合儿童喜好与自然相亲、热爱与动物相处的天性,也恰好说明游戏是儿童的主要生活方式。
伴随着游戏而生的,是儿童身上与生俱来的冒险精神,这一点,从孙悟空一头跳入水帘洞的那一刻就开始显现[7]。很快,他被众猴拥戴为尊,成为猴儿群里的“大王”,是称“美猴王”。他不仅勇敢,还具备“分派君臣佐使”的领导才能,更可贵的是他很有“合契同情”的团结精神。众猴恰似一群绝假纯真的孩子,他们毫无机心,他们对勇者的崇拜和尊重也表现得异常坦率,这是自然的由衷而发的本我性情。
“山中无甲子,寒尽不知年”,即使不曾刻意计算,快乐无忧的时光想必也总是易逝的吧。“一日,与群猴喜宴之间,忽然忧恼,堕下泪来”,从此,美猴王的童年时代结束了,他开始有了忧愁,有了对生命本身的思考与探索[8]。
孙悟空的少年时代开始于他对死亡的忧虑。他是生来自由的,受不得任何限制,就算是既定的命运,他也要斗一斗。因此,孙悟空离开了花果山,他要寻找一个人,一个可以教给他无上法力,教给他躲过轮回之苦的方法的人。少年必须切断童年的情绪依赖,才能成长为自立自强的成人,孙悟空离开花果山,犹如孩子离开母亲怀抱,而这一主动走出舒适圈的尝试,恰恰是人生成长的第一步。
此后,他搅东海借兵器,闯地府闹幽冥;他无视天宫戒律,不拜玉帝神仙;他大闹天宫,竟无一人是敌手……少年时期的主要特点就是渴望自由和张扬个性,此时的孙悟空否定一切的秩序,他对自己对环境都还了解得太少,因此缺少控制。他只依着本能的呼唤而行动,当他感觉到压迫或者需求时,就盲目地使用他的力量。人性自由的放纵、个性意识的高扬发展到极端时,他甚至企图把玉帝逐出凌霄宝殿,喊出“强者为尊该让我,英雄只此敢争先”的宣言。
孙悟空与包括神、佛、仙在内的整个代表着权威的等级体系之间的矛盾,可以看作是少年与成人社会、自然天性与文化秩序之间的冲突。
冲突之一发生在少年与成人社会之间。少年时期主要的成长任务是建立认同感,他们往往认为自己已完全可以与成人平起平坐,他们渴望被成人社会认同和尊重,但认同往往不易达成而且常会有冲突的产生。自尊自大自称王的孙悟空(少年),与道德规范森严的天庭(成人社会)构成强烈的对比,前者挑战后者的权威,后者也绝不认同前者的价值。两者的矛盾终于在蟠桃会上被激发,因为不在受邀之列,孙悟空那热切渴望获得认同的愿望落空,于是上演了一出惊心动魄的“大闹天宫”。这场冲突无疑是孙悟空谋求身份认同失败的恶果。
冲突之二发生在自然天性与文化秩序之间。其实,孙悟空的姓和名都各有深意。他的名“悟空”暗示着他将从天真的童年时代,叛逆的少年时代进入顿悟的成年时代。“孙”姓是“狲字去了兽旁”,表示离开兽性,离开自然之性,服从文明之则,这是进入社会的基本条件。此外,“孙”这个字契合“婴儿之本论”, 而正是婴儿般的赤子之心奠定了他的本性。然而这本性,使得他常常在释放天性与遵守秩序两者的冲突之间挣扎。
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一种具有强大规范力量的社会模式,这种模式为整个社会的思想体系和个体的行为准则设置了种种条规,而这些条规是建立在等级制和秩序观的基础上。在这样的社会模式里,离经叛道的个体,要么被毁灭,要么被修“正”。[9]因此,胆敢直言“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孙悟空,为了他的自由和狂妄付出的代价是:失去自由的五百年和整个花果山的覆灭。
少年的理想,往往如泡沫般绚丽又脆弱。纵使孙悟空本领再高强,也逃不出代表着最高秩序体系而扑面压来的五指山,纵使孙悟空心性再不羁,五百年的漫长囚禁也足以消磨他的骄傲,让他终于发现和承认自己的无力。看似没有尽头的日日夜夜,全身动弹不得的沉重负荷,仅限方寸之间的视野范围,让孙悟空冷静下来,“眼观鼻,鼻观心”,无声无息地开启了一种有别于过往行为的“智慧模式”:面对成人社会的要求,他开始妥协和迂回,也许他并不完全服气,但至少已不再莽撞地与天相争。因为他知道,他的敌人不是某一时刻的某一神仙,而是无尽岁月积累出来的全部秩序体系。
如果说大闹天宫隐喻着少年人野性生命力和自由心性的爆发和宣泄,那么,西天取经则隐喻着成年人为了特定的信仰和理想,而有意识地进行的心性修炼和意志磨砺。
成长并不一定意味着能力的强大,相反,取经路上的孙悟空屡屡被妖怪难住而不得不四处求助,这与他当年大闹天宫无敌手的威风形成鲜明对比。究其原因,大概是此时的孙悟空不似当年那么无拘无束了,紧箍圈约束的不仅仅是他的滥用武力,更是作为“心猿”那原本桀骜不驯的心性。
纵观全书,“心猿”这一宗教术语多次出现,成为孙悟空的专属别称。常言道“心猿不定,意马四驰”,因此“心猿意马”常用来比喻躁动的心灵。据说元代的虞集写过一篇《西游记序》,曾以“收放心而已”这一句话来概括《西游记》的主旨,孙悟空是被当做“人心的幻相”来刻画的。从这个角度说,成长对于孙悟空而言,是从“心何足”“意未宁”的“放心”阶段,经历“身压五行”的“定心”阶段,最终达到“心猿归正”的“修心”全过程。
戴上紧箍圈,踏上取经路,正是“心猿”走向“修心”之路。《西游记》一书中的“二心搅乱大乾坤,一体难修真寂灭”是颇具暗示性的一个章节,也就是真假猴王一节。两个孙悟空,长的一般模样,使的一般金箍棒,用的一般招式,念起紧箍咒来又是一般疼痛。那个让唐僧师徒分辨不得,令诸路神仙一筹莫展的六耳猕猴,最终被孙悟空“抡起铁棒,劈头一下打死,至今绝此一种”。有学者认为“二心”一指“本心”,二指“心猿”,假悟空不过是真悟空的“心猿”,是“皈依佛法、灵台澄明”的孙悟空与草莽中“顽劣异常、野性难驯”的孙悟空在交战,只有斩去“心猿”才能取得真经,修炼成佛。
可见,在不断扫除取经路上的外部障碍的同时,孙悟空也在努力“修心”,清扫来自自身心性的障碍。浮屠山上的乌巢禅师授给取经师徒的《心经》,可以看作《西游记》的精神扭结。对于《心经》,孙悟空的领悟甚至比唐僧更为透彻,他说:“只要你见性志诚,念念回首处,即是灵山”;“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只在汝心头。”就这样,完成了心性与意志的升华,孙悟空实现了如获新生的转变,这使他度过了狂风暴雨的少年时代,趋向不忧不惧、心神笃定的成熟状态。
三
当然,少年是否经历了成长,并不仅仅是收敛心性、着意“修心”这种飘渺的话语能够完全概括的,成长依然有着一些标识可供辨认。
首先,责任的承担暗示着社会对个人成长的肯定,同时也是人格社会化的过程,是“从自然状态的人向一个社会状态的人的转化与突变”。孙悟空走上取经的道路象征着少年的成长,保护唐僧取到真经就是他所必须负担的责任。塞林格在《麦田里的守望者》一书中这样说道:“一个不成熟男子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英勇地死去,一个成熟男子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卑贱地活着”,取经路上的孙悟空正在经历此种逐渐成熟的历练。原先尊性高傲、直来直往的齐天大圣,稍不顺心就举起金箍棒动用武力,如今也学会了顾全大局、稍作妥协。为了遵从师父的“好生之德”,孙悟空也收敛其暴怒好杀的一面,转而以智取胜。平日里只拜过佛祖、菩萨和师父的悟空,也会变成小妖去哄骗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的老母,他会一边哭一边劝慰自己这是为了救师父,然后“撞将进去,朝上跪下,放眼便哭”,从而成功骗取老妖信任。一个自尊而又能屈能伸的新的孙悟空形象鲜活起来,同时,“放眼便哭”这一细节又使他保留了原先孩子般的率真性情。
其次,人际关系的普遍改善也帮助孙悟空将自己与外在世界的冲突减至最低,同时也是他成长的一个标志。少年时代的孙悟空渴望获得认同,急切希望融入天庭,他“无事闲游,结交天上众星宿,不论高低,俱称朋友”。然而终于因为不通人情世故,更不了解天庭森严的等级秩序而处处碰壁。成长后的孙悟空,在人际交往方面变得成熟老练,这一点可以从他与龙王的前后关系变化看出来。之前,他跑到龙宫中强要兵器,气得龙王一直告到玉帝那里,两人的关系很恶劣。自踏上西天征途之后,孙悟空开始懂得卖弄人情,着意改善人际关系。孙悟空饶恕龙王敖顺的外甥黑河妖这一节就很精彩,他语言得体,软硬兼施,对龙王的管束不严之罪,只责以救回师父了事,这个恰当的顺水人情使他得到龙王的感激。在他遭遇红孩儿的三昧真火时,在他恶斗车迟国三魔时,龙王都赶来帮助他。类似这样,人际关系网的建立和拓展使得孙悟空在取经路上获得充分的支持和帮助,这也有助于他成功取得神佛所代表的成人集团的认同。
再次,从被领导者到领导者这一角色的转换,亦标志着孙悟空的成长和团队对他的肯定。取经之路刚开始,孙悟空野性未脱、做事直率,常被师父以紧箍咒约束。三打白骨精一节正是描写这对“父子”之间领导与反抗的矛盾激化。但即使被唐僧赶回花果山,遭受巨大的委屈和不公,他依然“身回水帘洞,心逐取经僧”,很快就不计前嫌,又随猪八戒回到了师傅身边。而孙悟空的这次去而复归,也让唐僧体会到了失而复得,并因此懂得了反思和珍惜。取经队伍成员之间,经历凡此种种罅隙与磨合,渐渐地,孙悟空占据了领导地位,每当遭遇事故,总是由这位在艰险之中成长起来的大师兄肩负起一切的责任。唐僧在黄风岭被妖怪用计擒拿,急得八戒泪流满面,悟空安慰他说:“莫哭!莫哭!一哭就挫了锐气。横竖想只此山,我们寻寻去来。”这番简单的话语,看似平淡,却颇能安顿人心。孙悟空临危不乱的镇定,是作为领导人不可或缺的要素。孙悟空不单在同伴中建立起领导者的形象,更是变成了师父心中的支柱。孙悟空曾这样劝解师父:“心无挂碍,方无恐怖”,“扫除心上垢,洗净耳边尘。不受苦中苦,难为人上人”。师父的惧怕由徒弟开导指引,这种关系的转变在小说中不断地被强调着。尽管他仍然以师父为依归,但更多的时候是师父仰仗这个大徒弟。
经历了以上三项巨大的转变,主人公可以说是经历了成长,但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成长的全部内涵。大多数成长小说的主人公是在与社会的矛盾冲突中成长的,他们逐渐完成社会化而成为社会的合作者。但是被社会规约完全同化,并不意味着主人公主体的生成。只有适应合理的社会规约而不放弃对不合理的社会规约的清醒认识和反抗意识,并坚持自我真性情者,才算是真正的主体的生成。
从这个角度来看,孙悟空的确是真正完成了成长主体的生成,一方面他不再妄想凭借武力为所欲为,而是接受取经任务,认同游戏法则和规约,承担起保护师父的责任,也肩负起自我成长的艰辛;另一方面,他仍然试图在等级秩序下适度地坚持自我,反对过度束缚,以保留一种强烈的个性精神。《西游记》成书后距今四百多年,以孙悟空为主角的各类文艺作品层出不穷,近年来火爆的国产动漫《大圣归来》就是中国人“悟空情结”的再现。孙悟空这个形象之所以具有历久弥新的魅力,在于他完全不同于中庸乏味、千人一面的众神仙,而是一个鲜活灵动的英雄,他那有如太阳光芒般无法掩饰的个性风采,至真至诚,尽管压抑了一些本性,但依然具有强烈的感染力,使得人们在漫长的时光中,不断地通过演绎孙悟空的故事来释放自己的个性诉求。
至此,孙悟空完成了个体成长,《西游记》也迎来了看似功德圆满的大团圆结局,但为何笔者却隐隐有一种难以言说的痛楚萦绕于心?
四
这种痛楚往往难以察觉,正是典型的中国古典悲剧中的那种“圆满背后的悲哀”,是“一种似无实深、似淡实烈的毁灭之痛”。就像被真悟空一棒打死的六耳猕猴,那何尝不是另一个“真悟空”呢?正如有的学者所认为的,那是孙悟空在自我的激烈冲突中,幻化出的另一个自己,所以真相何尝不是“只有悟空自己毁灭自己,才能完成由自然人变成社会人的过程”?那么后来的取经之路,谁能说得清,到底是哪个“真悟空”在艰难跋涉呢?修成正果的孙悟空看似得到很多,但谁又能否认,与“斗战胜佛”这个功名相比,在他身上那些已经永远失去了的青春、自由和野性,或许才更是他的“心之所向”呢?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倾向于将孙悟空归为一个悲剧英雄,确切地说,是中国古典悲剧中的悲剧英雄。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悲剧,故事过程无论怎样惨烈,都很少挖掘剧中人物作为“真实的活生生的个人”的内心挣扎,结尾却往往要大团圆,正义一方总要获胜,阅读效果势必要大快人心。20世纪初在美国倡导新人文主义学说的欧文·白璧德曾把这归因于中国悲剧缺乏伦理的真诚。直白一点,正如胡适所说:“这种‘团圆的迷信’……明知世上的事不是颠倒是非,便是生离死别……偏要说善恶分明,报应昭彰……这便是说谎的文学。”[10]
西方古典悲剧主人公往往在张扬个性的信念指导下,演绎一种“不自由,毋宁死”的悲壮人生。弥尔顿的《失乐园》可算是典型的例子:撒旦这个反叛上帝的英雄形象,为了坚持自由意志,宁愿从天使长堕落成为地狱恶魔,义无返顾地走向权威眼中的“自我毁灭”[11]。与此不同的是,中国古典悲剧的主人公通常牺牲自我来维护社会道德与秩序,比如窦娥捍卫贞操并以死尽孝,比如孙悟空,压抑野性天真,遍历取经磨难,终于将功赎罪,获取权威阶层颁发的功名。
撒旦和孙悟空的不同选择,无所谓对错,更不分境界高低。但是,就像我们会忍不住设想身在地狱的撒旦,日后究竟有没有一时一刻后悔过?我们也会去想,在以后无尽的优游岁月中,孙悟空是否会无声想念花果山的一帘洞天,是否会暗自回味大闹天宫时的快意酣畅?斗战胜佛所拥有的无上荣光,是否能抵得上野性天真时那有如烟花绽放、刹那然而灿烂的青春光芒?[12]
“圆满背后的悲哀”──正是这种暗藏在《西游记》精神内核中的悲剧底色深化了其作为成长小说的属性,因为,成长本就是一场交织着舍与得的旅程,而直面成长所要付出的代价,不回避,不粉饰也是一部合格的成长小说所不能或缺的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