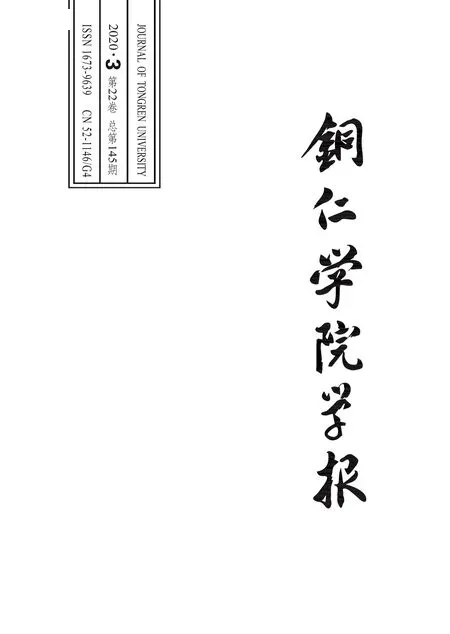改土归流后武陵民族地区人口流动社会问题治理的成效与启示
2020-01-10莫代山王希辉
莫代山,王希辉
改土归流后武陵民族地区人口流动社会问题治理的成效与启示
莫代山,王希辉
(长江师范学院 民族研究院,重庆 涪陵 408100)
改土归流后,通过发展生产力、统一文化精神、乡民自治、地域认同建构等方式进行人口流动社会问题治理。通过治理,基本实现了政治社会等层面的国家一体化,儒家精神成为统一的文化标准、群众国家认同度增强,经济、文化发展拉近了与外界差距,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态势显现,社会动荡减少。与此同时,也存在着人口盲目流动与地区资源匹配度不高、外来移民对少数民族生存空间挤压、文化歧视等问题。在人口流动社会问题治理中,发展经济是根本途径,强化传统文化规范是重要策略,加强对地方精英的引导是重要抓手,共同的文化精神建构在人口融入中起根本性作用,在移民人口融入过程中要对少数民族利益给予适当保护。
改土归流; 人口流动; 社会治理; 武陵民族地区
康熙四十二年(1703),清廷“开辟”苗疆,开启了清代武陵地区改土归流的大幕。经历雍正朝大规模改流后,至乾隆朝早期,武陵地区的土司制度基本终结。改土归流的实施,实现了中央王朝对地区的直接统治,随着土司特权被废除,人口流动的障碍被打破,外界人口大规模流入改流区。人口大规模流入不仅改变了该地区的人口结构、文化结构、经济结构,也带来了人地矛盾、贫困化、文化冲突、犯罪活动增加等系列社会问题。湘西苗疆“乾嘉苗民起义”和土家族地区“白莲教大起义”事件就是这些社会问题长期积累的集中表现。事件平息后,各地调整治理策略,通过提高生产力水平、构建以儒家文化为内核的区域多元文化、培育地方自治组织、推动民族交融等手段,取得了与前期截然不同的治理效果。相关治理经验、教训的总结,对当今民族地区流动人口管理,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一、人口流动社会问题治理
随着人口大规模流入改流区,改流区人地矛盾逐渐凸显,贫困化问题随之而生,在利益推动下,多元文化之间的冲突和碰撞表现得比较明显,这一切都影响着区域社会的稳定。各地通过经济、文化、政治多方面途径予以化解。
(一)提升生产力,增容地区人口承载率
人口大规模流入引起的人地矛盾、资源竞争、生态问题是改流区出现的最直接、最明显的社会问题。在人口流入和自然繁衍两方面作用下,改流后地区人口增长速度是极为惊人的,从宣恩县、永顺县、石砫厅、恩施县、松桃厅等地数据来看,约到乾隆中后期大规模人口流入停止时,各地有记载的人口数较改流初都有3至9倍的增长。要供养不断增加的人口,必然要求更多的物质产品,在交通条件没有根本改善的情况下,地区通过增加耕垦土地面积、提高单位面积出产率和大力发展劳动容量大的其他产业三种途径进行调控。改流后地区大规模的人口流入与垦殖活动是同步的,为了鼓励外来人口垦殖,各地官府在地权、税赋、入籍、农业生产工具补贴等方面出台了系列政策,取得了积极效果。据龚胜全研究,到嘉庆25年(1820)时施南府耕地面积255870顷、凤凰厅耕地面积26055顷、乾州厅耕地面积15855顷、永顺府耕地面积206430顷,较改流前均有数倍增长[1]。可耕垦土地面积的增加为更多人口的生存提供了必须的物质条件。在提升土地生产率上,一方面大力推广牛耕、蓄肥、水耕、精耕等先进生产技术,一方面推广玉米、红薯、洋芋等高产粮食品种,还积极推动油桐、茶叶、药材等经济林木种植。土地生产率的提升意味着单位面积物产资源的增加,对于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贫困人口和移民来说意义重大。在其他产业发展中,商业贸易、手工业等在各地蓬勃兴起,而这些产业都具有劳动力容量大、带动力强的特点,除了能直接提供大量就业机会外,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能为广大民众在农耕之余提供增加收入的途径。在经济发展、生产力水平提升过程中,人地矛盾得以缓解,与之相对应的贫困化问题也得以缓解,这为社会稳定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经济基础。
(二)以儒家文化精神建构区域多元社会文化
多元文化并存引起的各种文化歧视、文化失范、文化冲突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不稳定是改流区重要的社会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地方政府通过引导建构以儒家文化精神为内核的“一体多元”文化体系进行治理,取得了积极的效果。一方面,通过发展儒学教育体系,培养了一大批文化精英。改流区历任流官无不把修建学校、发展教育作为施政的首要任务,通过捐资助学、劝捐、引导等方式,各地均建构起了由学宫、书院、义学、私塾构成的多元教育体系。这些受过儒学教育的文化精英在社会中成为践行儒家精神、示范儒家道德、引领社会风习的文化先锋。另一方面,通过树立符合儒家规范楷模,模塑文化价值。在学校教育之外,各地利用石刻、牌坊、志书、口头传颂等方式,把那些符合儒家行为规范的人树立为楷模,通过赋予荣誉称号、封荫授职等途径扩大其影响力。再一方面,通过树立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化标识时时进行引导。各地在改流后第一时间就开始了儒家文化象征建筑的修建,圣庙、崇圣祠、名宦祠、乡贤祠、忠义祠、节孝祠、武庙、文庙、昭忠祠是修建的重点。每年,地方官府都要组织大规模的祭祀,并将所需经费纳入地方财政支出。这些由官方推动、数量庞大、参与广泛的蕴含儒家伦理价值观、道德观的建筑及祭祀活动长期存在,对群众思想和行为潜移默化,其作用是不言而喻的。经过长期儒化,到清中期时,儒家伦理道德在地区各族群众中已经根深蒂固,与内地并无多大差异。官府大力推动儒家文化的传播,但并不意味着要求群众在具体文化内容方面整齐划一。在“修教齐政,不易其俗”原则指导下,对差异性文化,只要不与儒家精神相违背,官方不予干涉其具体形式,对那些与儒家精神有悖但能主动调适重构者亦能容其流存发展,某些含有积极成分,有利于维护秩序的少数民族文化,在改造后甚至被官方纳入正统。在此情况下,区域文化生产生活习惯、宗教信仰、民族节日、文化艺术等方面多元特征得以保留。通过这种方式,既实现了文化价值观的统一,又实现了多元文化形式的并存,最大限度地实现了文化和谐。
(三)以乡民自治主导乡村社会运转
在移民社会,由竞争、贫困和文化冲突等引起的群体冲突、犯罪等问题是社会问题的重要内容,在这一问题治理中,官府通过将政府权力下沉,利用地方社会文化精英自治,体现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一方面,推动保甲组织建设。保甲是以维护社会稳定为主要使命的乡村社会组织,为了追求良好的社会治安和社会秩序,雍正皇帝在全国推行保甲制度,学者常建华甚至认为清廷是在推行保甲制度的过程中推行了大规模改土归流[2]。改流过程中,各地都在第一时间建立了保甲组织,在具体运转中,保甲组织承担了执行政命、维护治安、清查户口、征收赋税、教导乡民、举办公益事业、组织农业生产等一系列任务。另一方面,推动宗族组织建构。通过将稽查治安、禁革风俗、推行行政任务布置给族长的方式,倒逼有一定社会基础的姓氏建构宗族。加之土司家族、早期移民家族等强宗大姓的示范,乾隆时期开始,地区的宗族组织飞快成长,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族谱、祠堂等代表性文化的增多。宗族组织通过制定族礼、族约、族法、族规、族训、族禁等形成一套规范体系,这些规范体系实际上是儒家精神和封建道德规范的具体体现,其根本目的是为了灌输封建伦理道德、执行封建法纪、维护社会稳定。再一方面,培育乡村士绅阶层。从产生渠道来看,地区士绅阶层由以下几方面构成,一是接受过儒学教育的落第士子或及第未仕的生员,二是因祖先功勋而恩荫的权贵门第,三是因为贸易或耕种致富而发展出的乡村地主,四是掌握强宗大姓权力的宗族元老。经过刻意培养的士绅阶层迅速替代土司时期的社会精英,成为乡村社会的主导力量,他们或担任具有半官方性质的乡约、保长、甲长、牌头等职务直接管理乡村社会,或以社会贤达等身份实际插手乡村社会事务,或以族长、族正掌控宗族内部事务,在地方经济发展、社区建设、风俗引导、秩序维护、伦理道德、社会治安等层面起着主导作用。又一方面,推动以团练为主体的乡村武装力量建设。团练是在保甲基础上抽选丁壮进行武装化后实施社区自卫的武装组织,乾隆末、嘉庆初地区相继爆发的“乾嘉苗民起义”“白莲教大起义”为各地官府和士绅组建团练提供了契机,其后的太平天国运动直接助推了团练组织的大发展。团练兴起后,迅速为那些“公正缙绅耆老”“公正殷实士绅”“城乡公正绅士”所掌控,在流动人口管理、防御外来侵害、社会治安管理中发挥着积极作用。保甲、宗族、士绅、团练是地方社会治理的实际执行者,他们将国家意志与地方实际结合起来,是确保地方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文化融合不可或缺的主导力量。
(四)以“日常生活”建构地域新认同
不同来源地的移民进入同一地区,出现的基于文化传统、来源地、身份等而形成的认同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在外来移民融入地区社会过程中,官方在编甲、户口统计、税赋征收、社会治安、案件处理过程中逐渐淡化以民族、来源地、居住历史为标准的身份区分,当生活在同一地域的所有群体认识到身份区分并不能带来任何好处和利益时,推动区分的力量就会随之减小。同时,官府将地方治理权力下放到基层社会,而不同来源背景的群众生活于共同的区域,地方公共事务涉及到每一个群体的实际利益,在基础设施建设、生产生活实施建设、社会治安、抵御外来威胁、环境保护等的建设和运转中,需要相互合作和协调;在“同姓不婚”原则下不同群体需要缔结婚姻;不同资源禀赋的群体在经济活动中需要相互参与和取长补短;也都需要学习以丰富自身的娱乐生活内容。这些机制长期存在,推动着不同群体交往、交流、交融,逐渐在共同利益基础上形成具有地域特点的新认同。
二、人口流动社会问题治理成效与不足
通过官方与民间两方面综合治理,武陵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但也存在着一些不足。
(一)治理效果
改土归流后武陵民族地区发展历史表明,其后期人口流动社会问题治理是比较成功的,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政治、社会等层面基本实现与国家的一体化康熙年间“开辟”苗疆的根本目的是为消除“化外”,而雍正年间的“改土归流”也是为了使“数千里土民”“各遵王化”[3]。虽然在“开辟”过程中有流血和斗争,改流也并不是一帆风顺,而且“乾嘉苗民起义”后清廷在苗疆采取了以“隔离”为特征的“屯政”政策,但不可否认的是,清中央王朝的权力触角已经深入武陵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改流前那种“自相统属”“世有其土”“分占割据”的情况已经消失无存。具体来说,各地均设置了经制州县,官员均由王朝任命并统一管理,军队由王朝派驻并听命于国家派遣,教育体系遵循王朝规范并统一参与王朝人才选拔,税赋由官方征收并统一调配使用,律法由王朝制定并一体推行,经济贸易与外界联通并成为统一体系,各项重要政策也均与王朝同步实施。虽然在具体政策上在税收、入学、科举、基层官员设置和任命等方面对少数民族有所照拂,但也只属于大的统一体制下具体措施的变通而已,并不影响其与国家的一体化进程。人口大规模流入带来了资源争夺、文化冲突、身份认同等一系列问题,甚至分别在苗民聚居区和土民聚居区引发了大的社会动荡,但清王朝也得以以此为契机,不断收拢地方权力,进一步加深了对地区的实际控制。在政权、军队、人事、财赋、教育、律法、政策均与国家一体的情况下,武陵民族地区的国家一体化逐步完成。
2.儒家文化精神成为统一的文化标准,各民族国家认同感增强
文化的价值观影响文化主体的行为,而文化价值观的形成与文化主体的历史经验、文化传统、生存环境等均有密切的关系。改流时武陵民族地区多民族共存、大规模人口流入后“五方杂处”的社会状貌决定了地区不仅文化种类异彩纷呈,在文化价值观方面更是千姿百态,由此引发的冲突可谓层出不穷。自苗疆“开辟”和改土归流开始,尊儒家思想为正统的中央王朝和各地流官就不遗余力地推动儒家文化的传播以及本地化进程。在代表更高水平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的带动下,经过官方不断地引导、劝谕、宣讲、禁革、渗透,以及制度层面的学校、科举、模塑、人才选用的综合作用,经过长期磨合与选择,儒家文化精神成为地区各民族群众普遍遵守的文化标准。体现在文化内容上,与儒家精神相悖的内容逐渐消失,符合儒家价值标准的人物和事件为社会所推崇,各民族有特色的传统文化内容在调适的情况下也得以留存,由此形成了地区文化“一体多元”的状貌。“客土杂居处,习尚不一,然无巨奸大滑,畏上奉公,犹为易治。政教成于上,风俗清于下,《毛志》称归流之始,民习多陋,所载文告若干条,殷勤告诫,与民更始。今则彬彬焉与中土无异,于以庆吾民涵濡圣化”[4],“生童观感兴起,颇知刻劢,渐能文循法派,辞选华展。即各寨苗生童,亦知循名责实,矢志编摩。感化之心,蒸蒸日上”[5]的描述分别将土民、苗民聚居区的文化状貌概括得颇为贴切。文化价值观认同是文化认同的核心,而文化认同则是民族凝聚力和国家向心力的源泉之一[6]。改流后地区各民族对儒家文化精神的认同和融入强化了他们国家认同的心理依据和思想基础,在相应的归属感、政治制度权力忠诚、国家政策制度的服从与接受、国家利益维护等方面表现出积极主动性。在道光年间反新疆分裂战争、鸦片战争和同治、光绪年间反洋教、反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历次战争中,都有土民、苗民将领和士兵的身影,他们用鲜血谱写了保家卫国、维护祖国统一的光辉篇章。
3.经济、文化发展迅速,缩小了与外界的差距
改流前中央王朝之所以在武陵民族地区实施特殊的统治政策,与地区在经济和文化方面存在的特殊性有很大关系。作为一种制度变革,改土归流为地区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契机,特别是随人口流入而带来的先进生产技术、生产工具、生产理念、市场信息、贸易资本、生活理念、生活方式、文化传统等的传播,迅速提升了地区生产力水平,带动了农业、手工业、商业、服务业的兴起与发展。在此基础上,集镇、学校、道路、桥梁、寺庙等方有发展之基,而社会保障、文化教育、风俗教化、道德熏陶方有动力之源,从而形成良性循环。当然,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与内地相比,武陵民族地区无论在文教水平、城市发展水平还是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而这种差距也直接影响着后世地区的社会发展。但与改流前相比,这种差距已经大大缩小。因此,可以说,正是因为较好地处理了外来人口给地区所带来的利弊之间的关系,地区社会、文化和经济才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4.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态势明显
改流前,由于民族之间相对隔绝,土、苗民之间文化差异十分明显,且在中央王朝“以夷制夷”策略下,民族冲突时有发生。改流后内地人口流入之初,基于出发地的地域认同、文化认同、身份认同更是繁杂多样,“语言风俗、各服其贯”的情况普遍存在。随着生产力发展、儒家文化精神的传播、贸易繁荣,特别是日常生活中接触和互动越来越多,在官方主导下,不利于社会交往的因素逐渐减少,阻碍民族交融的狭隘意识淡化,各民族、各区域文化变迁速度加快、相互学习的情况日益增多,从而形成了交往、交流与交融良性发展的态势。到清末时,生活在现土家族地区的群众,已经初步形成了以各自区域为区分的文化体系,酉水流域摆手舞、茅古斯、西兰卡普、八部大神崇拜、哭嫁,清江流域向王崇拜、白虎崇拜、撒叶儿嗬,乌江流域傩戏、飞山信仰,澧水流域过赶年、大二三神崇拜等均已超越族姓成为区域性特色文化。苗族聚居区苗汉经济、文化、婚姻交流也得到迅速发展,苗汉通婚已日趋普遍,汉族生产、生活方式被苗民普遍采用,汉族节日普遍为苗民所接受,区域经贸也早已纳入更大的市场经济体系之中。在此情况下,同一生活区域的土、苗、汉之间文化边界越来越模糊,区分意识也越来越弱,民族“互化”现象明显增多。董珞对湘西大陂流、小陂流土家族苗化和土家族苗化[7]的研究,以及李然对保靖县丰宏村、棉花旗村、古丈县双溪沿岸村寨苗族土家化和土家族苗化现象的调查和研究[8]都表明,长期文化互动和通婚对于推动民族融合的作用巨大。
5.社会动荡减少,总体保持了社会稳定
在“开辟”以前,由于巨大的文化差异和持续不断的利益争夺,中央王朝对苗民的“征服”、苗民对中央王朝的抗争以及苗民对周边其他群众的劫掠从来没有停止过。乾隆《凤凰厅志》、严如煜《苗防备览》、但湘良《湖南苗防屯政考》、伍新福《中国苗族通史》中所列自秦汉到改流前湘西苗民大的抗争事件就不下二百次,特别是明代以后更是“叛服不常,伙瑶接獠,属为边患”[9]。正是在“反抗——镇压——压缩”的循环中,苗民的生存空间不断缩小,也才有了对苗民“以抢夺劫杀视若泛常”“顽狠好斗”[10]等不公正的评价。土司对中央王朝也是“叛服靡常”,特别是王朝对土司控制力减弱时期,周边地区的群众遭受着沉重的苦难。土司之间相互攻杀劫掠引发的社会动荡也一直是中央王朝头疼的事情。改土归流人口大规模流入后,虽然在短期内出现了人地矛盾、文化冲突、贫困问题、生态破坏负面影响,甚至在湘西和鄂西南分别引发了一次大的社会动荡,但从长远来看,人口流入所带来的生产力水平提高、人口结构改变、儒家文化精神的吸纳以及对国家认同度的提高都有利于减少社会动荡。据统计,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开辟苗疆以后至乾隆六十年(1795),有记载的苗民“动乱”仅有“勾补苗寨”事件1次,“乾嘉苗民起义”后至清末,有记载的“抗粮”“教匪”“滋事”等事件4次,且规模与前朝已不可同日而语。在湘西土家族地区,“改土归流之后百余年间,经济发展呈持续上升之势,这段时间里没有出现过大规模的反抗斗争,只是一些零星反抗”[11]。鄂西南土家族地区自“白莲教大起义”后,再也没有发生过大的社会动荡,在咸丰年间太平天国军过境事件中,新建构起来的团练武装等还给予了其一定打击。这充分说明改土归流是适应社会发展的历史大趋势,是有利于社会稳定的。
(二)治理不足
虽然在整体上治理效果比较明显,但并不意味着人口问题治理是十全十美的,受民族、阶层、文化偏见等方面影响,也出现了一些值得后世思考的问题。
1.人口盲目流动与地区资源匹配
在环境、资源、市场、技术、职业差异等因素的推拉作用下,人口流动往往具有盲目性。一定生产力水平下,当流动人口数量与流入地所能提供的资源相匹配时,就会推动流入地的社会经济发展,但当人口数量超过资源承载量时则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苗疆“开辟”以及改土归流后武陵民族地区一系列社会问题的根源就在于人口增长速度超过了环境、资源所能提供的承载量,当人口数量超过资源供应能力时,势必发生资源争夺,资源争夺又容易导致族群区分与歧视,而竞争失败者往往沦为被剥削阶层,由此引发贫困问题和犯罪问题,进而引起社会动荡。湘西“乾嘉苗民起义”就是在汉民不断侵蚀苗民土地和财富、苗民生存空间被急剧挤压的情况下爆发的,而鄂西南“白莲教大起义”也没有脱离外来移民过多并迅速贫困化这一历史原因。为了控制人口盲目流动带来的恶果,中央王朝也曾经发布过政令,但在清代信息条件和社会控制力较弱的条件下,人口盲目流动是一个几乎无法克服的社会现象,最终起作用的还是社会和资源的自我调控。对于我们当代人口流出地和流入地管理者来说,无疑具有警示意义。
2.外来移民对少数民族群众生存空间的挤压
当代表先进生产力水平,在技术、资本、市场、信息等占有优势的移民人口进入少数民族地区的时候,在相互交往、交流过程中,移民人口往往会对少数民族群众的资源、市场、文化等方面带来巨大冲击。如果任由其无序发展,少数民族群众往往会成为竞争的失败者,进而造成贫困问题,引发社会动荡。总体上来讲,中央王朝和地方官府在治理人口流动问题时,都存在着有意或无意忽略了体现为民族、文化、生产力水平等方面的差异性,从而引发了系列社会问题。改土归流以后土民生活区总体上发展迅速,但是在城乡、中心区与边缘区、平原地区与高山地区无论是在经济还是文化方面均存在巨大差异,而这种差异背后往往隐藏着社会争夺和资源分配的问题。从某种层面来讲,苗疆“屯政”就是汉民对苗民生存空间挤压从而导致社会动荡情况下中央王朝被迫采取的一种调控策略,虽然其阻碍了民族进一步交流,但也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保护苗民免受汉民挤压的作用。这无疑具有一定的警示和启示意义。
3.文化歧视
文化多样性是社会赖以发展的根源之一。文化多样性根源于文化差异性,而差异性又来源于文化存在的自然生态、社会环境和文化主体的历史遭遇。当遭遇差异性文化时,在利益的推动下,往往引发文化歧视、文化冲突。改流后多元文化汇聚于武陵民族地区,汉文化背景官员、群众对苗土文化的认识不够准确,在制度、政策、行为等方面存在着严重的歧视现象,基于文化歧视而发生的民族压迫、民族剥削和民族斗争现象层出不穷,而这些现象又直接影响到了地区的社会稳定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在处理文化差异过程中,中央王朝和地方官府往往简单地以禁、革、压为手段,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都造成了严重影响,这方面无疑也是值得反思的。
三、对民族地区流动人口管理的启示
人口流动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永恒现象,通过对武陵民族地区改土归流后人口流动与社会问题治理研究,可以为当下民族地区人口流动治理提供如下启示。
(一)发展经济是解决人口流动社会问题的根本途径
人口流动系列社会问题的产生是相互联系、环环相扣的,但根源还在于“资源”和“利益”上。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抓住“发展经济”这一关键点。在相对固定区间范围内,只有不断发展经济,提升生产力水平,经济资源总量才会得到增长,才能满足不断增长的人口数量以及群众的生产生活需求。相对应的,只有生产力水平提升,群众生活水平提高,地方财力增长,社会建设和社会事务才有经济保障,社会才会有持续发展的动力。武陵民族地区的实践也证实了这一观点:改流初制度变革带来经济红利时,地区承载的流动人口数量急剧增长;到乾隆后期经济提升遭遇瓶颈时,人口流动积累的社会问题集中爆发,并发生了严重的社会动荡;而后经济持续缓慢发展时,人口流入也日趋消退,社会问题持续消减。因此,当下民族地区在制定人口政策、处理人口流动社会问题时,一定要将发展经济作为第一要务,唯有如此,方能从根本上解决相关问题。
(二)强化传统文化规范是解决人口流动社会问题的重要策略
地方传统文化根植于群众的生产生活、历史传统、心理素质,与地方群众更贴近,更有弹性,也更能为群众所接受。传统文化规范在调节文化主体的行为、人与资源关系、社会关系等方面具有的能动性是国家律法的重要补充。人口流动社会问题是社会总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具有波及范围广、破坏性强和影响力大的特点,在解决相关问题的时候,必然要考虑到不同地区文化传统、历史进程和现实特点。如前所述,在武陵民族地区建构新的社会秩序过程中,各民族群众传统的风俗、习惯法、禁忌、社会组织、宗教信仰等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生态平衡维护中,宗族、信仰、习俗、禁忌也都必不可缺。因此,在当下解决人口流动社会问题时,一定要深入挖掘流入人口和流入地原住民的文化传统,找出其中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维持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促进民族和谐交往交流的思想、做法和规范,并将其与国家政策法规结合起来进行社会治理。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满足群众的需求,解决实际社会问题。
(三)培养地方人才,加强对地方精英的引导是解决人口流动社会问题的重要抓手
社会治理涉及方方面面,需要有足够才能、为群众广泛认可、能够理解和执行国家大政方针、服从国家管理、且有为地区服务意愿的人。凭借掌握的文化资源、地方传统知识、雄厚的经济资源或者社会品行而成长起来的地方精英满足这样的品质要求。由于享有较高的社会影响力、对地方风土人情了解较深、对生长的社区存在较深的感情,自古以来,地方精英都是区域社会治理的重要借助力量。在改流后武陵民族地区乡村社会治理中,不断成长起来的士绅、族老、乡贤、保甲、贤达等阶层实际担负着传播儒家文化精神、引导社会文化变迁、维持社会秩序、贯彻国家政策等一系列基层社会治理所需要的具体职责,起到了连接乡村与国家的积极作用。在当下民族地区人口流动治理中,一定要注意对那些知识技能水平、社会认可度、思想品德等方面水平普遍较高的人才的引导与培养:不仅要培养他们的管理能力,还要培养他们的责任担当和国家情怀;不仅要培养少数民族精英人物,而且要培养流动人口中的精英人才。只有紧紧抓住精英人物,社会治理才能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四)在流动人口融入地方过程中,共同的文化精神建构起着根本性作用
流动人口融入地方有自己的规律,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组织管理方式到文化习惯再到精神认同是一个逐步递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多元文化并存,交流、学习、激荡、冲突是必然的事情,文化失范和文化整合是社会治理必须直面的困境。要解决这一问题,只能由官方引导在多元文化基础上建构共同的文化精神,只有文化精神一致了,文化价值判断才会弥合,文化冲突才会消减。同时,人口融入最终标准是文化认同和地域认同,而这两种认同得以形成也必须以共同的文化精神为基础。改流后武陵民族地区治理过程中,官方不遗余力地采取各种手段和途径宣扬儒家文化精神,使之与不同文化相融合,正是弥合地域、民族文化差异、推行国家制度、维系社会秩序的精神纽带。在当下民族地区人口流动治理中,一定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体来讲,就是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统领各民族的道德观念、日常行为、社会规范、文化传统。在这一过程中,可充分利用学校教育体系、宣传舆论体系和文化习惯,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对符合这一价值观的行为、人员、事迹的宣扬,做到引领社会思想的作用。只有统一的文化精神确立了,各民族才会形成统一的规范,也才有新的认同方向,才可能形成地域认同并上升为国家认同。
(五)外来人口融入民族地区过程中,要对少数民族利益给予适当保护
受历史传统的影响,少数民族在生产方式、文化习惯、教育思想观念等方面往往有自己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既是少数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依据,也是少数民族引以自豪的资源宝库,更是国家多元文化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同时,在某些阶段,与其他民族相比,少数民族文化中的某些成分也有不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因素。加之自然地理条件的限制,少数民族生产力水平往往不高,教育科技水平与外界存在一定的差距,在与外界先进生产力水平、经济模式的竞争过程中,往往处于不利地位。相对应的,在社会资源、政治资源、教育资源、社会保障资源等的分配以及文化交往、社会评价等方面处于不利地位。如果任由这种情况发展,极有可能造成少数民族的不断边缘化,引发贫困问题,造成民族矛盾,并最终引起民族冲突,进而造成社会动荡。改流后由于汉民对苗民的欺诈、压迫、掠夺行为造成苗民生存空间不断被挤压,从而出现的有关“汉奸”的一系列称呼和一系列针对汉民的劫杀、抢夺、报复性行为,以及最终所引发的“乾嘉苗民起义”的直接原因即源于此。而土民在与汉民交往过程中出现的贫困化问题一直阻碍着地区的发展。因此,在外来人口大规模流入少数民族地区的过程中,一定要对少数民族的经济、教育、文化、社会保障和政治权益予以适当保护,只有当少数民族在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科技、教育水平与外来人口大致持平的情况下,才有实施统一政策的基础。
(六)基于日常生活的交往、交流、交融是流动人口融入的主要路径
日常生活具有社会参与面广、社会互动渠道多、涉及层面深、与群众贴近性强、对群众影响大等特点。外来人口进入移民地,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居住、生产、贸易、入学、婚姻、社区管理、节日、娱乐等日常生活的内容。这些环节处理的好坏,与移民地原住民日常生活密切程度,两者之间相互嵌入程度,即是评价人口融入度的标准,也是人口融入的主要内容。外来人口进入改流区后,与土民相互通婚、在社区建设中共同参与、社会管理中协同互惠、经济活动中相互交流、外来威胁时共同应对、文化娱乐活动中相互学习,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共同利益,在利益基础上相互联结。由于交流日益增多、交往日益密切,最终走向了交融。它对我们当下工作的启示是,在流动人口管理工作中,要推动流动人口参与到本地居民的日常生活中来,更要增强本地居民在日常生产生活中主动接纳流动人口的勇气和信心。具体来讲,政府在制定相关规划、出台相关政策时要考虑到流动人口的利益,制定相关计划时要考虑到流动人口的特点;本地居民在日常生活中要保持开放性心态,尊重外来人口的文化特点;流动人口要公平参与流入地的日常生活,主动学习不同生产生活内容。只有日常生活内容交流、交往增多,流动人口流入地存在感增强、与本地居民利益联结更为密切,才能形成对流入地的认同,也才有可能真正融入。
[1] 龚胜全.两湖农业地理[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98.
[2] 常建华.清雍正朝改土归流起因新说[J].中国史研究,2015(1).
[3] 清世宗实录:卷64[Z].台北:台湾华文书局,1973:1106.
[4] 吉钟颖.鹤峰州志[Z].道光二年(1822)刻本.
[5] 黄河清.凤凰厅志[Z].光绪元年(1875)刻本.
[6] 刘社欣,王仕敏.文化认同视阈下的国家认同[J].学术研究,2015(2).
[7] 董珞.巴风土韵[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
[8] 李然,王真慧.当代湘西苗族土家族互化现象探析[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2(4).
[9] 黄应培.凤凰厅志[Z].道光四年(1824)刻本.
[10] 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14辑[M].北京:中华书局,1990:151.
[11]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民委《民族志》编纂小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民族志[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49.
Effect and Enlightenment from the Governance of Social Problems in Floating Population in Wuling Ethnic Areas after Bureaucratization of Native Officers
MO Daishan, WANG Xihui
( Institute of Nationalities, Yangtze Normal University, Fuling 408100, Chongqing, China )
After bureaucratization of native officers, the social problems in floating population have been solved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e forces, the unification of cultural spirit, the autonomy of villagers, the construction of regional identity, etc. Through governance, national integration at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levels has been basically realized. The Confucian spirit has become a unified cultural standard and the national identity of the masses has been strengthened. Economic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has narrowed the gap with the outside world. The trend of multi-ethnic exchanges, communication and integration has emerged, and social unrest has been reduced. At the same time, there are also problems such as blind population flow and low matching degree of regional resources, the extrusion to the living space of ethnic minorities by immigrants, cultural discrimination, etc. In the governance of social problems in floating population,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the fundamental approach, traditional cultural norms are important resources, and strengthening the guidance of local elites is an important starting point. The construction of common cultural spirit plays a fundamental role in the integration of population, and the interests of ethnic minorities should be properly protected in the process of the integration of immigrant population.
Bureaucratization of native officers, population flow, social governance, Wuling ethnic area
K289
A
1673-9639 (2020) 03-0119-09
2019-05-13
国家社科重大项目“改土归流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历史文献整理与研究”(19ZDA182);重庆市社科规划项目“改土归流后渝湘土苗地区治理比较研究”(2018YBMZ148)。
莫代山(1979-),男,土家族,湖北恩施人,博士,教授,研究方向:武陵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与社会发展。
王希辉(1980-),男,土家族,湖北恩施人,博士,教授,研究方向:武陵山地区散杂居民族问题。
(责任编辑 车越川)(责任校对 黎 帅)(英文编辑 田兴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