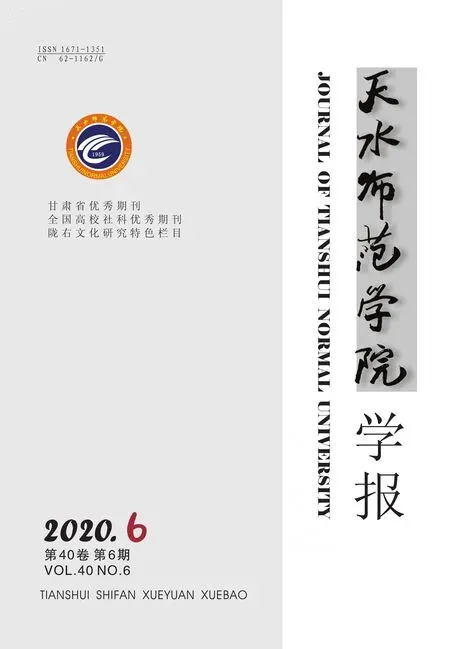融合·新变·构建
——评李志孝、张继红《承传与对话:新世纪文学与新文学传统》
2020-01-09缑悦
缑 悦
(天水师范学院 文学与文化传播学院,甘肃 天水 741001)
21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同样,文学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于文学的这种巨变,评论界将其称为文学的“世纪转型”。同时,“新世纪文学”的概念被提出,此后,研究新世纪文学与之前文学区别的论文也不断出现。但如果只看到文学的新变,而看不到其中的承传与对话,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事实上,新世纪文学与中国文学传统,特别是新文学传统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不可能割断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看到了李志孝、张继红的学术新著《承传与对话:新世纪文学与新文学传统》[1](以下简称《承传》)。该著作在宏观的文学史视野下,比较全面地论述了新世纪文学和新文学传统之间割舍不断的关系,“这种关系,既有题材选择,也有书写方式,还有审美取向、价值立场,当然更包含一种潜在的‘对话’。认真研究这种关系,特别是‘对话’,从而探讨新世纪文学新的话语空间、审美创造,为新世纪文学创作与研究建立合法的历史根基,积极参与‘中国文学精神’的建构”,[1]11-12这正是作者的目的。
一、动态的文学传统观
关于新文学传统,学界对此颇有研究,但大多是针对某一个方面的传统进行论述。如有人论述新文学的启蒙传统,[2],[3]有人论述新文学的人民性传统,[4]有人论述“茅盾传统”,[5]等等。新文学传统的构成本来就是纷繁复杂的,因此,单篇论文难以将其论述得透彻明白,只有将其放在流动的文学史中对其进行梳理,考察其发展和新变,这样才能让新文学传统重新焕发活力,继续为文学的发展提供内在精神动力和可靠的文化资源。正如陈思和先生认为:“文学传统也不是遥远的僵死的存在,它永远是一种与现实紧紧联系的、处于流动状态的过程。”[6]34
正因为如此,《承传》没有单独地去论述某个时期或某种新文学传统的发展与演变,而是将新文学传统放在了不同的题材类型和文学形态中进行探讨,进而从中看到新文学传统在新世纪文学写作中不同的表现。通过向内看,新世纪文学受到了新文学传统多方面的影响。文学传统不是固定不变的东西,它始终处在一种“流动”的状态之中。在该著作中,作者选取了“乡土文学”“城市文学”“底层文学”“知识分子书写”“女性文学”“历史文学叙事”六个主要的文学类型进行了分析,进而考察文学书写在历史发展中的“常”与“变”。就“常”来看:以上六个题材的叙述在新文学发展的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样貌,而这种叙述也没有在新世纪文学的发展中呈现出“断裂”和“消失”,新世纪文学的写作也主要围绕着这些题材类型展开。同样的题材虽然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关注角度、叙事角度、艺术方法和思想价值,但有着共同的精神联系;从“变”来讲:文学来源于社会生活,而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也必然会促进和改变文学的发展和走向。新世纪文学面临着与以前不同的社会现实和文化语境,知识分子既要把新文学传统中的“中国经验”表达出来,同时也不能囿于传统,要丰富和创化传统,要有“在场”意识,要把握当下“中国经验”的新内涵,这样才能在回望传统的过程中,审视历史,立足当下,为新世纪文学的发展找到内生的原动力。
余英时说:“所谓‘现代’即‘传统’的‘现代化’,离开了‘传统’这一主体,‘现代化’根本无所附丽。”[7]因此,在《承传》中,作者一方面梳理了新文学传统的发展路径并整合了其思想资源;另一方面对这些资源进行了现代化阐释,并且对新世纪文学的书写特点进行观照。以乡土文学和女性文学为例,能够发现其承传和创新之处。
《承传》作者在论及乡土文学时,指出了“五四”新文学传统的思想资源——“启蒙主义”和“人道主义”对其影响深远。如以鲁迅为代表的乡土作家对于乡土社会中愚昧和落后的批判和以沈从文为代表的乡土作家对于“田园牧歌式”乡村的赞美。从“左翼文学”到“十七年”时期的乡土文学的描写中带有明显的政治和阶级意识,乡村不再是一群人的落后和愚昧,而大都是正面人物对于反面人物的教育和改造;乡村不仅仅表现风俗美和风景美,而更多的是充满亮色的热土和思想改造的试验场。如赵树理的乡土小说《李有才板话》《小二黑结婚》等。在20世纪80年代的“寻根文学”中则表现出了对于乡土的一种复杂态度,作家一方面想在传统乡土中找寻民族文化的根,另一方面发现了乡村传统中的愚昧和迂腐。如阿城的《棋王》、韩少功的《爸爸爸》等作品。作者指出在新世纪文学写作中,乡土文学的书写不仅批判性地继承了以前的文学传统,如刘庆邦的《东风嫁》、宋剑挺的《水霞的微笑》等描写了有过不堪生活史的女子在回村后的遭遇,将村民的愚昧无知、自私狭隘表现得淋漓尽致,从中我们看到了鲁迅对于“国民劣根性”批判的影子和新文学启蒙主义的传统。同时也有作家继承了“沈从文式”的创作传统,如王跃文的《国画》、张鹤的《春叶》等作品体现了对自然、优美、理想和诗意浪漫情调的追求,而且表现出了在价值立场、叙事对象、审美特征等方面的新变。在价值立场方面,以鲁迅为代表的乡土作家对于国民性的批判,演变为左翼时期对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强调,到新世纪则出现了含混和犹疑——作家在面对乡村时,显示出对乡村落后的现代批判;在面对城市时,却表现出了对乡村的留恋和昔日美好的回忆。在叙事对象方面,作家由单一地描写乡村人物和乡村生活转向了农民工、乡土和生态的结合。在审美特征方面,作品当中的风景描写逐渐被日常生活描写所取代,因而也相应地缺少了地方色彩,但与此同时,方言的使用又饱含地域色彩;传统的风俗民情也失去往日辉煌,变得机械化和程式化。总之,新世纪的乡土文学书写中,一方面是对于新文学传统的批判性继承,另一方面是随着社会转型出现了对应性的新变,在“对话”的基础上有新的“创化”。
该著在论及女性文学时,认为“女性文学的起点与启蒙文学几乎是同步而且同质的,这使得以男性为主体的启蒙话语往往会遮蔽女性话语的生产”。[1]177也就是说,“五四”时期女性的觉醒仍然是男性笔下的“被启蒙者”,即便是女性作家,如冰心、庐隐、冯沅君等作家笔下的人物形象也存在着类型化、符号化的特征。革命文学阶段,革命话语代替启蒙话语,文学书写趋向“革命+恋爱”的模式。20世纪40年代,作家笔下的女性人物形象转向翻身与解放、政治话语和阶级身份等方面的描写。新时期以来,女性文学的书写开始注重日常生活审美,并且身体意识进一步觉醒,如铁凝的《没有纽扣的红衬衫》就表达出了少女的个性意识和对自己身体的审美认知。新世纪女性文学的书写转向“日常生活中女性意识的外化,即女性通过个体的自觉参与来确证自我的角色和性别特征,是‘如何讲述自我(女性)’的问题”。[1]187至此,女性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性别符号,而是作为一个主体参与到叙事中来。作者在该著作中概括了21世纪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城以及由此出现的“身体叙事”“道德叙事”“返乡叙事”和“憎恨美学”等方面的特点,比较全面地概括了女性在时代发展中所遭遇的矛盾和危机。女性一方面想要保持自身的独立,但面对现实情况时,她们最有价值的“资本”——身体,便冲在前面,身体和道德的复杂性便在于此;另一方面,当她们认识到自己陷入泥淖但是又不甘于沉沦时,她们想回到最初出发的地方——乡村,但乡村的伦理秩序对她们表现出厌恶和拒绝,而作家的叙事视点也表现得模糊:对现实和女性表达出“爱”与“憎”的态度,而一般情况是后者多于前者。但同时作者认为,新世纪女性文学的写作应在对城乡关系正确认识的基础上进行城乡想象,从而能够把女性进城书写建立在“身体美学”的基础上进行更深入的书写。总之,从“被启蒙”到自觉意识,从“政治身体”到“自我身体”,女性形象和自我意识一直在发生变化,尤其是在21世纪以来,女性面临着新的社会现实,而文学书写也在动态的变化中关注着女性生活和命运。
新文学的传统一方面在新世纪文学的写作中被继承了下来,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不同的社会历史环境下对于新文学传统的具体内涵的改变和扩充。两者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精神联系和对话意识,从动态的文学传统观中观照新文学传统和新世纪文学之间的传承和转化,通过对其共性精神的挖掘,进一步让传统“复活”,让未来文学有“根”,这样才能够为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建构奠定基础,才能在整体的文学史视野中掌握新文学传统和新世纪文学的发展轨迹和方向。
二、整体的文学史观
无论是从“五四”时期开始的现代文学,抑或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当代文学还是21世纪以来被称为的“新世纪文学”,都属于中国新文学这一整体概念。之所以将其进行区分,是因为新世纪文学在面对社会的快速发展时,出现了诸多不同于之前文学的新质。面对这种新质,研究者也提出了不同见解,如有学者认为新世纪文学“已经超越了‘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历史规定性,有了自己新的可能性”,[8]即认为新世纪文学具有了“断代”研究的可行性,“20世纪的结束从一个文学史的角度观察,也是‘新文学’的终结”。[9]但也有研究者认为,“在‘新世纪文学’与‘新时期文学’的联系上,‘断裂’将是一个难以立足的文学史概念”。[10]还有坚持“整体观”的学者认为,新世纪文学是新文学自然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与新文学传统有着密切的联系。有人甚至发出“重回‘五四’起跑线”的呼声。[11]1
《承传》正是秉持整体的文学史观,从宏观角度考察新世纪文学是如何“承传”和“对话”传统。作者认为新文学传统并没有出现“断裂”,而是几经流变,以一种新的姿态进入了新世纪文学的写作体系中。该著作既“向后看”,揭示了新文学传统对于新世纪文学巨大而复杂的影响;同时也“向前看”,分析了新世纪文学已经表现出对这种传统的响应或潜在的“对话”,这样就把两者放在了一个整体的框架之中,认识到新世纪文学对于新文学传统的承传与创化、选择与对话的关系。同时,作者高屋建瓴,运用多学科交叉研究和对比研究的方法对六种题材类型的作品进行深入的文本分析,不仅呈现出不同时期作品写作的“内部”特点,而且传达出更深、更广的“外部”文化研究。通读这本著作,可以发现作者的比较意识总体可以分为两大类:“共时性比较”和“历时性比较”。
所谓“共时性比较”,在《承传》中主要指的是同一时期作家之间的比较,这些作家可能涉及同一题材类型,也可能是不同的题材。如作者谈到四十年代的知识分子书写时,分析了许多作家笔下不同的知识分子形象类型;“历时性比较”在《承传》中主要体现在对同一题材的过去——现在——未来进行全方位的比较研究,进而分析它们之间的特点、关系、承传和超越之处。除此之外,作者还通过对个别作家如张贤亮、铁凝等不同时期的作品进行比较,以探究其书写转向的可能性。
只有通过大量的对比分析,才能看清新世纪文学在哪些方面对新文学传统有继承,哪些地方形成一种“对话”,哪些地方又有创新和超越,才能更全面、更透彻地从建构“史”的角度来看待新文学传统和新世纪文学之间的关系。
正因为作者以宏观的文学史视野来考察新世纪文学和新文学传统的关系,所以,在论述“乡土文学”“城市文学”“底层文学”“知识分子书写”“女性文学”“历史文学叙事”等六个题材类型时,都是先把其放在文学史的坐标上考察其书写方式,然后再分析新世纪文学,看其在书写姿态、叙事方式、美学风格等方面的新变,这样就会对同一类型题材的“前世今生”进行整体认识,在对比研究中发现其承传和对话以及由此产生的新变之处。
在《承传》中,作者认为“政治化”和“启蒙”是新文学的重要传统。就“政治化”而言,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政治就跟文学紧密地结合,政治标准高于文学的艺术标准和美学标准,文学变成了“席勒式”的传声筒,尤其是在“十七年”时期,显得尤为突出。21世纪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出现了诸多社会问题如生态环境恶化、贫富差距拉大、城乡互动加快等,文学创作领域在出现底层文学思潮的同时,相应地也出现了政治关怀的倾向。如有学者认为,“在当下中国的政治文化语境之中,如何恢复、保持和不断增强文学实践的政治活力而将我们的文学充分有力地‘再政治化’,并且以文学自己的方式相当有力地‘介入’中国历史和中国现实,将是文学的生机之所在”。[12]而新世纪文学的“再政治化”不再是走文学与政治联姻的老路,而是要重建文学与政治的常态化关系——两者是平行的关系,而不是命令与服从的关系。如茅盾的《子夜》有意识地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动向,作品中人物的角色是按照需要设计的;新世纪曹征路的《问苍茫》则表达了人物面对现实时内心的复杂和矛盾,同时又采用传统的“社会剖析”模式显示了作家的社会责任感。
“五四”时期的“启蒙”是要让广大民众从黑暗、愚昧的旧世界中走出来,开启民智,进而成为一个有个性、有思想、有尊严的“大写”的人,进而才能谈论到民族意识和国家富强。后来启蒙中断,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逐渐恢复。新世纪启蒙文学中,作家没有“五四”时期居高临下的姿态,也没有20世纪80年代慷慨悲壮的色彩,而是采取了一种平视的视角,在批判的同时又有着无可奈何的同情和感叹,从单一的宏大叙事转向宏大与日常生活相融合,体现出个人化和生活化。
从“政治化”和“启蒙”的传统中我们看到了新文学传统在文学史中的发展和新变。同样,当我们把具体的同一题材类型放在文学史的坐标中进行观察,也能够发现在新文学传统的建构和阐释过程中,它们呈现出的发展轨迹和在新世纪文学中发生的新变,比如城市文学的书写。
21世纪以来的城市文学展现的都市往往是欲望化的、让人情感迷失的以及“他者”的城市。城市不仅是消费和享乐的空间,也是冷漠与荒寒、冰冷与坚硬的化身,如熊育群的小说《无巢》、陈应松的《太平狗》、吴君的《亲爱的深圳》等作品表现了来自乡村的外来者,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融入经济发达的城市,但城市给予他们的是冷漠甚至是抛弃。左翼文学作家大多认为城市是文明的异化物,有着丑陋和罪恶,尤其是茅盾的代表作《子夜》,具有鲜明的阶级意识和对现代都市文明的批判;而海派作家笔下的都市则更具有现代化的“风景”,他们对城市持有一种暧昧的态度,一方面迷恋于充满欲望、享乐、喧嚣、刺激的城市带来的物质便利和精神享受,另一方面对城市腐朽、堕落的一面进行揭露和批判。通过比较可以看出,对于同一题材,不同时代背景之下写作的指导思想和叙事方法、技巧等都有差异。以文学史的视野来考察,就能够发现问题和不足、流变与创新,如有学者认为:“今天的城市文学,有作家,有作品,有社会问题,有故事,但就是没有这个时代代表性的人物。”[13]正是以往城市文学作品中如吴荪甫、赵伯韬、曹七巧、祥子等典型人物的成功塑造,让我们看到了新世纪以来城市文学的不足之处,这正是在与新文学传统进行交流和对话的基础之上得到的。
传统的题材和新的社会语境相遇,必然会出现有异于传统的审美方式和艺术形式。只有把两者放在文学史坐标中考察其相互之间的对话与交流、不足与超越,才能更清晰地看到文学的发展脉络和方向,才能为文学的发展找到出路,才能让新世纪文学在新文学传统的铺垫和指引下更好地反映当下现实情况,才能积极地建构两者之间共性的文学精神联系。
三、积极的建构意识
《承传》将新世纪文学现象纳入了宏观的文学史坐标中,在新文学传统的建构与阐释中,发掘承传与创化、选择与对话的关系;关注社会转型与文学转型的互动;聚焦文学研究和文学史建构的关系,为新世纪文学创作和研究建立合法的历史根基和当下性的诠释结果,并积极参与“中国文学精神”的建构。
作者认为“新世纪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自然生发的新阶段,也是当下中国文学世纪转型的典型显现”。[1]251作者不仅将新世纪文学的发展推衍到了新文学传统,而且在题材类型、叙事方式、艺术技巧等方面进行了回望,分析了各个时间段的特点和新变。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作者想要更进一步地研究文学发展的根基和走向,进而对新世纪文学的发展提出展望,为未来文学书写“中国经验”提供文学动力,为更好地建构“中国话语”奠定文化基础。结合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现状,作者在六种题材类型中指出了新世纪文学当前及其未来发展面临的问题和困境,对此进行分析并且提出建议,反映了作者对于文学建构的殷殷之心。
作者在论及城市文学时,认为新世纪城市文学的书写突破了新文学的宏大叙事,转向个人化叙事和日常生活的描写,比如老舍的《骆驼祥子》《四世同堂》等作品都有一个宏大的主题。随着新写实小说的出现,小说描写转向了世俗生活中的“一地鸡毛”,新世纪作家金宇澄的长篇小说《繁花》中描写的就是生活中的家长里短、人情世态以及饮食男女,展现给读者一幅上海市民日常生活的世相百态图。同时由于市场经济的刺激,城市文学在钢筋水泥的外表下有雷同化和类型化的趋势,作品更多呈现纪实性而缺乏想象性,缺乏性格鲜明的典型人物。因此,作者通过梳理城市文学的过去和现在,在展望城市文学未来的同时,提出首先要处理好城市和乡村的关系,要注重城乡互动的加快,要理性、客观、公正地对待城市;其次要有“家园感”,将城市作为“家园”,把自己看成是城市中的一分子,把审美的笔触伸入到城市的深处,“将城市作为‘风景’,拥有一种家园感,进而发现城市生活的魅力,提炼出城市生活的现代诗意,这是城市文学的重要前提”。[14]最后还要将写实和写意结合起来,追求小说的寓言化效果,寓言化写作不仅可以激发作家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而且可以使叙事话语具有诗性和哲理内涵。
作者在论及历史文学时,认为“五四”时期的作家们借助历史,从“人”的个性解放的立场出发,对历史进行重释。尤其是在历史剧的创作中,如郭沫若剧作《三个叛逆的女性》,同时也有作品对历史人物按照现代视角重新解释和定位,如鲁迅的《故事新编》等。“十七年”时期,历史文学具有了强烈的政治革命倾向和意识形态性质,如“三红一创”“青山保林”等作品迎合意识形态,将复杂的生活简单化描写,但同时这也实现了“对历史‘本质’的规范化叙述,为新的社会的真理性做出证明,以具象的方式,推动对历史的既定叙述的合法化,也为处于社会转型期中的民众,提供生活准则和思想依据”[15]107的目的。新历史小说出现之后,对历史的写作从官方(集体)转向民间(个人)立场,注重日常生活的描写,这是对历史进行解构之后的重新建构。同时历史文学创作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如历史文学作品的创作迎合影视化改编的需求,在追求经济效益的结果下文学性有所减弱;有些作品对历史人物的重写重评没有掌握好度;还有一些作品在个性化书写的旗帜下,一味地张扬世俗的东西,崇高被消解,英雄被解构。那么面对这种现状,在新世纪历史文学的创作中,应该怎样去书写呢?《承传》作者提出了三个问题:“历史真实”问题、“当代性”问题和“主观化”问题。新历史小说虽然打破了历史的“真实性”和“神圣性”,对历史进行了解构,但是历史的写作更应该注重文学的真实,而不是随着个人的主观化进行随意的编造。自由叙事但应该有前提,那就是尊重历史的真实性,在这基础上进行“失事求似”的写作才能把作家的思想和艺术的审美结合起来,历史书写才能不囿于泛滥的“解构”,才能不被变成市场利益的消费对象。
作者梳理了城市文学和历史文学的过去和现在,并提出这两种文学以后的发展方向。作者正是从新文学传统中进行资源的整合和梳理、选择与对话出发,想要为文学建构立体的发展体系。对于新世纪文学的研究,要做的不仅仅是去追寻传统,更重要的是通过对传统的承继和对话,找到发展的历史根基和出路,重新建构起中国文学发展的理论资源和思想资源,而这些就是在与传统进行对话之后进行创造性地解释和创新性地发展得到的。作者在书中提出问题,也是对建构“中国文学精神”的侧面推进,只有正视这些问题,朝着解决问题的方向进一步迈进,将“五四”以来新文学传统中的经验与新世纪文学发展中出现的新变相结合,才能形成具有“中国经验”的新世纪文学,才能为新世纪文学的发展寻得创新之道。
四、结语
《承传》从传统和传统的当代性阐释这两个角度对新文学和新世纪文学进行了整体的文学史视野关照,并就其六种题材类型进行了传统和新变的对比分析。在回望传统中试图找到新世纪文学发展的历史根基,同时又展望新世纪文学创作和研究的发展走向。通过对新世纪文学与新文学传统关系的考察,揭示两者之间的承传与对话、创新与超越,以期建立新世纪文学和新文学传统的内在精神联系,进而参与“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建构”,作者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
《承传》主要以叙事性作品尤其是以小说为研究对象,作者也指出了这样研究的缺陷就是没有把诸如诗歌、散文、戏剧等文学体裁以及在新世纪发展迅速的网络文学纳入分析的序列。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作者面对的新世纪文学数量是十分庞大的,任何一位研究者都很难对当下的所有文学作品进行全面的阅读,在这样的情况下,以某一种体裁为主进行研究既是一种无奈,也是一种策略。更何况,小说作为当下最重要最有成就的文学体裁,在某种程度上也最能代表文学的发展现状。而且,这也为今后更进一步地研究其他体裁类型提供了一个基础、思路和范式,可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建构”之路是任重而道远的,需要更多的文学研究者共同参与进来,“上下而求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