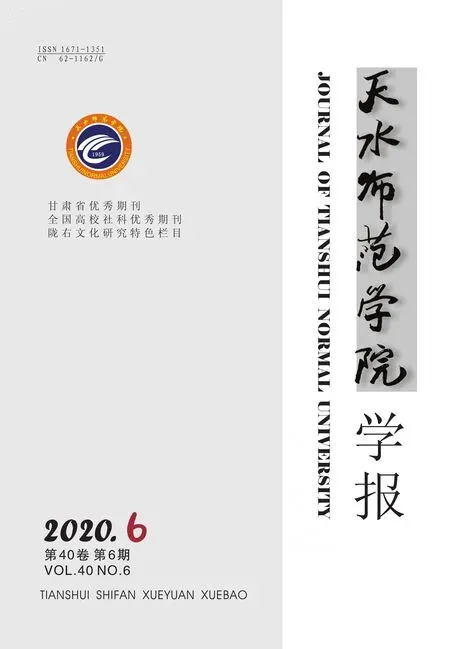21世纪以来敦煌歌辞研究回顾
2020-01-09许柳泓
许柳泓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234)
1900年,敦煌藏经洞的大门在无意间被打开,由此唤醒了沉睡千年的敦煌写卷,散存于各类写卷中的敦煌歌辞以其质朴而神秘的面貌吸引了众多研究者的目光。1920年,从王国维《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1]一文发表以来,学界逐渐对敦煌歌辞进行广泛地收集整理,仔细地校勘考证,涌现出王重民、任二北、饶宗颐、潘重规等研究专家,极具影响力的著作也相继问世,研究成果丰硕。在对敦煌写本进行整理研究时,最先面对的一个难题就是作品称名的界定。至今,学界对此问题仍有争论,不同的研究者对这些作品的不同称名反映出研究者对作品性质的体认。笔者采用“歌辞”这一称名,包含了曲子词、大曲词、俗曲、佛曲等多种歌辞品种或音乐文学形式。百年来,敦煌歌辞的研究以“敦煌曲子词”为主,研究者多将其纳入词学系统来加以观照与审视,而除此之外的歌辞则常常得不到重视。21世纪以来,随着研究者研究视野的拓宽,研究思维的转变,研究方法的改进,敦煌歌辞的研究呈现出崭新的面貌。21世纪二十年来,敦煌歌辞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四大方面:文献整理、语言文学研究、文化研究、写本研究,这无不展示着敦煌歌辞研究的进步与发展。
一、文献整理的深细化与相关理论问题的探讨
由于敦煌遗书多散落在海外,欲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则须将搜集整理工作摆在首位。20世纪50年代,王重民将自己搜集的敦煌歌辞作品加以整理,并融入词学观照,于1950年出版了《敦煌曲子词集》。该书除了提供文本外,也对敦煌曲子词的概念、起源提出了颇具参考价值的见解。随后,任二北在此基础上增录了包含曲子词、民间歌词和大曲在内的歌辞共545首,并于1955年出版《敦煌曲校录》。后又于校录的基础上出版《敦煌曲初探》一书,较为系统、全面地展现了唐五代的乐曲材料。在持续地整理研究中,任先生终于在1987年出版《敦煌歌辞总编》。全书共7卷,收录1221首敦煌歌辞,材料众多,内容宏富,有集大成的作用。在文学史上,其文献价值与贡献是不容忽视的。但因为任先生未能目睹敦煌文书的原本面貌,其校勘时多用“理校”之法,有主观臆测之嫌,由此造成不少争议。因此,针对《敦煌歌辞总编》进行论述校补成为后来研究者的主要议题之一。
20世纪90年代,对敦煌歌辞再次进行整理补充、勘误校正的代表作当属项楚的《敦煌歌辞总编匡补》。因其认为卷一所录的《云谣集杂曲子》已有潘重规、林玫仪等学者的优秀研究成果在前,故项先生从卷二开始,对《敦煌歌辞总编》中所收录的歌辞作品进行增补,同时也校正了其中的讹误,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更为准确的文本参考。[2]
近年来,各大高校的研究者在借鉴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时,也对敦煌歌辞进行了更为深入的考证辨析,展现出新的思考。他们或借助语言学知识,对《敦煌歌辞总编》中讹误的字词提出新见解,如张福通《〈敦煌歌辞总编匡补〉零拾》、[3]王洋河《〈敦煌歌辞总编〉补校札记》、[4]刘晓兴《〈敦煌歌辞总编〉校议》[5]等;或综合运用文献学、文字学、语言学等学科的相关知识,对《敦煌歌辞总编》所收录的部分歌辞重新整理并勘误校正,如刘晓兴《〈敦煌歌辞总编〉献疑》[6]等。
在整理、校勘工作相对完善后,通论类等具有归纳性的著作也相继问世。张锡厚于2000年出版的《敦煌文学源流》一书,第四章专门探讨了敦煌歌辞的源流及其艺术嬗变,重点讨论了《云谣集》及俗曲、辞调名的源流。[7]吴肃森《敦煌歌辞通论》对敦煌歌辞进行了多角度、多层次、多侧面的深入研究与论析。其中《论敦煌歌辞与词的源流》《论敦煌佛曲与词的起源》《三论词的起源》诸文,一步步论证了“词源于民间”这一观点,并认为敦煌歌辞是词的直接源头。这对历来学界众说纷纭的词源问题,起到了渐次廓清的作用。[8]伏俊琏《敦煌文学总论》一书则着重从文献学的角度来讲敦煌文学,强调敦煌文学的仪式性和表演性。第七章重点介绍了敦煌歌辞,由宏观到微观,先概述写卷形貌,再解析其传抄原因及功用,后又分析敦煌歌辞中的特殊句式及校勘情况,呈现了敦煌歌辞的文献价值。[9]
二、文学、语言学研究的拓展
自从敦煌遗书重现于世以来,研究者自觉地将敦煌歌辞纳入文学研究的范畴中,并采用文学主体学的研究方法,从多个方面探究敦煌歌辞的文学价值,这无疑是研究工作细致化、深层化的体现。
从意象上着手的研究不在少数,其中“女性形象”的关注度较高。刘洁《从敦煌歌辞看中古时期中国女性的情感观念及表情方式特点》一文指出:“一个时代女性的情爱观念,往往能够比较清晰地表现一个时代女性的精神风貌,折射出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状况,其意义不可低估。”[10]该文通过对敦煌歌辞中女性形象的分析,展现了中古时期女性对爱情的热烈追求以及勇于挑战男权主义的叛逆意识,进而窥探在相对自由开放的环境下女权意识的发展情况。魏凯园、郭艳华《论敦煌曲子词中“征妇”主题的双重情感及其成因》一文聚焦于“征妇”这一女性形象,认为敦煌曲子词中的“征妇”形象打破了历代文学中“征妇怨”的抒情传统,而带上“慕功”的心理,这一变化是被打上深深的时代烙印的。[11]赵波的硕士论文《敦煌曲子词的女性书写》则更为全面地考察敦煌曲子词中的女性形象,探究其对词学、女性文学发展的影响。[12]
对敦煌歌辞审美特征的探讨也是学界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在诸多论文、著作中皆有提及。专门对此展开较为详细研究的是王莎莎的硕士论文《敦煌曲子词的审美特征论》。该研究从语言、情感、文化习俗等方面展开论证,逐层深入,探索敦煌曲子词独特的审美特征,并分析了敦煌曲子词对后世词作审美特征的影响。[13]
一直以来,语言研究都是敦煌歌辞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此类研究侧重于讨论俚语俗语、句法句式的问题。敦煌歌辞之所以能长期受到学界的关注,得益于其内容中所蕴含的具有全面性的语料。正如刘传启在《敦煌歌辞文献语言研究》一书中言:“敦煌歌辞是我们今天研究唐五代语言的活化石。”[14]24该书重点探讨了敦煌歌辞的语词、句法,揭示敦煌歌辞的语言特点。刘传启认为敦煌歌辞所呈现出的语言现象乍看之下好像无规律可循,但是经过整理分析后却不难发现敦煌歌辞的特殊句式多出现于佛教文学的作品中,诸如佛曲、变文等。“这一现象的发现必将为我们在佛教世俗化这一大背景下讨论敦煌佛曲以及变文语言的中国化改造问题提供很好的切入视角。”[14]25敦煌歌辞中个别词语的考释在诸多论文中都有讨论,在此不一一列举。近年来,敦煌歌辞的语言研究有专门化、系统化的趋势。如易雪凤的《敦煌曲子词同义词研究》[15]和姚文婧的《敦煌歌辞反义词研究》,[16]分别选取了同义词、反义词为研究的切入点,较为完整地呈现出敦煌歌辞中的同义词、反义词的词汇系统。从音韵学角度考察敦煌歌辞的用韵情况也是敦煌歌辞语言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除单篇论文所讨论的个别音韵问题外,较为系统地展现敦煌歌辞用韵情况的有两篇硕士论文:陶贞安《敦煌歌辞用韵研究》、[17]霍文艳《敦煌曲子词用韵研究》。[18]
敦煌歌辞的文学地位问题也是学界讨论的焦点。研究者多从其开创性意义入手,论证其“奠定了后世词体的基本走向”的观点,这也为词体起源的探索提供了足资借鉴的新思考。近年来,由于“一带一路”经济发展战略的提出,敦煌作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城市再次引起学者们的重视,他们强调敦煌歌辞在东西文化交流中的历史意义。赵录旺《〈敦煌曲子词〉的历史价值探微》一文在讨论了敦煌曲子词于词体发展中的意义后,又指出敦煌曲子词在跨国界的传播中具有世界性的学术意义,特别是在以丝绸之路为纽带所展开的东西文化交流的新时代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19]
三、民俗、地域等文化的观照
敦煌,河西走廊西端的重要城市,曾经是北方游牧民族纵情驰骋的沃土,也是丝绸之路上东西文化交流的重镇,蕴含着丰富的多元文化。文化的力量在潜移默化中渗入到敦煌歌辞当中,通过对敦煌歌辞的研究以挖掘其文化内蕴是21世纪以来一部分学者的共同特点,相关研究成果较为丰富。
文化研究中,研究者多通过对敦煌歌辞中所蕴藏的民俗文化进行深入考察,由此来揭示其地域性、民间性的特征。台湾学者对敦煌歌辞所暗含的民俗风貌较为关注,其考察也较为细致全面。郑阿财《〈云谣集·凤归云〉中“金钗卜”民俗初探》一文,从敦煌写本《云谣集》入手,探讨《凤归云》一词所反映出的“金钗卜”民俗的性质、渊源及从唐代“金钗卜”到元明清“鞋打卦”的演变等相关问题,认为这类作品体现了中国民间妇女望夫盼郎之情思,彰显了中国俗文学与俗文化相辅相成的密切关系。[20]朱凤玉《敦煌边塞文学中“灵鹊报喜”风俗初探》一文通过对敦煌曲子词《鹊踏枝》《恭(宫)春怨》《菩萨蛮》《阿曹婆》等边塞词的分析,认为“灵鹊报喜”中的喜鹊寄托了妇女的相思之情,是妇女盼夫的心理投射,也是唐代民俗风情的深刻体现。[21]大陆学者在著作中也多有提及敦煌歌辞的民间性特征。单独探讨敦煌歌辞这一特征且较为突出的有敖峥《论敦煌曲子词的民间性》一文,该文从题材范围、艺术特色、表达方式三方面探讨敦煌曲子词强烈的民间特色。[22]又有何春环、何尊沛《论敦煌曲子词的民俗文化特征》一文,主要讨论敦煌曲子词中所映射出的信仰民俗、婚姻民俗、服饰民俗、节日民俗、游艺娱乐民俗五大方面的内容,认为敦煌曲子词“是唐代民俗文化的宝库,它形象而真实地反映唐代芸芸众生的世俗生活,展示了唐代社会鲜活生动的民俗风情,体现了大唐恢宏开放的文化精神。”[23]
此外,较具代表性的是汤君的研究成果。其早期的研究目光多落于敦煌曲子词与地域文化的探究上,有《敦煌曲子词与中原文化》[24]《敦煌曲子词与河西本土文化》[25]等文章发表。其博士论文《敦煌曲子词地域文化研究》打破前辈诸家所采用的传统校勘、微观考证、纯文学研究视角等的局限,“全面考察敦煌曲子词的写本状况,进而探寻其与隋唐音乐,尤其是唐五代敦煌地区燕乐歌舞的关系,从地域文化的角度,采取历史、文化与实证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分析,将敦煌曲子词视为整个敦煌学中一种文化现象或文史问题来研究,以探索它与西域和中原文化的内在血缘关系。”[26]由此认为敦煌曲子词有中原文化的痕迹,又是河西本土文化的产物。此研究在敦煌歌辞的文化研究中具有集成性、开拓性的意义。同年,该论文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成书。
近十年,敦煌歌辞的文化研究热度不减,学者们除了在民间习俗、服饰文化、地域文化等内容上进一步挖掘其文化意义外,又有新发现,也提出了一些可供参考的新观点。隆莺芷的硕士论文《敦煌曲子词与唐代商业城市风貌》认为“敦煌曲子词是唐五代商业文化繁荣的产物。曲子词的兴起与商业城市的兴起息息相关:曲子词在城市化的商品经济中萌发,而商业城市无疑是曲子词文化的现实载体。”[27]将敦煌曲子词与城市文化联系起来研究,拓宽了敦煌歌辞文化研究的视野,也提出了新的思考方向。王柳芳《敦煌曲子词与城市文化》一文更强调在城市文化的视野下敦煌曲子词的表演性和娱乐性特征。[28]乔薇《敦煌曲子词中的民间法律思想研究》一文另辟蹊径,认为“敦煌曲子词中大量的以描写民间生活内容的作品即是对于当地民族民间习惯的记载也是对于这种民间习惯的传承。”[29]民间习惯逐渐演变成为独特的“民间法”。
四、写本研究:文本物质性的探索
相较于其他因刊刻而传世的词集,敦煌歌辞以更为原始的写本形态存世。20世纪60年代,日本学者藤枝晃就指出了敦煌文学研究的新方法,即“将写本残卷重建为一个整体,并且找出个别写本或写本群在全部遗书中的位置”。[30]10同时,他也提出了以印刷术出现以前的图书为研究对象的“写本书志学”这一名称。作为“写本学”的开创者,其观点至今仍有指导意义。写本研究,强调以第一手材料为本,通过精读敦煌遗书的原卷资料,探索被忽视的信息以及写本中各部分内容之间的密切关系。写本研究是近十年来敦煌歌辞研究的重要内容,其研究热度有增无减。
对敦煌歌辞的写本做出较为系统研究的当属张长彬的博士论文《敦煌曲子辞写本整理与研究》。该论文以写本为研究对象,对53个敦煌曲子辞写本进行文献整理与分析,对每件写本的时空特征做了较为明确的定位。同时,研究者还对敦煌曲子辞的亲缘材料P.3539卷(抄录音乐谱字)、兑废经写本、调名与题名、以表演为主要传播方式的敦煌曲子辞等内容进行专题研究,充实了写本研究的内容。[30]除此之外,张长彬还以典型写本个案进行考证分析,如《敦煌写本曲子辞抄写年代三考》一文对抄录有《云谣集》的S.1441和P.2838以及S.2607、P.3128三种曲子辞写本文献的抄写年代予以重新考证。[31]又如其与伍三土合作的《敦煌曲子辞调名上的三宗“错”——兼论处理敦煌曲子辞文献中错讹与疑点的态度和方法》一文,以写本考察为手段,对敦煌歌辞的曲调名进行深入研究,指出敦煌歌辞写本中的九首《浪涛沙》(后世作“浪淘沙”)一直被学界误判为《浣溪沙》,又论述了《感皇恩》与《苏莫(幕)遮》曲之间的关系,并对写本中的“同前”辞现象提出了新的见解。最后指出面对敦煌写本中一些令人费解的现象,“如果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我们应该树立一种小心求证、多闻阙疑的态度,不可以用后人的标准简单地将敦煌文献判错。”[32]
写本研究中,伏俊琏教授及其学生的研究较具代表性,成果颇多。其研究多从写本入手,通过细读写本,关注写本本身所透露的信息,梳理相关信息之间的联系,糅合其他门类的知识与观点,从而串联文本所传达的整体信息。伏俊琏《一部家国血泪简史——敦煌S.2607+S.9931写本研究》一文,将S.2607和S.9931缀合起来看成是一部词集,从写本所呈现的基本情况入手,考证其抄写年代、编者,分析其内容与性质来源,由此窥探唐昭宗时期的历史风貌,让写本不仅拥有了文学意义上“词集”的概念,也挖掘了写本所蕴含的历史价值。[33]如郑骥的硕士论文《敦煌歌辞〈十二时〉写本研究》回归写本文献本身,发现写本中更多隐含信息,较为全面地考察了敦煌歌辞《十二时》对后世“十二时”类的佛教歌辞、民间俗曲的影响。[34]崔怡的硕士论文《敦煌歌辞〈百岁篇〉〈十恩德〉写本研究》,通过写本细读,对《百岁篇》《十恩德》两首敦煌歌辞进行解读,最后由歌辞中所表达的慈母之恩、劝人行孝的思想扩展到对中国孝道思想发展变化以及民间佛教信仰的研究。[35]徐会贞的硕士论文《敦煌歌辞〈五更转〉写本研究》从写本文献出发考证其创作、抄写的时代及作者、使用者的身份等相关内容,再由歌辞《五更转》在后世的演变中考察敦煌佛教的世俗性、多样性、集体性的特点。[36]又如谭茹《写本情境下S.2682+P.3128综合研究》一文通过细读S.2682和P.3128两个写本,探讨了卷子所抄录的《大佛名忏悔文》及其背面依次抄写“曲子词15首”和《太子成道经》《不知名变文》《社斋文》,得出“S.2682+P.3128写本是敦煌某寺院僧人惠深为了满足日常唱诵练习及参加僧俗活动的需要所抄”[37]的结论,由此可窥探当时僧人的生活情状。从写本入,又从写本出,使研究更具高度,从而具有超越写本本身的意义。这是伏俊琏教授及其学生们的研究所呈现出的最大特色,也为敦煌歌辞的写本研究提供了向上一路。从中也不难看出近年来敦煌歌辞研究的思维理路发生了一定的转向,研究者逐渐将研究目光从曲子词转移至佛曲、俗曲上来,关注其写本信息、思想内涵、风格特征、表演传播等方面的内容,重新评估其学术价值,挖掘其历史和文学的意义。
五、结语
敦煌歌辞的研究工作开展至今已有一百余年,名家辈出,硕果累累。应当说,敦煌歌辞依然有十分宽阔的研究空间。如今的成果只是冰山一角,仍有无穷无尽的奥秘藏于水下,等待有心人去发现。21世纪以来,敦煌歌辞的研究者在继承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学习其研究思路与方法的基础上,顺应时代潮流,逐渐开拓研究视野,转变研究思维,改善研究方法,让敦煌歌辞的研究焕发出勃勃生机。对于敦煌歌辞的进一步研究,至少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展开:
其一,关注敦煌歌辞文本背后的艺术问题。任二北先生称敦煌歌辞是一种“音乐文艺”,也对此进行了较为系统地考察,但其部分结论仍有待商榷。张长彬《敦煌曲子艺伎形态初探》一文也指出敦煌歌辞“这一宗音乐文学作品的性质及构成远比人们预想的要复杂,需要我们从多角度尤其是从曲学的角度深入研究。”[38]因此,理清敦煌歌辞文本背后所涉及的各类曲艺形式,溯其源流,究其影响,仍是敦煌歌辞研究需要努力的一个方面。
其二,重视敦煌歌辞中的俗曲、佛曲。在之前的研究里,学者们多将视线投向敦煌歌辞中的曲子词部分并将其纳入词学研究中,忽视了占有较大比例的俗曲、佛曲。但俗曲、佛曲同样可以加以文学观照,而这其中所关乎的也不仅仅是文学问题,更有民俗学、宗教学、艺术学等学科的问题。对待同一研究对象,不同学科有不同的研究思维与方法,若能将其巧妙融合,则研究对象所蕴藏的丰富信息就会被一一揭露。
其三,深化写本研究。21世纪以来,写本研究逐渐成为敦煌文学研究的一种自觉。诚如伏俊琏教授所言:“对文学写本的研究,实际上也是对一个个文学个体的研究,对已逝去的文学生命个体的感悟。”[39]一些文化的、历史的、民俗的宝贵信息在呆板的刻本中荡然无存,却残留于写本之中等待挖掘。对于敦煌歌辞的写本研究,已有的成果仍需完善,大部分歌辞的创作时间、抄录时间、创作者、表演传播等问题仍有待考证。
总而言之,在敦煌歌辞的研究中,最为基础性的工作是文献整理,在此基础上所展开的语言文学研究、文化研究、写本研究等是辅助性研究,其研究核心应是理论性的探讨。因此,应将敦煌歌辞置于文学历史的长河中,考镜源流,探索早期词体文学的丰富姿态。